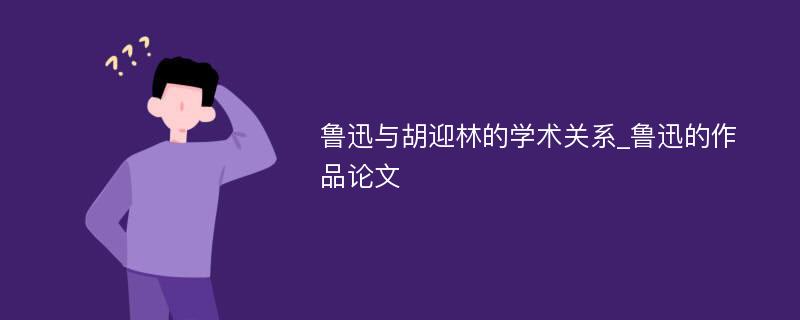
鲁迅与胡应麟的学术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学术论文,胡应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坊间已经出现了《〈中国小说史略〉批判》一书,不过只要还没有鲁迅所希望的“杰构”涌现,中国小说史研究恐怕依然如陈平原先生所断言:“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鲁迅时代’”,“不易超越”。①毫无疑问,“鲁迅时代”的终结,只能有待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创新和超越,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解读《中国小说史略》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如果从精神现象的发生角度考察,《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现,有两点已成定论:一、“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主专史。”文学史是舶来品,鲁迅从宏观到微观的直接借鉴,主要是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和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二、在需求接受方面,“文苑传”、“诗文评”的式微与文学史的勃兴,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选择。文学史著述“是伴随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②《中国小说史略》自身的产生过程,就是最好的例证。可是,如果把视角转向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结论就远远没有上述问题那样清晰。例如,《中国小说史略》对中国古代的小说研究成果和文学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其中的倾斜和侧重十分明显,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是如何对待金圣叹和胡应麟。然而,有关的研究以及鲁迅与金圣叹、胡应麟学术联系的研究一直尚欠深入。金圣叹是明清之际最负盛名也是最重要的小说戏曲理论家,其理论只是散见于对《水浒》、《西厢记》的评点中,却在人物论、创作论、鉴赏论等小说美学方面标志着中国小说美学理论的趋于成熟。当代有学者认为,从金圣叹开始我国才有了真正的小说批评。胡应麟的生活年代稍早于金圣叹,治学范围涉及文献学、目录学和辨伪学等诸多领域,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建树颇多,其小说理论堪称一座高峰。当代有学者认为,“他代表了明清两代小说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就是这样两位对古典小说研究施加了重要影响的学者,《中国小说史略》在借鉴方面的倾斜和侧重十分明显,即十分鲜明地选择了胡应麟。这其中固然有小说史研究同小说研究的区别上的原因,自然也有胡应麟学术成果自身的原因。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又字明瑞,号少室山人,后更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明万历四年(1576)举人,后屡试未第。在明嘉靖、万历间,胡应麟以藏书家、诗人、文学批评家、文献学家等诸多成就著称于世。他在兰溪山中筑藏书室“二酉山房”,藏书达四万两千余卷。他在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观点深受后七子特别是王世贞影响,因而被列为“末五子”之一。治学涉及文献学中之典藏学、目录学、辨伪学等领域。著述对后世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辨伪和小说研究两方面尤为显著,前者曾得到梁启超“辨伪大师”的称号,后者对后来的影响直至当代并有越发增强之势。胡应麟著有诗文集《少室山房集》(又称《少室山房类稿》)120卷,笔记《少室山房笔丛》48卷、诗论专著《诗薮》20卷。
鲁迅藏有胡应麟的所有现存著作。所藏《少室山房集》系番禺徐少棨汇编重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广雅书局本,1926年11月委托友人购于广州。《少室山房笔丛》和《诗薮》,见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二册,前者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广雅书局刻本,后者是民国十一年(1922)吴兴嘉业堂刻本。鲁迅对于胡应麟著作的收藏,从文本的关注和准备方面,证明了鲁迅对胡应麟的重视以及与他联系的可能性;有关方面的真正体现,还是蕴含于他的有关著述之中。
关于小说分类
在小说史研究中,鲁迅对胡应麟最重要的借鉴首推小说分类。
小说分类在小说研究中是一个前提性的课题,也是一个长期纠缠不清的复杂性课题。它的前提性体现在研究者对小说概念的理解和对小说范畴的界定;它的复杂性体现在历史上由于分类的变化导致了小说史研究的一系列变化。因此,小说分类在小说史研究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特点,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的高下由此奠定,凡进入这一领域者莫不倾力考察。
在胡应麟之前,历史上主要有两次小说分类。③第一次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杂述》对文言小说的分类: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日都邑簿。④
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认为小说与史书同属记事体,并将正史以外所有记事的作品都归入小说,从而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小说的范畴。但是,也正因为他以历史记事而非文学叙事作为分类标准,所收种类也就过于芜杂。第二次是元代初年的罗烨的分类,他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对话本小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除这八类,还有讲史一类⑤。这种分类法,主要侧重于题材的角度,纳入的小说更具小说特点。以上两次小说分类之后,最重要的小说分类非胡应麟莫属。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六类,每类又举重要作品为例: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容》、《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如举其重而已。⑥
胡应麟的小说分类,特点比较鲜明。首先,胡应麟的分类是从目录学入手的,因此尤其具有小说史的视角。胡应麟本是藏书大家、目录学家,他对所研究的内容进行文献梳理,并以宏观的发展眼光相驾驭本是应有之意。其次,胡应麟的分类主要偏重于内容上的考量,各类所举之例,既是联系具体作品的说明,也是这一思路的证明。
对于胡应麟的小说分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中完整引用,而且还用这一分类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加以比较。鲁迅这样做,其实与这一篇的全篇安排并不协调。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一篇,无论是标题《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还是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都对这一篇作了明确的界定,即鲁迅所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所包含的界定是:此篇的内容皆出自史家书目而已。这一点可以从多方面证实。在所涉及人物方面,这一篇中有班固、长孙无忌、魏征、曾公亮、欧阳修等著名史学家;在所涉著作方面,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著。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目录中,鲁迅在第一篇标题下的罗列是:
《汉书》《艺文志》说;《隋书》《经籍志》说。《唐书》《经籍志》始无小序;《新唐书》《艺文志》始退鬼神传入小说。明胡应麟分小说为六类;清《四库书目》分小说为三类。《四库书目》又退古史入小说。书目之变例。⑦
不难看出,《中国小说史略》能够将胡应麟及其《少室山房笔丛》收入其中,显然是一个特例。那么,鲁迅为什么非要如此呢?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优势之一就是文献学,其中包括了史籍目录学优势和小说资料学优势,这一知识和学术背景,决定了他必然像胡应麟一样选择从目录学切入,因此历代史著中的官修目录如《经籍志》、《艺文志》等自然成为考察的路径。但是,胡应麟的小说分类虽在官修目录之外,对于小说分类它实在太重要了,在这一课题中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鲁迅才不顾全局内在的“体例”而作了特殊处理。而这一点也恰恰凸显了胡应麟的小说分类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分量。
胡应麟的小说分类优点和缺点都明显而且突出。在缺点方面,一是由于缺乏统一标准而形成一二类类别的并存,二是缺乏理论性的说明。尽管如此,胡应麟的小说分类毕竟是小说分类历史上的高峰,不少优点至少在近代以前处于前沿位置,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鲁迅的小说分类。在胡应麟的小说分类中,前三类与现在所说的志怪、传奇和志人大体相同,已经包括了魏晋到唐代的主要小说类型。在这其中,胡应麟最大的贡献是把传奇小说单独分为一类,这一点在历史上有别于前后,堪称鹤立鸡群。胡应麟之前可以不论,就是胡应麟之后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持的小说观念反而大幅度倒退,依然不将传奇小说分作一类。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特设第八至第十一篇论述唐宋传奇,这几篇从分类到论述均被后代学人评为精彩篇章。如果追根寻源,传奇小说的分类并非鲁迅所独创,承袭的前人只有胡应麟一人。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现出的小说分类和小说类型设计,是这部著作取得的最高学术成就之一。一般认为,鲁迅的小说分类,对宋代以前较多地借鉴了前人,在此后则多数属于自己的创造。然而就思路而言,就很难作这种划分,即以鲁迅最具独创性的“谴责小说”的分类和命名而言,也很难排除前人的启发和影响。不过,只有到了鲁迅这里,才“第一次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部分类,把所有小说放在他的分类中来加以论述,从而为他的小说史的合理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⑧
关于小说观念
在鲁迅与胡应麟的学术联系中,小说观念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谈小说观念,首先涉及的是小说概念。在现代小说理论中,小说概念或称小说定义并不复杂。但是一旦进入中国小说史领域,小说概念就变得纷繁多变、众说纷纭。依据石昌渝先生《中国小说源流论》的梳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关小说的概念最大分歧,就是传统目录学家的小说概念与小说家的小说概念之别。石昌渝先生认为,“班固对于‘小说’的定义,成为了传统目录学的经典性概念。东汉以降,直到清代纪昀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尽管时代的发展,文学的样式和格局都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传统目录学却一直固守着班固的观念”。⑨石昌渝先生还认为,“‘小说’作为不同于传统目录学的概念,从现知的史料看,最早出现在宋元‘说话’门类中。”“到了明代,‘小说’的概念不但在‘说话’中由‘种’的位置上升到‘属’的位置,统摄了‘说铁骑儿’、‘说经’、‘讲史书’其他三家,而且由口头文学转为书面文学,具备了作为散文体叙事文学概念的内涵。”⑩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小说的起讫时间。传统目录学概念的小说,其发生发展贯穿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全过程;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是唐代以后才与前者并行发展的。更应该注意的是两种小说的根本区别,“分水岭就是实录还是虚构。说实话的(至少作者自认为)是传统目录学‘小说’,编假话的是作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11)石昌渝先生的梳理和论述,厘清了许多小说史著述中有关小说概念的各种纠缠,令人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感,同时他指出的唐代是散文体叙事小说的起点,也为鲁迅与胡应麟的学术联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上述两种小说概念和两种概念的小说是并存的,但在总体上是可以分辨的。例如,作为小说史家,鲁迅以他卓越的史识和非凡的艺术敏感,准确地发现并把握了小说在唐代的巨大变化,他指出: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中者(他书所收,时代及撰人多错误不足据),实唐代特绝之作也。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12)
这是最为小说史研究学者称道的一段论述,引用率极高。原因在于鲁迅用极其简明的语言,阐明了中国小说史上一次最为重要的转折,也是中国小说史上一种小说类型的重要开端:“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还进一步指出这一转折和开端最重要的特征是“意识之创造”,并且引用胡应麟的论述,指明这一重要发现和卓越的观点是借鉴了胡应麟的。完全可以说,这是胡应麟隐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重要的出场及最显著的身影。
鲁迅这里引用的胡应麟的论述,还是出自《少室山房笔丛》。论述旨在比较六朝小说与唐代小说的不同,关注点则在是否虚构。胡应麟以为六朝志怪小说并非没有虚构,而是没有完全的虚构,即所谓“传录舛讹”。意思是志怪小说的作者“访行事于故志”,记录下口头流传的异事,而人们口头流传的东西,由于口口相传,难免加入个人的臆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广生讹误,这其实是无意识的虚构。传奇小说的作者在记录时,也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想法,因此又会形成另一种虚构。这一创作过程,就是胡应麟所说的“未必尽设幻语”。唐代传奇小说在虚构方面则完全不同,传奇完全是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是作者自觉地将小说创作视为艺术实践和艺术创造。胡应麟的所谓“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即指此而言。据此可知,胡应麟是中国小说史上小说创作意识产生的最早的发现者;鲁迅是对这一多年埋没的观点的重新发现者,也是将这一观点运用于现代学术形式的植入者。
关于史料考证
在小说史料的考证方面,鲁迅曾几度援引胡应麟。
无论是对小说史料的钩稽,还是对小说史料的认识,胡应麟同样是一座高峰。他曾辑录《明世说》、《兜玄国志》、《酉阳续俎》、《隆万新闻》、《隆万杂闻》等多种小说杂记,只是后来全部散佚。他的《少室山房笔丛》收有《二酉缀遗》三卷,讨论的重点就是对小说史料进行考证辨别。对于小说史料的文献价值,胡应麟指出,小说“记述事迹,或通于史”,“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行纪》、《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刀,谗人之舌,此大弊也。然天下万世,公论其在,亦亡盖焉。”(13)这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前沿位置。鲁迅对于胡应麟在小说史料方面的造诣了如指掌,因而在工作中多有求助。
鲁迅最早从小说史料方面征引胡应麟著述是为了辑录《小说旧闻钞》。此书辑自《少室山房笔丛》的内容,集中在针对《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三部小说的考证,总计约1400字。其中就重要性而言,当属关于《大宋宣和遗事》的考证。鲁迅的辑录部分是:
(《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自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又郎瑛《类稿》记《点鬼簿》中亦具有诸人事迹,是元人钟继先所编。然则施氏此书所谓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独此外则附会耳。郎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尝戏谓是编《南华》《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则剧盗之靡耳。(施某事见田叔禾《西湖志余》。)(14)
胡应麟这里对《大宋宣和遗事》的考证,重点在于辨析源流和作者。胡应麟据《大宋宣和遗事》中与《水浒》中相近的人名和情节,断定《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宋江的部分系《水浒传》的雏形,现在这一观点业已成为治小说史学者的共识。
关于《大宋宣和遗事》,鲁迅还被牵入了一次争论,他因此又一次援引胡应麟。争论起自日本汉学家德富苏峰对鲁迅的批评。1926年11月德富苏峰撰文指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推断该书为元人所撰是错误的,该书应为宋椠。鲁迅撰文回应,逐一驳斥了德富苏峰的三个论据,并且也延及了《大宋宣和遗事》。鲁迅指出:
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15)
由此上溯到《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有关的论述是:
《大宋宣和遗事》世多以为宋人作,而文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则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类宋人者,则以钞撮旧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语也。书分前后二集,始于称述尧舜而终以高宗之定都临安,案年演述,体裁甚似讲史。惟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其剽取之书当有十种。(16)
以上梳理表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大宋宣和遗事》的论述,十分全面地借鉴了胡应麟。
鲁迅编校《唐宋传奇集》收入沈既济作《枕中记》,小说开篇写道:“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对于这一吕翁,后世多有歧义和争议,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对史料加以钩稽并作辨正:
明汤显祖又本《枕中记》以作《邯郸记》传奇,其事遂大显于世。原文吕翁无名,《邯郸记》实以吕洞宾,殊误。洞宾以开成年下第入山,在开元后,不应先已得神仙术,且称翁也。然宋时固已溷为一谈,吴曾《能改斋漫录》,赵与峕《宾退录》皆尝辨之。明胡应麟亦有考正,见《少室山房笔丛》中之《玉壶遐览》。(17)
在小说资料考证方面,鲁迅如此依重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绝非偶然。在诸多缘由之中,《少室山房笔丛》的内容和特点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少室山房笔丛》所收《二酉缀遗》三卷,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皆采摭小说家言”,其辑录和辑佚的小说资料及考证辨别,其专业性在古代学术笔记中鹤立鸡群。就全书而言,《少室山房笔丛》对治小说史的学者显然具有多方面的参照价值。对于该书,《四库全书总目》的概括是:“《经籍会通》四卷,皆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曰《史书占毕》六卷,皆论史事;曰《九流绪论》三卷,皆论子部诸家得失;曰《四部正讹》三卷,皆考证古来伪书;曰《三坟补遗》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以补三坟之缺;曰《二酉缀遗》三卷,皆采摭小说家言;曰《华阳博议》二卷,皆杂述古来博闻强记之事;曰《庄岳委谈》二卷,皆正俗说之附会;曰《玉壶遐览》四卷,皆论道书;曰《双树幻抄》三卷,皆论内典;曰《丹铅新录》八卷、曰《艺林学山》八卷,则专驳杨慎而作,其中征引典籍极为宏富,颇以辨博自矜,而舛讹处多不能免。”(18)这种极为简要的概括,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少室山房笔丛》与小说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在《少室山房笔丛》中,除《二酉缀遗》之外,《九流绪论》、《四部正讹》、《庄岳委谈》、《玉壶遐览》等部分,或提供了小说史料,或评论小说作品,或辨正前人旧说,都足资小说史学者参考。鲁迅的有关著述表明,鲁迅曾仔细研读过《少室山房笔丛》,对它在史料考证方面的征引只是鲁迅工作中浅层次内容,宏观的借鉴才是主要的。
关于辨伪
胡应麟在古代文献的辨伪方面,既考辨了经史子集七十多种典籍的真伪,又归纳了伪书的种类,提出了辨伪的方法。完全可以说,在辨伪领域胡应麟从具体操作到理论提升,都有力地推动了辨伪工作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梁启超因此对胡应麟有“辨伪大师”的评价,鲁迅在辨伪工作中对他也多有借重。
鲁迅援引胡应麟辨伪的例子,应首推认定是否《士不遇赋》系司马迁所作。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指出:
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吊屈原赋》及《服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司马相如传》上下篇,收赋尤多,为《子虚》(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自亦造赋,《汉志》云八篇,今仅传《士不遇赋》一篇,明胡应麟以为伪作。(19)
胡应麟对《士不遇赋》的考证,出自他的诗论专著《诗薮》。此书20卷,分为内编、外编、杂编和续编,杂编六卷是补遗和考证,前三编考证前代散佚的诗篇,胡应麟关于司马迁《士不遇赋》的考证即出自其中的《遗逸》卷。胡应麟认为,“董仲舒有《士不遇赋》,直致悁忿,殊不类江都平日语。且《汉志》无仲舒赋,伪无疑。太史亦有此赋,尤可笑。”(20)对于司马迁和董仲舒的同题二赋,胡应麟认为系“六朝浅陋者”的“赝作”。鲁迅在叙述胡应麟观点的同时并未表示个人观点,但他特别援引胡应麟观点的作法已很能说明问题。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引用胡应麟著作的拓展。本文上述内容,所涉及的胡应麟著作仅《少室山房笔丛》一种,这容易造成鲁迅并未读过胡应麟的其他著作的错觉。有关胡应麟对司马迁《士不遇赋》观点的引用证明,在胡应麟现存的《少室山房类稿》(又称《少室山房集》)、《少室山房笔丛》和《诗薮》中,除第一种属于创作类的诗文集外,鲁迅事实上读过胡应麟的所有评论著作。
在司马迁《士不遇赋》之外,鲁迅对所涉及胡应麟的其他辨伪并不尽信,并有所辨正,因而形成了与胡应麟超越时空的对话。
鲁迅曾辑有《任子》一卷并为其作序,在这篇《〈任子〉序》中,鲁迅对任子其人有所考证,其中涉及胡应麟的段落是:
奕书宋时已失,《志》云今有者,盖第据《意林》言之,隋唐志又未著录,故名氏转晦。胡元瑞疑即任嘏《道论》,徐象梅复以为临海任旭。今审诸书所引,有任嘏《道德论》,有《任子》,其为两书两人甚明。(21)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有一推断:“惟《任奕子》未得考。而道家有魏河东太守任嘏撰《道论》十二卷,或字之讹也。”而鲁迅据“诸书所引”,推翻了胡应麟的推断。
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鲁迅还就宋代传奇小说《赵飞燕别传》与胡应麟有一番“商榷”:
《赵飞燕别传》出前集卷七,亦见于原本《说郛》三十二,今参校录之。胡应麟(《笔丛》二十九)云:“戊辰之岁,余偶过燕中书肆,得残刻十数纸,题《赵飞燕别集》。阅之,乃知即《说郛》中陶氏删本。其文颇类东京,而末载梁武答昭仪化鼋事。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补缀以传者也。第端临《通考》渔仲《通志》并无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间叙才数事,多俊语,出伶玄右,而淳质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见也。”又特赏其“兰汤滟滟”等三语,以为“百世之下读之,犹勃然兴。”然今所见本皆作别传,不作集;《说郛》本亦无删节,但较《高议》少五十余字,则或写生所遗耳。《高议》中录秦醇作特多,此篇及《谭意歌传》外,尚有《骊山记》及《温泉记》。其文芜杂,亦间有俊语。倘精心作之,如此篇者,尚亦能为。元瑞虽精鉴,能作《四部正讹》,而时伤嗜奇,爱其动魂,使勃然兴,则辄冀其为真古书以增声价。犹今人闻伶玄《飞燕外传》及《汉杂事秘辛》为伪书,亦尚有怫然不悦者。(22)
关于《赵飞燕别传》的作者,鲁迅所见的《青琐高议》和《说郛》均署谯川秦醇子复撰。秦醇,字子复,北宋亳州谯人,传奇小说作者。《青琐高议》收入他的小说多篇,其中包括《赵飞燕别传》。《少室山房笔丛》中,胡应麟对《赵飞燕别传》的作者提出异议,认为“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复补缀以传者也。”胡应麟所以有此结论,一是由于《赵飞燕别传》前有一小序称,《别传》得自邻居李生家破筐中,虽编次脱落,尚可观览,于是乞其文以归,补正编次以成传。小序系以作者口吻,胡应麟误信了这个小序。二是《赵飞燕别传》最后有汉成帝为惩罚赵昭仪将其变为大鼋的描写,这个大鼋一直活到梁武帝时期,梁武帝认为这个大鼋即赵昭仪的后身。胡应麟据以上两点认为《赵飞燕别传》“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复补缀以传者”。鲁迅对此加以辨正。
胡应麟的辨伪工作,由于梁启超的“发现”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梁启超评价说:“专著一书去辨别一切书,有原理有方法的,胡应麟著《四部正讹》是第一次。”“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有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梁启超同时指出:“他所辨的书固然不多,他所辨别的真伪固然不能完全靠得住,但经史子集四部的书大都曾经他的研究而可供后人的参考。”(23)尽管梁启超对胡应麟的辨伪成果评价极高,但梁启超也以大师的敏锐眼光和科学态度发现胡应麟的不足和局限。纵观鲁迅与胡应麟辨伪方面的联系,应属同一性质。
如果把上述鲁迅与胡应麟的学术联系置于更加广阔的学术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鲁迅与胡应麟的“相遇”,不仅隐含着鲁迅极为深厚的文献学功力和卓越的学术眼光,其成果更具有学术上的历史性价值。这一学术背景是,从胡应麟的著作问世至20世纪初,胡应麟的学术成就长期被学界所忽视。对这一现象,最早编撰《胡应麟年谱》的吴晗曾指出:“似乎是胡氏的事迹,在校点本《四部正讹》未出世之前,还没有人注意过。有些攻驳他的就只攻击他的依附王世贞(《明史·文苑传》),又或如钱牧斋之专攻他的《诗薮》,沈德符和四库诸臣之吹毛求疵,检他不留心的偶误加以抨策;反之替他说好话的如朱彝尊之流,也只是空空洞洞地以‘读书种子’四字了之。至于他的事迹,则似从未有人加以注意,即有之亦荒谬不足据。”(24)吴晗的上述观点,是对胡应麟著作问世以来即陷于沉寂的四百余年学术现象的概括,文字出自1935年5月5日致胡适的书信。此前一年,吴晗编撰的《胡应麟年谱》在《清华学报》发表。年谱以坚实的史实对胡应麟的生平和学术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举大幅度提升了胡应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过,正如吴晗所说,在他之前的古史辨派的活跃期,《四部正讹》校点本的出版,已为吴晗的这一工作敲响了前奏。由此进一步上溯,1926年2月起,梁启超在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讲稿高度评价了胡应麟的辨伪成就。此举更被一些学者视为重新发现胡应麟的开端。而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初版的时间是1923年12月,据此并辅之以本文,胡应麟进入现代学术进程因鲁迅的工作而或可向前延伸。
注释:
①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2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
②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1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③方耀正:《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第14-21页,第85-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
④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
⑤罗烨:《舌耕叙引》,《醉翁谈录》第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
⑥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28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目录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⑧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第75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
⑨⑩(11)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9、7页,三联书店1994年2月。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1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26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
(14)鲁迅:《小说旧闻钞》,《鲁迅全集》第3卷第1819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11月。
(15)鲁迅:《关于〈三藏取经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17)鲁迅:《唐宋传奇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1881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11月。
(18)《少室山房笔丛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第1063页,中华书局1965年。
(19)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第4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20)胡应麟:《诗薮》第254页,中华书局1962年11月。
(21)鲁迅:《〈任子〉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22)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23)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梁启超全集》第17卷第502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
(24)《吴晗致胡适(1931年5月5日)》,《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第59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标签:鲁迅的作品论文; 诗薮论文; 鲁迅论文; 胡应麟论文; 中国小说史略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士不遇赋论文; 艺文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