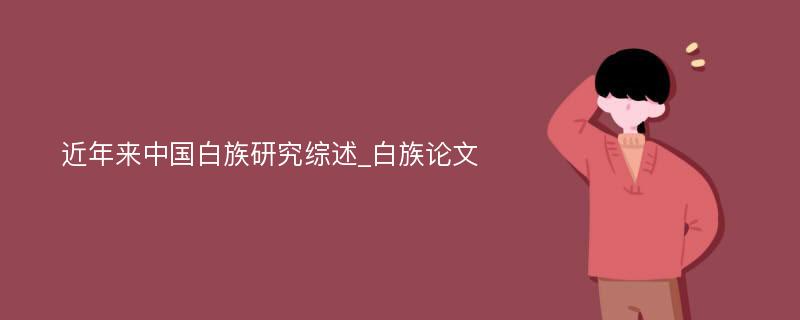
近年国内白族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族论文,近年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白族的研究,一直是西南民族研究中比较活跃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年发表和出版的论文、著作表明,白族研究继续向深广发展。对于某些问题的研究,在以前基础上又有所深入,而有些研究则填补了过去的空白,现将近年来几个方面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语言文字研究
白族的语言文字问题是白族研究中颇有争议的问题,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围绕着白语的系属问题、白族历史上有无自己的民族文字——白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关于白文,目前有两种意见。第一,学术界多倾向于白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白文。石钟健《大理明代墓碑的历史价值——(大理访碑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认为:在白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汉族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他们曾利用汉字写其语言,年深月久,因而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文字——“白文”,它是在白族吸收汉族文化达到相当熟练程度之后逐渐产生的。该文还根据碑铭和丽江《北岳卦》等“白文”资料,分别从其词汇和语法,来说明“白文”的特点。林超民《漫话白文》(《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认为:白文是白族用汉字作表意和记音的符号,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义,也就是用汉字来记录白族的语言。段伶《“白文”辨析》(《大理文化》1981年第5期),根据考古发掘出的白文文物认为:白文的使用由来已久。此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赵衍荪《关于白文及白文的研究》(《大理文化》1982年第1期)等论著,均认为有白文。第二种意见则认为白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张增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有字瓦——兼谈白族历史上有无“白文”的问题》(《文物》1986年第7期)一文,认为:在南诏时的文物资料中找不到“白文”。大理国遗留至今的文物中同样也无“白文”。而古代所说的“白文”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字,而是用汉字写白语(白族语言)的特殊形式。用汉字写白语的办法,最初可能只用在佛经的传授上,后来白族地区的民间唱本和记事书籍,甚至诗词上也采用过。此种形式,其流行时间大概从大理国晚期或元初开始,明代较盛行,清代就不用了。李绍尼《有关白族文字的几个问题》(《大理文化》1981年第4期)也认为:白族历史上没有文字。人们所说的“白文”只是极少数汉文水平较高的白族知识分子个人的记音工具,它在时间空间上,不能起到交际的功用。
关于白语的系属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周祜《从白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看汉白民族的融合》(《下关师专学报》1982年第一期)认为:白语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支,根据是白语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在现行白语中,从秦汉古音到近代的汉语词汇都有。到近代、现代,特别是当代,白语中的汉语词汇越来越多。除了白语的一些语法结构和一些古老的白语词汇,以及在历史上所吸收的附近兄弟民族如彝、纳西、藏等语言的词汇外,几乎都是汉语词汇了,该文还认为白族是没有系统的文字的。赵衍荪《白语系属问题》(《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认为:白语应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此外,徐琳、赵衍荪编著《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也认为:把白语归入汉藏语系缅语族彝语支是恰当的。第二种意见:杨品亮《关于白语系属的探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一文,认为白语和彝语不仅语音差异很大,而且词汇和语法也不具备同系属的特点。指出:第一,白语和汉语之间是同源异流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亲属语言。第二,当今的白语是在古楚语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自南诏与唐朝分庭对抗之后,先后六百多年时间内,白语和汉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自行发展,两种语言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白语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民族语言。根据白语的历史轨迹及现状,白语不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而应单立为白语支。李绍尼《白语基数词与汉语、藏缅语关系初探》(《中央民院学报》1992第1期)也认为:用彝语支属来概述白语,显然内容太窄。
二、哲学与宗教研究
关于白族哲学的研究,出版和发表新的著作和论文有:杨国才《略谈古代白族神话中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认为:白族神话是真实的历史和幻想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神话虽然并不就是历史,然而它却是原始人类生活的折射。白族先民利用神话这一幻想形式去认识自然、社会和把握世界,凭着原始的、朴素的世界观,白族先民把“云彩”、“水”看作是形成天地的始基,把“木十伟”看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原始物质,把人类的起源归结为某种自然物长期发展的产物。这种关于天地、万物、人类起源的观念,尽管是通过神话、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无疑是含有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龚友德《白族学者高奣映哲学思想初探》(《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认为:白族学者高奣映的思想,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有相近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是清初云南唯物主义者的一面旗帜”。主要表现在: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无神论观点、辨证法思想、历史发展观和带有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等等。龚友德还在(《民族工作》1983年第9、10、11期)对白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作了简介。并于199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族哲学思想史》专著。此外,还有杨国才、伍雄武主编《白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共收有关白族哲学思想史的论文十七篇。这些论文对白族的史诗、神话、宗教、哲学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跨度从古代白族先民哲学萌芽一直讲到近代赵式铭、王毓嵩等白族杰出人物的哲学观点。
关于白族宗教的研究,特别是对白族本主崇拜的研究,是近年白族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少专家就白族本主崇拜的性质、特征、思想、功能等方面展开了论述。主要论著有:杨仕《试论白族本主崇拜的性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在构成白族本主崇拜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中,属原始宗教基本特征范畴的因素占绝大多数,并起主导作用;而属人为宗教基本特征范畴的因素则相对要少得多,有的还仅只是萌芽或处于隐约状态,居于从属地位。白族本主崇拜的这种特性,无疑是一种处于由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转化,但转化还未基本完成的“过渡型”或“转化型”宗教。秋浦《关于白族本主崇拜的调查与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将白族本主崇拜归纳为以下特征:第一,凡是所崇拜的本主,人们都为之建立庙宇。第二,每一个本主庙内,在其正中位置,都有泥塑或木雕的本主偶像,接受人们朝拜。第三,凡是本主,都有他的传说。第四,每一个本主都有自己的节日。第五,人们祭祀本主所用供品,大都有一定的规格。第六,本主有男有女,地位完全平等。李学龙《白族本主崇拜社会功能试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认为:白族本主崇拜的社会功能主要有:凝聚功能、教育功能、参与功能、娱乐功能、精神调节功能等。此外,论述白族宗教的论著还有:李东红《白族本主崇拜思想刍议》(《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宋恩常《白族本主崇拜刍议》(《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杨政业《白族本主信仰概貌》(《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试述本主信仰对白族民族意识的凝聚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赵演松《试论白族本主的源和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詹承绪《试议将白族的本主崇拜定为民族宗教》(《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史继忠《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大理市文化局编《白族本主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李东红《大理地区男性观音造像的演变——兼论佛教密宗的白族化过程》(《思想战线》1992年第6期)、杨宪典《大理白族原始宗教——巫教调查研究》(《云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龚友德《白族的火崇拜》(《大理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刘龙初《白族的祭天仪式》(《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等等。
三、文化及婚姻家庭研究
关于白族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李缵绪著《白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白族文化主要由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口录文化和文人文化组成。其发展历史,大抵经历了原始文化、滇文化、爨文化、南诏文化、大理文化、元明清文化等几个阶段。其发展过程,在继承了固有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内,吸收了大量的仰韶文化和楚蜀文化;对外,吸收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的古文化,形成了白族源远流长、色彩斑斓的文化。服饰文化:尹素卿《白族服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指出:白族服装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男子服装一般与汉族基本相同。青年人喜欢穿白颜色对襟上衣,外穿黑色领挂,蓝色裤子,腰系拖须裤带,惯背一个艳丽夺目的绣花背袋,缠白色或蓝色的包头巾。碧江一带的白族男子,在衣服外边再加一件麻布坎肩,衣长过膝。乐夫《略谈白族服饰》(《民族文化》1984年第2期)则从白族的帽子和围腰、鞋子和袜子各种绣花饰物、各种首饰等方面,论述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区的白族在服饰上具有不同的特色。有关白族服饰的论文还有:章虹宇《鹤庆白族妇女服饰》(《大理文化》1983年第6期),王元辅《滇人和白族的发式服饰比较研究》(《大理文化》1985年第6期)。茶文化:苏松林《白族“三道茶”文化特征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第一,三道茶是白族文化的结晶。第二,三道茶体现了白族人生的哲理,即一苦二甜三回味,象征人生三部曲、事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三,三道茶体现的白族文化特征,即白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兼收并蓄这一特点。第四,三道茶文艺晚会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菡芳《白族三道茶》(《民族文化》1985年第2期)一文,则介绍了白族“三道茶”的民间传说、配制方法、上茶仪式等。指出“三道茶”寄寓着白族人民生活的哲理,同时也是三副预防疾病的好药。仙竹《白族特殊礼——三道茶》(《民族团结》1984年第11期)一文,也简要地介绍了“三道茶”的礼节和配制方法。居住文化:高登荣《试析白族的居住文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认为:白族民居既是白族文化的产物,也是汉、白文化交流的产物。白族所接受的儒家的社会等级观念、伦理道德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中庸之道等,都在白族民居中得到无言的体现。云南省设计院编《云南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则从自然与社会概况、民居建筑、实例等方面,用图文对白族民居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仅房屋建筑的内容就有:院落布置、基本单体、平面类型、剖面、及梁柱构架、防震措施、外观与装修等六个方面。此外还有:吕二荣《白族民居建筑初探》(《大理文化》1985年第6期)、李森《白族民居建筑的艺术》(《大理文化》1983年第6期)等文。关于白族“绕三灵”的研究,有以下不同意见:范玉梅《我国少数民族的节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认为:白族的“绕三灵会”,流行于大理一带,每年春末举行。节日这天人们身着盛装,边唱边舞,绕洱海一周,主要目的是为了祈求吉祥与丰收。清华《“绕三灵”并非绕洱海》(《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则对范玉梅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参加“绕三灵”节日活动的人们,要边唱边舞地“绕洱海一周”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主要根据是,第一,洱海之大,要边唱边舞地绕洱海一周,决非两、三天内所能做到的。第二,洱海东岸海东至挖色段有一长约10公里的悬岩陡壁,人不能通过。第三,所绕的“三灵”崇圣寺、圣源寺、金圭寺均在洱海西岸,无需绕洱海一周,故“绕三灵”并非绕洱海。程叙《对白族“绕三灵”的几点补正》(《民族研究》1989年第6期)则又指出:“清华对绕三灵活动行进路线等的说明,仍有不确之处。认为,第一,群众边歌边舞行进的路线并不经过金圭寺。第二,参加节日活动的大多数群众,也不经过佛都——崇圣寺。第三,仙都不应是金圭寺,而应是河矣城村的洱河祠。有关白族文化研究的论文还有:李正清《白族“火把节”探源》(《昭通师专学报》1987年2—3期)、李东红《白族火葬墓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91年第6期)、宋文熙等《略论明清白族学者对云南文献的贡献》(《昆明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董建中《白族“绕山林”起源的内涵及其变异》(《民族学与现代化》1986年第4期)、李东红《白族文化史上的“释儒”》(《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等文。
关于婚姻家庭研究。杨国才著《情系苍山、魂泊洱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版),该书是首次系统介绍了白族妇女的恋爱、婚礼、家庭及生产,生活和她们独特手工艺术等内容。张禄《试论白族婚姻制度的演变》(《下关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认为:由于居住地的自然、交通等环境条件的不同,出现了多种社会形态。因为这种复杂的条件,使得白族在婚姻制度上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白族的婚姻制度也沿着血缘婚——普那路亚婚(群婚)——对偶婚——一夫一妻婚的顺序发展演变的。徐琳《白族》(严汝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认为:白族的婚姻主要包括:择配与通婚范围、说媒与会亲、婚礼、妇婴保健和有关民俗等内容。家庭是由父母、子女、儿媳或赘婿所组成。颜智强《白族的“入赘”》(《云南日报》1982年3月14日第4版)认为:“入赘”是白族青年男女通婚的一种形式,在白族地区特别是洱源、剑川等县常见不鲜。研究白族婚姻家庭的著作还有:《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杨知勇等编《云南少数民族婚俗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
四、文学艺术研究
1、近年来对于白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专著有:张文勋主编《白族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主要内容有:白族古老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长诗及大本曲、吹吹腔等传统曲目。该书还将白族文学分为南诏以前的白族文学(公元748年以前),南诏及大理国时代的白族文学(公元748-1253),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白族文学(公元1254-1949年),解放后的白族文学(公元1949-1981年)等四个时期。李缵绪著《白族文学史略》(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主要内容有:白族远古时期的“打歌”和原始神话,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龙神话、“本主”神话、密教神话,民族风俗和地方风物传说、民间戏曲、文学,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白族民间诗歌、历史传说故事、机智人物故事、妖怪故事、寓言和笑话、作家文学以及建国以来白族文学概述等。杨亮才等选编《白族民间叙事诗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收入白族民间叙事诗八篇。《望夫云长诗集锦》(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81年版)收入了五十年代发表的五部“望夫云”长诗。扬宪典等编选《白族民间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收入230篇白族民间故事。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共收入74篇白族神话。有关白族民间文学的论著还有:《白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段赤城(童话叙事长诗)》(云南人民出版1980年版)、张长著《凤尾竹的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赵橹著《论白族神话与密教》(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杨秉礼《白族(创世纪)源流初探》(《思想战线》1984年第2期)等等。除了以上论著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著作收入白族的谚语、诗歌、童话、神话、情歌、传说故事等等,此不赘述。
2、关于白族艺术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伍国栋主编《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一部全面反映白族音乐的志书,全书共分五大类。第一类,综述,内容包括从古至今各个时代白族的音乐文化。第二类,图表。主要有白族的民歌、歌舞、曲艺、戏曲音乐、主要乐器等分布示意图;以及民歌、歌舞、曲艺、戏曲音乐、乐器、乐种等简表。第三类,志略。内容分为:民歌、歌舞音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乐器及乐种、曲目、唱段、音乐社团、音乐著述、音乐传说、轶闻、术语、谚语、口诀、楹联、音乐史料、音乐文物等方面。第四类,传记。有杨黼传、杨汉传、张明德传、李明璋传、杨杰传。第五类,主要是参考书目和英文目录。此外,还有大理白族自治洲文化局编《云南白族民歌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五、南诏和大理的研究
关于南诏、大理的研究,是近年白族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围绕着南诏、大理的族属、文化、婚姻、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学术界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有的同志已对1990年以前南诏、大理的研究作了综述。因此,本文仅介绍此问题1990年后的研究情况。马曜《大理文化的源和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1、2期)认为:大理文明是洱海周围土著民族文化向东发展和中原汉文化向西传播互相撞击融合的产物。第一回合是从商末的海门口到西汉的石寨山,形成云南土著文化的极盛时期。第二回合是东汉以后汉文化大量东来,形成南北朝时期的西爨白蛮文化。第三回合是云南文化中心逐渐西移,复归于洱海地区,汇合成唐、宋时期大放异彩的南诏和大理文化。上述几种文化的最早创造者,主要是司马迁所说的“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土著居民,他们与蜀汉时期的“下方夷”和隋唐时期的“西爨白蛮”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管彦波《试论南诏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格局》(《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认为:南诏文化是西北秦陇地区的氏羌文化、湘沅地区的楚文化、云南古代滇文化、爨文化的基础上,以一种开放性的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大力汲取、借鉴唐文化以及周边的吐蕃文化、印度文化的基础上,逐渐积淀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地方性,阶级性和区域性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下的一个子文化。它涵盖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它在文化的特质、构建及渊源上,亦呈现出多源与多元的特性。此观点的作者在《南诏文化积淀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拟唐试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也有详述。此外,认为南诏文化是多源与多元观点的还有:禺弛《南诏文化的特征》(《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认为:仿唐性、开放性和多元与多源性是南诏文化的主要特征。傅光宇《略论南诏文学的文化环境》(《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认为南诏文化是以彝族与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多部族、多部落文化,因而是不同质的多元组合的文化。管彦波《试论南诏的军事制度》(《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一文,对南诏的军事制度及其文化研究后认为:南诏的军事制度是比较完善的。其间,已经形成了大军将、军将、兵曹长、各府正副主将组成的“递相管辖”有明显级差的军事建制,其军制既仿周又拟唐,无论是训练、布阵还是晋升、赏罚都有了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军事上采取了“府兵制”与“民军制”相结合的特点,也说明了强大的军事机器是南诏赖以生存的支柱。苏建灵等《论南诏、大理国的建筑》(《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认为:南诏、大理国的建筑与今天白族、彝族、哈尼族建筑关系密切,一脉相承,说明这些建筑是这几个民族建造的,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南诏、大理国是这几个民族而不是泰族或傣族建立的。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一文,在驳斥了从百余年前起,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南诏国是泰人建立的说法这种观点后,明确指出,公元7-9世纪存在于中国西南部以云南洱海和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国,是中国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因此南诏国所在的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赵鸿昌《唐代南诏城镇散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南诏城镇的发展既与其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同步,反过来,城镇又支撑和强固着南诏政权;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域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个大的区域,主要具有政治军事功能,“择胜置城”是南诏城镇地理位置选择的思想出发点,并合理利用地形,加入若干地方民族特色。王丽珠《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南诏时期大理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人口较多的白、彝族相互间的关系和以他们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此外,论及南诏大理的论文还有:韩军《论南诏为乌蛮蒙氏与白蛮豪族共同建立的政权)、张金鹏《南诏时期佛教传播中的变异现象及原因探索》、王宏道《(蛮书)所载“承”上一辞含义的推测——兼论南诏前洱海地区地方政权的建立》、林超民《大理高氏考略》、徐兴祥《骠国与南诏的关系》,以上论文分别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1993年2、3、4期);张锡禄《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论》、管彦波《南诏商业交换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1991年第5期)、苏建灵《南诏王异牟寻与贞元年间的南诏、唐朝和盟》(《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等。
关于白族的族属问题,见拙作《近十余年云南少数民族族源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5期)、《近十余年僰人族属研究综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除了以上本文所涉及的论著外,近年还出版了一批有关白族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以及全国或省级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史专著中不少涉及白族社会、历史、科技方面的内容。这些著作,篇幅甚钜,而本文篇幅所限,不得不割爱于此文之外,敬请作者及读者谅之。
标签:白族论文; 白族三道茶论文; 白族建筑论文; 云南大理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云南发展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思想战线论文; 白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