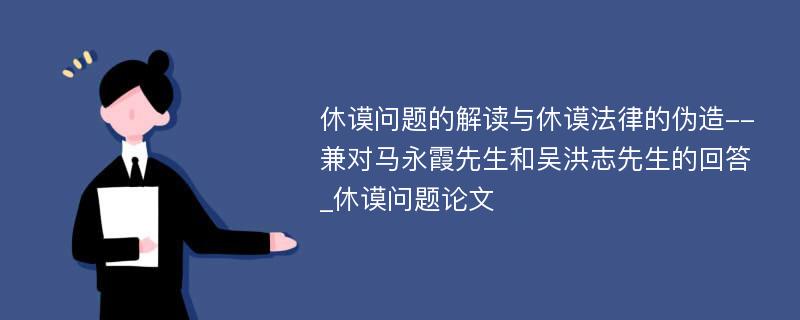
休谟问题的解读与休谟法则的证伪——兼答马永侠、武宏志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休谟论文,法则论文,武宏志论文,兼答马永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永侠和武宏志先生在《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载《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以下简称“商榷文”)中,对拙文《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上)——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质疑》和《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质疑》(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10、11期)提出了异议。分歧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1)休谟问题如何解读?(2)休谟法则能否证伪?对“商榷文”的看法我不敢苟同,下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再探讨,兼答马、武二先生,并就教于读者。
一、休谟问题如何解读
从“是”能否推出“应该”的问题,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可简称为休谟问题。休谟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那么休谟的原意是什么,对休谟问题应该如何解读?拙文认为,休谟问题包含两个相关的预设,首先是预设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即:不可能从“是”推出“应该”。拙文写道:“英国著名哲学家黑尔(R.M.Hare)则把这个否定答案称为‘休谟法则’。应该说,休谟法则是对休谟问题的正确解读,与休谟原意是没有实质性差别的。”(注: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上)——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第19页。)不过,黑尔赞同休谟法则,拙文则质疑这个“法则”。其次是预设了事实与价值二元论。拙文写道:“从逻辑的观点看,休谟法则依赖于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这个预设也就是休谟法则基本的哲学根据。休谟说‘是’与‘应该’所表示的关系‘完全不同’,就是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一个暗示,但休谟没有把这个观念明确展开。从历史的观点的看,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乃是休谟问题引发的结果,是休谟法则的深化和扩展,在20世纪才成为风靡一时的哲学思潮。”(注: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上)——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第20页。)
“商榷文”对休谟问题作了不同的解读,其一是断言:“休谟只是要求对从‘是’到‘应该’的推论作出其合理性的说明。他并没有断定这种推论是无效的……明确认定从‘是’到‘应该’的推论无效的人是摩尔,他将此推论概括为‘自然主义谬误’。”(注:马永侠、武宏志:《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59页。)其二是断言:“休谟问题预设的是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而不是二者绝对区分的二元论。”(注:马永侠、武宏志:《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59页。)因此,作者认为,我对休谟问题的预设的批判“犯了‘稻草人’谬误”。(注:马永侠、武宏志:《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59页。)
那么,究竟哪一种解读属于“谬误”?只有将休谟问题置于休谟的道德学体系及其哲学背景中加以考察,才能判定。而判定的关键在于休谟问题是否预设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从逻辑的观点看,休谟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3种可能的思想状态:(1)没有预设任何答案,就是说,连休谟自己也心无定见。(2)预设了肯定的答案,即:从“是”可能推出“应该”。(3)预设了否定的答案,即:从“是”不可能推出“应该”。按照二位先生的解读,休谟的思想状态非(1)即(2),但二者均与休谟的道德学体系相矛盾,惟有(3)才与休谟的道德学体系相吻合。这有两个主要的证据:
其一,休谟的道德学的出发点是情感主义,其正面论题是“道德的区别是由道德感得来的”,(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10页。)其反面论题是“道德的区别不是从理性得来的”,(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95页。)有关后者的一个主要论证是:“道德准则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理性自身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无力的,因此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97页。)由此看来,休谟对于休谟问题不可能抱有肯定的答案,因为主张从“是”可以推出“应该”,就等于主张道德规则可以是“理性的结论”,未必就是情感的结晶,而与他的论题和论据相矛盾。
其二,休谟提出了从“是”能否推出“应该”的问题之后,郑重其事地建议读者“留神”他的问题,说:“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10页。)当时道德学体系的主流是理性主义,其渊源可追溯于苏格拉底的名言“美德即知识”,在17-18世纪则充分地表现在斯宾诺莎和洛克的伦理学说之中,斯宾诺莎试图用几何学的方法证明道德原理,洛克则断言“道德的知识和数学是一样可以有实在的准确性的”。(注: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57页。)在理性主义的道德学中,从“是”推出“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休谟意欲“推翻”的所谓“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就是指理性主义的道德学。他批评道:“某些哲学家们曾经勤勤恳恳地传播一个意见说,道德是可以理证的;虽然不曾有任何人在那些证明方面前进一步,可是他们却假设这门科学可以与几何学或代数学达到同样的确实性。”(注: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03页。)矛头似乎就是指向斯宾诺莎和洛克的。从休谟的“推翻”理性主义道德学的抱负和自信看来,他对从“是”能否推出“应该”的问题必定预设了否定的答案,否则,如果他心无定见,或者预设了肯定的答案,那么他的道德学与理性主义的道德学就是相容的,又何足以言“推翻”呢?
由于休谟的答案隐藏于“问题”的黑箱,关于休谟的原意自然是有文章可做的。奇怪的是二位先生在《论“自然主义谬误”》中解读休谟问题时,看法却与“商榷文”的断言相反,即确认“反对从‘是’推出‘应当’”是休谟的主张。该文一则说:“摩尔……反对从‘是’推出‘应当’。就逻辑层面来说,摩尔……与休谟如出一辙。”(注:武宏志、马永侠:《论‘自然主义谬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28页。)二则说:“逻辑学家以及谬误研究者根据摩尔与休谟解释的一致性,把休谟指出的‘是——应该’谬误叫做‘自然主义谬误’,并且把主张‘自然主义谬误’的确是一种谬误的观点叫做‘休谟定律’。”(注:武宏志、马永侠:《论‘自然主义谬误’》,《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29页。)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在“商榷文”中作了180度的理论转向呢?先生们并没有透露任何理由,虽然人们有权改变自己的看法,但应该亮出理由,否则,无原则的理论反复也不免令人怀疑其出于人云亦云。我相信先生们从前的立论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还是应该返回原来的立场,把“休谟定律”即“休谟法则”(Hume's Law)还给休谟。
还应该指出,先生们在两篇论文中都把“休谟法则”与“自然主义谬误(说)”等同起来,当作一回事,这是不妥当的,它们之间有联系,也有差别。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说与“善不可定义”论互为表里,它蕴涵休谟法则,但反之不然。“自然主义谬误”说可以把一切试图给“善”下定义的伦理学者一网打尽,连休谟也难逃法网,1988年版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有云:“休谟本人对道德的阐释也会被摩尔列入自然主义谬误之列,因为休谟试图用旁观者的思想感情来限定德性”。(注:艾伦·格沃斯等:《伦理学要义》,戴杨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将休谟法则推到极端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就质疑:“自然主义的错误果真是错误吗?”(注: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1页。)并尖锐地指出:“就摩尔关于定义的一般论证而言,他的自然主义谬误说乃是混乱不堪的”。(注: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现在就不难澄清有关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问题。事实与价值二元论是一种把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加以绝对化而否认它们有任何逻辑关联的理论,它是休谟法则逻辑地依赖的前提。从休谟的《人性论》看来,他之所以反对从“是”推出“应该”,是因为认定“是”与“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根据,即“是”或事实命题来自理性,“应该”或道德命题决定于情感,“并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这是一种情感主义道德观,与作为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现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应该说明,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对《人性论》中的情感主义道德观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承认在那些要顾及效用和后果的道德决定中,“理性必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注: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7页。)尽管仍然坚持“道德性是由情感所规定的”。(注: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1页。)可以说,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至少是休谟的《人性论》中一个潜伏的观念,尽管他没有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和充分地展开,其后又使之弱化,但决不是谁编造的“稻草人”。至于事实与价值有区别的观点,那不是从“是”推不出“应该”的充足理由,二者的相对区别是休谟法则的质疑者也可以接受的。拙文在批判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时候,就从未如先生们所谓“否认事实与价值是有区别的”。
二、休谟法则的证伪何以可能
休谟法则能否证伪的问题,就是从“是”能否推出“应该”的问题,拙文的回答是肯定的,“商榷文”的回答是否定的。作者断言:“在演绎逻辑的范围内,‘自然主义谬误’是不可反驳的。”(注:马永侠、武宏志:《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59页。)这就是说,休谟法则是不可证伪的。不过,“商榷文”除了“引证权威”(满纸是‘阿佩尔的分析表明”,“诺顿斯坦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彼彻姆指出”,弗兰克纳“认为”,瓦尔顿“提出”……(注:马永侠、武宏志:《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60-62页。))之外,并没有给休谟法则不可证伪的观点提出新的证明,对拙文的反驳也陷入混乱和矛盾。下文主要从逻辑学的角度探讨休谟法则的证伪何以可能的问题,并澄清“商榷文”所引起的混淆和误解。
(一)证伪的逻辑
证伪是检验假说的科学方法,凡假说都是全称命题,从逻辑的观点看,证伪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反驳,即用某些已经被事实证实的单称命题,来反驳某一个全称命题。全称命题不可能被单称命题证实,但可能被单称命题证伪,这就是波普尔之所谓“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的不对称性”。(注: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编译,三联书店,1992年,笫28-29页。)他写道:“这种不对称性来源于全称陈述的逻辑形式。因为这些全称陈述决不能从单称陈述中推导出来,但能够被单称陈述反驳。因此,用纯演绎推理……从单称陈述之真论证全称陈述之假是可能的。”(注: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编译,三联书店,1992年,笫29页。)如果某个单称命题可以证伪某个全称命题,那么可以证实这个单称命题的某一个别的事实或有关的经验,就称为“反例”,反例就是证伪的逻辑基础。
拙文认为,休谟法则也是一种假说,即关于道德推理的经验性假说,(注: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第20页。)但是,在涉及社会事实的道德推理中存在着休谟法则的反例(见下文),所以,提出了“休谟法则可以用经验证伪”(注: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第20页。)的论题。拙文写道:“休谟法则等值于这样一个全称命题:任何从一组全部为‘是’命题的前提中推出‘应该’命题作为结论的推理都是无效的。显然,只要找到至少一个反例,我们就证伪了休谟法则,而证实了它的矛盾论题,即:从‘是’推出‘应该’是可能的(这是一个可能命题,相当于一个存在命题即特称命题)。这种反例有的是!”(注: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第20页。)为了行文方便,不妨把引文中一个等值于休谟法则的全称肯定命题换质为全称否定命题,并简化为:“所有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都不是有效的”,其形式为“所有S都不是P”。拙文证伪的思路是这样的:(1)以举出休谟法则的反例为逻辑起点。一个休谟法则的反例,是指一个从“是”推出“应该”的有效推理。它就是论题之所谓“经验”。(2)用一个休谟法则的反例证实一个这样的单称肯定命题:“这个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是有效的”,其形式为“这个S是P”。(3)根据“这个S是P”与“所有S都不是P”的反对关系,由“这个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是有效的”为真,推出“所有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都不是有效的”即休谟法则为假。值得注意的是,证伪休谟法则与证实与它有矛盾关系的特称肯定命题,即“有的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是有效的”(等值于一个可能命题:“从‘是’推出‘应该’是可能的”,即“从‘是’可能推出‘应该’”),是一回事;但是,证伪休谟法则与证实与它有反对关系的全称肯定命题,即“所有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都是有效的”,却不是一回事,因为从一个表述休谟法则的全称否定命题为假,推不出相反的全称肯定命题为真。这个全称肯定命题是一个不可能用休谟法则的反例或单称命题来证实的命题,它不是拙文的论题。拙文的论题与“有的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不是有效的”这个特称否定命题也不矛盾,所以,无论举出多少从“是”推不出“应该”的例子,都否定不了拙文的论题。
“商榷文”在反驳拙文的论题时,写道:“用有时或有些情形下从‘是’能推出‘应该’,并不能表明从‘是’推论‘应该’就是有效的……一个例子就可证明从‘是’到‘应该’的推论是无效的,即谬误;但举很多很多的例子也不能证明这样的推论是有效的”。(注:马永侠、武宏志:《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60页。)这个反驳完全是出于混淆和误解,症结在于不了解证伪的逻辑,把证伪与证实混为一谈,把拙文对休谟法则即全称否定命题“所有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都不是有效的”的证伪,当作对休谟法则的反对命题即全称肯定命题“所有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都是有效的”(“商榷文”表述为“从‘是’推论‘应该’就是有效的”)的证实,以为拙文用“有时或有些情形下从‘是’能推出‘应该”,就是为了证实这个全称肯定命题。我相信,哪怕是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也不至于愚蠢到妄图证实这个可以轻易地被常识证伪的命题。先生们的反驳就是以这个“稻草人”为“假想敌”的。
我还要反问:如果通过“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可以证实“有时或有些情形下从‘是’能推出‘应该’”这样一个特称肯定命题(等值于“有的从‘是’推出‘应该’的推理是有效的”),那么能否证伪它的矛盾命题即休谟法则呢?若说“不能”,岂不是违反矛盾律?若说“能”,岂不是自相矛盾?
“商榷文”不免陷入矛盾的困境。作者写道:“如果自然主义谬误是断定:从‘是’命题推出‘应该’命题都是错误的,则自然主义谬误的含义作为一个全称命题是容易遭到反驳的;但若自然主义谬误说的是,从一组全部为‘是’命题的前提推出‘应该’命题作为结论的推论都是无效的,要反驳这一断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引者按:引文中的“‘是’命题”原文作“‘是’的命题”,不通,引文删去“的”字)(注:马永侠、武宏志:《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60页。)这个看法是十分奇怪的。(1)“从‘是’命题推出‘应该’命题都是错误的”与(2)“从一组全部为‘是’命题的前提推出‘应该’命题作为结论的推论都是无效的”之间在逻辑上没有任何区别,二者都是与休谟法则或“商榷文”所谓“自然主义谬误(说)”等值的命题,(1)不过是(2)的简化。承认(1)“作为一个全称命题是容易遭到反驳的”,却坚持(2)是不可反驳的或者休谟法则是不可证伪的,那就是自相矛盾。
可见,“商榷文”对拙文的反驳在逻辑上是混乱不堪的。(注:“商榷文”有些话简直不知所云。例如:“显然,不难找到这一形式的反例,因此,它的无效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要证明它是一个有效式却困难百倍。”(见《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60页)按文意,“这一形式的反例”当指休谟法则的反例。“它”又何所指?指“这一形式”即休谟法则,还是休谟法则的反例?无论采取哪一个意义,说“它的无效性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是与作者维护休谟法则的立场相矛盾,就是与休谟法则的反例的定义(“一个休谟法则的反例,是指一个从“是”推出“应该”的有效推理”)相矛盾。说“要证明它是一个有效式却困难百倍”,也令人莫名其妙。)
(二)从“是”推出“应该”的逻辑根据
从“是”推出“应该”何以可能?拙文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时,举出了两个休谟法则的反例(以下简称“反例”):“张三是法官,所以,张三应该依法审案”;(注: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第21页。)“她是妓女,所以,她不是良家妇女”。(注: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第22页。)前一个从事实命题推出规范命题,后一个从事实命题推出评价命题,其共同点是:作为前提的事实命题所描述的都是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事实。我意在借此说明,承认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事实的特殊性,即社会事实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价值,这是从“是”推出“应该”之所以可能的哲学根据;存在着反映社会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分析命题或语义公理,这是从“是”推出“应该”之所以可能的逻辑根据。下面将选择从事实命题推出规范命题的逻辑根据问题,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对象。
让我们从下述一个更明显的反例入手:
(1)甲是反贪污官员,所以,甲应该反贪污
这是一个从事实命题推出规范命题的有效的直接推理,其逻辑根据在于与这个推理严格对应的蕴涵命题(假言命题),即
(2)如果甲是反贪污官员,那么甲应该反贪污
是一个分析命题。(2)又是下述一个概括性的分析命题
(3)对所有x而言,如果x是反贪污官员,那么x应该反贪污
的一个代换例。(3)是一个全称量化的蕴涵命题,等值于下述一个全称肯定命题:
(4)所有反贪污官员都应该反贪污(注:按照传统逻辑,在全称肯定命题“所有S都是P”中,主项S具有存在含义,本文按照现代逻辑对全称肯定命题的解释,取消S的存在预设,即允许S为空类,所以,命题(3)和(4)有等值关系。)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1)的有效性的逻辑根据归结为:因为(4)是一个分析命题。
为什么说(4)是分析命题?我们可以通过对(4)的主谓项的语义分析回答这个问题。在(4)中,主项“反贪污官员”是一个表示地位的概念,地位是指人在社会中占有的身份或职位;谓项“反贪污”是一个表示角色的概念,角色是指与一定的地位相关的行为规范,主要是权利(用“允许”表示)和义务(用“应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地位和角色两个概念都具有双重语义,就是描述性内涵和规范性内涵。地位主要是一个描述事实的概念,每一个这样的概念都描述了一个由地位占有者所组成的群体;同时,也含蓄着所描述的群体得以成立的行为规范(失去必要的行为规范,群体就不再存在)。角色主要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但又包含对人们的行为模式的描述。在(4)中,“反贪污官员”是一个关键词,可以分析为两个概念,即“官员”和“反贪污”,“x是反贪污官员”等于说“x是官员并且x是反贪污的”。其中“反贪污”表示“官员”的职责。职责有两个意义:一是职权,属权利范畴;一是责任,属义务范畴。依此,“反贪污官员”的定义可以表示如下:
(5)x是反贪污官员,当且仅当x是官员,并且x有反贪污的权利,并且x有反贪污的义务
这就是说,“反贪污”是主项“反贪污官员”所包含的一个义务条件,而谓项“反贪污”则与这个义务条件同义。可见,在(4)中,谓项只是把主项的内涵中关于职责的某些规定分析出来归于主项,所以说,它是一个分析命题。由于(4)属于规范命题,它就是规范世界中的分析命题。分析命题是必然的真命题,相对于“反贪污官员”的定义在其中成立的一切可能的规范世界而言,(4)都是真的,就算在一个以贪污为美德的可能的规范世界中,除非这个地位概念不成立,(4)也是真的。
分析命题可以通过对某些概念作定义替换(即以定义项取代被定义项,或者相反)化归为逻辑真理。根据定义(5),把(3)中的“x是反贪污官员”换为“x是官员,并且x有反贪污的权利,并且x有反贪污的义务”,同时以规范词“允许”和“应该”分别表示“有……权利”和“有……义务”,从(3)可以得出下述一个等值命题:
(6)对所有x而言,如果x是官员,并且x允许反贪污,并且x应该反贪污,那么x应该反贪污
它就是一个逻辑真理,是命题逻辑的合取简化律,即
(7)AΛB→B
的一个量化的特例(以“x是官员,并且x允许反贪污”和“x应该反贪污”分别代入(7)中的A和B,并加以全称量化,就可得出(6))。既然(3)等值于(6),而(4)等值于(3),则(4)等值于(6)。这说明,(4)可以借助“反贪污官员”的定义化归为逻辑真理。分析命题和逻辑真理的差别在于:逻辑真理单凭语形而必然为真;分析命题则兼凭语形和语义而必然为真,可称为语义公理。(4)就是规范世界中的一个语义公理。
我们可以给出反例(1)的一个非形式化的证明,这个证明用自然推理方法,(注:参见程仲棠:《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2-123、265页。)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同时引入逻辑真理(6)作为证明的根据(逻辑真理及其后承的前提集合均为空集)。令“{}”表示集合,“Φ”表示空集,(1)的证明可以刻画如下:
证明
{1}
1.甲是反贪污官员
前提
Φ
2.对所有x而言,如果x是官员,并且x允许反贪污,
并且x应该反贪污,那么x应该反贪污 逻辑真理
Φ
3.对所有x而言,如果x是反贪污官员,那么x应该
反贪污
2定义替换
Φ
4.所有反贪污官员都应该反贪污3等值替换
{1}
5.甲应该反贪污
1,4三段论
在最后一行中,命题5所依赖的前提是命题1,这表示:假设1是真的,5就是真的,这就证明(1)是从一个事实性前提直接推出规范性结论的有效推理,即休谟法则的反例。
在上述证明中,命题4就是语义公理(4),如果把它当作已证定理直接引入,就可以将上述证明中第2、第3行删去,余下3行可以构成(1)的完整证明,这表明:语义公理(4)可以直接地作为(1)的逻辑根据。
(1)也可以通过化归为逻辑真理而得到证明。如前所述,相当于(1)的蕴涵命题(2)是一个分析命题,通过对“反贪污官员”作定义替换可以化归为下述一个逻辑真理:
(8)如果甲是官员,并且甲允许反贪污,并且甲应该反贪污,那么甲应该反贪污
不难看出,(8)是(6)的一个代换例(是以“甲”代入(6)中的x而得出的结果),因而也是(4)的一个代换例。这再次证明,(4)是(1)的逻辑根据。
用类似的方法可以证明,“张三是法官,所以,张三应该依法审案”之所以形式有效,是因为“所有法官都应该依法审案”是规范世界中的一个分析命题即语义公理。“法官”也属于地位概念,可以分析为两个概念,即“官员”和“依法审判”,“x是法官”等于说“x是官员并且x是依法审判的”,其中“依法审判”是主项“法官”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谓项“依法审案”则与主项所包含义务同义,可见,这个命题是一个分析命题。
拙文还提出,与“所有法官都应该依法审案”不同,“所有骗子都应该骗人”不是分析命题或语义公理,而是综合命题,因为“骗子”的内涵不包含“骗人”的义务,骗人是一种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不可能是一种义务,所以,这个命题在现实的规范世界中是假的(类似地,“所有贪污的官员都应该贪污”也不是分析命题,而是综合命题,并且是假的(注:程仲棠:《规范领域中的分析命题》,《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5-16页。))。因而,“李四是骗子,所以,李四应该骗人”,就不是一个有效的直接推理;当且仅当引入“所有骗子都应该骗人”作为大前提,才成为有效推理。这时它就是一个三段论,两个前提都是假设,但由于大前提实际上是假的,当小前提为真时,结论未必就是真的。(注:程仲棠:《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第22页。)
“商榷文”却武断地说:“‘语义公理’说到底就是推论中隐含的前提”,并反问道:“难道我们不能设想一个由骗子组成的社会,他们就像我们社会中的法官应该依法判案一样,所有骗子都应该行骗,这不能成为那个社会的‘语义公理’?”(注:马永侠、武宏志:《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棠教授商榷》,《晋阳学刊》2002年第3期,第61页。)这表明作者没有弄清前提和语义公理两个概念,症结在于把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混为一谈。一切前提都是假设性命题,即可真可假的综合命题,在推理中我们只是假设前提为真,一个推理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假设前提是真的,则结论就是真的。语义公理是指凭语形和语义而必然为真的分析命题,分析命题可以化归为逻辑真理,它们都是从前提(假设)推出结论的逻辑根据。概而言之,前提是推理所依赖的假设;语义公理是推理所依赖的逻辑根据,本身不依赖于任何假设或前提(其前提集合为空集)。拙文断言“所有法官都应该依法审案”是语义公理,是因为它分析地真,从而必然为真,即在相对于“法官”概念成立的一切可能的规范世界中都是真的,换言之,在任何一个可能的规范世界(包括非法治或反法治的世界)中,或者“法官”的概念不成立,或者这个命题是真的。拙文断言“所有骗子都应该骗人”不是语义公理,是因为它并非必然为真,在现实的规范世界中就是假的。凭它在一个可以设想的“由骗子组成的社会”中为真,只能证明它不是永假命题,不能证明它是语义公理。
总之,在规范世界中存在一种表示地位与角色关系的分析命题,它们就是从事实命题推出规范命题之所以可能的一个逻辑根据。这种分析命题具有形式“所有S都应该P”,其中S为地位概念,P为角色概念。其定义可以表示为:“任意的一个规范命题‘所有S都应该P’是分析命题,当且仅当谓项P与主项S所包含的某一个义务条件同义”。(注:程仲棠:《规范领域中的分析命题》,《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4页。)符合这个定义的命题就是规范世界中的语义公理。如果“所有S都应该P”是一个语义公理,那么“这个M是S,所以,这个M应该P”,就是一个从事实命题推出规范命题的有效推理,即休谟法则的反例。
标签:休谟问题论文; 道德原则研究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证伪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逻辑谬误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晋阳学刊论文; 二元论论文; 推理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