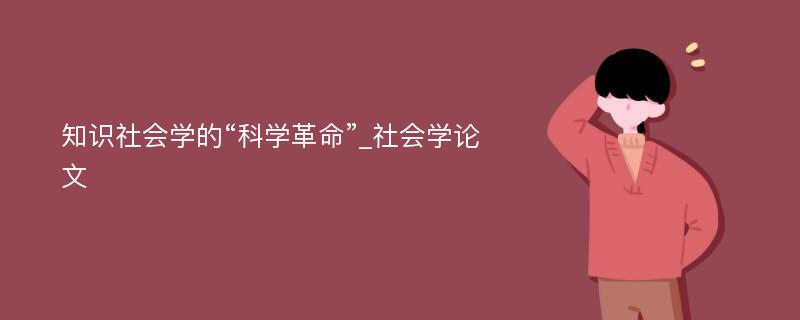
知识社会学的“科学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科学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可以说,人类对“真知”怀疑的历史几乎同人类对“真知”追求的历史一样久远,并且从未间断过。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里特就曾提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相对主义至理名言。进入近代以后,笛卡儿的“普遍怀疑论”,休谟的“世界不可知论”,杜威的“工具即真理”等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对“真知”进行了相对主义的阐释,试图告诫人们真知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然而,这些思想家的相对主义阐释却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即更多的是从认知主体的角度,而且是一个个孤立的、非社会性的认知主体的角度阐释,过于关注个人的主观意识,过于夸大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这种相对主义,实际上一种主观的相对主义,仅仅属于哲学范畴,确切地说是属于知识学范畴,还不能算作知识社会学。
启蒙运动以后,理性主义开始盛行。或许是因为对理性的崇拜,也或许是因为对理性的“无知”,再或许是因为对理性的畏惧,不管怎样,学者们逐渐把对“真知”怀疑的重心逐渐从主观领域转向客观领域。他们意识到,人不可能是孤立的、非社会性的个体存在,总是身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具有某种社会品格。所以,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产品的知识,也就不可能是纯主观的东西,必然具有某种客观社会属性。因此,学者对“真知”的相对主义阐释逐渐转向对知识产生的社会情境的阐释,即一种客观相对主义的阐释。于是,知识社会学便应运而生了。
知识社会学最早发源于欧洲。起初,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一词的含义是极其广泛的,几乎涉及诸如观念、意识形态、法律、伦理、哲学等所有人类文化成果。正因为如此,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是相当宽泛的,也是相当模糊的。不过,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是有着自己明确的研究宗旨:探讨知识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关注知识在生产、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关注知识生产、传播和发展的结果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正如默顿所言:“知识社会学主要致力于探究知识与人类社会或人类文化中存在的其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①迄今为止,知识社会学已经经历了三个比较成熟的研究传统或研究范式,它们分别是:古典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古典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知识或思想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一位知识社会学大师,曾被默顿誉为“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②。虽然马克思一生当中从未使用过“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知识社会学发展脉络中的奠基地位,因为他的很多著作中都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知识社会学思想。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同时,他还指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④马克思的这一知识社会学思想,后来被学者概括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可以说这是最早、也是最基本的知识社会学命题。对此,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基本成型。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也是古典知识社会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在知识的起源及其进化方面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⑤迪尔凯姆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对宗教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指出,宗教及其神圣性不可能来自宗教自身,更不可能是思想家苦思冥想的结果,它只可能是“集体表象”的结果。同时,他还认为,就连人类知识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逻辑范畴也都是“集体表象”的结果。所谓“集体表象”,是指一种社会性的信仰或道德思维方式,它不是产生于个体,而是形成于集体。因此,在迪尔凯姆看来,人类社会中的所有知识或思想都不可避免地是社会的产品,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集体表象”,因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或思想。
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舍勒(M.Scheler)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不过,在舍勒那里,知识社会学更像是知识哲学,只具有“辅助的”性质,是哲学的附属品,带有浓重的哲学色彩,还算不上真正的经验学科。⑥尽管如此,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思想仍然具有基础地位。与社会学家孔德类似,舍勒也把知识分为三种形态:一是效能知识,关涉世界的统治和改造,有助于生命生成,服务于生命的目标;二是教养知识,关涉精神“位格”的生成和发展,有助于精神生成,服务于精神的目标;三是神圣知识,关涉神性和上帝,有助于神性生成,服务于神性的目标。不过,在他看来,知识这三种形态都不同程度地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具有某种社会本性。正如舍勒所言:“全部知识的社会学本性以及所有各种思维形式、直观形式、认识形式的社会学本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即人们用来获得知识的各种心理活动形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都必然始终受到共同的制约,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⑦显而易见,舍勒也主张,知识本身永远都是社会决定的产品。
曼海姆(K.Manheim)是知识社会学创始人。1929年,他出版了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从而标志着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是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而来的。在该书中,他区分了意识形态的两种概念: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特殊概念”只把“对手”的部分主张视为意识形态,即当对手的生活境遇决定其主张是不正确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意识形态思想的存在。“总体概念”则更关注整个时代或群体的精神结构的构成和特点,主张所有群体(包括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暗含着意识形态。所以,曼海姆认为:“随着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方式的出现,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⑧因此,在他看来,所有的知识或思想都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地位、身份以及阶级利益的表达,源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即使是用以分类、收集和整理经验的范畴也是根据观察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⑨正因为如此,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后来又被概括为“社会情境决定论”。从这一思想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影子”。正如社会学家科塞所评价的那样:“(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马克思传统的影响的话,而曼海姆却如此广泛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⑩也就是说,同马克思一样,曼海姆也认为,知识或思想都是社会情境的产品。
总的来说,古典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或思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情境或社会存在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关联,具有某种社会本性。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或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产品,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必须接受知识社会学阐释。不过,古典知识社会学家们仍然相信自然科学是一个“例外”,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真知”,可以免于社会学阐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1)不难发现,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科学的地位极不同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精确的,而社会科学则是意识形态的。同时,迪尔凯姆也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发展,人类社会的成长和逐步的内部分化逐渐地使学术活动脱离了社会的限制,而科学思想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故而其结论比较而言是不直接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另外,曼海姆也认为,自然科学是真实的知识,可以极大地超越研究者的历史和社会观的影响。正如马尔凯指出那样:“要想对他(曼海姆)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做修正,必然导致其社会学体系的全面修正。”(12)总而言之,古典知识社会学家们还是不能接受自然科学因社会因素而改变的结论。因此,从本质上说,古典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带有“偏见”的知识社会学,具有明显的“知识二分”倾向。
三、科学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
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社会开始兴起。1938年,默顿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从而标志着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在文章中,默顿着重分析了作为一种文化因素的新教伦理与科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试图说明科学对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纲领性的文件。
默顿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拥有自己特定的制度目标,即“扩展被确证的知识。”(13)但是,究竟应当扩展何种“被确证的知识”?在默顿看来,科学制度自身似乎并不能自主决定。因为科学制度作为众多社会制度的一个部分,它并不是自主的,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从科学的研究兴趣上还是从科学的发展方向上讲,科学研究都必须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因为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获得大量的社会支持,才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资助。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们通常总是选择那些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的。正如默顿所指出的那样:“那些迎合当时社会和经济重点的课题吸引了科学家的注意力,使他们认为这些课题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14)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产品,是社会“需要”的结果。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D.Bernal)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开篇指出:“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15)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贝尔纳开始了他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通过对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现在正处于科学的社会改造阶段,科学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推动现代社会变革的核心因素。不过,他提醒人们,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并非全部都是“正功能”,同样也带有“负功能”。而这种“负功能”,主要是科学不当发展的结果。因此,贝尔纳认为,人们要想使科学为现代社会所充分利用,就必须首先对科学加以整顿,制定一种科学规划。整顿的关键在于,使科学能够自主发展。“如果让科学自由发展,它就会比现在为少数人谋福利时更有效地为人类谋福利。”(16)不难发现,在贝尔纳看来,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具有某种社会本性。
另外,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也是一位重要的科学社会学家。他在1940年出版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重点考察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他指出,知识人作为一种日益专门化的社会角色,似乎是“自由”的开展研究工作,但实际上常常受到社会因素限制。因为,他们的确很想执行一个社会公认的社会角色,找到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社会圈子,同时也希望拥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然而,这一切的实现,不仅要受到现实社会情境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领导者”的目标和兴趣的限制。正如兹纳涅茨基所言,知识发明只是“实现领导者‘目标’的必要‘工具’;由于领导者总是有一个明确的情境去应付,并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从领导者角度来看,专家的发明以满足他的需要为限,不必有更进一步的创新。”(17)就这样,不仅专家所要研究的问题被规划了,而且他们所要进行的知识发明也实际上被预先确定了,它们都从属于现实的社会理想或目标。因此,同其他科学社会学家一样,兹纳涅茨基也认为,科学本质上是社会的产品。
总而言之,科学社会学已不再把科学视为社会学的一个“例外”,并且着重考察科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研究科学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要关注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和制约。正如默顿指出的那样:“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是科学——作为一项带来了文化和文明成果而进行的社会活动——与其周围的社会结构之间动态的相互依赖关系。”(18)然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社会学阐释却仅仅只停留在制度层面。也就是说,科学社会学所研究的科学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只关注科学的外在制度形式,并不涉及科学的知识内容。可以说,从默顿20世纪30年代开创科学社会学以来,此后断断续续几十年的时间里,它一直都有意地回避对科学思想实质内容的分析。(19)正如知识社会学家金(M.D.King)所言:“科学社会学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门分析所谓的科学家的一定规范取向的社会学,但没有充分关注科学家明显变化的认知取向的社会意义。”(20)也就是说,与古典知识社会学一样,科学社会学也认为,科学知识无疑都是“自然之境”,是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反映。其中,科学社会学家德格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主张“真实的世界是独立于我们有关他的知识而存在的,通过逐渐接近的过程可以获得这一真实世界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之所以是真实的,在于它近似或类同于实际事物的结构。”(21)同时,默顿也认为,虽然社会结构因素可以影响科学制度,但是“科学的精神气质”作为一种科学的规范可以保证科学知识的“真”。因为它可以使得科学知识在获得认可之前,把先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标准有效地赋予一切知识主张。(22)另外,贝尔纳也认为,自然科学在本质上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是服从一定规律的,因而可以进行精确实验的各种一再重复的状态,因而是可以不受社会因素影响的。(23)正因为如此,科学社会学最终发展成为不讨论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学。(24)
四、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建构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特别关注行动主体,尤其是行动主体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过程。所以,建构主义主张,不存在唯一的真实或任何客观的实在,所谓的真实或实在都只不过是人类实践活动建构出来的产品,并且是始终处在被不断建构过程中的产品。正是在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知识社会学也迈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科学知识社会学阶段(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主要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等成员组成。他们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知识之社会学的研究纲领,而且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富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25)后来,这个小组被外界称为“爱丁堡学派”。
布鲁尔是爱丁堡学派的一个主帅。他在197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这也是一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布鲁尔对那种心甘情愿限制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学者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是对他们自己的学科立场的背叛。他认为,知识社会学完全没有必要限制自己的研究范围,“应当把所有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的材料来对待”。(26)为此,他还为科学知识之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基本的研究纲领——“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主要包含以下四个“信条”:①因果性,关注知识产生的条件和形成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感性、成功与失败的信念,两个方面都要解释;③对称性,说明方式具有对称性,即同样的原因类型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④反身性,是指说明模式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从中,不难发现,“强纲领”的核心,就是试图解决“知识划界”问题,超越“知识二分”原则。因为,在布鲁尔看来,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常规”的观点,源于特定的社会情境,是一种社会建构。“无论是一位社会学家,还是任何一位其他科学家,都没有理由因为他的那些理论来源于社会——也就是说,因为认为他的那些理论和方法是集体影响和集体资源的产物,是某种文化及其目前的各种境况所特有的东西,而感到羞愧。”(27)
巴恩斯是爱丁堡学派的另一位领军人物。他认为,科学并非始于观察,而是始于理论,遵循的是一种演绎的逻辑。但是,最初的理论又从何处而来呢?对此,巴恩斯的回答是:“如果按照推测,它必然是从科学家一般的文化资源中获得的,或者从这种资源中获得灵感,那么最终合理地选择的理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28)因为,他认为,科学家在进行理论选择时,依据的并不是他们的社会承诺,而是他们的信念。所谓信念,是指一种相信的状态,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地位的人,对于同一事物都会有不同的信念,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自然的信念是唯一合理的或是唯一的真理。因此,科学知识作为一种信念,只不过是一种已被群体接受的信念,并不是一种正确的信念。总之,在巴恩斯看来,科学只能是一种理论知识,而且“是完完全全的理论性的东西,而并非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性的。科学知识就是我们或我们的前辈所发明的理论,是我们仍然同意暂且用来作为我们理解自然基础的那些理论。”(29)
进入20世纪70年代晚期,英国以外的科学知识之社会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拉图尔(B.Latour)、美国学者诺尔—塞蒂纳(K.D.Knorr-Cetina)等。如果说布鲁尔和巴恩斯只能算作“理论家”,其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还略显宏大抽象的话,那么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则应当算作“实践家”,他们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转向,更加侧重微观实践研究,尤其关注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科学实验和科学认知活动的实验室。正如诺尔—塞蒂纳所说:“科学实验室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一个热门研究主题。从10年前几乎完全被忽视的状态起,实验室已经发展成为分析家关注的中心,已经以它的名字命名了新的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研究途径”。(30)
1979年,拉图尔与沃尔加(S.Woolgar)合写的第一部实验室研究著作《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出版,从而开创了实验室之社会学研究的先河。拉图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更多地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深入到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科学行动的实验室,观察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这一研究方法,明显带有自迪尔凯姆以来的法国特点。他认为,科学知识可以分为两种:“已形成的科学”和“形成中的科学”。“已形成的科学”是指科学行动的成品,即科学结论;“形成中的科学”是指科学结论得以形成的过程,由一系列科学行动构成。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已形成的科学”就像一个潘多拉的“黑箱”,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它。所以,拉图尔认为,若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研究“形成中的科学”,即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的生产过程,观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科学行动。在他看来,“这就是我们必须做出的第一个决定:进入科学和技术的途径应当经过形成中的科学那窄小的后门,而不是经过已形成的科学那宏伟得多的大门。”(31)他通过对实验室的长期人类学研究发现,实验室并非完全自足的,总是与外界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它必须谋取大量的社会因素——政府的投资、公司的设备等——以维系自身的运行。因此,科学行动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过程,科学知识也不可能是对自然现象的真实描述,它实际上是两个“行动者”——自然和社会——不断地变换角色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产品;既有自然品格,又有社会维度。
美国学者诺尔—塞蒂纳更是全景式地再现了实验室制造知识的机制和过程。她指出,科学结果从“与境(context)”方面说是特定的建构。(32)在诺尔-塞蒂纳看来,科学知识的建构或制造过程主要包含着两个链条:一是实验室中的“决定”,即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开展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中充满着“决定”。“决定”即选择,“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或“当地性”特点。也就是说,实验室作为“知识作坊”(workshop),不仅仅是科学行动或认知过程得以发生的物质环境,而且也是知识制造的机制和过程得以运行的社会情境,充斥着社会利益的分裂与融合。所以,在实验室中,科学家不是发现知识,而是制造知识。二是论文写作中的“磋商”。科学论文从初稿到终稿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者与批评者之间磋商的过程,同样充斥着社会利益的竞争和妥协,可以说是“实验室故事的继续”。(33)因此,诺尔—塞蒂纳主张,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并非是描述性的,而是建构性的。
由此可见,在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已不再赋予科学知识以“理所当然”的特权,并且着重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社会学阐释。正如巴恩斯所言,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它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知识的内容,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组织或分布。(34)因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科学知识绝不是什么“自然之镜”,它同其他类型的知识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品,具有某种社会本性,所以完全适用于知识社会学阐释。就这样,知识社会学第一次真正突破了科学知识这一“禁区”,超越了“知识二分”的原则。
五、知识社会学的“科学革命”:从现代到后现代
就像知识社会学主张所有知识都是特定社会情境的产品一样,知识社会学自身作为一种知识类型也不例外,必然也是特定社会情境的产品,具有社会本性。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自身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学阐释。正如布鲁尔在“强纲领”中指出的那样:“从原则上说,它(强纲领)的各种说明模式必定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35)
众所周知,古典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都诞生于现代工业社会。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知识可以说是一种“着魅”的知识,通常被当做“圣物”来对待,享受着神圣的特权。在这种社会情境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是出于对科学知识的“畏惧”也好,还是出于对科学知识的“无知”也好,知识社会学若要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坚定这一信念,“即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案例,而且如果人们无视这一事实,他们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错误。”(36)由此可见,古典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表现出“软弱”态度——坚持“知识二分”原则,赋予科学知识“理所当然”的特权——实际上并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情境的一个必然反映。套用知识社会学自己的话来说,古典知识社会和科学社会学实际上只不过是现代社会情境建构出来的产品。正因为如此,古典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又可以合称为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的“现代范式”。
与之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诞生于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科学知识的“神话”开始破灭,它不仅不再享有“理所当然”的特权,而且就连它自身也成为了“问题”,需要进行社会学阐释。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J.F.Lyotard)所言,“科学与非科学知识(叙述知识)的对比可以让人明白,至少可以让人感到,前者的存在并不比后者的存在更必然,也并不更偶然。”(37)因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表现出“强硬”态度——破除“知识二分”原则,免除科学知识“理所当然”的特权——实际上是后工业社会情境的一种必然表达。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后工业社会情境建构出来的产物,具有后现代特性。故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又可以称为后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的“后现代范式”。
由此可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知识社会学自身完成了一次库恩式的“科学革命”或“范式革命”,即从知识社会学的“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转换。所谓“科学革命”,就是“范式转换”,即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的过程。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实现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范式复制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倾向于将范式视为常态的、无问题的,并且大量的复制范式。其次是范式修正阶段,范式开始逐渐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于是人们开始质疑和修正范式。再次是范式替换阶段,当对范式的修正已无济于事时,旧范式就会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新范式的出现。(38)所以,如果说科学社会学的出现仅仅是对知识社会学范式的一次修正或创新的话,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无疑是对知识社会学范式的一次替换或超越。不过,这种超越的力量,并非仅仅源于自身,而且也是源于社会。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自身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品。
注释:
①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682页。
②R.K.Merton.The Sociology of Science.ED.By Storer N.W.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25页。
⑤W.P.Vogt.Early French Contribution to Sociology of Knowledge.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Sciences,Arts.1979,Vol.11.
⑥郭强:《论古典知识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
⑦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⑧⑨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9、130页。
⑩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导言10。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2)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林聚任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13)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821页。
(14)罗伯特·K·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4页。
(15)(16)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472页。
(17)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18)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793页。
(19)M.J.Mulkay.Some Aspects of Culture Growth in the Natural Sciences.Social Research,1969,vol.36.
(20)M.D.King.Reason,Tradition and the Progressiveness of science.History and Theory,1971,vol.10.
(21)G.Degre.Science as a Social Institu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55:37.
(22)R.K.Merton.Sociology of Science.ED.By shorter N.W.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23)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
(24)J.B.David.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The State of Sociology,ED.By Short,J.T.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1.
(25)刘华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
(26)(27)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艾彦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28)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29)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30)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31)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郑开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7页。
(32)(33)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205页。
(34)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前言1。
(35)(36)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艾彦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37)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6页。
(38)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