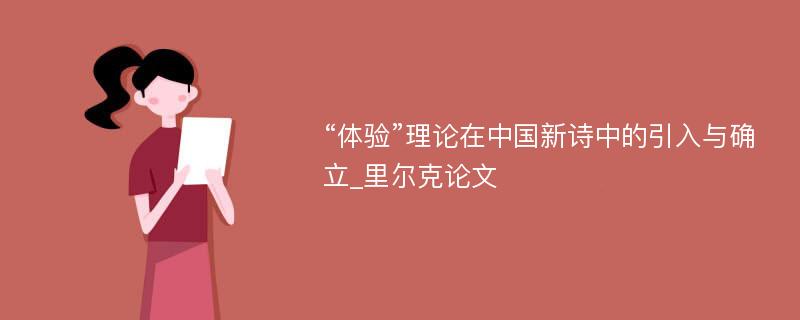
中国新诗“经验”之说的引进与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之说论文,中国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143—05
从1927年12月朱自清在《小说月报》发表译介文章《纯粹的诗》,介绍西方诗歌中的“纯诗”开始,艾略特、瑞恰慈、里尔克等人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得到广泛译介,不仅给时人的新诗方案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想象,而且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相当多的新诗实践被激发,使得中国新诗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就是新诗观念的变化,具体来说,即是由“情感”向“经验”的范型转变。关于这一引进过程,此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追溯和清理,但较多涉及其译介线索,很少探讨其观念之表达及在中国新诗中的建构。本文拟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中被屡屡提及的若干“名言”为中心,来探究那一时代与观念的歧异。
一
1934年7月,梁实秋的《偏见集》由正中书局出版,书中收录了他发表于《新月》等报刊的文学批评和论争文章三十一篇。虽然这些文章多是针对“讲‘主义’的”“文坛”,但作为由新诗人出身的批评家,他亦卷入此时新诗观念之分歧与争端中,并于文章中多处涉及对此时新诗的批评。
《什么是“诗人的生活”?》一文,是当时梁实秋对梁宗岱《论诗》一信的回应。梁宗岱借此信表达了自己的诗歌观念,批评“《诗刊》作者的心灵生活不太丰富”,并引用了里尔克的一句“名言”:
诗并不像大众所想的,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在这一“名言”之后,是里尔克的大段抒情化的表达,“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姿势。要得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光望着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1] 这段话实际上是列举“经验”,用以说明这一“名言”。但在梁实秋的这篇反驳文章中,恰恰针对着这段抒情化的言辞,在几乎原样照抄了这段话后,梁实秋讽刺说:“‘但要写一句诗’就要有那么多经验,‘伸出一句诗的头一个字来’又要有那么多的经验!”此后,梁实秋认为,梁宗岱以及他所引用的里尔克所说的其实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鲜”,而且其问题在于“太玄”。
两者的分歧,其实是在对“经验”之于“诗”的不同看法上,梁宗岱与里尔克强调其重要性,而梁实秋则更侧重于“个人的性情和天赋”,并不承认“经验”对“诗”的重要性。如他认为,“是诗人,他的生活自然的会丰富”,“不是诗人,他的生活自然的不会那样的丰富”,“虽然经验不少,那十行好诗还是写不出来”的。由此可见,梁实秋仍以“经验”为“材料”,而更注重运用“经验”的主体。
即使同是对“经验”的强调,梁宗岱和里尔克对“经验”之说的理解仍有差异。里尔克在谈论“经验”时,其立场是建立在对浪漫主义的反拨上,因此,其“经验”之说是与“情感”之说相对应的。梁宗岱在以里尔克此语批评《诗刊》时,更多强调的是经验的广泛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写作的难度。正如梁宗岱在引用这段话时给诗下的定义:“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换言之,虽则引用里尔克这一“名言”,但在梁宗岱对“诗”的构想中,“经验”之说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并未成为其诗歌观念的中心。
《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一文为梁实秋对英人伊斯特曼的著作《文学的精神:它在科学时代的地位》的述评。按梁实秋的介绍,伊斯特曼为“自命是以真正的科学方法研究文学”,而且与瑞恰慈“最引为同调”,在对“文人的‘随便乱说’”的批评中,伊斯特曼举了艾略特的例子,“在同一页上,伊利奥特先说诗是‘逃避情感’,随后又说诗不但是‘情感的真挚的表现’且是‘最有意义的情感之表现’。这些矛盾糊涂的语句,充分的表现文人运用名词之漫不经心,思想之紊乱驳杂”。这里涉及到的艾略特的观点,出自于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原句是:
诗不是放纵情绪,而是逃避情绪,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情感的人会知道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2]。
艾略特的这一“名言”是其“非个性化”诗学的核心观念之一,此文写于1919年,被收入于1920年出版和1928年再版的文论集《圣林》。但伊斯特曼显然并未去理解其含义,而简单地斥为“矛盾糊涂”。
在伊斯特曼对“摩登派诗人的作品”的“晦涩的现象”的批评中,他引用了瑞恰慈对诗的定义:“诗是一种传达(communication)的行为”,并将其理解为“一切文学乃是价值之字面上的传达”,因之批评“摩登派诗人对于这‘传达’的任务却吝而不行”。瑞恰慈的“诗乃经验之传达”,其要义在于,以“经验”为诗的主要成分,分析了经验的“错综复杂”,而非伊斯特曼所理解的“字面上的传达”。
对于伊斯特曼的这两处意见,梁实秋认为是“非常中肯的”,并说:“旧式批评家的思想之含糊笼统,诚是一个大病”;“新诗之趋于晦涩难解,是伊斯特曼所反对的,其实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反对的”。“凡是推重理性的人无不赞成文学尽其‘传达’的任务,而事实上好的文学作品亦无不令人了解的”。可见,持白壁德人文主义立场的梁实秋,或接受了伊斯特曼观念的影响,或在对艾略特、瑞恰慈的理解上与伊斯特曼的论调相同,且将之用于对中国新诗的批评实践。
二
《现代诗论》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4月出版,在书前的《序》中,曹葆华谈了出版此书的目的:“近十余年,西洋诗虽然没有特殊进展,在诗的理论方面,却可以说有了不少为前人所不及的成就。在这本书中,译者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由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作为一个以介绍西方最新“诗的理论”为目的的译本,曹葆华在《序》里特别推荐了“四位作家”,瑞恰慈和艾略特都名列其中,且被赋予极高的评价,虽然称赞之词都集中在他们的“批评”上,但评价的方向不同,或可表明时人对二人的兴趣所在和理解之差异。对瑞恰慈,是从其在批评史上的位置来谈的,被誉为“是一个能够影响将来——或者说,最近的将来——的批评家,因为他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趋附时尚的作家,实际上他的企图是在批评史上划一个时代”。在《诗的经验》一文后的“按语”中,曹葆华称瑞恰慈“在文学批评中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诗的经验》便是用心理学来分析诗的过程的”。《诗的经验》一文,正是瑞恰慈谈论诗与经验的关系的主要论述,原是其论著《科学与诗》的第二部分,曹葆华曾翻译并于1937年出版,在此又将其摘出,放入《现代诗论》之中。对艾略特,则是从他的批评与诗之间的关系来说,“爱略忒和梵乐希的诗论与他们的创作是分不开的,仿佛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就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诗”。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后的“按语”中也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他之主张诗人不能不吸收含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和读他的‘诗不是情绪的放纵,而是情绪的逃避……’这一段话,对他的诗必可以多一些了解。”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出现了此句“名言”:“诗不是故纵情绪,而是逃避情绪,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情绪和个性的人会知道逃避这些东西是什么意义”。
瑞恰慈的《诗的经验》从阅读行为来分析“诗的经验”并论证“诗之价值”,他的“经验”之说,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经验”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描述,在瑞恰慈看来,“经验”“分成两股”,“一股是主要的”,“可以叫做是主动的或情感的”;“一股次要的”,“可以叫做是智力的”。瑞恰慈认为,“经验”是由“情感”和“智力”组成,且“情感”为主要成分。他这样描述“情感”和“智力”之于“经验”的作用:
那主动的一股是真有作用的,因为整个激动底所有的力量都是由它而来,正进行着的思考好像是一种敏捷而有价值的调剂速度的机械底活动,它是被那主要的机器所运转而却支配着那主要的机器的。
所谓“激动”,正是瑞恰慈所说的“经验”,在“经验”这一系统中,“情感”被比喻成“主要的机器”,而“智力”则是“调剂速度的机械底活动”。瑞恰慈通过这样一个“机械运动”的比喻来解释“经验”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瑞恰慈认为“经验”是“错综复杂”的,在将“经验”分成“两股”之时,他就预先加以说明,“这只能当作一个解释者底手段”,而实际上“这两股有着无数相互的关系,并且又彼此密切地影响着”。在对“经验底主要的图形”的描述中,瑞恰慈是这样看待“经验”的:“通常它们未把自己表现出来,未显然明白地显露出来,大半是因为它们太过于错综复杂了”。
这种对于“情感与经验”关系的认识,如果对照bliss perry的论述,就会发现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抑或颠倒。Bliss perry的《诗之研究》一书,是闻一多新诗观念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译出后多次再版,对新诗坛影响甚大。在《诗之研究》中,bliss perry以“经验”为“情感”的准备阶段,并用金刚石的冶炼作为诗之产生过程的隐喻,在这一过程中,“情感”无疑占据主要地位,而“经验”与“情绪”虽是并行,但处于序列中较低的位置。而在瑞恰慈的论述中,“情感”虽仍占据主要位置,但却被包含在“经验”之中,成为“经验”的一部分而被处理。从“情感”到“表达”,经由“经验”这一中间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仅在1934年就被不同的译者翻译了三次①,在其传播和阅读中,时人最关心的是三个方面:“非个性化”、“情感逃避”和“客观对应物”。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核心观念在不同层次上的回应,而“情感逃避”之说在其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理由是:
第一,如同评论者所认为,在为艾略特的批评带来声誉的《圣林》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客观对应物’,有关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全部论断”,而且“情感分离”则在“整部文集中都能见到它的影子”。艾略特的观点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原因之一是“对个人的情感与经验有指导意义”[3](P96—97)。
第二,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情感与经验”关系的重构上。正因为如此,艾略特首先分析了“情感”与“经验”的关系,“这些经验,这些受接触变化的元素,是有两种:情绪和情感。一件艺术作品对于欣赏者的效力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和任何非艺术的经验全不相同。它可以由一种情绪组成,或是几种情绪的结合;各种因作者特别的字汇,语句或意象而产生的情感,也可以加上去造成最后的结果。”从这一表述来看,艾略特区分了两种经验:“艺术经验”和“非艺术经验”,并认为“情绪和情感”是包含在“经验”之中的。其次,艾略特以华兹华斯关于诗的著名定义为批评对象,从而破除了这一浪漫主义诗学观念带来的“情感”崇拜:
因此我们得相信“诗是宁静中回忆出来的情绪”是一个不精确的公式。因为诗不是情绪,也不是回忆,也不是宁静(如果不曲解字义。)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而这些经验在实际的一般人看来就不会是什么经验。
通过对华兹华斯诗以“情感”为中心为的批评,艾略特建立起诗的“经验”之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论述既是对该文第一节的主题“消灭个性的过程及其对于传统意义的关系”的呼应,而且将第二节所论“情感与经验”之关系引向一个结论,即“诗不是故纵情绪,而是逃避情绪,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情绪和个性的人会知道逃避这些东西是什么意义”。在这一定义中,艾略特的论述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强调“经验”之于诗的重要性,他之所以用“逃避情绪”、“逃避个性”之语,正是以“经验”为诗之主要内容。二是艾略特的论述并非否弃“情感”对于诗的重要性,而是为“情感”的作用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方式,或者说,“情感”之作用正是借助于“经验”展开的。如同艾略特以“经验”包容“情感”,韦勒克将之概括为:它牢守着诗的创造心理学为起点的诗学理论。诗不是强烈情感的流露,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情感组织。在此,“经验”不再同于以往的“经验”之含义,而是“情感组织”的基础。
第三,所谓“客观对应物”之说,亦是艾略特为解决“情感与经验”之关系而借助的一个概念或方法,在《哈姆雷特》[4](P13) 一文中,艾略特提出:“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4](P13)。由此可见,艾略特的“情感逃避”之说,虽则以“经验”代替“情感”为诗的主要内容,但其实质仍是“情感”之说,只不过他以“经验”为“情感”与“诗”之间的中介。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验”之说中,里尔克的相关名言亦经常被提及。1934年,冯至翻译的《马尔特·劳利特·布里格随笔》出版,其中出现了上文中梁宗岱和梁实秋提及的关于“经验”的表述,值得注意的是,里尔克的表述并非是二元对立式的,与艾略特易遭人误解的“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之语相比,里尔克此语虽然揭示了一个诗学观念上的根本对立,但方式却缓和得多,“诗并不像大众所想的,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这一表述实际上并不否认“情感”对于诗的作用,而只是反对“徒是情感”这种“大众”之见,因而得出“而是经验”的结论。如果将这一名言与冯至所翻译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后者恰好是这一名言的具体解说。在这些言说中,里尔克没有纠缠于“情感”或“经验”这些话题,而是具体地阐释了“体验”这一途径。
在瑞恰慈、艾略特、里尔克的文章中都出现了同一趋势:即以“经验”取代“情感”作为诗的特征。这一趋势标志着西方诗歌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不过,在这一言说中,取代并非排斥,而是以“经验”包容“情感”。
三
在瑞恰慈、艾略特、里尔克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中,值得一提的是袁可嘉、唐湜、冯至等人的理论构建和新诗实践。在朱光潜谈及新诗“成就”与“西方文学的影响”的关系时,曾以卞之琳、穆旦、冯至分别对应法国象征派、英美近代派和德国近代派。如果再清理其具体的资源谱系,其影响则分别来自瓦雷里、艾略特、里尔克等诗人。由此可见,他们在此时新诗中已有着范式般的影响。
里尔克在中国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一类诗歌写作“教科书”在中国的译介,而且在于他在中国拥有一位虔诚且具影响的实践者和传播者。这样,因而提供了一个如何“体验”“世界和现实生活”等“经验”并将其转化为诗歌的样本。冯至谈及里尔克的诗歌时说:“看不见诗人在叙说他自己,抒写个人的哀愁;只见万物各自有它自己的世界,共同组成一个真实、严肃、生存着的共和国”,他还引证和阐发里尔克的名言,“一般人说,诗需要的是情感,但是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5]。因此,这一“经验”是通过“体验”而获得的。冯至《十四行集》和《山水》的写作和相关论述恰好是一个实践里尔克诗学的样例。如《山水》的“后记”:
十几年来,走过许多地方,自己留下的纪念却是疏疏落落的几篇散文。或无心,或有意,在一些地方停留下来,停留的时间不管是长到几年或是短到几点钟,可是我一离开它们,它们便一粒种子似的种在我的身内了……[6](P77)
这种对“经验”的表述和抒情笔调与里尔克相仿佛。而且,在冯至此时的诗和散文中所显露的思考方式亦是里尔克式的。譬如,他在《两句诗》中谈到这样一种“体验”方式:“至于自己把身体靠在树干上,正如蝴蝶落在花上,蝶的生命与花的色香互相融会起来一般,人身和树身好像不能分开了。我们从我们全身血液的循环会感到树是怎样从地下摄取养分,输送到枝枝叶叶,甚至仿佛输送到我们的血液里”,其后,冯至又引用里尔克来说明这一方式:“里尔克有一篇散文,他写到在他靠着树时,树的精神怎样传入他的身体内的体验”,对照这两句可知,冯至对这种体验方式的感受和叙述实际上是里尔克的体验方式的扩展或实践,冯至因而将之归纳为“这不是与自然的化合,而是把自己安排在一个和自然声息相通的处所”[6](P15)。朱光潜在点评新诗时,曾言及冯至的风格特点是“融情于理,时有胜境”[7]。在这一评价中,冯至的“里尔克”式的体验方式又具有了与某些中国古代诗学中“融情于理”等范畴相通的意味。
袁可嘉被后人视为“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其所提出的“新诗戏剧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等重要命题,不仅归纳和应和了此时的新诗实践,而且往往被应用于对20世纪40年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的批评和评价。如果观察袁可嘉对于这些命题的表达过程,就会发现,瑞恰慈和艾略特的“经验”之说是其主要的理论资源②,袁可嘉正是以两者的“经验”之说为起点,结合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状况提出这些命题。
在对“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一命题的论述中,瑞恰慈的理论成为其立论基础和表现形式之一,“批评以瑞恰慈的著作为核心,有‘最大量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以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8]。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被应用于这一“新传统”的设想,“诗篇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这个批评的考验必然包含作者寄托于诗篇的经验价值的有效表现”[8]。在总结这一原则时,袁可嘉的语气与艾略特非常相似,“我们的批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而非作者的人格”[8],而且艾略特的名作《荒原》也被当作这一“综合”的样板。
“新诗戏剧化”这一命题,是袁可嘉针对“目前我们所读到的多数诗作”中“表示强烈感情或明确意志”的流行趋向,而提出“如何使这些意志和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在袁可嘉所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第一个方案即是由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之说转化而来,“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和情感。戏剧效果的第一个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和间接性”。在对这一方案的解说中,袁可嘉以戏剧为例,但与艾略特的《哈姆雷特》中的论述相差无几。第三个方案则是直接运用了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相关论述,“以为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没有一种理论危害诗比放任感情更为厉害”,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在于“你必须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9]。
唐湜是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的批评家,他的文章中交叉着上述诸人的影响。他曾回顾自己的批评生涯,“更在课室里念到T.S.艾略特、R.M.里尔克的作品,又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试作了一些新的探索。这个探索是从诗的评论开始的”[10](P193)。以《论意象》为例,其频繁的引证包括里尔克、艾略特、冯至,还有经由曹葆华所译介的叶芝、瓦雷里等。他说:
拜伦在《唐璜》里的“诗就是情感”的说法早已过去。R.M.里尔克说:“人应该等待又集中着一切生活里的甜蜜与光耀,如果可能,一段长长的生活,这样,也许在最后会写出十行好诗来。诗并非如人们所想的只是情感而已,它是经验[10](P11)。”
这段表述实际上是将艾略特和里尔克的“名言”粘贴在一起,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通过对华兹华斯的名言的批评提出“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而唐湜用拜伦置换了华兹华斯,且在结论中直接应用了里尔克“诗是经验”的名言。这种在行文中流露的表达方式,或许更能说明他们的影响在此时中国新诗中以某种形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朱自清所译的麦克里希《诗与公共世界》里,对于“情感”、“经验”与“诗”之关系的论述不再像艾略特、瑞恰慈、里尔克那样具有争辩性,而是作为一种“常识”出现:
艺术是处理我们现世界的经验的,它将那种经验“当作”经验,使人能以认识……艺术只是从经验里组织经验,目的在认识经验。它是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中间的译人[11](P161—182)。
在麦克里希的论述中,对于在诗中表现“我们时代的经验”的渴求甚至成为一种变革的呼吁,“经验”之说是艾略特、里尔克等诗人在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之说中建立起来的,如此又成为新一代的诗人(“新世代”)反对他们(“前世代”)的武器。事实上,“经验”已经取代“情感”成为人们谈论诗歌问题的重点。
关于这篇译文,朱自清不仅将其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和《中国新诗》上,而且他还根据麦克里希这篇文章所指出的“英美青年诗人的动向”,写了《诗的趋势》一文,对“抗战以来的诗”“侧重‘群众的心’而忽略了‘个人的心’”[11](P97) 予以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介绍西方诗歌的“趋势”,到40年代谈论“诗的趋势”,对朱自清的文学生涯来说,或许是一个并不奇怪的回应。但正是在这一循环之中,中国新诗的“风景”为之一变,其中,诗学观念最重要的变化,即是由“情感”向“经验”范型的转化。
[收稿日期]2006—11—20
注释:
① 三篇译文分别为曹葆华、灵风、卞之琳所译,曹葆华和灵风改其名为《论诗》,发表于《北平晨报·学园·诗与批评》第39期、第74期,卞之琳译为《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发表于1934年5月出版的《学文》创刊号。
② 袁可嘉后来说:“我所提出的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都明显受到了瑞恰慈、艾略特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而且是结合着中国新诗创作存在的实际问题”(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标签:里尔克论文; 梁实秋论文; 逃避心理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传统与个人才能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艾略特论文; 冯至论文; 袁可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