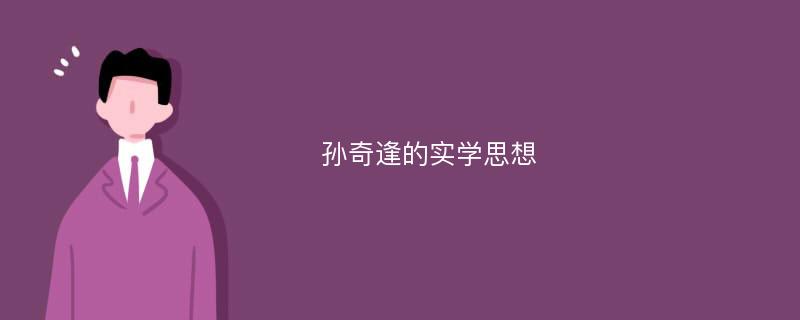
程飞[1]2011年在《孙奇逢实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孙奇逢针对明朝后期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弊端,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析和理解中,不拘门户之见,对各家学说进行调和和折中,进而返归孔孟,从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出发,承接了宋明理学和明清实学两种社会思潮,找到一条实学实用的道路。孙奇逢的思想中既包含了理学家的理之实,即孙奇逢思想中继承了本体实的一面,也没有放弃理学家的心之实,即孙奇逢同时也强调理学中心性论的道德实践的指向,在他晚年的讲学过程中也一直强调实学实用的重要性。在孙奇逢看来,理学在明朝末年逐渐走向没落,主要在于理学偏离儒学的轨道,而逐渐的走向异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以“实”为主线,试图把理学纳入儒学的大背景之下。同时,孙奇逢在把理学纳入儒学的正统,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合理性的道路上成就了自己的实学思想。就现阶段对孙奇逢思想的研究来说,一般都还是停留在对其理学思想的研究上,但经过对孙奇逢整体思想的把握,我们可以发现孙奇逢的理学思想更多的是在一种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来的,具有明显的实学成分,并且这种实学的成分不仅仅是停留在方法论上,而且贯穿于孙奇逢思想发展的始终,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本文通过对孙奇逢生平及着述的分析,发掘了其实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孙奇逢实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并阐述了孙奇逢本人及其实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赵春霞[2]2001年在《孙奇逢的实学思想》文中认为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着名的道学家,他虽承传于心学,却有着丰富的实学思想:本体论上,他坚持实理论,主张理与气不离,心与事不离,反对佛老以空无为本。人性论上,他坚持性一元论,反对将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就气质之性论善恶。修养方法上,他坚持实修、实功论,主张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反对静坐空谈。理学方法上,他超越门户之见,冷静地对待儒学内部的门户之见、是非之争,不求异不尚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求实方法论。孙奇逢的实学思想是对儒学传统实学的继承和发扬,对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吴强[3]2018年在《孙奇逢后学研究》文中指出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首先面临大崩溃,孙奇逢以王阳明心学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会通程朱、陆王以“直指孔子”,主张“躬行实践”,提倡经世致用。在整个学术环境内,创造出一套兼采程朱、陆王新学说。这种新学说,将学术彻底贯彻实行于社会实践,在北方及整个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学说以开放性的视角和全局性的战略回答了由于程朱陆王之争而导致理学极度空虚而带来的社会危机,解决了明清之际因政权交替而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缓解了“理”与“心”之争,为清代学术发展重新开辟道路。由此,孙奇逢成为夏峰北学及“实学”的开山之祖。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之下,迅速聚集了一大批儒生,由此形成了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学派。由于孙奇逢学术思想的特殊性,而使得其后学的学术倾向往往各有主张,如主张程朱理学的有魏一鳌、耿介、申涵光等人,主张通过体认天理、躬身实践来印证理学的经世致用,并基于以孝治天下的基础来维护社会秩序。而主张陆王心学的薛凤祚、耿极、王余佑、王之征、赵御众等人,在体认圣人之心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闲邪存诚,主张以慎独修身。还有如主张程朱、陆王二者兼融的汤斌、费密、张沐、胡具庆等人,通过道归孔子,主张二者兼融并以躬身实践实现经世致用的目的。他们对清初的学术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为陆王心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孙奇逢后学学术思想亦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影响着北方地区的学术风气和文化传统,对清代的实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对于当今社会重建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杨佳鑫[4]2014年在《孙奇逢《畿辅人物考》的史料价值与实学思想》文中提出《畿辅人物考》是孙奇逢晚年编纂的一部地方人物传记。该书在其生前未及刊刻,之后稿本又一度遗失。因此,同其姊妹篇《中州人物考》相比,该书长期埋没于世。书中所记载的许多明末人物与孙奇逢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其事迹来源于孙氏耳闻目见,对于研究明代畿辅人物和孙奇逢的生平交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在编纂体裁、体例和史论中都体现出了孙奇逢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也正是由于对实学思想的大力提倡,使得孙奇逢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重要推动者。
王坚[5]2006年在《无声的北方》文中研究说明儒学自诞生时,就有干预现实的强烈冲动。而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与权力正式结盟,进入“经学时代”。在儒学、儒生、权力叁者互动结构中,产生了“经学时代”的最大矛盾,即儒学服务于专制王朝系统与怎样服务的策略之间的张力。简言之,即“治统”与“道统”的矛盾。 在明代,由于理学过于心性化及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国家玩弄于鼓掌之间,“治统”与“道统”的矛盾、“礼”与“理”危机激化,儒生共同体分裂,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全面崩溃。 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变革中,在社会秩序首先崩溃的北方,孙奇逢以北学致用传统与阳明学为知识背景,以“直指孔子”与“躬行实践”并举,“礼”“理”合一,会通程朱陆王于寻行“孔子之道”,在整个儒学视野内,创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程朱陆王及汉唐儒学、最终落实于对“礼”的扬弃性实践的实践性“新理学”。这种新理学打通“礼”与“理”,融学术与做事为一炉,迅速波及北方及整个思想界,以其开放性、深刻性、全局性回答了由于程朱陆王之争而导致理学极度心性化而带来的种种问题,解决了明清之际儒学变革的深层问题,缓解了“礼”与“理”极度紧张带来的危机,为清代学术发展开辟道路。由此,孙奇逢不但成为清代北学及清代“实学”、“叁礼学”之开山,而且也是整个清代学术开山之一。 由于其重大影响,在孙奇逢周围迅速聚积了一大批儒生,由此形成了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北学。在叁百余年的流布中,他们渐变为以汤斌为代表的“理学名臣”,渐变为以费密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先驱,渐变为河北夏峰北学及颜李学派,渐变为中州夏峰北学。他们“通而不同”,共同传衍着夏峰之道。 随着西方强力入侵,中国进入近代,开始了漫漫现代化征程。在以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后学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下,夏峰北学开始了与不断变革的现代社
张枫林[6]2013年在《孙奇逢理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又号岁寒老人,是明末清初着名理学家之一,先后被明清两朝征聘11次,但都坚拒不出,故又被世人尊称为孙征君。孙奇逢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明代理学的总结者之一,又是清代学术的开启者之一,更是清代汉学的倡导与推进者之一。他品行高洁,心存故国,一生耕读讲学,大河南北学者多受其影响,被当时学者视为学术泰斗,被梁启超称为北学重镇,在当时与关中李颙、浙东黄宗羲并称为清初叁大儒。孙奇逢理学建构的态度是超越门户之见,建构的方法是“合会”,他通过融会传统社会不同思想家的思想,特别是朱熹与王阳明的理学思想,以孔子之道为准绳,参照易经哲学概念和辩证思维,从儒家传统经典中吸收养分,最终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理学思想体系。孙奇逢理学建构的核心概念是“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理论和宇宙论。他继承了传统理学家的理气说,认为天地有气有理,天理是天内在的运行规律,是气的主宰;他将“天”、“天理”、“太极”、“天命”、“天性”等进行整合并诠释,提出太极有阴阳,阴阳之理决定气的动静,按照天命运行,形成万物;万物秉承天理,一本万殊,为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提供可能。人作为理气的综合体,内含天理,所以人是天地之心,天理就蕴含于人心中,这表现为“性”;性的特质是“诚”,这特质未发为中,发为情,扩而为才,发而未发之际为几,几是心之动,始发处是善,这是天地之性,理气结合则为气质之性,表现为善恶不离的状态;天地运动的整个过程因玄妙难以描绘,因此称之为“神”,而整个过程即是“道”。人心中的天地之性即是人的良知,良知可以被认知,儒生通过对天地之性的认知得以自我的实现,其终极理想人格为圣人,圣人是天人合一的体现,是社会教化的开端。他继承传统理学家“圣人可学而至”的理论,认为圣人以体认天理为要,所以他提出“体认天理”是“天下第一等事”,“知学”是“人生最吃紧者”。孙奇逢认识论建构的可能来自于“虚灵之心”,其认识论建构的基础是“立乎其大”,模式是“下学上达”,方法是“读有字书,识无字理”态度是“随时随地体认天理”。孙奇逢工夫论分为叁部分,分别为处事之道、处人之道和处己之道。叁种工夫中,处己之道是核心,是处事之道和处人之道的前提,他继承传统的慎独说,主张在意念生发处戒慎恐惧,在已发后“主敬”收放心,目标是实现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从而达到“静”的状态。孙奇逢结合现实境遇,形成了独特的心性论、价值观、生死观等。他隐逸不仕,教授终身,弟子众多,形成了影响整个清代的夏峰学派。
王永灿[7]2007年在《孙奇逢心性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心性关系是宋明理学家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他们对其它问题的研究也是围绕心性问题得以展开。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理学内部自身矛盾,被宋明理学家高扬的心体与性体逐渐由形上向形下过渡;心性二元也逐渐向心性一元转变。孙奇逢作为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是研究宋明理学不可或缺的人物。通过对其心性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从横向了解明清之际的时代思潮,而且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宋明理学的总体演变。奇逢的心性论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他取用了宋明理学家所经常使用的“道心人心”、“本心习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诸多概念,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特征。在心学思想当中,他提出“道心人心非一非二”,他承认道心的形上性,同时承认善恶混杂的人欲,坚持本然与实然,形上形下的统一;“念前心,未发之别名也”,在吸取朱王未发已发思想的基础上,对朱王采取双谴双取的态度,他在形式上吸取了阳明的“体用一源”思想,在内容上则吸取朱子的“性体情用”,并且用念前心与天命之性结合起来,使未发已发思想更加具体化;“敬是知之凝然不放处”,在功夫论中,孙奇逢将敬与天理、良知结合起来,丰富和深化了程朱的主敬功夫论。在人性论思想当中,他提出“理通性命,则性即理也”,坚持在心性理一的基础上以心说性,以性说理。在承认人性的超越性的同时,也不否认后天的恶。在心性关系上,他利用对无善无恶的讨论心体与性体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严分心性,认为“心性岂容混一”;另一方面又讲“心性必不容分”,看似矛盾,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心性岂容混一”是指阳明“无善无恶”说心而不是说性,而“心性必不容分”则是指心体至善,是天命之性。并以此为基础,批判告子、释氏的无善无恶论。这些虽然体现了孙奇逢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超越,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传统的天理观将心性论结合起来,并以此来补救王学末流的玄虚与荡越之弊。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使儒家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但理学自王学以下,鄙陋日显,尤其是主体解放精神在明末过于显露和张扬,传统的天理观已经随着对朱子理学的消解而消解,对于当时士人己无束缚作用。在明末社会中,既然没有天理的制约,又无上帝做最后的保障,只能造成明末的狂禅派、性情派,对此,孙奇逢将理学心性论与宋明的天理观重新结合起来,以达到对明末儒学的救治。他在坚持心性理一的基础上,强调以心着性,强调性即理,使外在的天理与个体的内在意愿结合起来,达到心、性、理的合一,圆融了宋明理学心性论;在此基础上,以普遍的天理来制约士人的行为,以矫正日下的世风。孙奇逢在对传统心性论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并且在理论层面对王门后学进行补救。但是清初学术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能够健康发展下去,而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考证学一路,由于他坚持内在的功夫修养和外在的躬行实践,使得清初北学形成了极为朴实的学风,这也说明了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王门后学的玄虚与荡越,使得玄虚与情识之弊在清初有所收敛。
卢子震, 赵春霞[8]2004年在《孙奇逢的实学方法论》文中认为孙奇逢针对理学空疏的弊端和程朱与陆王两派的纷争提出若干理学求实的方法论原则。他批评了两派的门户之见 ,提出“我辈只宜平心探讨 ,各取其长 ,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关于学术异同 ,孙奇逢反对“以同异分是非 ,不以是非分同异” ,并进而指出 ,“凡异而同者 ,皆道之全者。异为真同 ,同为真异。见异于同 ,乃可辨道 ;见同于异 ,乃为见道”。孙奇逢由此而折中程朱陆王 ,提出两派的观点正可相资为用 ;并具体研究了朱熹格物与王阳明致良知的统一、顿与渐的统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 ,指出统一才是道 ,才是学 ,统一于躬实践才是真道实学。
陶英娜[9]2012年在《孙奇逢理学视域下的易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孙奇逢是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家,全祖望把他与浙东黄宗羲、关中李二曲合称“海内叁大儒”。明清之际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天崩地解”的时期,当时的思想家把亡国原因归之于王学的“空谈心性”,而倡导实用的经世之学。孙奇逢之学虽出于陆王心学,但他并不是一个只谈心性的腐儒,而专注于躬行实践的学问,并且以程朱理学思想来解释陆王心学,意欲会通程朱与陆王思想,调和朱陆。孙奇逢于六十七岁高龄始研易学,师从叁无道人李葑,其研易着作《读易大旨》也是自此开始,四订其稿而成。孙奇逢的易学思想承自其对朱陆之学的调和折中,不可避免地既带有程朱理学特色又兼有陆王心学之征。本论文以其易学着作《读易大旨》为基础,并结合《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日谱》等其他着作对孙奇逢的易学进行深入分析,以呈现出孙氏易学的主要脉络和创见之处。论文由绪论,正文与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了孙奇逢的生平着述,学术背景及学界关于孙氏易学的研究现状,以期对孙氏易学思想源渊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第一章阐明了孙奇逢之易学观。孙奇逢解《易》承自程朱解《易》思想,首先他认为易道准天地之道,《易》之道即是天地之道,《易》书是圣人摹写天地而作,《易》对天地的摹写始于乾坤。其次,孙奇逢解《易》明于义理,《读易大旨》多处援引前人易说来阐明《易》旨,这些学说偏重于义理,但孙奇逢并不反对象数。认为《易》之理须通过象数来显发,象数须放在义理中探讨才有意义。比如,他认为卜筮之结果必须结合人事,不仅是用来预测未来,更重要的是使人对于天道有所敬畏。在义理与象数的关系上,孙奇逢认为理数相即,但理为主,表现了以义理统摄象数的理路。最后,孙奇逢以卦爻辞和卦象为基础去阐发《《易》》所蕴含的种种人事之理。这是因为他提倡躬行实践的实学思想,认为《《易》》道只有在人事中发用流行,才能使生命主体之人体悟天道。第二章论述孙奇逢《易》学之本体论,他以“太极”为其《易》学最高范畴,“太极”不仅是天地万物化生、存在的终极根据,而且也是宇宙大化流行的法则,是对天地万物的总括,未有天地之前已然存在。同时,孙奇逢认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是指的“无极”为天地万物的根基,是无而未尝无,是对“太极”的本体规定,故“太极本无极”。八卦本于阴阳,阴阳本于太极,万物统体于一太极,太极本无极。所以圣人仰观俯察,见于此理,画奇偶之象而成八卦,刚柔八卦相为摩荡,天地万物于是乎生。八卦有健顺等性情的不同,所以万物的情状也相异。第叁章叙述了孙奇逢《易》学之心性论,其心性论思想是建立在其本体论基础之上的。孙奇逢以“太极”为宇宙间最高的理,《易》道本之于太极,而实具于圣人之一心,理总是吾心之理。又说,心之所在即性之所成,性心不二,理主性命,性即理也,由此心、理、性为一。无声无臭之中有“无极而太极”之至理,人禀受此理的天地之性因其不杂而是纯粹的善。但“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二气接于外物,而有昏暗强弱之分,表现为气质之性。孙奇逢确认性是至善的,虽然至善之性被外物蔽固则表现为恶,但恶也不能不称之为性。要保存这至善之性,回复本心即可,故尽性立命尽其心而已。第四章则阐述孙奇逢《易》学之工夫论。性为至善,但接于外物,为外物蔽固则表现为恶,那么如何保存善的本性?孙奇逢主张“诚敬”的工夫,“诚”即是真实无妄,天地之道因为至诚才能得以化用流行,人之本心禀于天地之道也是真诚而不伪的,所以要立诚、存诚来保存人之本心的善。“圣学主静”,孙奇逢认为“敬”包含“静”,“静”是“敬”的一方面,通过静心屏除一切心念,从而复现纯善的本心。同时,孙奇逢认为“敬”是一种危惧意识,人要始终保持危惧意识,对于天道有敬畏之心,惟其如此,才能修身治国平天下。无论“诚”或“敬”,都是要人挺立起人之为人的生命主体性,使天道在自身生命中得到圆融的显现,从而达到人与宇宙一体无隔,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最后本文对于孙奇逢《易》学作出了评价,认为其《易》学吸纳前人研《易》成果而成一家之言,以义理解《易》而不离象数,调和程朱、陆王学说,其易学最终落实到现实世界中,切于人事而主实用之学。
王记录[10]2016年在《百余年来孙奇逢及夏峰北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中研究表明百余年来孙奇逢及夏峰北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民国时期,徐世昌、谢国桢、嵇文甫等人极力表彰孙奇逢学术,对孙奇逢的学行及夏峰北学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梳理。其中尤以嵇文甫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改革开放后,李之鉴、陈祖武、张显清等人深入研究孙奇逢的生平、哲学思想、治学特点、学术精神及夏峰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学术关联,把孙奇逢研究向前推进一步。21世纪以来,一向比较冷落的孙奇逢及夏峰学派的研究出现了繁荣,一批青年学子选择研究孙奇逢,把孙奇逢研究推向高潮,相关研究领域得到拓展,问题得以深化。今后的研究要在叁个方面下工夫,继续深入挖掘孙奇逢的思想和学术价值;深入研究夏峰学派特点及夏峰后学的学术思想;加强对孙奇逢及其后学文献的整理。
参考文献:
[1]. 孙奇逢实学思想研究[D]. 程飞. 湖北大学. 2011
[2]. 孙奇逢的实学思想[D]. 赵春霞. 河北大学. 2001
[3]. 孙奇逢后学研究[D]. 吴强. 聊城大学. 2018
[4]. 孙奇逢《畿辅人物考》的史料价值与实学思想[J]. 杨佳鑫. 北京社会科学. 2014
[5]. 无声的北方[D]. 王坚.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6]. 孙奇逢理学思想研究[D]. 张枫林. 南开大学. 2013
[7]. 孙奇逢心性论思想研究[D]. 王永灿.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8]. 孙奇逢的实学方法论[J]. 卢子震, 赵春霞. 河北学刊. 2004
[9]. 孙奇逢理学视域下的易学思想研究[D]. 陶英娜. 山东大学. 2012
[10]. 百余年来孙奇逢及夏峰北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王记录. 清史论丛.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