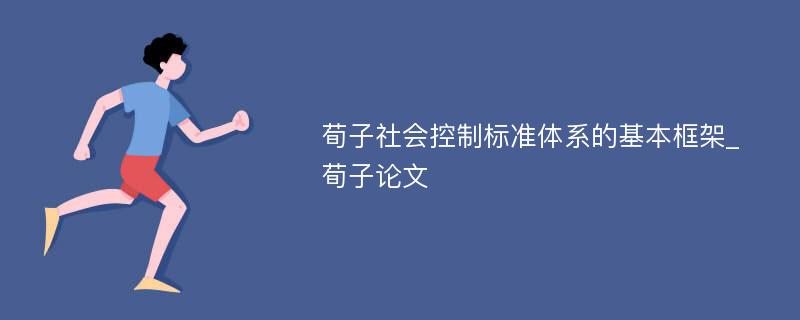
荀子社会控制规范体系的基本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构架论文,体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222.5
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控制就是通过社会的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指导和约束,使其与一定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的过程,因此,没有社会规范,社会控制就无从谈起。荀子的社会控制思想也正是以社会规范的考察为主干展开的,他所提出的“礼”与“法”两个方面的理论,基本上相当于现代社会学中软控制规范和硬控制规范的学说。
一、以“礼”为核心的软控制规范体系
荀子“礼”的含义比较复杂,但作为社会规范基本上是以软控制规范的意义存在的,这一意义上的“礼”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并最后归结于一个核心。
首先是习俗层面上的“礼”,主要通过人们生活中的礼节、礼仪等形式具体表现出来。荀子指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悖)乱提(偍)僈(慢);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注:《荀子·修身》(以下凡引《荀子》只注篇名))就是说,无论个人修养,生活、交往,都必须遵循礼。荀子还对人际交往、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作了详细具体的论述。作为习俗规范的礼,虽然并不具有强制意义,但由于这些形式已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而成为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不从俗的言行令社会其他成员感到“怪异”,因此,对社会成员的控制是以较自然的方式完成的。由于荀子的习俗礼与另外两个层面,特别是与社会的等级秩序密切相关,所以,习俗礼的社会控制能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正是荀子反复强调要“美其俗”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道德层面上的“礼”。在这一层面上,荀子主要是通过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来确立其道德判断标准的。在荀子这里,君子代表了善、是、正义、正当,小人则代表着恶、非、非正义、不正当。荀子认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注:《性恶》)君子和小人实际上代表了善和恶两种不同的势力。围绕着这两种不同的人,荀子分别作了相应的规范,并通过肯定君子来颂扬符合礼义的行为,通过否定小人来批驳违背礼义的行为。在此基础上,荀子还进一步阐述了礼所包含的其他道德规范,如“忠”、“孝”、“信”、“义”等。与作为习俗层面上的礼相比,道德规范意义上的礼具有更强一些的约束力和控制力,它包含着对一个人人格优劣及善恶的评价,是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来促使人们加以遵守的,由此而产生的对行为者心理上的压力比习俗礼更大,人们对道德礼的遵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觉”,而对习俗礼的遵守则较多地带有“自发性”的特点。
礼的第三个层面是作为治国之道的政治层面。荀子把礼推及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高到了治国之原则和方略的高度。荀子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规范,“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注:《王霸》)。“礼者,政之輓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注:《大略》)所以,荀子把礼视为“国之命”,认为在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都应以礼为原则。这一层面所讲的礼与现代社会控制体系中的典章制度相近似。与习俗礼和道德礼相比,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礼,由于和国家政权密切相联,因而其强制性几近于法,但它还不具备法的地位,可以看作软控制规范向硬控制规范的一种过渡形式。
荀子礼的三个层面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因而使得人们的习俗、道德行为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也使社会政治行为带有习俗、伦理的特征。这样,一方面加强了习俗礼和道德礼的控制强度,另一方面,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将外在的强制制度转化为内心信念和社会心理等意识过程,从而更容易被人自觉遵从。
荀子这种三位一体形式的软控制规范体系,集中体现在一个核心上,即对社会等级的划分。
荀子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注:《富国》)这是对礼本质意义的界定。荀子在对人类社会的考察中,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是由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的和谐稳定有赖于人们认清自己所应处的社会地位,并按照社会对该地位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方式的要求去行动,即“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注:《荣辱》)荀子认为,“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注:《君道》)争乱的根源在于无“分”。所以,荀子认为,消除争乱应从重新建立“分”开始,即要“明分使群”。所谓“明分使群”,就是要明确人们的社会地位,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并通过建立一定的社会机制,使人们都能按照“分”的要求去行动。荀子对社会等级秩序的划分已经涉及到了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稳定问题。荀子这种等级秩序的划分,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控制的规范形式。
这样,礼在荀子这里就成为以社会等级划分为核心,包含有习俗、道德和社会政治规章制度三个层面的社会规范体系。
荀子作为社会控制规范的“礼”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礼的普遍性。就控制客体而言,荀子的礼已基本打破了原有的“礼不下庶人”的界限,他更多地强调了礼对于社会中各类人的约束;就礼所起作用的范围来说,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礼的制约,无论个人的修养和行为,还是整个国家的治理乃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处理,甚至连法的制定和推行也要以礼为依据。荀子提高了礼在社会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其次是礼的非强制性,即礼作用的发挥主要不是靠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而是更着重于人们对礼的主动遵循。尽管荀子在对礼进行阐述时,有时也把礼与政治行为连在一起,显示出一定的强制性,但与硬控制规范相比就逊色多了,而且,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实施礼的控制,并不表明其非强制性的丧失,而更说明了荀子主张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也要以软规范来实现控制目的的倾向。礼的第三个特征是礼对社会成员控制的积极性,就是通过积极地引导人们应该做什么来发挥作用,礼的这种积极性是通过既对人的内心实施内在控制,又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外在控制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来实现的。
二、以“法”为代表的硬控制规范体系
在荀子的社会控制体系中,不仅强调了软控制规范“礼”的作用,而且还论证了“法”这种硬控制规范的重要地位。
荀子系统阐述了法的起源问题,并对法与礼所起作用的范围进行了区分。他说,“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其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如一。有离俗不顺其上者,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详,然后刑于是起矣。”(注:《议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以道德、礼义来引导百姓,以忠信诚实爱护百姓,以贤能之人来安抚百姓,以官爵赏赐来激励百姓,适时安排事情,减轻人们的负担,调整统一人们的行为,社会因此而稳定,但那些违背习俗而不顺从者却严重破坏了这种稳定,刑罚正是针对这样的人和行为产生的。荀子认为,法起源于礼所不能制之时。由于礼并不具备法的威慑力,尽管用各种方法引导人们去遵从礼的要求,但仍难免出现违规甚至严重的暴虐行为,所以,礼所不能制者则由法来禁。他认为,“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注:《性恶》)荀子的这一看法基本符合了人类社会规范诸形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社会规范诸形式基本上是沿着习俗→道德→法律的轨迹发展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是法,而主要依靠习俗和道德等非强制性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习俗和道德等非强制性规范不足以完成其社会控制职能时,特别是出现了国家和阶级对立之后,法才得以产生,发挥其强制性的特殊功能。所以,荀子认为法产生于礼之后,并与礼有不同的作用领域,应该说这一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荀子对法之起源的论述,可以看出荀子的法有其特定指向性,这种特定指向主要表现在与礼所不同的控制方式和控制范围上。与礼相比,法是从礼中分离出来的,通过国家政权体系强制实施的规范,不守法者一定要受到强力的制裁,而礼中的规范大多不具备这种特征。所以,当作为软控制规范的礼不能完全起作用时,法的威力就得以显现,因此,荀子指出,“出于礼者入于刑。”(注:《富国》)
作为硬控制规范,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首先表现在法本身的威慑力量上。荀子指出,“不威则罚不行……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注:《富国》)法正是通过这种强制力量,使人迫于刑罚之威严,而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避免越轨行为的发生。其次,这种强制性还体现在法的推行对国家官吏和国家机器的依赖上。“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戳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注:《王制》)另外,这种强制性也体现在荀子对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的主张上。荀子认为,制定和公布成文法,并大力进行宣教,可以使“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皆知夫为奸虽隐窜逃亡,由不足以免也。”(注:《君子》)他在《成相》篇中一再声称:“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就是说,法既然制定,就必须让人们知晓,在这里,荀子还意识到了法不仅是事后的制裁,而且,成文法的公布还有事先的警示与教育作用。“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注:《正论》)
荀子认为,法的本质是对犯罪的还报,这与庆赏是对功劳的还报性质上是相同的,他指出:“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注:《正论》)因此,刑罚的轻重也应与罪行的大小相当,这就是罪刑相称。荀子认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主张“刑不过罪”,“刑罚不怒罪”。(注:《君子》)根据这个原则,荀子认为,“赏功罚过”,必须“无恤亲疏贵贱”,(注:《王霸》)坚决反对以私害法,“刑称陈,守其银,下不得用轻私门,罪祸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注:《成相》)荀子的上述看法体现了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尽管在法律实践中,在阶级压迫社会里,难以真正实现,但在理论上确是真知灼见,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由于法在社会控制中的特殊作用,荀子在治国上非常重视法。他说,“法者,治之端也”。(注:《君道》)所以,君主要想统治人民,就必须严刑罚。他在批评“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的世俗之说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阐述。他说,“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注:《正论》)但荀子的“重刑”并非毫无原则的“滥刑”,实际上荀子是反对“滥刑”的。他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于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注:《致士》)他认为,赏刑要适当,如果不能完全做到,那么宁可失之“赏过宽”,也不能失之“刑过滥”。荀子的这种主张仍是建立在有法必依,有罪必罚,罚必当罪的原则基础上,因此在量刑时必须具体分析犯罪的原因。荀子认为,人们犯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罪之在己”,一种是“罪不在民”。治世的犯罪属于“罪之在己”。“明道而钧分之,时使而诚爱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响,有不由令者,然后俟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邮(埋怨)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注:《议兵》)反之,乱世的犯罪则“罪不在民”。在《宥坐》篇中,荀子借孔子之口说,“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奸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治世的犯罪既然在犯罪者本人,就必须予以严惩,乱世的犯罪既然“罪不在民”,而在于“上失其道”,当然应该从轻处罚。荀子反对无原则的“轻刑”、“重刑”,“轻刑”会导致民不畏法而达不到预期控制目的,而“重刑”同样达不到控制的效果。他把“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曰为乱人之道,百姓欢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称为“狂妄之威”。(注:《强国》)所谓“狂妄之威”,实际上指统治者用横征暴敛把人民逼上“犯罪”的道路,又继之以严刑重罚来杀戮人民的暴虐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不仅不会使人遵从社会规范,反而会导致混乱,甚至会使百姓弃国而去。”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戮无时,臣下凛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注:《议兵》)但对那些罪大恶极者必须严惩不贷,“元恶不待教而诛”,(注:《王制》)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礼与法两种社会规范的关系
在荀子的社会规范体系中,礼与法的作用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二者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偏废,所以,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注:《成相》)荀子在论及怎样才能达到“治世”时,总是把礼与法相提并举。“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注:《致士》)“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注:《性恶》)所以,荀子特别主张“隆礼”、“重法”,软硬并施,“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注:《强国》)礼与法成为社会控制中的两种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必要规范,各自用于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注:《王制》)
荀子“隆礼”、“重法”并提,把礼与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礼与刑”看作是“治之经”,认为没有刑威,不能“正法以齐官”,“不足以禁暴胜悍”。但在荀子的整个社会控制规范体系中,二者的地位又是有所区别的。总的说来,法从属于礼,礼是法的总纲,是立法的依据和指导原则。荀子指出,“礼者,法之大分。”(注:《劝学》)因此,礼比法更根本、更重要。荀子反复强调“国之命在礼”,“国之本在礼”,而且,把“礼”看作是“人道之极”。他指出,“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注:《礼论》)把礼抬到了最高、最根本的规范之地位。由此出发,在社会控制实践中,荀子主张先礼后法,礼主刑辅,“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注:《议兵》)“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表天下之乱。今废礼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祸患,此刑罚之所以繁也。”(注:《大略》)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如果能隆礼,法才会简约而天下“治”。所以,礼是法实施的依据,甚至可以说,在法的内容里渗入了礼的原则和精神,在社会控制实践中,应先申之以礼,后绳之以法,有时甚至主张礼即法。
综上所述,荀子为了实现更有效的社会控制,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以礼和法为主线的社会控制规范体系,主张既通过软规范的礼导之,又要用硬规范的法威之。从现代社会控制理论来看,软规范是以建设性职能为主,硬规范则以否定性职能为主,正是通过积极地建设合乎社会秩序要求的行为模式,否定破坏社会秩序的负面行为,来实现社会控制的最终目标。荀子由礼与法构建起的社会规范体系,也正是将积极的建设和消极的否定有机统一起来了,与现代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