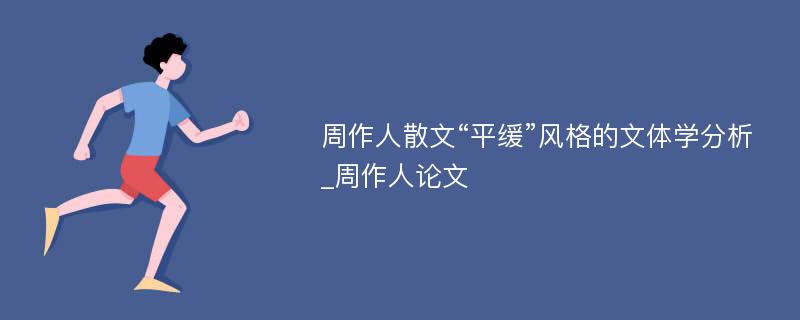
周作人散文“平淡”风格的文体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散文论文,平淡论文,风格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如果要推选一名最杰出的文体家,大概非周作人莫属。而他的文体,主要的特色是平淡。有人曾将他创造平淡美的艺术造诣同古希腊“高尚的简朴和静穆的伟大”之美相提并论,说:“我们景仰希腊艺术的不朽的美,可是它在时间空间上都离我们太远,只有周作人在我们的国土上,为我们创造出活生生的希腊式的美,其它任何人都没有做到这个”。[①]
一定文体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但都必须通过语言的因素(所谓“语言的指纹”),所以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章方法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也就是一种比较狭义的文体学分析。
一
周作人文体的平淡魅力,首先表现为语言的简单本色。他十分欣赏文潞公为一竹园题榜,“想了半天才丢开‘绿筠潇碧’等语,找到了一个平凡老实的‘竹轩’,”为作文提供了“极大的经验”。他认为,文章的至难之境是“本色”,文章的最高标准是“简单”:“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而“华绮便可以稍容易,只要用点脂粉工夫就行了”。[②]
语言的本色简单,实际上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是深厚的功底和高超的造诣的表现。且不论朱光潜说的“作者的心情很清淡闲散,所以文字也十分简洁”这一要“人格底子”做基础的方面,即只就语言形式本身而论,就至少包括语气、词藻、结构、修辞等项,我们试举最著名的“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典型”《雨天的书·自序一》予以分析: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象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会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无疑,在用词造句上,这是最讲究、最下功夫的书面语,但在语气上,却又极富口头谈话的风韵,非常自然随和,一点讲演和朗诵的腔调都没有(现代散文中的“絮语”、“娓语体”或“纸上谈话”都是以这种在用词造句和语气上辩证统一为基础构成的)。我们读的时候,也以一任自然呼吸节奏,一句句轻松从容地念出为宜。我们若把它与贾谊《过秦论》、苏轼《赤壁赋》、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吴伯萧《我还没有见过长城》等对读,它的特色就更加突出。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就是:它纯用散句、短句,不用一个词管多少个词甚至多少个句子(领字结构)或几个句子结构相同(铺排)这些需要憋足气一口读完的慷慨句调,真真是与家人友朋交心谈天式的。
在用词上,文章以名词、动词为主,运用副词、形容词极有节制,用得极少,并且都是普通常用的。其它虚词也用得很简省。整个文章完全是一派美人出浴,洗净粉脂见天真的效果。
尤其高不可及的是句子的简短及其结构的简单。全文共31个逗号句,11字以上的仅占7句,16字以上的仅1句,助词重迭的定、状语仅1处(周作人晚期写的一种“风干的文体”,就是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的,读者可参看比较典型的《三顿饭》)。复句结构有几处。但少用“一…就…”、“只有…才…”、“尽管…还是…”等紧锁紧连的形式,而是用一种比较松驰散淡的关联,以期造成从容轻蔓的效果(周作人赞扬优秀的日文“语长而助词多”,“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有无限妙处,[③]他自己结合中文加以变通,一般并不多用助词,而主要采用一种若断若连的松散长句,表现其纡徐优婉、雍容淡雅的风神;鲁迅也深受日文影响,“然而”、“因为”、“但”等助词频率极高,笔者有专门统计,将在鲁迅文体分析中专论)。
在修辞上,烘白炭火喝清茶谈天的比喻,出了气的烧酒的比喻,都是极富日常生活性的。正是这种富于日常生活性使人感到亲切,而其表现所比之事的贴切有力,又使人觉得新鲜巧妙、意味深永。
这里有必要对周作人在文章音调上的平淡追求专门地再说几句。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是毫不让步、十分严格的。相反,对于辞采色泽与文句结构,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灵活。他说:“我常觉得用八大家的古文写景抒情,多苦不足,即不浮滑,亦缺细致,或有杂用骈文句法者,不必对偶,而情趣自佳……六朝散文多如此写法,那时译佛经的人用的亦是这种文体,其佳处为有目所共见,唯韩退之起衰之后,文章重声调而轻色泽,乃渐变为枯燥,如桐城派之游山记其写法几乎如春秋之简略了”。[④]又说:在“有人称他为‘絮语’式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⑤]可见,他对像六朝文那样讲究辞藻色泽,以及吸收运用骈偶句法、欧化语、俗语等都是有所肯定的。这在他的文字中也不难找到例子。而且,就是依靠这种“适宜地杂揉调和”,才使他的文体平淡而不单调、枯窘,平淡而摇曳多姿、文味深永。
但是,在音调上,他却是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他坚决反对追求音律、“凡是文章须得好念”,有如昔人念韩愈《送董邵南序》,铿锵镗鞳,各有腔调,甚至“数易其气而后成声”,[⑥]他认为“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跟了上句的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弄得“只是在抑扬顿挫的歌声中间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地陶醉着”。[⑦]而这样做对文章最严重的伤害就是做作,“是在做文章而不是在说话”。[⑧]由这里出发,各种高调、假话、慷慨豪迈却空虚不实之词都可能奔涌而出,其结果,就不仅仅只是损害平淡的文体风貌而已了,所以,偏重音调气势,这在他的文字中是绝对避免的。
二
周作人平淡文体的第二个方面,是一种独到的文章内容处理方法和表现方法,这种方法总括地说就是对迫切、重要、与人生紧密相关的种种问题作静化、淡化、内化、深化的处理。可以说,周作人的平淡之主要特色是“平淡化”。这有时是取退避姿态以保持一段距离,有时是一种表面不动声色的包容深含。具体说,平淡的处理方法一指情感的平淡化方法,二指议论的平淡化方法。现在先讲第一点。
周作人多次称自己是“褊急”、“焦燥”、“积极”的人,以这样一种性情,生在当时的中国,报纸里“总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一出门“就看见女人扎缚的小脚……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⑨]更不用说直接受到一些人的挑战、攻击和批评,时常要挑动起一腔怨愤之气。但周作人通过一些独特的表现方法,把这些情感都包含、压制或改变了,也就是平淡化之“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时时检点”,包住火气与芒角,尽量“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⑩]表现一种庸容和谐、静穆闲雅的风貌。
这首先是含情不抒。人最好是对社会世事作低调反映,喜怒哀乐不入藏腑,可人是有热血的情感动物,这一点无论如何实难做到,但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使情感深蓄渊含,克制抒发,绝不宣泄,让喜怒哀乐入心但不露面,爱情止于脉脉注视,怨恨避免恶口相骂,尽量保持住一种绅士的尊严和风度,他很赞成南齐的沈麟士和宋代富弼“对于横逆之来轻妙的应付过去”的方法,并引发写下一段绝妙的文章:
我在北京市街上走,尝见绅士戴獭皮帽、穿獭皮大衣,衔纸烟,坐黄色车,在前门外热闹胡同里岔车,后边车夫误以车把叉其领,绅士略一回顾,仍安然吸烟如故”。[(11)]
这种并非没有不愉快,但只是不愿做得太难看,就是他写文章追求平淡所极力追求的,因为他认为:“我觉得与人家打架的时候,不管是动手还是动口或是动笔,都容易出现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12)]
其次是用叙述方式,让事实替自己发言,或避免语气的激扬峻厉。这实际上是要用文字和事实构成一道帘幔,让情绪冲动掩在幕后。在文章中,客观场景和客观事实的叙述处理得好,其力量是永远大于主体直接登台抒情的。因为直接登台抒情,总难免表现得过于刻露,令人一览无余;如果这种抒情又到了亢声高呼的程度,更容易为宣泄的快感所左右,失去深厚绵长的风度,而叙述,把事实推在最前面,仿佛是就事论事,但实则把自己的感受、倾向深寓其中,或者也不禁要站出来略加点示,总之那事实本身的表现是那样深厚、充实,决不让人感到是作者逞力的夸张和血涌气喘的造作,尤其是那些与自然、风俗、故地、友情等相关的文字,以叙述带抒情更有一种氤氲袅袅、幽深无尽的效果。我们且看《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中的一段杰作:
般若堂里的空气,近来很是长闲逸豫,令人平矜释躁。这个情形可以意会,不易言传,我如今举出一件琐事来做个象征,你或者可以知其大略。我们院子里,有一群鸡,共五六只,其中公的也有,母的也有。……有他们白天躲在紫藤花底下,晚间被盛入一只小口大腹,象是装香油用的藤篓里面。……夜里酉戌之交,和尚们擂鼓既罢,各去休息,篓里的鸡便怪声怪气的叫起来。于是禅房里和尚们的“唆,唆——”之声,相继而作。这样以后,篓里与禅房里便复寂然,直到天明,更没有什么惊动。问是什么事呢?答说有黄鼠狼来咬鸡。其实这小口大腹的篓子里,黄鼠狼是不会进去的,倘若掉了下去,他就再也逃不出来了。大约他总是未能忘情,所以常来窥探,不过聊以快意罢了。倘若篓子上加上一个盖……也便可以省得他的窥探。但和尚们永远不加盖,黄鼠狼也便永远要来窥探,以致“三日两头”的引起夜中篓里与禅房里的驱逐。
这大概可以作为周作人平谈文体的一个最杰出的代表吧!这是一种闲适之情,是与人的自然生活相接触、相亲近所得的一种得意忘言、几近禅家机锋式的体会,满纸是幽趣洋溢,作者的赞叹充满于字里行间。但是,事尽而止,他就是不抒泄出来,深含渊蓄,优婉无尽。如果把它说明为和尚们的春情向往之类,那种最深的禅境不是就给破坏掉了吗?我们如果把它与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对“作客山中的妙处”的种种主观的浓笔抒写对照起来看,其幽隽平淡的至味感,就更加强烈了。
再次是变怒目为戏谑。这就像与人意见不合,说着说着气就冒出来了,但若一任气性发泄出来,又有所不愿或不宜,于是变愤怒之辞为戏谑之言,维持面子上的笑容,或者,亦只热话冷说而止。周作人在论王季重时曾说,“戏谑乃是怒骂的变相,即所谓我欲怒之而笑哑兮”。[(13)]他又说,这是一种“值得赞叹”的“降龙伏虎手段”。[(14)]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段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例如1927年江浙清党,杀了许多人,而吴稚晖却诬蔑挖苦被难者“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怜,”周作人对此极端愤怒,但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却只说:
我们平常不能世故,轻信众生,及见真形,遂感幻灭,愤感失望,继以诃责,其实亦大可笑,无非自表其见识之幼稚而已。语云,“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谓马肿背,”痛哉斯言。愚前见《甲寅》、《现代》,以为此辈绅士不应如是,辄“动感情”,加以抨击,后稍省悟,知此正是本相,而吾辈之怪讶为不见世面也。今于吴老先生亦复如此,千年老尾既已显露,吾人何必更加斥责,直趋而过之可矣。……[(15)]
从自己“少见多怪”的角度说了一句戏谑的话,仿佛是要用文字来平气,其实只是把气愤掩饰一下,语气平淡些,而劲力并未减轻,等于表示:一,世上什么坏言行没有呢?二,人心坏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可说呢?过了些时,他改变了这种态度,写了一段怒斥叱骂之文:
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骷髅为饮器无甚差异。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后身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吴君是十足老中国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
这是没有经过变形的原生情感的直接表现。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到,周作人说他身上有“绅士”和“流氓”两个魂,说他有“隐士”与“叛徒”两重性,说他有“浙东性”和“师爷气”,说他“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16)]的文字与思想,说他“不肯消极,不肯逃避现实,不肯心死”,不能不写“讽刺与牢骚杂文”,[(17)]都是确实的。我们引这样的一节文字来作为对照,就更可见其戏谑文体的装饰力量了。
三
议论的平淡化处理在周作人的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因为周作人与苏轼一样,“长于议论”,[(18)]作品中“艺术性论文”[(19)]特多,在这数量可观的“艺术性论文”里,其平淡化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反对用作论腔调谈大道理,而用陈述语气,只从人生实用处说去。他虽以写议论为主,但却最反对“作论”。他引冯班《纯吟杂录》说;“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作论”是写文章的一种腔调,即好讲些“高调空论”,“只图自己说得爽快”,不顾事实,更不顾言与行能否相及。周作人说: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狂热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恶,皆为我所不喜欢,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子女听的,也决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20)]因此虽在体裁上是议论式的,但却用“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21)]的笔调,用陈述自己心得的方法。他所喜欢和追求的,是这样一种内容:“平常而实在,看来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处,正好比空气和水”,或“昔人所说的布帛菽粟”。[(22)]表现这种内容,当然宜用冷静的态度和平静的语调,像平常说话似的,平易而自然。
这里最值得提出来专门分析的,是用陈述语气发表议论。本来,凡有自己主观见解要发表的人,都容易为自己的高见得意,以至想方设法强化、吹胀自己那一点见解,因此其文章表现出意色不凡的姿态,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是发表议论而又太强调自己的结果。周作人力图不像这样,他似乎认为,他的议论都不是什么高招新见,而是平常生活中存在着的,为人格健全的人实行着的,或为理智清朗的先哲所早已见到说出过的,总之,它原本已很实在地存在于那儿,自己像只是在“转述”和“代言”而已,所以象是在“陈述”观点而不是在“发议论”:
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向来有一种乡愿的调和说,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有一种国粹优胜的偏见,只在这条件之上才容纳若干无伤大体的改革,我却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和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譬如国语问题,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的意见,大抵以废弃周秦古文而用今日之古文为最大的让步了;我的主张则就单音的汉字的本性上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纳“欧化”,增加他表现的力量,却也不强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做骈文律诗,但也并不忽视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的对偶的可能性。总之我觉得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面不可。倘若偏执一面,以为彻底,大家高论一番,聊以快意,其实有什么用?[(23)]
国粹欧化问题?是当时争论得多么激烈的问题。但是,不管争论者各人主观态度多么激烈,事物却自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这就是以自己的质地为基础,恰逢其会地尽量向前发展,“大家高论一番,聊以快意”,但全盘欧化既不可能,保守国粹必保守不住,徒然“高论”又有何益处呢?倒不如心平气和承认事实,跟随客观发展的脚步前进。周作人提观点,举例证,辨别擘析,都似乎只是在指示客观事实。既然只是指示客观事实,自然就用不着固执矜张,自炫己见,所以语调态度也就自然从容平和了。
很多时候,周作人也用一种绝然主观的笔调发议论。《苦茶随笔·小引》从自己喜欢诸葛亮、陶渊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一路说下来,说到明季公安竟陵,赫然写出一大结论:“三袁自称上承苏白,其实乃是独立的基业,中国文学史上的言志派的革命至此才算初次成功,民国以来的新文学只是光复旧物的二次革命”。一段话,他一共用了十来个“我”,几乎一口一个“我”,纯是我觉得…我认为…这样的口气,周作人在他的序跋文中,谈自己对文学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大都是如此(顺便说一句,周氏序跋文是序跋散文中最杰出的文字,在他自己的全部作品中也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一种。这种成绩大概与“我怎样……我怎样……”这种文体方式有关)。周作人坚信自己中心有得,但他又不愿意像有些文章那样,摆出一幅多么了不得的架子,仿佛自己就是真理、进步的化身,他利用“我……我……”这种文体,仿佛是说,这只是个人从经验中得来的,对自己来说是不可移易的真理。他是自信的,但口气是一己之见,亲切平易,不是号召,不是高呼,没有高调门。
陈述代言也好,纯然主观也好,他说的都是他所“亲知”,不只是援引,不只是趋时。因为是亲知,所以就特别自信;因为特别自信,所以说出时心平气和,如果借一个他自己的词形容这种平淡,那就是“我慢”,[(24)]做文章发议论的“我慢”,就是既有真见地真本领,下笔却又讲究风度,自信不自傲,自尊不凌人,矜而不争,威而不猛,泰而不骄。
第二,用“我田引水”法,引别人代自己说话。这既做到了以资料启新知,实现了他“有所为而作”的写作目的,又减省了亲自捋拳上阵,自己说话不多而仍不减文章力量。这是周作人“文抄公体”的一个主要奥秘所在。正因为如此,他的引述或“文抄”,不只是作为证据,而常常就是他自己的意思的直接或隐喻的表达。
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秉烛谈·茨村新乐府》引述明朝为李闯攻灭后,不少官员纷纷出来报名听点,遇到侮谑,只是缩首低眉,不敢出声,甚至有人“献金求大拜”,有人说“新主待我礼甚恭”,有人“撰劝表登极诏,献急下东南策,逢人便说牛老师极为欢赏”,对这样的事,作者引了一句议论“其辱更甚于被刑焉”,然后说:“我想要加添几句话,都觉得无用”,“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天下最高与最下的东西,盖往往同是言语道断也”。[(25)]因为若真要由作者出面议论,怕不要切齿痛骂才能相当。作者不愿这样做,所以只以引述为主,然后略加点染,并不特别指责说道,而那种善变化、无操守、钻营求进之徒的嘴脸已被揭露无遗,实实地为古今卖身投机者立下了一根耻辱柱。
第三,章法上优婉疏劲。这与一本正经地做社论和学术论文不同,没有必然怎样写的限制,而突出随笔而谈的自由。这样一种漫谈式的话题结构(谈法),对于周作人文体的平淡风貌具有极大意义。舒芜先生对这一点有精辟的分析:
朋友漫谈之间的说理,不象学术讨论会上那样要注意逻辑的严密和论证的周密。周作人的散文有时只从某一个具体事例,便引出许多大道理。例如只是介绍了印度那图夫人向英国戈斯请教作诗,戈斯教他先要丢掉夜莺呵蔷薇呵之类的英国诗歌中的习见语,再开手去做他自己的诗,方能有所成就,只介绍了这么一段话,紧接着便说:“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创作不宜完全抹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
这四条结论都很大,从戈斯教那图夫人那么一件事,便得出这四条大结论,论据本来不足,但在见解相近学识水平相近的朋友之间谈话,常常有这种情形,好在是互相启发,互相交流,并不是别人一定要听你论证充足之后才懂得那些道理。倘若避忌了这种种情形,处处都是归纳演绎,原因结果,大小前提,本证旁证……这么来一通,严密是严密了,可不象漫谈了。[(26)]
注释:
①舒芜《知堂小品·序》(刘应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②《风雨谈·本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7页。
《周作人回忆录·一八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③《苦竹杂记·和汉文读法》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8页。
④《药堂杂文·画钟进士像题记》,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6页。
⑤《永日集·燕知草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78页。
⑥《药味集·春在堂杂文》,转引自钟叔河编《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48页。
⑦《看云集·论八股文》,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48页。
⑧《谈虎集·古文秘诀》,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北新书局版,第313页。
⑨见《雨天的书·自序二》,《自己的园地·山中杂信》,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书合印本1988年版,第224—226页和194页;及《瓜豆集·自己的文章》,宇宙风社1937年版,第246页。
⑩见《苦茶随笔·杨柳》,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26页;《立春以前·几篇题跋·秉烛后谈序》,太平书局1945年版,第180页。
(11) (24)《立春以前·关于宽容》,太平书局1945年版,第8—9页。
(12)《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6页。
(13)《瓜豆集·关于谑庵悔谑》,宇宙风社1937年版,第288页。
(14)《夜读抄·文饭小品》,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27页。
(15)《谈虎集·偶感四》,上海书店影印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284页,下段引文同此。
(16)《知堂回想录·一三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页。
(17)《苦茶随笔·后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07、206页。按:这些话写于1953年。
(18)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卷八引李刚己。
(19)此用周作人自己《美文》中的说法,见《谈虎集》第40页。
(20) (21)《书房一角·原序》,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4、5页。
(22)《药堂杂文·汉文学的传统》,新民印书馆1994年版,第4页。
(23)《自己的园地·国粹与欧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25) (26)分别参见舒芜《知堂小品·序》(刘应争编),第8节与第3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