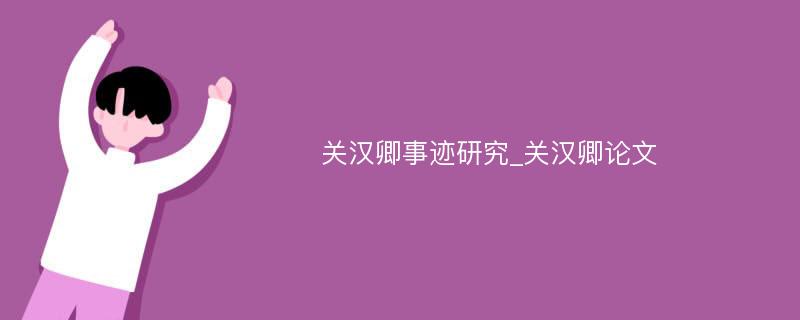
关汉卿行迹推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迹论文,关汉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汉卿一生行踪资料甚少,迄今未见直接或正面的记载,但欲对关氏创作深入考察,其行踪探索即为不可避免之事。今拟就手头有关资料,结合关氏作品,作一些推考。
一、做官、退隐、涉足曲坛
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关汉卿原籍山西解州,曾官金太医院尹,生年约在公元1210年至1214年之间[①](金大安二年至贞祐二年),金都恰在1214年南迁汴梁。关汉卿何时离家赴京任职,目前不得而知,但总要等到成年之后则是一定的,故可断定关氏离开解州大约在公元1225年以后至1230年以前这个阶段,而这正是该地区杂剧演出的繁盛时期。
据今人考证,远在金都南迁之前,今晋南地区的院本杂剧即已十分繁盛。从目前出土文物看,有金代前期的稷山县马村、化峪、苗圃金墓杂剧砖雕,金代中后期的稷山县吴城村金墓砖雕等等。特别是侯马市(距解州不远)牛村出土的金董祀坚墓葬文物,反映了大安二年(1210)杂剧演出状况,尤为研究者所重视[②]。其后直至入元从蒙古蒙哥汗六年(1256)到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下葬的芮城县永乐宫旧址潘德冲墓土石棺前壁戏台,仍可看出当地的戏剧演出一直繁盛不衰。关汉卿出生于此地,自小即受到表演艺术的熏陶,这对他后来丰富的戏剧创作无疑有着良好的影响。
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金廷弃汴京南逃,又在蔡州苟延残喘了两年。这期间关汉卿的行踪未见明确记载,推测起来有两种可能,一是逃走降宋或降元,一是随残金南下。从关汉卿具体情况看,此时年纪尚轻,又处朝内闲职,对时局的敏感较军政要员来说要迟钝得多,不会在短时间内作出投靠新主的举动,甚且不可能逃亡避祸。据《金史》,金室虽然因南迁蔡州苟安,以致许多朝政难以正常进行,但太医院事却大抵维持运作。如直到哀宗天兴二年(1233)八月,即金亡前五个月,《金史·哀宗下》尚有如此记载:“辛丑,设四隅和粜司及惠民司,以太医数人更直,病人官给以药。”显然太医院职能一直维持到最后,至被作为维系围城人心的重要依靠。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太医院正职官的关汉卿出走和逃亡都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肯定关汉卿任太医院尹一直和残金共命运,则金亡后关氏的命运及政治态度即可想而知了。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有这样的记载:
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此,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由此看来,亡金遗民后大多归入河北真定。这大概亦是元好问携白朴于金亡后不回山西隩州故里而“卜筑于滹阳(真定)”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次大规模移民毕竟不同于流放囚犯,控制得不可能太严密,只要在这一带方位不变,具体落脚点也略可选择。根据现有资料,关汉卿并未在真定居住过,而是在真定东北的古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境)留下了踪迹[③]。因金甫亡,蒙古统治者既不准亡金遗民留居金后期都城汴梁和蔡州,也必不允许他们回到原来的金都中都(今北京)去(忽必烈重建中都并更名大都是金亡数十年以后的事)。关汉卿新居住地既无回解州原籍之可能,即可推定他已于此时定居祁州。祁州距真定旧城不过区区百里之遥,符合遗民流徙的大致方位,况此地自宋时即始为“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④],有“药都”之称,关氏担任“掌诸医药”[⑤]的太医院尹期间即有可能常至此地,乱后投靠老关系来此隐居极有可能。按年龄推算,关汉卿此时不到30岁,父辈应当健在。今安国县伍仁村镇周围仍流传关氏祖父、叔父等事,或可参证[⑥],但这同关氏祖居该地的传说构不成因果关系。
关汉卿在祁州既可以说是乱后避难,也算得上是隐居。伍仁村是个乡镇,无论多么繁华,对于他这个“盖世界浪子班头”来说,不那么适宜。真定虽然近在咫尺,又有“故都之遗风”,但毕竟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样,同样处于附近不远的燕京(中都)即成了关汉卿理想中的新居住地。
中都乃金之故都,金室南迁后改为大兴府,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重新营建此地,复名中都,四年后增建新城并迁都于此。又五年(1272)正式定名大都,此距金亡已逾30年之久,关汉卿也已由一个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步入了知命之纪。然按诸史实,金亡后不久,志在经略中原的忽必烈即重视“汉法”及对亡金遗民的搜罗任用。从公元1242年任用刘秉忠(僧子聪)、1224年任用金状元王鹗开始,金遗民事实上已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优遇。到了公元1252年,亡金名儒,素为遗民之首的元好问也北上朝见忽必烈,并奉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⑦]。此时,关汉卿虽未出仕,但其活动当不会感到困难,作为一个天性好动不喜静的“高才风流人”(陶宗仪语),他不会甘心局促于乡村终老而毫无作为的。解州、汴梁这些他的原籍和长期居留地固不必说,真定即在附近,当亦为常游之地。“离了名利场,钻入安乐窝”[⑧],这个“安乐窝”不仅是隐居地,而且还是“嘲风弄月”的另一个代名词。可以说,此时的关汉卿,一个人即沟通了平阳、汴梁、真定三个元杂剧早期集散地。正是处在这些环境和条件下,他的“初为杂剧之始”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关汉卿天性不甘寂寞,自老荒野,“一心待向烟花路上走”(《不伏老》套中语),故至少在燕京重新繁荣之后,即已迁居于彼。至于具体时间,尚可推断。据史实,元太宗窝阔台于金亡后第二年已在燕京置版籍,核定人口。后三年(1238),又在此建书院,文化重建由此始,至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三月,又在燕京设断事官,建燕京行中书省,可以说该城的复兴也已拉开帷幕,关汉卿入燕,亦当在此前后。即使认定燕京行省建后繁盛尚需时日,而关氏之进入,至迟不会晚于公元1250年,《元史·世祖纪》载自是年“总天下财赋于燕”,经济如此,其市面繁荣可知。这样,自金亡至入燕,关汉卿大约在祁州乡间待了十余年[⑨]。
对关汉卿来说,这次入燕至为重要。和早年由解州进入汴京不同,虽然俱由外地进入都市,但此次已不是为了做官,而是“嘲风弄月”、“向烟花路上走”的需要。事实上他也正由此走上了毕生从事戏曲活动的道路。元人邾经《青楼集序》对此曾有过专门论述:
我朝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杜散人”即杜仁杰,“白兰谷”即白朴。对于他们的“不屑仕进”,有关史籍并有明确记载。事实上,凭着解州关氏的世族声誉,加上曾任太医院尹的经历和“高才风流”的个性,在官制混乱的蒙古时代,关汉卿是不难弄到一官半职的。他没有这样做,其主要原因恐怕仍是恪守家族遗风的缘故。“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关氏《单刀会》杂剧中为族祖关羽设计的这句曲辞,也许同样道出了自己的心曲。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关汉卿进入大都时,恰恰赶上了杂剧之形成,兴起和最初的繁荣时期(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在公元13世纪中叶)。一代伟大的戏剧家就在这里诞生了,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二、南下楚湘江浙
元灭南宋,统一中国,这是对关汉卿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正如当年不甘终老乡里而入汴入职和迁居大都一样,尽管此时他已年近七旬,却仍旧兴致勃勃地南下了,从而实际上开了“北杂剧中心南移”的先河。
关于关汉卿南下的详情,学术界一直很感兴趣。田汉先生于50年代创作《关汉卿》剧本即处理为关氏偕同朱帘秀一道南行,并在此之前还安排了关、朱为了创作和演出《窦娥冤》而得罪权贵终被驱逐的情节,颇具戏剧性。前不久有论者即从这个角度撰文进行论述,认为“关汉卿的南下杭州,恐是与朱帘秀戏班南流一同前往的。”[⑩]事实上,这是绝少可能的。
朱帘秀的生年没有记载,元人夏庭芝《青楼集》小传中已透露她和胡祗、王恽、冯子振、关汉卿等人交往的信息。据今人考证,朱帘秀是在扬州和胡、王等人交往的,时间当在至元二十六年冬至二十七年春(1289~1290)。当时胡出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出任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二人同行(11)。胡并有《朱氏诗卷序》,是为朱帘秀而作,其中有“虽可一唱而三叹,恐非所以惜芳年而保遐龄”之句。朱帘秀此时既为“芳年”,估计不会太大,然既已出诗集,估计也不会太小,当在30岁左右。故一般皆以朱帘秀生年为1260年(中统元年)前后,大致不误。而元灭宋时,朱氏刚刚成年,故关汉卿在祁州、大都的这一段活动她都不可能参预。王恽(秋涧)有[浣溪沙]词,是赠朱帘秀的,中有“烟花南部旧知名”句,可知朱帘秀出名是在扬州,故与关汉卿在北方的戏曲活动不会有什么联系。王恽另有诗《题〈朱帘秀序〉后》,同样为朱帘秀而作,称颂其为“七窍生香咏洛姝”,有论者因而推测朱帘秀原籍为河南洛阳,后来南下扬州。然而即令如此,仍旧不能证明关、朱曾结伴南下,据关汉卿的《杭州景》套曲,他称杭州为“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可见在宋亡后不久即到该城。而据史实,扬州陷落是在临安(杭州)陷落之后,这之前该城一直是兵端纷争,战乱不休,朱帘秀南迁扬州如果属实也决不会在此之前,可以肯定是在宋亡至该地重新繁荣之后,而在此之前关汉卿则早已到达杭州。或以为关、朱结伴南来,朱至扬州即留居,关则径赴杭州,如此则过于偶然,且不合情理,因目前留存唯一证明关、朱交往的关氏散曲为[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其中明明写着“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显而易见,关见到朱时,朱已在扬州多年,故关、朱结伴南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有可能和关汉卿结伴南行的,首先应当是他的好友杨显之。《录鬼簿》称杨为“关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就是说杨显之可以称得上关汉卿创作上的最好伙伴。这从现存关氏剧作亦可看出来,不仅早期作品如《调风月》、《救风尘》、《鲁斋郎》都有杨显之剧《酷寒亭》的文辞痕迹,即使其晚年剧作《窦娥冤》,人们也可看出与杨剧《潇湘雨》存在明显的相通处(特别是作为肃政廉访使的父亲最终为女儿申冤的情节构思),由此可见二人的合作是有始有终的。只有常在一起,才有彼此切磋的可能。
其次,有可能和关汉卿结伴南行的,还有他的另一位老友费君祥。《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一栏将其收入,明确称之“与汉卿交”,贾仲明吊词说得更加明白:“君祥前辈效图南,关已相从看老耽,将楚云湘雨亲把勘”。“关已”当即关已斋,因词格限制故省略一“斋”字。贾氏吊词虽不见于钟嗣成原书,但贾本人生于元末,一般论者皆公认其补《录鬼簿》卷上[凌波仙]吊词可信程度较高。
然而,贾仲明吊词没有提到去杭州、扬州之事,如此即产生疑问,关氏决定南行,其东线(杨、杭)和西线(楚、湘)是不是一次总体规划的相继行动?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根据现有资料,关汉卿一生南行只能有这一次,它既包括东线(杭、杨)也包括西线(楚、湘)。此从内容上涉及南方背景的作品创作时代也可以看出来,诸如《窦娥冤》、《望江亭》等剧和《杭州景》、《赠朱帘秀》等散曲皆为关氏晚年作品。显然,垂暮之年,两次南行辗转往返是不大可能的。由此我们还可以对关氏南行路线亦即其晚年踪迹作一大致的勾勒。
关汉卿此次南行,显然并非有如论者所言,是沿古运河从河北、山东进入江浙的。因为“隋炀帝开凿的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13),元代重修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始的,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掘“通惠河”成,南北交通才算是畅通无阻。而远在此之前,关汉卿早已在南方了。无疑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线。
根据现有资料推测,关汉卿离开大都出行,很可能在宋亡以前即开始了。因为经常“面傅粉墨,躬践排场”(14)的他,既然全身心投入戏剧活动,即不可能老在大都,他得参与戏班的流动演出,而元前期戏曲演出最盛的,莫过于山西平阳以及河北真定(山东东平虽然戏曲演出也很活跃,但关氏对该地区不熟,可置不论)。故可设想关汉卿一行离开大都,经由真定,然后转入山西、河南,此皆有关氏昔年居住地,其中还有着他的原籍和家园。故他们在这些地方创作和演出是很方便的,也容易站住脚和打开局面,关剧多以这些地区为背景绝非偶然。
当然,这不是说关汉卿一行离开大都即没有再回去过。事实上恐怕直到宋亡后南下之前,他们在上述几个地区的活动都是随意的,但大都没有失去基本立足点的地位。
元灭南宋时,关汉卿一行可能正在河南一带,他们南下第一站当是沿陆上驿道直接进入湖北、湖南,而潭州(今长沙)是他们最重视的一个落脚点。据史载,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潭州先于临安被元兵攻破,湖南大部旋被平定。次年,元朝廷在此设立荆湖等路行中书省,其城市繁荣可知。关氏名剧《望江亭》当即作于此时。另外,他们还可能在湖南各地流动,并曾到过湘南的衡州(有他的《刘盼盼闹衡州》一剧可证)。
湖南并非关汉卿南行的最后一站,甚至在此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在元军平定湖南稍后一段时间,南宋都城临安亦已被元军占据。不久,南宋即宣告灭亡。“江南佳丽地”在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于是随即向东经过江西进入浙江,最后到达杭州,此时应当是公元1280年以后了。从关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来看,关汉卿对此地怀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年事已高,却仍是兴致勃勃,所谓“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了笔”(15),正是这种心境的真切显露。
应当说,关汉卿在杭州待的时间比较长,和当代的戏曲界也多有往来。目前所见《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即收入关剧四种,其中《单刀会》则径称为“古杭新刊”,可见关氏剧本已在南方流行。另一杭州曲家沈和甫,还被尊为“蛮子关汉卿”,可以看出关氏在当地的影响。
然而,关汉卿并未因此在杭州终老。此时的他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古代中国人“人老还乡”、“归葬故园”的传统心理促使他决定北返故里。当时南北运河已开通,在内河乘船旅行,既可免受陆路颠簸之苦,又可饱览沿岸风光,这对于年迈但又殊“不伏老”的关汉卿来说,当是乐意而且可以胜任的。如此即结束了生了生中最具影响力的南方漫游生活。
三、北返,魂逝祁州
最能证明关汉卿北返的,首先是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此曲系其在扬州停留时所作。熟悉地理的人们当然知道,扬州乃一运河沿岸城市,为关氏乘船北上的必经之地,且为一历史名城,关汉卿在此暂作停留,上岸休息访友当亦情理中事,由此又引出元曲史上的一段佳话:和朱帘秀的认识和相会。
朱帘秀是元代曲坛上最负盛名的女演员。关氏曲中“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一句,很清楚地表明关、朱此次会面地点是在扬州,而朱在扬州看来已居住了许多年头了。至于此前他(她)们是否会过面,目前不得而知,但朱帘秀既为洛阳人,并且宋亡前后成年,且正是青春年华,艺术精进之际。关氏当年亦在河南诸地活动,二人或者有会面之机。而此次会面,关汉卿固己垂垂老矣,朱帘秀也已适人,故关曲中有“你个守户的先生肯相恋”句。这里的“守户先生”当是指钱塘道士洪舟谷。元·无名氏《绿窗纪事》记载:
钱塘道士洪舟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先是,故(胡)紫山以此妓为朱帘秀,尝以[沉醉东风]曲赠之。冯海粟先生亦有[鹧鸪天]云:(略)。皆咏帘以寓意也。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亦记有此事,且载洪道士于朱氏死前应其要求所作曲一首,中云“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痴迷”,可见朱嫁洪20载而卒。至于始嫁于何时目前亦无直接史料,然据今人考证,朱帘秀于至元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289—1290)在扬州与胡祗、王恽等人交往,至大德元年(1297)还一度到过湖南,与卢疏斋(挚)有过往来。其《答卢疏斋》小令有云:“恨不得随大江东去”,可见感情投入之深。很可能此后不久,即真的“随大江东去”,回到了扬州,而这位“玉堂人物”卢大人不过是一时逢场作戏,朱帘秀最终嫁给了洪道士。关汉卿此次到扬州,见到的朱帘秀这位“守户的先生”当然即为洪舟谷了,或许他(她)们正婚后不久。无论如何,这都证明关、朱这次会面以及关曲《赠朱帘秀》均为其晚年的事,时间当在公元1298年到1299年之间。此与学术界公认的关氏最后一个剧作(也是以扬州为背景的唯一剧作)《窦娥冤》的创作时间也大致吻合。可知关氏创作生命力至晚年仍常盛不衰。
关汉卿离开扬州北返,已年近9旬,是真正的老态龙钟,如他自己所述,已是“风寒不解忧成病,火暖难温老去情”(16),不久于人世了。目前河北安国留存的关汉卿墓表明他沿着运河北返后即归葬于此地,一代戏剧大师即在这里找到他的归宿。
然而此处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关汉卿为什么没有返回他的出生地山西解州,反而在河北祁州终老?
这个问题应从关氏此时的年纪和精力进行考虑。关汉卿年近9旬,从杭州一路北上由于是乘船,问题倒是不大,但如果再换陆路由河北转入山西,再到晋南的解州,山路崎岖,车马颠簸,则无疑是难以想象的。回解州还有一条水路,即自淮安向西折入黄河上溯,但逆水行舟,水高浪急,颠簸之苦亦非9旬老人所能承受,故亦可不予考虑。
其次,祁州虽非关氏的出生地,但他金亡后即已迁入,如前所述,其父辈可能亦在此地终老。老宅尚在,故园犹存,迁徙扎根在这里的山西移民亦不在少数,乡音乡风随处可听可见[①⑦],对关汉卿来说祁州不啻第二故乡,故归根于此亦属正常。况就地理环境而言,祁州水路通畅,境内之滱水,附近之滹沱河、漳水皆从靖海汇入古运河,北返舟行至家亦无不便。这样,关汉卿决定留在这里终老便毫不足怪了。
通过以上推论考述,关汉卿解州出生,汴梁做官,祁州退隐,大都嘲风弄月以及晚年南下楚湘江浙,最后归葬祁州,一生行踪可说显示得比较清楚了。以此为线索,似可对关汉卿现有作品作一个分期乃至编年的尝试。
注释:
① 参见拙著《关汉卿研究》第一章(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文献》(京)1994第4期并载有该书详细摘要。
② 参阅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清乾隆时纂修《祁州志》卷八“纪事”。另外,张月中《关汉卿丛考》(《河北学刊》1989年第1期)部分论述亦可参考。
④ 河北安国《药王庙碑铭》,转引自王强《关汉卿籍贯考》(《戏剧》1987年第1期)。
⑤ 《金史·百官二》。
⑥ 参见张月中《关汉卿丛考》。
⑦ 《元史·张德辉传》。
⑧ 《关汉卿散曲集》第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⑨ 关汉卿此次入燕,可能并非举家迁入,因为祁州距燕京并不远,他在彼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能算是客居,而且并不排除他有时也回祁州老宅住一阶段之可能。
⑩ 孔繁信《关朱戏班南流臆测》(《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11) 李修生《元代杂剧演员朱帘秀》(《戏曲研究》第五辑)。
(12) 参见拙著《关汉卿研究》第二章“创作分期及编年初探”。
(13)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7册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 明·臧晋叔《元曲选序二》。
(15) 《关汉卿散曲集》第21页。
(16) 《乐府群珠》卷一。
(17) 据今人调查,宋元明三代祁州所属近200个自然村中,山西移民建村竟达115个之多,超过半数。发表于《戏剧》1987年第1期的王强《关汉卿籍贯考》对此有专门考述,可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