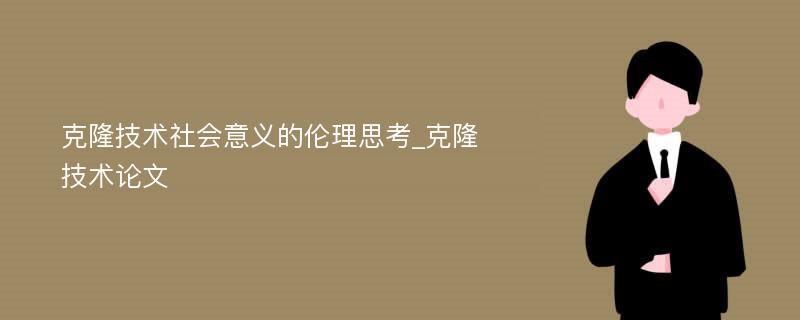
关于克隆技术社会意义的伦理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意义论文,克隆技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隆”(clone),在一般意义上用来指用无性生殖产生个体有机体或细胞的遗传拷贝。它涉及一系列技术,包括胚胎分裂、将体细胞核移植到去核卵以及用细胞培养建立来源于一个体细胞的细胞系。[1]克隆技术大致经历了植物克隆、微生物克隆、生物大分子克隆和动物克隆四个阶段,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从1973年美国研究人员限制性酶切割技术的运用到1997年“多利”的诞生,也只经历了短短的二十余年。
一、拷问“克隆”——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克隆技术作为基因工程的关键性技术,在未来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命运。一方面,人类的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健康、粮食、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在当今特定的条件下,粮食的增长和资源的有效利用都是有限的,克隆等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为解决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克隆技术的实施和深入,又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价值问题,尤其是人的克隆,将对人本身及社会、经济、文化带来重大影响。我们究竟应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作为行为的准则呢?正像二十年前没有人料到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一样,若干年后,人类延续了上万年的繁衍方式会不会受到克隆技术的挑战?这一技术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人类社会的结构会不会因此而改变?
据有关科学家预言,十年之内将会克隆出完整的新器官——人体的心脏、肾等,届时,医院就像一个汽车配件商店。生物世纪(21世纪)将给人类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转基因植物及动物产品可以解决饥饿人口的温饱问题;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的能源及纤维可构筑一个“可再生的”新社会;借助效果神奇的药物及基因疗法可以生出更健康的婴儿,使人消除病痛,延年益寿。[2]但是得到上述一切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自多利羊问世以来,克隆动物的家族先后又添了牛、猪和猴子等。但它们肩负的重任都是服务于医疗研究,而不是满足于商人赚钱的目的。2000年4月,一种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商品——克隆金鱼,由美国一家基因复制公司投市。克隆宠物鱼的上市,一方面使克隆技术一改生命科学的严肃面孔,走近了普通人家;同时,它那高额的回报、巨大的商机,又可能诱发一片市场新天地。可以预见,不久就会有克隆鲑鱼、克隆鲇鱼等上市,你吃还是不吃?
“多利”的问世,表明人类离克隆自己仅“一步之遥”了,到时候两个完全相同的“我”站在一起,是觉得有趣还是觉得伤心,是可喜还是可悲?许多人对此很是悚然。许多国家和组织已经以立法形式予以禁止,但是否禁得了?事实上,有关克隆人的实验仍在许多地方进行。1998年一家美国公司(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宣布把人的体细胞移植在去核的牛卵细胞里。据说在体外已开始像胚胎一样地进行细胞分裂,只是实验到此为止没有再做下去。1999年初,韩国一家医学院做了人的体细胞克隆,把妇女的卵丘细胞移到妇女的去核的卵细胞里,在体外让其分裂,这一实验做到胚胎细胞分裂,没有再做下去。[3]从以上情况看,尽管各个国家都禁止克隆人的实验,但事实上还是有人在做。那么,克隆人究竟该不该做?到时真的能克隆出一个真正的“爱因斯坦”来吗?
最后,再看看植物克隆。作为克隆技术的最丰硕成果的转基因农产品,如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等早已进入百姓世家。但近年来,世界性的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呼声却日渐高涨。因为,人们担心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造成潜在的危害,转基因植物的扩展可能会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系统。尽管有关人士一再声称转基因食品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仍然小心翼翼。同时,生态学家们担心转基因作物所具有的新特性可能会转移给附近的野生植物,会导致野草蔓延和虫害成灾。据《参考消息》报2000年6月3日版报道,有一种转基因大豆可能会被放弃,因为它可能引起变态反应。不堪重负的地球,到底需不需要转基因食品?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克隆等基因工程所揭示的前景也完全是双重的。它在基础学科领域和许多其他领域给人类展现出的前景是辉煌的,将会给未来社会的高度文明奠定基础,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个空前壮举。但是,也应该认真注意它的另一面——它对人和人类潜在的威胁是极端重要的,归根结底它触动生命本身。要知道,由于科学家的一时疏忽或别有所图,或被人胁持或利用,或由于商业活动的干扰扭曲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等等,都可能“放出妖魔”,造成无可挽回的、对于整个人类构成严重威胁的后果。因为在科技上可行的、经济上有利可图的事情,不一定对社会是可取的,更不用说在道德和伦理上是可容许的了。而当今科技发展是如此迅速,根本使人们来不及制定相当的配套而严整的规则来规范科技的发展,且科技本身也并不能说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现实本身也并不能立刻做出判断。因此,价值观、基本信念、戒律(即道德规范)也许将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
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扮演上帝的权能无可避免地放在了人的手中。人能否扮演上帝而不失去理智呢?
二、“克隆”之辩——我们到底应该克隆什么?
自克隆技术问世以来,便引起了社会学家、环境学家及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争议。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更是触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关于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的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的大讨论。大讨论所涉及到的人类伦理价值观念的层面,却是科学本身怎么也无法厘清的难题。岂今为止,大讨论意尤未酣,莫衷一是,综合比较,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不应该发展克隆技术。克隆技术是令人担忧的,它将从根本上破坏自然生存法则,破坏生物个体的独一无二性。因为自然界是长期进化的产物,任何一个生物物种都是经过上万年甚至上亿年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适应力。而克隆产生的新物种,不是生物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而是按人的意志、人的需要“嫁接”出来的物种,很难想象它能经受住自然选择的考验,它也可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甚至直接对人的生存构成威胁。英国的疯牛病、美洲的杀人蜂、“多利”和中国的克隆山羊“元元”的“早逝”都不同程度的说明了这些问题。至于人的克隆更是违背人类伦理,应予坚决制止。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们不仅应该克隆动植物而且应该克隆人,以提高人类在智能和体能方面的进化速率,或以克隆人来弥补有些个体的生殖缺陷。美科学家布鲁斯·默生在《驰向未来》一书中指出:“遗传工程学最富有革新精神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创造一种崭新的人提供了前景。”[4]前苏联生物学家A·A·涅法赫指出,运用遗传工程技术在人身上进行细胞核移植,就可以做到保留或复制出少数天才人物,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涅法赫说,因为用这种核移植方法保留和复制出一定的基因型,只是极少数人,所以不会造成任何原则上的新问题。[5]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更是认为“无性繁殖技术将使人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再生,使世界充满了他们的孪生兄弟姐妹。”[6]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托氏的这一设想与当今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法律规范多么格格不入。
第三点观点认为,克隆动植物是可以的,克隆人是不能允许的。美国微生物学家C·罗伯茨认为这样的优生学没有任何爱情和美德信息。因为按照这种设想,就会制造出因热衷于科学或政治而牺牲了道德原则的一代人。[7]还有一些学者尖锐地否定了用克隆复制天才的观点。他们认为,人不仅有生物学属性,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属性。那种认为可以“克隆天才”,实际上夸大了人的生物遗传结构的意义,否定了人的成长中社会因素的作用。所以,克隆专门用来执行某种特殊社会职能的人的思想,不仅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道德的,应从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斥责。
还有不少学者对克隆技术的可能被滥用表示担心,譬如被用来复制一种侵略成性的人或“狮身人面”的怪物。这在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者加腾一郎认为,人类为自己创造了文明,就决不能允许比人类更高的生物出现和繁殖,人类将永居主宰世界地位。[8]纽约州生物伦理智囊库哈斯丁中心主任汤姆斯·穆瑞表示:“我不认为提升猿的基因可以使它们有能力背诵莎士比亚诗,但是会使它们变得聪明些。但到那时,我们可能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和猿到底有什么不同的问题。”[9]他认为人类不断追求完美的思想看似崇高,但却含有潜在的心理和文化弊端。
克隆技术,就像所有人类心灵的原始创作一样,发展的结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如果我们有可靠的标准为依归,事先在知识玩具上标定良与窳,将更能够明智的管制其发展。只可惜我们都缺乏这种高瞻远瞩的智慧。恰如英国诗人弥尔顿所认为的那样:管制那样“善恶未定,但对善恶双方具有等效作用的事情”有其实际的困难。
三、“克隆”的未来——走向以人为本
马克思说过,“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克隆技术的发展,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10]关心人的本身,就是要关心的人价值、尊严、平等、自由和发展。否则“弱肉强食”或“人猿不分”,也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义,人也就不成为其人了。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对克隆的技术的社会评价问题也只能以人为出发点,只能从人的角度思考、判断、评价和选择。没有了人类,世界也就无所谓善与恶、美与丑、欢乐与苦难。如果没有了人类,也就没有了世界。人需要世界,同样世界也需要人。世界应该是有情的世界,人更应该是有情的人。克隆技术的发展只能更加丰富这个有情的世界,而不能淡化人的情感世界甚至连“舔犊之情”也不复存在了。那么,这样也就背离了人类的初衷,也就意味着世界的结束。
进化史表明,有性生殖明显加快生物进化的速率。克隆作为无性生殖手段,如果应用于人类总体,那么必将导致人类基因的纯化,降低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这无疑于给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生物性功能严重退化的人类“瓦上加霜”;其次,人类从总体上克隆自己,这与现今以血源人伦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价值体系和基本结构形式够成直接的冲突。克隆人类会导致家庭的解体,人类不必求助于异性既可产生后代,那么两性之间就不再存在子代血缘纽带关系。这样将彻底搞乱世代的关系,同时法律上的继承关系也将无以定位;再次,如果人类仅仅允许部分人克隆自己或为自己的目的克隆人,那将对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并由此而建立的社会结构形式产生根本性冲击。如果人人都争相克隆,那么谁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克隆?事实上,确定部分人具有克隆的权利一事本身就是对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无论是根据人的智能还是体能来确定克隆人的标准都是对人权的干涉;最后,如果我们允许一些人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克隆人,那么也许这些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克隆某些特殊的人来担当某些工作,这就剥夺了个体选择的权利,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只有以克隆形式产生的人比有性生殖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符合人类伦理道德发展的观念时,我们才能克隆人。显然,目前条件尚远未具备。
科学不应该只是满足单个人的目的,也不只是满足人类自然欲望的工具,更不单单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应当与合乎人性的价值体系以及行为原则相配合。一方面不能损害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同时又有益于人类延续生存以及文化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理想目标,“惟有树立一种价值观,借着科学的分析、理性的行为才能做到”。[11]正如当代遗传学家杰荷姆·雷杰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本身并不值得我们惧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运用科学。科学能产生最好和最坏的结果。真正的危险在于人自己。”[12]因此,就克隆等基因工程所带来的问题进行的辩论不能看作某种科学发展过程中暂时的、过渡的、偶然的东西,它将伴随科技发展的始终。它们成为科学活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证明科学发展进入新阶段,证明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科学作用在增长。
事实上,目前人们对克隆技术的认识,由于受技术本身实践的限制,也还是处于感觉经验阶段,多是一些理论上的推论,而自然界的发展是充满多样性和变换性的。克隆技术本身的发展进程和前景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事实就是如此,生存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的过程。”[13]但贯穿这一认识全过程的中轴只有一个,那就是——以人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