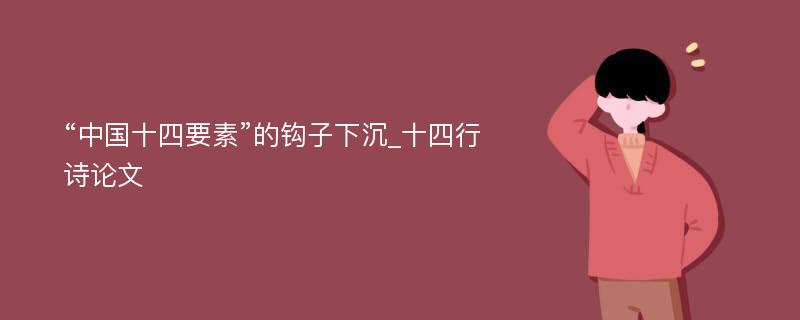
“十四行体在中国”钩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钩沉论文,中国论文,四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四行体(Sonnet),是欧洲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从二十年代初开始移植到我国。七十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创作了数千首中国十四行体诗,中国诗人已经完成了十四行体从欧美向中国的迁徙,实现了十四行体由印欧语系向汉藏语系的移植。这是中国诗人对世界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十四行体这一世界性诗体发展历程中光辉的一页。现把我们接触到的若干关于“十四行体在中国”的重要资料辑录于下。
胡适与十四行诗
一般现代文学史都以1917年2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作为白话新诗的最初“尝试”。其实,胡适用白话写新诗起始于1916年7月22日。再往前推,在此之前,他在留学美国期间,受欧美Sonnet的影响,曾尝试写过四首Sonnet,却长期被人所忽视。胡适自称:“在绮色佳(Ithaca)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带有试验的意味。”(《尝试集》自序)
胡适早在1914年12月22日曾用英文写过一首Sonnet,是意体,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现代中国诗人所写的最早的十四行诗。写这首诗的动因,据胡适日记云:“此间世界学生会(Comell Cosmopolitan Club,余去年为其会长)成立十年矣(一九○四——一九一五),今将于正月九、十、十一,三日行十周年祝典。一夜不寐,作诗以祝之。”几次修改后的诗如下:
A SONNET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ORNEMMLL COSMOPOLITAN CLUB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greatest as lea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spoke our Founders;so our work began;
We made no place for pleasant dance and feast,
But each man of us vowed to serve as priest
In Mankind's holy war and lead the van.
What have we done in ten years passed away?
Little,perhaps;no one grain salts the sea.But we have faith thatcome it will——that Day——
When these our dreams no longer dreams shall be,
And every nation on the earth shall say:
"ABOVE AMMLL NATIONS IS HUMANITY!"
为了便于理解此诗,我们请屠岸先生翻译如下:
十四行诗
康乃尔世界学生会成立十周年有感
“但愿从此地开始人类的共济,
在此地西方与东方自由地往来,
人把人至少当万物之灵来对待。
使彼此了解,亲爱,乃我们的目的。”
创始人如是说;我们把工作担起:
此地并非欢舞与饮宴的所在!
我们都立誓要有牧师的襟怀,
去带头冲锋,为人类的圣战出力。
过去十年中,我们有何事完成?
怕极少;一粒盐掀不起大海的咸浪。
但我们坚信,那一天终将来临——
其时我们的梦想不再是幻想,
地球上每个国家都异口同声:
“人类的博爱超越在各国之上!”
此诗的思想核心是提倡世界大同和人类博爱。诗的结构用四四三三段式,呈起承转合之势,如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每行节奏为五个音尺。韵式为ABBA ABBA CDC DCD,是典型的意大利彼特拉克体。
写此诗10天后的1915年1月1日,胡适又写了一首意体英文Sonnet,也抄录如下:
TO MARS
"Morituri te salutamus."
Supreme lord,we who are about to die
Salute thee!Come have we all at thy call
To lay down strength and soul and all in all
Without a murmuring,nor knowing why!
And thou serenely watchest from on high
Man slaughter Man and Culture tott' ring fall!
And lo! the wounded——men all!——cry and craw!
And upward meet thy smiles with their last sigh!
O know thou what these dying eyes behold:
There have arisen two Giants new,more strong
Than they that made thee captive once of old.
These,Love and Law,shall right all human wrong,
And reign o'er mankind as one common fold,
And thou,great god,shalt be dethroned ere long.
我们也请屠岸先生译成汉语如下:
告马耳斯
至尊的大神!我们,赴死的人们,
向你敬礼!我们应号召而入列,
来为你效力,献出灵魂和一切,
毫无怨言,也不知为何去牺牲!
你高高在上,安详地注视人和人
互相杀戮,文化也濒临毁灭!
看啊!所有的受伤者在呼喊,趔趄,
带着临终的叹息,仰望你笑吟吟!
你知道垂死者目睹何等景象:
两位新的巨人站起来,比之于
曾把你囚禁的两巨人更加顽强。
“爱”与“法”,将匡正人间的一切谬误,
将主宰人类,进入大同的理想,
而你呢,大神!不久就会被废黜。
这首《告马耳斯》,胡适自己在日记中写作《告马斯》,他说:“马斯者(MARS),古代神话所谓战祸之神也。此诗盖感欧洲战祸而作。”形式格律都与前一首类似。
这两诗不仅在中国十四行诗史上有重要地位,且在胡适思想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胡适于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先到美国绮色佳进康乃尔大学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国际学生联合会是外国在美求学者组织,要旨是“促进国际青年间的和谐,以消除彼此仇视甚至要诉诸战争的各阶层中的偏见、怨恨。”胡适在其中担任职务。两诗表达的主导思想是提倡世界大同和人类博爱,这正是胡适当时一再鼓吹的。如1914年7月22日,胡适在世界学生会会上作了题为“大同主义”的演讲。10月26日,他畅谈“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藏晖室札记》卷七)12月12日又说:“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读以上两首英文十四行诗,能帮助我们把握胡适当时的思想。
胡适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了十四行诗,而且也是第一个把欧洲十四行诗的格律介绍到中国。《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12月22日写道:
此体名“桑纳”体(Sonnet),英文之“律诗”也。“律”也者,为体裁所限制之谓也。此体之限制有数端:
(一)、共十四行;
(二)、行十音五“尺”(尺者〔foot〕,诗中音节之单位。吾国之“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为一尺,仄仄为一尺,此七音凡三尺有半,第四尺不完也);
(三)、每“尺”为“平仄”调(Iambic),如:
C 卜 | C 卜 | C 卜 | C 卜 | C 卜
(四)、十四行分段有两种:
(甲)abab cdcd efef gg
(乙)abba abba cdc(cde) dcd(cde)乙式或不分段。
(五)、用韵法有数种:
子、abab│cdcd│efef│ gg│
丑、abab│ bcbc│ cdcd│ ee│
寅、abba│ abba│ cdc│ dcd│
卯、abba│ abba│ cde│ cde│
辰、abba│ abba│ cdd│ ccd│
巳、abba│ abba│ cdc│ dee│
午、abba│ abba│ cdd│ cee│
胡适这段话的价值有三个方面:
一是胡适第一个给予Sonnet以汉语的译名:“桑纳”体,只是没有公开发表。
二是胡适最早向国人介绍了十四行诗的体裁的特点,诸如行数、节奏、音调、段法、韵法等,为中国人移植十四行体提供了应遵循的最基本的格律法则。
三是胡适试图把十四行体的格律形式同中国传统的诗体形式联系起来,尤其是指明了十四行体的音尺同我国律绝体的诗顿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诗人解决诗的节奏问题提供了思路。
郑伯奇的汉语十四行诗
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说:“中国人模仿商籁,似乎以戴望舒为最早,但戴氏的诗并不是商籁的正则。”这结论明显不确。戴望舒仅有一首十四行诗,题为《十四行》,是他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中第一辑“旧锦囊”里的第十二首。据周良沛先生说:“《我底记忆》这个集子,每首诗后全未注明写作日期,只知道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去法国为止的作品。前后编排也基本是按写作先后而定的。”(见《戴望舒诗集》编后)十分明显,戴望舒决不是我国最早写作汉语十四行诗的诗人。在戴望舒以前,有闻一多、郭沫若、朱湘、孙大雨、刘梦苇、冯乃超、李金发、陆志苇、徐訏等人写作了十四行诗。其实,王力那话中的“似乎”也透露了他对此缺乏把握。
据现有资料,我国最早写作汉语十四行的诗人是郑伯奇,题为《赠台湾的朋友》,原诗如下:
我血管中一滴一滴的血,禁不住飞腾跳跃!
当我见你的时候,我的失散了的同胞哟!
我的祖先——否,我们的祖先——他在灵魂中叫哩:
“我们同享着一样的血,你和着他,他和着你。”
我们共享有四千余年最古文明的荣称!
我们共拥有四百余州锦绣河山的金城!
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还有更大的,
我们的生命在未来;我们的未来全在你!
太平洋的怒潮,已打破了黄海的死水,
泰山最高峰上的积雪,已见消于旭日;
我们的前途渐来了!呀!创造,奋斗,努力!
昏昏长夜的魇梦,虽已被光明搅破;
但是前途,也应有无限的波澜坎坷;
来!协力,互助,打破运命这恶魔!
诗人在诗中,对“我的失散了的同胞”(下加着重号)倾注了深厚激情,而且是一种“禁不住飞腾跳跃”的激情;诗人在诗中抒唱,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应该同心协力,团结互助,战胜恶魔,创造未来。如今读此诗,我们仍会受到极大的感染,鼓舞我们去为祖国的统一而努力奋斗。我们惊叹作者当年的预见,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朽之作。尤其是,《赠台湾的朋友》是比较典型的意大利彼特拉克式,四四三三段式,每行基本上是六个音步,韵式是AABB CCBB DDD EEE。
此诗原载1920年8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上,比闻一多的《爱底风波》发表早了九个月。诗末注明是写于“九,五,二夜京都”,也就是1920年5月2日,那么,就写作时间说,就比《爱底风波》早了一年。原署名“东山”是“郑伯奇的笔名”。这诗即写于留日期间,时年26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荷兰和西班牙人分别侵入台湾,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1895年台湾又被日军占领,诗人写诗时正值日军占领期,因此诗人在诗中倾注了对同是炎黄子孙的台湾同胞的激情。当时,诗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不久,郑伯奇还同郭沫若等一起建立了创造社;《赠台湾的朋友》抒唱的内容,同“少年中国”和“创造社”的精神完全一致。诗人还在当时的论文《新文学的警钟》里写道:“形式上的种种限制,都是形式美的要素,新文学的责任,不过在打破不合理的限制,完成合理的制限而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诗人写出有严格道格律限制的十四行诗,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郑伯奇的《赠台湾的朋友》出现在《少年中国》上也不是偶然的。《少年中国》是个综合性的社科刊物,但始终关注新诗,不仅发表了大量的新诗,而且发表了不少重要诗论。尤其是一些诗论讨论了诗体革新之形式问题,其中就注意到欧洲的十四行体。康白情、李思纯等人都论说过十四行体,成为新诗史上最早公开谈论这一问题的文字。如李思纯在《抒情小诗的性德及作用》(载1921年《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和《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载《少年中国》2卷6期)中,都说到十四行体。他认为十四行体是欧洲律文诗的一种形式。他说:“十四行诗,是短诗之一种。大约分诗体为四段,前两段每段四行,后两段每段三行,合为十四行体。莎士比亚弥尔敦大家的集中,也有许多美丽的十四行体,其作用略似中国诗中的绝句体。”李介绍欧洲诗体,目的是为了“输入范本,以供创作者的参考及训练”。由此可见,《少年中国》发表汉语十四行诗,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第二首汉语十四行诗
闻一多写于1921年5月的《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载1921年6月《清华周刊》第7次增刊),评论了在那之前一年中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十首新诗,其中一首名为《给玳姨娜》。闻一多批评说:
这里的行数、音节、韵脚完全是一首十四行诗(Sonnet)。介绍这种诗体,恐怕一般新诗家纵不反对,也要怀疑。……我作《爱底风波》,在(本)想也用这个体式,但我的试验是个失败。恐怕一半因为我的力量不够,一半因为我的诗里的意思较为复杂。浦君这个作品里有些地方音节稍欠圆润;不过这是他初次试验这种体式,已有这样的结果,总算是难能可贵了。
这给我们寻找第二首汉语十四行诗提供了线索。据查,《给玳姨娜》发表在第210期《清华周刊》,时间在1921年3月4日,署名的“浦君”即浦薛凤,是江苏常熟人。如果不能发现新的资料,《给玳姨娜》应该是中国现代第二首汉语十四行诗。
为此诗,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在给笔者的信中介绍了闻一多与浦薛凤的关系:
浦1914年插班入清华,与家祖同班,在校时关系甚密,还在莱年暑期互相写信,有诗唱和。五四那年,家祖在上海出席全国学联大会,会后为建立学联会到常熟募捐,浦与吴泽霖、钱宗堡等做东接待。五四后,他们共同创办“美司斯”,家祖任书记,浦为会计。当时,浦设计过《清华周刊》某期封面,家祖堪到有批评,即写《出版物底封面》一文,已收入《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21年六三惨案,清华同学举行同情罢考,家祖所在辛酉级面临毕业,压力尤大。浦最终参加大考,与家祖立场不同。时,家祖与浦两人同居高等科一室,似互有沉默,不过浦说家祖对他还是理解的。
赴美后,家祖与浦及梁实秋、罗隆基于1924年夏共创大江会。浦学成回国,先在昆明东陆大学任教,旋辗转返清华,与家祖又成同事。抗战时,两人随校迁昆,但浦没两年便征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从此两人没有往来。
闻黎明来信中还透露:浦有两本回忆录,均在台湾出版。他现已九十多岁了,在美国度退休生活,数年前续一太太。
现把《给玳姨娜》全诗录后:
紫空里嵌满着几千万斛
灿烂闪耀的星球,
环拥那仙姑驰驭的明月。
这幅神洁的画图,
难道不许世人共睹
直到夜深才肯吐露?
看,一派浩荡的银潮,
把河山底埃垢丝尘都荡尽。
行行,忘了路底迢遥,
在茫无涯际的天空里前进——
为的是世界底光明——
你总守着你的定向。
玳姨娜可使我的心
同你这颗宝钻一样?
第一个有意试验种种体制的陆志韦
陆志韦曾是“五四”之后诗坛上比较活跃的一位诗人。他1920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戴着哲学博士的桂冠,曾任教于多所高等学校。他受西欧格律诗的影响,首先在中国提倡新诗的格律化,并出版了诗集《渡河》、《茅屋》、《渡河续集》、《申酉小唱》等。朱自清说:“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视过去。”(《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如今读过陆志韦的代表诗集《渡河》的人恐怕极少了。即使当时,注意他的人也不很多,因为“五四”之后新诗刚从旧诗体中解放出来,如脱缰的野马,多热衷于自由不羁;而发现自由体之不足者尚寥寥,所以陆志韦的种种新格律实验影响不大。然而我们今天客观地观照新诗发展历程,陆志韦作为新韵律运动的第一位旗手,其功是不可没的。
《渡河》出版于1923年7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所收诗乃1920年至1923年的创作。他主张“节奏千万不可少”和“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我的诗的躯壳》)。因此他的作品,有对传统的长短句的纵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的洋格律的借鉴,十四行体便是后者之一种。这期间陆志韦创作的十四行诗有《青天》、《瀑布》(1921年2月21日)、《动与静》(1921年3月18日)、《梦醒》(1922年6月5日)等。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十四行诗,只是做到了基本押韵。各首在段式的排列上均不相同。《青天》采用了每段首行顶格,其它行缩格的排列方式;《瀑布》采用四行顶格,四行缩格的排列方式;《动与静》采用八行顶格,四行缩格的排列方式;《梦醒》采用四四六分段的排列方式。由此可见,作者是有意在作各种实验。
陆志韦虽主张在节奏上“舍平仄而采抑扬”,但在创作实践中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这四首十四行诗都未能体现他的格律主张,都缺乏规律性节奏安排。
这里仅抄录其中的一首《瀑布》,以飨读者。诗行节奏虽不统一,但情意深挚,意象新颖,颇具动人的魅力:
尽有别人的头发强似你的头发。
尽有别人的身子还比你的瘦弱。
日升日落,你总是活泼泼的。
月生月死,你总是冷瑟瑟的。
无端跟你下山来,
在这冬青林下过,
你也不知何处去,
我也不知何以故。
或有一天,
我们到了海边,
听潮音为你我说姻缘。
我们这一次来,料不是偶然的。
待我送你到大智慧者面前,
了这一番心愿。
闻一多与十四行体
闻一多给予“Sonnet”的中文译名流传深广。1921年5月28日,他在《清华周刊》时,较早把“Sonnet”译成“十四行诗”,并指明是种“诗体”。到二十年代末,人们一般称它为商籁体,而把“Sonnet”音译成商籁体,最早的也是闻一多,是他在1928年《新月》创刊号上发表他所译的白朗宁夫人情诗时。以后,新诗史上多数人就使用十四行体或商籁体的译名,有时甚至二者混用。当然也有例外的。六十年代初,郭沫若、田汉、宗白华、王力、陈明远等讨论过闻一多的译法,认为不妥,主张改译为“颂内体”:“商籁体”是音译,但两个音都不准(闻一多的湖北方言中SH—S不分,L—N不分);至于“十四行诗”的译名虽有人采用,但Sonnet这种诗体的格律并不仅在于“十四行”,何况莎士比亚和霍金斯等许多诗人都写过“变体颂内”或“截尾颂内”,并非十四行。(见《新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菲律宾华人施颖洲先生主张音译为“声籁”,对此,屠岸认为,“商”和“声”的声母都是SH而不是S,尤其是“籁”的声母是L而不是N,所以不确,他主张音译为“索内”。虽然如此,他又认为:“‘十四行诗’这个名词已经广泛流行,我无意用‘索内’来代替。”(《十四行诗形式札记》,载《暨南学报》1988年第1期)事实上,闻译“十四行诗”和“商籁体”名仍最为流行。
闻一多又是我国最早创作中文十四行诗的诗人之一。1921年5月,他写了《爱底风波》,发表在《清华周刊》第220期(收入《红烛》时改题为《风波》)。原诗罕见,现录后:
我戏将沉檀焚起来奉祀你,
却不知道他会烧的这样烈;
他的精诚化作馥郁的异香,
那些渣滓——无非是猜疑和妒嫉。
你的接吻还没有抹尽的——
布作一天云雾,障碍了我的眼睛;
我看不见你,怕的不得了,
便放声大哭,如同小孩掉了妈妈。
“丑的很!不要怕了,我还在这里。”
我听到一个微柔的声音讲,
同时又听到你的心如雷地震荡。
你又笑着说,“好!我得了个好教训!”
但是,我的爱,这种“恶作剧”怎好多演?
到如今你的笑何曾把我的泪晒干!
对这诗,闻一多判以失败,我们尽可视为自谦,但这诗意思也确实太复杂了,到收入《红烛》时抽去了不少意思,改变了诗情发展急促紧张的状况。
到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闻一多写作了大量的新格律诗,包括五题十四行诗,即《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静夜》、《天安门》、《回来》,前四首收入《死水》集,末首载1928年5月10日出版的《新月》1卷3期。这些诗格律严格,音步整齐,是中国十四行诗佳作,尤其是《静夜》和《天安门》分别连缀了两首十四行诗,二十八行连贯而下,值得注意。1928年3月,闻一多在《新月》创刊号发表了他译出的二三十首白朗宁夫人十四行情诗,朱自清在四十年代的评价是:“他尽量保存原诗的格律,有时不免牺牲了意义的明白。但这个试验是值得的,现在商籁体(即十四行)可算是成立了,闻先生是有他的贡献的。”(见《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3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闻一多还在理论上介绍十四行体。1922年回家乡度蜜月,他完成了重要诗论《律诗底研究》,以“商勒”称十四行体,他说:
抒情之诗,无论中外古今,边帧皆极有限,所谓“天地自然之节奏”,不其然乎?故中诗之律体,犹之英诗之“十四行诗”(SONNET),不短不长实为最佳之诗体。
律诗实是最合艺术原理的抒情诗体。英文诗体以“商勒”为最高,以其格律独严也。然同我们的律体比起来,却要让它出一头地。
(律诗)的意义有时还译得出,他的艺术——格律音节——却是绝对地不能译的。律体的美——其所以异于别种体制者,只在其艺术。这要译不出来,便等于不译了。英诗“商勒”颇近律体,然究不及。
闻一多在对比中介绍了十四行体的重要艺术特点,即单纯、精严、音律。这些论述当时未发表,所以没有影响。
闻一多对十四行体介绍在当时产生影响的是他致陈梦家谈商籁体的信(刊《新月》3卷5、6期,1930年5、6月)。陈梦家有十四行诗《太湖之夜》:
老天竟然苍白得像死人的眼睛!
那种惨:太湖细细的波纹正流着泪,
远处紫灰色的梅苞画上一道清眉,
满山焦黄的岩石露出它的饥馑;
这光景够使我想起自己的伤心,
可是黯淡里谁能说晦色不就是美?
无限的意义都写上太湖万顷水,
尽是单纯:白的雪,灰心,心的透明!
看不见落日,黑夜带来死的寂寞,
尖锐的旋风卷走最后的声响;
灯火不能安慰我无边际的虚惊,
我耽心着孤岛真会顷刻间湮没——
要不是清晨看见你,雪天的太阳,
万顷的灿烂,你的晶光的眼睛!
闻一多读此诗后说:“恐怕这初次的尝试还不能算成功”,主要缺点有四:
第一,不讲起承转合。闻一多认为,十四行全篇分为四段,分别呈起承转合,“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最忌的是一条直线。”《太湖之夜》第三段三行仍沿上思路发展,毫无转势,末段三行依旧写自己的忧心,全篇“合”成,确是一条直线下来。
第二,有些诗句费解。闻一多指出,第二行的“太湖细细的波纹正流着泪”和第三行的“梅苞画上一道清眉”,都属此类。
第三,押韵用字重复。闻一多指出:“十一、十四两行的韵与一、四、五、八重复,没有这种办法。第一行与第十四行不但韵重,并且字重,更是体裁所不许的。”
第四,语言运用不当。闻一多指出,第七行末的“水”字之下少不得方位词。陈为了押韵起见,改成了“青水”。闻一多又指出,第十二行“耽心”的“耽”是“乐”的意思,应该用“担心”。
陈梦家参照闻一多所提意见,修改了《太湖之夜》,发表在1931年4月的新月社《诗刊》2期。陈梦家的修改,首先,在总体结构上,改动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字词,而在起承转合的问题上并无大改观,未能改变脉络嫌直的缺点。其次,前三行改的结果,未必更好。第一行把具体形象改成一般性感叹,第二行用撒下铅白灰来代替波纹流泪,缺乏美感,第三行以浪头取代梅苞形象,含意仍费解。修改稿的好处,是对原稿过于感伤的情调有所改善。第三,韵式修改后克服了原来的弊病,后六行CDECDE,是意体正式。最后,陈梦家在用字上,又将“耽心”改成“担心”,效果较好。
陈梦家的两首《太湖之夜》,在中国十四行诗史上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更重要的是,闻一多借此从构思、语言、用韵和用字四个方面,发表了他对十四行诗创作的见解,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
孙大雨与十四行诗
中国早期十四行诗创作,经历过“无意”和“随意”阶段,正因为如此,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我国诗人也未解决好十四行体音步移植问题。
到了1926年,随着新诗形式运动的发展,中国诗人创作十四行诗进入“有意”即自觉的阶段,并在实践中基本解决了十四行体音步移植的问题,对此有突出贡献的是孙大雨和闻一多。孙大雨深谙中西诗律,他在那时探索新诗节奏后认为,“在新诗里则根据文字和语言发展到今天的实际情况,不应当再有等音计数主义,而应当讲究能产生鲜明节奏感的、在活的语言里所找到的、可以利用来形成音组的音节。”(《诗歌底格律》,见《复旦学报》1957年第1期)那么,什么是“音组”呢?他说:“音组乃是音节底有秩序的进行;至于音节,那就是我们所习以为常但不大自觉的、基本上被意义或文法关系所形成的、时长相同或相似的语音组合单位。”(《诗歌底格律》)可见,孙大雨所说的音组,同我们今天所说的“音组”是一个意思,他是新诗史上最早拈出音组的诗人。非常有意思,正如他所说:“我最初在我国语言里探索这音节,结果发现了它并且加以试验,是在一九二五年底夏天,在浙江海上普陀山。就在随后的冬末春初时,和闻一多先生等交换心得的结果,我曾写过一首含有整齐的音节数的十四行体,在当时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诗歌底格律》)这首十四行诗即《爱》,写于1926年3月17日,发表于1926年4月10日出版的《晨报副刊》。这诗的每行音数有差别,但都可以划分为五个音组,每个音组大致是二音或三音。这诗的格律追求是:以每行的整齐音组去改换十四行体诗行整齐的音步。以后,孙大雨写作了《诀绝》、《老话》、《回答》等十四行诗,仍用音组排列节奏方式来对应移植印欧语的十四行体的音步排列节奏。如果说,英诗的宠儿是十音五步律的话,那么,孙诗同样每行还它五个音组,只是就节奏而言,每个音组都是一个大致等时的声音段落,他的有序排列,同样可以形成整齐节奏。与孙大雨以上探索同时,闻一多获得了相同的认识。他把诗节奏单元称为音尺,类似于中国传统的“逗”。他在1926年写《死水》时,就用西诗的音尺概括中国新诗的节奏单元,同时依据汉语特点赋予音尺以全新内容,即把重轻尺改成二字尺或三字尺,完全从字数着眼,从而成功地对应移植了西诗节奏单元,并依此认识,写作汉语十四行诗。正如卞之琳所说:“闻先生是较早基本上按照他的基本格律设想而引进西方十四行诗体的,那就是《死水》诗集第二首《收回》和第三首《‘你指着太阳起誓’》。”(见《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8年版)孙大雨和闻一多的实践,使中国十四行体创作进入了一个对应移植的自觉阶段,他们创作十四行诗的成功,也标志着新诗音组排列节奏的形成。
正因为如此,孙大雨的十四行诗,产生了重要影响。《诀绝》、《老话》、《回答》后来均收入陈梦家的《新月诗选》和闻一多的《现代诗抄》中。当时的评论是:
单就孙大雨的《诀绝》而论,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不绝的十四行诗,作者底手腕已有不可及之处,虽然因诗体底关系,节奏尚未能十分灵活,音韵尚未能十分铿锵。(梁宗岱:《论诗》,载《诗刊》1期)
孙大雨的商籁体的比较的成功,已然引起不少响应的尝试。梁实秋先生虽则说“用中文写sonnet永远写不像”,我却以为这种以及别种同性质的尝试,在不是仅学皮毛的手里,正是我们钩寻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的“字的音乐”(Word-music)的可能性的较为方便的一条路:方便,因为我们有欧美诗作我们的向导和准则。(徐志摩:《诗刊》2期前言)
十四行诗(sonnet)是格律最谨严的诗体,在节奏上它需求韵节在链锁的关连中最密切的接合;就是意义上,也必须遵守合律的进展。孙大雨的三首商籁体给我们对于试写商籁体增加了成功的指望,因为他从运用外国的格律上,得着操纵裕如的证明。(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
孙大雨在四十年代还有十四行诗发表。《遥寄》四首,发表在1943年8月7日重庆《民族文学》1卷2期和1943年12月《民族文学》1卷4期上。那时,孙大雨只身执教于西南大后方,而妻子却滞留在沦陷区的上海,“东西相隔着万水千山”,他的《遥寄》就是写给远方妻子的,把离别之痛扩展为民族之恨。以下是《遥寄》(之三):
杜鹃该已经漫山遍谷地殷红,
但今年在病里消磨了一半春荫,
不复有登临的逸致。杜鹃一声声
啼着“不如归”,可是遥望江之东,
淞之浦,寇氛正幂天扑地似的浓,
纵使有家怎得归?没奈何,向亲人
得传语道,“还是你西来,待明春
鸟蹄声里折山花,悲偕喜也同。”
别时方黄叶初残。日永如长年,
到如今一整度寒暑早已捱过,
山色再回青,春又韶华快要老。
可恨未荡平丑类,烧绝倭巢前,
(悭吝的飞行恐怖迟迟不西渡!)
只有你历尽了辛苦千重来的好。
千行十四行诗——李唯建的《祈祷》
李唯建1907年生于四川成都。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得到徐志摩的教诲,颇受英国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诗人的影响。已出版的有长诗《影》、《祈祷》和英文诗集《生命的复活》等。其中尤以《祈祷》这千行抒情十四行体长诗,更为现代诗史所罕见。
《祈祷》写于1929年1月12日至22日,出版于1933年6月(上海新月书店),原书封面标明“一千行长诗”。题为《祈祷》,容易让人感到似乎与宗教有关,其实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十分积极的:
你们问我为甚么要写这本书,为甚么题名《祈祷》?我答道:我向来不服从,除了真理,我决不祈祷,决不在鬼神面前跪着祷告:盲目的崇拜,服从,我是最怕的,怕的要死。在这里我须说明,我要的是宇宙的统一,最大主权,真理,神明,心中得不到他们,我便不欲生,不愿度这紊乱无纪的生活。因此,万分的虔诚,亿分的服从,无限的沉静,我来——来跪下仰天祷告,希冀天神早日赐我以最美丽的真理;这样,即得不着,我死,也是个美丽的死。
显然,诗人只不过是为了艺术构思的需要,借用了宗教的外衣,以表达其追求真理的主题。这里引第十五首为例,即可见全斑:
可是人们说真理并不在世外:
真理栖息在那最污浊的地方,
它在最黑暗和最愚凝潜藏,
它是不朽和永久的吼啸和鸣籁,
但是它有时也坐在白云霭霭,——
真理住在何方?真理住在何乡?
存在我们心中,发出无限光芒;
它能使一切的“不真”完全淘汰。
上帝从天堂遣使我来这世上,
原是叫我在这世上寻找真理,
叫我张开心容纳纷杂的万象,
我自当将我的精神完全振起,
拚命挣扎,如洪涛的泱漭澎荡,——
挣扎努力?可是,一个美丽的死!
如此积极的思想内容,并不因其被沉埋数十年而失去光华。在艺术上,诗人采用意识流情绪型结构,通过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展现出一种超时空的艺术境界,类似屈原《离骚》的手法和风采。
李唯建在写此诗时,也正是他与庐隐热恋之时。除了《云鸥情书集》中六十八封情书记载着他们恋爱的经过,以及长诗《影》在封面上就赫然印着“情诗一首献给庐隐女士”之外,在《祈祷》中围绕着热爱真理的主题,李唯建又不由自主地揉进了他对庐隐的爱恋:
你的来临并不是偶然的,我爱
我现在能碰见你,并非无原因;
冰凉的冬过了自然是那芳春;
我的呼吸永远住在你肺腑内,
我们前生便是一对相当佳配;
呵,爱,看我的嘴上有你的吟呻,
我的嘴唇还是说是你的嘴唇,
还是说是我的,我心里的姊妹;
不,不必这样;我们俩哪有分别,
问上帝他很知道我俩的关系,
谁不知道你的血里有我的血?
谁不看见我的眼能流你的涕?
爱情已经把我俩生死的连结,
我们的一生真可以说是美丽。
诗中全是真情实感的吐露,不假任何伪饰,适宜于用铺陈的写法一泻无余。
《祈祷》在形式上,诗人将十四行的意大利彼特拉克体和法国的亚历山大体融合起来,即段式和韵式用彼特拉克体的四四三三结构和ABBA ABBA CDC DCD的押韵方式,而每行的音节数却用亚历山大体的十二音。大约是依据汉语诗律是建筑在具有独立音节的方块字基础上,这种汉语的音节诗律体系,使诗人舍音步而采音节,也是探索新诗格律的一种途径。更难能可贵的是,全诗七十首十四行统一采取这种格式,无一例外,足见诗人的匠心和功力,这在中国现代诗史上亦属绝无仅有的。
关于《祈祷》,还要说明的是写作动机。一是感谢徐志摩的帮助登上诗坛。为此,李唯建特意在《祈祷》正诗前面写了题为《赠志摩》的一首(八行)序诗。他写道:“亲爱的好友,我深深谢你;请收下这些残缺的稿子。”李唯建还预言:“它们总有天会失了生存,但不朽的永是你之灵魂。”二是诗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祈祷》小序说:
我们像雨滴点从云端掉在地上,或像种子自地隙间钻出,我们从无论什么地方出来,我们所由来的地方无论如何不同,但我们的使命总是不异的。自呱呱坠地时起,我们在这干枯无味的世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已经固定了。我们不能似无舵的船,无尾的鸟,任凭风和浪的流荡飘漾的乱动;我们认清在世上的使命和责任,这才不算虚存世间空度一生。在二十年代那动荡不定的旧中国,诗人作为一个20多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十分可贵的。因此,他要寻求真理,实现理想,就成为写作《祈祷》的原动力,由此激发起澎湃的创作激情,非千行长诗不能尽意。
郭沫若与十四行体
1921年11月4日,郭沫若作《雪莱的诗》小引(载1923年2月《创造季刊》1卷4期,收入1926年3月上海泰东图书馆版《雪莱诗选》),郭沫若在“小引”中说:
做散文诗的近代诗人Baudelaire,Vemaeren,他们同时在做极规整的Sonnet和Aiexandrian……谁说既成的诗形是已朽骸骨?谁说自由诗体是鬼画桃符?诗的形式是Sein(存在)的问题,不是Soiien(应该)的问题。
郭沫若认为,极规整的Sonnet这种“既成诗形”不是“已朽骸骨”。在这一段时间里,郭沫若翻译了雪莱的十四行组诗《西风歌》,收入《雪莱诗选》。1925年,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小说《新时代》并写长序,《新时代》里有一类似主题歌的诗《遗言》,正是十四行诗。《新时代》的翻译,在郭沫若的思想发展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一生珍爱《遗言》,多次吟诵、修改。1925年3月24日傍晚,郭沫若还创作了一首德国式的宽式十四行诗,即《瓶》第三十六首。
1928年初,郭沫若写了十四行诗《牧歌》。当时他正被蒋介石通缉,避难在上海,大病初愈,心情也不好,正月二十八,他在日记中写:
“想改编《女神》和《星空》,作一自我清算。”
“看了方某给仿吾的信,十分不愉快。这些小子真是反掌炎凉。”
“晚入浴时博儿右膊触着烟囱,受了火伤,以安娜所用雪花膏为之敷治。此儿性质大不如小时,甚可担心。安娜的歇斯迭理也太厉害了,动辄便是打骂,殊人不快。”
这段日记反映了当时郭的处境和心情,而正是在这则日记中,郭沫若记下了十四行诗《牧歌》:
春风吹入我们的故乡,
姑娘呀,跳舞吧,姑娘。
我们向碧桃花下游行,
浴沐着那亲蔼的阳光。
你的影儿和我的影儿俩,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场上。
春风吹入了我们的草场,
姑娘呀,拥抱吧,姑娘。
小鸟儿们在树下颠狂,
蝴蝶儿们在草上成双。
空气这般地芬温暖洋,
含孕着醇酒般的芬香。
春风吹入了我们的心房,
姑娘呀,陶醉吧,姑娘。
诗描写牧场上一对恋人陶醉于春风中,情调清新明朗,同诗人那时的心境和处境形成鲜明的对照。
1931年4月29日,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又写了十四行诗《夜半》:
崎岖的寥寂的一条陇道,
夜半的狂暴的寒风怒号。
铁管工场底烟囱底顶上,
有蒙烟的一钩残月斜照。
北斗星高高地挂在天空,
斜指东北的斗梢摇摇欲动。
我们在陇道上并着肩走,
向着北方的一朵灯光通红。
“我的手,你看,是在这样地发烧。……
哦,你的冰冷,和我的却成对照。
让我替你温暖吧。”——“怕不把你冷了?”
我们在寒风中紧紧地握着两手,
在黑暗的夜半的陇道上颠扑不休;
唯一的慰安是眼前的灯光红透。
这又是一首情诗,抒写寒夜里彷徨于陇道上的一对情侣相互依傍,把“北方的一朵灯光”当作“唯一慰安”。
《牧歌》、《夜半》两诗同时发表在1932年11月上海《现代》杂志2卷1期。郭沫若写信给编者说:“这两首诗并列在这儿有点儿矛盾,但这个世界正是充满矛盾的世界,要紧的是要解除这个矛盾。我所希望的是在《夜半》之后有《牧歌》的世界出现。”这就揭示了两诗写恋情具有的象征色彩和政治意义,我们对诗可以理解为:《夜半》写的是诗人和他的朋友在时代的“夜半”时分,手紧握着手在陇道上颠扑不休地前进,而《夜半》过后的《牧歌》世界,当指祖国自由解放时代,诗以爱情的狂欢形象象征人民解放的狂欢境界。两诗同时发表,不仅在于都是十四行诗,而且把郭沫若在革命低潮期间的特定情绪表达得十分充分。
三十年代以后,郭沫若对十四行诗的看法出现反复。从他对十四行体的批评看,主要是他认为新诗不需要定型化,认为新诗的发展基础是中国古典和民间诗歌。
柳无忌的十四行诗
柳无忌是学贯中西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兼诗人,1907年生,江苏吴江人。他的诗作大多发表在二三十年代的报刊上,《抛砖集》是其仅有的一本诗集(桂林建文书店1943年1月出版,此书大多散失,连诗人手上也没有),共收诗三十九首,都是1927年至1942年间的作品。分三辑:第一辑全为十四行诗,收二十一首;第二辑标为“诗歌”,收九首,是各种新格律诗和半格律诗,形式多样;第三辑为“无韵诗”,收九首,齐言排列。书前有《新诗和旧诗——代序》,书末有《后记》。
柳无忌创作新格律诗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着意探索的结果。他在《后记》中说:“我历年来有一贯的信仰,以为诗须有固定的形式与体裁,而这数十首就是这个理想的实验。”他是在总结了新诗十余年的创作得失后,才作这番“实验”的。他说:“白话诗从旧诗解放出的初期,趋向于无韵无格的自由体,矫枉过正,走上另一个极端。这是革命的破坏的精神。破坏是建设之母,经过了这个混沌的阶段,在它的演进过程中新诗应能创造出一个自己的特殊的格调。我个人曾试着移植西洋诗体于新诗,尤其是十四行体,无韵体,及有韵分节的抒情短诗。十几年来写作时都以此为鹄的,因成此集。”
十四行体是其“尤其”努力“实验”的一种新格律诗体,因此在数量上占全集的半数以上。二十一首的题目是《读亚诺德(东与西)诗》、《怀诗人济慈》、《读师梨诗》、《嫦娥》、《题维纳斯石像》、《新生》、《冬宵》、《途中》、《纽约城》、《别情》、《爱的呼声》、《圣佛仑台恩的选择》、《择偶节》、《捉弄》、《伦敦的雾》、《死与爱》、《生死两镜》、《爱与家国》、《婚礼》、《病中》、《屠户与被屠者》。这些诗中,爱情诗占相当的比重,这里引《爱的呼声》:
快些来吧,我心爱的女郎,
快来投入我热情的胸怀,
让我们亲呢呢地永相爱,
紧紧地拥抱着不再释放;
听,听这两心相应的音浪:
我心爱的人儿,快点儿来,
这是你情郎呀在此呼喊,
这是他每天的唯一希望!
他望你立刻就现在面前,
用温存的笑语给他慰藉,
免却了徒然的相思无限,
在客地中得到些许甜蜜。
爱呀,别让那光阴蹉跎去,
最应爱惜的是青春良期!
从上诗可以看出,柳无忌的十四行诗直抒胸臆,热情澎湃,一泻无余,激动人心。所有的十四行诗都排列十分整齐,每行一律地十音节,基本上是四音步。前八行统一是两个抱韵即ABBAABBA。后六行的韵式则多变,此诗九至十二行用的是CDCD式,末二行用的是DD偶韵。不过诗人在押韵时,受家乡吴语方言的影响,如“来”与“喊”相押,“藉”与“蜜”相押,都不甚合辙。尽管如此,诗人倾心“实验”的努力,是不应被人遗忘的。
除爱情诗外,柳无忌有些十四行诗抒写国际题材,记下了诗人在美欧的见闻和感受,在中国十四行诗史上有开拓意义。这些诗的重要特点是把国外现代都市的描写与个人的特定心情结合,传达出现代观念。如《纽约城》不但具备西方现代城市诗所特有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而且把海外游子思念故国和亲人的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这批外国题材的十四行诗,实际上是一批海外游子的爱国诗。
柳无忌的十四行诗还有两首也值得注意。一首是《病中》,是诗人知道了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抒写的内心感受,充满着爱国激情。另一首是《屠户与被屠者》,表达了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忧患意识:
当世界是这般的颠倒疯狂,
人是烦闷懊丧,天空是灰阴,
风在狂吼,飞沙掩住了阳光,
阵阵吹来,夹杂的硫磺血腥;
忽然,在这团混沌中,显现出
操刀的屠户,霍霍的磨刀声;
一群被屠的羔羊,驯服,黯默,
束手等待着,漆黑黑的命运。
宰割的日期不是早经注上?
刀锋的锐利,刽子手的饱满:
眼看这无辜的被屠者,都将
牵上祭坛,献给杀人的好汉。
听着,霍霍的刀声,响了,愈近……
难道这群羔羊,没有一声嘶鸣?
诗写的是屠户宰羊,但诗注明“写于二五年四月十六日天津八里台,校外日军练习枪炮声砰砰有感”,这就使我们对诗有了新的理解。前四行渲染的不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是社会的背景。在那特定的年代,日寇在屠杀中国人民,诗人悲壮地呼喊:“听着,霍霍的刀声,响了,愈近……难道这群羔羊没有一声嘶鸣?”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这是用象征手法写成的政治抒情诗,情绪骚动悲越,同传统的十四行诗的平静进展不同,这在以前中国十四行诗中是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