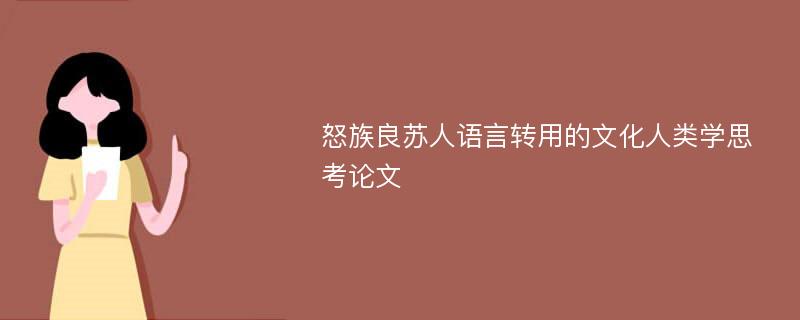
怒族良苏人语言转用的文化人类学思考
陈海宏1,谭丽亚2
(1.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云南昆明650500;2.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摘 要] 良苏人是怒族的一个小支系。长期与傈僳族相互杂居、良苏话的社会功能不断弱化等因素,使良苏人整体转用傈僳语。语言转用对良苏人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传统文化传承有重要影响。文化多样性是怒江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保护和传承良苏人的语言文化,既对构建多民族聚居区和谐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构建怒江地区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良苏人;语言转用;文化人类学
多民族杂居区的不同民族在长期族群互动和语言相互接触过程中,“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放弃使用母语而转用另一民族语言的现象称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1]一个民族的语言转用程度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持和文化认同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云南怒江州福贡县自称为“良苏”的怒族与傈僳族长期杂居,在相互往来的过程中,良苏人已经逐步转用傈僳语,属于整体语言转用的类型。良苏人的语言转用不仅是语言演变的现象,而且是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竞争在语言使用格局上的体现。本文拟就良苏人语言转用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思考。
数据的分类存储对提高系统开发、维护和系统管理的效率具有很大的作用。根据数据的分类进行存储进而产生数据库的组织结构,系统数据库主要由2部分构成。
一、良苏人概况
良苏人属于怒族的一个小支系,约有三千人,主要分布于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子里甲乡的甲怒、马祖底、甲打、腊母甲等村和架科底乡的架科、腊安甲等村。“良苏”的含义是从山那边迁徙过来的人,良苏人从澜沧江流域迁徙到福贡县子里甲乡一带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良苏人有自己独特的始祖神话:“相传,在很久以前,天神造了天,地神创了地,但甲怒大地没有人烟,后来天神创造了一男一女,取名为闷友西和闷有娣。闷友西和闷有娣结合后,生育九男七女,从此,就有了良苏人。闷友西和闷有娣就成了良苏人的始祖。”①
厦门是ABB在中国扬帆启航的起点,20多年前ABB在这里建立第一家合资企业,如今厦门已经是ABB在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产业基地之一。2014年ABB决定在厦门投资20亿,在翔安区建立工业中心,2018年11月工业中心落成仪式,园区的8家工厂全面应用ABB AbilityTM智能化数字解决方案,打造ABB最先进、最大的制造生产基地。
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的论述中也有所提及。由于冷桥现象的存在,导致外保温复合墙体在进行热传导的过程中,部分热量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难以完成快速的传导,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热能损失的情况,从而导致建筑使用会有较大的能耗。
良苏人的始祖神话传说与怒族其他支系的始祖神话不一样。良苏人主要生活在碧罗雪山的半山坡上,其传统民居是“千脚落地房”(竹篾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很多良苏人住上了现代小洋楼。传统服饰方面,良苏传统服饰与傈僳族传统服饰接近,男性服饰是对襟麻布衣上衣和长裤,女性服饰是紫色右衽上衣和麻布长裙。饮食方面,主食以玉米和荞麦为主,蔬菜以洋芋、豆类、瓜类为主。婚俗丧葬方面,良苏人是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喜欢自由恋爱,良苏人在婚礼上要吟唱《婚礼歌》;良苏人很久以前盛行火葬,现在主要是土葬。宗教信仰方面,良苏人信仰传统宗教,认为万物有灵,而且至今保留着各种祭祀神歌;基督教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怒江地区后,良苏人逐渐信仰基督教,目前每个村委都建有教堂。交通方面,良苏人居住的村寨以前不通公路,各种生活物资运输都依靠人背马驮,近年来已经修建了通往怒族村寨的公路,许多良苏人购买了摩托车,有的人购买汽车参与运输。
与其他怒族支系的语言相比,子里甲乡良苏人的母语良苏话与怒苏语较为接近,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良苏人与怒苏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存在较大障碍。在《怒族简史》《怒族社会历史调查》《怒族文化史》等与怒族相关的文献中,学者们很少提及良苏人。子里甲乡的良苏人和匹河怒族乡的怒苏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归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县管辖(该县于1986年被撤销),因此,学者们主要将良苏人归为怒族怒苏支系,但是根据笔者调查,良苏人并不认同自己属于怒苏支系。
二、良苏人语言转用状况
良苏话是良苏人的母语,学界一般将其划归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良苏话属于极度濒危语言,主要保存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子里甲乡甲怒村,甲怒村现有1031位怒族人,是良苏人的主要聚居地。良苏人长期与傈僳族人相互杂居,目前,良苏人已经整体转用傈僳语。笔者和课题组其他成员自2014年至2017年先后五次到子里甲乡进行调查。从良苏人的年龄看,良苏人语言转用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老年人
这是家庭中最长的一辈,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甲怒村有220位良苏人达到六十岁以上的年龄。在良苏人寨子,六十岁以上的良苏老人之间可以使用良苏话进行交流,日常生活中则主要使用傈僳语同晚辈交流。根据我们的调查,由于很长时间不讲良苏话,部分老人需要思考一会才能用良苏话与人交流。我们调查的良苏老年人的语言使用特点是在日常交际中能够熟练使用傈僳语;汉语水平整体比较低,甲怒寨子里有很多老年人不会说汉语。
(二)中年人
良苏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傈僳族、白族、汉族等先后迁入怒江地区,良苏人善于向周边民族学习,他们向傈僳族学习制作铁器的技术,向白族、汉族学习牛耕技术。这些生产技术促进了怒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国时期,怒江地区出现了十多个初级市场,良苏人经常在农闲时走出寨子,将黄连、蜂蜜、兽皮等山货带到集市上出售。傈僳语是怒江地区的通用语,良苏人为了生计需要,就用傈僳语与其他周边民族交流。20世纪80年代之前,怒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怒族、傈僳族许多青年人都不会讲汉语。近三十年来,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和广播、电视的普及,良苏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良苏人走出怒江村寨,到六库(怒江州府)、大理、昆明等地学习、工作,良苏人又逐渐兼用汉语。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对良苏人语言转用的影响虽然是潜在的,却发挥着实质性作用。
煤层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是最重要的瓦斯参数,其大小和突出危险性密切相关,也是进行煤层突出危险性区域预测和区域防突措施效果检验的关键指标,工作面前方煤体的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可作为预警的重要指标。综合上述,瓦斯地质预警指标体系如图3所示。
(三)青少年
这是良苏人中年轻的一辈,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甲怒村有424位良苏人属于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良苏人的母语已经不是良苏话,他们从小就习得傈僳语,傈僳语成为年轻良苏人的母语,他们也听不懂本民族语言良苏话。年轻的良苏人大都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有些年轻人在乡镇工作,有些人在外地打工,还有一部分在各级学校读书。随着怒江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电视、智能手机等现代传媒对良苏人的社会生活影响也越来越大,年轻良苏人的汉语水平普遍较高。青少年良苏人的语言转用特点呈混合型,不仅能够熟练使用傈僳语,而且能熟练使用汉语。
三、良苏人语言转用的原因
傈僳族进入怒江地区之前,良苏人主要使用自己的母语良苏话,那时处于单语使用阶段。到清末民国时期,傈僳通古宗、怒子语者绝少,傈僳语则“全境通晓,尽人皆知”[2]。我们由此可知,此时良苏人已经处于使用双语时期。目前,六十岁以上的良苏老人还能够使用良苏怒语,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良苏人处于使用双语阶段,在使用自己母语的同时,傈僳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良苏人的语言生活中,良苏人的母语代际传承开始出现断层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良苏人逐渐整体转用傈僳语。
福建省部分城区儿童家长与儿童安全用药相关的认知、态度及行为调查与分析 ………………………… 林津晶等(12):1594
(一)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而且具有文化认同功能。“学界一般认为文化认同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等。”[4]文化认同不仅包括对本族文化的认同,而且包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语言转用与文化认同关系密切,一个民族转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过程,也是文化认同的过程。文化认同在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增进民族交流、增加民族认同感、促进多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1.良苏人传统文化的脆弱性
良苏人的数量非常少,主要以村寨的规模聚居。怒江地区山高谷深,交通极为不便。长期以来,良苏人的社会经济仍然保留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模式和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模式,与之相适应的是崇拜自然、万物有灵的传统宗教信仰和明显带有血缘色彩的氏族文化。良苏人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良苏传统文化存在的基础相当薄弱,面对强势外来文化的冲击时,良苏传统文化抵御能力不强,文化修复能力很弱,良苏传统文化难以保持。
2.良苏人的“傈僳化”
在政治方面,良苏人长期受傈僳族统治。傈僳族自从进入怒江地区后,势力逐渐强大,傈僳族不断强占怒族的土地。民国时期,傈僳族管理着怒族各村寨的赋税和一切行政事项:“怒人每有事务必与傈僳协商。有诉讼者,必求傈僳头目排解之;有疾病者,必请傈僳‘尼扒’除之。”②因此,傈僳族在政治方面的强势为文化上同化良苏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物质文化方面,清代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载:“怒子,男女披发,面刺青文,首勒红籐,麻布短衣,男着裤、女以裙,覆竹为屋,编竹为垣。”由此可见,良苏人在清代乾隆时期仍然保留浓厚的传统文化特征。后来受傈僳族强势文化的影响,良苏人不仅在服饰和建筑方面,而且在生产方式和饮食起居等方面,都与傈僳族逐渐趋同。
在精神文化方面,宗教信仰是良苏人传统文化的核心,宗教信仰的变迁是良苏人语言转用的重要原因。良苏人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信仰万物有灵,良苏人患病时经常采用祭鬼的方式进行治疗。基督教传入怒江地区后,《圣经》《赞美歌》等典籍都是使用老傈僳文翻译的,而且信徒祈祷、唱圣歌都使用傈僳语。良苏人大都信仰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就必须认识傈僳文、会说傈僳语。“基督教的传入,使傈僳族、怒族基督教徒有了共同的宗教文化生活,促进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怒族对傈僳族文化的认同。”[3]因此,宗教信仰的变迁是良苏人转用傈僳语的重要原因。
肇庆市政府指定疏浚物处理项目由肇庆市国资委管理,肇庆市国资委委托城投公司组织公开招投标。最终,方少瑜名下的广州市安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约6500万元中标。
(二)怒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是家庭中的第二代良苏人,年龄在三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甲怒村有387位良苏人属于这个年龄段。中年良苏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使用母语良苏话,但是能够听懂一些良苏话。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傈僳语,同时兼用汉语,傈僳语水平明显高于汉语水平。甲怒村不少良苏中年妇女略懂汉语,即不太会说汉语但是听得懂一些汉语。从整体上看,中年良苏人已经不会使用自己的母语了,而且他们的傈僳语水平明显高于汉语水平。
(三)良苏话社会功能的局限性
语言具有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的双重性:“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其根本意义在于人类在创造了语言这种符号系统的同时,又借助于它来保证自己更有效的生存和发展。”[5]文化认同在文化存在的状态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在历史上,良苏话通行于福贡县子里甲乡的甲怒、马祖底、甲打、腊母甲和架科底乡的架科、腊安甲等村寨怒族人民之中,交往十分便利。”③良苏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族群文化,具体表现为:有独特的族群起源传说《闷有西和闷有娣》;有本族群的语言良苏话;有古老的制陶技术,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委加车组良苏人保留着传统的制陶技术,生产土锅、土盆、土碗、土罐等各种陶器,销往维西、兰坪,乃至缅甸各地;有独特的乐器和民间歌谣,良苏人的乐器有“达杓”(琵琶)和“佳汪”(口弦),民间歌谣有《流浪歌》《婚礼歌》《教儿育女歌》等;有传统宗教信仰,良苏人有自己的巫师,保留着古老的祭祀神歌等等。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良苏人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等传统语言文化随着良苏人语言转用而失去了承载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消逝。由于语言转用,良苏人不知道本族群的传统节日如何用良苏话表达,大部分良苏人都信仰基督教,良苏人的传统宗教信仰也不断被弱化。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转用意味着良苏人对良苏传统语言文化认同感在不断弱化。
四、良苏人语言转用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一)语言转用与良苏人的文化认同
由于傈僳族人口数量多,分布广泛,傈僳族逐渐成为怒江地区的强势民族。在与傈僳族的长期互动过程中,良苏人受到了傈僳族文化的深远影响,这是良苏人语言转用的基本动因。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转向了更有侵入性的方法,譬如去除表面的一些组织或直接向脑中刺入微内窥镜这种微小的光学仪器。另一种非入侵性的替代方法,可以观测1毫米内的不透明组织,称作双光子显微镜。这一技术使用更长波长、更低能量的光,能够深穿入组织。由于双光子显微镜一次只能照射并记录一个点,捕捉图像的速度过慢而跟不上脑中快速的电位变化。但专家们相信技术的进步将很快使人们看清GEVIs产生的信号。吉娜表示:“这绝对可行。”
1.语言转用体现了良苏人对传统民族文化认同的不断弱化
良苏人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还使用傈僳语和汉语,这三种语言的使用场合和社会功能不同。在村寨和家庭里,良苏人主要使用良苏话。在乡镇集市上,良苏人主要使用傈僳语与傈僳族、白族等民族交往;在教堂内,良苏人使用傈僳语祷告、吟唱圣歌。在怒江地区各级学校和现代传媒等场域,良苏人主要使用汉语。由此可知,傈僳语和汉语使用场域广泛,社会功能非常强大,并且已经深入良苏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良苏话被良苏人用在家庭内部,使用场域最小。随着怒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良苏话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弱,良苏人逐渐放弃使用自己的母语良苏话,逐渐转用傈僳语和汉语。
2.语言转用反映了对外来民族文化认同的不断强化
良苏人与傈僳族长期交往,良苏人对傈僳族文化认同不断强化。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本族群与其他族群相互交往的重要工具,一个族群的语言转用情况反映了本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对傈僳族文化的高度认同,逐渐引起良苏人传统文化的变迁。
在宗教信仰方面,良苏人的传统宗教信仰有自己的巫师和祭祀神歌等,随着基督教传入怒江地区,良苏人和傈僳族人大都信仰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怒族群众不再被允许信仰怒族传统宗教信仰,不允许参加传统宗教祭祀活动,良苏传统宗教信仰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良苏人语言转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语言使用方面,良苏人已经整体转用傈僳语,傈僳语成为年轻良苏人的母语。
在传统节日方面,良苏人和傈僳族的年节都称为“阔什”(傈僳语),也过圣诞节等节日。可以说,从房屋建筑到饮食起居,从传统服饰到民族节日,从语言运用到宗教信仰,良苏人的民族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大体和傈僳族趋于一致,良苏人已经逐步“傈僳化”。走进良苏人的村寨,我们很难感受到良苏人的独特文化,良苏人整体转用傈僳语,除了他们自称为“良苏”外,我们已经很难区分良苏人和傈僳族人。文化认同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又是良苏人与傈僳族长期的互动过程,也是良苏人对傈僳族文化认同不断增强的过程。
(二)语言转用与良苏人的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6]。民族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宗教和语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民族认同心理的改变和认同范围的扩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而改变的。”[7]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认同的主要依据,民族语言是民族交际的重要工具,是民族成员之间交流信息、传承文化、维系民族认同感的媒介,因此,弱小族群可以通过语言来增强自己的民族认同。
电脑上的照片并不清楚,但仍能看清那个瘦小的女孩儿有一双清亮的眼睛,万姐坐在电脑屏幕前仔仔细细地看着,毫不掩饰地哭了。晚上,我把打印好的照片拿给她,她仍然显得有些激动,爱惜地抚摸着,就像在抚摸女儿的头发。
语言认同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被认为是最稳定、最不易变的因素。语言转用是影响弱小族群民族认同的重要前提。良苏人和傈僳族都信仰基督教,在语言上整体转用了傈僳语,良苏人的语言转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散居的良苏人的民族认同。良苏人数量很少,属于弱小族群。部分散居的良苏人在与傈僳族杂居的环境中明显处于弱势,为了自身的生存,不认同为怒族,而认同为傈僳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良苏人转用傈僳语,给部分良苏人的民族认同为傈僳族创造了前提条件。良苏人整体转用傈僳语,而且长期与傈僳族人相互往来、相互通婚,也给部分良苏人认同为傈僳族创造了条件。良苏人在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等方面与傈僳族的差别逐渐缩小,有的良苏人就认同自己为傈僳族了。语言转用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弱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也有利于弱小民族自身的生存发展。我们在怒江地区调查发现,部分怒族人认同自己为傈僳族,部分白族人认同自己为傈僳族,这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也是弱小族群自身生存的重要方式。
(三)语言转用与良苏人的文化传承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身份和心理认同的主要标志。如果一个族群没有自己的语言,那么这个族群将无法传承特有的族群文化,族群的特性将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消亡。良苏人的语言转用对良苏人传承本族群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传承良苏人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良苏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的本质是人们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依据文化发展规律进行文化保护、文化传承与文化创造的过程。”[8]良苏人只有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才能为自身语言文化传承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
良苏人已经认识到了传承本族群语言文化的重要性,没有良苏话,良苏人的传统文化将失去存在的依托。为了保护极度濒危的良苏话,在良苏人退休干部叶世富先生的带领下,自发保护、传承良苏话的“《甲怒良苏怒语》编委会”成立了。没有专家学者的指导,良苏人就自发动员起来,开展对良苏话的搜集整理工作。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编委会搜集整理了五千余条良苏话词语以及良苏人的一些祭辞、谚语等,并用老傈僳文分门别类记录下来。在怒江州各级政府的关怀下,良苏人终于在2007年出版了用老傈僳文记录良苏话的《甲怒良苏怒语》。良苏人大都信仰基督教,大都能够认读老傈僳文,《甲怒良苏怒语》的出版,有利于良苏人学习、使用良苏话,有利于良苏人后人对良苏人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013年,带有圆筒阀的单机容量世界最大的溪洛渡水电站机组投运发电;向家坝水电站80万千瓦机组投入商业运行,刷新了单机容量世界最大水电机组的纪录;同年,首台国产AP1000核电站所采用的1407兆伏安核能发电机制造成功。
结语
怒江地区是傈僳族、怒族、白族、汉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多元文化的和谐与交融,促进了怒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良苏人与傈僳族长期杂居、相互通婚,逐渐转用傈僳语,傈僳语已经成为良苏人的母语。良苏人的语言转用说明他们对自身传统语言文化认同的不断弱化,影响了良苏人的对自身传统语言文化的认同。因此,加强良苏人的文化自觉意识,保护和传承传统良苏人的传统语言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在多民族聚居的怒江地区保持多元语言文化,有利于怒江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有利于促进怒江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注 释]
①叶世富《心灵的赞歌》,见怒江州文化局2013年内部资料,第85页。
②张征东《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见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6年资料,第190页。
③甲怒良苏怒语编委会《甲怒良苏怒语》,见怒江州文化局2007年内部资料,第1页。
[参考文献]
[1]戴庆厦,王远新.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J].语文建设,1987,(4):13—17.
[2]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第四册)·卷七十·方言考五·怒子古宗栗粟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36.
[3]高志英.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19.
[4]陆学杰.文化认同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J].广西社会科学,2009,(7):84—87.
[5]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论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181.
[6]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17—21+92.
[7]江承凤.新疆多元语言文化互动下的民族认同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1,(6):239—243.
[8]王林平.对文化自觉本质的思考[J].学术交流,2017,(10):85—88.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19)05-0025-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云南濒危怒语良苏话的抢救性记录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5XYY02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海宏,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言人类学;谭丽亚,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人类学。
[责任编辑 高 宇]
标签:良苏人论文; 语言转用论文; 文化人类学论文;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论文;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