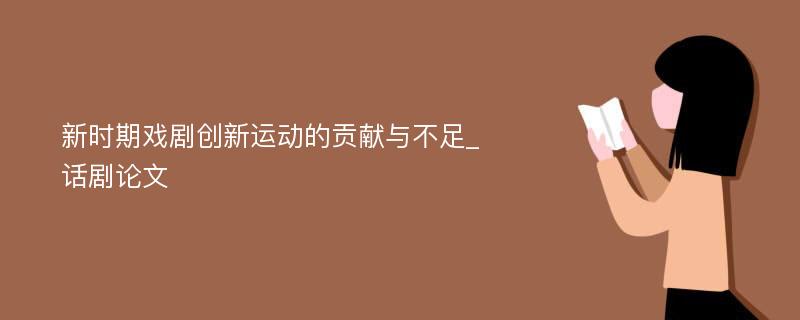
新时期话剧革新运动的贡献及其不足和纰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纰缪论文,话剧论文,新时期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新时期话剧革新运动”这个概念的运用,有个时间的规定性,即:它的上限是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限是本世纪80年代末。本文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是在这个时间段里中国话剧的革新运动,但因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前因后果,所以必要时也会向两头延伸。
现在,当我们站在本世纪末的最后时刻,回过头去观照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国话剧所经历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的时候,绝大多数戏剧圈内的人士都会毫无疑问地认为:这是我国话剧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则是以“探索戏剧”的出现为标志的。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这股革新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果把它的尾声都算在里面的话,前后持续了有十年之久。在这一浪潮中,诞生了一大批以艺术探索为旗帜的剧作和舞台艺术作品。它们被统称为“探索戏剧”。这一浪潮,无论是从它的气势、规模来看,还是以它的实绩、影响而论,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它是我国话剧史(乃至我国整个戏剧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戏剧革命。戏剧界应该为有此次浪潮的出现而感到自豪。
从在革新浪潮中出现的戏剧观论争及其艺术实践本身来考察,这次运动的直接目的,乃是要突破我国话剧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以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为剧作模式,和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写实主义——幻觉主义演剧方法为舞台艺术创作模式的大一统局面。回顾这段历程,可以肯定地说,它所追求的这个直接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它的影响力、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则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有了这次革新运动,我们才结束了原有那个一种戏剧观念、一种创作模式延续了几十年的单调划一的话剧时代,开创了一个从戏剧观念、美学法则到创作方法、演剧形态等等,都是开放的、多样的、更富于表现力的,因而也更富有生命力的话剧新时代。
当然,像任何一个事物一样,有正面就会有负面。因此,这场革新运动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不管是正是负,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财富。所以,我们今天来总结它的历史性贡献和曾经出现的不足或纰缪,是一件于今于后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革新运动的历史性贡献
新时期的话剧革新运动,其历史性的贡献,犹如它的规模和冲击力一样巨大。这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获得验证。
第一,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高度,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戏剧的本性,并在实践中发展了这种本性。
戏剧自从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以来,虽然它的本性在不断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并在不断地发展,但它的一些基本的本性是早就形成并且是永恒的。这些基本的本性是:作为活人的演员的精湛表演;观众和演员之间的活生生的交流;舞台的假定性法则等等。任何一个戏剧品种,都少不了这几种本性。话剧也不例外。但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对戏剧的本性的认识存在着差异性。因此,在如何实践和发展戏剧的本性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表现。拿我国话剧在80年代前与80年代后的情形相对照,就会发现这种明显的差别。80年代前,由于各种原因,形成了我国话剧在舞台艺术创作上独尊写实主义——幻觉主义一家,排斥其它流派的单一局面。而这一流派,在它的戏剧观念、戏剧美学中,在它强调制造逼真于生活的舞台幻觉的原则下,对待戏剧的本性持一种较为谨慎、保守的态度。其表现有三:一、尽管对于戏剧来说,舞台假定性是回避不了的,但它却仍要想方设法用逼真的写实形式将其掩盖起来;二、在演员的演技方面,强调要在舞台上“真实地生活”,反对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因此,与现实生活相近似的“生活化”表演,便成了演员不可逾越的法规;三、由于上述两者的规定,致使在舞台演出中只允许角色与角色之间可以进行直接交流,而坚决不允许演员与观众、角色与观众之间有直接交流。由此可见,在80年代以前,由于我国的话剧所遵循的是模仿生活的戏剧观念和美学法则,因此在对戏剧的基本本性的认识和实践上,形成了它自己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当然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但是,长期囿于这一种规定性而排斥其它,对戏剧的发展显然是有较大的局限性的。我国话剧在80年代以前的发展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戏剧基本本性的认识和实践,还存在着别的规定性。例如,古希腊戏剧和中国的传统戏曲,以及20世纪西方各种现代派戏剧,都公开承认和乐于利用舞台假定性;公开承认舞台是表演的场所,演员在舞台上是进行“表演”,而不是要求演员要像现实生活那样去“生活在舞台上”;在演出中,除了要有角色与角色之间的直接交流之外,还允许和乐于发扬角色与观众、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活生生的直接交流。这种对戏剧本性从认识到实践的规定性,乃是一种非写实主义——非幻觉主义的规定性。它无疑也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而且,比起前一种规定性来,它较少自我限制,自然会更有利于戏剧艺术的发展。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我国一大批锐意出新的话剧艺术家,在重新审视了人类戏剧的发展历史以后,认识到了对戏剧的本性可以有多种规定性,而不是只有一种规定性。即:既可以有写实主义——幻觉主义流派这样的规定性,也可以有非写实主义——非幻觉主义那种流派的规定性,甚至还可以创造性地将写实主义与非写实主义、幻觉主义与非幻觉主义相结合,在对逆杂交中确立一种新的规定性。由于认识的拓展,观念的解放,新时期的“探索戏剧”在怎样利用和发挥舞台假定性,怎样利用和发挥活人(演员)的精湛表演,怎样利用和发挥角色与观众、演员与观众的活生生的交流这诸种优势方面,作出了属于它自己的、也是属于时代的选择。其剧作和演出,都放弃了纯粹写实主义——幻觉主义的规定性,选择了另外两种规定性。尤其是对写实主义与非写实主义、幻觉主义与非幻觉主义相结合的规定性的选择,则更是一种富于现代意义的革新和创造。写实与非写实(写意)、制造幻觉与破除幻觉,乃是戏剧本性发展中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的产物。而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广阔的中间地带。在这块“中间地带”中,写实与非写实(写意)、幻觉与非幻觉,两者正可互相结合起来。而且,结合的比例和方式可以千变万化。因此,在这类结合中,戏剧的本性也可随之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变奏曲。在80年代的“探索戏剧”中,这种结合型的作品占据了很大比重,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类话剧的出现,正表明我国新时期对戏剧本性有了更为宽阔和更为深入的认识。这对我国后来话剧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90年代话剧艺术的发展中,已经得到了印证。当然,新时期话剧革新运动对戏剧本性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显然是受到古希腊戏剧、中国戏曲和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启发。但是,它毕竟是我国话剧界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高度,利用现代人的知识水平、现代人的认识能力、现代人的技术力量而作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最新选择。因此,从总体上看,这种发现和认识,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挥,既不是对古代戏剧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对西方现代戏剧的盲目照搬,而是在现代社会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下,在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的基础上,对戏剧本性的一种新的发展和提升,是我国当代戏剧新思维的具体表现。不过,也必须指出:它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写实主义——幻觉主义话剧流派的否定,而是在现代意义上对话剧流派的丰富和拓展。这一点,也已为我国90年代话剧的发展状况所证实。
第二,推动了我国话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性转换。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是人类戏剧的大转型时期。欧美戏剧,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已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型”戏剧向“现代型”戏剧转型的历史任务。写实戏剧在它的发祥地已不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非写实的戏剧则成了时代的主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我国新时期所掀起的话剧革新浪潮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认识,即:这股浪潮揭开了我国话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的序幕,吹响了这种转型的号角。所谓话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话剧的现代化。曾记得,80年代初,戏剧界围绕着话剧要“民族化”还是要“现代化”的问题,开展过一场大讨论。当时的情势,几乎一致认为“现代化”是话剧发展的当务之急。呼声之强烈,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看来,这是大趋势。而这其间整整十年的话剧革新运动,确实是直奔这个方向而去的。首先,通过这场革新运动,现代戏剧观念已初步确立起来。“现代戏剧观念”,乃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它不仅包含了对戏剧本体的新认识,也包含了宽广的戏剧美学思想和宽广的戏剧文化内涵。它的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和包容性。我国以往话剧的戏剧观念,内涵比较狭窄,排他性强,其基本特征是封闭性和单一性。它推崇在舞台上制造“第四堵墙”的美学思想,因而形成了写实主义——幻觉主义话剧艺术几十年一统天下的停滞局面。新时期戏剧革新浪潮中出现的“探索戏剧”,打破了原有观念上的封闭性、单一性和排他性。如上所述,戏剧革新家们从对戏剧本性的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中扩展了艺术视野,从而认识到:写实主义——幻觉主义戏剧观并没有穷尽戏剧的真理。戏剧观念既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写意的,还可以是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因此,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不仅写实话剧仍可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其它各类非写实的话剧,诸如“写意话剧”、“大写意话剧”、“音乐歌舞话剧”、“歌舞故事剧”、“现代寓意剧”等等标新立异之作,均应运而生。话剧的美学思想、美学精神得到了大解放,话剧的文化内涵获得丰富和拓展。这就形成了容纳百家、多元发展的现代戏剧观念。这是我国话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性转换的基本点。
其次,创作方法也不再一花独放。过去,对于话剧来说,我们只承认现实主义一种创作方法。除此之外,别无分店。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不断地介绍进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包括现代派戏剧)。理论界有人称它们的创作方法为“泛表现主义”方法。我国的“探索戏剧”,受其影响不小。其中有些作品,例如《车站》、《野人》、《屋里的猫头鹰》、《蛾》等等,其创作方法显然已脱离了传统现实主义而走向“泛表现主义”。当然,大部分“探索戏剧”,例如《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中国梦》等等,则可以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同时又吸收、融合了“泛表现主义”的因素。它们既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精髓,又具有一定的“泛表现主义”色彩。创作方法上走向多样化。这种局面的出现,自然与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但反过来,它又成为我国话剧向“现代型”转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审美感觉、艺术思维、表达方式趋向现代化。话剧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最直观、最具体的一点,是要在审美感觉、艺术思维、表达方式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具体而言,要做到四个“符合”:一要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二要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三要符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现实时空相对缩小,心理时空相对扩大);四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心理需求。从新时期“探索戏剧”的艺术实践来看,已在朝着这方面努力去做。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一、审美注意的焦点,由侧重于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再现,转为侧重于对心灵世界的表现。话剧的革新、探索,从一开始起,在它对自己的表现对象——“人”——进行审美观照时,就对其心理活动、心灵轨迹、内心奥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时的理论界将这种现象称为“向内转”或“内向化”趋势。戏剧家们尽力革新传统话剧原有的艺术手段、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他们喜欢运用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常用的一些方法和手法,将人物虚幻、飘渺、空灵、稍纵即逝的内心活动(包括意识和潜意识),化作可感知的物化形态,转变为鲜明、生动的舞台直观形象。这就拓宽了戏剧对表现现代人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表现力,也适应了现代观众热衷于探寻人物心灵秘密的审美欲求。二、在审美意蕴上,追求哲理象征。现代艺术大多讲求包蕴较为深广的哲理内涵,而象征恰恰能成为作品的哲理内涵较为理想的载体。所以,话剧革新家们,把对“哲理象征”的追求,也视为话剧艺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探索戏剧”对“哲理象征”这一艺术方法和艺术手法的运用,大体上包括局部性和整体性两种。局部性哲理象征的作品比较多见。这是因为,突破了传统话剧纯粹写实的表现方法,结合进了写意的方法之后,更适合于象征手法的滋生和哲理意蕴的翱翔。但是,局部性的哲理象征其意义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努力创造出整体性哲理象征的艺术形象,以便蕴涵和传达更深邃隽永的哲理内涵,自然是革新家们所渴求的更高目标。于是,在“探索戏剧”中出现了“寓言象征”、“生活本体象征”的艺术表现方法,创造出了诸如《车站》、《挂在墙上的老B》、《蛾》、 《二十岁的夏天》等这样一些属于整体象征的剧本和舞台演出。它们以某种“哲理象征”作为艺术意象,以此从总体上结构剧情,塑造形象,使作品从现实层面升华至诗情哲理的层面。三、表述方式由冲突型变为叙事型。“探索戏剧”不再严格地遵循“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的戒律。它们独辟蹊径,以散文诗式的情绪结构取代事件集中的冲突结构,以意境的艺术魅力取代悬念的吸引力。它们大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不设置贯穿全剧的中心事件,也不组织一个全局性的戏剧高潮;不分幕不分场只分段,每段长短不拘,可伸可缩,基本上是一段叙述一件事,段与段之间、事与事之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情节的跳跃性大,内容的容量也因此而扩大;叙事文学特有的夹叙夹议的手法,往往也被大胆采纳。这种由冲突模式向叙事模式的变化,也是对传统型话剧的一大突破。以上这几项艺术革新、艺术探索(当然不只是这几项,这里只是择其要者而言之),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现代人的审美感觉、艺术思维和艺术表达方式的具体特点。它们使我国话剧走向快节奏,走向立体化地表现生活、表现人,走向审美功能的多样统一(审美功能不再单一和纯粹,即不再只讲求娱乐性而不讲求其它,只讲求情感共鸣而不讲求其它,只讲求理性思索而不讲求其它,而是将各种功能有机融合,达到审美功能“多样统一”的境地)。
由此可见,新时期戏剧革新运动,对我国话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给我国话剧业已蜕化了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击一猛掌,使其不再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乃至倒退。我国的话剧艺术,是有着较为深厚的、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这种传统,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而由曹禺、夏衍、田汉等先生的作品奠定其基础。但是,在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并没有始终不断地得到健康的发展。尤其是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一段时间里,在“左”的和极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这一现实主义传统或已经衰退,或几乎已经蜕化变质,沦落为“庸俗社会学”的现实主义、“假、大、空”的现实主义、乃至伪现实主义。“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初期,“社会问题剧”模式的现实主义话剧得以恢复,轰动一时。但是只持续了两三年便一落千丈地衰微了。观众都不爱看这样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戏了。这些现象说明,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话剧剧坛上的现实主义,已经自我蜕化、自我封闭而失去了生命力。其实,这也就成为促使新时期戏剧革新运动的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正是这新时期的戏剧革新运动,反过来又给这正处在岌岌可危之际的现实主义击了一个猛掌,致使它有所醒悟,开始摆脱自我封闭状态和自我停滞状态。这主要表现为:首先是使它回过头去,返观自己的优良传统,从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真正内涵。戏剧家们从曹禺、田汉、夏衍等先生的作品中从新认识了现实主义的精髓,即:真正的现实主义,它应该是能够深刻地把握社会生活的底蕴,塑造出活生生的然而又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并以深入地刻画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为其审美重心,又要能够以生动的感性形式赋予自己的独特内容;与此同时,在同西方现代戏剧文化的撞击中,戏剧家们也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现实主义也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吸取别的创作方法的长处,丰富和发展自己。经过这样的调整,到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的现实主义话剧终于又出现了既有像《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这一种类型的,也有像《黑色的石头》、《天下第一楼》这种类型的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现实主义话剧的生命力又开始活跃起来了。1995年杨利民的力作《地质师》的问世、姚远的历史剧《商鞅》的演出,再一次有力地证实了这一事实。
第四,为东西方戏剧文化的交流架设桥梁,促进了中国戏剧文化的现代化。
从20世纪西方戏剧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来看,它在20年代至50年代,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曾受到过中国传统戏曲的深刻影响。前苏联的梅耶荷德、德国的布莱希特、英国的戈登·克雷等一大批推动西方戏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的革新大师们,都无不从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原理、美学思想,特别是它的写意特性和舞台假定性中,获得过很大启发,吸收过丰富的养料。时至80年代,历史来了个轮回。当我们把国门敞开之后,我国的话剧首先受到了来自西方现代戏剧文化的强烈冲击。西方现代戏剧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艺术手法,普遍成为我国话剧革新家们效法的对象。这一历史现象,可以说是曾经受过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哺育过的西方现代戏剧文化,对中国当代戏剧文化的反哺。这种“反哺”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话剧,而且也通过话剧而辐射到了我国的传统戏曲。在这一过程中,话剧则充当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把目光既投向西方的现代戏剧,同时又返观我国的传统戏曲,从两者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养料。因此,它是西方现代戏剧文化和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直接融合者和受惠者,由此加速了它自身的变革;另一方面,它又以沟通中西戏剧文化的桥梁的身分向传统戏曲传递着西方现代戏剧的新思潮、新信息,从而也促进了我国戏曲的自我革新,使其由“古典型”向“现代型”转换。这一点,已经由80年代出现的具有探索性特点的戏曲作品和90年代戏曲整体面貌的新发展,得到了证实。当然,西方戏剧,也十分自然地通过这座“桥梁”,不断地获取我国戏剧(包括话剧和戏曲)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信息、新养料。由此可见,新时期话剧革新浪潮所起到的沟通东西方戏剧文化的“桥梁”作用,不仅对于话剧自身,而且也从总体上推进了我国戏剧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戏剧汇入了世界戏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的时代大潮。
革新运动的不足和纰缪
我国新时期的话剧革新运动,确实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不足和纰缪。归纳起来,大抵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如何正确地对待戏剧发展的“他律”和“自律”及其相互关系上,还未完全达到自觉地把握和裕如地驾驭的境地。
我国新时期掀起的话剧革新运动,乃是由它的“他律”和“自律”两股力的合力推动而产生的。所谓“他律”,即是外部规律。也就是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社会的开放改革所带来的历史大转折,促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全面而又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话剧艺术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因而,促使话剧产生了要以自身的变革来适应已经变化和还在继续变化着的外部生存环境的自我要求。所谓“自律”,即是内部规律。也就是说,与“他律”在发生作用的同时,话剧自身的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运动,也在促使话剧不得不发生自我变革和自我更新。这是因为,新时期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给话剧提供着无穷的新内容。戏剧家们对戏剧艺术如何观照生活和如何反映生活,也在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审美认识和新的审美视角。而这一切,与传统话剧原有的戏剧观念、表现形式之间,发生了深刻的矛盾。这样,不拓展其戏剧观念,不发展其创作方法,不革新其艺术形式,不采纳新的艺术手段和手法,便适应不了表现新内容的要求。于是,话剧革新便势在必行。由此可见,正是“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使这场话剧革新运动得以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如前所述,社会开放改革的客观形势,把话剧艺术推上了不变也得变的历史轨道。这是由“他律”所规定的。但是,戏剧革新家们在抓住这一时代契机的时候,是被动的顺应多于能动的驾驭。比如,进入80年代以后,在经济领域里,商品经济大潮铺天盖地而来,一切社会产品都被纳入了商品流通的渠道。文学艺术产品也不例外。戏剧革新家们一面积极地投入话剧的变革,一面却对这种形势感到困惑。他们还不认识或不愿意承认戏剧除了具有艺术的属性之外,也具有商品属性这一面,因此对于文学艺术的市场机制是生疏的。由于生疏而去熟悉它,那就是正常的。但他们却出于清高和认识上的局限,不愿意去熟悉它。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悖论:话剧的探索、革新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但当它面对戏剧产品必须进入商品流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要接受市场机制的制约时,却犹豫不前,固守清高。这就不由自主地违背了时代潮流。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探索戏剧”作品,虽然在形式、手法的新颖别致上作了很大努力,在内容上也一反以往传统的题材和主题,但在观众上座率和演出场次上,却十分“疲软”。这就表明,话剧的革新产品,虽然在艺术属性方面与传统话剧拉开了距离,显出了新面貌;但在商品属性方面,未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因而没能成为吸引广大观众的“畅销货”。许多革新家都热衷于搞所谓的“精英戏剧”、“高雅戏剧”,不屑于搞通俗化、大众化的戏剧。他们瞧不上这后一种戏剧。殊不知,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里,话剧艺术要真正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寻找到能适应这种社会形态所需要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青睐。而只有把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吸引到剧场里来,使他们对演出发生浓厚的兴趣,话剧的探索、革新才能从根本上站住脚跟。但当时的戏剧革新家们还没能真正理解这一点。这只能说明他们在对待市场机制方面,还没有改变旧有的观念和调整自己的艺术实践。幸好,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已有较大改变。这是一种前进的表现。
在如何对待“他律”方面所表现的不足,还反映在另一点上,即:戏剧革新家们在对待外来戏剧文化的态度和如何借鉴的问题上,存在过一定的盲目性。有的作品,为了赶时髦,只要是外来的东西,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不加分析和批判,全都认为是好的、有用的、全盘照搬过来。既不考虑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也不考虑与本民族的欣赏习惯能否相容。这种受外来文化因素盲目制约的举动,更加重了“探索戏剧”作品在面对市场机制时出现的“疲软”现象,因而也减弱了它在文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也有某些打着“实验”旗号的戏剧演出,则依然我行我素。
在如何对待“他律”问题上,还存在第三个不足,即:如何对待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的问题。新时期以前,当话剧处在“左”的思潮控制下沦为政治的“工具”的时候,作品的创作和演出走向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极端。在革新浪潮中,戏剧家们对“政治工具论”进行了反拨。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这“反拨”的过程中,也曾产生过偏差,即:因为急于要摆脱话剧对政治的从属关系、依附关系,所以就片面地认为艺术创作离政治越远越好,把政治内容从作品中剔除得越干净越好。其结果,使“探索戏剧”曾一度出现了疏离政治的现象,并由疏离政治而走向疏离现实生活、疏离时代的不良倾向。一时间,反映现实、贴近生活、关注社会热点、表达人民心声的作品,几乎没有。这也是“探索戏剧”上座率“疲软”、戏剧革新运动渐趋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时期的话剧革新运动,在“自律”这一点上,同样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悖论:一方面,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给新时期的话剧艺术提供了丰富多采的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使其旧有的创作模式、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等因素因不适应表现新的内容的需要而必须进行改革。“探索戏剧”的出现,正是顺应了这门艺术自身的这种内在要求的。这是合乎文学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的。但是,另一方面,当它在进行艺术革新的时候,由于过分地相信结构、手法、手段等形式因素的自我律动、自我更新对促进话剧艺术变革能产生重要作用,因此,在革新运动的过程中,曾一度出现过重形式出新而轻内容出新,或者是虽然内容上有新意但在形式出新上并不完全切合其内容的实际,甚至不顾内容的需要而只顾形式猎奇等不良现象。这就造成了人们曾指出过的“形式大于内容”、“形式主义”的偏向。在这一运动中,虽然也出现过《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中国梦》这样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得很好的作品。但是,从大部分剧目来看,它们在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问题上,在新的艺术方法、手法、手段是否运用得自如、和谐的问题上,往往出现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话剧革新运动在建构新的话剧形态方面,在当时还没有进入到完全成熟的境地。
第二,在追求“现代化”时,过于忽视甚至排斥“民族化”。
中国话剧是“舶来品”。在90年的历程中,始终在进行着“民族化”的艺术实践。当然,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话剧也仍然需要在与西方现代戏剧的不断对话中提高自己“现代化”的程度。但是,其“民族化”则是它必须要坚持到底的课题。
新时期的戏剧革新运动,使话剧在向“现代化”方向转换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把“民族化”与“现代化”人为地对立起来,对“民族化”加以贬抑乃至排斥,则是这一时期戏剧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纰缪。首先,它不知不觉地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在新时代,话剧在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的过程中,已不再需要继承和发扬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包括戏剧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其次,在具体创作中,它使某些(不是全体)话剧革新者在勇往直前地进行各种突破、开拓、创新的时候,几乎是毫无鉴别、不分优劣地吸收一切外来的戏剧文化。有的作品,甚至照搬、套用、堆砌各种各样外来手法,以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我国话剧的“现代化”。这种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的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毕竟使一些“探索戏剧”作品减弱了民族审美意识的根基,很难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有鉴于此,我认为:由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常不断地、尽其所能地多多吸收外来戏剧文化中的精华,因此,“民族化”的任务不可能是减轻了,而是相应地加重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提出这样发展话剧的主张,即:以“现代化”为前提,以“民族化”为基础,走“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要在当代和今后的话剧艺术家中确立起一种现代人对待文化艺术的健全、合理的心态,既不借口“民族化”而实行关门主义、排外主义,也不借口“现代化”而崇洋媚外、食洋不化、乃至全盘西化;在开放改革的历史潮流中,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戏剧文化”为总目标,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把民族传统戏剧文化和一切外来戏剧文化中积极的、有用的因素,自觉地加以分析、批判、综合、改造,在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形成我国的既是“民族化”又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话剧。
第三,虽然具有追求戏剧理性品格的强烈愿望,但实际上却又并未真正做到注重作品的思想深度。
新时期的“探索戏剧”,比起传统话剧来,它的理性品格确实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它比较重视对作品哲理意蕴的追求,又讲究通过“间离效果”等艺术手法和叙述体结构方法来减弱观众的情感共鸣而增强其理性思索的缘故。这种追求,在一些优秀作品(如《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中,得到了印证,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也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如果从时代的要求来衡量,那么,“探索戏剧”整体所达到的思想内涵的深度,是不够令人满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探索戏剧”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本来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多一些富有巨大思想概括力和历史纵深感的作品来的。因为在当时,思想上的解放运动,不仅提供给了艺术家们观察生活、思考人生的新视角,而且“文化反思”热和“人性反思”热的出现,也使艺术家们有可能深入地触摸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起来的深层文化心理,触摸到更深层次的人性特征,从而给戏剧创作以思想的、历史的和人性的穿透力。遗憾的是,这样的力作为数甚少,更谈不上有旷世之作问世。
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乃是艺术家们在考察社会,认识生活,感悟人生的深度上,尚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说,戏剧革新家们的思想高度,认识能力,决定了“探索戏剧”总体思想水平只能达到它当时表现出来的这个程度。人们可以从不少作品中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剧本和舞台艺术作品中的思想哲理,往往是从当时中外思想理论界所得出的结论中获得的,而不是由创作者自己对社会、人生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和深思熟虑中喷薄出来的。所以,戏剧家们只是用自己比较一般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素材去验证和体现别人的思想观念,却缺少对生活底蕴浸透了自己无限甘苦和深邃哲思的独特的发现。这就又落入了某种新的观念演绎的套子。从另一方面看,在艺术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不少“探索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往往较为片面地强调诉诸读者观众以理性思索,以为只有这样才算增强了作品的理性品格。它们或者过分地增添议论、评说的成分,或者喜欢插入一些令人不知所云的所谓的象征语汇,尤其是在演出中不加选择地滥用“间离”手法。这种种不恰当的做法,虽然打的是增强作品“理性品格”的旗号,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其实,采用一定的手法、技法来增强作品给观众以理性思索的成分,这不是不可以,而是要看怎样用,值不值得用。如果像《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这样,人物形象本身对生活已经作出了富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历史纵深感的艺术概括,那么,再恰当地运用一些增强理性因素、激发理性思索的手法和技法,是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的。但是,在那些人物形象本身对生活并没有作出富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历史纵深感的艺术概括的作品来说,任意地运用那些增强理性因素、激发理性思索的手法和技巧,反倒会成为一种艺术的奢侈。遗憾的是,当时还有人提出了所谓“思考大于欣赏”的理论,并由此而产生了膨胀一时的对“理性品格”的片面追求。这不仅不符合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规律,而且使话剧革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出某种浅薄化的倾向。从表层上看,这种对理性的追求似乎是为了使剧作和演出更富有思想内涵和哲理深度;然而,在深层次上,却只引发剧作家、导演艺术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手法、技法上面,忽略了在深入开掘生活底蕴的基础上进行的充满思想性的巨大的艺术概括力。
综上所述,我国新时期的戏剧革新运动,无论是它的贡献还是它的不足和纰缪,都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在这世纪之交,我们一方面应该努力发扬新时期戏剧革新运动的成绩和长处;另一方面,也应该把它作为一面镜子,自觉地克服它所余留下来的不足和纰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