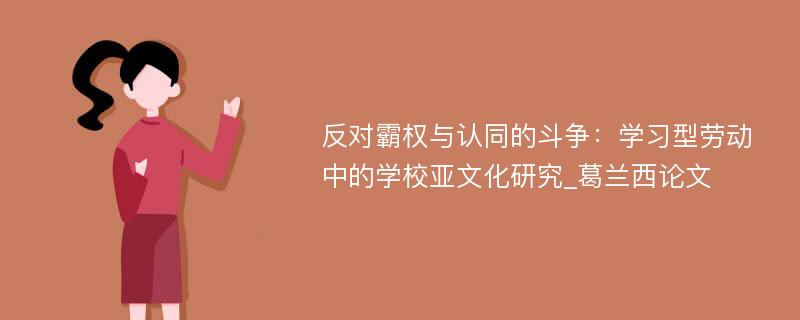
反霸权斗争与身份认同——《学习劳动》中的学校亚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身份论文,学校论文,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2)02-0060-05
众多社会学研究指出,底层总是极力向上层社会攀爬。但在威利斯的《学习劳动》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运动。《学习劳动》是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一部探讨学生反学校文化,也就是学校亚文化的重要教育著作。威利斯采用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模式,展示了学校体制与学校学生之间的一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底层的学生却极力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甚至甘愿维持自己的从属地位,这为我们理解复杂的青年文化提供了一个案例。
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Hegemony,译为“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不再使用武力来强迫人民大众接受其统治,而是采取温和的文化策略,通过赢得大众的同意来实施自己的统治。葛兰西通过深入细致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而一方要赢得另一方同意,并不是很容易的,就有着双方的谈判,有谈判也就有让步或折中平衡的问题。正如葛兰西所说的,“毫无疑问,考虑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获得领导权的前提,必须达成一定的折中平衡”[1],也就是说当事双方都要作出一定的牺牲。葛兰西在谈到要成功组织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历史集团时说,这“就需要改变某些必须吸收的力量的政治方向。由于两种‘相近的’力量只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或武力要么互相结成联盟,要么强行使一方服从另一方,方能接入新肌体,此处的问题是一方是否具有某种力量,使用这种力量是否‘富有成效’。如果两种力量的联合旨在击败第三方,诉诸于武力和胁迫(即使假定它们可行)不过是假设的手段;唯一具体的可能是妥协”[2]。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批判了那种单一视角看问题的方式,而是强调对立双方之间的对抗、斗争与谈判和协商,最终在双方相互退让中,达成一个协议性的结果。这一理论在《学习劳动》中具体体现为学生对学校体制的反抗,以及学校在这种反抗下的协商和退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反学校亚文化的特点及其运作特征。
二、“小伙子们”反抗之种种花招
威利斯把学校那些反抗学校文化的12岁左右的学生亲切地称之为“小伙子们”。那么,这些“小伙子们”是如何反抗学校文化的呢?首先,威利斯明确地指出,这些“小伙子们”的反抗“包含了一种明显的对权威所持有的普遍价值的颠覆。勤奋、听话、尊重——这些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给予解读。”而这种反抗“几乎是他们日常生活组织的仪式性的组成部分”[3],也就是说,反抗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具体说来,反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学习劳动》的第2章,威利斯从7个方面全面展示了反学校文化的各种“要素”。简而言之,包括不好好上课而趴在桌子上睡大觉,或向窗外偷看,或无聊望着墙壁,总之“弥散着一种无目标的抵抗”。或者是联合起来捉弄老师,成功后用“V”字手势表示胜利。还有经常性的逃课——虽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反抗方式。在外出参观,如参观博物馆时,他们虽然被要求要老实,但趁老师不注意时,他们会溜出去抽烟。还有通过制造滑稽场面而“打破枯燥与担忧,克服艰难和存在的问题”,如在老师还未到教室之前告诉他副校长要找他,你不用上课了,而后又到二、三年级的教室里告诉那些学生说校长要过来看他们,他们可能有麻烦,由此而使这些学生们紧张起来等。另外就是打架斗殴,以展示男子汉的气概;追逐女性以显示自己的性能力,等等。
所有这些都展示了“小伙子们”对学校体制的反抗,而这些反抗和排斥也典型地集中在他们对资本主义为他们所提供的消费品的挪用上,这与研究中心的青年亚文化是相通的,也与后来的费斯克的理论相通。具体说来,《学习劳动》主要阐述了这些“小伙子们”对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三种消费品的挪用,这就是服装、香烟和酒精。对于服装,这些“小伙子们”通过穿着奇装异服,向学校的所谓的正常秩序和权威发出了挑战。作者指出,服装是他们选择出来作为“向权威斗争”的基础,“这是一种文化之间的流行的斗争形式之一。它最终会转变为一个关于作为一个机构的学校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另一方面,与服装样式相连的是性的吸引和性活动,而“这种双重的接合是反学校文化的特质”[4]。当然,这些“小伙子们”的服装(还有发型),显然是受到了社会上的青年文化的影响。但作者也指出,社会上的商业性的青年文化被他们吸收过来,主要是为了自我的表达,从而缺少了这些商品最初的商业上的生产意义。
“小伙子们”把抽烟喝酒作为一种反抗形式,还有着其内在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成人价值观的认同和追求,他们把抽烟看作是“一种与成人价值和行为相联系的在学校面前的造反行为”[5]。最终他们追求成人的真正生活而超越了“学校生活的压制性的青春期”[6]。但不管怎么样,“小伙子们”通过利用体制所提供给他们的资源成功地抵制了体制对他们的压制。
与反抗教师权威相连的是反对“耳朵眼”,即那些学校里听老师话遵从学校制度的学生,他们甚至会向老师和学校打小报告,揭露那些不遵守学校制度的人。这些“耳洞”们表现出一种的强烈的顺从主义,这对于那些“小伙子们”来说意味着消极和荒谬,“好像他们总是在倾听而从来不去做:从未有他们自己的内在的生活活力,而只是毫无定形地僵化地接受。这些耳洞是对人类躯体最少表达的机体之一:它只对他者的表达做出反映。”[7]可以说,这些“耳洞”不仅其顺从性与这些“小伙子们”的反抗相背,而由顺从所体现出的萎缩的生命力上,显然也是这些“小伙子们”所不齿的,因为“小伙子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力的展示,而这典型地体现在他们对打架斗殴的青睐上。
打架斗殴不仅仅是为了消除枯燥烦闷的生活而寻求的刺激,打架斗殴这种极端的反社会行为对他们来说还有更深层的含义。首先,打斗这种社会暴力行为是对“顺从”(以“耳洞”的行为为代表)的打破,也是对专制的颠覆。在这种打破与颠覆中,自上而下的“意义流动”方式被打破了,而“关于自我从过去流向未来的通常的假定被阻止了:时间的辩证法被打破了”[8]。也就是说,体制所期望于你的在时间中的流动与发展在打斗中给阻断了,一切都停留在了“现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巴赫金对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对包括打斗在内的双重体的精彩的论述的影子,即打斗在两者的文本中都具有打破和颠覆的意义,但两者又有着深刻的不同:巴赫金的双重体强调的是打破现在而走向未来,但“小伙子们”则在打斗中执著于现在,这与他们自动地接受工人阶级的工作有着深刻的联系。另外,通过打斗,这些“小伙子们”与其他的团体,主要是与学校划分开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正是这些更为极端的行为把他们与‘耳洞’和学校完全划分开。”[9]而也正是在这种划分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团体——非正式的团体。我们甚至可以说,打斗是他们建立自己的团体的一种考验的方式,它“是你在另类文化中被完全确认的时刻”[10]。也就是说,只有在打斗中你才能被这种文化所认可,才会被确定为是他们中的一员。由此,打斗也是他们确认自我身份、形成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方式。
三、身份认同:区分与整合、确认与失位
所谓“区分”,就是工人阶级文化创造性地把自身与特定的体制区别开来,从而在其内部把自身确证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区分是一个过程,借此,官方体制范式所期待的典型的交换,在相关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感受和意义中被重新解释、分隔和辨识。它的动力是对抗体制”[11]。由此可以说,区分就是一种对体制的反抗形式。
与“区分”相对的就是“整合”。威利斯指出:“整合是区分的对立面,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借此阶级对抗和意图在一系列明确合法体制关系和交换的内部,被重新定义、减缩和积淀。在区分成为非官方对官方侵袭的地方,整合则把非官方的逐渐建构进正式的或官方的范式中。”[12]这实际上就很清楚地指出了区分与整合之间的一种霸权与反霸权的关系,而接下来,威利斯的阐述就更明确了:“所有的体制都保持一种区分与整合之间的平衡,而区分在功能上绝不与断裂或失败同义……区分被那些相关者一方面经验为是集体习得的过程,借此过程,自我及其未来批判性地与预先给定的体制上的界定分隔开来;另一方面通过体制的能动者被经验为是不可解释的断裂、抵制和对抗。被生产的东西,一方面是被改造和被再生产进入特定体制形式的工人阶级的主题和活动;而另一方面是对官方体制范式的删节、僵化或软化……在学校体制内部,根本的官方范式关注一种特殊的教学观和与之相区分的反学校文化的生产形式。”[13]
在这里,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在“区分”和“整合”之间的一种霸权与反霸权的关系。这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相通的,也几乎是相同的。
但体制要整合成功,当然不能单纯靠压制。学校与学生关系是建立在要“赢得一种来自于学生内部同意的形式”基础之上,由此,“认为传统的(教育)范式只是单纯地对学生实施压制……是完全错误的”[14]。在这里,威利斯阐述了学校意识形态的两种功能:“确认”和“失位”。“确认”,就是把不确定的文化样式及结果,通过意识形态的运作把它确定下来,并不断地去巩固它,使之自下而上地被形成,被定型,由此而在社会形成“一个真正的和活生生的共同点”,并进而“使所有阶级合并成一种类型的同意,而这种同意是再生产现状的基础”[15]。简单地说,确认就是通过确定某种文化形式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同意的共识,从而维护体制现状。而“失位”则是通过不断地宣扬机会、命运和运气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上的不平等、压制与剥削等现象的真正的根源,强调这些“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有的只是个人的原因而不是“系统上对生活中个人机会的压制”,“是人类本性而不是资本主义才是人类的陷阱”。所有的不平等都是“自我制造”[16]的。这就在根本上取消了阶级的对立,从而使阶级失去了位置,消解了人们的反抗的意志。而也正是通过这种“失位”,体制获得了同意。
但即便如此,同意的获得也不会那么容易,体制与反体制、霸权与反霸权之间的斗争总是持续不断,葛兰西把这种战斗称为“阵地战”。而威利斯在谈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斗争时,用的则是“游击战”一词,但实际上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长期的、非正面对抗的“阵地战”。如教师不让再提骑机动脚踏两用车的事,而他们偏要提,在读戏剧的时候,用自己的语言替换戏剧中的语言,等等。由此教师与学生之间就有了持续的“游击战”[17]。
四、结论与讨论:反抗的意义和底层的再生产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以学校为代表的体制和以那些“小伙子们”为代表的反学校文化之间的斗争,是一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而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小伙子们”以自己的文化自主,强烈地反抗着和颠覆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压制,从而凸显了人的能动性。正如威利斯所说的:“社会能动者并不是意识形态的消极的承载者,而是积极的挪用者,他们通过斗争、争夺和一种带有偏向的对这些结构的渗透来再生产现存的结构。”[1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显然也走出了和超越了庸俗的决定主义对社会和文化生产的解释。
威利斯等人在《共同文化》中指出:“我们坚持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的创造性与表现中,有一种活跃的符号生活和符号的创造性——即使有时候是不可见的,被忽视了或被轻视了……大部分的青年人的生活……实际上都充满了表达、符码和符号,借此,个体与团体创造性地寻求建立他们的在场、身份和意义。青年人一直在表达或试图去表达关于他们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文化意义的东西。这是活生生的共同文化领域。也许有些庸俗,但同样也是无处不在的‘共同’存在着、对抗着、坚持着。”[19]贝弗莉·斯凯格斯(Beverley Skeggs)也指出:“第一次,工人阶级在其创造性中被呈现为强大的、反抗的和好战的,也呈现为幽默的。”这是一种从消极受害者的转变,“它展示了年轻的工人阶级如何掌握权力。也展示了他们又如何促进了他们自己的从属地位”[20]。
如果说斯凯格斯前面一句话说的是《学习劳动》的优点的话,那最后这句话恰恰暴露了青年亚文化的不足,就是工人阶级虽有反抗,但最终还是只获得工人阶级的工作。这也许正是本书所给予我们的有些沮丧或悲观的结局。而就其原因,显然就是工人阶级的小孩过分保持自己的文化所导致的结果,正如威利斯所说的:“我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才最为有效的为许多工人阶级的小孩接受体力劳动作好了准备,我们由此可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在这些小孩们所承担的从属地位中,有一种自我贬损的因素。”[21]而这种自我贬损在客观上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的再生产。这里便有了一个哈里斯(David Harris)所说的“主体的自相矛盾”,就是愈选择与他者的分离,就愈会加深他们对自我的认同,而这就会愈使他们“自愿地”去寻找工人阶级的工作,而“这一相当沮丧的结论会导致在学校儿童中更进一步地扩大(认同或促进)抵制和反抗的领域”[22]。这典型地体现了学校青年文化,乃至整个底层文化的复杂性。陈广兴说得好,我们必须认识到,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机制既存在于阶级关系的宏观背景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微观制度支持中,后者要求我们理解日常生活实践中,尤其是教育和劳动过程中“甘愿”和“压迫”结合的方式,以及属于底层的、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政治社会”[23]。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此就否定这些“小伙子们”抵制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这里有一个宏观革命和微观抵制,或阶级斗争的革命与日常生活的抵制这样的区别。我们往往更多地关注那种通过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而推翻旧体制这样一种革命形式,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进行的微观抵制。这种抵制也许微不足道,不可能对旧体制产生迅速而根本性的撼动,但它长期的不断聚集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侵蚀力量,正如斯科特(James Scott)通过分析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后所指出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抵制的不断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24]。从这一意义上说,威利斯的研究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收稿日期]2011-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