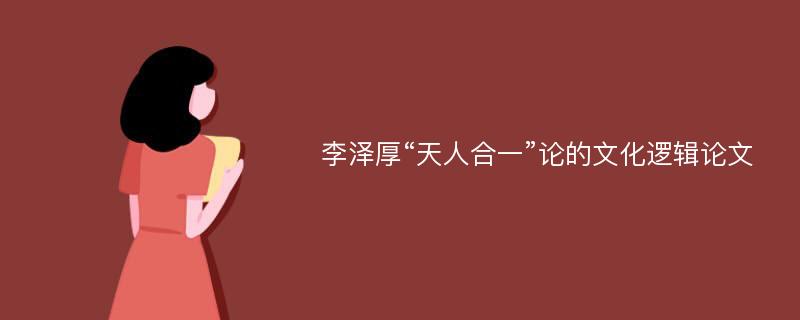
李泽厚“天人合一”论的文化逻辑
张飞翔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李泽厚以“传统的现代转换创造”为总文化逻辑,以本体论为理论依据,阐释“传统天人合一”命题在揭示“人的真正存在”时所具有的优越地位。这一地位的确立,使得他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大儒学谱系观”的文化史构造,并进而借助这一构造阐明其“儒道互补”双线文化逻辑与“人生在世”之间的文化联系,彰明以“人”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审美理想。由此,李泽厚实现了“中—西、传统—现代”间的文化沟通,构筑了实践美学以“文化—哲学—审美—文化”为逻辑次序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李泽厚;天人合一;文化逻辑;人
长期以来,学界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研究汗牛充栋。其研究焦点一方面集中在其不断提出的新概念、新命题上。比如,对工具本体、主体性、情本体、积淀等概念、命题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则集中在如何从整体上认识和评价实践美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比如,后实践美学从整体上界定的,“实践美学属于古典美学范畴,缺乏现代性”。总的来看,这两种研究的优势和劣势都异常明显。前者眼界过小,虽然有利于从微观层面深入挖掘其美学思想,但往往流于片面,走向极端;后者虽视野开阔,也着力于从整体上理解实践美学的历史性发展和变迁,但往往流于表面,难以深入。基于此,我们将视野聚焦到李泽厚中后期以来提出的“天人合一”论,以求在宏观与微观的多重视野中,为深入理解和客观评价实践美学提供一个崭新视角。选择“天人合一”论作为聚焦点的原因则主要在于,这一命题在表面上从属于微观范畴,但在整体风貌上却又处处显现出微言大义的宏观特征。进而言之,李泽厚“天人合一”论,虽然有其明确的理论边界,但由于其以宏观视野下的实践论为理论基础,使得其整个流动的理论环节几乎关涉了实践美学的所有重要概念和体系建构。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李泽厚“天人合一”论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其整个美学思想的微缩形式。从而,探明这一理论的文化逻辑,为学界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价实践美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或能提供一个相对崭新、独特的视角。
汤甲真在学生时代就爱读传统诗歌。离休后,他在教育家汤匊中的指导下,下功夫学写诗词,创作出一些诗文作品,讴歌新时代、新生活、新风尚,有些还发表在媒体上。
一、“天人合一”论及其文化特征
何为天人合一?李泽厚的理解有两种天人合一。
第一,源发于中国古代小农社会充满先验性、想象性、神秘性的精神理想。据李泽厚道,它源于中国“远古巫师的通神灵,接祖先”的巫术活动。在儒家,发端于孔孟,经“汉代以阴阳五行为构架的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而形成基本构型;到宋明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而发展到顶峰;终于形成中国传统由“自然本体论到伦理本体论”的“天人合一”论。在道家,则主要以老庄解构儒家伦理关系的“道”论为主体,形成了超越于儒家人事社会制度之外的自然论“天人合一”。此外,墨、法、阴阳各家也分别以其不同的理论基点和社会政治目的为依据,形成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论。李泽厚所理解的“传统天人合一”命题,则主要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体,以道家自然身心修养为辅翼的“天人合一”论。前者强调赋予“天”以伦理道德的含义,以人事社会的合法合理运行为基本含义释“天人合一”;后者强调还原“天”的“自然”义,以个体身心的自由发展为基本含义释“天人合一”。
第二,以马克思唯物史观所阐述的“自然人化论”为主要内核的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展望。它在李泽厚那里包括:“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两个维度。前者强调回到“人类如何可能”这一命题,以突显“社会历史实践”或曰“工具本体”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含义;后者强调“主体性”(包括人类和个人两个方面),即在人与自然相分离的前提下,又主动拥抱自然以获取外在物质文明和内在精神自由发展的含义。李泽厚所彰明的“天人合一”论即后一种,它在理论基础和发展构型上属于去先验性、想象性、神秘性色彩的“现代天人关系论”。进而言之,乃是与唯物史观相一致,具有强烈现实意图的现代哲学理论。李泽厚说:“我讲的‘天人合一’,首先不是指使个人的心理而首先是使整个社会、人类从而才使社会成员的个体身心与自然发展,处在和谐统一的现实状况里。这个‘天人合一’首先不是靠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是靠人类的物质实践,靠科技工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对这个发展所作的调节、补救和纠正来达到。这种‘天人合一’论也即是自然人化论(它包括自然人化与人自然化两个方面),一个内容,两个名词而已。”[1]289简而言之,李泽厚“天人合一”论,就是其一贯阐释的马克思“自然人化论”。只不过,李泽厚以“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对其作了更为细致的拓展和延伸罢了。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时,李泽厚曾简明扼要指出:“古代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和‘道在伦常日用中’,则更深地揭示不是由个体——上帝,而是现实世间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的真正存在”。[2]419借此,李泽厚在哲学层面澄清了其“天人合一”论的核心要点:人的真正存在。这说明,在李泽厚那里,“传统天人合一”命题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对现实社会人生的重视,对“人的真正存在”地揭示却又超前地赋予了这一命题以无比优越的地位。它着眼于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来考察,并进而将人放置到这一整体关系中来理解,以此规定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这即是说,“天人合一”,既是“人”与“自然”合一,也是“个体”与“群体”“个体”与“自我”合一,“人”成为这一命题的核心和归宿。这个“人”,在以后被李泽厚通过引入康德哲学,而进一步明确为“主体性(人性)”。显然,这个经由康德哲学所引入的主体性概念“(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的”。钱善刚说:“主体性是李泽厚的关键范畴之一,在《人类起源提纲》中第一次得到揭示,人们往往在认识论的构架下来理解主体性,实际上我们看到李泽厚在这里通过对人类发生学的考察,强调主体(人类)的本体性。”[3]26事实上,李泽厚以“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来命名自己美学体系的时候,这一点就再清晰不过了。由此我们说,“‘传统天人合一’命题揭示的这个‘人的真正存在’”,正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与马克思、康德乃至他以后所提及的海德格尔,都具有某种内在的文化相关性。
如上所述,李泽厚“天人合一”论就是发源于马克思“实践论”的“自然人化论”。既称“自然人化论”,他又缘何冠以“天人合一”之名呢?
二、“天人合一”论的总文化逻辑
这段话表明:其一,儒道同源,即同源于这个“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其二,儒道互补,即所谓“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由此观之,李泽厚所理解的儒、道实乃这一“同源”文化理性化“分流”的结果。这也即是说,儒、道本同源于这个“巫术宗教”传统,但其在各自“理性化”过程中却又各有走向。从“同源”角度出发,这一“巫术宗教”传统后来被概括为“巫史传统”,而“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等这些“中国文化特征的概念,其根源在此处”[9]156-157。由这一根源起,先秦这股“理性主义思潮”实质上也就不仅限于儒、道两家了,它应当包含所有从这一文化根基上所衍生出的学术流派,否则它就不是“中国的智慧”,而只是“儒家的智慧”了。换言之,儒、道、墨、法、兵、农、阴阳等这些流派实质上都可以被归结到这个根源上来,只是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而已。而从“分流”角度出发,“道家”却又以相反相成的方式构成对儒家文化的适度“反叛”。这一“反叛”使得道家尽管不强调人事,甚至厌弃人事现有的繁文缛节,却依然想通过回归自然来重构现实社会人生的存在形态。细酌之,这一重构实际上具有一种双重意义:其一,它延续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持续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重要特点,这使得李泽厚能够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统一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儒家文化,从而不是以“孔孟程朱陆王”这一贯谱系,而是以“儒”这一新概念来重新包罗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其二,它在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制造了一种“迥异”的成分,即带有自然本体论意味的“人生在世”论。
纵观李泽厚为“人自然化”所设定的这三层含义,可以发现,“人自然化”正好是“自然人化”的拓展和延伸,而且,这一拓展和延伸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纯粹美学理论的领域,更多已经着眼于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文化表达。因为,这种通过物质实践所作的对人类现实存在的定位与对人类未来的无限畅想,尽管在许多方面都将审美作为其根本出发点和核心所在,但在最终呈现方式上,却已经被展示为人类生存文化的现实图景和未来憧憬。这即是说,它固然重视审美,但在实质上却又与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塑造息息相关。要而言之,李泽厚“天人合一”论,与其说是“美学思想”,倒不如说是“审美化的生活理想”,它从属于文化范畴;既从属于文化范畴,则其必然要遵循着某种文化逻辑来构建。从而问题便在于:其文化逻辑究竟是怎样的?
笔者以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回到“儒学四期”说的源头上来看。追本溯源,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从先秦起“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了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思想、文艺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8]51。
事实上,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李泽厚论“天人合一”的诸多文本时,我们就会发现其真实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融传统于现代的文化需求,用他自己的话说:即“西体中用”,或“传统的现代转换创造”。
“孩子跟了曲。S有时也会想起曲和儿子,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混蛋,不负责任,而责任感曾几乎将他压垮。在区民政局签字离婚时,曲说,儿子快两岁半了,会叫爸爸了,真希望他记住你的模样,你可以走了。曲笑了笑,又说,如果当时你一想走就让你走,孩子就不知道爸爸是谁了。S胃里泛起了酸水。他闹离婚时,不知道曲有孕在身。曲算计了他一把。这次曲也是借题发挥。难道他就一直不见儿子吗?他还没有想好,但暂无打算。他觉得自己比一个小男孩还要脆弱。以前跟曲的婚姻生活,他就像铁栅栏中的猛兽,憋得发慌,但没想到跟Y在一起,情形更严重。Y的冷漠犹如一个钟形罩将他密封,透不过气来,如今他正在摆脱。他找到了望远镜这个透气孔。”
具体说来,“自然人化”主要指人在漫长的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改造自然界,同时改造和发展自身以逐步脱离自然的阶段。从而,“人之为人”的整个历程都包含在这个使用—制造工具的历史进程中,人的感性身心由此获得发展,并随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张而有了审美能力。“人自然化”是指人在不断与自然相分离的过程中又主动投身到自然怀抱,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以审美化的方式对待自然,并从对自然对象的审美中获得最高级精神享受的过程。前者是后者基础,后者予前者以纠正、补足;二者均不脱离“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活动。“人自然化”在此基础上,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人与自然友好和睦,相互依存,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其二,以自然为欣赏、欢娱对象,栽花养草、游山玩水、流连景观、投身自然;其三,呼吸吐纳,调整身心节律,与自然合一。
马克思从宏观视角提出“人化自然论”,认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不在人与人形成的表层社会关系,而在于“整个人类以自然为中介和对象所构成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以此论证了人的社会存在,它构成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康德以“知情意”三分法来构筑“人性结构”,从“先验的心理形式”(指康德的三大批判哲学体系,而并非心理学)角度,分别揭示了“认识如何可能、道德如何可能、审美如何可能”这一系列关于“人的主体性”的问题。进而言之,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人的主体为自然界立法”[4]9的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之关系,彰明了“人之心理能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海德格尔以“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悟中”[5]6为发问之前提,将“形而上的存在之‘本体’”与“形而下的存在之方式”融为一体,揭示了“在世之中存在,在世之中来实现死亡”[6]的本己性存在方式,以彰明“人生在世”的价值和意义。这三者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性特征。马克思着眼于物质生产的性质;康德强调主体世界的价值;海德格尔则寓物质与精神于一体,强调“人生在世”的价值和意义。从本体论视角看,这三者尽管有着显明的差异性,但实质上又都可以被归结为“人之为人”基础上的“人生在世论”。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泽厚所理解的“天人合一”论便具有了同时容纳中西哲学的文化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既来自人类各种哲学理论在思想文化上的“异质同构”特征,更来自李泽厚自身所直面的“人的哲学”,这一看似通俗实则晦涩艰深的命题。尽管这一命题所具有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本身难以被穷尽,但在本体论意义上,却可以作某种文化上的等量齐观。在这一意义上,“天人合一”这一看似“理论化”,实则趋于“信仰式”的中国哲学基本命题,恰恰能够以最含混的语言方式,表征和容纳中西文化在“人”这一问题上的相似性、相通性。
这样一来,所谓“西体中用”或“传统的现代转换创造”,便都以“人生在世”这一最具普遍性的哲学话题为基础,被总括为“天人合一”这一“审美化的生活理想”。换言之,李泽厚只要回到最具包容性特征的“传统天人合一”命题,并对其理论基础作一改换,便能“简洁高效”地实现中西文化的贯通与“互用”。这既构成了李泽厚“天人合一”论的总文化逻辑,又在最终意义上决定了其整个实践美学理论的文化逻辑。
自2011年以来,我国教育部相继印发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标准》)和《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等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对职业学校教师的从业要求在逐步提高。因此,对于专门培养职教师资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在师范生的培养方面,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尤其应当重视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培养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教育知识以及熟练的教学技能的师范生。
三、“儒道互补”的文化逻辑
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工作还只是一种宏观视野下的“思想比较”和“文化理路分析”,而并未真正切入“天人合一”论在其历史性地生成中所展现的具体文化逻辑。但正是前述部分这些工作,使我们能够对“实践美学”作一整体式的理解。这一理解为我们扫清了诸多繁复概念和表面现象间的复杂性关系,使我们能在理解“天人合一”论的同时将之与实践美学的整个发展历史相联系起来,以作思想文化层的对比和关照,从而更加有利于我们下面的分析。
式(1)中,S为变电站所属所有10 kV馈线负荷全转移标识的乘积。如变电站任何一条10 kV馈线负荷不能全部转移,即其中任一个SN=0,则变电站全停校验结果为0,不能实施全站停电。由此可知:要使S=1,该变电站所属所有10 kV馈线负荷全转移标识均为1,才能够实现变电站全停下的负荷全转移,即变电站全停通过;当S=0时,该变电站所属10 kV馈线不能够实现变电站全停下的负荷全转移,即变电站全停校验不通过。
回到实践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李泽厚八十年代出版一系列重要著作不断谈及“天人合一”论,不正是理论化的中国审美实践论(《美的历程》)到中国化的实践美学的理论化总结(《华夏美学》)吗?《美学四讲》不正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将“天人合一”与实践美学理论充分融合了吗?由此我们说,李泽厚“天人合一”论围绕着“西体中用”或“传统的现代转换创造”这一总的文化逻辑所开散的枝叶,正是由“儒道互补”的双线文化逻辑具体落实的“文化—哲学—美学—文化”的逻辑次序所构成的。在文化层面,“天人合一”论是“大儒学谱系”观(巫术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的“文化史构造”;在哲学层面,“天人合一”论是“人之为人”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人生在世”哲学交相辉映;在美学层面,德国古典美学确立的“哲学—美学”体系与中国传统“审美化的人生理想”深度契合,而终于构成李泽厚所彰明的“天人合一”论。由是观之,实践美学最终确立的:美的哲学基础(自然人化)——哲学的美学拓展、延伸(人化自然)——美的哲学归依(天人合一),这一完整体系恰恰是以“天人合一”论所确立的文化逻辑为基本前提的。
回到思想文化视角,李泽厚八十年AI写作作《孔子再评价》和《试论中国的智慧》两篇文章,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其文化逻辑建构的真正开端。因为,当李泽厚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血缘根基为认识基点重新阐发孔子“仁学结构”,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的学术判断时,就已经为他后来阐述的“天人合一”论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层层铺垫。李泽厚后来总结的:“‘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是‘儒学四期’说的天人新义,即对作为传统儒学以至整个中华文化核心命题的‘天人合一’所作的一种新的解释”[7]30,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那么,这一由李泽厚所阐述的“传统天人合一”命题究竟是如何被发挥为“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这一美学命题的呢?或者说,李泽厚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逻辑支撑起了实践美学所阐述的“天人合一”论?
在《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曾谈及:“古典哲学的语言常常被现代某些潮流视为呓语,但恰恰在它的某种程度的模糊含混中,有时比现代精确的科学语言更能表现出哲学的真理”[1]285。可见,以“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古典哲学的话语来表述“自然人化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现代学科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但问题在于,仅仅是现代学科语言局限性的缘故,就让李泽厚放弃了精确客观的现代学科语汇,而代之以“天人合一”这一含混的古典语汇吗?从上述“自然人化”到“人自然化”的整个表述方式和思辨方式上,我们发现问题显然不止于此。那么,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
理解文化逻辑问题还得回到李泽厚所使用的“天人合一”这一术语上。因为,这个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彰明了李泽厚美学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态度和实践方式。
这样一来,李泽厚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抑制—转换”机制。所谓“实用理性”便同时兼容了两种倾向: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实用理性”不断向“社会人事制度”奔袭的路上,道家则将“实用理性”抑制在了个人层面,并将之“转换”为一种“自我意识”地不断塑造。从而,“乐感文化”虽以儒家“礼乐”论为主,但这里实际也隐含了道家“乐”(愉悦)的维度。只是按照李泽厚所说,它被儒家吸收与转化了。“传统天人合一”命题由此而包含了儒家“自然人化”与道家“人自然化”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走向。
显然在“儒道”分野的根源上,“巫史传统”这一基本判断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此时,我们再来回顾“儒学四期”说,就会发现其文化逻辑的底层必须以这庞大的“深层文化根系”为基础才有可能成立。笔者在此意谓表明,“儒学四期”说,虽以“儒家”为主,但其实质上更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大儒学谱系观”。只有基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儒”在李泽厚的意识里,应当是包含和融合了先秦乃至后世各家各派思想的一个“大儒学谱系”——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以儒为主的文化谱系”。因为正是这个“谱系”地建立,使得“传统天人合一”命题在文化层面,能够充分涵盖整个中国传统思想之汇集与交错,而又以“儒家”为主,以“道家”为辅,形成“儒道互补”为主体形态的双线文化逻辑。
由这一双线文化逻辑来关照“传统天人合一”命题,就会发现“四期”之分,本不应当被看作一种客观的思想史叙述或研究,而更应当被看作李泽厚基于唯物史观基础所作的一种文化构造。这一文化构造所意欲表明的主要观点即“人之为人”这一命题。在这一点上,“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之历史性生成过程实际上便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的真正存在”。融入了“人的真正存在”这一命题,李泽厚所主张的“儒道互补”也就不仅是在阐述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与道家“自然本体论”之简单对立与补充,而毋宁是在阐述“人之为人”的本体与审美精神之内在联系。因为在李泽厚看来,所谓“人之为人”的最终依据即在于“主体性”(人性)之生成,“主体性”显然是以审美作为人性之巅峰的,它包含并超越了认识与伦理。从而,李泽厚这一所谓的“理性化”过程,虽重在言说“传统天人合一”命题之生成与变迁,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它又何尝不是对“人的真正存在”的高度哲学概括呢?以社会人事制度为本的儒家和以自然无为为本的道家,它们又何尝不是在建构起自己的“人生在世”论呢?儒家予人以理性精神(敬鬼神而远之),极大地发挥人的能动性特征,使人从“巫史礼仪”的狂热情感宣泄中逐步解放出来的同时,又能够以“敬鬼神如鬼神在”的虔诚情感充分地实现人之现实要求和目的,这不正是李泽厚所谓的“自然人化”吗?道家亦予人以理性精神(天地不仁),并借助这理性恰当地抑制了人之过分能动性对外在社会人事可能造成的伤害,创造性地将之转换为“自我意识”(如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地塑造,极力言说自然无为之积极意义,这不正是李泽厚所谓“人化自然”吗?它们经由前述唯物史观的先行介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显然,这一普遍性之意义并不在于其具体历史流变是怎样的,而在于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表征李泽厚“人之为人”这一现代哲学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所呈现的“人生在世”这一现代哲学命题所具有的审美化生活理想。
具体来说,李泽厚“天人合一”论,作为美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其八十年AI写作作的“美学三书”中,尤以《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的联袂出现而渐具雏形。其中,《华夏美学》以叙述中国美学为主,《美学四讲》以理论概括为主。而九十年代末所作的《说“天人新义”》则偏重从理论上对前二者加以系统化,而终成体系。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体系,仍以李泽厚一贯擅长的提纲式方式呈现,始终“挂一漏万”,从而探析“天人合一”论的文化逻辑就仍需在整合以上内容的基础上漫溯攸关,才有可能做到有所兼顾,客观准确。
由表4可以看出,当“三遥”终端数量超过7个时,总的经济投资收益将出现亏损;数量为7时,投资收益ΔC为正,同时可靠性可取得最大值。综合考虑,可以认为此方案为最优配置方案。但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基于最优的配电自动化实施方案,仍不能满足此区域供电可靠性的要求,也说明了单纯依赖配电自动化提高供电可靠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可通过加强网络结构,如采用双环网,提高服务措施,缩短故障修复时间等措施,以满足供电可靠性的要求。
总而言之,由“西体中用”到“儒道互补”这一双线文化逻辑地确立,为实践美学体系地建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和致思方向,它们构成实践美学的文化逻辑前提。如果缺失了这一基本前提,我们就无法解释李泽厚以“天人合一”这一含混的古典话语来表征“自然人化论”的意图所在;就无法解释李泽厚不断为其美学理论建构“儒学四期”说这一旁逸斜出的思想文化铺垫的真实意图;我们自然也无法阐明实践美学所阐述的“自然人化论”为何会包含:“自然人化”—“人自然化”—“天人合一”这一理论进深。
结语
回到李泽厚前后几十年间不断写作的“哲学提纲”与其不断提到的“同心圆”概念,可以发现,李泽厚正是基于对“人”(人之为人、人生在世)的关注而不断地将“传统天人合一”命题阐释为它所彰明的“天人合一”论的。
在《人类起源提纲》,我们看到了李泽厚对“人类如何可能”的追问;而到《康德哲学与人的主体性论纲》时,在“人之为人”这一追问背后,李泽厚所用力的重点则已转向“人之为人以后”的命题。前者,可以被看作李泽厚的“问之所问”:“人之为人”的本体是什么;后者,可以被看作李泽厚“问之何所以问”:追问“人之为人”的本体的原因(目的)是什么。前者,李泽厚答以“历史”“实践”“工具”,构成其“自然人化论”的哲学基础及“天人合一”论基础义;后者,李泽厚答以“文化—心理结构”“心理”“情”“主体性”,构成“人化自然论”的文化转向及其“天人合一”论的核心义。它们在李泽厚文化视野与哲学理论的交织中,进一步结晶为马克思、康德与中国传统的“异质合成”,形成其以“人”的核心的美学理论,构成其“天人合一”论所畅想的“审美化生活理想”。这三部分围绕“人”这一圆心而运转,构成其同时容纳中—西、传统—现代、文化—哲学—审美—文化的“同心圆”。这些“同心圆”在最外层显现为“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次一层显现为“哲学—美学”的逻辑递进;再次一层反向回归,显现为“美学—文化”的逻辑终点。这三点围绕唯物史观所限定的历史的、具体的“人”(包括人类和个人两个层面)这一圆心运转,构成了“天人合一”论的完整形态。显然,这个历史的、具体的“人”不是别的,而恰好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现代变迁所引发的关于“人”的焦虑与价值重估;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对自现代社会以来,“人”的现实境遇与未来憧憬的无限畅想。它指向审美但不以审美作为终结,指向现实生活但不以生活现实作最终判断,它在相当程度上破除了现代性所引发的“人”的焦虑,又在相当程度上为“人”的重新确立提供了动力和希冀。
饮水安全,实乃民生大事。作为一个水资源极度短缺的省份,农村饮水安全受到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从“饮水解困”到“饮水安全”,从“饮水安全全覆盖”到“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我省农村饮水从“面的覆盖”迈向了“质的提升”,广大农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由此,我们说实践美学正是在“天人合一”论所确立的文化逻辑的基础上,而能够不断为后来的美学提供参考和借鉴,尤其是在“从实践性转向主体性,从工具本体转向情感本体”[10]——即在实践美学内部实现的“人的重新定位”这一命题上,能够不断激起后来美学流派的反思与借鉴。后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生命美学、生活论美学等正在蓬勃发展的当代美学流派,尽管其理论基础不尽相同、理论路径五花八门、理论话语各美其美,但在文化表达和理论核心问题上却始终是围绕着“人”这一核心命题而不断深化的,这也许正是实践美学留给当代美学最宝贵的财富。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包括书面评价和口头评价,书面评价的优点在于经过深思熟虑,因而正式而切实,口头评价的优点则在于它的自由度和及时性。每个学生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初中生正处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教师评价的导向作用不容小觑。因此教师必须牢记评价分层的重要性,善于鼓励、及时提醒,以正确而适时的评价为学生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钱善刚.本体之思与人的存在:李泽厚哲学思想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4] 邓晓芒.判断力批判释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6] 李晓明.海德格尔的死亡问题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6.
[7]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8]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9]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0]张敏.论李泽厚美学思想中的主体性话语[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67-73.
Cultural Logic of LI Zehou ’s Theory of “Harmony of Nature and Man ”
ZHANG Feix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
Abstract : LI Zehou takes “the converted creation about tradition into modernity” as the total cultural logic, and puts ont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explai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roposition of “traditional harmony of nature and man” in revealing “real existence of human”. Based on this,LI Zehou makes a cultural history struc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n uses this structure to clarify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ouble line cultural logic of “Confucian and Taoist complementarity” and “living in the world”. The aesthetic ideal of “harmony of nature and man” with “human” as the core is expounded. As a result, LI Zehou realize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Western, Traditional-Modern”, and constructs the practical aesthetics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logical order of “culture-philosophy-aesthetics-culture”.
Key words : LI Zehou; harmony of nature and man; cultural logic; human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 2019) 05-0010-08
收稿日期: 2019-03-15
作者简介: 张飞翔(1991-),男,陕西渭南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露〕
标签:李泽厚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 文化逻辑论文; 人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