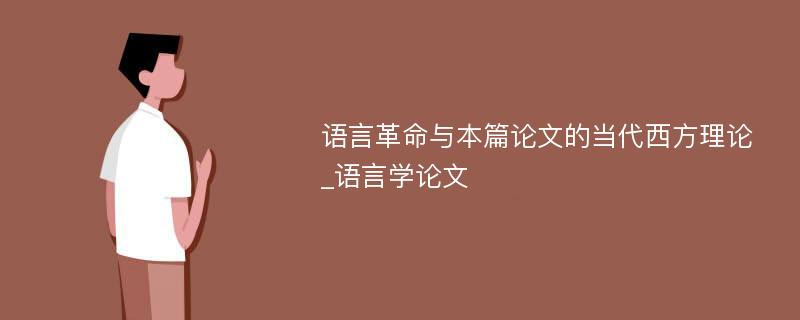
语言革命与当代西方本文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本文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 “镜式”本质的终结与语言本体观
西方人文科学在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传统的“镜式”本质观的终结。这种终结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人的“镜式”本质被废弃,转而开始向人本身、人的生存状况掘进。这一转化从康德就初露端倪,在后来的哲人如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的不断追问下,形成了20世纪以来的一股强大的人本主义思潮。另一是在这种背景下的语言的“镜式”本质的终结,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注:关于本世纪出现的“语言学转向”, 盛宁先生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本世纪初分析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哲学自身的探索方向转向了语言逻辑问题;一是本世纪60年代对索绪尔语言学的重新阐释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生成,标志着人文科学的认识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参见盛宁《“语言学转向”》,《思想文综》1996年第1 期。后一种“转向”拙文称之为“语言论转向”(王一川译语),以示区别。),从语言工具论转向了语言本体论,它是以分析哲学的出场为标志的,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人是打碎语言“镜式”本质的关键人物。
“镜式”本质是近代认识论对人的本质的基本规定。然而到了现代,由于提问方式的改变,近代认识论表现出了向现代本体论转换。康德晚年对“人是什么”的追问启示了后来的哲学思路。对人本身的认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认识,构成了一股强大的人本主义思潮。如叔本华的“意志冲动”、尼采的“生命力”、柏格森的“直觉”、海德格尔的“亲在”等,似乎我们又回到了“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命题之中。认识的本体化可以说是这一转换的基本特征。王岳川提出,“认识论不应再是关于如何把握自然实在的学说,而是关于如何领会人自身的学说;认识论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确定不变的复现和认识,而是具有了明显的‘生命—历史相对主义’色彩”(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7页。)。所以,“镜式”本质终结的关键在于,现代本体论完全放弃了近代认识论所持有的二分框架,它不再去研究人与外界的关系,研究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与被认识之关系,研究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与被认识之关系,而是思考人之存在本身,思考人之存在的价值、方式等;它不再去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有多大,人如何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事物,而是思考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人在认识论中是一个先验的前提,而在本体论中成为了思考的对象。从认识的二分模式到人的一元论,人的“镜式”本质终结就在这种转化中实现了。
“镜式”本质终结的第二维度是语言的“镜式”本质的终结。第二维度与第一维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认识与语言是相互对应、相互影响的。如人的认识来源与语言意义来源的对应,人的认识能力与语言反映事物真相能力的对应,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与语言对观念的关系的对应等,归结起来,就是认识的二分模式与语言的二分模式的对应。人的“镜式”本质的终结必然引起语言的“镜式”本质的终结。
20世纪开始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意味着传统语言观的终结。新时代的语言哲学家们认为,他们这次变革与历来所谓的哲学革命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他们不是去争鸣旧有理论是否错误,而是认为它们丝毫没有意义,进而干脆拒绝它们。分析哲学家们把目光转向了语言本身。他们提出,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揭示语言使用中的错误,阐释语言的意义(注: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1—42页。)。实际上,在他们的这些理论主张背后隐匿着他们解构二分模式的理论冲动。他们从关注语言与外物相符程度到关注语言自身逻辑的完整性,从关注语言的内容到关注语言的形式,从关注语言的目的到关注语言的存在。这一切表现出他们对形而上学语言本质观的唾弃,对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这种二分模式的存在价值的消解。
现代语言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确立起来的。它的基本观点可以大致归纳如下:1.语言是一面反映外界事物的镜子,这是一个假问题。语言本身作为一种抽象符号不存在与外在世界的对应关系,语言对事物的命名并不表明语言的存在取决于事物的存在。语言命名是任意的而非必然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它实际上不过体现了人自身对事物把握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把语言与外界隔绝开来,语言只存在于语言自身之中。这是从二元论走向一元论的关键。2.语言与观念(或思想)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是假问题。语言不是一个容器,可以随便填装任何东西而不发生改变。实际上,语言与观念是直接同构的,没有语言的观念是不可想象的,反之同样是不可想象的。3.语言的意义不是由传统理论中所谓的观念或事物决定的,而是由语句出现于其中的语境决定的。弗雷格的名言就是:“一个语词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注:引自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页。)。这种语言思想成为现代语言观的一个核心思想,而且不仅是语言本身具有自在自决的特点,由语言构造的一切符号、概念、命题等的语言或语句形式都统统具有这种特点。4.传统语言观认为的语言本身所表述的真理及其理性知识不复存在,真实与真理成为一种虚构之物。卡西尔曾指出,“那种声称语言具有真理内容的幻想业已完全破灭;所谓的真理内容只不过是一些心灵的幻影。……不仅神话、艺术、语言是幻影,就连理论知识本身也是幻影;因为,即使是知识也永远无法按照原样来复现事物的真实性质,而必须用‘概念’来框定事物的性质。‘概念’又是什么东西呢?概念只不过是思维的表述,只不过是思维创造出来的东西罢了;概念根本无法向我们提供客体的真实形态,概念向我们展现的只是思维自身的形式而已”(注: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页。)。所以,现代语言观把语言不再视为一种工具,而是视为一种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
6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的“语言论转向”对语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其中一个关键性环节就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重新阐释。索绪尔是生活在本世纪初的一位瑞士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思想反映在由他的学生根据笔记编辑整理、在他死后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被巴特、德里达等人发掘出来,在他们的至关重要的阐释中,索绪尔的语言学开始在新的意义上播散开来。如巴特对语言学地位的突出强调,德里达从意义生成及批判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角度对语言差异的关注,从不同侧面揭示乃至引申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从而也把语言问题进一步推向了人文科学的中心(注:巴特、德里达等人对索绪尔语言学的阐释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这里只是就本文论题举其要者作一介绍。关于他们各自对索绪尔的论述可具体参见他们的有关著作,如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和《立场》等。除了巴特和德里达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对索绪尔的语言学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如卡勒、杰姆逊等。)。索绪尔对当代的影响已经在西方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其语言理论的意义和地位正如罗比所说,“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注: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如果说本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只是语言学内部的一种转向,那么“语言论转向”则波及到整个人文科学。
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要建立科学的符号学。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并说“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科学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已把它归属于符号学”(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页。)。然而,巴特对语言学和符号学关系的阐释却离开了索绪尔的初衷。他说,“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颠倒索绪尔的断言:语言学不是一般符号科学的一部分,甚至也不是具有范导性的一部分,而恰恰是, 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注:转引自AnnetteLavers,Roland Barthes:Structuralism and After,Methuen&
Co.Ltd,1982,p.138.)。巴特还从符号的诸种系统的语言学特征方面,如服装系统、食物系统、家具系统、汽车系统等,对语言学的主导地位进行了分析和强调。巴特的这一置换和具体的阐释确立了语言学模式的权威,开创了语言学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语言学方法最终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的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德里达则是从关注索绪尔的语言差异(difference)问题入手的。语言差异问题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重点考察的一个问题,也是索绪尔理论的一个关于语言的意义如何产生和语言如何存在的关键性问题。索绪尔说,“如果我们从符号的整体去考察,就会看到在它的秩序里有某种积极的东西。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但是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段相配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7页。)。 所以,语言内部的差异是索绪尔寻求语言意义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独立的语言系统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德里达对索绪尔的差异概念进行了改造和发挥,由此提出了他的分延(differance)概念。分延不仅包含了索绪尔差异概念的基本内涵,而且更加深入和丰富。德里达把符号的差异问题从符号本身的声音和概念、能指和所指以及它们的序列存在之间的差异推进到了符号在空间和时间的存在之中,推进到了符号内在的历史语境(“踪迹”、“补替”)之中。德里达说,“只有认为‘到场’的(呈现于在场阶段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既联系于它本身之外的某物,又保留着过去的组成部分的记号,并被与其相关的未来的组成部分的记号所掏空时,分延才使意义的运作成为可能。……为了使在场成立,间隔必须把它与非它分割开来,但是在在场里构造在场的间隔,还必须同样地分割在场本身,并随在场一起分割一切在其基础上可能被设想之物,即任何存在——尤其是我们的形而上学语言所说的物质和主体”(注:转引自G.Dlouglas Atkins, ReadingDe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 Reading,the University Press ofKentucky,1983,p.18.)。 在索绪尔看来,意义来源于同一系统内部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来源于符号的“整个此在”(杰姆逊语)。而德里达认为意义在于符号此在的空间和时间的空隙,这是内在的历史性空隙,它浓缩于差异性的符号结构之中,构成一个张力场:在/非在、它/非它、过去/现在/未来,在这里相互作用;索绪尔表明差异是符号本身的一种基本特征,德里达则指出分延不仅如此,分延还是根除形而上学符号观的有效手段:对在场的分隔无疑是对语言本质始源的分隔。形而上学通常坚持存在某物(res)或所指, 先于语言或被语言所表达,这是构成形而上学语言的各种显现的根基。“正是德里达等人所主张的把能指和所指分隔开来的这一新的本文性功能,使得所指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始源”(注:Robert M.Strozier,Saussure,Derrida,and
theMetaphysics of Subjectivity,Mouton deGruyter,1988,p.218.)。从而,德里达用分延把差异的索绪尔式的意义生成功能推进到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推进到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从差异到分延给整个的人文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
索绪尔在巴特、德里达等人的阐释中的复活以及这种复活的被借用,反映了当代西方学界的一种普遍的思想动向,即对人文科学的结构问题和意义问题的关注,对语言学模式、语言学模式对非语言学模式进行消解的关注(注:我在这里之所以选择巴特和德里达作为当代西方语言问题和索绪尔复活的典型阐释者,是因为他们实际上表现出了两种不尽相同的倾向,巴特更注重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科学中的主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而德里达则更多地强调语言解构形而上学在场的价值;前者是结构主义,后者属解构主义。但两者尚有根本性的相通之处:无论是结构还是解构,它们都承认语言在人文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都承认语言的自在和自足性,都承认语言泛化对文化存在的符码化。这一问题甚是复杂,也从整体上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故仅在这里作一简要的提示。)。在这种关注中,一方面语言学获得了独立性和中心地位,获得了它在整个人文科学中的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还从“语言学转向”所形成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争执中解脱出来,把具有前提意义的作品形式主义研究推进到了实质阶段的本文研究。所以,仅从本文理论出台的背景来看,本文理论所涉及的就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如罗比所说的“整个社会和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本文如何涵盖、规范乃至支配非语言事物、世界乃至人的问题,是本文构造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意义的问题。
下篇 本文理论的建构与基本策略
我们之所以在讨论本文理论之前,用比较大的篇幅来考察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本文理论的建构首先是从文学领域开始的,而文学本文与语言之间又无疑具有天然的联系。(文学)本文是语言的产物,是语言的一种存在形式。但众所周知,在语言革命和语言本体观确立之前,(文学)本文与语言的这种天然联系所形成的不是本文(text)理论,而是作品(work)理论。作品理论是以古代和近代的语言工具论为基础的,本文理论则是以现代语言本体论为基础的。巴特曾对作品、本文与语言的关系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如果说作品可以根据它与语言的异质关系加以定义的话(从书的版式到社会历史决定因素等的一切),那么本文,就它本身而言,与语言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同质关系。 除了语言, 它什么也不是; 它只能通过语言而存在”(注:转引自Jeremy Hawthorn,A Concise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Literary Theory,Edward Arnold,1992,p.188.)。本文与语言的这种同构性导致了本文与语言之间的相互认同。本文把语言符码(code)作为自我特征的内在根据,它自身则是这一符码的展开和语境化。如果说“语言学转向”所变革的只是文学研究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即形式和内容哪一个对文学更具有本质意义,从而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文学内容的关注,对文学客体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文学主体(包括作者和读者)的关注,而文学观念的这一变化可以看成是本文理论建构的一个前奏,那么,“语言论转向”对语言与本文的同构性的确定则暗含了一种更为本质意义上的变革,即语言本体论与语言和本文同构论的结合把本文本身也推到了与语言同样的高度。这一变革在本世纪60年代之后充分地表现出来。本文理论从昔日的文学形式和内容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转向了本文的地位、意义和功能等方面的讨论,进而构造了一种普及于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一般而言,本文(text)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本文通常是指语言的具体存在形态,与作品或作品中的形式意思相近,通常它所强调的是语言本身的形式性;广义的本文则不限于语言和语言构成的作品,而是可以更加宽泛地指涉一切符号现象,它所强调的是本文符号的普遍性,本文符号的人为性,广义的本文更真切地构成了本文理论的范围。这时的本文不仅限于文学形式,而且在更加深入的层次上涉及了与语言、符号的关系;本文不仅结构语言本身,而且还对非语言事物进行意义化建构;本文不仅把语言的言说方式、语言意义背后的人的存在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而且还把意义输入到一切可言说的对象之中。
本文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大抵始于英美新批评,但这时的本文实际上只具有与作品或作品的形式相似的意义,常常与作品或形式一词替换使用。本文概念真正获得它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内涵和意义,是在随后而来的作品结构化和结构本文化的浪潮中,作品结构化把作品的具体问题引向了作品的抽象问题,引向作品的类型和形式上所体现的结构性,从而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策略,如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就是把作品进行结构化研究的一个先例。在这部被西方视为结构主义的前驱性著作中,弗莱指出,所有的文学作品说到底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喜剧的、浪漫的、悲剧的、嘲讽的;这四种类型可以视为与春、夏、秋、冬有着象征性的对应关系。“所有的文学表达被很少的几个永久性的最一般的文学概念所制约,‘四个叙述的前发生的’范畴,它们‘逻辑地先于’普通的文学类别”(注:Frank Lentricchia,After the New Criticis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p.8.)。弗莱的这种研究模式无疑是结构化的,它使我们不是再去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开始面对抽象结构。当然,他还没有达到结构本文化的程度,也就是说,还没有在语言结构的意义上来研究本文结构问题,但对抽象结构的关注从根本上为语言模式从总体上介入作品分析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就潜在地为本文理论的真正形成奠定了基础。60年代是结构本文化的时代。叙事学继续开拓弗莱的思路,不仅去寻找作品的深层结构,如托多罗夫对诗学的定位,诗学“不同于对个别作品的解释,它不是要揭示个别作品的涵义,而是要获得关于统辖每一部作品产生的最一般法则的知识;但是,与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不同,它是在文学自身内部寻找这些法则。因此,诗学是一种文学的‘抽象的’和‘内在的’方法”(注:TzvetanTodorov,Definition
of Poetics,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Theory:A Reader,ed.K.M.Newton,Macmillan Education,1988,p.134.)。而且文学研究还更多地表现出对语言学模式的归附和演义,从语言的基本结构和模式出发来寻找本文的模式和范型,寻求对本文的解释。如托多罗夫的《从〈十日谈〉看叙事作品语法》一文,就试图从叙事作品与语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入手,从词类的划分以及体现出同类划分的语态、语体、语式和时态入手,来分析本文的语言学特征。“对叙事作品的分析,能使我们划分出专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具体单位,它们与词类划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注:兹维坦·托多罗夫:《从〈十日谈〉看叙事作品语法》,见张寅德选编《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其实, 在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布雷蒙等人的叙述学研究中,托多罗夫的倾向是他们普遍的倾向,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更加曲折而已。巴特甚至说,“文学不再是关于‘人类心灵’而是关于人类语言的科学的或起码的知识,它所研究的不再是第二位的作为修辞对象的形式和人物,而是语言的基本范畴”(注:RolandBarthes, 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in the StructuralistControversy: 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of Man,ed.Richard Macksey and Eugen'o Donato,the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p.45.)。这里,语言学模式不仅主宰了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而且是从根本上表现出了语言本身被置于一个高于叙事作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地位。我们说,这正是本文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基本表现形态。
在文学研究之外,本文理论更有效地运用了语言学模式的垄断权力。就本文与语言的关系而言,语言学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本文观念的变化。在60年代的“语言论转向”的催化下,语言已经从语言学的既定轨道上脱离了出来。按照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观点,语言已经具有了赋予有形对象以形式的能力。语言预构对象,把对象明白无误地显示在一个既定的结构里,其结构和显现对象的方式就是通过语言的文化符码。巴特指出,所谓符码是指语言构造现实的所有形式,从而预示了我们对现实和我们自身的知觉。例如,用于句子语法形式的句法符码,描述一定因果逻辑的叙述符码,制约我们所观察的决定文化意义的语义符码,等等(注:参见Irena R. Makaryk General Editer andCompiler,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Approaches,Scholars,Term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3,p.640.)。 恰恰就是这种对象的符码化,我们对卡勒(Culler)的如下描述有了切实的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和与之相关的不是物理的客体和事件,它们是有意义的客体和事件:不是复杂的木结构而是桌椅;不是物理姿势而是礼貌或敌视行为”。“倘若我们去理解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世界,我们必须不是将其视为独立客体而是意义结构、关系系统,这一结构和系统通过使客体和行为拥有意义而创造了人的世界”(注: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25.)。这种意义无疑是来自符码化,这种符码化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本文性(textuality)。本文性把外界包容在本文自我的规则中,给外界赋予意义,反映了本文地位和强力。这一特点把本文的范围推到了它的极点,它把一切事物(无论是本文的还是非本文的、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统统视为本文或本文的表现对象,这就潜在地承认了主体与对象始终只能是一种本文性的关系。不仅对象的存在是一种本文性的存在,就连主体的存在也是一种本文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在本文之外涉及事物。离开本文,一切均不可想象。德里达说过, “没有任何东西在本文之外”(注: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rans.GayatriChakravorty Spivark,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p.158.)。尽管德里达的出发点是欲揭示形而上学本身的虚妄性,即他把可识之物统统包括在本文之内,而把如本质、终极之类的形而上学东西去掉;但这一表述同时也说明了本文的能量。任何对象都可以被视为有待破译和解释的本文,意义只能停留在本文的全部的此在之上。
从这里,我们进入了本文的语境(context)之中。 语境是本文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暗示本文所蕴含的背景,更主要的是把背景作为本文构造的有机环节,而不是与本文疏离的独立外物,它要说明的是本文意义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意义的深层形态。语境如同一个大本文,正如西尔沃曼(Silverman)所说,“语境不是本文的一部分, 也不同于本文,但它构造本文。语境可以是政治的、历史的、文学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尽管其中的许多特点完全被认为是与本文相异的、外在于本文的、与本文不同的。然而,它们与本文相伴随并被本文化了(texted)”(注: Hugh
J. Silverman,Textualities:betweenHermeneutics and Deconstruction,Routledge,1994,p.85.)。 本文性与语境互为表里,本文性指本文的向外扩张,表明了本文的同化能力,构造对象的能力;而语境则是本文性的内在内容,表明了本文的内在视野。语境之所以与我们通常所谓的“背景”或“条件”不同,就在于它是显现在本文之中的,是经过本文化处理过的,而不是外在于本文的一种“客观的”东西。所以,语境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对本文意义可能性的限制及其限度。 与语境有关的另一个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则从不同的角度对本文意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揭示。“互文性”是由克里斯蒂娃提出并加以阐发的。在本文性泛义地强调外界本文化之际,“互文性”却把本文化进一步嵌入了具体范围和操作之中。“互文性”据说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关系密切。在巴赫金看来,本文存在着横向(主体—接受者)和纵向(本文—语境)两条轴线,由此形成了对话(dialogue )和互渗(ambivalence)两种关系。对话指的是语言本身固有的语言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生活可能性的领域”;而互渗则指的是“把历史嵌入本文,把本文嵌入历史”。这两条轴线的功能意味着,“人和本文的建构都是引语拼合的结果;任何本文都是对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注:Julia
Kristeva,Positions,trans,Alan Bas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26.)。所以,本文的意义问题可以说就是一个本文与本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先在本文(包括共时的和历时的本文)对后在本文的启示和规范以及后在本文对先在本文的阐释、借鉴和延伸的问题。在《诗歌语言中的革命》一书中,
克里斯蒂娃进一步指出,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意味着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其他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因为这个词不能在‘起源研究’这一平庸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所以我们选用了互换(transposition)一词, 它恰当地说明了从一个意指系统到另一个意指系统这一过渡所需要的一种新的规定性联结——阐释的和指示的立场”(注:转引自Susan Stanford Friedman,Weaving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Re)birth of the Author.)。可见,“互文性”具有双重焦点:一方面,本文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其他本文的存在,因为某事已经被先在地书写了,也就是说,一个本文从一开始就在其他本文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决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历史起源式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后者在克服前者的决定性中不断用阐释来完成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互文性”把本文放入历史和社会之中,这种历史和社会同样是本文性的,是作者和读者通过把自我植入其中而加以重写的产物,本文在这里起到了一种标志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文性”与其说是对本文与它先前的某一特定本文之间的关系的命名,不如说是本文参与不断变换的文化空间的一种标示。语境通过“互文性”揭示了本文意义的建构方式。
本文理论从根本上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人文科学提供了新的基础,即我们已经粗略讨论过的本文性和语境问题。此外,本文理论的修辞泛化策略也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在本文理论中,修辞问题已经不仅局限在文学本文之中,而且扩展到了整个人文科学本文,从而形成了整个人文科学本文的修辞化特征(注:注意,这里所谓的“修辞”不是指语句意义上的修辞,而是指一种具有文体风格意义的修辞。)。从修辞化角度来讨论人文科学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任何本文都是修辞性的也只能是修辞性的,其中暗含着或隐或显的非本真性和虚拟性。关于这一点,怀特(Hayden White)提出的语言转义论(tropology )就是一个重要的论证。转义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传统认为,事实构成历史话语的“身体”,而文本只构成它的多少具有吸引力但绝非根本的“衣衫”;现代则认识到,写实性本文与想象性本文一样,其中的语言既是形式也是内容。所以,历史本身的叙述性成为了决定历史特点的东西。这种叙述性,据怀特所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展开。一是它在“外展”方面,即:1.事件固然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但把它们整理为特定时间单位所使用的编年代码却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2.把事件转化为故事(或故事的集合体),需要在历史学家的文化传统所提供的许多种不同情节结构中进行选择;3.历史学家的任何论证不仅涉及到事件本身,而且涉及到事件编写成某一类故事所使用的情节,所以,历史话语的论证是第二级的虚构物。另一是它在“内含”方面,这包括了修辞学所提出的“隐喻”、“借喻”、“提喻”和“反讽”等四种比喻,它们与四种基本的本文情节类型相互联系,即(上面提到的弗莱的)传奇、悲剧、喜剧和讽刺。“它们也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话语无论在它给事件赋予意义时所使用的策略方面,还是在它所涉及的真实性的类型方面,是如何与虚构性叙述相似或实际上相汇集的”(注: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修辞泛化可以说是本文理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它潜在地反映了语言和人的存在的泛化,与我在“上篇”论述的两个“转化”密切相关。
由于修辞泛化,本文也必然表现出自身的多样性特征。本文的多样性包含这样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本文结构的开放多样性,一是本文阐释的多样可能性。关于前者,本文理论首先解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关于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尽管卡勒认为,解构所倡导的本文理论并不谋求消除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
建构一种一般的无差别的本文性(generalundiffierentiated textuality),而是强调“对哲学作品的真正的哲学化阅读……就是把它视为文学,视为一种虚构的、修辞性的结构,它的要素和秩序是由不同的本文需要确定的;相反,对文学作品的最有力和最恰当的阅读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哲学的姿态,以取得支撑它的其所涉及到的哲学对立的意义”(注:Jonathan Culler, On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Routledge,1989, p.150.)。在我看来, 这一解释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说明哲学与文学之间的不是混淆而是区分的关系。实际上,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在整个西方的人文科学的本文中。譬如,在福柯的历史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摒弃历史知识的传统阐释观念,如怀特指出,福柯“拒绝了一切传统历史和科学论述中被当作阐释的‘还原’策略”,因为在福柯看来,“人文科学一直为话语的修辞所控制,在其中,这些修辞构造(不仅仅意指)它们假装研究的对象”(注:海登·怀特:《解码福柯:地下笔记》, 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6页。)。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具有同样的性质。拉康不同意无意识先于语言,而认为“无意识的原料与语言的原料是相同的,无意识是结构化了的语言”(注:Jacques Lacan,Of Structure as an Inmixing of anOtherness Prerequisite to Any Subject Whatever,in the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p.188.)。所以,在拉康那里,精神分析转化为一种语言分析,从而导致了一种分析的结构化。本文理论的这一特点实际上是在语言与本文同构基础上的对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抹杀,是以解析意义的方式来理解一切的本文存在。从而,无论何种本文,只要它是本文,就难以摆脱语言本身的风格气息,即它的修辞特征。哈贝马斯曾指出,“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之间的界线,逻辑意义与修辞之间的界线,以及严肃言语与虚构言语之间的界线,这一切在一场广泛的文本的浪涛中被冲洗掉了。”所以,“保罗·德·曼将卢梭与普罗斯特和里尔克的著作不作区分地阅读。德里达对胡塞尔和索绪尔的研究与对阿尔托研究也并未作出刻意的区分”。(注: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 页。)。
关于后者,一种本文,它的解释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是存在某种权威的解释,还是各种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这是一个普遍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理论的回答是,任何一部作品,一个本文,无论它是文学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伦理的,甚至科学的,都不可能具有某种统一的标准,都不存在客观的权威。因为索绪尔和德里达对于语言本质的揭示,已经从根本上把本文的终极本质根除了(注: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想表达不可表达的东西的企图,乃是一种想通过发现其意义直接得自世界、得自非语言的词语来摆脱语言的最近的、最疯狂的形式。这种企图自古希腊以来就一直继续着,但却注定要失败。因为语言,正如索绪尔所说,乃是各种差别的表演。这就是说,语词的意义只能来自与其他词的反差效果,例如“红”只能通过与“蓝”、“绿”等比较才能有其所指的意义。“存在”如果不与“存在物”比较,不与“自然”、“上帝”和“人类”,甚至事实上不与语言中所有其他的词比较,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一个词获得其意义的方式是自亚里士多德到罗素为止的哲学家所期望的:成为某种非语言的东西(如情绪、感觉材料、物理对象、理念或柏拉图的形式)的直接表达。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5页。)。在一个本质虚无的本文中,也就不存在如何寻求本文的真理性问题,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内涵在等待人们去寻找和发掘。例如,德里达在解构斯特劳斯的神话学本文时,就指出过,“神话没有统一性和绝对本源,神话的焦点或本源总是闪烁不定、不可实现,是并不存在的影子和虚像……这种无中心结构的话语,亦即神话,其本身是不会有一个绝对的主体或绝对的中心的”(注:J.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lated by Alan Bass ,Routledge,1978,pp.279-280.)。这里所谓的无中心、无本源也就是把神话放到了一个漂浮的境地,所以人们不可能从神话的背后寻找到什么绝对不变和恒定的东西作为客观标准的基础,从而也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客观标准。本文的这种本质真空,从另一面说,就是语言修辞化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对语言的终极本质意义的拆解中,它的最基本的语言表述就是一种非逻辑式的、非“科学式”的修辞性表述。修辞使得语言与表述对象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和想象的关系,一切“真实的”、“确定的”联系都在“隐喻”中被遮蔽乃至埋葬掉了。与此同时,关于本文阐释的合法性问题必然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合法性问题的提出暗示着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合法性建构是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因为在所谓的本质主义发生危机之后,如罗蒂所言,这种本质或本体可能是某种像上帝、或柏拉图的善的形式、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实用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出场的形而上学”,即希望发现某种固定不变的、使我们有可能用认识来替代意见的东西(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作者序》。)。在本质主义遭到普遍怀疑之后,人如何在一种空前的没有本质的真空中来确立本文的意义,来确立自我言说的“正确性”,这确实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又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解释学中有所思考和解释,但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甚至在纷争中变得更加困难不堪。
整个20世纪是西方人文科学的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从这一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本文理论,可以看到,本文理论在语言本体观的支撑下构造了文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之后又把本体模式用于具体实践,形成了人文科学中最强有力的和最具普遍意义的方法。这实际上在本体与方法之间完成了一场复杂转换。当然,人文科学中是否需要一种本体论,是否需要一种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追问,这恐怕需要思考和提问下去,尽管这一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了本文理论自身的范围。但本文理论所给予我们的无论是本体意义上的还是方法意义上的提示,都是不应该忽视和回避的,也是不能忽视和回避的。
标签:语言学论文; 索绪尔论文; 德里达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普通语言学教程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语言文化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