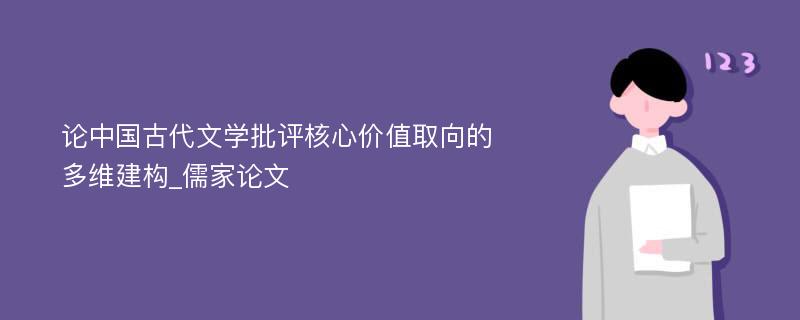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核心价值取向的多维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文学批评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0)06-0018-08
文学批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传统和现实,这既是在历史逻辑性和一脉相承传统的内在结构逻辑性中生成和构建的,又是在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的“通变”、“因革”关系中不断创新和升华的。因而,批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必须以中国古代批评优秀传统为基础,一方面应吸收、借鉴和利用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以此作为构建的重要的基础和资源;另一方面利用其夯实中国批评的根基,以培育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批评精神,强化批评在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再一方面应将其作为文学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批评贯通,作中国文学批评整体观,使其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融合,达到推进中国批评当代发展的目的。
考察中国古代批评发展的源头,无疑会追溯到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国学传统的文、史、哲源头。先秦时期在诸侯纷争中崛起的诸子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批评的思想根基和理论源头。儒家的“仁义”、“礼乐”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既体现了多样化和多元性的不同价值取向,又体现渴求统一、寻求和谐、追求安定的共同价值取向。尽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及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后,儒家思想被社会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统治思想及其主流的核心价值取向,并经过汉代儒学、宋明理学的不断强化,逐步构建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但也不可否认在儒家思想统治的同时,道家、墨家等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和影响,也并不排斥儒家思想对道家、墨家思想的吸收、借鉴和改造,更不能漠视儒道互补的思想协调和融合,逐渐在文化思想争鸣、碰撞、对话、交流中融汇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思想精神传统,构建人文精神核心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人文精神核心价值取向构建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在历时性的历史逻辑以及传承和革新关系中建构批评传统,又在共时性的逻辑结构和内在关系构成中生成批评价值结构体系;既立足于儒道文化思想的互补共生的精神传统,又扎根于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实践,形成三维立体的批评核心价值取向。所谓“三维立体”指批评取向维度的三足鼎立的结构层次,即和谐价值取向维度、自然价值取向维度和“心学”价值取向维度,三者相互作用,互为交流,构成人文精神核心价值取向整体,形成结构性、系统性和统一性的价值体系。
一 批评的“和谐”价值取向维度的构建
中国古代批评观表现出鲜明的和谐价值取向,形成其人文精神的一大特点和亮点。早在原始氏族社会中,一方面中华民族文明始祖尧、舜、禹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形态孕育氏族和谐、族群和睦的理念;另一方面,在原始巫术、原始宗教仪式中确立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并在“万物有灵论”中确立了“神灵”观念,以“神”生成和谐万事万物之理念。进入周代奴隶社会后,人与自然的神事逐渐转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人事。杨华在《先秦礼乐文化》一书中指出:“研究古代的中国文化就必须首先从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先秦时期有过重要影响力的礼文化着手;而研究古代社会的礼文化又不可忽视对古代乐文化的研究,二者缺一都会陷于片面和疏漏。”[1]其原因就在于礼乐协调补济的和谐关系,“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乐论》);乐的功能价值主要在于和,“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2],可见,诗教、乐教的教化目的指向和谐。“礼乐”之制是等级制社会中“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乐记·乐论》),通过礼乐协调、互补、调节而导向和谐的方式,也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礼制与乐制的和谐构成形式。这在先秦元典中都表达出和谐理念精神,也在诸子百家争鸣中,儒家继承和发扬周代礼乐文化精神传统。无论是此后被儒家奉为四书五经之经典,还是《周礼》《礼记》《礼仪》的“三礼”元典,礼乐价值观、礼乐制度、礼乐文化都导向和谐的社会价值取向。儒家倡导“和为贵”、“中和之美”、“中庸之道”、“温柔敦厚”、“温、良、恭、俭、让”、“仁者爱人”等,无不彰显“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精神;道家倡导“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3]等观念也凸显“自然之道”的人与自然和谐之精神。尽管儒道之和谐精神中因流派不同而有所区别,儒家旨在以伦理道德教化来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家旨在以回归自我心灵的自然无为方式和谐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但两者在核心价值取向的和谐理念观上则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文学批评在这一基本理念精神及其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构建核心价值取向。上古最早文献《尚书》中所记载的、被朱自清称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说:“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4]这段在观乐后的批评集中体现和谐精神,可谓批评核心价值取向生成产生的标志。其中出现的关键词“和”与“谐”是核心范畴。“和”与“谐”首先说明“乐”作为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达形式,故而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以及“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诗、乐、舞的和谐整体表达形式;其次,说明“和”与“谐”是文学艺术最为内在形式的节奏、韵律、声调、音色的基本要求,“八音克谐”更说明只有使不同的音符和声调协调搭配才能构成和谐悦耳音乐之道理。再次,说明制乐、奏乐所表现的内容与形式除了要协调搭配外,还必须在表达情感和思想内容时注意调节,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审美表现和欣赏效果,说明审美情感要素关系之间的调节与协和的艺术辩证法之道理;最后,批评揭示出艺术更深层次的内涵及更为深广的社会文化作用:“神人以和”,说明艺术不仅提供审美价值,而且提供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神”与“人”之关系在当时可谓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集中体现,早在原始巫术、原始宗教仪式中孕育和生成的“乐”,其本义是用以人神沟通及其敬神、拜神、娱神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和冲突,并以神来协调彼此之关系,从而依托神灵保佑、神灵附体、神灵感应而强化人自身的力量,以其信仰和崇拜形成人内心的精神支柱。故而乐所追求的“神人以和”目的和境界,也是审乐中追求的“神人以和”的社会作用和效果。由此可见,作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所言之“志”其实就是追求文学艺术“神人以和”的和谐理念精神之“志”,这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之根基,而且也主导和引领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发展方向。无论“诗言志”此后如何解读和阐释,也无论“诗言志”的内涵和外延此后发生如何的变化,“志”或作为志愿、志向、志气的表达,或作为情感、情绪、情志的抒发,或作为思想、功用、意义的传达,都表示“志”就是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表达,其“和”、“谐”显然是情感取向、思想取向、意愿取向的实质性内容,可谓是文学艺术追求的核心价值取向。
明白此理,我们就不难理解“诗言志”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均有所表述和传达,尽管百家之说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立场和方法的解说和发挥,甚至汉代还有过“诗言志”还是“诗言情”,抑或“情志一也”的讨论,这不仅没有影响“诗言志”在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中的奠基地位,而且还在进一步巩固“诗言志”地位的同时强化了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和谐精神的作用和意义。
先秦儒家孔子在其诗教、乐教的“礼乐”关系框架中来阐发“诗言志”的价值取向。孔子论诗实则是论《诗》,即特指《诗经》,“《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5]”这是在诸侯纷争、礼乐失调语境下儒家试图拨乱反正、重整纲纪的“正名”结果,其取向无疑是以和谐作为正面、正确的价值取向来倡导。“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在提出文艺的兴、观、群、怨社会功用中特别看重的还是以“思无邪”的正确导向来调节社会人际关系,其目的是指向和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看中的是用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大目标、大方向,诗可用于从政治国,协调和治理国家内外各种关系;诗可用于出使外交,协调和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和指向也是为了社会和谐。孔子论文,主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代礼乐制度是孔子追求的礼乐协调的和谐社会。因为“礼乐”与“仁者爱人”相通,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是依靠“仁”者的爱人之心建立,也是儒家人文精神及其人格道德精神的体现。孔子论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既强化了乐在成人、育人中的作用,又说明了礼、乐、诗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强调“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子路》),正礼、正乐是孔子拨乱反正以维护礼乐制度和谐统一的初衷,故而“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对诸侯纷争中犯上作乱的破坏礼乐制度的行为表示愤慨,也对“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表示不满,其目的是维护秩序,希望和谐。从文艺内部关系的协调而言,儒家主张“文质彬彬”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统一;“尽善”、“尽美”的真善美关系的统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与理关系的统一;“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的统一,等等,从而构成儒家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此后又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追求的核心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批评自魏晋南北朝进入自觉时代开始,历代文论批评家一方面在儒家思想文化大背景下构成主流、正宗、正统的核心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在吸收、传承和发扬和谐文化传统中确立人文精神。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气”说,不难发现与儒家孟子所倡导的“浩然之气”的“养气”说关联;陆机《文赋》提出“缘情”说也对儒家“情志一也”的阐发中进一步拓展;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宗经”、“征圣”更能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文与道、圣、经的关系中建立起和谐生态关系;钟嵘《诗品》的“滋味”说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的“乐味”说有一脉相承关联。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论文,陈子昂、白居易论诗,也无不与儒家和谐思想文化关联;宋代的苏轼、黄庭坚论诗评词,朱熹、二程论文说理,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基础;元明清批评的主流、主导倾向无疑也与儒家和谐核心价值取向吻合。无论历代批评家提出任何观点和学说,在最基本的理念和最基本的思想取向中,都会打上儒家和谐思想文化烙印,因为文学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来构建的,从而也使文学及批评构建和谐核心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批评范畴,诸如意象、意境、神韵、滋味、体性、通变、因革等都会表现出意与象、意与境、神与韵、滋与味、体与性、通与变、因与革辩证关系的和谐协调的取向;中国古代批评的艺术辩证法也在彼此对立、对应关系中体现和谐精神,道与法、言与意、心与物、情与景、浓与淡、阴与阳、文与质,等等。这足以说明儒家和谐精神对文论批评的影响和作用,也足以体现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核心价值取向的和谐维度,从而集中表现为对和谐美的价值追求。
二 批评的“自然”价值取向维度的构建
中国古代批评在两千多年发展中不仅形成和谐美的核心价值取向,而且也形成自然美的核心价值取向,这是道家思想文化影响的结果。先秦道家思想源远流长,这一方面应与远古初民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缔结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有关,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及其意识形成道家思想文化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应与周代的礼乐制度相应而独立的因民间信仰系统及其约定俗成的习俗惯例构成的民间文化制度有关,其天、地、人合成的宇宙观、自然观构成道家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道家以“道”为名确立“自然之道”的核心价值取向,建构起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道”的宇宙本体论和自然无为方法论的思想文化体系。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是其理论核心[6]。任继愈综合各种观点解释“道”有五种含义:一是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二是自然界的运动;三是最原始的材料;四是肉眼不见,感官不能直接感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五是事物规律。[7]故而“道”带有客观唯心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性质和特征。庄子的“自然”主要有三方面义项:一指自然界,是相对于人而言确立的自然,指宇宙万事万物的客观存在及表现状态,故而以“自在而然”来表述其性质和特征颇为恰当。所谓“自在而然”强调自然本身的属性和存在价值意义,自然存在本身是这样就这样,具有自身规律和内在逻辑性,具有自身存在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定性。故而庄子主张“天地有大美”,“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知北游》),“天籁”之声(《齐物论》),“自然之命”(《天运》)的自然之道和自然之态。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确立的顺应自然的人的生存状态,也就是相对自然而言人性的自然状态,这可用“自为而然”来表述其性质和特征。所谓“自为而然”也即自主而然、自己而然,强调以自然无为的状态和表现方式呈现自身,而反对以人为之性来改变自然。故而庄子主张“以鸟养养鸟”而不是“以人养养鸟”、“天籁”之声胜于“人籁”之音,“天乐”超于“人乐”。三是在对人类的行为方式和表现方式的自然无为要求中强调顺应自然,这可用“自然而然”来表述其性质和特征。这是从人的“无为而无不为”角度强调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对自然的态度,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精神。故而老子主张“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庄子主张“莫之为而常自然”(《缮性》),“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自美则不美”(《山木》),“无怠之声”,(《天运》),“至乐无乐”(《天道》)等。“自然”的三重义项分别从本体论、存在论、方法论角度确立道家自然思想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同时也是其“自然”观的三个维度,构成彼此和谐交融的联系,也构成三位一体的整体。其整体性表现在都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强调自然观,并构建自然核心价值取向的。道家自然观与儒家和谐观虽有很大区别,但也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有某些共通点和交叉点。道家追求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说明道家也主张“和”,也具有和谐价值取向;区别在于道家认定“与天和者”高于“与人和者”而已,从而体现出“自然”与“人为”的差异性。
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对道家思想文化的吸收和弘扬主要体现于道家的“自然之道”核心思想取向上。从表现方式看主要有四条渠道:一是旗帜鲜明地表达秉承道家思想文化传统,以道家为宗师、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建立其文论批评观及其理论体系,如葛洪、刘义庆等;二是化道为文,融道于艺,潜移默化地融合道家思想文化资源,表现出道家思想与艺术精神融合取向,如钟嵘、石涛等;三是以儒道兼容体现于外儒内道、先儒后道、儒道补济等复杂形态上,如刘勰、苏轼等;四是以佛教禅宗的表达形式而融入道家思想文化资源,道释兼容,道释互补,道释结合,如司空图、严羽等。从批评观价值取向看主要有四方面内容。
其一,自然本体论。以自然为本源、本原、本质构建文论批评理论根基。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就是探原文之道,并非在于简单探讨为文之道理,而是旨在探寻文之本原。“原”具有寻根探源以还原文之源流、根本、本质、本体之义。与儒家将文学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审视的视野相对,道家是将文学放置在宇宙天地、自然万物的大背景下来确立大视野;与儒家将文学与道德人格结合而形成“道德文章”的批评传统相对,道家则将文学的自由性与人的个性、天性及自然属性结合从而形成“时姿纵而不傥”(《庄子·天下》)的批评传统。故而刘勰综合儒道思想是在天、地、人关系中“原道”,从而将宇宙天文、地文的自然之道与人文自然之道结合而成文,其指向无疑是“自然之道”。也就是说文之道所原为“自然之道”,与道家“自然”观及其自然核心价值取向吻合。这一方面说明文艺是本原于自然,是在天文、地文、人文的大背景下构建的,宇宙天地万物与作为“天地之心”的人构成文艺本体和本质;另一方面,文艺表达的自然天地万物对象,其本原也是来自自然。《原道》曰:“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绵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8]自然界万事万物之所以千姿百态,其本原不在于“外饰”,而在于内在的“自然”,在于遵循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的结果。文艺表现社会生活,表现宇宙天地万物,其本质是表现其中蕴含的自然本性、本质、本原。故而,刘勰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本乎道”的文艺本体论,并以之构建了以自然为美的核心价值取向。
其二,自然创作论。从文艺创作资源和对象来源于生活的观念出发,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提出“感物”说,或“心物交感”说,或“情景二元质”说。所谓“物”、“景”无疑都与“自然”相关,甚至作为主体之“心”也离不开自然。曹丕《典论·论文》“文气”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9]158说明创作之心与自然之气的联系。陆机《文赋》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芳;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宜之乎斯文。”[9]190说明文艺创作是感物而心动的结果。刘勰《物色》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说明以物动情、以情成文的道理,其旨归合于“自然之道”,故而《明诗》曰:“人禀七情,应物所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当然儒家也提倡“感物”说。《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在“感物”说上,儒道殊途同归,区别在于儒家之“物”主要侧重于社会人事之“物”;道家之“物”主要侧重于自然天地万物之“物”。故而在“感物”说中体现儒道的和谐与自然交响的核心价值取向,共同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理论基础。
其三,自然真诚的创作主体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强调“真”,是儒道追求的共同价值取向。道家之“真”的追求主要体现于真情实感的朴素、真诚、自然态度上。庄子《渔父》提出“贵真”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在,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故而“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在《田子方》中以“解衣般礴赢”认定这种自然真率的艺术态度和创作状态,“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以“贵真”说评价绘画,提倡“真画”,以此推断就应有“真乐”、“真诗”、“真文”,从而也就有“真者”、“真人”,亦即具有自然真诚、朴素率直创作态度的艺术家。道家“贵真”说表现了以自然为美的核心价值取向,形成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一个优良传统,历代后继者不乏其人。汉代司马迁以“实录”强调文艺创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9]79;王充主张“疾虚妄”(《论衡·佚文》)以批判“众书并失实”(《对作》),从而提倡“真美”[12];魏晋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在“人物品藻”中提倡“尚自然”、“清畅似达”、“清通简畅”、“真独简贵”、“旷淡”、“掇皮皆真”、“真率”、“清易令达”、“风骨”[14]等等,价值取向无疑是自然真诚;刘勰提出“为情而造文”以反对“为文而造情”,是因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情采》);钟嵘提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诗品序》);等等。以此奠定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主体论,确立主体的自然真诚艺术态度的核心价值取向,引领此后陈子昂的“兴寄”说、李白的“清真”说、韩愈的“慎其实”说、白居易的“著诚去伪”说,一直到清末况周颐的“真字是词骨”(《蕙风词话》)说与王国维的“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人间词话》)说,构成贯穿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两千多年发展的重要脉络,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核心价值取向,并在真、善、美的有机统一中不仅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审美态度取向,而且也作为文学追求的价值目标,更成为批评的重要标准和原则。
其四,自然无为方法论。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自然”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自然而然、不假雕饰的表达方式,以此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艺术效果。因而,自然无为表达方式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呈现:一是以朴素无华、不加雕饰的自然表达,达到本真、本原、本来状态的真实表达效果;二是以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为的效果,这是在“有无相生”的艺术辩证法中强调了“无”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言之美”、“此时无声胜有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作用。“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相对于有意为之的人为刻意的“有为”而言的顺应自然而为,率性顺心而为;三是“无为”如同严羽所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无迹而为,所谓“无迹”指不留痕迹,亦指不留装饰雕琢的人为痕迹,更指庄子所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大美无迹。这在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方法论中比比皆是,如司空图《诗品》所描绘的二十四风格类型中,他所推崇的“自然”为:“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薄言情晤,悠悠天钧。”[15]他在描绘“自然”形态中提到一些关键词,如“即是”、“不取”、“俱道”、“着手”、“真予”、“不夺”、“空山”、“薄言”、“天钧”等,均可见源自道家的“自然无为”观。
除此之外,道家思想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还对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艺术辩证法产生了重大影响,道家的“有无相生”、“虚实相生”、“阴阳共生”、“美丑相对”等理论命题对文论批评的意与境、情与境、形与神、道与法、心与物、浓与淡、雅与俗、隐与秀、张与弛等关系调节中归总出艺术辩证法命题,其中蕴含自然美的道家核心价值取向不言而喻。
三 批评的“心学”人文价值取向维度的构建
先秦百家争鸣中崛起的儒道两家学说之所以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中成为两大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其原因不仅在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将儒家思想文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社会思想主流;也不仅在于魏晋玄学之风张扬了道家精神,并借助佛教在中国传播中佛道结合而形成禅宗从而扩大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儒道学说在先秦之际就夯实了思想理论之根,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之本,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从而不仅确立起儒道学说的核心价值取向,而且也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因而才对批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代批评对儒道思想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虽然都会有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和人们需求的种种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儒道的文化基因中也存在图新求变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早在儒道之前产生并对它们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周易》之“易”就从远古占卜算卦中总结归纳出变易思想。对《易经》阐释解读的《易传》无疑就包含有儒道结合的因素。《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两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3]这显然将儒道思想糅合为一体了。其实,先秦百家争鸣固然有对立的一面,但也有交流的一面,在争鸣中无形也会形成互补互动的效果,也会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具有殊途同归的共同价值取向。儒家的“和谐”取向和道家的“自然”取向,两者虽有差异性,但也有共同性。“和谐”包含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也包含结构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协调和谐,更包含有艺术精神、审美精神与人文精神、自然精神的和谐。“自然”包含有自在而然、自为而然、自然而然等层面的含义,也需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协调与和谐,也需要以顺应自然达到和谐自然的效果,更需要在“无为”中达到“无不为”的境界。故而道家也倡导“和”,提倡“天和”。庄子《马蹄》曰:“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这种理想化的“至德之世”表面看起来几乎与原始社会状况以及原始初民的自然素朴民性并无二致,但实质上则是为了更为具体、形象地表达老庄的“自然之道”观念,其中包含的宇宙天地之和、万物之和、民性素朴之和、人与自然之和等和谐指向也是十分明确的。这足以说明,先秦儒道学说尽管在百家争鸣中针锋相对,但在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上具有共同性;在和谐与自然的价值取向维度上虽各有侧重,但其基本精神和实质内容上具有共同指向,故而才会在历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相互作用,互为补充,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取向。
历代对儒道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并不是简单对儒道思想文化观念的吸收和借鉴,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通过对两者内在精神实质的融合、化解、交流,构建起立足于儒道精神又超越儒道对立而旨在儒道整合的核心价值体系。历代统治者尽管也有时而尊儒、时而崇道的取向,但也有尊儒而又崇道的取向;民间虽有尊儒崇道的不同选择,但更有儒、道、释并存的共同选择,儒道在历代发展中既双峰并峙、两水分流,但又有或明儒暗道、互为表里,或儒道互补、亦儒亦道,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两全处世原则和方式。与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繁杂多样有所不同的是,在文论批评中大体呈现的是儒道结合或交融的状况,据此可谓儒道和谐共生。
曹丕《典论·论文》以“气”论诗评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文气之“气”既包含儒家“养气”所涵养和养成的人格、品质的道德之气;又包含道家宇宙天地之自然之气,两者综合而成为自然生命与人格生命之气,故而有阴阳和谐、生命灌注、生气贯通、性格凸显的个性化特征,此后延伸为文气风格之论。
刘勰《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本体论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以“原道”、“宗经”、“征圣”作为文道之基础及思想理论之根源。《原道》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以说明文与宇宙天地并生及其文源自于自然之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以说明文、言、心三者的内在逻辑联系与心生-言立-文明的规律。这既是自然逻辑则与自然规律,又将文、言、心最终归源于自然;“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以说明“敷章”、“设教”均以“道心”、“神理”之自然为源头,阐发了文学以自然为根、本、魂之观点。据此说明,刘勰“原道”是原儒道整合之“道”。刘勰在《宗经》《征圣》又明确以儒家“经”、“圣”作为“宗”、“征”、“法”的对象,说明刘勰尊崇儒道思想并据此作为其文论批评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的用心,同时也是作为“文心”的重要支柱和基本内容,以此确立文学之“文心”的核心价值取向。这说明,刘勰是通过“道”、“圣”、“经”关系将儒道交融互渗而构建其文论批评体系的,故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文在“道”“圣”经的结合中奠定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向,构建儒道思想融合的核心价值体系。
钟嵘《诗品序》提出“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9]308并在《诗品》中以“滋味”评诗。“诗味”说源于“乐味”说,乐味是超乎于肉味之上的更隽永韵致、更延宕扩伸的“美味”,故而“滋味”说源自于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同时,“诗味”说也源自于道家,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从更为内在的辩证逻辑性中探究“乐味”之韵味源自于“有无相生”、“虚实相生”之理;老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更从其“虚无”角度凸显“滋味”的深层内涵,为“滋味”说提供了道家思想的理论依据。据此而言,钟嵘“滋味”说也是儒道结合的结果。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古代批评史中,儒道结合是主流取向,并不排斥儒道差异和对立;在儒道结合中侧重于儒或道也会有所差别。儒道之所以能结合互补,关键在于从文论批评角度而言,对儒、道思想的吸收、兼容进行了改造、革新和发展,融入了时代要求及其文艺审美需求。更重要的是文论批评对儒道思想的选择在于对其核心价值取向及其主导思想的选择,也就是着重于儒家“和谐”取向与道家“自然”取向的选择,两者的相关性、共生性、兼容性显而易见。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对和谐与自然的选择,不仅是对儒道思想的选择,而且也是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选择,在选择和整合中构建中国古代批评的和谐与自然交织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才有文学与批评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文学人民性、民主性、进步性的追求,对文学的“心学”人文精神的追求,对文学的审美境界和艺术价值的追求。
批评的“心学”人文精神维度的构建不仅源自于儒道结合从而体现出“和谐”、“自然”的价值取向维度,而且在于批评自身历史发展及其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文学的“心学”人文精神传承和发展的结果。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工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14]这足以说明“心斋”所悟的“自然之道”精神也是与文学的“心学”的人文精神沟通契合的。刘勰《文心雕龙》书名中的“文心”,就提出了一个足以让批评扎根、立本、树魂的重要命题,据此认定与人密切相关的“心”是文之根、本、魂所在,故而“文心”具有明确的“心学”指向。同时,“文心”与《周易》提出的“人文”也密切相关,故而也带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刘勰确立“文心”为文学内核和中心,首先是在天地人关系中来审视文学,天文、地文、人文之“文”是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原因,同时也是依天文、地文而创造人文的结果,故有“三才”说。其次,刘勰高度评价人心的作用,他认为在天地之间所生之人,实为天地之心,“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原道》),认定人心不仅是人之心,而且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秀、万物之灵长,这是因为人心集天地之精华而独有性灵。继而,刘勰指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这一方面说明刘勰对道家“自然”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心——言——文的逻辑发展和内在结构。这就提出“文心”来自人心的“心生”结果,“心生”才有“文心”。最后,刘勰进一步提出“道心”说,认定不仅人之有心,道亦有心,故而文学“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显然“道心”也是从“人心”推衍而出,有如“人心”指人文精神,“道心”指道的精神,故而“道心”可谓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既体现出道的自然规律性,又体现出人文精神。至此,道心——人心——文心就构成为文之道的基本脉络,也构成文学的内在逻辑结构,“文心”说也就成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心学”的基本观念和基本价值取向。正如黄霖、吴建民、吴兆路在《原人论》中指出:“‘原人文学论’,就是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千言万语,归根到底就是立足在‘原人’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核心就以人为本原。”[15]故而“原道”实质“原人”,再进而“原心”,从而与“文心”吻合。历代对“心”的功能作用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孟子提出“尽心”,认为“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荀子·解蔽》);董仲舒曰:“身以心为本”(《春秋繁露·通国身》);宋明理学家朱熹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朱子全书·观心说》);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心者,身之主宰”(《王文成公全集·传习录下》);刘熙载明确提出,“文,心学也,”(《古桐书屋六种》附《游艺约言》)等等,均在不断强化对“心”的功能作用认识的同时最终提出文学为心学的观点。这既是刘勰上承儒家思想的“诗言志”、“思无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养气”诸说的传统,道家“心斋”、“养心”、“齐气”、“虚静”诸说的传统,又是刘勰加以综合和改造而形成文学批评“心学”传统。此后历代文论批评家后继者不乏其人,不乏其论,围绕“文心”形成心、神、意、气、境、味、韵的传统,衍化为文论批评范畴意境、意象、神韵、神思、风骨、体性、知音、妙悟、心学等,也构成文学关系讨论的种种命题,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虚与实、无与有、真与伪等,更推动了与此相关的各种学说观点的提出,“师心”说、“童心”说、“赤子之心”说等。同时,在“文心”的引导下,又有“诗心”、“词心”、“曲心”、“书心”、“画心”等心学理论批评涌现。更为重要的是,“文心”不仅表现在“为文之用心”上,而且也表现为文学之心上,如同人的心脏是其生命表征和精神象征以及人体结构的中心枢纽一样,文心也是文学的生命、精神和中心枢纽,表达出文学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内涵。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16]批评确立“文心”观、“心学”观、“人学”观、“心声”观,也就确立批评的人文精神核心价值取向,涵盖了批评的和谐与自然价值取向,真、善、美的价值取向,人民性、民主性、进步性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古代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奠定了现代批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坚实基础。
收稿日期:2010-09-28
标签:儒家论文; 儒道论文; 道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道家思想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价值观取向论文; 读书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天道论文; 礼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