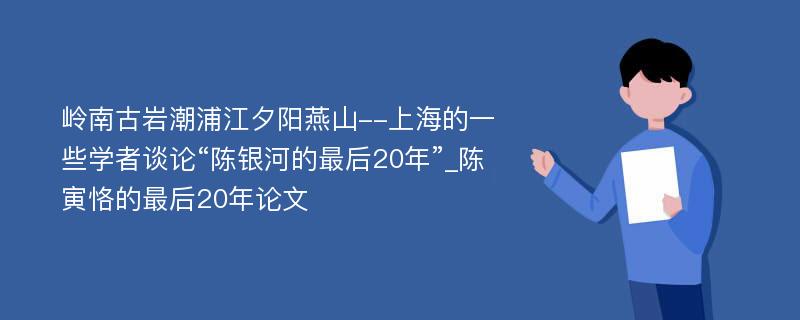
岭南孤烟直 浦江落日圆——上海部分学者谈《陈寅恪的最后2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岭南论文,落日论文,上海论文,学者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一本独特的传记《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由岭南学人写的书,虽然没有经过宣传包装,却不胫而走,在文化人中间引起很大震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陈寅恪现象”。最近,岭南学者吴定宇先生的《学人魂——陈寅恪传》已在上海推出,使大家更加关注这次由岭南到上海的文化潮流。为此,我们不妨听听部分上海学者的专题谈论。
殷国明(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我想,这本书之所以震撼人心,首先是和当代人的文化思考直接相扣。这些年来,人们不断地谈论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等问题,但是都未能真正深入下去,只是一阵从理论到概念的泛泛而谈,并没有真正涉及到真实具体的生存和生命状态,所以显得很虚假,很泡沫,有点搞“文化装饰”的味道。但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却不是这样,它首先展示的是人的具体生命和生存状态,确实一下子刺痛了所有中国文化人的神经。
陈惠芬(《上海文化》编辑):
我很同意这个看法。何为文化?何为中华文化的命脉和精魂?这一系列严肃的话题,不应该是口号式的哗众取宠,或者去搞什么概念演释。在中国,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生命现象,它有血肉,有悲欢离合,有几十年上百年的付出和代价,这本书就是用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生命唤醒人们对文化的责任。
夏中义(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这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的话题。在我看来,一本书写什么,往往比它怎么写,更引人瞩目。《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所以迷人,不仅在于它用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为一代宗师留下一帧线条准确的遗像,更重要的是,传主的弘毅气节及悲怆抗争,委实将现代学统演绎得很个性,很传神。
《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魅力在相当程度上沾了传主的光,而传主的人格魅力,对当下大陆学界而言,与其说源自他曾是清华园最博学的教授,源自他以诗证史,重在综合的治学模式,源自他失明后仍喋血著述《柳如是别传》等名著,毋宁说是因为他在风云变幻、残阳泣血的晚境,竟能如此独特且传奇地坚执其价值承诺。这就将现代学人最珍贵、也最难得的高文化质素即学统人格化,昭示于天下了。
李劼(华东师大教师):
我曾在1993年第4期《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将陈寅恪称之为继王国维之后唯一的中国文化亡灵守护人。不意最近面世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以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和具体细节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位文化守灵人。按照当今大众媒体的一般效应规律,此书并没有被“热炒”,但几乎应该读到此书的人们大都读到了。也许有人从中读出了灵魂的审视,也许有人从中读出了生存的艰辛,但不会有人从中读出玩笑的意味。在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面前,昆德拉式的聪明变得不无轻浮,甚至油腔滑调,因为倘若将陈寅恪最后20年的生存姿态看作一尊雕塑的话,那么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拉奥孔》。紧张的线条,阳刚气十足的悲剧气势,而从中透出的又是《柳如是别传》那样的高标见嫉和贞烈遭危。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在此已经不是潇湘妃子的写照,而是中国文化气脉的最后一位传人的实录。相形之下,尽管《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的作者在字里行间声泪俱下,但毕竟缺乏与这一文化悲剧相应的笔力,以洞幽烛微地照见出悲剧主人公种种悲悯和苍凉。在此,我突然想起两句古诗,可以表达陈寅恪最后20年的气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袁进(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
对此我也深有同感。学者首先必须生存,才能求“道”。然而古往今来,学者又往往为了生存而忘了自己“求道”的使命,只有守住“求道”立场的学者,才能真正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极左政治摧残中国学术发展之时,居然还有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学者,死守“求道”的学术立场,为知识分子立一楷模,虽属凤毛麟角,却令斯文一脉不致断绝。《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不仅为陈先生树了一块碑,也成了一面镜子,促使我们自省。
殷国明:
其实,这本书的一个中心话题是文化与人的关系。本来这个话题并不深奥,文化是人创造的,而人又受到文化的造就和制约,二者是互相依存,共同演进的。但是我们一旦进入到具体文化语境之中,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文化和人并不一定非常和谐,也并不一定非常一致,人可能会破坏和摧毁文化,而有的文化也会摧残人,压抑人,人成为被捉弄的对象。
陈惠芬:
比如在专制体制下,很可能制造出一种“非人”的文化,来和人自己作对,来消灭文化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精神。
周武(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
这也许正好显示了陈寅恪的文化人格价值。读完陆键东君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我首先想到的是40年代末叶景葵写给张元济先生的两句诗:“人与百虫争旦暮,天留一老试艰难”。陈先生晚年盲目膑足,蛰居金明馆,卧榻沉思,燃脂瞑写《柳如是别传》,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种悲死悯生的情景,我不知道,除了上述两句诗,还有什么文字能如此逼真传神地摹写出他最后20年那种异常尴尬的现实处境和傲然特立的人格风骨。他的遭际,实在就是中华人文在那段特殊岁月里的命运缩影。
20世纪中国文化始终笼罩着一股驱之不散的悲凉之雾,但在它的前半期犹有动心忍性以全副生命为民族文化的根命护持薪火或为古老文化续命弘道者。他们在内圣之不修而亟亟于外王的混浊之世里,一直抱持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激浊扬清,破相显性,摧惑显宗,以一种磅礴大气和清明理智捍卫人道之尊和生命之美,于暮色苍茫的“旧邦”中开掘出足以立心立命的鲜活的文化“新命”。然而,具有如此廓大气象和刚健心怀的贤哲如寅恪先生者,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已如长夜寒星,落寞孤明。无怪乎矢志拯亡续绝的唐君毅先生要大声疾呼中华人文大树崩倒,花果飘零。呼吸领会于这样“落英缤纷”的风气中,非有“虽千万人我独往矣”那样苍凉豪迈的孤往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样坚忍刚毅的担荷情怀,“平沉大地,粉碎虚空”那样悲壮激烈的强勇之力,以及“一掴一掌血,一棒一条痕”那样深沉内敛的自省功夫,要孤抱苦持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此种精神和思想,又如何可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若心志受俗谛的桎梏,又如何可能去惑解蔽,发扬真理!
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我倒也想起两句诗,是陈寅恪自己写的:“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我以为这是他精神形象的最好写照。他生命的最后20年,绝不是他人生历程的孤立阶段,毋宁说这是他在大变动的现代中国坚持自我的必然归宿。
百多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和相应的思想氛围的转折之剧烈、之频繁,回首反顾,往往令人心惊。“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冻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这貌似的退转,实际便是所谓“不进则退”,但不是“逆水行舟”的境况下,而是“随波逐流”的推动中——是义无反顾的往而不返,还是以自己的省思抉择方向。我们看到得太多的是知识分子在思想与思想间的跳跃,像踩着火热的烙铁无法驻足。似乎人们也习惯了用“飞跃”、“转折”之类的词汇来描述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却忘记了探问一下在这与时俱进的游戏中,真正的立场何在?诚然,真正的立足点在流沙般移动的现代思想潮流中的确立谈何容易,但至少不应将自己的尝试意向都抛弃了。辜鸿铭曾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他说世上只有两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是蔡元培,自从鼓吹革命就始终不渝;还有一个便是他自己,过去是保皇,今天还是保皇。这里表现了一种文化人格和气节问题。
夏中义:
说到文化人格和气节,还应加上现代学统。陈寅恪早就将这现代学统铭勒在碑石上了,这就是他为王国维所撰的著名碑文上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我所以将这八字视为现代学统之精髓,是因为无论古今书生,心底多少活着某种儒生道统,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当作一撮无根基的毛,总想归附到某张权力的皮上。他们不习惯用自己的学识、才华来兑现自我价值期待,而老想通过与权力的关系,或他们对权力的影响,或权力对他们的青睐度与御用度,来衡定自己的社会价位。亦即其座标是官本位的,学术纯属依附性或服务性行业,不具独立位置。这就导致古今书生情不自禁地靠近权力,以至孟子批评孔子,若数月无人请孔子去当官,他便会惶惶不可终日。王国维年轻时是将文哲之学看得很高的,但到晚年他亦挡不住紫禁城的诱惑而入值南斋任废帝的五品行走,过一番“读书当官”即儒生道统之瘾。故真能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当座右铭来践履,当现代学统来光大的,倒是陈寅恪,诚然这在大陆又亟须付代价的。
李劼:
这里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在先秦诸子是如此,后来的魏晋风度当亦然。文化的这种芬芳,生命的这种气韵,表面上看有类于伯夷叔齐式的迂执,实则恰好是《山海经》故事里诸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之类的英雄礼赞。这样的礼赞是如此的意味深长,以至于陈寅恪的双目失明都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仿佛眼睛的失明使陈寅恪的内心变得更为明亮一般,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世事面前,陈寅恪毋须一瞥,便能明察秋毫。在睁着眼睛的人们大都变成瞎子的年代,瞎了眼睛的陈寅恪却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袁进:
这种品质实在太宝贵了,但是在现代中国能够坚持很难。以陈寅恪“清华国学四导师”、国际著名学者的地位,以他“门生遍天下”的学界影响,以他无党无派、从不介入政治集团的纯学者身份,理所当然要受到政府的礼敬。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礼敬之中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一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不是在“大跃进”中发表文章,为“亩产万斤”提供“科学依据”吗?熊十力不也修改了自己的《新唯识论》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吗?“为帝王师”历来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郭沫若、刘大杰不正是为了获得领导人的青睐而“曲学阿世”吗?然而“士志于道”、“为帝王师”的目的其实是在“行道”,而不是“曲学阿世”。陈先生的可贵就在于他始终能坚持“志于道”的立场,把“道”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从而再现了“士大夫”的“风骨”。
陈惠芬:
也许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在于一个“人”字,它不仅源于人,以人为本,而且以人格为依托,以人的生命本质为归宿。而所谓文化情怀,并非老是怀抱一种“文化英雄”或“文化领袖”的心态,总想去树旗帜,提口号。我总觉得这是当代文人常见的一种“毛病”。
殷国明:
其实所谓文化,一旦失去了人格和气节的风骨,就没了生命意蕴,而且很容易成为一种“工具”文化或学术。就此而言,中国文化近百年所面临的危机,并非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而是在于自身被抽掉了人格和气节的生命基础,这是一种从内部开始的“釜底抽薪”的悲惨过程,结果使文化趋向于功利化和工具化。
李劼:
这也使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显得更有意义。自由只是为文化人格和气节提供一种可能性和空间。
袁进:
其实,“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先生争取的其实是最低限度的自由,是思想不受控制,学术自由发展的自由。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它的核心——思想学术的发展,而思想学术的发展不仅包含着外部允许自由争鸣的环境,也包含着学者主体必须具有独立的实事求是的自由探索精神。这是陈寅恪先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实质,也是他无可奈何之举;即使无法改变外部社会不容自由争鸣的环境,学者主体本着独立自由的立场不断探索,打破人为设置的禁区,其探索成果也是古人所谓“藏之名山”,终有出头之日。而学术发展之脉,终究不会断绝。学者忠实于学术自由发展的立场,这已经是退到极限了。
周武:
这也许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即使在陈先生所处的时代,我仍然相信许多人心里肯定认识到此一道理,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具有贵族气质的真纯学人坚持了,而更多的人则弃守了。于是,涵摄生命的永恒追问,相继让位于政治化的大批判吼声和商业化的骚动与喧哗!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浮乱名流、明星学者、媒体教授乃大行于天下!于是而有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学界当为后世所记者仅二人二书(二人指熊十力和陈寅恪;二书指熊先生“衰年定论”《乾坤衍》和陈先生“述事言情”的《柳如是别传》)之说!
陈引驰:
陈寅恪先生有他自己的抉择。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能够坚持的,只是在文化学术上守先待后的传承人立场。陈氏祖孙三代,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日渐疏离,陈寅恪先生晚年可以自慰的便是“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文化的血脉正是在这样的忠诚和坚持中流衍的。非道弘人,乃人弘道,陈寅恪先生便是体践者。至于学术文化之后的真精神,陈寅恪先生是有他的把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29年到1953年,他两次申明这一宗旨,又是那么醒目的一种坚持姿态。
我们确实应该反省这样一个在日益逼仄的空间中追求或者仅是坚持维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灵魂如何挣扎直至毁灭的故事。
夏中义:
这确实涉及到人格与文化精神的统一问题。陈寅恪对现代学统的人格演绎,为何竟如此感动当下学界?这大概与学界的价值苏醒有关。人文精神讨论所以延绵数年之久,根由之一,是因为它提出了学人的价值定位命题。当不少学者从新时期人文启蒙中心,被迫地退居社会边缘,不免心理失衡,这就像在舞台唱红的名角突然隐入幕后甚至被掷到剧院外,他(她)当会浑身不自在,并进而怀疑自己的存在理由,且认不清我是谁或应去何方了。而陈寅恪的晚年历程,恰似路标敬告尚在迷惘的学人,普天下除儒生道统这一路外,还有现代学统另一活法;既然陈寅恪在风烛残年尚能坚执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下学人就没有理由再为日前失范而凄凄惶惶。这样,令学人百思难得其解的生存方程式,也就一下子获得真正的价值之根,且此价值之根是被人格化的,看得见,摸得着,可资仿效,不难操作,尽管你学识不如大师宏富,地位不如大师显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