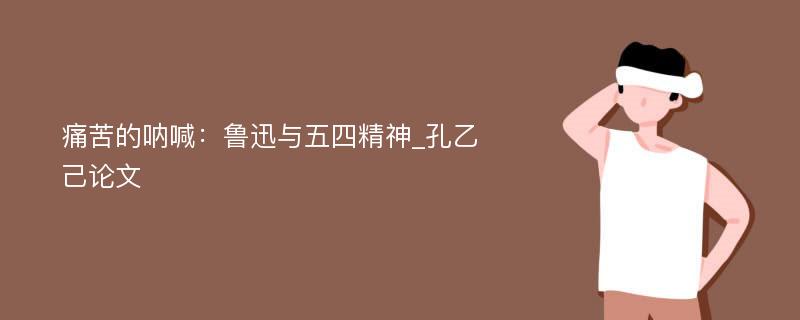
狂痛呐喊:鲁迅与“五四”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精神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鲁迅的《狂人日记》以一全新的面貌开始了新文学的篇章:语言新,用的是白话,是白话文战胜文言文在文学上的实绩;结构新,用日记体,又没有确切日期,用情感、心理、思想来组织顺序,是对旧小说的时代、地点、出身、身份一一交代清楚,然后清楚地讲述故事的一种反叛;人物新,一个疯子,西方文学的重大特征之一,是人物往往要在极端的生理或心理状态下,才能看清楚真相。俄狄普斯在眼睛正常的时候,并没有看清自己,在刺瞎双眼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命运;李尔王在清醒的时候是糊涂的,当他疯了的时候,才真正清醒了;哈姆雷特要知道真相也必须装疯,斯多克曼医生陷入最大的孤独,成为“人民公敌”时,才看清了社会的真相。《狂人日记》前面一段用文言,是正常的,清醒的,说狂人已愈,到某地候补去了。后面正文从“一”开始,用白话,呈反常话语,是疯子语言。正是这狂人,看出了真相,喊出了真理!这是思想的新。
新文学的呐喊和新文化的呐喊一样,首先是:全盘否定传统!
狂人变狂,自己追根溯源,是“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中国的传统,历史悠久,从未间断,是绝不能容人说“不”的,“我”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就成了恶人,慢慢地疯了。在疯人的心态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自封为“仁义道德”的文明史,其实是血淋淋的吃人史!“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里把史书上的记载、现实中的实例和小说中情节并置在一起,要想起到的就是一种超越小说的现实效果:以新文化否定旧文化!
然而这直露的思想又是非常艺术地表现出来。
小说从狂人看到街上女人打儿子,嘴里说,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但眼睛却看着狂人,于是狂人从“咬人”开始联想痴想,自然地而艺术地演进到前面所引的“查历史”,推出了吃人的主题。
《狂人日记》不仅为鲁迅的小说奠定了一个大主题:揭露中国的“吃人文化”,而且为吃人是如何可能的,作了艺术的又是逻辑的描绘。整个社会构成了一个吃人的网。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深思熟虑的象征性和代表性,构成了这个网的基本结构:
赵贵翁:百家姓中赵为第一;贵,与富不同,富是财富,贵是地位,中国社会是一个崇尚等级地位的社会;翁,老年,中国是一个尊老社会,由老人统治青年、小孩;赵贵翁是中国社会最高权力的总代表。
古久先生:中国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象征,当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历史书写),赵贵翁听到风声,就代不平,脸色铁青,于是约了大人小孩与之做对。
狼子村:中国文化以村庄为基本单位,有“狼”之名,有吃人之实,狼子村代表和象征了吃人文化的基本单位。
医生:是老头,老年社会维护者,姓“何”,喻其人品医术的暖昧;其祖师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中有吃人的记录。
哥:家庭中的家长,家中的吃人者,吃了妹妹。狂人的直接管理者。历史吃人故事的转述者。
母亲:在悲伤中仍按文化的意愿行事。无意或有意而无奈地吃过妹妹。是历史吃人故事的认同者。
陈老五:老五,排行最后,跟在别人后面行事和帮忙。陈,陈年旧帐的陈。是听家中家长(哥哥)指挥的帮手,负责按家长的意思对狂人进行强制行为。
小孩们:在父母的教育下,也对狂人铁青着脸。
狗:是赵家的狗,文化的卫道者——“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在这个中国社会文化的网络中,吃人是怎样吃的呢?狂人悟了出来:“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地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崇。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文化杀人,是杀人于无形之中,杀人而不见血。揭示这种杀人,是新文化全盘否定传统的最重型的武器,因而成了鲁迅小说的重要主题。《孔乙己》、《故乡》、《祝福》是这一主题的丰富展开。
这吃人的文化,几千年吃了下来,而且还要继续吃下去,在于这样的事实:“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进化论告诉人们,人类一代代地在进化,青年人胜于老年人。中国之所以不能一代胜过一代,在于孩子在成长中就被精心地教了吃人:“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中国要进步,必须否定这吃人的老年文化,让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正常生长。《狂人日记》的最后,喊出的是时代的主题:“救救孩子!”
二
旧文化吃人,在《狂人日记》中以狂言的方式提出的“五四”主题,在鲁迅以后的小说中以真实而具体的方式得到了更深入的展开,这典型地体现在三篇小说中:《孔乙己》、《故乡》、《祝福》。
《孔乙己》以小说中主人公为篇名,姓孔,孔夫子的孔,寓意为孔夫子的徒子徒孙,旧文化中的读书人,“乙己”是别人以戏谑的方式替他取的外号,别人不叫也不知道他真实的名,他也不以为意,任人这样叫他,任这号成为他实际的命名。孔乙己没有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主见、自己的灵魂,他已经被以“孔”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和以“乙己”为象征的社会现实所占有。
他连正常的话都不会说,才说两三句口语,就无意识地回到文言里去,句型上是酸得可笑的“之乎者也”,词汇上是大众难懂的成语典故,成为大众的笑柄。从传统的观念看,他有很渊博的知识,如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但这类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实际中有什么用呢?连作为小酒店小学徒的“我”也对他的知识和教诲不屑一顾。
在人品上,孔乙己是一个好人,在这个篇幅甚短的小说中,作者三次细写他的善良:第一,在酒店里他从不拖欠,间或赊一次,不出一月,定然还清。第二,对儿童充满友好,把自己不多的茴香豆也分给他们吃。第三,好心地想教“我”识字。然而,头脑里装满传统知识的孔乙己,像旧时代的很多读书人一样,“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更要命的是他“贪喝懒做”。懒做,以致无法谋生,是传统给他的毒害;贪喝,是他受毒太深的隐喻,他已经醉在传统中。懒做贪喝,使他走上了一条自相矛盾又无法自拔的可悲的路:偷。
给孔乙己致命一击的,正是传统社会中的权势者——丁举人。被丁举人打折了腿的孔乙己,在保持自己本能的洁操(喝酒给现钱),保护自己本已没有了的名声(不承认是被人打折了腿),和在大众的取笑中,死去了。
当然,他自己,把他打折了腿的丁举人,取笑他的大众,都不明白,他,忠于旧文化的读书人,实际上是被旧文化给“吃”了。
《祝福》以旧历年的大典为篇名。“祝福”是旧文化的欢庆时刻,这时,人们“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正是在这人人欢庆的时刻,祥林嫂,一个勤劳善良老实的劳动妇女,却悲惨地死去了。她是被封建礼教和封建意识形态“杀”死的。和孔乙己坚信和坚守旧文化读书人信念和准则一样,祥林嫂相信和坚守旧文化的道德和观念,然而旧文化却容不得她的存在。在逼祥林嫂走向死亡的路上有四种关键人物:
一、她婆婆,代表封建家长。为了换取自己小儿子娶亲的钱,用暴力把祥林嫂从她做工的鲁四老爷家中抢回,用暴力将之改嫁。坚守传统道德的祥林嫂用尽了一切力量反抗,甚至奋力一头撞在香案上,以图自尽。终因对方人多势众,进入第二婚姻。婚后一家三口本还幸福,不幸男人突然害伤寒死了,小孩不慎被狼吃了,于是孤身一人又来到鲁家帮工。她婆婆强使她成了她本不愿做的改嫁人。
二、鲁四老爷,代表封建制度。他把改嫁过的看作不洁的人,有关祝福祭祀的一切重要事,都不让祥林嫂干,因为祖宗不会吃不干净的人做的东西。而以前这些活都是祥林嫂干的。就在这类活动中,祥林嫂作为败坏风俗之人的地位被有形和无形地确立了。
三、柳妈及村人,代表封建习惯。村人对祥林嫂的命运,最初的同情之后,就只是轻视和取笑,柳妈还向她普及封建知识:“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祥林嫂被整个旧文化制度和观念压垮了,她努力想改变自己,按柳妈的指点,去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然而鲁家及村人也仍把她看作是不洁的。她挣不脱旧文化的罗网。
四、“我”,知识的代表。祥林嫂临到被旧文化压垮之前,求救于新知识,由“识得字、出过门、见识多”的我来判定: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究竟有没有一个地狱在等着她?然而,“我”最初用了旧文化知识回答她,说:也许有吧。最后又不愿回答,说:实在说不清。
祥林嫂就在这旧文化的家庭、制度、习俗、观念的大网中被压垮了。在祝福的大典进行的时候,在欢乐的爆竹响起的时候,也是每一年祥林嫂更深地体会到自己“不是人”的时候,她悲惨地死去了,被旧文化吃了。
《故乡》的主人公是闰土,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叫闰土,取名已经渗透浸满了旧文化的内容。小说的主体,就是把童年的闰土与成年的闰土进行比较。童年的闰土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孩,他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诗意般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而成年的闰土却完全变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的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
成年的闰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故乡》中的吃人,已经不是《孔乙己》和《祝福》那样,是一种肉体死亡,而是一种人的变形,由一个活泼泼的人变成一个木偶般的人。
新文化和进化论是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故乡》却揭示了,孩子确实是可爱的,但在成长中却被社会扭回到大人的不可爱中去了。成年的闰土就和当年他父亲的模样一样,同样,闰土的儿子水生又和童年的闰土一样可爱。然而,闰土的命运已经预兆了水生的命运。闰土父亲、闰土、水生,一个社会—文化—生活之链将之束缚在一起。闰土、水生,取名中就有一种更深的旧文化的关联,是照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的。这是一种循环的理论,闰土三代演绎了循环的现实。
在这一代又一代的循环中,在一代一代的儿童的童心被“吃”,而变成木偶人的历史现实中,《故乡》的主题已经豁然而出了,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呼声:“救救孩子!”只是用了更现实的表现方式。
《孔乙己》、《祝福》、《故乡》表现了旧文化给三类人的苦难,读书人,妇女,农民。这三类人既是中国旧文化的支柱,又是旧文化的殉道者,而在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中,这三类人的问题正是最大的问题。鲁迅小说的持久魅力,正在于它本有的象征结构。在这三大问题未被历史发展解决之前,这种象征会始终保持其力量。在这三类人被旧文化吞吃中,《故乡》在农民的苦难中突出了小孩被吃。妇女问题和小孩问题是“五四”的大问题。这样,鲁迅小说的“吃人”主题,包含了两套结构:
读书人 妇女 农民——中国现代性问题
妇女 小孩——“五四”问题
三
旧文化是一个吃人的文化,它能够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一代一代地吃下来,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的不觉悟。要否定扫除吃人的旧文化,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根本的改造。国民性批判,构成了鲁迅小说的一大主题。《药》、《风波》、《阿Q正传》,是这一主题的经典体现。
《药》,寓意极深,沉痛极深,悲哀极深。茶馆主人华老栓,一个善良而愚昧的国民,用钱买革命者的血,给自己儿子治病。茶,悠闲高雅,文化的象征;到茶馆里的人,都有文化类型分派。康大叔,职业郐子手,保卫文化秩序和健“康”。没有出场,由康大叔讲述,成为茶馆话题的红眼睛阿义,监狱官,文化道“义”的维护者,康大叔是挥刀见血,他是眼睛充血。二人都属官方,康呀,义呀,以文化所标榜的东西为姓名。来茶馆的其他人,没有自己的姓(个性),只有身体状态,国民一,花白胡子,显其衰老(按进化论,老必朽);国民二,驼背五少爷,年纪轻,身已残(心已残);国民三,“二十多岁的人”,显然既不老,也不残,而是年轻力壮,但糊涂得连任何特征都没有了。这茶馆的坐客不正象征中国的各大类国民?
再看店主一家,姓华,华夏之华,主人华老栓,完全给旧文化“拴”住了,他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儿子绝症,华大妈,与丈夫一样,十分感谢康大叔给她信息。小栓,一样给(旧文化)“栓”住了,得了“痨病”绝症,快要死了。这意味着华家要绝后了。怎样才能救这华家,让它祖辈相传的香火不被断绝,继续传下去呢?哪里去得到灵丹妙药呢?
革命才可能救中国,革命者姓夏,华夏之夏,“夏四奶奶的儿子”。为什么不说夏四爷的儿子呢,大概不是他爸死了,就是儿子不认爸了。旧文化是容不得革命的,茶馆里国民们对革命不理解、不支持,而且很气愤。革命者要用自己的血来救中国(华),华家夫妇却虔诚地愚昧地用革命者的血来救自己的孩子。华家茶馆中的国民认为革命者“发了疯了”。革命者的血,并没有唤起国民!
当然,人血是救不了病入膏肓的华小栓的,于是西关外城根的地面,多了两座新坟。夏家的儿子“瑜”死了,正如“瑜”字字面所诠,清白光亮。华家的小栓死了,正如“栓”字字面所喻,被(旧文化)“套”住了。在旧文化,华夏之家,儿子不得不死,不是因袭传统而被“栓”死,就是起来革命而被杀死。旧文化就是一个“杀子”文化!旧文化中的国民是用血也唤不醒的国民!
《风波》告诉人们,尽管已是民国了,乡村仍罩在非常落后的旧文化之中,上层之中旧知识的代表,保皇的赵七爷掌握的知识,只是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下层之中,因帮人航船,每日进城一回,而“很知道些时事”的代表七斤,传播的主要是“什么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革命与复辟是一个关系到普通国民性命的大问题,一听到皇帝重坐龙庭的风声,赵七爷立刻放下盘在头上的辫子,向没有辫子的七斤发难:“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但普通国民们对革命和复辟的真正意义却毫无所知,也不想去知。乡村中被卷进革命里的人物七斤,也是进城时被别人强剪了辫子的。因为没有辫子,听说皇帝重坐龙庭,全家忧心,互相埋怨,吵嘴,打小孩出气。七斤也失去了村人的尊敬。听说皇帝又不坐龙庭了,赵七爷把辫子重又盘在头上,坐着念书了,无辫子的七斤当然又成为新潮流的代表。于是全家合好,七斤重获了妻子和村人的尊敬。
《风波》中的人物,除了赵七爷,以赵姓表明其忠于皇帝,村民们都没有姓名,只用了出生时的重量做小名,七斤的爸,是九斤,七斤的女儿是六斤。中国的国民,只有一种生理上区别,没有精神上的个性。九斤老太斤斤计较的,也是这种生理上的区别,七斤比他的爸少了二斤,他的女儿比他又少了一斤,于是九斤老太把祖孙三代斤两的减少作为她认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代不如一代——的实例。
上层知识界的代表,赵七爷,信奉的是完全过时的书本知识《三国志》;家庭权威的代表,九斤老太,相信的是自己五十以后(不正常)的感觉经验:一代不如一代。时代新知的代表,七斤,相信的是城里咸亨酒店里的道听途说。村民们也是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这就是中国的国民。因此,虽然皇帝确已不坐龙庭了,六斤还是缠了小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往来……社会依旧,风俗依旧,国民依旧。
《阿Q正传》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
阿Q,鲁迅一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不知道应该怎样命名, 显出了人物的身份含混和身份危机。权且用Q,是英文字母, 表现出跟上时代的洋化;在字形上,像一个人拖了一条小辫,全然是传统的类型。 阿Q之“Q”,正是国民的画像。
阿Q,一直想确定自己的身份,却从未能确定自己的身份; 一直要获得自己的尊严,却从未能得到自己的尊严;这构成了阿Q 的命运悲喜剧。阿Q,一方面虔诚地按照传统的观念要求自己和世界, 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按照实用的要求去改变自己的观念。这构成了阿Q 性格和行动的悲喜剧。
阿Q是无固定职业、无自己房屋的穷人,却要去姓“赵”, 传统文化最高的姓,也是未庄最贵人家的姓。赵老太爷气得给了阿Q 一个嘴巴,不让阿Q姓赵,阿Q不配姓赵。阿Q不敢公开姓赵了, 但村人“还是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点的稳当”。阿Q虽然挨了打, 但还是得了些认本家的好处,在内心,他还是把自己认作姓“赵”的。阿Q 挨了王胡的打,很意外,他想,“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他了么?”自己明明在实际上和名义上都已被传统抛弃了,却还要死认传统,这就是国民的心态。实际上是臣民心态。
阿Q进过几回城,能够把未庄与城里进行比较, 用未庄的知识嘲笑城里,又用城里的知识嘲笑未庄,于是自以为自己“见识高”,“所有全未庄的居民都不在他的眼里”。其实这种见识完全是无识。阿Q 的真正悲剧就在于:既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又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
阿Q是很穷的,但大概以前确实姓赵,因此很自尊, 与别人口角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很像中国人在现实中比不过西方,就大提五千年辉煌的文化。
阿Q自身又确有缺点,如头皮上有癞疮疤,这是有损自尊的, 于是阿Q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 ‘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中国人最怕的就是真实,最重的就是面子。不是正视现实来维护自尊,而是用遮掩现实、忌讳现实来维护自尊,是国人的传统。
阿Q,有缺点,又很自尊,就免不了常与别人冲突, 他又穷又无力量,冲突的结果总是失败的时候多。失败当然更损自尊,又不可能在现实中转失败为胜利,于是他用精神胜利法在心理上转失败为胜利,被人打了,就想,儿子打老子。各种失败他都有各种方法很快在心理上转失败为胜利。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在一次一次的惨败中活过来,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就是靠了类似的精神胜利法吗?
阿Q在现实中有太多失败的经验, 对比自己强大的人是绝不去惹的,但对比自己弱小的人主动去欺侮,对王胡,对小D,对小尼姑。 一个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和家长社会造成的和需要的只能是这种人格。旧中国政府的怕洋人、欺百姓也是这种人格。
阿Q自认姓赵,他是虔诚地按照传统文化的观念来看待自己、 他人和世界的,然而他又本能地根据实用的需要改变自己的观念。而在改变观念的时候必然包含着一种滑稽的纠缠,其结果往往是悲喜剧的。在男女关系上,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很严,有排斥小尼姑之类的异端的“正气”;当他因一个偶然机会拧了小尼姑的脸而引发了性的欲望时,就时刻留心女人,终于惨遭“恋爱的悲剧”,在未庄身败名裂。对革命党,他一向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当他发现,上至举人老爷,下至未庄的鸟男女都害怕革命的时候,他也跳出来革命,大喊造反了。对外来异端,他十分痛恨,钱家大儿子留洋回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阿Q见了, 就暗骂他是“假洋鬼子”,“里通外国的人”,认为他老婆不跳第四回井,就不是好老婆。但发现假洋鬼子先他一步投了革命党,先他一步到尼姑庵去革了一块皇帝龙牌的命,就赶紧去找假洋鬼子了。结果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 革命!
阿Q的革命是什么样的呢?用他白天喊叫的话来说, 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用他傍晚的想象来看,就是,一是复仇,让未庄的一伙鸟男女向他下跪求饶;二是要钱要东西;三是要女人。阿Q这样的受苦人确实需要革命来改变命运, 但他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革命,更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结果,在他哄闹革命中,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断头台。
阿Q的自我定位始终是错的,他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阿Q的自我意识始终是错的,他找不到真正的自我。他的认同对象,先要姓赵,次要恋爱,后要革命,包含了他的自尊和追求,还是错的。他的认同行为给他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失败:不准姓赵,不准恋爱,不准革命,最后杀头。走向刑场的时候,他记起来的,仍是传统的戏文和传统的套话,还有他那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
阿Q,走向死亡中的不觉悟的国人。
四
旧文化是一种吃人的文化,旧文化中的国人是不觉悟的国人,《故乡》中闰土一家祖祖孙孙的循环暗喻是这样的沉重,《阿Q 正传》中的革命描写,知县老爷、举人老爷、带兵的把总都是原班人马,无非换了名字,也是这样的沉重。在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国民中,中国真正的先觉者,真正的革命者——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呈现出了他们的命运。
《在酒楼上》这令人一醉的地方,“我”碰上了当年做教员的旧同事,曾经共同革命而且很敏捷精悍的吕纬甫,然而他已经重回到革命前的状态和心态了。尽管他们曾经同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曾经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为此打起来。现在,他在一个同乡家中,按主人的要求,教《诗经》、《孟子》、《女儿经》,模模糊糊、随随便便地得过且过了。吕纬甫这样自嘲:“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这个比喻实际上就是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个主题象征,《孤独者》开篇就用的这种象征:“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伤逝》中还是这一象征,在寂寞的会馆里等待中开始着对旧的婚姻礼法的冲击,惨败后又回到寂寞的会馆。这里使人回想起《故乡》里的循环。但闰土们的循环,是在旧文化内的循环,因此,闰土要一个香炉,是真心地向旧文化的神灵祈祷;而吕纬甫们的循环,是从旧文化飞向新文化,又从新文化返回旧文化的循环。因为已经飞向过新文化,他们不可能信奉旧文化。他们返回旧文化是被迫的,内心充满了战败者的悲痛。
他们的失败,是他们的新思想、新行为不能见容于整个旧社会,于是整个社会“合谋”断了他们的生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连连发表新思想的文章之后,连遭匿名和流言的攻击,最后被校长辞退,失业了。《伤逝》中的涓生,自由恋爱后,连遭冷眼和流言,最后被局里辞退,失业了。这种失业,不是正常失业,而是异常失业,意味着只要他们坚持自己的新思想和新行为,就再也找不到职业。魏连殳们面临的问题是:要活下去,还是要新思想?于是,吕纬甫只有去教子曰诗云;魏连殳只好去当杜师长的顾问;涓生不得不让子君离开,各自去谋生。
他们的回到传统,不是自愿,其结果是三种:一、子君型,子君回自己的家中,等待她的只是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般的威严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很快就死了;二、魏连殳型,以新的心灵在旧式的娱乐和生活中,自觉地慢性自杀,表面上是宾客、馈赠、颂扬、打牌、猜拳,私下里是冷眼、恶心、失眠、吐血,很快就死了;三是吕纬甫和涓生型,和吕纬甫的得过且过一样,涓生决心“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
真实,在中国,是阿Q们和闰土们不知道如何去看、如何去说的,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完全受旧文化摆布。真实,对旧社会旧文化中的好人来说,也是不堪承受的,涓生把真实告诉了子君,造成了子君的回“家”和死亡,吕纬甫的母亲对现实中的事情的观念与现实本身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但吕纬甫并不愿把现实的真相告诉母亲,而是告诉她一种谎言,以使母亲安心。真实,对旧社会旧文化本身,是最不愿意有人去看、有人去说,谁去看了、说了,它一定要布下天罗地网去迫害,就像对狂人的迫害,就像对吕纬甫、魏连殳、涓生的迫害。在这一意义上,《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是《狂人日记》以来“吃人”主题的一种深入:旧文化要吃掉任何觉悟者!
然而,鲁迅的这类知识分子小说与旧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小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写出了先觉者置身于庞大的旧文化、麻木不争的国民们、无法沟通的亲人的巨大包围中所体验到的巨大的孤独感。
《在酒楼上》可以说,写出了与亲人无法沟通的孤独,吕纬甫的母亲要他去迁葬他兄弟的坟,因为坟边已经浸了水,他去迁时,发现棺内根本就没有尸骨,但他还是用被褥棉花包了此处的泥土,装在新棺里,运到父亲的坟边埋了。他骗了母亲,为了不要她再悲痛。他做客,主人的女儿阿顺——一个可爱的姑娘——做的荞麦粉实在难吃,但看见阿顺远远地看着他,怕她失望,于是装成喜欢把一大碗很快地吃了下去。虽然由此尝到了硬吃的痛苦,晚上做了一夜的恶梦,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这里当然有人类最美好的情操,但也包含了与最喜爱的人不能沟通的孤独。重要的是亲人与旧社会和旧文化之间有一个网中的联系,是这个网使他们不能沟通,这种不能沟通真是使先觉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伤逝》可以说,写出了与爱人无法沟通的孤独。而这种无法沟通是由于旧社会迫害之网向他们逼来,他们面临着如何解决生计的时候开始的,在作为男人的涓生看来,人的生活第一是求生,求生之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倘只知捶着一个人的衣角,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但这种理解,并不适合于被旧文化所“定义”的女性,也不适合在既定的“定义”中冲击着这“定义”的女性。涓生只理解自身的真实,不了解作为特定网中的新女性的子君的真实,造成了他与爱人无法沟通的孤独。当他把自己的真实告诉了子君,造成了子君的死亡,自己得到的只能是无法弥补的悔恨和悲哀,同时进入了更深的独立于天地间的孤独。
《孤独者》写出了最深的洞世者的孤独。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以痛哭始,以痛哭终,开始是魏连殳痛哭他的祖母,一个孤独的妇女,最后,是“我”从魏连殳的尸体上感受到他灵魂的痛哭。魏连殳对旧文化的洞悉已经到了极深的程度。他祖母去世,这似乎应发生一场新与旧的较量,族人们商量半天,拟定三条,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之,一切照旧。出乎他们的意外,魏连殳说:都可以的。魏连殳已经不在乎这些人是卫道、是谋私、是真悲、是做戏,他需要的,只是自己内心对祖母的一种理解和悲痛。后来,为了生存,他在形式上,投向了旧社会旧文化,他不在乎现在旧文化的同类对他怎么看,也不在乎以前新文化的朋友对他怎么看,在给“我”的信中,他写道:“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了,我都可以的。”他知道自己灵魂上的孤独,在他为一种希望攻击旧文化的时候,是孤独的,他因绝望而成为旧文化时,仍是孤独的,他注定了有一颗孤独的灵魂,小说开始一次,结尾一次,用同一句段对他的描绘,确实用强调的手法,写出了这颗心的孤独:“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中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五
鲁迅的小说,强烈地表现了与中国现代性第一阶段的顶峰——新文化运动——相一致的思想:全盘否定旧文化,揭露其“吃人”的本质;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又包含了与中国现代性第二阶段相一致的思想:1.描写了以农民为主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提出了如何去唤起他们的问题;2.他对社会上层(姓赵系列和姓钱系列)的揭露已经初步为革命对象定义;3.指出了知识分子在改革社会中的无力和失败,他对知识分子的无情解剖,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性中角色变迁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鲁迅成为第一阶段的顶峰和第二阶段的偶像的基础。
标签:孔乙己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阿q精神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祥林嫂论文; 祝福论文; 风波论文; 伤逝论文; 在酒楼上论文; 孤独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