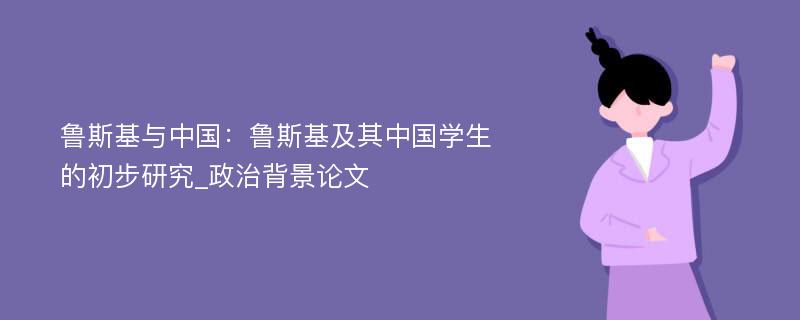
拉斯基与中国:关于拉斯基和他的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中国论文,中国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05—0087—06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J.Laski,1893~1950), 英国工党的著名理论家和主要活动家,费边社成员,19世纪20~50年代欧美主要政治哲学家之一,
长期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TheLondo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执教。其间, 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受业于他的门下,拉斯基的朋友马丁说:“我记得战前不久有一次听中国驻伦敦大使说,当社会主义似乎仍然通过同西方修好而不是与之为敌来获取胜利时,如果哈罗德访问中国,他定会受到他许多门生的殷勤款待,其人数之众多足以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注:金斯利·马丁:《拉斯基评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8~299页。)然而,大使的潜台词近乎成谶,拉氏的弟子后来多因其师的背景而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虽有雨霁云开之日,但当事人有的已经作古,在世者也惊悸犹存。是以,这层史实已不大为晚辈所知,因而颇有探讨的价值。
拉斯基1916年至1920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师。他在哈佛主要讲授欧洲史、英国史,以及政治思想史,同时潜心研究国家主权问题。是时在哈佛研究院研究政治学、教育行政学及法律哲学的雷沛鸿即受业于拉斯基。他曾说“拉斯基先生是我就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时的业师”(注: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上册,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我和林毕同在拉士其教授Prof.Laski班中同学”(注: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下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当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张奚若、 金岳霖同攻西方政治思想史。1918或1919年,哥大的比尔德(Charb Beard )和罗宾逊(Jame Robinson)因不满该校的陈旧办学方法, 在市中心设立了社会研究所。这个机构请了3位英国人来讲学, 他们是当时在哈佛讲学的拉斯基和曾著有《政治中的人性》的瓦拉斯(Graham Wallas), 以及拉斯基的老师巴克(Earnest Barker)。当时,拉斯基比张奚若还小4岁,但张奚若非常佩服拉斯基。 (注: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金岳霖说拉斯基可能比张奚若还小1岁,系回忆之误。 张奚若生于1889 年, 拉斯基生于1893年。)1919年9月入哥大研究院的徐志摩虽读经济, 但对政治很感兴趣。他们3人当时可能都受到拉斯基等3位英国老师的影响,这为他们后来到英国去学习打下了基础。1919年夏进入哥大研究院的蒋廷黻和拉斯基也有过师生之缘。据蒋氏晚年回忆,当时讲授《政治思想史》的是邓宁(W.A.Dunning)和拉斯基。他上午去听邓宁的课, 下午去市中心的社会研究所上拉斯基的课。“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辨滔滔的口才慑服了我们。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授课时他会引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斯丁、圣·阿奎那以及法国大革命前各家的著述,授课时,他从不停止。我们常被他的言语带开。我认为有许多次他自己也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注:《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第30卷,第4 期。)
拉斯基因为声援1919年波士顿警察工会罢工一事而结怨美国当局,遂离开哈佛,于1920年夏季回到了英国,应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之聘,任讲师。1925年出版《政治典范》,伦敦大学特设讲座,擢之为教授,从此任伦敦大学教授直至其去世。在此期间,先后有数十名中国人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进修,其中一些是他的受业弟子。2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拉斯基指导的中国学生有钱昌照、陈源、徐志摩、罗隆基、王造时等。钱昌照于1919年10月考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了3 年。第一年学的是基础课,第二年读选修课,规定要有一位导师,钱昌照的导师就是拉斯基。(注:《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同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的陈源也在拉斯基指导下,研究政治与经济,得博士学位。(注:参见《传记文学》第16卷,第6 期,第47页;第23卷第3期,第108页。)
徐志摩于1920年9 月得哥伦比亚大学文硕学位后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拉斯基学政治。(注: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7页。)不久,他认识林徽因并深陷情网而不能自拔,烦恼、痛苦、忧郁纷至沓来。因此,要应付在伦敦已注册的6门功课,谈何容易! 他便常常旷课,甚至干脆不想学了。当该院注册处向拉斯基查问徐志摩的下落时,拉斯基复了一张短柬:“……我倒是不时见他的,却与读书事无关。”(注:梁锡华:《徐志摩新传》,《徐志摩传记资料》五,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徐志摩在这学院只混了半年,便“闷着想换路走”。1921年春,经狄更生介绍,转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特别生。此后,徐便走上文学一路。
1925年,杭立武获安徽省公费留学考试第一名,同年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政治学。1927年,受拉斯基的鼓励,杭立武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担任名誉研究员。翌年获颁威大硕士学位,旋即返英,继续攻读政治学,于1929年完成学业。(注:《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6~7页。)罗隆基也是1925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其导师也是拉斯基。40年代末,罗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过“拉斯基一门徒”(注:转引自谢泳:《罗隆基的一生》,《谢泳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 页。 )。 王造时是1928年8月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作为研究员, 跟拉斯基学习,研究政治思想与比较政府。(注:何碧辉、赵寿龙:《王造时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6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
30年代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有程沧波、储安平、龚祥瑞、吴恩裕、楼邦彦、邹文海、王铁崖、樊德芬、费孝通、萧乾等。其中程沧波、龚祥瑞、邹文海和吴恩裕直接师从拉斯基。程沧波1930年进入该学院,从拉斯基学习政治哲学,韦伯斯妥教授(Charles K.Webster)习外交史。(注:《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台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2页。)龚祥瑞1935 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毕业考取“第三届留美公费生”,于1936年被送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抱着“吏治救国”思想,专攻公务员任用制度。拉斯基当时是龚祥瑞的督导员(Supervisor),指点他研究行政机关的内部民主,包括公务员应有罢工权利这样激进的课题。(注:龚祥瑞:《我的专业的回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6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在龚祥瑞进来之前已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的樊德芬也专攻政治制度。他的硕士论文题为《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他本不打算发表,后以拉斯基之劝,以为如在国内发表,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将不无补益;因译成中文,于1934年由南京钟山书局印行。书前附有拉斯基的序言,拉斯基在序言中指出,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均为托基于民意之领袖政体,为中国所亟应了解者”,“中国研究政治学者,对于其成功之所以然,自须努力以求之”;“一伟大首相如英之格兰斯顿,或一伟大总统,如美之林肯,其所树立之领袖模范,实为中国今日所急需”;“须知吾英之人多以为中国政治之能否上轨道,实与全世界幸福有密切之关系”。(注:樊德芬:《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钟山书局1934年版。)
和龚祥瑞同年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吴恩裕1933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初到英国的时候,考取的是历史学名额的留英公费生,如果改习哲学,会被取消公费。由于他爱哲学远甚于历史,这件事使他彷惶、苦闷。经朋友提醒,他改从拉斯基学习政治哲学。如此,既得名师指教,又不丢弃哲学。他和拉斯基第一次谈话主要讨论他的论文选题。吴恩裕本打算做《黑格尔的国家论》,但拉斯基得知吴恩裕在国内出版过《马克思的哲学》,便劝他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学说。吴恩裕后申请改读博士学位,得到拉斯基的同意,论文题定为《马克思的社会及政治思想》。在吴恩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拉斯基不仅在学问上悉心指导他,而且关心中国的前途,希望中国能真正统一,以对抗日本的侵略。拉斯基还慷慨解囊,两次帮助吴恩裕度过经济上的困难,使吴恩裕得以完成学业。(注:吴恩裕:《拉斯基教授从学记》,《客观》(重庆版)第10期。40年代国内出版3种名为《客观》的杂志, 分别是重庆《客观》周刊,上海《客观》半月刊,广州《客观》半月刊。)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调整了留学政策,大量削减赴海外攻读法政专业的留学名额,又值世界大战,英伦也遭纳粹战火,物价飞涨,因此,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拉斯基读政治经济的中国学人恐怕就凤毛麟角了。
二
拉斯基的学生回国后多在教育界、新闻界、政界任事,在研究、译介和传播拉斯基思想学说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拉斯基早年致力于攻击一元主权论,主张政治多元论。(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后,反对国家主权论的政治多元论思潮在欧陆与英伦兴起,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巴克(E.Barker)、梅特兰( F.W.Maitland)、柯尔(G.D.H.Cole)、拉斯基(H.J.Laski ),法国的狄骥(L.Duguit)、朋哥(Paul-Boncour), 德国的奇尔克(Von Gierke),荷兰的克拉勃(H.Krabbe)。 关于政治多元论的评述可参阅E.Barker,The Discredited State,Pol.Qtly.,2:101~121;F.W.Coker,The Technique of the Pluralistic State,Am.Pol.Sc.Rev..15:186~213;H.J.Laski,The Pluralistic State,Phil.Rev.,28:562~575; G.H.Coker,Pluralistic Theories and the Attack upon State Sovereignty,in Merriam and Barnes (edi) ,Political Theories,pp. 80~119; Coker,The Pluralistic State,Am.Pol.Sc.Rev.,14:393~407(参见Hisiao,Kung Chuan (萧公权):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London,Kegan Paul,Trench & Trubner Co.Ltd,1927,p.1页下注), 以及萧氏该著和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中岛重:《多元的国家论》,京都市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2年发行。)他对16世纪法国律令学者布丹(Jean Bodin)以来的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政治一元论作了激烈的批评,认为所谓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说是虚构的,实际上国家不过是一种社会团体,它与工会、教会等没有地位高下之别,只有职能不同而已,他主张社会联治,包括区域自治和职业自治。拉斯基对国家主权论的攻击,令欧美政治学界和哲学界为之侧目。当时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院的萧公权就以拉斯基等人所提出多元政治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先后写成硕士论文《多元国家的理论》和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 拉斯基的弟子当时虽未公开评说其师的多元论,但徐志摩、金岳霖、 张奚若则私下屡向国内的张君劢介绍拉斯基的形容与学说,徐志摩还赠张君劢拉斯基著的《近代国家中之权力》一书,使张君劢对拉氏颇为心仪。张说这是他与拉氏神交之始。后来张君劢以讲学社名义,拟聘拉斯基来华讲学和翻译拉斯基的《政治典范》。(注:拉斯基著,张士林(即张君劢)译:《政治典范》,“赖氏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页。)
1927年,拉斯基的《共产主义》(Communism)一书出版, 对共产主义从学理上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和批评。这在当时英美自由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对峙的政治背景下, 以拉氏的声望, 此书自然风靡一时。1927年又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际,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焦点问题,此时占优势的政治舆论乃是反苏反共,但批评多是肤浅的叫嚣和偏见的宣泄,缺乏学理深度。这在一些留学英美偏爱英美政治的留学人士看来,是不能满意的。拉氏《共产主义》的发表,正好适合他们的需要,因此很快即引起他们的关注,南开大学的黄肇年不久便着手翻译该书。徐志摩此时正主持《新月》杂志,他将黄译该书第一章引论刊登在2卷2号上,并加按语。徐志摩在按语中说:“拉斯基教授为现代政治学学者中最卓绝的一人,亦为在学理上掊击共产主义最有力的一人。但在他的《共产主义》一书内,他取的是完全学者的态度,从历史及学理方面作研究,绝无一般专作宣传反共产者的粗犷与叫嚣的不愉快。本书早经评定为剖析共产学说最精深亦最可诵的一部书”。黄译全书则于1930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张奚若则在《现代评论》上撰文评论该书。张说该书是当时很少见的以公正的学术立场来对共产主义进行学理评述的著作。然后逐次叙述每章内容大概并加评骘。他认为讨论唯物史观的第二章差不多是全书中最精采的一章,而第三章讲共产主义的经济学要算全书最弱的一章;最后指出拉氏思想的立足点一方面厌恶资本主义不满于平民主义,同时希望他们改良;一方面赞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但不赞成它的方法。
杭立武回国后于1930年开始担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受其邀请,1931年拉斯基有函来,答应于11月间莅华讲演,朱家骅、杨杏佛尤极力赞助,朱家骅还答应筹集川资招待各项费用。议定之后,不料“九·一八”事变发生,拉氏也以教务羁身,函请展期。此前,杭立武为迎接拉斯基来华,准备出版一书,向国人介绍拉斯基的思想学说。他约请了萧公权、卢锡荣、吴颂皋、张奚若分头撰述关于拉斯基思想学说的文章,至12月全稿完成,交商务印书馆代印发行。商务刚开始排版,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军炮火。至秋间商务复业,在印刷所旧址瓦砾灰烬中捡得残稿数十页,经整理仅得《政治典范要义》一篇,杭立武又从萧公权处索得《拉斯基思想之背景》一文底稿,复自另撰《读拉斯基思想之背景书后》一篇汇辑成册出版。从萧、杭关于拉斯基思想背景的文章来看,杭立武不同意萧公权对拉斯基思想背景的分析,认为萧公权批评拉斯基在三个地方是不妥的。第一,萧公权说拉斯基“虽自命为边沁之依钵,实不过取功利主义之面目而弃其精髓”,杭立武则认为拉斯基思想与功利主义中心主张相同;第二,萧公权说拉斯基一面既接受格林的伦理个人主义,一面又拒绝其据此而成立的公意说,不免自陷于矛盾。杭立武则认为“真意及公意,与伦理之个人主义,并无如萧君所谓有连锁性也”。所谓伦理、所谓公意皆无先天预定的必然性或普遍性,一切皆依各人日常亲历的经验而定;第三,萧公权认为拉斯基应用詹姆士宇宙多元论于政治哲学是失败的,其故有二:一是拉斯基主张政治权威多元,但又未“计划相当之复性机关,以表示施行之”,二是拉斯基所采用的多元论与其思想背景中的其他原则相抵触。杭立武则认为拉斯基既然主张政治权威为复性,就无须画蛇添足以计划具体制度。而所谓思想背景抵触云云,实因未能细按之故。(注:杭立武:《政治典范要义》,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33~142页。)
1929年,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对欧美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乃至人心的冲击是空前的,对始终关注现实并不为学问而学问的拉斯基也有不小的思想影响。这种背景促使他进一步关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以及社会平等问题,《现代国家自由论》及此后出版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国家的理论与实际》、《自由主义的兴起》等都含有这种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使他“从绝对的自由主义出发而转入于一种的社会主义。从个人的自由,而转入社会经济的平等”(注:张维桢:《读拉斯基的〈现代国家中自由问题〉》,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3号。)拉斯基思想的这种变化,引起民国知识界的关注。尤其是王造时,他先后翻译了《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王造时说拉斯基的思想“这几年来有急剧的变化。回想1929年至1930年我在伦敦听他的讲,与他在一块讨论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不出进步的自由主义的范围。现在我译完这书之后,我很诧异他的思想前进程度的深远了。1929年起的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及1930年后国际政治的急变,尤其是侵略国的穷兵黩武,及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大概给了他极深刻的印象。”(注:拉斯基著,王造时译:《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译者序”。)“这两本书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转变,并且是1930年来世界各国政治急剧变动的反映”,“如要明瞭现代民主政治与国家的本质,这两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注:拉斯基著,王造时译:《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译者序”。)而张奚若对拉斯基思想急剧的变化则难以接受。1936年,拉斯基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一书出版后,张奚若撰文评论该书,称它“乃是对于自由主义一种富于极端挑战性的唯物史观式的解释”。他不满拉斯基同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他说:“一个人尽可相信共产主义,不必定要相信马克斯主义;尽可接受马克斯主义的革命部分;不必定要接受它的唯物史观部分;尽可承认唯物史观的相当部分,不必定要承认它的全部分,更不必拿它的全部分去解释人类的全历史。”(注:张熙若: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书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
三
拉斯基思想自大的方面来看,是欲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成份,早期偏重自由主义,30年代开始偏重于社会主义,转变为一个激进的费边主义者。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认为掌握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会运用国家政权力量来维护其根本利益,不愿用民主制度来解决阶级关系,经济越是恶化,资产阶级越是不愿解决社会问题,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趋尖锐,则革命的企图将不可避免。但革命不一定成功,俄国革命的成功不过是“特殊经济环境的产物”,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不要奢望革命一定就能带来好处,“暴力革命纵使获得了成功,也必然会停止民主的程序。……我们从1789年和1917年的经验知道,它会引进一个残酷的时代。如果暴力革命失败,它就会把人们……带进一个可怕的丛林,人的尊严将被对权力的欲望而牺牲掉。”(注:拉斯基:《论当代革命》,转引自刘绍贤主编:《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2页。 )而资产阶级若要维护其根本的利益,就要搞“同意的革命”,就是“用和平的方式,以协商而不是以暴力来改造国家的各项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拉斯基偏爱资本主义,他其实是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追求一种非根据财产所有权而是根据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公民的资格的社会平等。他认为作为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非常偶然的结合。当民主政治成为要动摇资产阶级财产权力基础的时候,资产阶级将视民主政治为仇敌,因为民主政治是给群众以正式宪法权力的。政治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性又必然受到经济领域的所有权的限制,“只有在公共所有制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才能不偏不倚地被用来保护社会内每个成员的利益。”(注:拉斯基著, 王造时译:《国家的理论与实际》,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7页。 )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实行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而是结合资本主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制度,即“计划化民主国家”。
拉斯基的这番见解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特别是他的一些学生。王造时和龚祥瑞就曾明确承认他们受拉斯基思想的影响。王造时说他受拉斯基影响很深,在师从拉斯基的1年中,钻研的主要对象是费边社会主义, 结果使自己没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误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途。(注:《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9页。)龚祥瑞曾参加过民盟,他说:拉斯基“的著作和讲授,使我推翻了三十年代风行的国家论和形式主义的法律观,深信文官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才能建立和发展,而‘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则是公民(包括公务员在内)对国家——现实世界中的政府——的态度问题。那就是事务官,一方面要能毫无顾忌地发表和负责大臣(政务官)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又要无条件地服从政府和大臣的决定。因此,事务官和政务官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对政府只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对两党的中立性),也就是说,只有在作为后者的一部分或从属于后者的条件下,才有必要和可能保持这种独立性,享有职位保障,以保证国家政策的持续和政局的稳定。这种独立性,即统一性和精巧性,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对英国的民主程序和“自然公正”的法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大力宣扬民主个人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合成的“政治康拜因”以及文官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行政拖拉斯”,并对本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作出了一个初步研究计划。(注:龚祥瑞:《我的专业的回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6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学说也反映在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中,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通篇赞扬了英国的议会政治和英美的人权保障,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的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而这个报告是由罗隆基执笔起草的。(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9月第1版,第137~138页;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但是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它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中国未必适用。其学生樊德芬对此早有警示,他说:“东西文化进展之历程,有先后不同。时代的问题之呈于前者,亦轻重各别,我之所视为当前急务者,在彼或不成问题,而彼之所视为潜伏危机者,在我则或尚无影响。且国情民尚,彼此判若鸿沟;是以筹运推施,亦宜各觅途径。拉氏之书实为了解近代西方政治之索隐,其所示途径,亦为医治西方时代问题之良药”,然“若一得自喜,不察始末,妄投重剂,以治弱躯,则实冒食古不化之嫌;若恐淆乱思想,束书不阅,伏隅自足,不察世变,亦难逃井蛙自囿之讥。惟肯运用理智之民族,始有自救自拔之希望。”(注:樊德芬:《国家之理论与实际》,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第2号。)然而,在西潮激荡的年代里,能如此不迷失民族本位、不一味趋时者毕竟是少数。但是,历史自有其运行规律,趋时与不趋时都有其盖棺论定的时候。
基金项目:本文是课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民国知识界”的前期成果之一,该课题研究得到中山大学桐山青年研究基金的资助。
收稿日期:2000—05—11
标签:政治背景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张奚若论文; 龚祥瑞论文; 客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