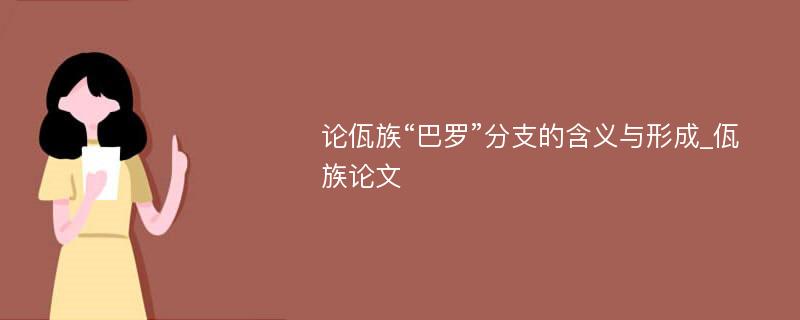
论佤族支系“巴饶”的含义及其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佤族论文,含义论文,支系论文,巴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P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4)05-0123-05
佤族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民族,是中国西南地区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使佤族内部发生裂变,出现蘖枝,大体言之有“勒佤”、“巴饶”和“佤”三个分支,其中以“巴饶”人口居多,分布最广,文化个性也最为显著。本文通过对零星的文献记载和考古等资料的爬梳钩稽,索引探微,第一次探索和分析了“巴饶”的含义及形成。
一、“巴饶”的人口与分布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佤族人口396610人,其中云南省383027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沧源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以及与它们相邻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永德县等地。这一带地区所分布的佤族人口占我国佤族总人口的80%以上,一般俗称阿佤山。其余佤族人口分散在德宏、西双版纳两个自治州和保山地区内。
“巴饶”是佤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支系。据民族语言学家研究,“巴饶”方言有三个土语,即国内的岩帅土语、班洪土语和邻邦缅甸境内的完冷土语。[1](P167)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国内操“巴饶”方言的佤族约有25万人,占佤族总人口的60%以上,其中岩帅土语主要分布在沧源的岩帅、团结、勐角、勐来、永和,西盟的中课、力所,双江的沙河、勐勐、南榔,耿马的四排山、耿宣、贺派、孟简、孟定、福荣,澜沧的东河、文东、上允、雪林等,使用人口约22万人;班洪土语主要分布在沧源的班洪、班老、南腊等地,使用人口约3万人。完冷土语的使用人口,由于资料缺,难以统计。
二、关于“巴饶”的含义
“巴饶”是一个自称,其译法另有“巴饶克”、“布饶”、“巴敖克”、“格尔巴饶”等。译法尽管稍异,然而其意义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表述的规范要求上看,“巴饶”最为简洁,又比较接近佤语的发音。“巴饶”作为佤族的一个自称,是何含义,目前尚有争议。
先说“巴”字。“巴”在佤语中有两个含义,其一,作为助词使用,作用是加强语气可以省略。有人认为,“巴饶”是跟着癞蛤蟆走的一群佤族之意。[2]就属于这种情况,“巴”及后面的“跟”字可以省略。其二,作动词,有拥有、占领或做的意义,比如“布比布巴”这句话,其中“巴”字即做的意思,意为东一下,西一下,是指作风漂浮、做事不扎实的人。有的学者把“巴饶”译为居住在山上的人。[3](P4)取的就是这一含义。
再说“饶”。“饶”在佤语中有五种含义,其一,陆地,与洲、湖泊相对应;其二,森林,比如“饶拷揉”,意为桦桃树林;其三,癞蛤蟆;其四,旱地;其五,野地、野外之意。
有人把“饶”诠释为“山”,这是不正确的,在佤语中,山称为“拱”(goη)。所以把“巴饶”简单理解为居住在山上的人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佤语中“饶”为陆地,这应当没有什么争议,至于后三种含义,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关于“饶”有森林之意。相传古代时佤族有一个势力强大的部落,他们向四周扩张,势力所及以砍伐森林为标记,为此,他们得称“永饶”,即拥有大片森林的佤族部落。“永饶”的“饶”是同一个词。沧源勐董镇永和大寨,佤语称“永饶”,可译为“森林中的村寨”,他们或许沿袭了历史上的“永饶”这一地名。
关于“饶”为癞蛤蟆之意。相传,远古时人类像神仙一样会生不会死,并且每天都生下一个孩子,大地上挤满了人类。天神“达西爷”感到人类太多祸害无穷,就翻江倒海,兴风作浪,让大水淹没整个地球,灭掉人类。人类是地神“西拥”创造的,为了不让她伤心,天神为了有意留下心地善良的人,为此就变成了一只癞蛤蟆,跳到人们奔命的路上。只有达姆依这个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把癞蛤蟆捡到了路边的岩石上免糟践踏,癞蛤蟆跳到路上,他又捡回去,反复多次。天神断言达姆依就是好人,就变成了鹤发童颜的老人,告诉达姆依躲进木仓里,并带上一条母牛。洪水过后,地球上只有达姆依和母牛了。地上没有吃的,达姆依无奈把母牛杀了,它的肚子里有一颗葫芦籽,他把它栽了下去,结出了巨大的葫芦。在小米雀的帮助下,达姆依打开了葫芦,人类及其他动物鱼贯而出。从此,地球上又恢复了生机,热热闹闹的……
以上就是佤族人类起源神话“司岗里”的故事梗概。流传这一故事的佤族称我们是靠癞蛤蟆的指点才能生存下来的,“我们是跟着‘饶’(癞蛤蟆)走的人”,他们似乎把“饶”看成是再生父母,赋予一种崇拜的感情。“巴饶”这一自称由此而产生。
在佤语中,旱地称“麻饶”。这里“饶”与“巴饶”的“饶”字是同一个字。还要值得注意的是在佤语中“麻饶”有时似乎特指“旱谷地”,与水田“得更”相对应。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前,佤族主要以种旱谷(陆稻)为主,是一个精于耕种陆稻的民族之一,并且陆稻品种多,据农科人员研究,仅西盟一个县内,陆稻品种达132个,这些品种具有耐旱、耐瘠、耐寒、抗病、高产、优质、高效等优点。[4]沧源糯良一带旱稻种植技术也极为考究,播种前要耕翻碎土五至六次,品种达65个(含野生稻品种一个)。[5](P171)所以,“巴饶”的又一个含义大概就是善于耕种陆稻的佤族。
关于“饶”有“野地”、“野外”之意,它与“得也”(家里)、“得羊”(寨里)等词相对应,即家、寨子以外的地方。“巴饶”到底为何意?佤族学者魏德明先生作了一个较全面的概括:“佤语‘布饶’有三种意思:一是居住在洲渚岸边的人;二是发展兴旺过的人;三是种旱地人”。“所以解释‘布饶’为种旱地(陆稻)或住在河海岸边,以及发展过的人更为恰当,也符合布饶人自己的传说。”[6](P27)从对佤族历史的考察看,他们在中国的西南亚内陆曾经强盛过,他们拥有非常广袤的地区。然而这里的自然地形地貌以山区为主。如果简单地理解佤族是拥有广大山区的民族似乎也可以。这种诠释似乎比较全面、准确。魏德明先生的第二种说法与笔者所调查的伐树为界的口碑资料是相一致的。
佤族在文献资料中也多有记载。比如《太平御览》卷791引晋郭义恭《广志》:“黑濮,在永昌西南,山居”。道光《普洱府志》卷18载:“蒲蛮,又名蒲人,宁洱、思茅、威远有之。……古称百濮,……散处山林。”“黑濮”、“蒲蛮”均指国内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山居”、“散处山林”大体上也反映了当时佤族的生产、生活情况。
三、关于“巴饶”的形成过程
“巴饶”是怎样分化、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佤族的来源及族称的演变。
关于佤族的族源,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有学者称,“滇文化是以孟高棉文化为基础,并吸收了中原文化、百越文化乃至印度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滇文化创造者滇人“与现今云南境内的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都属同一族群的民族”。[7]大致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1世纪,四川西南部和滇西一带广大地区的“大石墓”,他们是佤族先民的墓葬。[8](P78)云南距今3000多年的云南沧源崖画是云南古代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学者们一般认为其族属是佤族。滇西澜沧江中上游的云县忙怀、耿马石佛洞、双江忙糯等等新石器文化,学术界一般也认为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各族先民创造的。以至于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今孟高棉语诸民族,他们是云南最早的土著民族。”[9](P280)
史学、民族学界一般认为,佤族先民是古代的“濮”人或称“百濮”。所言甚是。在后来的文献中,“濮”常写成“蒲”、“扑”、“卜”等,有称“蒲蛮”、“扑子”等。在佤语中“濮”即人(Pui)或“什么人(Pui?)”的意思。远古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大多有过自称为“人”或“人人”的现象,从而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至今有的民族的族称仍然保留着这种称呼,比如我国的布依族,族称“布依”即布依语复数“人”的意思。[10]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与佤族同一个语支的德昂族,其自称中有的还保留着“巴”这一读音,比如德昂族自称“布雷”,这里的“布”显然与“巴”音近。这一“布”,也有人之意,与“濮”意义相同。作为现代佤族保留得比较古老的族称主要有“牢”、“佤”等。“牢”是“巴饶”对“勒佤”支系的常用称呼,“牢”与“勒”音近,当只是方言语音的区别而已,意义相同。“牢”到底为何意?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人名。也就是“哀牢”是以祖先名而命名的。事实上,《后汉书·西南夷传》等书也认为“哀牢”是一个人名。与这种说法如出一辙。当然由于资料缺乏“哀牢”为佤名这种说法只能存疑。但是巴饶称“勒佤”支系为“牢”这一称呼,以及“勒佤”的“勒”与“哀牢”的“牢”显然是同音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云南省著名史学家方国瑜、[11](P22)江应樑 [12](P252)诸先生,认为“哀牢”乃佤德昂语支民族不无道理。
“佤”这一称呼不仅是佤族三个支系都认可的,而且与佤族同语支的部分布朗族也保留着这种称呼。“佤”为何意?目前仍有争议。在佤语中,“佤”是“门”的意思,有些地方加前缀“阿”、“艾”、“西”、“日”等,成为“阿佤”、“西佤”、“日佤”等,然而“佤”作为中心词的地位是不变的。佤族为何自称“门”?由于目前缺乏资料我们还无法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正确的回答。佤族人类起源神话“司岗里”传说认为佤族是第一个走出“司岗”(即人类的母体,有的说是葫芦,有的说是山洞)的民族,所以,他们自称为“艾佤”,“艾”意为长子,也就是说他们以“长子”自居。“佤”也许与他们的这一神话传说有关,即他们自称是第一个走出“洞门”的民族。佤族为什么以“门”自称,这确实是饶有趣味,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弄清这一族称的来龙去脉,也许可以真正弄清佤族这一民族的源和流。
汉文献记载也值得注意。晋朝人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条载“值南夷作乱,闽濮反,乃南移永寿,去故郡千里,遂与州隔绝”。著名民族史学家尤中教授认为“闽濮”“是近代孟一高棉语族的布朗、佤、德昂族的先民。”[13](P632)《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字道将,是晋世蜀郡江原县(即今四川省崇州市)的一个世家大族。他少年好学,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显然,“闽”字即“门”字框中的“虫子”,应当属于作为封建主义史家的常氏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谓。这一含义,与佤族自称“佤”含义相同。常氏是否以佤族自称为基础,作此记载的呢?另外,“濮”字前文已存论述,它是佤族最早的自称,而这里也出现了。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如果常璩真是基于佤族的自称“门”而写了“闽濮”这一族称,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论,“佤”确实是佤族先民继“濮”以后的又一个很有意思的古老族称了。这说明佤族的先民已经超出了仅仅把自己看作“人”与其他动物加以区别的粗浅认识了,而是把自己与“人”相比,认识更深了,更提高了。佤族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走出“洞门”的民族,这应当有深刻的历史内涵。
史学家有人对“闽”为何意进行了考证。比如已故的任乃强教授认为:“闽濮,后云孟族是也。闽、孟一声之转,其人自称曰‘孟’,古人加‘濮’字以便称用。今滇西南地名有孟、勐、猛字者,皆其小王故邑也”。[14](P289)孟是“蒲人”的望族,曾执掌顺宁(今凤庆县,当时顺宁包括今临沧全境及保山地区昌宁等地)数百年,到猛廷瑞时被明朝万历政府镇压,改土归流。之后孟氏衰落。今天,永德县一带还有大量的姓孟的佤族,他们当是孟氏的后代,显然“闽”与佤族有较多联系。
唐宋以后,有关佤族的汉文献更多了,更明确了。“佤”的记载最早见于汉文资料的是唐代樊绰的《蛮书》卷4、卷6以及《新唐书》卷222南蛮传等均有“望苴子”、“望蛮”、“外喻”等等记载,“望”、“外”与现代佤族自称“佤”元音略有变化或尾音稍异。《蛮书》卷4“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说明佤族经过历史上的不断迁徙到唐朝时已相对集中于澜沧江以西的广大地区。
外文资料也值得注意。缅甸第二大城市、缅北重镇曼德勒,缅语意为“入口处”。[15]这个意义与佤语大同小异。这可能与佤族大规模迁徙缅甸有关,这是一个主要的通道。
综上所述,佤族是一个分布广泛、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的与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双重影响,其内部发生分化、裂变,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是自然的了。
“巴饶”又自称“国佤”,意为“阿佤的后裔”。这说明“巴饶”是从“佤”分支出来的。然而,“巴饶”的分化当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饶”这一族称,最早见于《后汉书》的《孝安帝纪》和《南蛮西南夷列传》,前者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三月,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后者称:“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资治通鉴·汉纪》也有相类似的记载,并称“僬侥国,人长不过三尺”。言其矮小。这正是南亚语系民族的体形特征之一。清朝时倪蜕《滇云历年传》卷2也载:“僬侥,八蛮之一也。古称天竺,咳首、僬侥、跛踵、穿胸、儋耳、狗轵、旁脊,是为八蛮”等等。
文献中的“僬侥”是从濮或哀牢中分化出来的,哀牢以永昌(今保山、德宏、临沧等广大地区)为腹地而分布。而“僬侥”已远离了永昌郡而在其西,然而,他们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当有深刻的历史作为背景。汉武帝时开发“西南夷”,设立了犍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开凿了经过博南山(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境内),渡澜沧江通往永昌的道路,派遣大批汉人移民进入永昌,并在永昌境内设不韦、巂唐等县属益州郡所辖,郡县的设置加强了佤族与中原王朝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密切联系和友好交往,推动了社会发展。公元69年,东汉政府把益州郡的不韦、巂唐、比苏、斯榆(叶榆)、邪龙、云南6县划分出来,增设哀牢、博南两县,设永昌郡。据《续汉书·郡国志》载,该郡计二十多万户,一百八十九万多人,在东汉一百零五个郡国中人口数位居全国第二。这样,永昌郡内的哀牢人(即佤族)直接纳入了中原王朝郡县的管辖之内,他们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然而,封建朝廷即使能为历史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也是伴随着剥削和压迫进行的。郡县制度在云南执行以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官吏们对少数民族进行疯狂的敲榨和剥削,结果导致各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初元年(公元76年),永昌郡以哀牢人“反叛,攻(越)巂唐城。太守王寻楪榆”。后官兵利用“以夷治夷”的方法,利用“昆明夷”(当是氐羌民族)首领卤承把起义镇压下去了,为此,东汉政府“传首洛阳,赐卤孙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傍”即“濮”之音转,也就是“哀牢”人。可能就是因这次被镇压,使佤族向今临沧地区及中缅边境一带大规模迁徙。佤族就这样远离了永昌地,成为“永昌徼外”的民族。这部分佤族可能就是“巴饶”的前身,这时他们已开始以“饶”来自称了。这正是文献中出现“僬侥”的原因。“僬”当是佤语“类别”的意思,即“僬侥”是“佤”的二个“类”而已。
从东汉末年到元朝时,“侥”这一族称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部汉文史料中,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是他们已远离了中原王朝,其二是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出现,两个地方政权使佤族的“巴饶”支系断绝了与中原王朝及其地方政府的交往。这正是这部分佤族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巴饶”的分化,佤族有民间传说流传。相传人类在“门高西爷”(此地不详)诞生之后,佤族的先民追野猪,追到一个湖边,野猪跳进湖里,他们认为这是“西爷”(天神)的旨意,便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下来。后来其他民族来跟佤族争这个地方,他们施了美人计才就使佤族输掉这个地方,为此佤族称这个地方为“挪塞”,意为“输掉的湖”,据说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滇池。后来,佤族先民分散迁徙,其中有一支往滇西,一直迁到今天缅北重镇曼德勒,曼德勒是佤语地名,意为“歇息的地方”,佤族在这里停留了若干年,因为这里土壤肥沃,粮食丰足,他们又把这地方称“挪尔”,意为粮仓。后来,这一支佤族又南下到达今缅甸腊戍一带,他们在这里生活若干年,后来又分为两支迁徙,一支往东进入沧源、澜沧两自治县,他们就是“巴饶”的前身;另一支继续南徙,他们就是“勒佤”的前身。正因为腊戍是佤族发生重要分支的地方,他们称之为“得夹”,即“人们分开的地方”之意。[2]
佤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的历史主要靠口碑的形式流传下来。从我们对佤族历史的综合分析和研究来看,以上民间传说大体上与佤族的迁徙历史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佤族是个迁徙极为频繁的民族之一,他们之所以迁徙,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是首要因素。他们也正是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产生分支的。
总之,“巴饶”作为现代佤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支系,大体上在两汉之际开始从濮人这一群体中分化出来,之后由于不断迁徙,越来越远离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受到的辐射和影响也越来越小,导致了他们经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元明清时期,由于中央王朝的机构设置逐步深入到阿佤山腹心及边缘地区,比如元朝时孟定路的设置。同时,缅甸从12世纪起蒲甘、勃固、东吁等封建制王朝的崛起与扩张,使佤族不得不迂回迁徙,逐渐靠近中国历朝政府的地方设置机构,自觉归属中国的地方政府。这也正是明清以后有关佤族记载在各种文献增多的原因。值得提及的是明末清初,李定国率部进入阿佤山区,与班洪、班老佤族、孟定傣族土司三方歃血为盟,共同开发茂隆银矿之事,对佤族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此,大部分佤族开始把自己纳入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到明清之际,佤族内部的分化就更加明显了。明朝文献《百夷传》载:“古剌,男女色黑尤甚,男子衣服装饰,类哈剌”。《滇略》卷九说:“古喇,男女色黑尤甚,略同哈剌”。显然,“古喇”和“哈喇”是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部分。《滇略》卷九又说:“哈杜,稍类哈剌,皆居山巅”;天启《滇志》卷30说:“古剌,种类略同哈杜,亦类哈剌,居山,言语不通”。由此可见,“哈杜”与“古剌”、“哈剌”皆为同一民族,即佤族。这种以不同的称呼说明佤族内部的分化畛域已十分明显了。雍正《云南通志》卷24说:“卡瓦,永顺东南辣蒜江外有之,……有生熟二种,生者劫掠,熟者保路”。卡瓦与明代的“哈剌”当是同一群体,后来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8年)的《清文献通考》也有此记载:“葫芦国,一名卡瓦,界接永昌府东南徼外……地方二千里,北接耿马宣抚司,西接木邦,南接生卡瓦,东接孟定土府”。“卡瓦”当源于傣族对佤族的侮辱性称呼,到近代傣族仍然保留着“永顺”即永昌和顺宁两地,前者指今保山,后者指今临沧地区大部,辣蒜江即小黑江,澜沧江支流,“永顺东南辣蒜江外”这一带地区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阿佤山的大部分地区。所谓“生者”应该是指保留着猎人头祭祀的佤族,他们对外来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反抗行为和排斥,而“熟者”则不然,他们已革除了猎头祭祀,对外来民族、文化是积极欢迎、吸收的,他们应当就是“巴饶”支系。著名的民族史家尤中教授认为“近代沧源县班洪一带的佤族自称‘布剌’或‘剌’,盖即明代‘古剌’、‘哈剌’名称的延续”。[3](P633)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清文献通考》中“卡瓦”特指的是“熟者”,已经把“生者”独立出来看待,从地望上看,也符合实际,“生卡瓦”即“勒佤”,有的地方又称“大卡”,他们正处于“熟者”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且,已明确提到“葫芦”,人类由葫芦而出正是“巴饶”有别于其他两个支系最明显的文化特征之一。总之,从文献记载来考察,明清之际佤族“巴饶”支系已经完全形成,成为佤族最有特色的三大支系之一。
【收稿日期】2004-05-28
标签:佤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