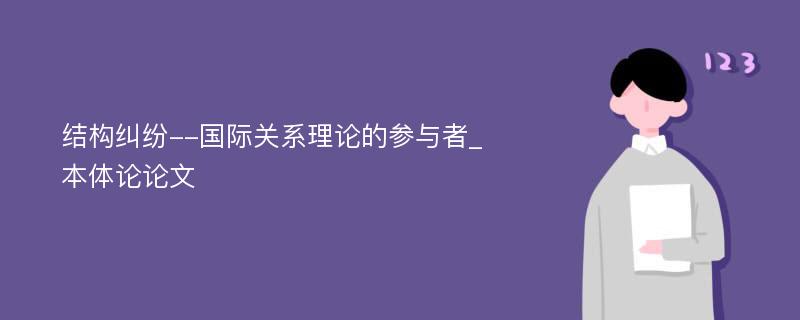
国际关系理论的行动者——结构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之争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温特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行动者—结构问题》一文后 ,在国际关系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行动者—结构问题的激烈争论。正是从行动者和结构 的关系入手,非主流理论向主流理论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从而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和 认识论进行了新的解读,为进一步理解国际政治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 问题的提出
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中,温特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动者—结构问题。“问题” 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认识论。本体论涉及的是行动者和结 构的性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认识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解释形式的选择,这种 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和结构的性质在因果分析上的重要性;第二个是行动者 解释和结构解释在社会理论中哪个相对重要。温特利用巴斯卡(Roy Bhaskar)的科学实 在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两把刀子,剖析了当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处理 行动者和结构的两条路径: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按照华 尔兹的结构定义,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体系的排列原则(无政府状态),单元的特征(功 能相同),单元的权力分配(力量大小)。但在华尔兹的分析中,无政府状态被视为一个 常数,单元的功能问题也被置于讨论之外,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造成了国际体系中的 变化,因而导致了各种不同的结果。“虽然权力分配是单位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属 于整个体系的特征,其作用不能还原到单位层次。”(注:[美]华尔兹著,胡少华等译 :《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在温特 看来,新现实主义表面上具有强烈的反还原主义特征,从结构的层次而不是从行动者的 层次来解释国家行为,而实际上,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在本体论上仍然是还原主义的。国 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先于体系和体系的结构。体系的结构不过是国家(行动者)的创造物 。体系的结构约束了行动者,行动者外生于体系的结构。“个别单元为自己而行动,从 同类单元的共同行动中,形成了影响和制约它们的结构。结构一经形成,市场本身就成 为一股力量,而且是进行单独行动或较少进行共同行动的单元无法控制的力量。实际上 ,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市场的创造者都多多少少成了市场的奴隶。”(注: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106页。)华尔兹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和公司来类比国际体系的 结构和单元(行动者)。“国际政治体系,像经济市场一样,从根源上说是个人主义的, 是自发产生的,不是有意的。”(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8页。)他的个 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本身暗含了还原主义的思想。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则与新现实主义相反,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由世界经济的组织 原则,特别是国际劳动分工来定义。它建构或生成了(constitute or generate)行动者 (国家和阶级)。行动者的存在由它们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生产出来,并加以解释 。世界体系理论家在分析资本主义的体系结构和国家(阶级)的关系时,把结构物化了。 物化是指“把人的活动产品理解为似乎不是人的产品的物体。物化的世界……被人经历 为陌生的实在物体,成为他无法控制的外生事物,而不是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的内生 事物。”(注:[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94页。)一旦客观的社会世界建立,则物化的现象也 随之发生。世界体系的结构实际上就是物化的结构,成为独立于行动者的外在之物。行 动者的活动只是体系结构功能需求的结果。体系在本体论上先于并创造了国家,国家不 过是体系结构的木偶。这样,体系理论家陷入结构决定主义,即结构功能主义的陷阱。 世界体系论处理行动者—结构的方法是结构主义的(structurationism)
不过,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在处理行动者—结构问题上具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把 本体论上先验的实体当做既定的。新现实主义把国家当做既定的,因而新现实主义处理 行动者—结构的个体主义视角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国家理论。世界体系论则把体系看 成是不变的,所以世界体系论没有体系理论。新现实主义通过把分析的单元置于本体上 原初的地位,以个体主义方式把结构还原为国家的属性与互动,体现了个体主义本体论 。世界体系论把国家(阶级)还原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再生产要求的作用和影响,体现了 整体主义的本体论。
温特认为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不能解释它们所分析的单元的性质,并提出了自 己处理行动者—结构问题的生成视角(generative approach)。温特用科学实在论解决 两个问题:不可观察的事物如生成的结构是否具有本体论的地位;科学解释的性质和条 件。对于不可观察的事物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温特认为,“科学实在论是一种科学哲学 ,认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存在的,成熟的科学理论势必指涉客观世界,并且即便是科 学研究的客体是不可观察的事物,科学仍然坚持指涉客观世界的原则。国家和国家体系 的结构虽然是不可观察的,但却是实在的和可知的。”(注: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 理论》,第61页。)这和经验主义的观点——存在即被感知不同。经验主义把本体论置 于认识论之下。对于第二个问题,温特认为经验主义只是对可观察事物的因果问题的回 答,使现象包摄在法则似的规律之下。按照休谟的观点,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不间断的 联系,对于不可观察的因果机制,我们永远也无法获得确切的知识。科学实在论则认为 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需要回答如何和是什么的问题,即探讨行为的因果原因和建构原因。科学实在论为温特去认识社会结构提供了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温特利用结构化理论揭示了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承认 不可还原的、潜在的、观察不到的社会结构的实在性。2.强调需要一种实践理性和实践 意识的理论,来解释人的意向性和动机;3.通过对行动者和结构进行辩证综合,克服个 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不足;4.社会结构与时间和空间结构不可分 开。(注: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1987,p.356.)温特在生成 的意义上把结构定义为一组内在的关系。一个社会结构的成分可能是行动者、实践活动 、技术和领土,其内在关系不可能还原为各组成部分互动的特性。这些成分不可能独立 于它们在结构中的地位来定义,如奴隶—奴隶主,教授—学生等。根据这种视角,“国 际体系的结构将把国家理解为国家与其他国家内在关系的结果,而不只是国际事件的原 因。”(注: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1987,p.346.)尽管社会结 构可能观察不到,但社会结构的影响可以观察到,按照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它们仍是真 实的实体。在温特的理论中,行动者是国家。温特之所以把国家当作行动者,是因为国 家体系的组织原则把国家建构成单个的决策单元,国家对他们的行动负责,不过,体系 结构把国家建构为行动者不应被看成是把国家作为政治权威的结构的概念排除在外,政 府行动者反过来也嵌入其中。(注: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339,note 6.亦可参见温特:《国际政治的 社会理论》第9页。)所有的行动者具有三种固有的能力:“1.能够提供行动的原因;2.反思性监控其行为;3.做出决定。”(注: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359.)在结构化理论看来,行动者 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正如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依赖于并由行动者的实践和自我理解 建构一样,反过来,这些行动者的因果力量和利益由结构建构并加以解释。”(注: 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p.359.)恰如吉登斯所言:“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 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 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构。”(注:[英]安东 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社会不是人的能动作用的无条件产物,也不独立于人的能动作用而独立存在。个体的行 动既不完全决定社会形式,也不完全被它们决定。这样就避免了个体主义的还原论和结 构主义的物化论。
二 争论的过程与内容
温特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场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行动者和结构的属性以及它们的关系;2.行动者和结构对解释行为哪个更重要;3.行动者在受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使动(enable)和制约时有多大的行动自由。由于哲学和 社会观的差异,学者的争论侧重点可能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德斯勒(David Dessler)认为行动者—结构争论的最重要问题在于承认人的动因(agency)是社会世界的行动、事件和后果的惟一力量,不过,人的动因只有在结构之内 才能认识到。“所有的社会行动以社会结构为先决条件,反之亦然。行为体(actor)的 行为之所以是社会性的,是因为存在可以利用的社会结构,只有通过行动者的行动,结 构才能被再生产出来。”(注:David Dessler,“What's at Stake in theAgent-Structure Deb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1989,p.452.)他把 结构定义为行动的媒介和结果。媒介包括两个方面:资源和规则。资源是物质能力,规 则是使行动成为可能,并再生产和改变行动本身。规则又分为两个方面的特性:即规定 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建构性规则或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规定性 规则规定了特定情形下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构性规则创造了行为的种类,涉及意 义的构成。在实践中,彼此都蕴涵了对方的意义。与温特一样,德斯勒批评了华尔兹的 结构现实主义,并把结构现实主义命名为位置模型理论(positional model)。华尔兹的 理论从本体论上说,单元在体系之前,单元的互动产生了结构。“一旦(结构)形成,市 场(体系)本身就成为一种力量。”行动者和结构是一种线性关系。德斯勒根据巴斯卡的 社会活动转型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替代理论模型——转型模型理论(transformationalmodel),在这种模型中,行动者与结构是一种生成关系。
1991年,温特进一步阐述了1987年文章的观点,由此拉开了90年代前期主要以温特为 一方和霍利斯及史密斯为另一方关于行动者和结构关系的论战。温特指出,霍利斯和史 密斯混淆了分析的层次与行动者—结构两个问题。分析的层次问题是解释问题,确定社 会集合的哪一个层次的原因对国家行为更具解释力,是民族国家还是国家体系,是官僚 政治还是个人的心理。而霍利斯和史密斯则把分析的层次问题描述为“是根据组成国际 体系的民族国家行为来解释国际体系的行为,还是根据国际体系的行为来解释民族国家 行为。”(注:Alexander Wendt,“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7,1991,p.388.)所以,他们的分析单元在不断的变化,首先是国家行为体的行为,然后是国际体系的 行为。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分析层次的问题,而属于本体论的问题:某一分析层次上的单 元的属性和行为是否能还原为另一层次上的单元的属性和行为。
对于动因、结构和体系问题,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否只有一 种体系理论,即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类比基础上的体系理论。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 是,体系理论是只解释单元的行为,还是也要包括他们的认同和利益。温特认为,在霍 利斯和史密斯的心目中,只存在一种体系理论,即华尔兹的体系理论,所有其他的理论 都是还原主义的。温特拒绝在还原论和体系论中做选择。他认为体系理论的范围应该扩 大,包括认同和利益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应该被看成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无政 府状态是国家对它的理解或建构(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国际体系有 多种逻辑,国家可以使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也可以改变它(但不容易),这取决于国家的 主体间性的实践对认同和利益的塑造。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首先假设国家是自利的,然 后分析了这些行为体的行为是如何被体系压力(竞争的奖惩)塑造的。在这个世界中,没 有复杂学习和自我的再定义,认同和利益是不变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只有一种逻 辑:自助和充满竞争的权力政治,因而他的体系影响的只是国家行为而不是认同和利益 。华尔兹似乎是一个整体主义者,因为他把行为体的行为看成是结构决定的,但由于他 把国家的认同和利益当成既定的,而不是社会互动建构的,没有涉及这些利益如何产生 ,因而,他实际上还是一个个体主义者。
温特认为,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要求局内者的角度,如先前存在的信念在社会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有的则要求局外者的角度,如战争对国家物质能力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不同的问 题要求不同的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像霍利斯和史密斯所说的那样,总是有两个故事 要讲。
针对温特的批评,霍利斯和史密斯给予了回应,认为行动者—结构问题涉及本体论、 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本体论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系统和单元所指的真实世界有 区别吗?系统和单元的关系如何?共有的指涉主要是系统的还是单元的?认识论是指如何 知道国际关系的陈述是对还是错?方法论是指采取解释的形式还是理解的形式。问题的 争论在于三者中哪个更重要。他们批评了温特在处理行动者—结构问题的理论基础—— 结构化理论和科学实在论。对于结构化理论,他们认为它只是描述社会生活,而不是解 释的基础。温特利用结构化理论并没有解决行动者—结构问题。行动者和结构在各个方 面并不容易结合,解决的方法常常不稳定。由于结构化理论使用单元间的结构关系和诠 释概念而使行动者—结构问题复杂化,因为单元并不一定是人,而诠释概念的指涉一定 是人的行为体。在这一点上,存在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区别。巴思卡的科学实在论根本没 有解决古老的柏拉图难题——寻找掩藏的真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 我们就已经找到了它。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找到它时也不会认出它。”(注: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Beware of Gurus:Structure and Action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1991,p.408.)在霍利斯和史密斯看来,华尔兹的结构概念是模糊的,一方面,华尔兹说,“分散型 经济的市场,从根源上说,是个人主义,它是自发形成的,并非有意建立起来的。”( 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6页。)这似乎有利于温特和德斯勒的诠释。另一 方面,华尔兹也强调:“从同类单元的共同行动中,形成了影响和制约它们的结构。结 构一经形成,市场本身就成为一股力量,而且是进行单独行动或较少共同行动的单元无 法控制的力量。”(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6页。)这似乎意味着体系有 它自己的生命。尽管温特和德斯勒从华尔兹体系结构的微观经济学类比中读出的是个体 主义的本体论并没有错,但它还意味着市场一旦建立起来,就是单元行为的原因。对于 分析的层次与行动者—结构的关系,他们认为分析的层次和行动者—结构两个方面都涉 及动因的性质。分析的层次不仅仅只是如何解释行为,还涉及对行为体的意义。这就涉 及解释与理解的关系。行动者—结构和分析的层次两个问题并不能分开。
查尔斯勒思(Walter Carlsnaes)认为行动者—结构问题包括两个相互有关的方面,一 个是严格的本体论方面,另一个是广义的认识论方面。前者关注行动者和结构的基本属 性:二者是否是原初的,关系如何;而当问及动因(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是被想像为客 观的还是主观的时候就出现后者。查尔斯勒思认为那种要么把行动者,要么把结构看成 惟一的原初物,然后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对行为进行分析来解决行动者—结构问题是有 疑问的,因为纯粹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排除了明显的相互作用,哪一个当作主要 的,只是假设的问题。(注:Walter Carlsnaes,“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Foreign Policy Analysi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6,1992,pp.245 —270.)查尔斯勒思以阿切尔(Margaret Archer)的形态论(Morphogenesis)代替结构化 理论。阿切尔认为,“社会—文化体系的突现特性隐含了互动和他们的产物(复杂体系) 之间的非连续性。这就要求在处理结构和行动问题时采取二元论的分析。行动当然是无 休止的,对于体系的连续性及其对它的阐述至关重要,但是随后的互动将与以前的行动 不同,因为后来的互动受到以前行动的结构结果的条件限制。因此,形态论的视角不仅 是二元论的,而且是连续的,涉及结构条件/社会互动/结构阐述的不断循环。”(注: 转引自Walter Carlsnaes,“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Analysis,”p.259.)这一立场与结构二重性把结构看成是过程而不是产物的概念形成了 强烈的对比。这就概括了结构—行动者互动不断循环的本体论概念。
对查尔斯勒思的文章,霍利斯和史密斯提出不同的观点,重申了结构和动因的理解和 解释的两个故事的主张。虽然形态论批评吉登斯在给定的时间点上混淆了行动和结构问 题,但在他们看来,形态论即使引入时间变量也没有解决动因—结构问题,而且使事情 更糟,似乎行动者和结构交替影响了社会世界。形态论的主要症结在于它没有说明我们 如何把结构和行动者整合在一个故事中。另外,查尔斯勒思声称本体论是首要的,霍利 斯尽管同意本体论对认识论上接受的东西产生了影响,但应该承认反过来也是对的。认 识论不能被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否则,对事物下论断是武断的。只有当你清楚原因 是什么的时候,认识论才是第二位的。人们不考虑更重要的认识论问题,也就不能解决 本体论问题。(注: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Two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1994,pp.241—51.“AResponse:Why Epistemology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Review of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2,1996,pp.111—116.)
1997年多蒂(Roxanne Doty)对温特、德斯勒和查尔斯勒思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提出 了批评:1.作为解决行动者—结构问题理论基础的科学实在论,仍然固守结构的本质主 义观念,这种结构观与给予行动者的实践以本体论和解释上的优先地位相矛盾;2.结构 化理论的悬搁(bracketing)概念在逻辑上本身就与结构化理论的本体论不一致,这种本 体论替代了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本体论。不过,与温特的观点相反,结构化理论的辩 证综合并没有克服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本体论的矛盾,这种矛盾以非常微妙的形式体现 出来。多蒂以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凝视了行动者—结构问题。她把后结构的实践概念引入 到行动者—结构中来,实践代表着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y)和不可决定性(undecidability)。它和意义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注:Roxanne Lynn Doty,“Aporia: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1997,pp.365—392.)
科林·怀特则指出多蒂误读了温特、德斯勒和查尔斯勒思在行动者—结构争论上的争 论,同时批评了以前的行动者—结构之争偏向结构方面,(注:Colin Wight,“TheyShoot Dead Horses Don't They?Locating Agency in the Agent-StructureProblematiqu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1999,pp.10 9—142.)并对温特在结构概念上的摇摆提出批评,(注:温特在1987年的文章中,结构 一方面被认为是规则和资源(来自吉登斯的观点),另一方面,结构被认为是一组真实的 、不可观察的内在关系(来自巴斯卡的观点)。)也对他把行动者局限于国家的国家体系 工程表示不满,认为温特把国家类比为人,作为个人集合的国家同样具有利益、恐惧, 因而是行动者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国家即使是受目标引导的行为单元,可以被认为是行 动者,但它也不是人。恰恰相反,国家是人建构的制度结构。温特把国家看成是行动者 ,实际上物化了国家,没有给人的动因留下空间。怀特利用巴斯卡的复合社会本体论(complex social ontology)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动因方式,提出了动因的批判实 在论(critical realism theory of agency),即动因的多层次透视(multi-layeredperspective)。怀特把动因分为三个层次:动因1、动因2和动因3。动因1是指主观性的 自由,具有认识自我(self)的能力。动因2是指动因1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成为行 动者(agent)的方式。动因3是指行动者1(对应于动因1)在动因2中所处的地位(status) 。也就是说行动者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而又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且这种社 会关系使行动者处于不同的角色地位。一个行动者的行为是三方面作用的结果,而对行 动者行为的分析是不可能还原为任何一个动因层面。
海德米·苏加纳米(Hidemi Suganami)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解读了行动者—结构关系, 提出了三方间图式(tripartite scheme)。(注:Hidemi Suganami,“Agents,Structures,Narrative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19 99,pp.365—386.)三方指机制过程(mechanistic process)、机会巧合(chancecoincidence)和意志行动(volitional act)。社会事件不过是三者结合的结果。机制过 程是一种叙述表达。意志行动只是有意图的行动,并不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行动。机会 巧合不是说事件没有原因,而是指两个或更多的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同时发生。苏加米 从叙述的角度提出了对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看法。“讲故事是一种‘解释’,正如听故事 是一种‘理解’一样。‘解释’和‘理解’因而可以被想像为同一叙述硬币的两面…… 不是不相容而是不可分离。”(注:Hidemi Suganami,“Agents,Structures,Narrative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1999,p.372.) 行动者和结构并不是已经给定的、独立的存在,他们部分是叙述的结果。
安德斯·别勒等人则根据罗伯特·考克斯的新葛兰西主义视角,提出了以前行动者— 结构争论中所忽视的部分。(注: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TheGordian Knot of Agency-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2001,pp.5—3 5.)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历史主义和历史结构的社会本体论;世界秩序的历史结构 。历史主义的方法集中在构成物质世界的历史结构的主体间性,通过历史来分析历史创 造者的不断变化的心智过程去理解社会世界。“结构通过人的集体活动建立起来,反过 来,又塑造了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历史的变化就被想像为结构和行动者的互应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注: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TheGordian Knot of Agency-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2001,P.21.) 历史结构的社会本体论是指不断的社会实践,它由人的集体活动创造并通过这种活动而 改变。在历史结构中,观念(ideas)、物质能力(material capabilities)和制度(institutions)三种因素相互作用。观念既是主体间的意义,也是社会秩序的集体形象( collective image)。物质能力是可以看见的资源。制度是前两个因素的结合。三个因 素呈现一个复杂的实在,但反过来它们都在社会生产关系、国家的形式和世界秩序三个 活动领域起作用。只有通过历史结构来理解历史变化的过程,才能回答客观的世界是如 何通过主体间性的变化而建构起来的问题。国家形式和生产关系的模式不同,世界秩序 也不同。
三 初步结论
从上面的争论过程中,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争论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是在温特与霍利斯和史 密斯之间展开,焦点集中在国际关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哪个更占主导地位。在这之后, 后结构主义和葛兰西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卷入争论的旋涡。这种争论有助于我们对 国际政治的理解,认识行为体的行为动因,扭转主流理论过分强调结构而忽视行动者, 对行动者的行为进行功能主义解释的倾向。无论是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基欧汉的新 制度主义,都体现了结构优先于行动者的特征。无政府状态是它们共同的前提假设,这 种结构是与行动者无关的。他们的争论主要表现在行动者之间是否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是追求绝对获利还是相对获利。结构有如一枚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行动者的头上,行动 者成为一个被动的木偶。主流理论的这种行动者—结构观实际上是当时美国社会学中占 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理论的折射。功能主义的宏大体系结构观淹没了行 动者的微观活动,遮蔽了行动者的互动过程及其所导致的体系变革。以建构主义为代表 的非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则利用社会学中的后结构主义、符号互动理论、结构化理论等, 更多地强调行动者的反思一面,对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重新审视,动摇主流理论的功能 主义大厦。这样,行动者和结构之间不再是一种线性决定关系。这种行动者—结构观是 与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消退、各种结构化理论的发展密切相联的。
2.如果说主流理论探讨行动者—结构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单元—结构的关系,理论 资源主要来自古典微观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理性主义假设,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者更多地与经济学家和博弈论者结盟来解释单元(以国家为主)的行为,那么,参与行动 者—结构争论的国际关系学者主要凭借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之光,或照亮主流国际关系 理论所忽视或未被注意到的空间,或审视传统理论大厦的根基。他们更多地与哲学家和 社会学家联姻来理解行动者的行为。这种差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与非主流理论之间 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国际关系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实在,还是蕴涵了社会(国家的拟人化) 的意义,是一种社会实在。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差异,尽管以温特为首的建构主义学者对 主流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剑指国际体系的根基,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没有 对主要由温特引发的行动者和结构之争给予积极的回应,基本上隔岸观火,因此这种争 论还局限在非主流理论之间。
3.行动者和结构是社会学中的一对核心概念,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一直是社会学所要面 对的问题。两者关系的争论折射出社会学的发展高度,也反映了社会学的理论分野。这 一对范畴的关系在社会学中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而,在国际关系中围绕它的争 论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最后的答案。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我们对国际政治本体论进一步 思考,而国际政治本体论恰恰是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所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种争论也许还 会持续下去,但这并不妨碍国际关系学者利用目前的社会学理论去探究国际问题的奥秘 。
标签:本体论论文; 新现实主义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认识论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华尔兹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