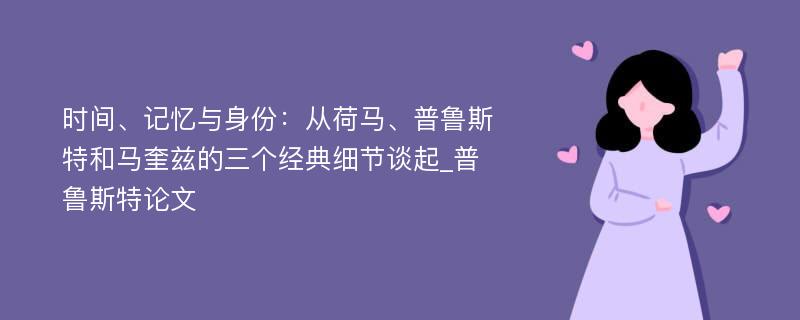
时间、追忆与身份认同——从荷马、普鲁斯特和马尔克斯笔下的三个经典细节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尔克斯论文,斯特论文,笔下论文,普鲁论文,细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为抗拒遗忘而生。据希腊神话,回忆女神摩涅摩绪涅与宙斯交合九天九夜后生下了九位缪斯,史诗、悲剧和琴歌都归缪斯女神管辖。因此,记忆或追忆,既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文学叙事的基本手法。
记忆进入语言文字得到讲述。但记忆具有选择性,并不是所有进入脑海的东西都会被记住;讲述具有筛选性,并不是所有被记住的东西都一定会被讲述出来。什么东西应该记住,什么东西应该遗忘,哪些东西应该讲述,哪些东西应该抹去,生理的和文化的筛选机制均起了作用。从文化筛选机制考察,每个个体、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或原则。但无论这些标准和原则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异,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都必然会涉及到身份的认同问题。因为人类对自身的存在和身份的感知是以记忆的延续为前提的。一旦丧失了记忆,或中断了记忆的连续性,身份就无法得到确认,自我就没了灵魂,存在就成了虚无。正是记忆把我们的感知经验联为一体,使我们确认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具有连续性的存在者。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奥德赛》《追忆似水年华》和《百年孤独》中三个关键细节的对比分析,探讨文学叙事与时间、追忆和身份认同的关系。
一、奥德修斯的伤疤
我们的讨论从古老的荷马史诗开始。《奥德赛》第19卷讲到,奥德修斯在历尽艰险终于返归家乡伊萨卡的时候,为了考验分别多年的妻子是否对他忠诚,乔装打扮成一个乞丐,在自己家门口行乞,结果被佩涅洛帕收留。老女仆按照好心的女主人的吩咐给这位“外乡人”洗脚。在所有的古老故事中,这通常是向疲惫的流浪者表示好客的第一道礼节。老女仆打了凉水,兑上热水,这时奥德修斯坐在柴火旁,立即把身子转向暗处,因为他倏然想起,老女仆抓住他的脚,会立即认出他小腿上的伤疤(那是他小时候打猎时留下的),从而暴露自己的身份。果然,老女仆给他洗脚,立即发现了那伤疤。
接下来的情节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关于洗脚的叙事暂时中断了,荷马插入了足足74行讲述了奥德修斯伤疤的来历。之后,
老女仆伸开双手,手掌抓着那伤疤,
她细心触摸认出了它,松开了那只脚。
那只脚掉进盆里,铜盆发出声响,
水盆倾斜,洗脚水立即涌流地面。
老女仆悲喜交集于心灵,两只眼睛
充盈泪水,心头充满热切的话语。
她抚摸奥德修斯的下颌,对他这样说:
“原来你就是奥德修斯,亲爱的孩子。
我却未认出,直到我接触你主人的身体……[1]
她还来不及兴奋地喊出声来,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便轻轻捂住她的喉咙,对她又哄又吓,不让她出声,以免坏了自己的大计。直到第21卷,他与儿子特勒玛科斯合作,用计将外来的求婚者统统杀死后,奥德修斯才撩起衣衫露出大伤疤,分别二十年的夫妻经过一番互相试探,才最终相认,合家团圆。
显而易见,在上述这个著名的片断中,被追忆和讲述的核心不是奥德修斯的“伤疤”,而是这个浪游者和冒险家的身份。伤疤无非是身份的一个标志,是讲述身份的一个引子或线索。二十年的离家-返乡之旅使奥德修斯感到担心和恐惧的正是自我身份的失落,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标志个人价值的东西(财产、地位、荣誉等)的消失。没有了身份,他就成了一个孤魂野鬼,一个无法被自己的家庭和部族认同的“外乡人”。没有了身份,他的回归就没有了意义,他向求婚人的复仇就没有了合法性基础。但悖论的是,他只能首先将自己的真实身份隐匿起来,才能获得自己的身份;只能先“非其所是”,然后才能“如其所是”。因此,伤疤就成为整部史诗叙述的一个关键细节。荷马既要让他的听众知道奥德修斯的真实身份,又要隐藏起这个真实身份;既要让听众知道他的伤疤的来历,又不能让女主人知道而坏了他的大计。换言之,他既要追忆,又要遗忘;既要展示这个伤疤,又要隐匿这个伤疤;既要讲述伤疤的来历,又要保守伤疤的秘密。伤疤深藏在时间这个巨大的折皱中,从童年一直到壮年,中间经历了十年的特洛伊大战、十年的海上历险,是刻骨铭心的身份标志,必须好好隐匿-讲述,不能轻易和盘托出。
从整个史诗的结构来看,有西方学者指出,《奥德赛》具有一个双重结构:整个史诗前半部分(第1至12卷)讲述奥德修斯归返以前的准备以及归返本身。后半部分(第12至第24卷)则讲述奥德修斯归返后,如何成功地实现其归返的目的。[2]显然,第19卷的伤疤在整个史诗的叙事结构中起到了一个转折和收尾的作用。从时间进程来看,《奥德赛》全诗的基本顺序讲述的是主人公在回归途中40天内发生的事情,而关于奥德修斯伤疤和相认的故事是在第38天发生的,之后两天便是弓箭比赛,杀死求婚者,夫妻相认和父子团圆。换言之,前37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为第38天展示伤疤即确认身份作准备,最后两天则是确认身份后顺理成章的结果。可见伤疤在整个史诗叙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奥德修斯追寻自我身份的时间之旅的终点,也是发现、展示和确认自我身份的起点。
二、小玛德莱娜点心
似乎巧合的是,在普鲁斯特笔下,叙述者也是从回忆在外祖母家度过的童年生活开始他的追寻时间之旅的。不过,玛赛尔拥有的不是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而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小市民家庭。类似奥德修斯从壮年向少年的回归,玛赛尔也从中年凝望着自己的童年。
这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除了同我上床睡觉有关的一些情节和环境外,贡布雷的其他往事对我来说早已化为乌有。可是有一年冬天,我回到家里,母亲见我冷成那样,便劝我喝点茶暖暖身子。而我平时是不喝茶的,所以我先说不喝,后来不知怎么又改变了主意。母亲叫人拿来一块点心,是那种又矮又胖名叫“小玛德莱娜”的点心,看来像是用扇贝壳那样的点心模子做的。那天天色阴沉,而且第二天也不见得会晴朗,我的心情很压抑,无意中舀了一勺茶送到嘴边。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玛德莱娜”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也许,这感觉并非来自外界,它本来就是我自己。我不再感到平庸、猥琐、凡俗。这股强烈的快感是从哪里涌出来的?我感到它同茶水和点心的滋味有关,但它又远远超出滋味,肯定同味觉的性质不一样。那么,它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哪里才能领受到它?[3](28-29)
一块小小的点心引出一种纯粹个体化的味觉,升华为超凡脱俗的快感,促使作者反思生命、存在与追忆的深层联系。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纯粹主观的感觉记忆为轴心而旋转的文学叙事空间。零乱杂散的记忆碎片,从浸泡着小玛德莱娜点心的茶杯中脱颖而出,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世界。追忆成为生命的根基,存在的连续性标志。叙述者的生命由一连串小玛德莱娜点心式的细腻而温暖的回忆构成。现时的感受引出往事的回忆,带回一段逝去的时间。按海德格尔的说法,过去的状态并未消失,而是曾在着(gewesen),亦即现在还现身在场着(wesend)。[4](203)——脚踩在斯万家高低不平的石阶上,使他重新找到了青年时代踩踏过的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台阶的感觉;手摸到仆人递来的浆过的餐巾,蓦然使他回想起巴尔贝克海滨浴场上用过的同样粗硬的毛巾,勾出一段已逝的爱情;斯万家的门铃声将他带回贡布雷老家花园的铃声,引出一段童年往事……
像生活在神话时代的奥德修斯一样,生活在理性时代的玛赛尔也关注着自己的身份,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同一性。不过,他所关注的不是外在的、生理性的身份标志,而是内在的、纯心理性的身份认同感,因为经历了500年的现代性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市民社会正在越来越趋向物质化、体制化和均一化。对于一个努力想保持自己个性的人来说,该被追忆和讲述的不是物质的伤疤,而是精神的“伤疤”,一种独一无二的、刻骨铭心的、完全个体化的情感体验,而这种情感体验在现化性的进程中正面临缺失的危险,从而危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导致存在的被遗忘。因此,小玛德莱娜点心就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担当起了类似奥德修斯的伤疤在《奥德赛》中曾经担当过的叙事功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追忆和讲述,玛赛尔找回了一段又一段温情脉脉的时光,从而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认识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即通过回忆往事,追寻失去的时间,将生活变成艺术,从而延续自己的生命,避免存在的被遗忘。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从一个字的发音、一片叶子的颜色,到一张皮的触感——都可以用来将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感(自我认同)加以戏剧化和具象化。因为,这一类东西在个人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过去哲学家认为可以(或至少应该)只由普遍共通的东西来扮演的。这一类的东西可以把我们一切言行所负载的盲目模糊印记加以象征化;它们表面上杂乱无章地凑合,其实都可以构成生活的基调;任何这样的凑合,都可以构成人生奉献服膺的无条件命令。[5]普鲁斯特通过他的独特的“追忆”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想告诉我们的是,生活,我们所过的生活是由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纯个体化的感觉及其回忆构成的,“这一切回忆重重叠叠,堆在一起,……有些回忆是老的回忆,有些是由一杯茶的香味勾引起来的比较靠后的回忆,有些则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别人的回忆,其中当然还有‘裂缝’,有名副其实的‘断层’,至少有类似表明某些岩石、某些花纹石的不同起源、不同年代、不同结构的纹理和驳杂的色斑。”[3](109)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完全属于个人的私密化的小叙事,而不是什么涉及国家政治命运的大叙事。“当大家都在谈论狄奥多西二世国王作为国宾和盟友在法国的访问将产生的政治影响时,我连听都不听。但与此相反,我是多么想知道当时斯万是不是穿着他那件披风式的短大衣!”[3](239)就这样,凭借个体化的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一种完全属于个人的记忆被开采出来,一个纯粹私密化的空间被展现出来,一种与启蒙大叙事(grant narrative)格格不入的个人小叙事(petit narrative)诞生了。
三、见识冰块的下午
如果说,普鲁斯特以“小玛德莱娜点心”显示了私密化记忆对现代性体制化社会的顽强抵抗,从而开启了一种个体化的身份叙事,那么,马尔克斯则以童年时代外祖父带自己去香蕉公司仓库见识冰块的追忆[6](33)为起点,成功地将私密化的个人记忆转换为集体记忆,展开了对族群身份问题的反思。
《百年孤独》的开头耐人寻味,如同《追忆似水年华》一样,那也是一个成人对童年时代的追忆,不过,这是一个面临生命终点的成人,从心理学层面上讲,他的追忆更加遥远,更加清晰,也更加刻骨铭心。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贡多是一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落,用泥巴和芦苇盖的房屋就排列在一条河边。清澈的河水急急地流过,河心那些光滑、洁白的巨石,宛若史前动物留下的巨大的蛋。这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7](1)
叙述者从现在出发,推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个事情的亲历者又将在将来的现在回想过去,随后,叙事时间又从较近的过去滑向更远的过去,直至史前时代。由此,小说展开了一个人、鬼、物交感的世界,体现了具有拉美本土文化特色的、建立在古老的“万物有灵论”基础上的魔幻和巫术世界观。
为什么追忆以“冰”开头,为什么那个见识冰块的下午是如此之“遥远”?对于从来没有见识过冰的小奥雷良诺来说,冷冻的感觉与“煮开”的感觉没有什么差别。从隐喻的层面上看,冰块是一系列外来的、陌生的、无法理解、无法把握的东西的表征。而它正是一位名叫墨尔基阿德斯的吉普赛人带来的。这个外来者不光带来了冰块,还带了磁铁、放大镜、望远镜等一系列新鲜的、陌生的事物,进而带来了封闭的小镇原住民对异域的向往,带动了布恩地亚家族第一代人对马贡多以外的世界的探索,之后带来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概念,引发了一系列的选举、起义、暴动、罢工与血腥的镇压,带来了那场整整下了4年零12个月零2天的雨,鱼可以游进门,游进窗子……
《百年孤独》以个人追忆始,以集体遗忘续,以预言实现终。第一章开头布恩地亚上校的追忆与第三章中间遗忘症在小镇的流行,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其所表征的正是族群记忆丧失的这个历史事实。族群记忆-遗忘是整个小说身份叙事的核心。由于大量外来人口和新奇事物的涌入,原先封闭而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马贡多的原住民全都患上了由失眠症转化而来的遗忘症,“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白痴”,[7](37)以至大家不得不赶在记忆完全丧失之前在每件物品上贴上标签,写上“这是XX”,“那是XX”,作为引发集体记忆的线索。一个丧失了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族群,其必然的命运就是灭亡。小说结尾,奥雷良诺·布恩地亚面对丧妻失子的哀痛,忽然领悟了墨尔基阿德斯提前一百年写在羊皮纸手稿上的这个家族的历史,随即他与马贡多这座幻景城一起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
在接受哥伦比亚作家兼记者普利尼奥·门多萨的采访时,马尔克斯自陈,写作《百年孤独》的初衷是“为我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归宿”。[6](103)这个归宿最后落实在布恩地亚家族的历史中,而这个“布恩地亚家族的历史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历史的翻版”。[6](105)同时,他又指出,“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至今,在我们中间,还有着健忘症。只要事过境迁,谁也不会清楚地记得香蕉工人横遭屠杀的惨案,谁也不会再想起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6](105)这样,个人叙事、家族历史和民族寓言这三者就融为一体了。借助童年记忆,马尔克斯成功地为布恩地亚家族-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制造了一架巨大的“记忆机器”,通过《百年孤独》的追忆和讲述,将遗忘之物呈现在世人面前,促使人们牢记过去,消除遗忘症,摆脱消失于飓风中的命运。
四、时间、追忆与身份叙事
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与追忆相关的时间上来。无疑,回忆中的时间只能通过叙事才能得到表述。而叙事对时间的表述决不是毫无节制、顺其自然的,必定要经过精心的筛选和复杂的再组织。在上述三个细节中,时间都被叙事者重组和扭曲了。只不过重组和扭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荷马史诗中,时间的重组是有理可依、有章可寻的。荷马一面在追忆他的主人公的往事,一面也在追忆和歌唱希腊部族的历史。在关于伤疤的插入情节中,荷马“以田园牧歌式的笔调讲述了奥德修斯的孩童和少年时代”。[8](19)但是,正如奥尔巴赫指出的,在荷马史诗中“所有事件都呈现出一种连续不断的、有节奏的动态的过程……任何地方都不会留下断简残篇,现象的进展总是处在主要位置,始终处在地点和时间的现时性中”。[8](5)荷马仿佛站在奥林波斯山上的阿波罗,俯瞰着山下的芸芸众生在欲望的催逼下摸打滚爬,而他则以地中海水般清澈的目光观察着、记录着这一切。他的叙事不带任何个人偏见和主观色彩。他的时间模式是一种“客观现时性”,[8](6)一种属神的,处于时间之外的、永恒的现在时。荷马关注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讲述现在。在荷马文体里,先讲一大段往事之后再讲现在的这种现时主观性视角的写作技巧是找不到的。“荷马只懂得运用前景,只会运用着墨平均的客观现在时”。[8](6)“荷马风格是使事件展现在画面的前景,他的诗里虽然有大量的前后跳跃,但他每次都把正在讲述的事情作为目前惟一而不与其他事情相混淆,没有讲述人视角的出现。”[8](12)简而言之,奥林波斯山的众神牢牢地主宰着时间的进程和叙事的进展。
但是,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荷马式的客观现在时转变为普鲁斯特式的主观现在时。时间的亲历者和时间的讲述者、回忆的“我”和反思的“我”合而为一。普鲁斯特自觉意识到,“这颗心既是探索者,又是它应该探索的场地”;“我并非处于时间之外,而是像小说人物一样受制于时间的规律”。[3](277)时间在叙事中展开非线性的跳跃。“当前、过去和将来交织在一起,三种时间绽出状态(Ekstasen)同样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手法。”[4](187)这种叙事时间模式显示出,荷马笔下的那个完整的、统一的、神性的世界已经崩解。由神创造并赋予意义的世界变成了由人自己构建并赋予其意义的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时间链条脱节了,完整而统一的个人身份崩解了。追忆者所能抓住的只是自己生存的一些碎片和残屑。“但一旦重新感受到一种已经听到过的声响,一种早已熟悉的气味,而且这种声响和气味既是当前的同时又是过去的,是现实的但又不在眼下,是观念性的但又不是抽象的,这时候,那持久地存在着而通常隐而不显的事物的本质就立即会获得释放,有时似乎久已死亡但实际上并没有全然死亡的自我,就会苏醒过来,从供奉给它的神性佳肴中获得新生。”[4](214)正是通过这种被莫洛亚称之为“无意的记忆”[9](15)的方式,即通过现时的感受与某一回忆的巧合而产生无意的记忆,作家进入时间之中而又越出时间之外,逃脱了物理时间的压迫,进入绵延的心理时间、生命的存在本源,确认了自我的同一性。
与《追忆似水年华》相似,《百年孤独》也采用了一种多维的时间模式。布恩地亚上校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成了叙事时间起承转合的关键。四种复杂的时态交汇在了一起,现在中的将来、将来中的现在、将来现在中的过去、过去中的过去融为一体,体现了人类对时间的感知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发展,它不光是线性的、流动的、四散的、漫溢的,更是互相交融、互相穿插、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荷马式的简洁明快转化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万花筒式呈现,普鲁斯特的非线性跳跃升华为令人目不暇接的烟花般的绽放。记忆的空间变得更加广阔,更加激动人心。由于整个族群的集体记忆已经在民族大迁徙和克里奥尔式的杂交中丧失或部分丧失,援引已往经典作品中的类似记忆碎片就成为恢复族群记忆的一种手段或途径。小说中的布恩地亚用了14000张卡片制作他的记忆机器,而现实中的马尔克斯则大量运用了从古希腊、希伯莱到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原型,使人感到历史的延续性和时间的循环性。马贡多的开发者布恩地亚与其妻子的乱伦关系,以及其后他俩离开家乡、自谋生路的经历令人想到《圣经·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被放逐的故事。布恩地亚率领马贡多的村民寻找通向外部世界出路的故事,显然与《圣经·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希伯来民族寻找迦南地的故事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小说中那场下了整整4年零12个月零2天,冲刷了被政府军屠杀的罢工工人的血迹的大雨,也明显与《圣经·创世纪》中的大洪水有相似之处。布恩地亚家族的大女儿阿玛兰塔终身未嫁,把自己关在家中,不断为自己缝殓衣的情节,令人想起《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帕为应付求婚者而不断织布的故事。上述多重时态和多重文化隐喻折射出的,是一种“博采众长而丰富的发展起来”的“混合文化”,[6](73-74)一种包括西班牙、非洲黑奴、美洲土著在内的地理、文化渊源,即加勒比,它正是马尔克斯最深刻的身份认同感之源,正如作家自陈:“它(加勒比)不仅是一个教会我写作的世界,也是我不感到自己是异国人的唯一地方。”[6](73-74)
上述三个经典文本中的细节,分别来自古典时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后殖民时期,都涉及一个成年人向自己孩童时代的追忆。三位作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以不同的叙事方式,不同的时间模式,通过个人化的追忆,确认了自己的或自己所属的族群的身份和历史使命。奥尔巴赫曾提醒我们,在他引用的关于伤疤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洗脚这一祥和的家庭场景是怎样嵌进伟大、重要、崇高的返乡情节中的”。[8](25)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奥德修斯的伤疤、玛赛尔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和布恩地亚见识冰块这三个小小的细节,是怎样嵌进更加伟大、重要和崇高的身份叙事中的。伊萨卡、贡布雷、马贡多与其说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其所表征的是人们对自我身份和族群身份深深的眷恋和怀念。
由此可见,身份(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族群的)不是已经在那里等候被发现的一种本质性存在,而是通过文学的讲述,从细微的追忆碎片中建立起来的。文学的追忆不是单纯的再现,而是通过想象的创造。只有对处在理性和体制双重压迫下的记忆加以钩沉、开发、重组和重构,把散乱的记忆整理为叙事,让分散的经验凝聚起来,使之变得更为强烈、更为集中、更为深刻,才能建立起个人的或族群的身份认同,更有力地发挥其促使个人和族群新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作用。
标签:普鲁斯特论文; 奥德修斯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马尔克斯论文; 荷马论文; 追忆似水年华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百年孤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