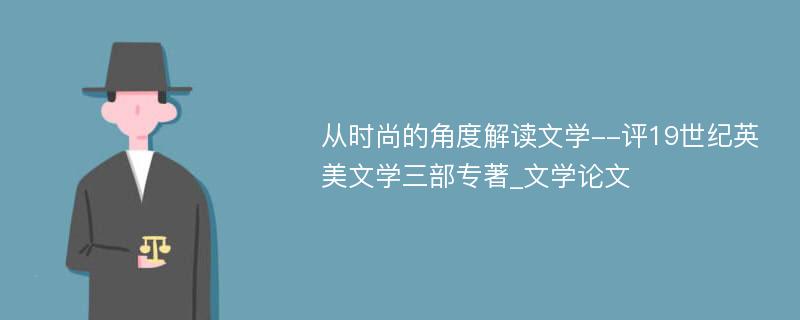
从时尚解读文学——评三部19世纪英美文学研究专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专著论文,英美论文,世纪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时今日喧喧嚷嚷的后现代社会,一切都似乎具有了无穷的可能性,文学研究者们似乎也耐不住寂寞,用腻了各式各样的文艺批评理论后,他们尝试着如何让文学研究突破学科的界线,让研究的触角尽可能地触及时代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时尚这一原本看似与文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让传统学人不以为然的事物,如今已经成为学者们创新文学研究视角的一个法宝。这些研究者们在对诗歌、小说、书信、散文等文学作品的细读中,发现了其中对作品所处时代家居生活、服饰、发式等时尚细节的丰富描绘,这些描绘为人们了解当时的风貌,理解作家及其作品,乃至反思当今的经济文化与创作提供了拓展的空间,于是他们将时尚引入文学研究的殿堂,使之由世俗之物摇身变为学术研究的手段和内容。
2009年在英美出版的三部文学研究专著在这方面很具代表性,它们立足于文本,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文学文本中19世纪的生活细节,以服装、发式等时尚要素为核心,结合当时的产业发展、消费经济动态,透过学术的视野挖掘这些作品中的时代精神和文化风貌,从时尚潮流的细微处拓展人们对这一时期的理解。这三部别有情趣又不乏学术意义的作品分别是:克里斯汀·贝利斯·考弛(Christine Bayles Kortsch)的《维多利亚晚期妇女小说中的服饰文化:修养、纺织业与激进主义》(Dress Culture in Late Victorian Women's Fiction)、但宁·沃德罗普(Daneen Wardrop)的《艾米丽·迪金森与服装制作》(Emily Dickinson and the Labor of Clothig),以及加利亚·奥菲克(Galia Ofek)的《维多利亚文学文化中对头发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Hair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这三位研究者也许由于本身性别使然,在研究过程中尤其关注到潮流之物如何影响到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的建构与修正、女作家的创作等问题,但她们的研究又是超越性别研究的,她们将之与消费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等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的探索,使其研究成果具有普遍的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们知道,在19世纪,无论是人们对性别政治的理解,还是与纺织相关的科学技术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布料和服装制作由手工生产向规模化机器生产发展,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也随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女作家们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变化有所反映和再现,她们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了考弛等时尚文学研究者进行科研的极佳文本。以女作家的创作为研究基本,这些研究者们或广泛涉猎或专门研究19世纪的文学作品,从中谋取时尚与文学文化间的联系,探究了现代性的形成与特质。
考弛在《维多利亚晚期妇女小说中的服饰文化:修养、纺织业与激进主义》中即以19世纪晚期女性作家尤其是新女性作家(New Woman writer)的小说为研究内容,其中有奥莉芙·施赖纳、萨拉·格兰,以及知名度不高的玛格丽特·奥利芬特和格特鲁德·迪克斯,也涉及到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夏洛蒂·勃朗特及乔治·艾略特等前辈知名女作家。在书中,考弛细致考察这些作家与服饰相关的小说、书信、散文等各种素材,探讨服饰文化与当时风行一时的“新女性”及创作间的关系。
该书的开篇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某博物馆里陈列的白色亚麻织物,上面书写着一位13岁开始从事家政并屡遭欺辱的女性的自白。另一个例子来自于有第一位新女性作家之称的奥莉芙·施赖纳的作品《从人到人》(From Man to Man)。在这部小说里,缝纫成为女性无法在公众世界里表达自己的隐喻,小说里的叙述者说男人可以用笔书写他们的观点,而女性只能用缝纫针蹒跚而行,她不禁发出这样的质疑:“钢笔或铅笔能像缝纫针一样那么深刻地浸到人类的血液中吗?”缝纫制衣似乎成为限制女性甚至是毁灭她们的意象。然而,考弛指出正是在这同一部小说里,缝纫也象征了女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书中的女主人公们谋得了经济自由。通过这两个例子,考弛提出了诸如“维多利亚女性如何理解缝纫和写作的关系,如何表现并利用这种关系?”等问题,并运用“服饰文化”和“双重修养”(dual literacy)这样的概念对之进行探讨。
考弛的“服饰文化”指向缝纫与对服饰的阐释两种活动,她把服饰文化当做一种“特别的交流形式”,并在论著中着重于探讨服饰语言与文字语言的联系。双重修养这个概念强调的即是女性的文学修养与衣着修养之间的关系。在考弛看来,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作家具有既能创作阅读文本也能编织解读服饰的素养,从而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她在书中讨论了维多利亚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尤其是缝纫等女红的教育,还洋洋洒洒地追溯了那一时期女性内衣的发展史,探究“新女性作家们如何运用文学和服饰文化的双重修养处理服饰、性道德和社会激进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考弛的阐释中,维多利亚女士们擅长的缝纫犹如一种符号学的体系,象征着女性人物“丰富、有意义的活动”,表现出维多利亚女性群体的意识,以及女作家们在写作和制衣双重活动下的创作特征。她指出,这些19世纪末作家们创作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关于缝纫行业中女性劳力价值、服装穿着的适当性与否的争执。她的服饰文化之说不仅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新女性小说,也给现今的女性写作带来些启示。
无独有偶,考弛的服饰文化之说在但宁·沃德罗普的《艾米丽·迪金森与服装制作》一书中得到一定的共鸣,只不过该书聚焦于19世纪的美国诗人迪金森一人。沃德罗普非常细致入微地探究了迪金森与服装的关系,甚至于颠覆了诗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
身着一袭白色高领长裙,生活在新英格兰的迪金森总是给人留下与世无争、内敛隐遁、远离时尚的印象。沃德罗普通过对19世纪中后期的市场经济,尤其是纺织服装业状况的分析,潜心琢磨散见在迪金森诗歌和书信中有关服饰的表述,以详实的资料,细致的文本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关注自己外貌打扮、生活情趣盎然的女诗人。在她的笔下,迪金森和她同时代的女性一样会设计、缝针、包边、漂白、熨烫、织补等女红,是一个会为自己服饰的样式和材质而焦心烦神的可爱女子。沃德罗普对迪金森闻名遐迩的白色长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连裙子上几颗纽扣、扣子大小以及材质都一一道来。不仅如此,她从迪金森的文字中寻觅到披肩、巴斯克式紧身衣、靴子、灯笼裤、帽子、蕾丝等有关女士服饰的内容,并逐一分析它们隐含的文化变迁,挖掘它们对迪金森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诗人如何将之转化为情色符码,表达情感与欲望,创作出她所谓的迪金森的不同于传统田园诗的“修正田园诗”(revisionary pastoral)。她在结论中说:“艾米丽·迪金森,既是女人又是艺术家,她生活在这段经济和时尚审美观发展的时期,她在制作、穿着衣服方面的角色必然影响到她的艺术实践。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文与其衣着互为表现”。沃德罗普的分析紧扣当时的物质文化语境,一点点让人们看到服装的生产制作与销售在当时成为家庭和工厂工人物质生存的一种基础,愈发明白服饰文化对于迪金森个人生活及其创作的影响。
沃德罗普和考弛通过服装的演绎解读19世纪的文化历史,获得对作家的新的理解,加利亚·奥菲克则在她的论著中对另一时尚符号——头发进行解码。她借头发大做文章,探讨女性特征是如何在维多利亚文学文化中得到建构、定义和修正的。
奥菲克告诉我们,在维多利亚时期,头发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恋物”(commodity fetish),一种有价的财产。女性拥有一头健康漂亮的秀发越来越成为她们骄傲的资本,时髦的女性不停地变换着时尚的发型。市场上对假发、护法、美发产品的需求也随之猛涨,甚至会发生“抢发罪案”。区区头发可以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文学作品中也就时常可见它们多变的样式与色泽,透露着主人的心情、身份,传递着社会文化的信息。在分析过程中,奥菲克运用弗洛伊德学说、19世纪兴起的恋物理论、玛丽·杜格拉斯的身体政治说、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等,饶有兴致地谈起维多利亚人对头发的迷恋,从而引出头发的象征意义和商业价值,及与其相关的性别、社会政治身份等问题。
在她的研究视野中,除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乔治·艾略特,玛格丽特·奥利芬特、布朗宁夫人、E.L.林顿、M.E.布莱登等这些女作家之外,还有查尔斯·达尔文、安东尼·特洛诺普、D.G.罗塞蒂、查尔斯·狄更斯、托马斯·哈代、奥博利·比亚兹莱等著名男性作家。她穿梭于这些艺术家的小说、诗歌、文评、漫画等作品,评析男性作家作品中将头发居家化的描写,思考女性作家对头发的描绘是否改变或动摇了这个符号,是否表明她们向“女性气质在于,而且能够被符号系统所控制”这种观念妥协等等问题。她力图通过对头发这看似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无足轻重的物质的分析,揭示出当时的社会如何寻求“将女性的头发收藏、修整、柔顺或者分类,作为展开讨论女性性欲望的方法,以及在政治动乱期稳定两性间的力量关系的手段”。她指出,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对头发的描绘“既反映又偏离了女性特质的标准化过程,以及女性对自主决定的追求”。
这三部专著都是从21世纪的现代社会回眸久远的19世纪,并创新性地将时尚的概念引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通过研究风行一时的物质文化,强调服装、发式中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性别因素,同时又生动形象地表明人们对衣着和发型的选择是如何深植于制造业、商业和广告体系之中。更有意义的是,它们将服饰、发型等风行之物上升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层面,剖析它们的符号意义,通过它们演绎维多利亚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对女性写作与时尚文化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引申到女性身份、气质、创造力等核心话题。如此,它们在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的语境中对时尚元素进行了解读,并进而实现了对现代性形成的解读。这样从时尚事物切入的研究方法似乎脱去了迂腐之嫌,比较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而其严谨的研究立场也会为文学文化研究者所尊重。
《艾米丽·迪金森与服装制作》一书的序言中讲道,“无数的文学研究聚焦于阶级、经济、性别,以及文化历史某些的具体方面,文学研究中的时尚研究依然处于起始阶段”。这三部书正是处于起始阶段具有推动力的作品。自然,不仅仅是这三位研究者在这条道路上奋进,她们还有不少志同道合的伙伴。如R.S.考本(R.S.Koppen)在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时尚与文学现代性》(Virginia Woolf,Fashion and Literary Modernity,2009)一书中也是从服饰时尚入手探析伍尔夫创作的现代性。科斯蒂·布莱尔在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文评中提到,男性消费者、读者和作者业已培养了阐释自己和女性服饰的能力,也许只是在程度上没有那么私密,如布伦特·香农(Brent Shannon)2006年发表的《君子好穿:男人,服饰与消费文化》(The Cut of His Coat:Men,dress,and consumer culture)。不仅如此,还有些出版社也在推动这样的研究。《维多利亚晚期妇女小说中的服饰文化》与《维多利亚文学文化中对头发的再现》这两本书都是Ashgate出版社在英美同时出版的论著。《艾米丽·迪金森与服装制作》也是新汉普郡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之一,这套丛书包括《伊迪丝·华顿与时尚风行》(Edith Wharton and the Making of Fashion)、《斯拉夫人的肉之罪: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食物、性与食肉欲》(Slavic Sins of the Flesh:Food,Sex,and Carnal Appetite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Fiction)等十余部作品。该丛书之服饰解读系列的编者在扉页上写明,编辑出版这一系列专著的目的就是探究历史、文化、文学的多种形式与服饰、纺织、设计、生产的关系,他们力图将时尚与学术结合,探究物质文化与社会历史、文学文本的交织在哪些方面与现代的读者和学者产生共鸣。
这三部作品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材料详实,图片文字相得益彰,对19世纪的物质文化做出了细致的调研与分析。也许细致不免会让人觉得琐碎。布莱尔在评论中说,考弛和沃德罗普的文本细读有时过于强调女性参与服饰文化的意义而显得有点站不住脚;“双重修养”这个概念不错,但这并不需要人们拥有大量的缝纫知识,把握当时复杂的时尚理念,才能理解施赖纳《从人到人》中那个白天穿着粉红丝袍,蕾丝衬裙和昂贵的裘皮外套走在街头的伯蒂,是个“堕落的女人”。对于奥菲克不懈余力地挖掘维多利亚时期发型这一符码所蕴含的两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布莱尔也不无调侃地说,从奥菲克的作品可以预见到以后更大的研究空间,也许会出现对男人面部毛发或两性体毛时尚的研究;而且,奥菲克尽管研究细致,却并未涉及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色情文学,或许只有在那些作品里,年少主人公才能坦诚女性腋毛对他的吸引力。这样的调侃虽然有点尖刻,却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在当今喧嚣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像以上三本专著那样详尽地探究以往的时尚也许并不会产生多大的惊奇效应,但它们对于激发读者的兴趣、拓展读者的视野不无裨益。而且,这三部作品所采取的细腻、亲和而严肃的研究态度,在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的跨学科探索的尝试又是值得学术研究者们借鉴和思考的。况且,这些研究还多少摒弃了文学研究中的“势利气”,关照到一些声名并不显赫的作家和文本,为时下“经典”之论也增添了些活力和研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