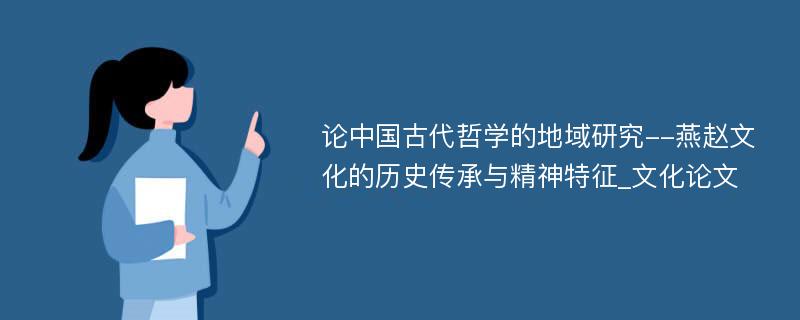
“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研究”笔谈——燕赵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精神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赵论文,笔谈论文,地域性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特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5)01-0014-14
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民族性,而且具有地域性。时代性反映了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时间向度,民族性反映的是不同族类在实践活动中传承积淀而成的文化类型和精神特质,文化的地域性反映的则是文化的民族性(共性)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空间、不同的社会人文空间所呈现的多样性。燕赵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传承和地域特征看,大体相当于今日行政区划所辖属的河北区域文化。这里所谈的燕赵文化,指狭义的燕赵思想文化。
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
远古时期,“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就在燕山脚下留下了历史文化遗迹。原始社会晚期,黄帝部落由渭水流域迁徙到当今河北省西北部,《史记》就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记载。可见,河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中的《邶风》、《卫风》、《鄘风》,其部分诗篇即产生于河北南部。战国时期,燕、赵不仅成为独立的诸侯王国,而且以重义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风骨,屹立于七雄之林。汉代乐府民歌中的不少诗篇,如《战城南》、《上邪》、《有所思》、《陌上桑》、《饮马长城窟行》、《孤儿行》等,即属于反映河北一代民风士气的燕赵民歌。先秦、两汉时期诞生在燕赵大地的文人学士很多,如荀卿、慎到、公孙龙、董仲舒、李延年、崔骃、崔瑗、崔寔等,他们的哲学思想或散文诗赋,均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大放异彩。魏晋南北朝时则有地理学家郦道元、数学家祖冲之、郭守敬,文人张华、刘琨、卢谌、杨炫之等,他们的科学创新和文学创作,广为世人所知。
唐代政治相对稳定,燕赵文化进一步发展。从文坛上看,唐初有“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武则天时有李峤、苏味道,盛唐时有高适、李颀、李华、李嘉祐、刘长卿、卢纶、司空曙,中唐有贾岛、卢仝、刘禹锡、崔护、张祜,晚唐有高蟾、卢汝珍等,没有他们,有唐一代的文学就会大为逊色。两宋时期,国家重文治,此种国策肇始于祖籍河北涿州的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北宋,荆公新学、温公史学、三苏文学、二程道学等,学派分立,互有高下,至南宋思想文化一归于朱子学。从总体上看,此一时期国家政治文化重心南移。而燕赵文化传承,仍有拓展。河北籍学者李昉编辑《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的文苑盛事,即其一例。另外还有一度在河北任官的欧阳修、苏洵、苏轼、黄庭坚、贺铸等外省人士,也曾为燕赵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元明时期,燕赵大地戏剧词曲艺术异峰突起。元曲三大活动中心有两个在河北境内,一为元大都(今北京),一为真定(今正定)。约50名著名的元曲作家中,河北就占31名。其中,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剧作《窦娥冤》、《蝴蝶梦》、《望江亭》等历演不衰,影响深远。其他如白朴、王实甫也是举世公认的戏剧创作大师。还有刘因、蔡松年、赵秉文、王若虚、李治、元好问、完颜亮等,或理学、或诗文、或词曲,在燕赵文化传承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清代文化学术的主流是以训诂考据为特色的朴学,但性理、词章之学并未中断。在燕赵学者中,定兴鹿善继、容城孙奇逢是清初性理学的代表,“其学以阳明王氏为宗”,桐城派学者方苞称其为“百数十年间,北方真儒”(《望溪集》卷十四《重修阳明先生祠堂记》)。博野颜元,生于穷乡,长于乱世,艰苦卓绝,力倡“习行”之学,是清初实学的杰出代表。颜元痛斥理学,鄙弃词章、考据,北方学风民气为之一振。乾嘉之际,朴学鼎盛,《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晓岚为此时朴学兼词章之学的名流。同光年间,清廷主张洋务新政,南皮张之洞则是晚清洋务派的后起之秀。他系统阐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
辛亥革命前后,先后废除科举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经学时代宣告终结,“重新固定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应运崛起。生长于燕山脚下、渤海之滨的李大钊是现代史上最杰出的燕赵儿女、思想巨匠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此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时代赋予燕赵思想文化以全新的意义。
二、燕赵风土民性及文化特性
不可否认,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风土民俗、文化性格、心理气质等具有重要影响,在生产力低下,交通、教育、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从自然地理环境看,作为燕赵大地的河北,东临渤海,西倚太行,南接大河,北枕燕山,地理环境自古如斯。东海之阔,黄河之动,太行燕山之雄奇厚重,自古生存于如斯环境,祖祖辈辈从事农耕生活间或从事些手艺和小本生意的传统意义上的河北人,养成质朴厚道的民风,木讷爽快的民气、重义任侠的民性和勤奋耐劳而不精明的民智。这就是燕赵风骨或河北人的文化性格。此种文化性格,通过生理性的和社会历史性的遗传,至今不同程度地流淌在现代河北人的血液中,积淀为他们的心理气质并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
从人文历史环境看,燕赵文化自古形成于华北平原的中部,东南与尚功重智、知礼乐仁、民性仁厚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毗邻,西边与尚法、尚兵、重商、民性刚毅的秦晋文化肩连,西北与高寒地带金戈铁马、弯弓射雕的游牧文化相望,东北与地广人稀、游牧与农耕并举、民性剽悍的关东文化接壤。燕赵文化处于周边不同区域文化的边界带,经过战争、商旅、民族交往、移民等途径,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形成自身兼容并包、多样杂糅的区域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燕赵文化兼容开放性强。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燕赵文化兼容游牧文化的典范;平原君不拘一格招贤养士,同样表现了这种兼容性格。先秦时期慎到的早期法家思想,公孙龙的名家思想,荀子的儒家思想,都可以在赵国产生。其二,荀子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名家的名学分析,前期法家的重参验、正名实的理智主义因素,克服了孟子先验论道德理想主义的局限性,才卓然成就一家哲学,是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第一次批判综合。董仲舒以儒学为根底,吸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建立起来的今文经学体系,同样体现了燕赵思想文化的兼容性格。其三,由于兼容性强,所以燕赵学者门户之见淡漠,历史上有众多的燕赵籍学者,却很少形成影响久远的学派。即使到了宋明时期,思想文化界仅理学内部就有众多的学派,如湖南有湖湘学、濂学,河南有洛学,陕西有关学,岭南有闽学,江西有象山心学,浙江有阳明学等众多的学派,燕赵却没有自己的学派。清初形成了颜李学派,但不过数十年就消失了。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三、京畿之地的区位文化优势
自13世纪初蒙古人举鼎中原,继之立国大都(今北京),历经明、清,七百年间,燕赵河北一直是京师所在的畿辅重地,又名直隶,这种靠近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近水楼台”效应,给燕赵文化打上深刻的烙印,形成燕赵文化如下的区位优势:一是历史名胜文化蕴含深厚。今属京、津的名胜已不须说,古已有之的邯郸赵王城、古丛台,保定燕下都、满城陵山靖王汉墓等著名历史遗迹也不必说,仅就清代河北境内就有清东陵、西陵,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陵、园林,被誉为近代“将军摇篮”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遗址,全国现存唯一的保存最完整的直隶总督署,建制较早而清代鼎盛的保定莲池书院等历史名胜。这些名胜古迹,作为凝固的历史,有形的文物,承载着明清畿辅文化丰厚的内涵,诉说着明清时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民族命运的起伏,历史人物的功过。
二是戏剧艺术及早期市民意识发达。封建时代的京师,自然是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富贾缙绅、文人学子云集的理想去处,所以,一般说来,政治文化中心所在的京畿之地,在生活消费、社会见闻、文化水准以及社会矛盾对国人政治意识、文化心理的冲击上要高于“天高皇帝远”的周边地区。这是元、明、清时期戏剧艺术及早期市民意识在燕赵文化中崛起的根本原因。元代,戏剧文学有如繁花似锦,“勾栏瓦肆”遍布城乡。明清以降,随着南戏弋腔、昆腔北上,山陕梆子东进,河北出现了第二次戏剧艺术高峰。清末民初以来,祖籍在河北或活跃于河北境内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不可胜数。戏曲艺术是思想的载体和大众传播媒介,它的活跃表征着早期市民意识的崛起和封建文化内部自我批判意识的萌生。
四、慷慨悲壮的爱国情怀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元明清和近代时期,燕赵河北在推进中国历史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现代史上,慷慨悲壮的爱国主义异常高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率先在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先驱。卢沟桥事变后,河北成了抗日战争第一线。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先后创建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燕赵河北的抗日爱国运动如火如荼。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延安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东北干部队铁流社、抗大二分校文工团、一二○师战斗剧社等涌入河北,抗战文艺的空前高涨,极大地鼓舞了燕赵儿女的抗日救国热情。解放战争后期,河北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战斗征程中,燕赵儿女再次演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谱写了爱国主义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