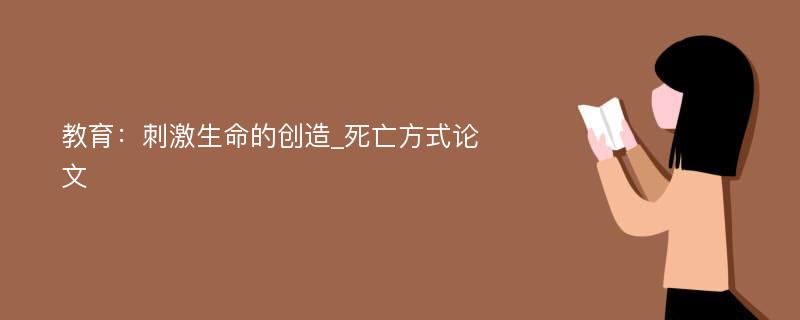
教育:激发生命创造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义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认识上的,一是价值上的。当我们在认识的意义上使用“意义”一词时,我们是在寻求某种解释,是要阐明某种事情或某个事件;另一方面,我们使用“意义”一词时,往往也体现出我们所怀抱与追求的价值理想。生命的意义当然离不开解释和说明,但生命的意义主要不是解释和说明所能建构的,生命的意义需要创造,是我们永不停歇的价值追求。
一、生命:需要意义
尼采说,“人是有病的动物”,因为他要不停地追问生命意义。弗洛伊德和弗洛姆也持相同的观点。或许我们会说这是哲人的自以为是,普通人并没有这样的“疾病和烦恼”。确实,一个人可以相当持久地将意义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埋头于眼前的蝇头小利,陷于维持生理需要和物质享受之中,或者热衷于权力的勾心斗角之中。但是,死亡是人不可逃避的宿命,总是在有意无意间提醒着人们:你的生命是否值得、是否有意义。
意义问题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人总是不断地追寻存在与生命的意义,渴望实现自身的价值。动物,只要生理需要满足就能“生活”得很好,人与动物相比有太多的“毛病”:不仅要满足生存需要,还要满足精神或意义需要;不仅要适应环境和自身的现实,还要超越环境和自身的现实。当萨特讨论自我时,他把自我说成是“永远被追求却永远达不到的东西”。我们可以把人的这种特性称为人的“未完成性”:人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成人”,他的生存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人性不是抽象的,人的这种“未完成性”同样也不是抽象的,体现在人的生活之中。换句话说,人不仅拥有现实生活,而且拥有可能生活。所谓可能生活是人根据自己选定的价值理想在精神中建构的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产生于现实生活之中,又为现实生活提供了目的和意义参照。现实生活永远是未完成的生活,对可能生活的追求同样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正是在这无尽的追求和创造中,生命才获得了意义。
生命的意义建构在一定意义上,起源于人的有限感和死亡意识。正是意识到生命总会终结,我们才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是弥足珍贵的。假如人类真能长生不老,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许多人会因此失去生活的目标,失去应有的创造力,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活着。死亡意味着人是有限的存在,然而正是由这有限性,人们才渴望无限和永恒;正是因为死亡毁灭人的创造性,人们才创造各种文化成果以超越这种毁灭。
人在生活中时常会陷入现实的琐碎而忘却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但他人(尤其是亲人和熟人)的死亡和人生后半期肌体的变化会使人惊醒。既然死亡是人不可避免的未来,那么,活着或者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不解决,自我显然难以达到心灵的真正宁静与安然。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所以,死亡使我们能够通过创造和表现价值而克服死亡,这些价值不仅显示了生命的意义,而且推动我们进入更新的生存状态。我们在世界上固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我们建构的价值和文化成就却不会消失。通过这种创造活动,我们得以超越死亡:尽管我已死亡,但我所创造的价值仍然生机勃勃!
二、意义:不是“发现”而是“创造”
我们以往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方式是“发现式”的,似乎在生活之中或生活之外存在着静态、客观的意义等着我们去发现。在人类的思想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认为存在一个终极的存在和至高的善,而这终极的存在和至高的善为生命提供了意义。宗教更是明确地表明上帝或其它超验的存在,人的生命意义则是由这些超验赋予的。这种依赖外在的存在为自己的生命涂上“意义的色彩”也许是可行的,但终究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有人戏言,上帝创造人之后,它的任务就完成了,因为它赋予人的特性就是创造性,如果人的生活意义还要靠上帝来赋予,那上帝一定会很后悔:还创造人干什么?
这种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方式,即把意义当作生活外之可以找到的某种存在物,已经被人类精神和社会发展史证明不是好的提问方式。应该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是如何创造意义的?在新的提问方式下,生命的意义首先源于对生命的惊奇。如果我们对生命感到惊奇,我们就会感觉到生命的重要性,感觉到生命的可贵,就有保护生命,使之通过生活得到充实与完善的意愿,意义的创造由此展开。
对生命的惊奇只是意义创造的“初始阶段”。对生命的珍视态度产生了进一步的意义创造: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不懈努力。不同的人,需要和愿望不同,行为目标也不同,生命和生活的意义自然就不同。所以意义的创造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需要一个中介——理想。人的需要和愿望是多种多样的,但人总是从中选择一种最具有价值意义的作为他的理想,而理想赋予生存以意义,人的生存意义只能寓于为实现理想的自主与自觉努力之中。确立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人的生活意义化的过程。
不能在生活之外“发现”一个最高实体作为生命意义的最终根据。生命的意义不是“发现”的,而是人在生活中创造的。但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意义仅仅是人主观的创造吗?应该承认,没有一个统一的意义模式,每个人建构意义的方式和内容都是不同的。但不能由此而走向绝对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将意义的创造仅仅看成单个人的事情。生命具有主体间性,人的意义建构和创造也不能脱开这一基本生存境遇,人在意义创造的过程也是与他人、群体、类进行交往与对话的过程。以人类作为自身生命意义建构的背景和基础则是生命意义创造的最高境界。历史上有很多人在自我意识没有上升到类意识的情况下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也因此而灿烂;也有一些人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文化视界,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自觉自为地肩负起人类发展的责任,这些人的生命和生活也因此而辉煌。
三、教育:激发生命创造意义
生命需要意义,而意义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创造。从生命及其意义创造的角度审视教育,我们会发现教育的一个庄严使命:教育作为人类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可以在生命和意义创造之间架起一个桥梁,激发、助推生命的意义创造。根据生命创造意义的基本原理,教育可以从几个方面激发生命的意义创造。首先是呵护生命,使学生感受到生命的惊奇;其次是认识生命的有限性,增强生命意义创造的紧迫感;第三是激发生命的道德挺立;最后是促进生命走向卓越,在生命的完善中实现意义创造。
呵护生命是激发生命创造意义的前提。意义创造是生命的使命,没有生命,或者说生命的生长遇到了阻碍,生命的意义创造必然会受到干扰。所以呵护生命对于激发生命的创造意义至关重要。呵护生命意味着教育不能体罚、虐待生命,不能让生命工具化。教育是为生命服务的,是对生命的一种“特殊关怀”,为的是使生命发出光彩。如果教育背离了这一基本价值,体罚、虐待生命,就会在折损生命的同时使自己失去合法性,失去生命依据。生命是完整的,身体、心理、精神(道德)是一体的,对生命的呵护理所当然地包括对受教育者心理和精神的呵护。对身体的体罚、虐待要不得,心理虐待和精神折磨同样要不得。事实上,对生命的体罚与虐待往往既是身体的,又是心理和精神的。当然,呵护生命不是对生命的放任,内在地包含着对生命的约束。“呵护”中的“护”除了保护的含义之外,还有建立“围栏”约束之意味。辩证地看,合理的约束就是保护。比如,一个孩子要做危险的动作,父母不让他做,表面上看是约束,实际上却是保护。
教育对生命的呵护还可以帮助学生感受生命的惊奇,学会珍爱生命。学生珍爱生命的观念和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生自身的感悟,一是教育的引发。有效的教育引发应该是教育者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方式。如果珍爱生命只是一种口号,而实际的运作则缺乏生命关怀,这对学生无疑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学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漠视生命的意识和态度;如果教育本身是呵护生命的,视教育为关怀生命的一种特殊方式,这对学生则是另外一种强烈的暗示和明示,能够强有力地孕育学生珍爱生命的品质。
生命的意义创造与生命的有限性密切相关,正是生命的有限性激发了人们努力在短暂的生命周期中活得有意义。但作为受教育者主体的青少年,处在生命周期的开端,有大把的青春资本,往往无法体会生命的有限性。在加强身体锻炼的人群中,中老年人的比例之所以明显高于青少年,就是因为中老年人对生命的有限性有深切的体会,而青少年因为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往往没有生命的紧迫感。这一“自然现实”,正是教育大有可为之处。教育通过提醒青少年认识生命的有限性,就可激发青少年珍惜生命、增强生命意义创造的紧迫感。
基于促进学生认识生命有限性的需要,死亡教育应该成为教育不能回避的话题。我们以往的教育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死亡,以为灰暗的死亡会为阳光的儿童心灵蒙上阴影。但死亡是生命无法摆脱的宿命,也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为生命服务,让生命焕发光彩的教育实际上根本无法完全回避死亡。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往往从他人的死亡开始的,他人的死亡往往会激发人对生命产生惊叹,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短暂。因此,死亡教育可以从认识、体会他人的死亡开始,进而体会自己生命的有限,激发生命意义创造的紧迫感。
道德挺立是建构生命意义的方式之一。英国社会学者鲍曼认为用于个体的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意义建构方式,即在“后世人的记忆中得以永存的种种机会”是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专用的“桥梁”。其实也不尽然,社会大众虽然并不拥有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那样多的机会以在后世的记忆中得到永存,但每一个人都拥有道德挺立的机会和可能,通过道德挺立,普通人也可以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更大的意义。即使一个目不识丁的村民,如果其道德足够高尚,他同样可以在其生活圈中获得人们恒久的景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先贤,如孔子、屈原、司马迁等,之所以得到人们永久的景仰,与其说是因为其学术上的造诣和思想上的贡献,倒不如说是因为其人格的崇高。个人的道德挺立之所以能赋予生命以意义,在于其将自己的生命和人格与人类文化融为一体,实现了人性的深度内涵,从而完成了自我实现并超越了个体短暂而“弱小”的生命存在。人是伦理性的存在,这是人逃避不了的选择,也是人主动、自主的选择。道德挺立是对人作为伦理存在的深度开掘,触及到了存在的内核。虽然“道德天才”不能代替大多数人的德性水平,但真正的道德挺立和人格的崇高由于是以存在的本质为依托而实现的生命境界的升华,就是从他人的角度看,也具有巨大的理想激励作用。
因此,激发学生追求道德理想,是激发其创造生命意义的方式之一。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到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应真正体现教育的道德性,真正将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精神追求。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价值取向的调整。如今的教育,功利的取向过于浓重,家长、学校、社会都在宣扬一种片面的成功观,似乎不做大事,不成名成家,就是没有出息,人生就没有意义。这种功利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取向对受教育者具有巨大的误导作用。实际上,教育的正确价值取向应该是,不强求每个人都成名成家,而是引导每个人都有扎扎实实做一个普通人的情怀。要让学生明白,做一个普通人,只要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同样可以从另一条路径上实现生命的卓越,同样可以使生命富有意义,这应该是教育恒久的价值追求。
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但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完满应该是人最根本的需要。人永远都是“未完成的”,永远都在追求卓越的途中。刚出生的婴儿,异常脆弱,要到一岁之后才能掌握作为人最基本的技能——行走和说话,属于“生理性早产”,与动物相比,各方面都处在未定状态。正是这种未定状态,使人的发展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注定了人一生都处在发展之路上。生命是渺小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但生命的发展却是无限的,走向生命卓越的路途也是无限的。使有限的生命逼近卓越,焕发出无限的光彩,生命的意义也就创造出来了。
教育是生命走向卓越的通渠。或者说,教育可以帮助生命克服有限,接近生命的极限,达至生命的顶峰。第一,生命走向卓越,不能从零开始,只能从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出发。教育可以帮助生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饱览人类文化的精髓,为生命走向卓越奠定一个文化的高起点。第二,生命的潜能有时候会被生活、制度、社会惯性所压抑,需要教育的激发。教育在给生命以文化支持的同时,也要帮助擦拭环境给生命蒙上的尘埃,让生命焕发活力,使生命的最大潜能得以爆发。第三,在生命走向卓越的过程中,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诱惑,抵挡不了,就会误入歧途。所以教育还要给生命以价值引导,使其不至于因歧路而迷失方向。教育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就能在激发生命走向卓越的同时,激发生命创造意义的活力。
标签:死亡方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