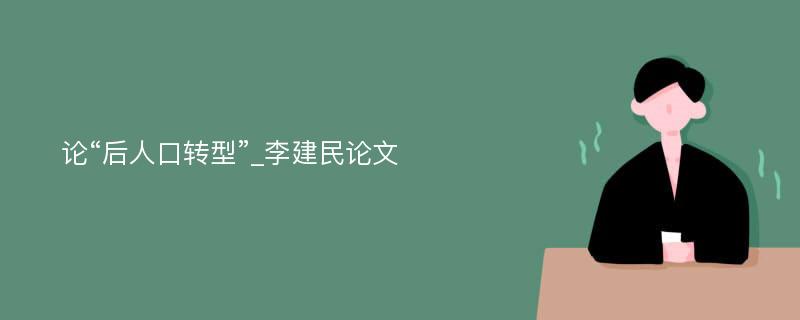
关于“后人口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以Adolphe Landry 1909年发表的“人口的三种主要理论”作为人口转变思想首次提出的话,那么,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口学界围绕着“后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做人口转变作为一种理论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活力的表征。尽管学者们在“后人口转变”问题上歧见显然,似乎很难调和,但笔者以为,这样的讨论对于人口理论的发展,对于更深入地认识和探讨中国现实的人口问题是颇有裨益的。所以,作为“后人口转变”概念的提出者和使用者之一,笔者乐于参与讨论,献己一孔之见。
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
在国际学术界,“后人口转变”(the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有的简写为P-DT的)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尚不清楚,但至迟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被使用。Jerome H.Barkow and Nancy Burley 1980年发表在《动物行动学和生物社会学》第1期上的“进化生物学、生育和人口转变”一文中就使用了“后人口转变社会”一词。Rechard Leete 1987年发表在《Population Studise》上的“东亚和东南亚的后人口转变:与欧洲的异同”一文中,甚至专门讨论了“后人口转变”问题。在他看来,在一个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并持续一段时间后,就可看做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归为进入“后人口转变”的国家进行讨论。之后,使用这一概念的论文时有所见,不少学者还把Leete的论文列为重要文献加以引用(包括他本人后来发表的论文)(Leete,1994)。在2000年的PAA会议上,还专门列有“后人口转变”问题的专题讨论(即在3月24日下午举行的第92专题:“后人口转变的挑战:对全球经济的含义”)。可以说,在国际学术界,“后人口转变”作为一个术语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并开始成为人口转变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当然,在作为概念使用时,在术语上也有一些差异,除了“后人口转变社会”、“后人口转变时期”外,还有“后人口转变阶段”(Wertheimer-Baletic,1990;Leete,1987、1994)、“后人口转变国家”(Anzo,1985)和“后人口转变时代”(Pulaska-Turyna,1991),甚至还有“后转变生育趋势”(Dissanayake,1996;Demeny,1997;Katus,1997)、“后转变人口发展”等。大抵而言,学者们一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后人口转变”概念,一是相对于“前人口转变”(Pre-demographic Transition)而提出的“后人口转变”,大多用于分析欧美国家的人口转变新阶段,即人口转变过程完成后的阶段,同时使用的还有“第二次人口转变”概念(Zakharov,Ivanova,1991);二是相对于传统的人口转变过程而提出的“后人口转变”,大多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口转变趋势。
在国内,应用人口转变理论来分析中国的人口问题并非近年来的事情。早在80年代初,人口学研究刚刚复兴时,许多人口学家就开始用人口转变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80年代后期,笔者试图应用人口转变理论的阶段模式来分析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结果发现,中国的人口转变历程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而且也有别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50年代前期的人口转变具有经验模式的早期扩张特征,而此后一直到70年代初,则和发展中国家相似,是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形成的高速人口增长阶段。70年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类似于后期扩张阶段,但下降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未见,原因也不是经验模式中的自然转变原因,而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更为独特的是,当中国的出生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不是继续趋于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两次波动。由于这一阶段为中国人口转变过程所独有,笔者称其为“缓冲阶段”。
然而,这一“缓冲阶段”,到80年代末似乎就结束了,出生率持续下降,整个90年代都处于这种下降之中,人口增长率越来越低,人口转变似乎已经进入完成阶段。特别是在上海、苏南等较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地区,相继进入了负增长状态。譬如,在苏南地区,按照通常的人口转变标准衡量,早在70年代初就已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之后,主要是在很低的出生率水平上波动,并伴有人口负增长出现。这种状态有别于欧洲国家的经验模式,也不符合Black的减退阶段特征。为了形容这种人口转变状态,笔者使用了“后人口转变时期”这一概念(注:之所以称其为“后人口转变时期”,按照当时的论述,原因有三:“一则苏南人口虽然在70年代初即已完成转变,但并非像发达国家所曾经走过的道路那样出现停滞或波动,而是继续下降,直至80年代由于年龄结构作用才开始波动,这种继续转变的特征是独特的,不能用‘减退’等特征来形容;二则苏南人口转变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完成转变后顺其自然,而是继续施行人口控制,使其出生率下降至更低水平,以实现人口控制目标,这一特征也是独特的;三则苏南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化态势也与发达国家不同,在出生率降至苏南80年代初的水平时,发达国家已经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其原因在于有和出生率相同或更高的死亡率,而苏南人口死亡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所以,虽然出生率低,但人口增长仍较快,至于个别年份的负增长,也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在稳定的年龄结构下形成的,而是畸形的年龄结构周期惯性使然。这一特征无疑也是独特的。综上三点,笔者以为,用‘后人口转变时期’来描述70年代以来苏南人口转变是合适的。”(朱国宏,1992))。
1993年上海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引起了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了关于人口负增长和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的讨论,进而引出对人口转变理论的重新思考。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
跨世纪之际,人口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开始回顾和检讨20世纪的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研究(于学军、解振明,2000)。在这种情势下,对现阶段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及未来走向的关注很自然地摆上了议事日程。于学军和李建民关于“后人口转变”观点的形成与80年代以来的人口转变研究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二、“后人口转变”概念的意蕴辨析
于学军和李建民论文的观点是判定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已经完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可称之为“后人口转变时期”。对于这一论点来说,可引起争议的有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人口转变过程是否已经完成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是这一个新的阶段是否可以命名为“后人口转变时期”?三是“后人口转变”是否可构成人口转变理论的一种新理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于学军和李建民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其论文的主旨就是要论证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已经完成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论证其观点,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包括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中国人口转变的各项指标和各项指标的社会经济含义及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等等。在笔者看来,这种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学术探讨。然而,唯其是一种探讨,其结论也并非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恰恰相反,在诸多问题上,尚需更多的经验证据来支撑,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说,叶明德和李建新的“质疑”,与其说是否定于学军、李建民的观点,毋宁说是修正或补充他们的证据。尽管他们在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和是否可称之为“后人口转变”问题上持有异议。
事实上,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认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人口学界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人口转变问题的方方面面,就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问题而言,既有判定为完成的,也有判定为没有完成的。其分歧既有判断标准方面的又有认识角度方面的。在判断标准上,既涉及衡量指标问题,又涉及量化标准问题。关于前者,正如叶明德(2001)所指出,于学军的论文中只给出生育率指标和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指标是不够的,李建民(2000)用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指标代替死亡率指标似乎也可以商榷。这其实是关于衡量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指标体系问题。应当承认,迄今为止尚未有专门探讨这种指标体系的。至于量化标准,目前是各取所需,均缺乏充分的理由。叶明德批评李建民(2000)所给出的四个指标的数值,同时又以北欧和西欧国家1982年的数据作为标准,这似乎并不能证明李建民论文的错误,因为北欧和西欧国家并不是1982年才完成人口转变的,以此作为完成人口转变的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过,在人口转变标志上确实也还没有公认的统一标准,原因有二:一是各人对人口转变的认识不同,给出的标准也不同;二是人口转变涉及多个指标,而指标值的变化在不同国家里并不一致(典型的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急剧下降,而出生率却几乎不变,用死亡率指标衡量,发展中国家很早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而用出生率指标衡量,至今尚未完成),所以很难给出统一的标准。又由于没有一个综合指数可供衡量,在衡量指标上各取所需也就不可避免。笔者(1992)在探讨中国人口转变问题时为衡量标准问题所困扰,最后是引用Ansley J Coale在模型生命表中使用的人口转变不同阶段的出生率、死亡率数据,并以此来判断中国的人口转变阶段。
在认识角度上,差异更为明显。这种差异在于,是就人口转变论人口转变,还是联系社会经济因素来讨论人口转变。若是前者,虽然相对简单,但由于前述的衡量标准问题,仍然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而后者,正如李建新(2000)所指出,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人口转变,那么,结论可能会大不一样。在他看来,“中国人口转变充其量在统计指标上,在表现形式上进入所谓‘后人口转变’时期,而本质上、内容上还处在人口转变之中,还处在人口与‘发展’变量之间的关系转变之中”。笔者认为,将社会经济因素引入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不在于它是否构成对“后人口转变”的否定,而在于它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此前的许多学者已经揭示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诸多特殊性,如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其现代化过程、中国的人口转变主要依赖于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间有波动等。这种特殊性意味着,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因而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来规范中国的人口转变历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国是否完成了人口转变完全可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判断,这种判断既可以是依据人口转变本身的指标体系,也可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来作出,因而人口转变既可以是形式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指标变化,又可以是人口研究意义上的“彻底转变”。
所以,笔者以为,依据人口指标来做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的判断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实际上此前已有多人根据这些指标得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的结论。问题在于,做出这一判断的目的何在,如果是为了探讨中国人口转变的趋势及其意义,无疑有助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相反,如果由此引申到政策层面,据此断定中国人口控制任务已经完成,那么,确实存在叶明德所指出的“误导”可能。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已经完成,那么完成后的人口转变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可如于学军和李建民那样称其为“后人口转变时期”?这里涉及的问题首先是,人口转变完成后进入的是什么时期?什么是“后人口转变”?
从人口转变过程本身来说,完成人口转变后的阶段就是“转变后阶段”。正如Ansley J Coale的“三阶段论”所描述的,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分别是“转变前阶段”、“转变阶段”和“转变后阶段”。如果用“转变后阶段”来形容中国完成人口转变后的人口转变状态,似乎不容易引起误解。
那么,于学军和李建民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是否指“转变后阶段”呢?笔者以为是。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过程已经完成,现在进入了“转变后阶段”,而这一阶段具有一些与前一阶段不同的特征。如果说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话,那么无非是提醒人们关注这些新的特征。
用“后人口转变时期”来描述中国目前的人口转变状态,在笔者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事实上,Rechard Leete早在80年代就这样描述东亚和东南亚的人口转变状态。中国的人口转变与东亚和东南亚的人口转变有相似之处,东亚和东南亚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自然也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当然,如果用“转变后阶段”来理解这种“后人口转变”,那么,应当注意中国的“转变后阶段”和欧洲国家的不同,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实际上,Rechard Leete(1987)正是为了探讨东亚和东南亚的人口转变与欧洲的异同。在笔者看来,使用“后人口转变时期”来描述目前的中国人口转变状态并无不妥,倒是在使用“第二次人口转变”概念时要小心,因为它有特定的含义。
关于第三个问题,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分析和探讨是否能够构成“后人口转变理论”?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人口转变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由其发展史可知,人口转变理论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正是这种发展使得其具有足够的理论张力和解释力来理解不断变化的人口转变事实。如果说人口转变思想最早是由Adolphe Landry于1909年提出的话,那么,他只是在时间序列的意义上对人口转变过程进行描述。1929年Warren Thompson将其应用于划分地区类型,可以看做人口转变思想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Frank W.Notestein又将其应用于分析刚刚开始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历程,再次发展了人口转变思想,使之成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人口理论。此后,关于人口转变理论的修正和补充一直没有间断过。1947年C P Black在Frank W.Notestein三阶段论的基础上发展为五阶段论,Kingsley Davis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转变各个阶段的特征,Harvey Leibenstein结合经济增长过程来分析人口转变的各个阶段,AnsleyCoale和Edgar M Hoove、C P Kindleberger和B Herrick、J C Caldwell、REasterlin也分别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侧面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补充。一直到1997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人口联盟的大会上,时任联盟主席的J C Caldwell还在呼吁建立大一统的人口转变理论。可以说,人口学家一直在致力于发展人口转变理论,而这也正是理论的魅力所在。
从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史也可以看到,人口转变理论最初形成于形式人口学的范围之内,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入,逐渐将社会经济因素纳入人口转变理论的框架之中。而分析的问题也不再限于人口转变的阶段划分及其各种指标,也包括与人口转变过程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建新批评李建民的论文只关注形式人口学的指标而不顾其他因素,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以形式人口学各个侧面的研究现状来否定李建民在这方面提出的问题,似乎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二者并不矛盾,而且很多理论正是建立在各个领域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问题恐怕在于,李建民是要发展人口转变理论还是建立“后人口转变理论”?如果是前者,“后人口转变论”一文的做法无可厚非,尽管李建新称他所指出的是人口转变理论的“界限”而不是局限,所发展的也是早已有之的研究成果。如果是后者,或许应当更多地考虑新理论建立的基础。
按照笔者的理解,李建民的论文并非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理论,而是针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局限”而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人口转变理论。因为,“后人口转变论”一文是从分析人口转变理论的“局限”开始的,而关于“后人口转变”的种种分析也只是为了说明传统视角的拘囿,因而关于“后人口转变”研究的新发现也就可以补充人口转变理论的不足。这其实是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而做出的修正或补充人口转变理论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并非自李建民而始,事实上,在人口转变领域,中国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努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情况确实有许多特殊之处,非现成的理论所能规范,而通过对中国现实的深入研究,完全可能为国际人口学界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点,已为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在人口转变领域,同样有着许多学者的努力,而且有的学者试图为人口转变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譬如,邬沧萍和穆光宗(1995)就明确提出“补充和发展”人口转变理论。因此,李建民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试图对人口转变理论做出贡献。
至于“后人口转变论”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理论,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因为,要建构一种理论,恐怕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别是,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不久,许多新的特征不过是初露端倪,很多假设也需要假以时日来验证。通过现在这种讨论或许有助于最终形成一种建立于中国人口转变经验历程基础上的人口转变理论。
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人口转变问题上见仁见智的问题着实不少,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也很多。笔者以为,可以通过这次围绕“后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探讨中国人口转变上的诸多相关问题。
其一,人口转变概念的界定问题。人口转变在概念上似乎是很清楚的,指的是伴随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动的人口变迁过程。但是,从这次讨论来看,人口转变概念似乎还有界定的必要,因为,要讨论“后人口转变”首先必须明确“人口转变”,而人口转变究竟是纯粹形式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变化,还是人口研究意义上的人口变化?如果不加界定,就很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
第二,衡量人口转变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问题。衡量人口转变的指标似乎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出生率指标和死亡率指标,但是,现在看来,也有必要重新加以讨论。根据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化而有人口转变的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和五阶段论,其区别就在于依据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对变化的时间和幅度,而处于相似阶段的不同国家,其人口转变的内涵是有区别的,不同原因引起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其意义也是不同的。因而,需要讨论衡量人口转变的指标体系。相应地,也需要建立具有合理性和可比性的评价标准。
其三,人口转变阶段的划分问题。如果仅仅用经验模式来规范,是很容易划分人口转变阶段的,问题在于,在实证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时,究竟应当怎样判断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阶段的开始和结束如何判定,阶段与阶段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很难在判断目前的人口转变状态上达成一致的看法。
其四,对中国目前人口转变状态的认识。从这次关于“后人口转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主要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将目前的人口转变状态称为“后人口转变时期”(尽管这也仍有争议),而在于对中国目前的人口转变状态如何认识,而这种认识其实也涉及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判断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所以,对中国目前人口转变状态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中国人口的现状和趋势的认识,而这应该是人口学界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