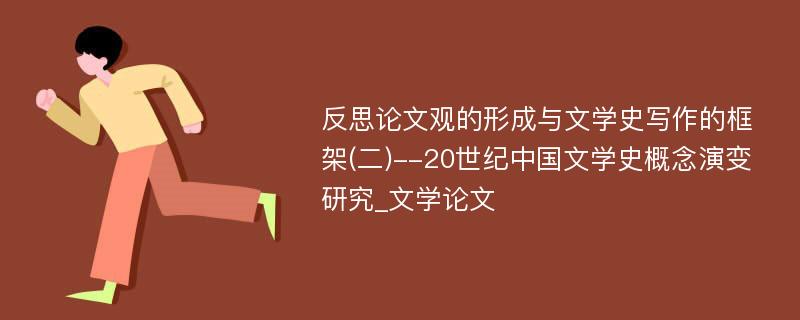
反映论文学观的形成和文学史写作的框架(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念演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反映论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十年代的反映论文学观体现在文学史的撰写上,最为彻底最为突出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学生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这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后,于一九五九年再次修订出版(修订本的字数由七十多万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万,内容上大大扩充,并删除一些过于剑拔弩张的批判言辞,如对林庚、陈子展粗暴的、激烈的批判)。① 尽管这是年轻学子的集体著述,却基本奠定了日后一大批中国文学史的基调。无论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由余冠英等主持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一九六二年),还是游国恩等主持编撰的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一九六三年),或者是其他高校陆续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站在文学反映论的立场,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史撰述和文学作品阐释的指导性纲领。例如上述两部著作,在编写说明中都强调“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观点来探究我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这里就是以反映论和阶级论方法来阐释文学发展过程和林林总总的文学作品。游国恩还在编写说明中称,按照北大一九五五级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分为九个时期,并在第一编的概论中写道: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阶级而存在。但上古时代的社会还未分裂为两个对抗阶级,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到了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一切文学艺术就不可能不打下阶级的烙印,同时也揭开了两种文化斗争的序幕。② 这里,与其说是在强调阶级论的反映论,不如说是为第一章“上古文学”中没有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神话作一个说明。按正常的逻辑和学理讲,这是无须申明的,但是游国恩等的谨慎,表明了阶级论的反映论是必须时时得到贯彻的最高原则,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虽然没有类似的申明,但是在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起源”中既强调了原始社会文学和艺术起源于劳动,又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③的说法以保证政治正确。 “艺术起源于劳动”有如反映论中的阶级论,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了人的相关理论,也不仅仅是因为恩格斯的被人们反复引用的那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各段论据,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中没有地址的信和苏联的相关教科书的种种论述,也因为原始社会的劳动和日后阶级社会的劳动阶级相联系。如果说艺术起源于巫术、艺术起源于游戏、艺术起源于娱乐,起源于模仿或者起源于其他,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艺术起源于劳动就更加神圣,更加崇高(必须说明,一度“艺术起源于游戏”或起源于其他活动的理论和假说,曾受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对艺术起源的歪曲,“他们的目的是在为其‘艺术无目的’论、‘为艺术而艺术’论寻找客观根据,以便麻痹人民,使艺术更好地为剥削阶级统治服务”)。④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建立在活的劳动时间上的,不是建立在沉淀于资本的、过去的死劳动上的,只有活劳动才创造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比起其他的社会实践更有活力,更有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因此,相同的观点在游国恩主编的文学史中表达的更加直接,在游本第一章“上古文学”中,开篇第一句就是“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 既然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那么将原始的文学艺术看成原始人生产和劳动生活的反映,也就顺理成章,因此,无论是《吕氏春秋·古乐》中的“葛天氏之乐”,还是《吴越春秋》中的“弹歌”均可以看成是农耕生活或渔猎生活的某种写照,故游本写道:“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是一种生产行为的重演,或者说是劳动过程的回忆,也可以说是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⑤这里连续用了“生产行为”、“劳动过程”、“生产意识”等概念,最后才勉强加上“生活欲望”,确立了先生产劳动,后生活的次序,可见,没有生产劳动的生活和“生活欲望”是十分可疑的。可以说“艺术起源于劳动”不单单是本质论艺术观的一种表达,也是阶级论反映论的上推和逻辑延伸。因此关于“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阐述,似乎成为反映论文学观的最初的出发点。 辨别一本中国文学史是出版什么年代,只要翻开第一章,看看其关于艺术起源的说法,就大致可判定其出版的年代。如词学家詹安泰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中国文学的起源》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劳动创造文学”,作者写道:“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整部过程,都是劳动创造的过程。没有劳动的作用,直立人类的形成就是一个大迷……文学,不但最低级的雏形是来自生产劳动,它最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原则上也和生产劳动部门具有某些一致性。”⑥并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相关论述来加以阐释。我们在这本二○一一年新版的文学史中,不难找到作者最初的撰写年代(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和出版年份(一九五七)。 再往前,就没有这类斩钉截铁地劳动起源说的说法。如在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有“名与字之起源”、“诗之起源”、“散文之起源”,这里的“起原”是最初的出现的意思。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第一讲“中国文学的起源”,也是指文学最初的出现。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文字的起源”,文学的起源就略过了。柳存仁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上古秦汉文学史》有“中国文学之起源”,不过也是由文字的起源说起,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尚书》。并不探求文学发生的背后的动因。 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要特殊一些,观点明确,即文学起源于情感:“因为人生不能无情感,有感于中,即发泄于外。”他的例证是班固和朱熹。班固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朱熹说“有欲则不能无思,有思则不能无言,言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影响节奏,而不能已。”⑦这涉及文学起源的心理学动因。 这里,又要以刘大杰为例,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订情形比较微妙,也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其一九四三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在谈及文学的起源时,先说道:“文学的创始,无论谁都知道是歌谣,但歌谣最初的形式,是同音乐、跳舞混合在一起,不容易分开。虫鸣鸟语,可以说是音乐,也可以说是歌谣,渐渐的进化,较为完备的乐器与文字出以后,于是音乐与诗歌才分为独立的艺术,由于跳舞而演化为戏曲。”然后才谈及艺术起源于劳动,口气似不够坚定,他认为:“艺术的起源,前人多主张起源于游戏,近来许多新兴学者的研究,则主张起源于劳动。普列汗诺夫在《原始民族的艺术》内,费了很长的篇幅,说明劳动先于游戏,实用的生产先于艺术。”⑧一九五七年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章也谈到同样的意思,但是次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行文中首先谈艺术的起源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然后才进入到文学的创始及与歌谣的关系。⑨到一九六二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干脆将原先的章节改换扩充,作重新安排,将“文学的起源”单列为第一节,亦即整部文学史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艺术起源于劳动;它最初的内容和形式,都决定于劳动生产的实践。”⑩至于普列汉诺夫的主张或其他的相关观点,如“艺术起源于游戏”什么的,一概删去,以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无须论证,也不必介绍有关的各种争议。 在中国文学史的写法上,能够体现反映论文学观的最显明的特征,莫过于每一个时段前都有“概说”或“概论”的文字,这不仅是某种写法或文体特征,也是将反映论文学观贯彻到文学史中的一个必要步骤。 起先,笔者并不注意这“概论”或“概说”一小节文字的特殊功能,只是将它看作是进入具体的文学史叙述的一个入口,一种铺垫。即在论述具体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前,总要谈谈大的社会背景和相关缘由。然而,当翻开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诸多文学史,发现情形并不如此,无论是林传甲、黄人的,还是谢无量的文学史,无论是胡适的还是郑振铎的文学史,或者是傅斯年、游国恩早年的古代文学史讲义,刘大白的或刘经庵的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的文学史,或者是由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杨荫深、吴梅、柯敦伯、宋云彬、张宗祥等八位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大文学史》,再或者被朱自清所称道的刘大杰的或林庚的文学史,均没有这种概说或概论的文字。 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例,分上中下三卷,有总的绪论,另外在每一时段前均有鸟瞰式论述,即“古代文学鸟瞰”、“中世文学鸟瞰”、“近代文学鸟瞰”,为总体描述。上述由八位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大文学史》在每一时段前也均有绪论,就该时段的文学概况作背景交代。但是这些文学史没有日后的中国文学史这一类“概说”式文字,因为由北京大学文学系五五级学生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所开创,由游国恩等学者定型的这一类概说或概论,最最关键之处是要强调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赖和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有没有这类概说或概论,是反映论文学观能否得到运用和贯彻的一个表征。 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为例:四册共九编,每一编的第一章是概论,而所有九编的概论均整齐划一分为两个部分,一为社会概况,二为文学概况。而所有的“社会概况”均须对该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概括的交代。只有在这一交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深入下去,谈论文学的概况。如在先秦文学的“社会概况”和“文学概况”中,以下这样的文字就比较典型,有代表性。先看先秦文学之“社会概况”: 由于大量奴隶劳动力的使用,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特别是春秋初年铁器广泛的运用于农业生产,使得奴隶主不仅可以经营天子诸侯所赐予的公田,而且还可以开发大量无主的荒地。这就成了他们的私田,这些私田不属于国家,因此也没有贡纳的义务。这样,由于“私田”的大量发展,就必然导致国家所有制的崩溃。我们再从奴隶生产来看,也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业的个体经营成为可能,并且逐渐地形成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经济,这样就为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11) 接着是对先秦文学之“文学概况”的描述: 西周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长,周厉王行苛政,人民还因此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暴动。统治阶级慑于人民的力量,为了“观风俗,知得失”,收集了一些当时的民间的“里巷歌谣之作”,这就是《诗经》的精华——《国风》和《小雅》中的一些作品。(12) 这里,“社会概况”就是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阶级之间的对立程度。而“文学概况”则是描述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文学的总体状态和风貌,并指出后者是怎样来反映前者的。而在这中间,能够反映人民的疾苦文学,则是最有价值的文学。 这种“社会概况”和“文学概况”两分的写法,是中国史中反映论文学观的典型表述方法,足足影响了文学史撰写近半个世纪。 尽管,在而后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其他的一些文学史中,虽然有关“概说”或“概论”不再机械地划分为社会的和文学的两部分,但是其基本精神却保留了下来,即无论研究哪个时代的文学,必得先了解该时代的经济、政治、阶级和生产力的总体状况,最后才能够谈及文学。以游本《中国文学史》为例,他在各编的第一章之前,均有近万字的概说,将该时期内的有关经济、政治和阶级冲突,以及思想和文学状况作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描述。以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概说为例,有如下表述,我们耳熟能详: 东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黄巾大起义,给东汉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起义虽被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东汉帝国也已名存实亡。从献帝初平元年(一九○)开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张了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混战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13) 以上可以看成是该时期的社会总体概况,接下来的一大段,就相当于“文学概况”: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建安文学有了崭新的面貌。建安文学以魏国为主。吴、蜀很少作家与创作。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徕文士,围绕着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倾向于曹操的缓和阶级矛盾以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的政策,思想上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又都曾卷入汉末动乱的漩涡,接触了较广泛的社会现实,因此能够直接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14) 应该说,以上段落的表述内容和句式,曾是中国文学史一种最有代表性的表达文字。笔者年轻时,读这类文学史教材,几乎总是匆匆跳过前面的“概说”或“概论”,直接进入到文学史的具体阐述之中,但是即便如此,看到上述文字仍感相当熟悉,因为这种由经济而政治而阶级斗争,最后才进入文学的阐释路径,基本是一种思维模式,出现在不同的教材、著述和文章中,亦即无论在文学史,或者在有关具体作品或文学现象的解析中,都是这一套路,这几乎浸淫到一代人的脑髓之中。在五十年代之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教材中,在每一个时期的文学之前,基本都有这么一个概说或概论,而所有的概说或概论是同一话语体系的不同表述。而所谓的不同表述,只是言辞表述方面的差别,没有大的思想观点方面的不同,谨笔者手头掌握的材料来看,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马积高、黄均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有郭兴良、周建忠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15)…… 当然,就体例而言,也有例外,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没有这类“概说”或“概论”,但是,编撰者们会把相同的内容移到相关篇章的第一节,如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篇内,各个时期的第一节有如下名目:“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魏末和晋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南朝的社会、政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北朝的社会、政治与文学”等。 在明代文学篇内,介绍每一个时期的第一节分别是“明初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成化至隆庆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万历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明末“社会动乱对文学发生的影响”等等,有关清代文学的各章,也基本作如此安排,这里能看到每一位编撰者在相同的话语逻辑中,大同小异的文字表述。 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九十年代后,一些文学史编撰者已经突破反映论文学观,以审美本质或情感本质文学观来统率文学史写作,但是在写法仍然沿用概说和概论这一体制,来给每一个时期的文学作一个大的概括,因而在内容上也往往沿袭旧例,从社会经济到社会政治,再到思想文化状况,然后才轮得到文学。如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在其总的“导论”中,一方面对反映论文学史观提出商榷,并有明确的质疑;另一方面,确立了该文学史的编写立场,即要从“人性的发展”、从“审美意识的变化”、从“个性”和“情感”方面来揭示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过程。但是具体到每一编开首的“概说”中,仍然不能脱当年的窠臼,总是要从该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入手,最后才谈谈文学的形式或新文体的产生,而不能直接从“人性的发展”、“审美意识的变化”和文学本身的演进规律着手来进入主题。当然,比起以前诸多的概说和概论来,这本一九九六年版的文学史可以说面貌一新,在文字的表述上,也一扫以前古板的写法。但是内在逻辑上,这种由社会经济、政治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给出文学的总体面貌的写法,却是反映论文学观的思路体现。因此,在这本当初看来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史中,出现了这样的悖谬情形,即每一编的概说和总体指导思想(即导论)之间是脱节的。这种情形的出现,或者可以归结为每一个编写者对总体指导思想的把握还有所欠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种概说的写法,将编撰者的思路控制住了,使得反映论文学观成为一种表述习惯。 将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简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颇有争议的事情。例如,钱穆在《国史新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若说春秋社会有一些像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到战国,可说完全变样了”。(16)因此“我们不妨称战国为游士社会,西汉为郎吏社会”,(17)又说“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不妨称之为科举的社会”,“这一种社会,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始定型。这一种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科举制度之用意,是在选拔社会优秀知识分子参加政府。而这一政府,照理除却皇帝一人外,应该完全由科举中所选拔的人才来组织”。(18) 钱穆关于战国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可命名为“游士社会”、“郎吏社会”、“科举社会”的概括,虽然可以商榷。但是这种从中国的具体社会历史形态出发来描述国史的情形,比照搬西方的历史分期来套用中国社会进程更值得尊敬,当我们从反映论角度来替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和文学状况作概述时,理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形,不能简单套用现成的说法。 这里无须统计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或者说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撰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面世之后到八十年代,有多少种文学史是以反映论文学观作为其论述基础的,反映论文学观既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必然要体现在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只要翻翻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没有一种谨是从反映论立场出发,来统率整部文学史的,就能明白这一观念的转变曾经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乃至思想史的撰写)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反映论文学观并不只体现在每部文学史的概说,在对文学作品的选取和阐释上,也要有这一思想的贯彻。 在反映论文学观统率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之前,不同的撰写者在文学观念和对文学的理解上虽然大有不同,秉承不同的观念,但是在作品的选取上的是经验主义的或依传统的惯例,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在观念上似是倾向于阮元一路的,但是在具体的作家和作品上,是兼收并包,所以有学者认为谢的“大文学史”之大,是取广义的文学之意,与来自西方的狭义的文学相对。(19) 其实,中国文学史在草创阶段,对于什么作品应该选入文学史内,并未形成套路,往往是经史子集均收录在册,还有佛学著作等。特别是历史文献,在谢无量的大文学史中占了一定的篇幅,即除了《春秋》和《史记》,还有“二班与史学派”、“晋之历史家与小说家”、“范晔与史学”、“诸史之纂集”、“刘知几”等章节。大概是唐及唐之后的史书大都是集体编纂,所以不再被谢无量收入文学史中。也许谢无量多少受章太炎的影响,如前文所说,章太炎曾放论:“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20) 这《昭明文选》或许就可以归入“滑泽者”之列的。 当然,日后的文学史编写,没有按章太炎和谢无量方向走,特别是在对历史著作的处理上,有明显的变化,即除左氏春秋和史记(有时也包括《汉书》)进入了文学史外,其他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献都不再被当作文学,这一情形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汉以前中国的各类文献资料都留存较少,如果将历史文类划将出去,那么在早期文学史中就只有《诗经》、《楚辞》等诗歌,而没有叙事类作品;二,也可以理解为早期中国,自觉的文类意识还没有形成,文史不分,因此在文学史的编撰过程中,也不能分得太清楚。 走过文学史的草创阶段,我们看到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在作品的选取上,虽然各有偏好,但是大的方面有所趋同,即在先秦时期,除了诗经和楚辞,就是诸子散文,此时,“五经”不再以整体面目出现于文学史中。至于从林传甲到谢无量等所谓的“群经文学”、“五帝文学”、“夏商文学”等则一律被摒除,这显然是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和学术界疑古学派的冲击,对于先秦各种典籍的可靠性有诸多怀疑,因此许多文学史基本只从《诗经》起头。诗经几乎成了所有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起点。因此在对《诗经》的介绍和阐释中可以看出各种文学观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可从具体的作品批评过程中,看到中国文学史写作观念演变的轨迹。 作为文学作品,《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关注度最高、研究最多,研究历史最长的文本。以今人眼光看,传统的诗经研究基本是考据学和阐释学的研究,因此当诗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进入中国文学史时,大致上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得到展开的。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在介绍《诗经》时,都要对它的由来、体制体例、功能或题材做一番介绍和考辨,而在具体诗句和辞章的读解上,往往依据一家之说或综合诸家见解,务求对诗歌意义有准确理解,当然是就诗论诗,几乎不从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来解诗,更不从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来分析作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映论文学观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对《诗经》的解读就不同了。这是文学史写作的一个转折,对诗经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大转折。不同的文学观;使读者在文学史中见识了不一样的《诗经》。 先说说《诗经》的第一种面貌。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诸多的文学史中,对诗经介绍篇幅最多的,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柳存仁的《上古秦汉文学史》。这些著述基本延续诗经的研究传统,对诗经的考辨,放在首位,即对诗经的形成年代和产生的地域,以及风、雅、颂、比、赋、兴六义的理解,然后在考辨的基础上,对诗经的功能有所解说,并对某些诗歌作具体的释义。 例如,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认为以往流行的对于风雅颂的划分方法并不靠谱,即“诗经中所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他先后列举了毛诗序、朱熹、郑樵和梁任公的说法,认为他们关于从题材、功能和相关性质来区分风、雅、颂的见解,于理不合。 《诗大叙》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叙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的用明白的话替他疏释一下,便是:风是属于个人的,雅是有关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风、雅、颂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竄乱,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任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抵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假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朝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证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性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区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閟宫》可算是祭祀乐歌,其他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 在否定了《诗大序》和朱熹的见解后,郑振铎又质疑了郑樵和梁启超的划分有关风、雅、颂是按音乐来分类的说法: 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21) 在检讨了各种旧说之后,郑振铎对《诗经》的解说建立在不同的创作群体的划分上,即将诗三百分为诗人的创作、民间歌谣、贵族乐歌三个部分,当然每个部分之下又分为若干类别。亦即,他认为不必顾及风、雅、颂的体例,而是从诗人群体的区分入手,对一些诗歌作了介绍和阐释。一部文学史本来就是由具体的个别的诗人、作家组成,因此将诗三百按照诗人群体,可考的诗人——无名诗人——民歌——贵族乐歌,先后道来,似乎也合乎整体的逻辑。然而,具体到《诗经》,情形就不同,由于人们对周公、尹吉甫、卫武公、卫壮姜等是否某些诗篇的具体作者均有疑问,郑振铎自己也认为,“《诗序》所说的三十几篇有作家主名的诗篇,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其确可信的作家,不过尹吉甫,前凡伯、后凡伯、家父及寺人孟子等寥寥几个诗人而已”。(22)因此对多数读者而言,《诗经》的作者几乎都是无名氏,如按诗人群体来划分:可考的诗人,无名诗人或民间歌谣,对于诗经的阐释上,并无特别的意义。故柳存仁在《上古秦汉文学史》中对于郑振铎的这一划分亦认为“其分类亦未尽详惬”。(23) 相比郑振铎,柳存仁在文学史中对《诗经》的介绍用了更大的篇幅。除了对采诗、献诗、孔子删诗等说法进行了比较分析,还对《商颂》的成诗年代作了考辨。 柳本文学史并不对《诗经》中的个别作品有具体的释义,而是主要介绍了《诗经》的各种社会功能,即“三百篇之于周代,实非后世仅以文学作品视之而已者。”认为“吾人苟以后世社会生活之眼光观察之,其言殆不可解。不知同时贵族士大夫间之典礼、讽谏、回答、言语,往往假三百篇之言辞为应用”。(24)并就诗三百用于典礼,用来讽谏朝政,用于言语交谈的三种情形有所阐释。 关于诗之用于典礼者,有点像章太炎的看法。章认为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柳存仁则认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诗与典礼相关。 《诗》之应用于典礼者甚多,如祭祀则有《小雅·楚茨》,宾宴则用《小雅·鹿鸣》、《白驹》、《周颂有客》,庆贺则用《大雅·崧高》、《小雅·出车》,颂辞则用《周南·螽斯》、《桃夭》。《仪礼·乡饮酒礼》、《燕礼》、《乡射礼》、《大射仪》各篇,均有乐功歌诗之记载。(25) 当然,诗的讽谏功能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一社会功能,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 至于三百篇之用于讽谏朝政者,其事实亦甚众。《国语·周语》述邵公之谏厉王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又《国语·晋语》,范文子戒赵文子曰:“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凡此皆可认为周代讽谏诗产生之环境。至于讽谏之作品,则如《魏风·葛屦》、《小雅·节南山》、《小雅·何人斯》、《小雅·正月》、《小雅·雨无正》,或意在规劝,或警戒暴虐,均为不可多得之讽谏诗歌也。(26) 诗在人们交谈和言辞往还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修辞功能,即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就表达了这一层意思。 赋诗之用,多为主宾间相互之称美及祝颂。孔子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云云,足证赋《诗》常为列国间外交上一种至为庄重优美之辞令。(27) ……至于《诗》之用应对言语者,则更有实质上之作用可见。 三百篇代替言语之用,如宣公二年传: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襄二十五年传: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蚊子闻之曰:“呜呼!《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诗》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28) 以上所举的郑本、柳本本文学史,对于诗经的介绍和阐释尽管各有侧重,但是其内容集中在如何理解诗经,人们见到的《诗经》还是传统眼光下的诗三百,是有关恋歌、悼歌、农歌,宴会歌、田猎歌、战事歌、宗庙乐歌、颂神歌等等的合集,而反映论文学观作为文学史的指导思想,诗三百就呈现出另外一幅面目。 这里,应该首先提到詹安泰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本撰写于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的文学史,就已经运用反映论文学观来解析古代文学,如在《诗经》一章中,一上来就谈“《诗经》产生的社会基础”,而所谓社会基础,首先就是人类的经济活动: 农业经济在殷商时代已经开始发生了,到了周代,农业生产就占着社会生产最重要的地位。我们看《大雅》中的《生民》(叙述后稷诞生和艺种的历史)、《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开辟疆土、组织国家和经营耕稼的历史)、《緜》(叙述公刘九世孙古公亶父避戎狄迁至岐山,从事耕种。建筑域邑和设立官司的历史)等诗篇,可以见出周人很早就是重视农业的。《史记周本纪》说文王“遵循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而教化大行”这又说明了周代累世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因之农业生产才能占着社会生产中最重要的地位。(29) 以上这种开篇介绍社会生产形态以作《诗经》的缘起,在以前的文学史中似无缘得见,但这正是反映论文学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一种表达模式。即从理论上说,文学史虽然要和一般的历史著述相区分,但是却要求进入文学史的文学作品是反映历史、反映社会、反映现实生活。 自然,在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中,将这一部分的内容挪到前文提及的各种“概说”或“概论”中,并有了规范化的表述。 詹本文学史认为,既然《诗经》的风、雅、颂到底是以什么原则来加以划分的,已很难厘清,“因此,我们需要从新的立场观点来给它们一个比较恰当的说明”。(30)这一立场,就是以是否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为其价值尺度。由此该文学史将《诗经》的价值分为三个等级。毫无疑义,《国风》最有价值,因为其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是当时的民歌、民谣,“可以说是当时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的总汇。毫无疑义,它在《诗经》里面的价值是最高的”。 第二等级是《小雅》,因为“《小雅》里也有一些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具有相对的正义感的作品,如描写被迫给统治阶级服役的苦况的《何草不黄》,揭露统治政权的腐朽本质的《正月》之类都是。像这类的作品,其价值仅次于风诗,我们应该把它们和《小雅》中其他的部分分别看待”。 第三等级是被第二等级摈除的一部分小雅、还有大雅和“三颂”,“其中虽然许多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作品,可是,它们里面也包孕着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对《雅》、《颂》里面关于劳动生产以及其他能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还是可以有选择地来进行批判地吸收的”。(31) 正是从这样一种价值尺度出发,詹安泰对《诗经》的内容作了不同于郑振铎、柳存仁等的分类,即既不是按诗人、无名氏、民间创作、庙堂诗人等群体来划分,也不是按诗歌的社会功能如典礼、讽谏、交谈中的修辞来划分。而是按诗歌在经济生活、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划分。由此我们看到了以下内容组合的诗三百: 1,“关于农业生产”的诗(如《周颂·良耜》);2,“关于畜牧生产”的诗(如《小雅·无羊》);3,“关于反映人民反对统治阶级斗争”的诗(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4,“不正面表现强烈的斗争,只是反映劳动人民被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从而显示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作品”(如《豳风·七月》、《豳风·东山》、《王风·君子于役》);5,“关于男女恋爱的歌词”(如《郑风·籜兮》、《郑风·褰裳》、《唐风·绸缪》);6,“表现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诗(如《小雅·巷伯》、《秦风·权舆》、《小雅·巧言》等)。(32) 同样是“诗三百”,在詹本文学史中,读者领略到了不同于以往的阐述立场和读解视角。可见一种新的文学观,会给同一部经典带来不同的面孔。 或许,对《诗经》最有颠覆性的表述,就数北大五五级学生的那本《中国文学史》了。在该文学史中,我们看到作为整体的诗经,被“周代民歌”和“周代文人诗及庙堂乐歌”这两个概念取代并分解了。即在以往的各种文学史的著述中,“诗三百”总是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以其整体而被予以关注并得到阐释的。但是在北大五五级版的文学史中,读者则要从“周代民歌”这一名目来进入主题,即先是从周代民歌这个大概念中来认识大部分《诗经》作品(主要是指《国风》),然后再另起一章,从“周代文人诗和庙堂乐歌”认识其中的另一小部分诗歌(如《雅》、《颂》等)。 换言之,《诗经》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保存了周代民歌。因为“周代民歌是现存最早的一批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精华”(33)而介绍周代民歌,主要是介绍“《诗经》中的《国风》的大部分作品和《小雅》的小部分作品。”而其他的民歌虽然在“先秦典籍中也保存了一些断章的歌谣,可惜全貌已不可见了”。(34) 接下来,我们看到,从民歌的角度,该文学史认为最值得写入文学史的是两类作品:“第一,反映阶级压迫,阶级觉醒,统治者荒淫无耻,人民苦痛生活的诗歌。”如“《豳风》的《七月》、《魏风》的《伐檀》、《硕鼠》等正是这类作品。”(35)之所以选这些作品还有一层意思在:因为这些诗歌既反映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在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几乎喘不过气来”的生活,也表现了他们“用歌声鼓舞自己的斗争,倾泻自己的满腔愤恨和不平,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6) 第二类作品,主要是“反映劳动人民乐观主义精神、坚贞不渝的爱情诗歌”。如《魏风》的《十亩之间》、《卫风》的《木瓜》、《郑风》的《籜兮》、《鄘风》的《柏舟》等。(37) 在对这些爱情诗篇作阐释时,该文学史顺带批判了某些传统的学说,认为是传统的封建礼教歪曲了这些爱情诗歌的主旨。正是这些诗歌“对爱情的忠贞,对爱情阻碍的反抗,有力地冲破封建礼教的阵脚,这就不能不使统治者感到严重的威胁,于是从汉代经学家开始,历代封建文人无一不对这些诗大加歪曲。《关雎》本来是首平常的恋歌,可是《毛传》却说什么文王后妃之德”,《鄘风柏舟》“是一个极有反抗性的恋歌,但《毛传》却硬说是一个贵族寡妇共姜作的,说什么共姜丈夫早死,守寡,而‘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38) 由于该文学史将《诗经》分成“周代民歌”和“周代文人诗和庙堂乐歌”两个部分来讲解,所以有关以往《诗经》研究必然涉及的如年代、体制、复杂的社会功能等话题和与之相关的考辨就统统略过了。比较有意思的是,该北大本文学史仅在一年之后的修订本中,就恢复了《诗经》的整体面目,并增加了“诗经介绍”、“周民族史诗”、“贵族讽喻诗”、“歌功颂德的贵族诗歌”等内容。(39) 这里,必须提及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是反映论文学观指导下,比较成熟的文学史著述。在吸收以往的《诗经》研究成果同时,该文学史将唯物史观运用其间。考虑到《诗经》是“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之间形成的,因此从更加开阔的视野来认识诗经的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游本文学史不是先强调《国风》,而是率先介绍《雅》、《颂》,该文学史认为:“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运用的乐歌。由于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直到今天还有其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40)正是从民族史诗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意义上,游本文学史肯定了《诗经》的整体价值,而不是从民粹主义立场出发,只首肯《国风》作为周代民歌的价值。 所以,该文学史认为,应该看到“大雅的大部分和小雅少数篇章,和周颂一样,都是在周初社会景象比较繁荣的时期,适应统治阶级歌颂太平的需要而产生的”。特别是“大雅”,“更能体现雅诗重视社会生活描写这一特点”,这是因为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诗,“与后世的叙事诗相当接近。这些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41) 至于《小雅》,意义就更加丰富了。 小雅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深刻地反映了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社会现实。这些雅诗的作者大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由于他们在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他们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本阶级的当权者的昏庸腐朽持有批判的态度,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因而使他们的创作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内容。(42) 当然,即便如此,在游本文学史中,“国风”还是《诗经》中的翘楚,“它们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晶莹的珠宝”。因为“‘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了他们对剥削、压迫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43)也就是说,坚持反映论文学观,就必然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就必然要有倾向性和阶级性。 以上,从对中国文学史源头的《诗经》的阐释中,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变化是如何渗透到具体的作品批评中的,并且又是怎样从传统的阐释转换到反映论的立场,并确立其在文学史上无可撼动的地位的。(本文完) 注释: ①在1958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前言》中,对林庚有300来字的较严厉批判,认为林庚在“文学史的标期上,什么‘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奇怪的名堂也被搬弄出来了。丢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地研究文学现象,结果也就丢掉了文学史的科学性,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学现象,深刻地阐明文学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就不能不仍是一笔糊涂账”。——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5页。 ②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5页,1963。 ③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中国文学史》第一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④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中国文学史》,第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⑤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19页。 ⑥见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第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⑦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第3页。 ⑧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⑨⑩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7、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1)(12)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中国文学史》,第17、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3)(14)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225、226页。 (15)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6)(17)(18)钱穆:《国史新论》,第8、16、27-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9)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第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0)《国故论衡》,第83页。 (21)以上均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38-3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2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6页。 (23)(24)见《中国大文学史》(上),第48、4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25)《中国大文学史》(上),第43、44页。 (26)(27)(28)《中国大文学史》(上),第43、44、46-47页。 (29)詹安泰主编:《中国文学史》,第5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0)(31)(32)詹安泰主编:《中国文学史》,第54、54-55、57-78页。 (33)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上),第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59年4月第一次印刷。 (34)(35)(36)(37)(38)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上),第19、20、20、23、25页。 (39)笔者认为,这一修订本是吸收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指导意见后完成的,因此与日后游国恩本的《中国文学史》更加接近。 (40)(4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上),第33-3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2)(43)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上),第37、39页。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艺术起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诗经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谢无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