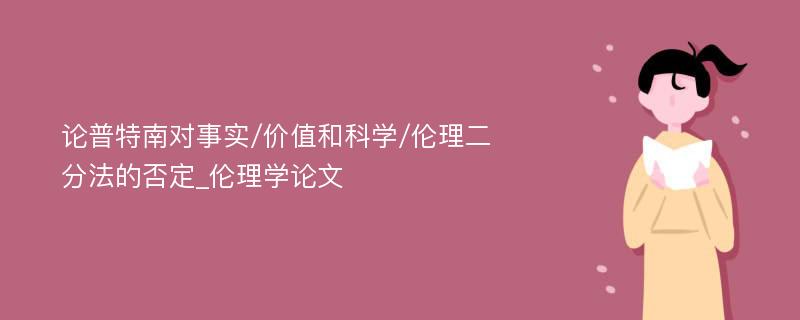
论普特南对事实/价值、科学/伦理学二元分割的否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事实论文,价值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观/客观二分法的破除和事实/价值二分法的瓦解,不过是一个钱币的两面。认识不可能追求与世界的对应,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行为,只能在文化共同体内部进行。这样,话题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价值”。在西方学术界,自韦伯提出价值判断不能从理性上被肯定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事实与价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科学与伦理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普特南否定了事实(客观性)的形而上学基础,这就意味着他必定要否定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否定科学与伦理学的本质区别。
一、事实与价值的分割不能成立
坚持事实/价值二分法的人常常会说,事实与价值的根本区别,首先表现为客观真理只是对事实的断言,与价值无关;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因而与“价值无涉”。普特南要否定事实与价值的分割,就必须证明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不能成立。
普特南指出,用事实来解释真理,无非就是像塔斯基对真理所定义的那样:“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它所涉及的只是真理的形式定义,与现实中人们把什么接受并理解为真理根本无关,因为持不同真理观的人都可以同意这一点。这个T等式,只是表明对象语言陈述的真等同于元语言表述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理解事实。“雪是白的”这一事实贝克莱可以承认,实证主义者可以承认,实在论者可以承认,神秘主义者也可以承认,但是由于对这个事实的理解不同,他们之间可以是南辕北辙的。仅仅说科学“寻求发现真理”,这只是一种纯形式的陈述,它不过是说,如果雪不是白的,科学家们就不会断言雪是白的。关键的问题在于,“雪是白的”这一判断是怎么得出的。普特南说,当一个神秘的宗教徒眨着眼睛径直跟我们说“雪是白的”时,我们未必会认为他的话是事实,他的判断是真的,除非我们自己去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位宗教徒的合理性标准是什么,客观性标准是什么,他是否把梦中的启示当作“真的”合理性标准。我们相信经验证实标准的合理性,我们的客观性标准是由感觉经验(或者融贯性等)确立的,我们得通过亲自观察来确定事实。因此,一个判断是否为“真”,是否符合事实,和作出这一判断是否合理是一致的,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合理性标准,然后才能知道这个判断是否为真。普特南指出:
将确定雪是否白的科学方法与确定雪是否白的其他方法区分开来,……需要一些合理可接受性的标准。只要我们对这个合理可接受性的标准系统一无所知,这些纯形式的陈述也将是完全空洞无物的。(注: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这样,真理是否与价值无涉的问题,就变成了合理性标准是否与价值无涉。由于合理性标准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内有不同的内容,在这个共同体中,它和融贯性、简单性、工具效用性等密切相关,故是和价值融为一体的。那么能不能说,这些优点并不是“价值”而只是关于理论特征的事实描述呢?普特南认为不能。他不仅反对把事实与价值分开(这点后面再谈),而且认为即使退一步说,有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这些词也和所谓典型的价值词(如“善良”、“好”、“美”)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第一,“融贯的”、“简单的”和“善良的”、“好的”一样,都是作为赞誉词使用的,“把一种理论描述为‘融贯的,简单的,辩明的’,在正确的背景下,也就是说,接受这个理论被证明是正当的;而说一个陈述的接受被(完全)证明为正当,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接受那个陈述或理论。”(注:H.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38.)第二,我们把什么作看融贯的、简单的、证明为正当的,和我们把什么看作善良的、美的、好的一样,“都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注:H.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63.),这里没有什么超历史的中性标准可以指望。第三,关于什么是融贯的、简单的,和关于什么是善良的、好的、美的一样,“一直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哲学争论之中”(第147页),这里同样没有元标准。
如果用旧的主、客观二分法标准,这些词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如果从内在实在论的眼光看,它们都是客观的,它们和人类兴盛的观念连结在一起,是价值同时也是事实。“没有融贯性、简单性和工具效能这些认知价值,我们就没有世界,也没有事实,甚至没有某物相对于某物如此这般的事实,因为这类事实与其他事实的处境是相对的。这些认知价值如果不看作是对人类兴盛的整体主义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就是任意武断的。”(第147页)
真理与合理性相关,从而与价值相关。科学理论被接受为真理,离不开这些价值。话说到此,还只是从一个方面否定了“真理与价值无涉”的主张。逻辑实证主义等科学主义的捍卫者们坚持事实/价值二分法的另一个理由是:事实的陈述是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的,而价值判断则是“不可证实”的。
普特南指出,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它设想有关于孤立句子的证实方法的存在,经过了奎因的“整体论”之后,这种想法已经不值得重新提起了。科学陈述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面对经验的检验的,认为每一个科学陈述有自己所对应的证实或否证的观察经验,是完全错误的。一个陈述是否是事实,并不能由“证实的方法”来确认。其次,普特南认为,即使说价值判断的句子由于没有证实方法因而是无意义的,也得不出事实/价值二分法的结论。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价值二分法是建立在另一个二分法基础上的,这就是分析/综合二分法。关于这一点,沃尔什(Vivian Walsh)曾有过很好的分析,普特南对此深表赞同(第148页)。沃尔什说,现有“谋杀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命题,实证主义者会问:有没有经验可以证实或否证它?当我们把这个命题看作是对某个社会信念的事实报道时,可以用经验来检验它,即它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命题。但做出道德判断的人肯定不会同意这个分析,于是实证主义者会说,既然这样,它就是一个只表达情感的同义语反复,因为按照分析/综合的二分法,如果“谋杀是错误的”不是一个综合命题(可用经验检验)的话,那么就一定是一个分析命题,而分析命题实际只是同义反复。如果做出这种道德判断的人连这一点也不接受的话,那他的命题便只能是一个“伪问题”。
普特南实际上从沃尔什的分析中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没有意义和二分法是不同层次的判断,不能等同,否则的话,形而上学判断、道德判断就都是同样性质的判断了。逻辑实证主义确实得出了这一结论,但即使是按照沃尔什所阐述的逻辑实证主义自己的分析,它们也是不同的;第二,事实/价值二分法既以分析/综合二分法为基础,那么在奎因《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之分,分析/综合的区分已经崩溃,事实/价值二分法也应一同抛弃。
那么,事实是怎样与合理性相关、从而渗透了价值的呢?
在普特南看来,事实并没有形而上学实在论所自诩的所谓“客观性”,这一点甚至连所谓“最硬的”物理事实也不能“幸免”。举“猫在草席上”为例,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陈述是怎样渗透了文化价值的。“猫在草席上”这个陈述包含了三个概念,即“猫”、“草席”和“在……上”。普特南要说的是:这些资源是由特定的文化提供的,它们的出现和普遍存在,展现了有关那种文化乃至几乎每一种文化的利益和价值。我们有“猫”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把世界划分为动物与非动物是有意义的,并且更关心某个物动属于什么种。这样,说草席上有只“猫”而不只是一个东西,这样才是贴切而合理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有“草席”这一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把动物以外的事物划分为人造物与非人造物是有意义的,并且更关心某个特定的人造物所具备的用途和性能,因此说猫是在“草席”上而不只是在某物上,这样才是贴切合理的。普特南指出,“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把这些东西视为贴切范畴的倾向,他就不会承认‘猫在草席上’是合乎理性的谈论”,从而也就不会认为“猫在草席上”是一客观事实。一个文化的贴切性标准以及与其相关的“合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第212-213页),是事实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客观性的前提。
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有其语言学根据。他把语言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具有描述的功能,涉及的是事实;另一部分具有表达的功能,它们只是传达人们的主观价值、情感等,没有真假问题,因而不具有客观性。普特南认为,卡尔纳普把语言的功能截然二分的作法是难以成立的。他引述他的妻子安娜.普特南(Ruth Anna Putnam)的话说:“这种论证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许多描述性谓词是天然地获得情感力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使衬衫沾满了污渍’这个句子……字面上看虽然是个描述句,但即具有强烈否定的情感力。”(注:H.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p.209。)而当我们说“好”这样一个价值词语时,也必定不只是某种主观情感的表达,同时也表述了某种事实:“把一项行动称之为好的最一般理由就是它具有一些好的后果,其中某些后果就是最终引起一些自然被认为有价值的状态或情形。”(注:H.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p.209。)“好”既然涉及到后果问题,它就不只是主观情感的表达了。实际上,“‘描述性的’词语可以用来赞许或责备,……而‘评价性的’词语也可以用来描述或解释。”(注:H.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p.210。)普特南并不否认,在语言的描述性用法或赞许性用法之间,存在着某些区别,但按照他的理解,这只是用法上的区别,不是语言本身功能上的区别,而语言用法上的区别只有在语言共同体内部谈论才有意义。
如果说连物理学所谈论的事实都不能免于价值“污染”的话,那么关于社会生活、人文环境的事实就更是如此了,这里甚至无法在理论的层面上分辨出事实与价值,更遑论对两者作出区分。
当我们说“琼斯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时,它无疑是描述事实的,但难道这里不同样包含着一种责备吗?能不能说,在“琼斯是一个很粗心的人”这个句子中,实际包含了两种因素,一种是事实的因素,一种是加在事实因素之上的评价的因素?普特南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只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将这些事实说出,就已经导致了评价,哪怕不说出所谓纯粹的“好”、“美”这样的评价词来。比如现在如果有三个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关于约翰的“事实”判断:“约翰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约翰只想着自己”,“约翰为了钱几乎什么都干”,那么从这三个陈述的合取中,我们已经就得出了评价性论断,根本不需要再加上“约翰不是个好人”这样的字眼。“当一种处境或一个人或一个动机被适当地加以描述时,关于某个事实是否是‘好’或‘坏’或‘对’或‘错’的决定自然也就随之而来。”(注:H.Putnam:Realismwitha HumanFace,p.166。)实际上,我们只能在最抽象的层面上有所谓如“善”、“恶”等价值词的出现,这些词并没有任何内容,一旦把它们稍微具体化,我们就很难再分清哪些是描述词,哪些是评价词了。
因此,不能说评价是主观的。如果像“善良”、“好”这些所谓的伦理价值是主观的话,那么“融贯”、“简单”这样的认知价值就也是主观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太多了,比如:都是赞誉词;都是在历史中变化着的;都是充满争议的;等等。而如果这些认知价值也是主观的话,那么合理性标准便是主观的,因为把什么看作合理的,正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这些认知价值所描述的特征。如果合理性标准是主观的话,那么真理也就成了主观的了:我们关于真理的谈论无非是关于合理性的谈论。而说“真理是主观的”,显然不是主张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人所能接受的。普特南要展示给他们的恰恰是:只要你不把真理当作主观的(如果真理是主观的,那么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便是自我否定的),那么你就不能把价值看作是主观的。事实不像二分法者所说的那么客观,价值也不像二分法者所说的那么主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也就不像二分法者所认为的那样清晰可见了。
二、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一旦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不能成立,客观性只能是“就人类而言的客观性”(注: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第179页。),则科学与伦理学的截然区分也就不攻自破了。物理学固然是客观的,但伦理学也同样是客观的。
逻辑实证主义攻击伦理判断是主观的,理由是它不是建立在中性事实基础上的,无法找到一个客观中立的标准来判断它的真伪。现在,既然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不能成立,既然“客观性”只能在合乎理性标准的基础上才能被理解,那么伦理判断的客观性就完全可能和科学判断的客观性一样被接受了。在普特南看来,“某物为善”如同“猫在草席上”一样,其客观性并不在于它与对象的唯一对应。客观性的概念无法在这种形而上的意义上理解,它只能在一个文化的内部才能得以把握。是特定的文化为“善”提供了合理的可接受的标准,从而在文化内部,“善”具有了某种和物理事实同样的客观事实性。伦理学同样是关于事实的理论。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帮助贫困的人的行为是善的”是一个客观的陈述,一个不争的伦理事实。
普特南指出:“伦理学与物理学并不冲突。只是,‘公正的’、‘善的’和‘正义感’属于那类不能还原为物理学话语的话语中的概念”(第156页)。但不能还原为物理学并不等于不是客观的。以数学为例:在数学领域中,“一个新提出的公理(比方说“选择公理”)之所以能被接受,部分是因为它符合专业数学家的直觉,部分是因为它的成效。”(第157页)再比如说视觉:“一个生理学家或心理学家对视觉的描述不能告诉我们在虹里看见色带是否可称作‘正确地’看见”(第157页)。在道德领域中同样如此:“当一个人‘看出’一个行为不正当时,对他脑运动过程的描绘并不能告诉我们这种行为是否确实是不正当的”(第157页)。不论是伦理学还是数学、视觉心理学等,都是不能还原为物理学的,何以偏偏伦理学就因不能还原而成了仅仅是“主观的投射”?因此,普特南断言:“如果伦理学不可还原为物理学就表明价值是投射,那么色彩也是投射,自然数也是如此。就此而论,‘物理世界’也是如此。但是,在这种意义上是投射,并不等于就是主观的。”(第158页)
逻辑实证主义曾经认为,科学的客观性还在于它是由精确的方法指导的,而伦理学则由于是情感的投射,因而是没有方法可言的。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受到了普特南的抨击。
在普特南看来,科学诚然是讲求方法的,但科学方法并不像人们所误以为的那样,是纯粹形式的、超时空的,相反,“人们日益相信,在科学的内容和科学的方法之间无法泾渭分明地划出一条界限;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如科学的内容一样,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第201页)自15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和哲学家们即着手提出一套新的方法论准则,这一工作至17世纪达到鼎盛。但这些准则并不是精密的形式规则,它实际上需要运用非形式的合理性因素,如理智、常识等。从关于波义尔、波普等人的方法论的探讨中,普特南得出结论:这些理智、常识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决定着科学探究的方式,“简言之,存在着一种科学方法,但是这种方法预设了一些先验的合理性概念。”(第206页)如果不把科学的方法视为科学所独有并且是超经验的规则,而只是说科学的推论、科学的研究必须遵循逻辑(其规则并非先验不可变的),必须杜绝个人喜好的话,那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在此意义上,伦理学并不是不讲方法的。普特南指出:
我们并不把伦理学的判断只当作是趣味的问题;我们关于它们的论证是严肃认真的,我们试图使它们正确,就像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论证和思考中使用着客观性的语言。例如,当我们就伦理学问题作推理时,就像我们就集合论的问题,或物理学的问题,或历史学的问题或任何其他领域中的问题作推理一样,我们都使用着同样的逻辑法则。(注:H.Putnam:Words and life,p.154.)
科学论断总是能达成一致,而伦理学的论断却总是充满了争论和歧见,但这种差别是不是像人们夸张的那么大,以及这种差别是否证明了在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有本质的不同,这是问题的关键。普特南认为,科学预见所要涉及的基本语句,如“天平的右秤盘下垂”,“我正站在地上”以及“猫不生长在树上”等等,关于它们之所以没有争论,并不是因为它们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有某种形而上的原因(如这些语句对应了世界本身),而是因为社会规范使然。这些规范具有习俗化的本性,是隐蔽的标准,决定了我们对于上述语句的认可。和维特根斯坦相近,普特南认为,假如没有这些社会化的公共规范,即一个共同体所共有的、并且构成了“生活形式”的规范,那么语言甚至思想都将是不可能的;这些基本语句的无争议不是由于对应了什么外部世界本身,而是社会习俗要求我们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必须遵守一些说话方式。“当一位怀疑论者非要我们‘证明’像‘我正站在地上’这样的陈述不可时,我们对他的反应的本质,证实了存在着一些要求人们在合适的场合同意这些陈述的社会规范。”(第116页)
普特南的分析实际上告诉我们,由于都是以社会习俗化的规范为前提,故在这个层面上并不能说科学陈述和伦理学陈述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至于更高一层的科学理论,普特南认为,其一致性其实只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一致性,因为普通人并不了解这些理论。比如对狭义相对论,普通人只是由于社会智力劳动分工的缘故,对专家的判断予以信任和尊重,“判断是一些权威人士作出的,而这些权威人士是由社会指定的,他们的权威被一大批习俗和风尚所承认,因而是习俗化了的。”(第117页)因此,所谓“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一致”在此并不存在,而且即使是科学家也会因范式的不同而有意见的差别,想用唯一标准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是行不通的。实际上,科学家们在选择理论时也充满了价值的考虑,这些考虑归根结蒂和伦理学关于“好”、“幸福”的判断是不可分的。
普特南并不是不承认科学和伦理的区别,他要否定的是它们之间有一种独立于人类实践、文化之外的所谓形而上层面上的区别。排除了这一点,他承认伦理学领域“所要权衡的事复杂而且含混”,言下之意,范式的建立是更加困难一些。但是,普特南指出,虽然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在某些抽象伦理(如什么是好、什么是善良的)判断上存在着分歧,但是在一个文化内部,人们关于某些描述性的伦理判断,如什么是残酷,什么是贞洁,什么是自私等等,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即使是在前一个层面上的分歧,只要有民主对话的文化氛围,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也不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坚持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有一条形而上学鸿沟的人,在思想深处具有很重的科学主义情结,总认为物理学(科学主义的范例)才是真正对应于实在的,合理性只能是科学的合理性,于是其他不具有这种合理性的学科或观点便都成了主观的,伦理学就是这样被划到了与科学相对立的阵营中。普特南指出,要根除这种二分法,我们必须意识到:
事实上,形而上学实在论和主观主义不是简单的“对头”。在今天,我们对物理学太倾向于实在论,而对伦理学又太倾向于主观主义。这两个倾向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我们对物理学实在论倾向太重,正因为我们将物理学(或某些假定的未来物理学)看作是‘唯一真的理论’,而不仅仅看作是适合某些问题和目的的合理地可接受的描述,我们才倾向于对不能‘还原’为物理学的描述采取主观主义态度。对物理学少一些实在论和对伦理学少一些主观主义同样是相互关联的。(第154页)
归根到底,关于主观/客观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二分法是导致其他一切二分法的基础。
三、对威廉姆斯关于科学与伦理学区分的回应
旧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论证今天已经被很多哲学家们所放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样放弃了科学与伦理学的二分法。英国著名哲学家威廉姆斯(B.Williams)在他的《伦理学和哲学的界限》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论证,认为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不能成立,但科学与伦理学的二分法必须捍卫。普特南不止一次地反驳了这一观点。
威廉姆斯的观点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立场为出发点的。他把真理和绝对区别开来,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真理,一种是相对于文化、语境的真理,比如“草是绿的”。这类真理是和当下视角分不开的,是渗透了价值的。太空人可能没有我们这样的眼睛,也没有我们划分世界的方式,因此他们不会用“绿”、“草”来描述世界,然而不能说“草是绿的”所陈述的不是事实,这里的事实与价值是互相依赖不可分离的。在此意义上说,伦理学的判断同样可以是真的:“玛丽是贞洁的”,“彼德是残酷的”,这类伦理学判断和“草是绿的”、“雪是白的”一样,都是对事实的描述,都是真理。所以,在这一层面上说事实与价值分离,伦理学判断没有真理是错误的。威廉姆斯并不完全否定这种分离,他只是要把这种分离由认知领域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他认为,上述真理由于渗透了价值,因而都是受认知条件限制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绝对的真理,它是关于世界自身的描述,独立于一切视角(perspective free)。威廉姆斯承认这并不是我们在某个确实的时刻可以达到的真理,它只能存在于一切关于世界的研究注定会聚的最后描述中,只有这种描述才能在“独立于视角的最大程度上”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只有这种真理才是“绝对的”。因此,尽管伦理判断可以是真的,但它不可能是绝对的,世界本身是“冷酷的”,对于它的本来面目的揭示只能由科学的会聚来完成;价值是被投射到世界上的,而不是从世界中发现的,在绝对真理的层面上,科学与伦理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话语。(注:普特南关于威廉姆斯观点的转述,见H.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p.168-170;H.Putnam:Renewing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chapter 5.)
威廉姆斯这套主张的核心是科学能最终会聚,普特南的反驳也从这里开始:“我首先要审查支配威廉姆斯的科学图画,即科学会聚于一个单一的真理论,一个单一的关于宇宙的解释图画”(注:Realism witha Human Face,p.170.)。他重述了自己概念框架相对性的论证(注:普特南关于概念框架相对性的论证见H.Putnam:Many Faces of Realism,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1987,p.32-40.),得出结论:“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科学会聚于单个理论的主张(这主张对于威廉姆斯相信“关于世界的绝对见解”是至关重要的)。”(注: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p.171.)
人们不免会问: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的结束部分,普特南不也设定人类的对话会有一种真的“理想的结局”吗?罗蒂为此指责他“在这里无路可走之时又溜回他在其他论著中正确批评过的唯科学主义去了”(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15页。)。公正地说,普特南在这里确有含糊其辞、不能自圆其说的毛病,他对这一困难的明确解决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把普特南与威廉姆斯混为一谈,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有没有外在基础的设定。普特南声称,“在我们辩护的概念中,根本没有‘基础’这种东西存在”(第227页)。人类当然是在努力向更好的、更加合理的方向会聚,但这个方向并不是实践之外的力量所确立的,人类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合理”的标准本身也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这里所说的会聚,只能是在很不确定的意义上说的;只要人类是面对共同世界,从事大体同样的实践活动,只要人类还是讲道理的(否则就不用对话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指望这种会聚的可能达成。而威廉姆斯所设想的会聚与此显然不同,它是由世界本身所决定的,是一种较强意义上的会聚是会聚于某单个科学理论;尽管这个理论我们无法设想,但在上帝眼里它是明确无疑的,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在未来达到它。所以,普特南说的会聚,是人类自己为自己设定目标;而威廉姆斯意义上的会聚是世界为人类设定目标。普特南说过:“我并不怀疑在科学认识中有某种会聚……我们只是没有证据证明,关于科学是否‘注定’会聚于某一确立的理论图画的思考是正当的。”(注: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p.171.)
只要这种会聚不能证明,则我们便无法保证关于“绝对性”的设想是合理的,就像普特南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一设定,即科学借助于一种独特的本体论和一套独特的理论性质会聚于一个单一确定的理论图画的话,整个‘绝对’的概念就要崩溃了。”(注: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p.171.)于是,用科学能通过会聚达到绝对、而伦理学则不能达到这种会聚来区分两者的观点便也随之崩溃,“伦理学的认识确实不可能要求绝对,但这是因为绝对概念是不清楚的”。(注: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p.171.)不光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不能离开我们对于概念框架的选择,而且数学、物理也同样不能摆脱概念框架面对世界,“不论我们谈论什么,世界都不会向我们强加一种单个的语言。”(注: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p.171.)
普特南指出,与此相关,威廉姆斯想用与世界本身的符合来解释“绝对真理”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符合”本身是我们无法理解和谈论的。在讨论塔斯基真理论时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清楚,在我们的语言内部,我们可以谈论雪,可以谈论雪这个词,还可以谈论它们之间的对应,对此持不同形而上学立场的哲学家都可以无保留地同意,所以“一种言语的符合不可能扮演解释的作用”(第173页)。普特南认为,威廉姆斯所说的符合是一种真正的符合,是语言之外的符合,事物是外在于语言的,符合也是外在于语言的,而这是很不明智的。第一,“对象”的概念并不是一个,不是世界固定我们对于“对象”一词的使用,而是我们的生活实践决定了对于“对象”一词的使用,因此对它的使用是有无数多的可能性的,这是一个开放的系列;第二,世界决定对象和语言之间的符合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模型理论论证已经表明,即使我们以某种方式固定了语句的真值,语词的指称仍然是不确定的,唯一的符合是无法“挑选出的”;第三,即使我们用因果联系来说明这种符合关系也同样不能成立,因为“因果联系”这一概念是渗透着“意向性”成分的,而意向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解释性的概念,它本身也是一种视角的产物。用因果联系解释符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解释:因果联系是用来解释我们思想、语言的,它反过来又要由我们的思想、语言来解释。因此,普特南认为,谈论外在意义上的“符合”是不明智的,“关于世界的绝对见解”的概念必定要被放弃,科学与伦理学区分的形而上学基础最终也必定瓦解。
普特南关于事实/价值、科学/伦理学关系的论述是他整个内在实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他关于指称/意义的主张、关于真理/合理性的学说、关于道德哲学的思考等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笔者认为,他的论述既着眼于“大的哲学问题”,又注重细致入微的剖析,相当有力。普特南的立场明显地表现出他由科学主义向生活实践的转变,表现出他超越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对立的努力,这一点也受到了哈贝马斯的好评。然而,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是在传统二元论的舞台上演出的一台叛逆的剧目,他对于二元分割的否定是用传统二元分割的语言说出的,先承认了内在心灵和外在事物的存在,再来否定用它们之间的关系解释事实、真理、客观性等等的合法性,其困难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说事实只能在文化内部确认,那么究竟还有没有非相对的事实,有没有脱离文化价值的真理,有没有不同于认识论的本体论问题?应该说,普特南对这些难题的解决还不能令人满意,罗蒂对于他的责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普特南的方向是向前而不是折回去,真正的对于各种二元分割的克服,有待于进一步向着生活、实践的前行。90年代中期以后,普特南反思了自己原先的主张,仍然坚持对于事实/价值、科学/伦理学的二元分割的否定,所有的论证仍然保留,但整个图画的底色已经改变,实用主义“实践优先”的主张真正被当作“第一原则”。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阐释,限于篇幅只能留待以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