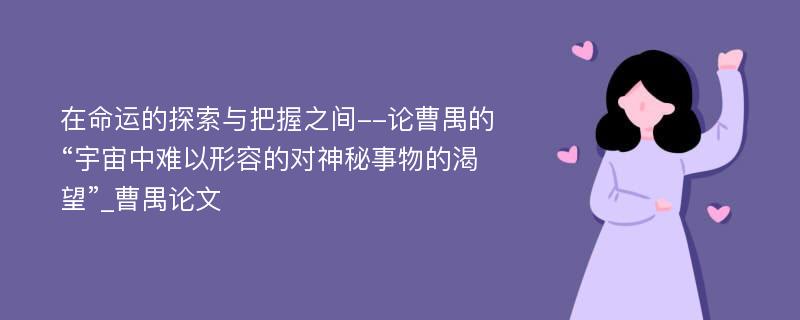
在命运的探幽与把握之间——试论曹禺剧作“对宇宙间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言喻论文,剧作论文,试论论文,宇宙论文,事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曹禺剧作从《雷雨》到《原野》,始终表现了一种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在对人类命运的探幽与把握之间显示了其独特的追求。命运对人的主宰和人对命运的抗争,构成了曹禺剧作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而这正是曹禺剧作“说不尽”的魅力之一。
关键词 曹禺剧作 命运探幽 《雷雨》 《日出》 《原野》
中外文学史上能够被称之为“说不尽”的作家作品是不多的,一代戏剧大师曹禺及其剧作算得上是其中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曹禺剧作神秘迷浑的主题意蕴、奇巧无比的戏剧冲突以及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人们有着“说不尽”的话题。然而我们觉得在曹禺剧作中,似乎还有一层更为幽深博远的思想蕴含在时时引发着人们无尽的思考,这就是曹禺剧作在对人类命运的探幽与把握之间所显示出的独特追求,用他自己在《雷雨·序》中的话说,就是始终怀有一种“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在改编的剧作《家》里,他通过主人公高觉新之口再次发出了对命运的无限慨叹:“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哦,天哪!”实际上,人类命运的难以把握与作者知难而进的力求把握,构成了曹禺剧作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而这冲突才是贯穿曹禺剧作的真正“说不尽”的一个重要根由。
一
曹禺历来不太在意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但却非常在意别人的执导、演出自己剧本时的删改。这大概不仅与他本人有着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有关,而且也与他投入在作品中的思考不易为人“解悟”,甚至常常被人曲解、误解有关。1935年4月《雷雨》在日本首次公演之后, 曹禺在及时表达了对剧本上演的欢欣之余又流露出对导演删去“序幕”和“尾声”的深深惋惜和遗憾,他在《〈雷雨〉的写作》中着意强调了“序幕”和“尾声”的特别重要性:“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推溯这件事,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作为对自己剧作的首次论述,曹禺这段话有两点甚为重要:一是他明确否认《雷雨》是一部社会问题剧,而认为它是一首诗。发表曹禺此文的编者当时在杂志上写了编者按,特意说明“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这又从编者、观众的视角反证了曹禺《雷雨》的创作意图与直接暴露现实、讽刺没落者存在较大的差距。二是曹禺自己明示“序幕”与“尾声”的用意在于引导观众,在回荡着巴赫音乐的“序幕”中“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内,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内。”〔1〕关于这一点曾有论者指出, 这“的确表现了曹禺的艺术思想,主要是‘欣赏的距离说’影响着他”。曹禺后来说:“这是因为看了朱光潜的美学著述的缘故。随着演出的实践,他不再感到割去序幕和尾声是一种遗憾了。”〔2〕虽然这是可信的, 曹禺后来在对《雷雨》修改时也曾亲自删掉了“序幕”和“尾声”。但从上面谈及曹禺当初强烈感到的《雷雨》与观众的距离来看,恐怕这不仅仅是个艺术欣赏的距离问题,而更蕴含着对剧本思想内涵的理解距离。那么,这个“距离”究竟在哪里?或者说,除了对现实的暴露和对没落者的讽刺之外,《雷雨》还要表现什么?还表现出了什么?这是《雷雨》留下的谜。
既然问题出在“序幕”和“尾声”,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两处去看看吧。
较之其他剧作家,曹禺更醉心于场景的交待和描写,有时显然超出了舞台演出的需要而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东西。正因如此,这种场景的描述可能于演出本身并不重要,而于剧本的内涵则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关联。《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正是这样。它们主要是场景的描述和气氛的渲染:远景是一个教堂医院的客厅,并间接交待了这房子是周家卖给教堂医院的;近景则是屋内格局和陈设的特写,这屋内的一切都已“呈现着衰败的景象”,但唯有壁炉上方“空空地,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火焰熊熊地,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映出一片红光,这样,一丝丝的温暖,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画外音是远处教堂的钟声和“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作者强调“最好是”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 时间是旧岁将除新年将至的腊月三十。人物除两位修女看护、两个小孩之外,主要是一位“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的“苍白的老人”即周朴园,他来此看望两位疯了的亲人周繁漪和鲁侍萍。“尾声”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绝望、迷茫的周朴园“坐在炉旁的圈椅上,呆呆地望着火”,与此同时,修女看护“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经读着。”
无需多说,这两幕首尾相贯的场景和气氛太像一首宁静安详、和谐而又凄婉的宗教诗了。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为何作者要精心制造这种浓郁而神秘的宗教气氛,更令人寻思的是作者为何要把周朴园放到这种气氛中去煎熬?尽管是“追认的”,毕竟作者承认了这出剧意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3〕,而作为这个大家庭整个悲剧的总根源, 周朴园及其自身的悲剧结局往往被看作罪有应得。人们普遍认为《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除了周朴园,谁都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恰恰是抖尽周朴园罪恶的作者却没有把他归为千夫所指就此了结,偏偏又让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去忏悔,给了他一份独特的同情。我认为,“序幕”和“尾声”给周朴园加上的这一笔,不仅关系到周朴园这个艺术形象性格和命运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及整个《雷雨》的根本看法。在《雷雨·序》中,曹禺差不多谈到了对所有主要人物命运的看法,唯独没有怎么提到周朴园,所以“序幕”和“尾声”里对周朴园的交待就尤显重要。
与正剧相比,“序幕”和“尾声”中的周朴园早已失去了“昔日的丰彩”、“贵人的特征”,那种“起家立业的人物”的“威严”和“峻厉”也都荡然无存,象征着他“平日的专横、自是和倔强”的那“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均已消失殆尽。现在的周朴园已经是一个忧郁、颤抖、衰弱的苍白的老人,坐在同一把他曾经主宰过一切的圈椅上,默默地承受着命运对自己的主宰。如果说在正剧中周朴园对侍萍多年存留的那一丝情感,对鲁大海悲剧的某种程度的内心自责,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人性浮现,那么在“序幕”和“尾声”中,周朴园则作为一个彻底还原了的人,一个“上帝之子”在接受命运的审判,以虔诚的忏悔来延续着自己的残生。在周朴园命运的轮回变换之中,我们看到的虽不只是简单的30年河西,30年河东,但却深深感受到命运的难以捉摸,感到“天”之主宰的神秘与威严,冥冥之中的报应最终在周朴园身上化作一种“弃恶从善”的力量。尽管曹禺本人否认《雷雨》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但“序幕”和“尾声”里明显的说教意味客观上昭示着因果报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周朴园的忏悔不仅使自身性格趋于“圆型”,而且它升华了剧作的主题:善人的悲剧值得同情,恶人的忏悔更值得深思。
其实,不轻易让罪人死去(死去的也不让其灵魂得到安宁),这是曹禺剧作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朴园如此,《原野》中的焦阎王、《北京人》中的曾老太爷亦都如此。《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不仅通过周朴园的忏悔阐扬了基督教文化的善恶观,而且借助于宗教文化的特质,营造出极富神秘色彩的艺术氛围,增加了一份特有的诗意。与正剧环环紧扣的激烈冲突相比,“序幕”和“尾声”则显得舒缓、平静,教堂悠扬的钟声,时隐时现的巴赫弥撒曲,周朴园近乎自言自语的絮叨,还有那个教堂修女诵读《圣经》的轻哦,这一切似乎把正剧里的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全部溶化了,使人们从侍萍、繁漪、四凤、周冲等人的悲剧中走出来,也从周朴园的罪恶中走出来,去咀嚼、回味更深长、更辽远的问题。显然,这里不仅仅体现了艺术欣赏的距离,更显现出内涵思考的距离:不要把整部《雷雨》仅仅当作一部社会问题剧,还应以更悠深的目光探索人及其命运的本质问题、终极问题。周朴园在“序幕”和“尾声”中的忏悔至少引发人们深思:《雷雨》决不只是周朴园及周家的悲剧,它也是人性的悲剧,因为正是在把握自身命运方面,人类及其本性往往显现了其自身的悲哀和弱点。一个曾经随意支配别人命运的人,其实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而这种变化甚至是顷刻之间的事。对此,曹禺在《雷雨·序》中有过这样的阐述:“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
然而曹禺在《雷雨·序》中又反复申明:“《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天地间的“残忍”和“冷酷”,他甚至说由于周冲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曹禺的这些论述与《雷雨》所表现出的思想内涵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矛盾状况。但正是在这种矛盾当中,我们感到曹禺实际上是在竭力表明一点,即宇宙天地之间的“残忍”和“冷酷”虽然可能蕴含着因果报应,但它们又一定大于因果报应。这又使我连想到曹禺在《雷雨·序》中对人物设计的构想,特别是对周冲命运的论述。周冲这个在《雷雨》人物排名中通常被列为最后的人物,却是曹禺仅次于繁漪之后第二个“想出”的形象,并明言“他也是我喜欢的人”(除了繁漪、周冲母子之外,曹禺还未说过喜欢谁的话),而且还特意提到对周冲扮演者的非常失望:“只演到痴憨——那只是周冲粗犷的肉体,而忽略他的精神。”曹禺为何这样喜爱和重视周冲?这个人物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在论及《雷雨》人物的悲剧时,曹禺特别重视“无过”这个词。繁漪、侍萍、四凤等都“无过”,甚至周萍也无甚“大过”,而周冲尤其“无过”,“他最无辜而他与四凤同样遭受了惨酷的结果”。他对谁都不妨碍,只是“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能了解他的周围。”“他看不清社会,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们。”他是个永远做着“海,……天,……船,……光明,……快乐”之类的“最超脱的梦”的人。所以曹禺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以后那偶然的或者残酷的肉体的死亡对他算不得痛苦,也许反是最适当的了结。”在谈到繁漪悲剧的根源时曹禺说过“只好问”“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那么周冲呢?曹禺没说,只是强调他是一个不断“探寻着自己”的“梦幻者”。其实这就是答案,这就是周冲的“精神”所在,也是其悲剧的根源。在曹禺心里,周冲是清纯和理想的化身,然而正因如此他才处处归于破灭。这才是命运真正的冷酷无情,“这的确是太残忍的了”。所以曹禺在强调命运主宰的同时又对上帝的公正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应该提到的是,周冲这个形象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大戏,而实际上在周冲身上相当程度地投入了作者对社会、人生以至宇宙的某些深刻看法。曹禺对周冲扮演者的期待可能永远难以满足,因为这个人物的戏不在舞台上而在曹禺心里——这的确太难演了!
反复体味周朴园和周冲的命运,我总感到曹禺在《雷雨》中实际上表达出了两层思想内涵:第一层,命运是有主宰的,有法则的,有因果报应的,周朴园的命运是很好的映证;第二层,命运又没有主宰,上帝又是不公正的,因果报应是不能解释一切的,周冲的命运则是有力的说明。而后一层蕴含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赋予了《雷雨》积极、崇高的意义。《雷雨》中的确闪现着“劝善惩恶”、“忏悔赎罪”的基督教色彩,甚至也含有某种人性异化的思想因素,但这些并不是《雷雨》的全部和根本。《雷雨》多层次地展示出这样一对矛盾冲突:命运对人的无情主宰和人对命运的无尽抗争。这是一个近乎永恒的“太大,太复杂”的矛盾,它的存在既决定了人的悲剧的难以避免,也决定了人对神秘命运的“不可言喻”的永远“憧憬”。这个主题很难用一种色彩或一种思想去界定,这个谜很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谜底,它只是作者对人之命运的“辽远”的思索,这或许正是《雷雨》永远迷人的地方。我认为,看不到基督教文化思想对《雷雨》的影响,无疑会限制对该剧思想价值的体认;而把基督教思想解释为《雷雨》的谜底,则又是对扩大了的视角的又一种限制。正如可以说没有“悲天悯人的宿命论思想”很可能就“没有《雷雨》”〔4〕,但决不能说《雷雨》仅仅阐扬了宿命论的思想。
对曹禺来说,《雷雨》的确是个重要而又神秘的开端。此后,对人类根本命运的探究,包括对宗教文化的某些理解,一直在较深的层次上伴随着他的思考和创作,尽管他的目光一刻也未离开过具体的社会现实。
二
相对《雷雨》而言,曹禺在第二部力作《日出》中明显拓宽了生活和艺术的视野,显示了作者新的创意。因此它未经演出,刚在1936年《文学月刊》连载之际就引起了文坛的轰动。所以有人指出:“《雷雨》是直接得益于舞台实践的”,而“《日出》的主题更符合时代的要求,更具有现实意义。它不再是在抽象的哲学意义上探索宇宙的隐秘和人的命运,而是把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与对现实世界的揭露结合起来,不仅控诉了那个糜烂的社会,而且还在漆黑的世界的背后透视出黎明,预示着日出,展现出生命与时代的亮色。”〔5 〕但这种看法又明显走向另一种偏差:似乎从《雷雨》到《日出》,曹禺是从家庭走向了社会,从表现抽象命运转入了剖析具体命运。唐弢先生对此就曾表示过很大的疑问:“我不明白:难道《雷雨》写的仅仅是一个家庭,仅仅是周朴园和他周围的几个人物,而不是同时又是那个正在没落的腐朽社会的反映吗?”〔6 〕我认为《日出》在着力展示现实社会生活画面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人的根本命运的哲学思考,人生的终极价值依然是《日出》所思考的一个焦点问题。
“《日出》里没有绝对的主要动作,也没有绝对主要的人物。顾八奶奶、胡四与张乔治之流是陪衬,陈白露与潘月亭又何常不是陪衬呢?这些人物并没有什么宾主的关系,只是萍水相逢,凑在一处。他们互为宾主,交相陪衬,而共同烘托出一个主要的角色,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虽然曹禺1936年在《日出·跋》中如此突出地强调了该剧的社会意义,但陈白露个人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仍然是全剧的核心,这一点得到了评论者的共识。可是围绕陈白露的命运有两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尚未起普遍重视:一是陈白露的命运呈现出一种难以挣脱的苦难,而这种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悲剧也正是《日出》悲剧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陈白露对自身命运的最终醒悟和抉择,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作者对人生终极价值的看法。
不管说陈白露是一只抗争过、奋飞过,但却“折断了翅膀的鹰”〔7〕,还是说她是一个“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 是一只“关在笼里尚不自觉的金丝鸟”〔8〕, 有一点是令人震颤的:陈白露毕竟从一个“天真可喜的女孩子”,一个“书香门第的小姐”,堕落在人间最“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并且“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了。所以曹禺特别诗意化的用“竹均”这个名字来勾起人们对过去的陈白露的记忆。如果说从竹均到陈白露这个堕落的过程已经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那么从陈白露到翠喜则强烈地暗示出这个悲剧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曹禺极其重视《日出》第三幕的原因。有关第三幕的长期争执也可谓《日出》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谜。评论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尽管这一幕内容很重要,但它于整个剧情是一个明显的“游离”,在艺术结构上是失败的。因此在演出时也常被删去,以求得剧情发展的“紧凑”。而曹禺本人在《日出·跋》中则反复强调自己对这一幕所耗费的“气力”和“苦心”,认为“《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还略具形态。”删去它简直是“‘挖心’的办法”,比《雷雨》删去“序幕”、“尾声”的“斩头截尾还令人难堪。”曹禺作为一个公认的特善戏剧结构的作家,又刚刚总结了《雷雨》结构上的不足,却在《日出》中偏偏写出一幕“游离”剧情之外的戏来,这似乎不太合乎情理。我认为,在第三幕中翠喜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但作者是把她作为陈白露命运的象征来描写的。第三幕陈白露没有上场,也没有必要上场,她的形象、她的命运已经融汇、重叠在翠喜的形象及命运之中。这一幕写的是翠喜的悲惨遭遇,本质上是在交待陈白露的结局。因此,第三幕并不是“游离”,而恰恰是与陈白露的命运有机交织在一起的,是与整个剧情有着内在关联的重要一幕。认识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日出》的艺术结构,更有助于体悟陈白露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与完整性。
无可挣脱的悲剧使陈白露最终面临对自己命运的抉择。有人指出,陈白露“已经决定自杀了,而又忽然向人借起钱来,表明她又是多么的不甘心就死”〔9〕。所以有人作出结论:“‘不想死而不得不死’,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10〕。其实,清醒地、理智地、甚至是主动地去选择死,又何尝不是更大的悲剧!陈白露看穿了周围现实的一切,从方达生对从前的呼唤中又毁灭了理想的一切。因此她可以安然地让自己的灵魂随着太阳的升起去寻求一种解脱了。特别在陈白露极为平静地“一片、两片、三片……十片”数着安眠药片往嘴里放的情景,令人感到这与许地山《命命鸟》中主人公“一步两步三步……”数着步子走向水里的情景实在太相像了!唯有彻底看清了自己的路,看穿了自己的命,才会有这样的抉择和抉择的方式,才会有这份义无反顾的宁静与从容!虽然曹禺说过自己早年“对佛教不感兴趣,大约它太出世了。”〔11〕可他在《日出》里却让自己的主人公彻底“出世”了一回。我总觉得在陈白露身上不仅体现出一种单纯的悲剧力量,而且还隐含着一种对命运难以把握的神秘的力量。有意思的是,那位口口声声地感化陈白露的方达生其实是最看不清楚陈白露的人,而曹禺又偏偏强调“方达生究竟与我有些休戚相关”〔12〕,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作者特意对陈白露悲剧命运的难以把握、难以捉摸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思考空间呢?对于《日出》,人们较多地看到了它从思想主题到艺术结构对《雷雨》的突破与创新,其实《日出》也保留了某些与《雷雨》相贯通的东西,比如命运对人的主宰和人对命运的抗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断突破着、创新着的东西固然重要,但他始终执著追求着、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的东西也许更是不应被忽略的。
三
从《雷雨》、《日出》到《原野》,人们都说曹禺走入了一个他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冒险地闯入现实斗争的天地。可唐弢在《我爱〈原野〉》中说:“‘原野’这个名词意味着多么广阔、多么辽阔、多么厚实的发人深思的含义呵!”确实,如果我们不用“原野”等于“农村”的眼光去看这部剧,可能收获大不相同。
首先应该看到《原野》的创作确与当时的现实斗争特别是30年代蜂涌而起的农村题材创作浪潮的影响有关的。然而这部剧本身却存在着某些明显不和谐现象:作为农民形象的仇虎,一方面是狂热而冷酷的复仇,另一方面在复仇之后陷入极度的恐惧和忏悔之中,以这种极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来展示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太不具有代表性了;作为农村现实生活背景(尤其与当时许多作家笔下热火朝天的农村景象相比),《原野》那“鬼气森森”的房屋、漆黑神秘的森林,也太不典型了。难怪有人说《原野》是农民不像农民、农村不像农村。然而问题很可能就在这为何“不像”上面。
一般认为,仇虎的复仇是《原野》的核心情节,但我觉得,仇虎复仇后的忏悔也是剧情不可分割的核心环节。全剧不得安宁的灵魂有两个而不是一个:除了害人者焦阎王之外,还有一个是被害者仇虎。这就大大增加了剧情的复杂性。如前所述,曹禺不会轻易放过那些罪恶的灵魂,因此焦阎王虽死,但他不可饶恕的罪孽依然要回到他自身,甚至须用他的后代加倍偿还,还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这报应的全过程。所以作者把他钉在墙上,让他死了也要忍受这活活的煎熬。这种安排明显传达出基督教恶有恶报的强烈意识。剧作如果以仇虎杀死大星和小黑子并象征性地朝焦阎王画像连发四枪来结束这场恩怨,那问题就简单多了。可是复了仇的仇虎非但没有丝毫的快慰,反而一下跌入负罪的深渊,杀了仇人反而迷失了自我,感到自己犯下弥天大罪。《原野》是力图揭示恶人终不得善报这个主题的,但作品又隐隐透露出这个主题在当时的社会里不过是个幻象,是难以真正实现的。作者进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这样的问题:被损害的善良之人,报了仇、雪了恨,却又会产生新的惶感不安:这复仇本身不也是在作孽吗?这种内心的折磨、灵魂的拷问太不公平了!虽然这种惶惑不符合一个反抗中的农民的觉悟,复了仇又忏悔,这似乎与当时的农民应有的阶级属性相去甚远,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作者对仇虎命运的揭示已自觉不自觉地远远超出了对一个具体的阶级典型的描写,走向了整个人与命运的对应关系这个更为开阔的主题。惩恶扬善这本来是要表现人对命运的把握的,但随着人物性格及命运的深入发展,愈来愈显示出人对命运的把握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天是没有眼睛的”,在“天”即命运面前,人真是个“可怜虫”,“谁也不能做自己的主”(《原野》台词)。这里应该强调:恨这个“天”,认清看透了这个“天”,并不意味着就把握住了这个“天”。仇虎终究不能逃脱迫害,实际上反映出对这个“天”的无能为力。这里表现的并不是绝对虚无,也不是命运的神秘莫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喻示着人对命运的抗争也许是一个艰难的永恒的主题。这本身蕴含的是一种积极的宗教情绪,而决不是消沉无奈的宗教心态。因此说,仇虎作为一个当时农民的代表可能是不典型的,但从他复仇的全过程去思考人与命运的根本关系则可能更有启发。这个意蕴的确是广阔、辽阔、厚实而发人深思的。
曹禺20岁起即“苦苦地追索着人活着是什么的问题,探求着宗教的奥秘。他有时到法国教堂去参加礼拜,有时去观察基督教的洗礼,参加复活节活动。他领略过教堂静穆的气氛,醉心于教堂庄严神秘的音乐之中。”〔13〕这种青年时代便孕育出的宗教情结不可能不对他的创作产生深刻而重要的影响。的确,从《雷雨》到《原野》,曹禺始终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表现出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这些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力度的作品往往也都蒙上一层很厚的神秘色彩。然而有人说“神秘,是作家找不到出路的产物”,可我认为不尽如此。神秘是曹禺积极思考命运之谜的产物,是给我们留下的更为阔远的思想和艺术的思维空间。至于出路本身,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要求作家一定要找到一条明确的出路,或一定要找好出路后才能去创作,关键是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人们提供了多少可以寻求出路的思路。这个要求已经很不低了。曹禺显然无愧于这个要求。
注释:
〔1〕曹禺:《〈雷雨〉的写作》, 载《杂文(质文)》月刊1935年第2号。
〔2〕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3〕曹禺:《雷雨·序》,载《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年版。
〔 4 〕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5 〕王卫平:《接受与变形——曹禺剧作的主观追求与观众的客观接受》,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6〕唐弢:《我爱〈原野〉》,载《文艺报》1983年1期。
〔7〕陈恭敏:《什么是陈白露悲剧的实质》, 载《戏剧报》1957年第5期。
〔8〕徐闻莺:《是鹰还是金丝鸟》,载《上海戏剧》1960第2期。
〔9〕钱谷融:《谈谈〈日出〉中的陈白露》,载《剧本》1980 年第5期。
〔10〕陈恭敏:《什么是陈白露悲剧的实质》,载《戏剧报》1957年第5期。
〔11〕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载《戏剧论丛》1981年第2期。
〔12〕曹禺:《日出·跋》,载《日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13〕田本相、张靖编著:《曹禺年谱》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