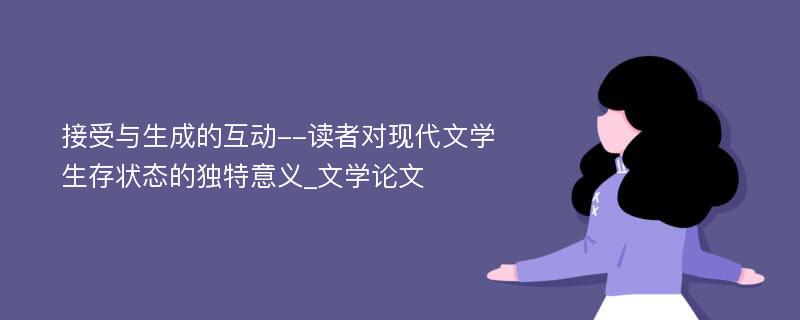
接受与生成的互动——读者对现代文学生存状态的独特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现代文学论文,生存状态论文,独特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6)02-0053-08
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毫无疑问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读者的接受程度也是一个独特的方面,特别是对读者与现代文学生存状态的关系加以整体考察,从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社会化过程考察近现代读者的性质、特点,及其作为文学鉴赏者和文学消费者的二元化身份所带来的文学多样化、商品化特征,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读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复杂的存在。文学史上经常讨论的“读者的大众化”,其实是一种很不确定的文学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众读者不过是作家的理想,而不是一种文学现实。”[1] (P138)
读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
随着中国近代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变和市场消费机制的形成,文学作品除了具有艺术审美特征,也成为“一种工业品”,一种带有“物”的特性的文化“消费品”[2] (P32);而读者除了作为文学鉴赏者,同时又成为文化消费者,文学出版物的购买者。这一事实给文学创作与欣赏的美学关系注入了经济因素,一方面,作为商品的文学必须接受消费者的选择,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实现其交换价值;另一方面,读者的收入状况、生活方式、消费结构、购买能力等,也参加到文学的社会化过程中来,作为鉴赏者同时作为消费者,读者的阅读趣味、需求,常常通过文学市场成为决定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某种关键性因素。
首先,读者的兴趣爱好、消费倾向对文学传播过程中的编辑思想、出版策划以及作家的稿酬标准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茅盾20世纪30年代编辑大型文艺刊物《文学》时就曾感慨道:“事实上,开始‘人办杂志’的时候,各种计划、建议都很美妙,等到真正办起来了,就变成了‘杂志办人’。”[3] (P199)读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的客观存在,常常会借助于市场、社会舆论等外力因素,形成一种巨大的制约性力量,反过来左右编辑的文化选择。“杂志办人”典型地体现了读者市场等出版文化因素对编辑、作家的强制性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读者的意志还会迫使出版物不断做出相应调整。如20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改革《小说月报》的深层隐情,实在是那些旧式文人把持的《小说月报》读者市场萎缩得太厉害了,以致面临赔本,为了生存,商务只得抛弃鸳鸯蝴蝶派文人,根据读者市场需求发表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但到了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走向低谷,读者对通俗作品的阅读兴趣又有所抬头,同样是为了生存,商务再度乘势创办了通俗文学刊物《小说世界》作为《小说月报》的姊妹刊,重新登载旧式文人的作品。无独有偶,30年代《申报》副刊《自由谈》由周瘦鹃转交黎烈文主持后,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但是《申报》不久又增辟副刊《春秋》,仍由周瘦鹃主持,面向市民,以填补《自由谈》改革后留下的真空。这两次民国最重要的报刊的改组和再改组,都充分地印证了茅盾“杂志办人”的论断,对于本质上属于经济活动的现代出版业来说,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
出版机构给予作家的稿酬虽有一定的标准,但也常会随行就市。如张恨水20年代中期连载《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作品时,“他的小说也不过只卖到四、五元一千字,有时只有二、三元一千字”[4] (P131),但30年代初《啼笑因缘》在上海一炮打响后,张恨水的小说“千字卖八元,还是你抢我夺。连早在北平出版过的旧作《春明外史》,也由世界书局出了千金的版权费收买下来,重行刊布”[5] (P346)。不同作家间这样的情况就更是常见,林纾的翻译较近代其他作家的稿酬要高,梁启超的稿酬也享有与一般作者不同的标准。梁启超2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与商务“六折算账”,不仅收取四成的版税,还得到每千字20元的稿费,这是当时高梦旦准备拉拢郭沫若而给他和《创造》稿费的5倍。[6] (P206)
其次,读者所代表的市场关系对作家创作及生存的影响也是直接而深刻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大众生活》杂志上曾发生过的一段趣事:茅盾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腐蚀》自1941年5月17日开始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连载,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读者们最为关注的一点,就是作为女特务的主人公赵惠明,她的命运结局将会如何(或者说将应该如何)。不少读者纷纷给编辑部写信,强烈要求应该给赵惠明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而不希望让她走向死路。广大读者这样一种热情的关注和急切的愿望,无论对连载《腐蚀》的《大众生活》编辑部,还是对作家茅盾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和压力。为此,刊物编辑部专门召开了一个由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多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后,将大家的发言作为《大众生活》杂志的编辑后记予以发表。其中,夏衍在座谈会上还特别提到一个日本现代作家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广大女读者深受小说感染,纷纷来信要求作家不要让女主人公最后死去,但作家最终还是让女主人公死去了,这一结局致使当时很多女性读者纷纷为女主人公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所有这些,对当时尚在继续创作《腐蚀》的茅盾有着很大的震撼,茅盾最终“被迫”接受了大家的要求,终于“给了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①。这段趣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作家创作在发表过程中所受到的读者多方面的有时甚至是深刻而重大的影响,至于那些因为没能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而导致写作失败,出版无名,被埋没在历史的封尘中的作家、作品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读者在文学社会化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意味着文学与市场联系的进一步紧密。文学与市场关联的建立,其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有效的商业化运作,能够真正地促成文学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使文学精品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读者、市场作为经济因素又与纯文学有着天然的矛盾,会对作家的审美精神自由产生很大妨害。从这一角度,叶圣陶就主张:“凡为文学家,必须别有一种维持生计的职业,与文学相近的固然最好,即绝不相近的也是必须,如此才得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不致因生计的逼迫而把它商品化了。”[7] (P61)有意味的是,叶圣陶的话与当年鲁迅和老舍反对作家兼职的言论恰成反调。但本质上,他们三人的观点彼此却并不矛盾。作为不同的创作主体,他们从各自的经验和生活实感出发,指出了使作家的创作自由不受侵害的种种办法。鲁迅和老舍认为,作家兼职不仅占用写作之间,影响写作质量,而且写作还会受到所从事的其他职业的潜在影响;叶圣陶主张作家应该在写作以外有其他的职业作为经济基础,则是从职业作家该如何抵制商品化的侵袭这一角度提出的建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读者与文学的通俗化
作为消费者的读者,在市场中不再是被迫地去接受某种文化,而是在众多的“商品”中挑选最能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一种,其欣赏口味和阅读层次的多样化特点,客观上促成了现代文学的多样化格局。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样化不仅体现在整体格局上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并存,而且也体现在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内部,不同的文学样式、流派手法各有各的读者,各有各的市场,始终处于共存状态。
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通俗文学的批判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但事实上,新文学代表的文学主流并没有获得改造“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胜利,“鸳鸯蝴蝶派”也没有因为新文学的抵制和痛斥而退出历史舞台。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始终共生共存着,这正是文学的市场化机制作用的结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新文学的主要读者对象;市民则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后者拥有比新文学更为广阔的市场,并且在创作和销售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新文学。即使是在新文学如火如荼地兴起并取得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以后,通俗文学仍然呈现出坚强的生存和竞争能力。难怪连批判“鸳鸯蝴蝶派”最为有力的茅盾也不得不承认:“事实是,二十年来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者所否定,还没有被新文学所否定,更没有被大众所否定。”[8]
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群——市民大众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从总体上表现出认可“现代化”进程的心理趋势,但“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中国市民大众在社会变革中文化心理的相对滞后性,又使他们在精神意识的深处有着相当浓厚的封建色彩”[9] (P206)。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市民读者的文化程度也是有限的,他们还保留着喜欢阅读“游戏”小报和“醒世”闲书,喜欢看悲欢离合、大团圆故事,寻觅茶余酒后谈资的欣赏习惯。读者大众总体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使得出版业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增强作品的趣味性,降低阅读难度,选择时下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并不断变换结构技巧,这样的需求为通俗文学的大量滋生提供了土壤。
与新文学不同,通俗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为游戏的和消遣的性质,就把自己当作商品,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随着市场的节奏,形成一定的流行规律,体现出“趋时附新”的新潮性特色。[10] (P380)随着社会思潮的起伏,通俗文学作品的题材、体裁、形式等都会趋奉时尚而不断革新、变化,如同所有时尚商品一样体现出潮流化的批量生产的特征:一部小说一旦畅销,其他小说家便趋之若鹜,竞相仿效;一位作家一旦成为畅销作家,便连篇累牍,不断炮制同类作品。“有时是哀情小说成了潮,有时是社会小说成了潮,有时又是武侠小说成了潮,……一个潮起来,‘五光十色’、‘如火如荼’,过了一个时期,退潮了,也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又换了一个潮。”[11]
与新文学作家不同,通俗文学作家很少有新文学作家那样强烈的启蒙意识和先锋意识,取而代之的是鲜明的市场意识。通俗文学作家懂得为小说商品市场——市民读者的欣赏兴趣写作。他们并非没有道德,但他们的道德观认为:“文学商品化是天经地义的,这丝毫不会亵渎文学。”[12] (P5)在他们看来,好的小说的标准就是能让读者爱不释手,“读者不看本志则已,看了以后,一定不肯失去了一期不看,——换一句话,每期都有可以一读的价值,那,读者自然会一心一意地想着它,不愿失去一期不看了”[13]。他们决不会像有些新文学作家那样有意无意间忽略作者的存在,或是只注意自己的作品,而忘却了读者。
与新文学相关,五四以后,有不少“鸳鸯蝴蝶派”作家以其娴熟的写作技巧,游刃有余的故事情节,轻而易举地开始了新文学题材的写作。他们也关注家庭冲突、妇女问题,甚至涉及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对当时的新文学构成了相当的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大环境的迫使下,对新文学实行了“文体的投降”,采用白话,“又大致摒弃了‘聊斋’式或纯章回体的叙事模式”[10] (P462),在作品的整个艺术构思以及表现的技巧方法上向新文学作品接近。30年代以后,通俗文学还开始在内容和形式上趋于雅化,这一方面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使然,另一方面,如果从市场的角度去分析,则是通俗文学对向着“中产阶级”趣味转变的新兴市民社会的一种主动跟进。
张恨水作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领域的代表作家,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完成了约3,000万言的作品,在他的上百部小说中,有很多不仅作为当时的畅销书而家喻户晓,即便在今天的读者中也仍然大有市场,堪称经典。这与他写作“追求入时”、“内容、思想随时而变”的一贯作风有很大关系。[14] (P215)继《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在北平产生轰动性影响以后,张恨水又针对上海等南方读者的口味,创作了《啼笑因缘》。1929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北上,张恨水经钱芥尘介绍,认识了《新闻报》编辑严独鹤。严独鹤看到张恨水的新作,也听到他在北平的声誉,约他为上海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写一部连载小说,张恨水欣然应允。张恨水知道,上海乃中国通俗文学大本营,那里的读者生活环境与北平不同,“北平近官,人们对官场风云的关注,社会黑幕的兴致很大。而南方近商,讲究通俗文化的娱乐性、趣味性”[12] (P241),于是他对自己的写作策略作了一番调整:重点设计了“言情”故事,再加一些“武侠”传奇,使小说熔社会、言情、武侠于一炉。结果,《啼笑因缘》在上海一发表即引起读者注意,《新闻报》销数直线上升,张恨水也成为《新闻报》的“财神”。严独鹤后来在为《啼笑因缘》单行本作序时回忆了它连载时的盛况:“在《啼笑因缘》刊登在《快活林》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欢迎了。至今书虽登完,这种欢迎的热度,始终没有减退。一时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之能使读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15] (P2)老舍也赞叹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16],这一评价似乎还没有哪一位新文学家获得过。
对于新文学始终难以实现的大众化问题,通俗文学作家也从自身的经验中提出了一些看法。张恨水就说过,“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17]。他同时还表示,“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般人工作”[17]。对消遣性和趣味性文学的需求,客观上形成了庞大的市民文学市场,维系了通俗文学持续不断的生命力;而新文学自觉与游戏消遣划清界限,与“趣味”断绝联系,等于主动放弃了巨大的市民读者群,在客观上帮助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成功。
读者与文学的市场化
如上所述,现代文学走向“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某些变异,发展到极端,即演变为严重的媚俗倾向。这种情况无论在近代还是现代,无论在通俗文学还是新文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民初职业作家出现以后,小说的商业化倾向日益严重,传统固有的鄙视小说的态度与卖稿赚钱的“拜金主义”相结合,助长了一股粗制滥造的风气。当时的文人就曾写下一段气愤而又无奈的话:
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遽出以问世,如《水浒》、《红楼》等书是已。今则不然,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即已无人顾问。盖操觚之始,视为利薮,苟成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于愿已足,虽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甚有草创数回即印行,此后竟不复续成者,最为可恨。[18]
媚俗倾向在新文学的部分作家中也典型地存在着。20年代末到30年代,张资平、叶灵凤等引发的“性文学热”虽然遭到新文学主流的强力抵制,但仍然在市场上泛滥开来,正是读者的某种接受意识所致。性意识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潜在影响和作用,显然有着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更为深层的时代动因。1926、1927年分别出版了《飞絮》和《苔莉》两部长篇并以其中的性描写而吸引了大批读者之后,张资平的作品持续好几年行情一直看涨,光《飞絮》一书就行销了数十版,读者数量之多在当时是少见的。如果把当时那么多读者愿意读张资平的作品仅仅归结为读者的情趣低下,那就简单化和片面化了。读者数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象,掩隐着多层次的社会内容。对作品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是读者对自己的理解,同时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自己的解释。当时读者对张资平作品性意识描写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的确与他们自身对性意识的强烈关注和真切感受密切相关,这是无须回避的。其中,也并不排除因张资平的性挑逗而导致一些读者从中寻求一时的感官刺激。其实这本身就蕴含着特定的时代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中国历史长期对性文化、性意识的禁锢,不仅加剧了人们对性的好奇心和神秘感,而且形成了人们的一种潜意识的逆反心态。尤其是中国千百年来层出不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的巨大压力,强化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某种变态心理。因此,许多人读到张资平的作品,尽管都是千篇一律的题材,单调乏味的故事,但还是接受了。与其说读者对张资平的作品有兴趣,不如说他们对自己更有兴趣,对自己需要的性意识更有兴趣;与其说张资平的作品是故意的“性的展览”,不如说它是读者对性意识的自觉追寻和无意识的契合。
张资平曾经拥有过那么多的读者,他是幸运的;但是读者却从来没有在他的作品里产生过强烈的审美感受,他又是悲哀的。更可悲的是,他自己也并不理解读者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真正内涵,所以,在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上他陷入了困境。从接受的意义上说,作家创作的潜意识既受控于读者又得力于读者,这本是一种激发作家创造力的积极心态,而张资平却误解并误用了这一读者机制。他是有生活的,也不缺乏才华,甚至在开始创作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追求和个性的。所以郑伯奇说过,在初期创造社作家中,“张资平最富于写实主义倾向”,他的“写作态度是相当客观”的。[19] (P2)但是当他看到自己的作品越来越有市场的时候,便开始竭力迎合读者需要,并很快发展为大量的粗制滥造。这种丧失了作家使命感的编造显露了张资平小说的特有困惑和矛盾,尤其在人物性心理的描写方面,这种困惑和矛盾显得更为突出:男人们一方面表现出那种雄性动物特有的占有欲,并多方面表明这种占有欲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又始终有一种摆脱不了的负罪感,总是在下意识里不停地忏悔自己深重的罪过。女人们则一方面无力地重温着多少年来的道德规范,恪守着早已不存在的美德;另一方面又总是在内心深处燃烧着主动的欲火,并时常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因此曾有一些评论者对张资平笔下的女性所表现出的不可压抑的疯狂性欲及对男性的主动追逐大加抨击,并指出这种描写的不真实、不现实,是完全图谋实利的人为编造。其实并不完全这样。这种客观上的不真实,张资平本人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纯粹出于谋利,他尽可以在这方面编造出大量的“更真实”、“更现实”的东西,为什么偏要编造这些一眼就能看出破绽的东西呢?显然,这里有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矛盾:他想尽可能地编造出“更真实”的东西来迎合读者,但潜意识告诉他,似乎只有这样写,才能表现出女性在长期压抑之下比男性更深广的性苦闷。应该说,这确实是“更真实”的东西。实际上,在人物性心理的矛盾反差之中,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沉淀着张资平对传统性文化的认识,沉淀着他对时代发展和现实变动的理解,沉淀着他在传统文化与现实变动相冲突过程中的矛盾。对张资平等某些新文学作家的媚俗化写作,从市场的诱惑和驱使的角度去理解,做出的阐释就合理多了。
读者与批评家的互融
在读者当中,还有一特殊的群体,就是批评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已经与作家作品本身一起成为重要的文学内容。不论是巴金编辑、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还是赵家璧主编、良友图书公司印刷发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等,都将文学批评作为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并列的一个门类而列入其中,可见对于批评的重视由来已久。事实上,有很多名字因为与文学批评相联系而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并与诸多一流作家并驾齐驱。如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20] 中作为重要“景点”而选入的14位批评家:王国维、周作人、成仿吾、梁实秋、茅盾、李健吾、冯雪峰、周扬、胡风、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李长之和唐湜,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同时从事创作,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如周作人、茅盾、沈从文等,但他们同时又以批评文字见长,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作为批评家,他们一般都对文艺抱有一份热爱甚至是敬爱,他们浸润于艺术之中,“所论证的问题是经过多年研究的,提出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他坚定地相信应该是这样而不应该是那样的”,“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合理解决必将大大有益于文艺事业的发展,他为此而激动”。[21] (P2—3)他们的批评无论从个性与特色方面,还是从产生的实际影响方面来看,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历史内容。
对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生产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将其与文学评奖放在一起,从文学的“评价机制”[22] (P239)角度给予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如认为书评是“著述、出版、阅读之外的第四个系统,也是前三个系统的中介”,“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反馈功能和引导功能”[22] (P240)等;但我们想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书评,因而其功能也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社会流通过程中的“反馈功能”和“引导功能”,其对于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的发展来说,更主要的功能和意义在于一种审美的和为艺术本身的价值评判,“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创造”[20] (P1)。如众所周知的关于郁达夫《沉沦》引起的争议及争议的平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学批评家帮助大众读者铺就了认识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之路,从而为作家作品确立了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问世以后,其独特的题材、人物,独特的抒情性以及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立即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关注,如茅盾在写于该小说集出版后不到四个月的一封“通信”中即指出《沉沦》中的三篇,“除第二篇《银灰色的死》而外,余二篇似皆作者自传”,首先对《沉沦》进行了“印象式的批评”;但茅盾同时也认为,“作者自叙中所说的灵肉冲突,却描写得失败了”。[23] 关于小说所表现的所谓“灵肉冲突”问题,日后成为读者和批评家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小说中直露的“色情”描写和“颓废”倾向,更是招致了许多非议,“诲淫”、“不道德”等批评甚至责骂一齐向郁达夫包围过来。郁达夫自己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社会上因为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百次。”[24] (P329)第一个站出来对郁达夫小说作肯定性评论和客观解析的是周作人。在一篇署名仲密的文章中,周作人开篇即对读者和评论界某些人认定《沉沦》为“不道德的文学”的调子进行了纠正:“我在要谈到郁达夫所作的小说集《沉沦》之先,不得不对于‘不道德的文学’这一个问题讲几句话,因为现在颇有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小说。”[25] 周作人援引英国莫台耳(Mordell)《文学上的色情》一书中对于“不道德的文学”的界定,指出郁达夫的小说不属此列,《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只是“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说与颓废派的著作,大抵属于此类”。[25] 在文末,周作人再一次郑重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25] 在这里,周作人用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坛出现的新人新作,并用他一贯的广博的知识向文学界以及读者指出了对于《沉沦》的正确解读之路,不仅帮助《沉沦》厘清了非议,而且其对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而非一般人的读物”的高度赞誉,对于《沉沦》文学史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批评家作为一种特殊读者的介入,还常常会使文学作品产生某种特殊的效应:作品因批评而声名鹊起,批评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文本本身的价值。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艺理论集一》[26] 的“作品批评篇”中由易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华汉(阳翰笙)所写的《〈地泉〉五人序》被作为新文学第二个十年重要的“作品批评”赫然列入其中。同一部小说前收入五人为之作的序,而且都是当时有分量的批评家,这首先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阳翰笙以华汉的笔名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30年10月由平凡书局出版,作品本身思想和艺术都不是很成熟也不是很成功,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论争;该书1932年7月由“左联”的湖风书局重新出版时,书前增加了易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的四篇序言以及作者本人的重版自序。这五篇序言共同围绕着小说诸多“失败之处”展开了批评,并将其作为1928—1930年间所产生的一批“革命+恋爱”小说和“革命文学”中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它的分析进而对当时同类的作品和作为一种“风气”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随后,在围绕《地泉》所展开的关于普罗文学的讨论中,《地泉》重版时的这五篇序言不仅对认识《地泉》本身,而且对推动整个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都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有很多读者都是通过《〈地泉〉五人序》而知道《地泉》和阳翰笙的,这五篇序言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地泉》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在作为批评家的读者当中,还有更为特殊的一类人,就是作家自己。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又有着一般读者包括其他批评家都无法代替的作用。隐藏在作家内心深处的创作动因、审美追求以及作品的主旨,等等,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正所谓甘苦自知。比如曹禺的第一部话剧《雷雨》问世之后,无论是编、导、演还是读者、观众乃至专业批评家,都几乎一致地认为这是一部暴露上层社会大家庭罪恶的社会问题剧,然而曹禺本人却不但不认同《雷雨》是一部社会问题剧,而且超出任何人的想像,他发出了与所有人都不同的见解:《雷雨》“是一首诗”[27],是“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28] (P2)。应该说,这样的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解读和批评也只有作为“零距离的读者”和“第一读者”的作家自己才能够做得出来。而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作家同时作为读者和批评家的这个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也是无法被取代的。
注释:
①上述材料参见孙玉石为孔海珠《聚散之间——上海文坛旧事》(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所作的序《上海文坛的疑云旧迹》和杨建民:《〈腐蚀〉:读者参与创作的名著》(《文学故事报》2004-04-26~2004-05-02)。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艺术论文; 张恨水论文; 茅盾论文; 啼笑因缘论文; 读书论文; 雷雨论文; 张资平论文; 春明外史论文; 腐蚀论文; 新闻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