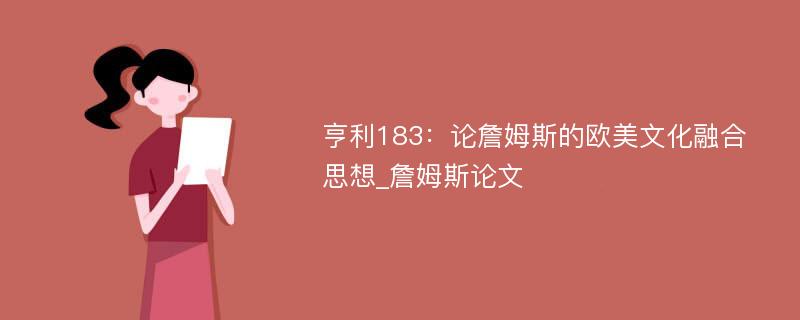
亨利#183;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詹姆斯论文,亨利论文,刍议论文,思想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下半叶,美国虽然在政治和经济实力方面跃居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之首,但在文化领域里仍然没有摆脱殖民影响,这是许多美国思想家都意识到的事实。1884年,美国学者亨利·卡伯特·洛奇在他的《美国国内的殖民主义》一书中指出,尽管美国的财富与日俱增,但美国的文化却没有什么建树。(注:亨利·卡伯特·洛奇在《美国国内的殖民主义》一书中说:“物质财富的增加产生了奢望,高等教育的发展孕育了精神上的品味,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使许多人滋生了对外国生活和外国风格的爱慕。这种倾向和机会使得快要灭亡的殖民怀旧又重新复活。……许多受了过多教育并且丧失了国格的美国人或是在欧洲,或是在美国,以殖民地精神做画、搞雕塑和作曲,完全受卑劣的思想所支配……有时,这类人成为勉强有成就的法国艺术家,但他们的国格和个性全没有了,独创性和力量也随之不复存在。”——转引自布尔斯廷《民主的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 第570—571页。)美国诗人惠特曼也在《民主的远景》( 1871)中痛心地说,“严格地讲,这个国家可能还根本没有文学”。 (注: WaltWhitman,Democratic Vistas,quoted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American Literature,third edition,vol.1,part 3,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9,p.2095.)里查德·布罗德赫德在《文学与文化》一文中说,“美国继承的是一种殖民地形态的文化遗产:即使在政治独立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还在继续不断地从英国输入文学作品,并且照搬他们评论这类作品的一整套批评概念和术语。”(注:查德·布罗德赫德“文学与文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埃默里·埃里奥特主编,朱通伯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美国文化不仅被笼罩在欧洲殖民文化的阴影里,而且还遭受本国商业文化的侵蚀。在兼有宗教和商业精神的美国,“虔诚而有益的书籍”被认为是“有学问的人应该拥有的全部藏书”,(注:布尔斯廷《开拓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 342页。)而艺术的审美与优雅,对于这个国家的普通读者来说则是闻所未闻。因此,如何在欧洲文化的压迫和美国商业文化的浸染下,营建一种理想的美国文化模式,便成了整个19世纪美国学者思考的主题和努力的目标。身处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美国现代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HenryJames,1843—1916)当然也对这个重要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写下一系列欧美主题小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本文拟就詹姆斯早期的几部欧美主题小说,对詹姆斯关于欧美文化融合的重要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他对美国文化的建设所起的作用加以评说。
一、文化融合思想的产生
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的产生,源于他对美国文化匮乏状况的不满,和对欧洲文明中“审美”与“经验”的认同,其中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对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文化融合思想的借鉴。
1843年4月,詹姆斯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父亲——美国哲学家和神学家老亨利·詹姆斯——在把金钱转变成知识和精神财富方面,给下一代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詹姆斯从小即随家人往返于欧美大陆,承受欧洲文明的熏染,对欧洲文化情有独钟。古罗马的雕塑艺术和竞技场,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博物馆,以及贵族社会充满高雅情趣的休闲、社交活动,都在詹姆斯的心目中反衬出美国文化的匮乏与粗俗。
1869年,詹姆斯第一次作为成年人到欧洲旅行,他在给哥哥威廉·詹姆斯的信中,谈到了对欧洲的美国人的印象:
对他们只有一个词——庸俗,庸俗,庸俗。他们的无知——他们对欧洲的一切表现出的小家子气、抵触和对抗——一事当前,他们永远要用某种只存在于他们毫无顾忌的吹牛聊天中的美国标准或先例去衡量——于是我们蹩脚而贫乏的谈吐、声音和嘴脸——这些东西可怕地盯着你。(注:Quoted in Leon Edel,Henry James,A Life,New York:Harpe r & Row,Publishers,1985,p.101.)
詹姆斯对美国人在欧洲的粗鄙表现出的厌恶和批评,显然是基于他对欧洲社会的礼仪、智慧和文化修养的认同。在这方面,他似乎和法国政治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一样,也认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必须要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托克维尔看来,培育文学的沃土是贵族制而不是民主制,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因为“一种事物越久远,通常也越使人觉得壮丽和宏伟,并在这种思古幽情的影响下,使它更适宜于产生供描写的理想对象。”(注: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4页。)
詹姆斯对美国文化状况的不满,也许最集中地体现在他1979年出版的《霍桑传》中。在这本书里,詹姆斯几乎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开列了一份美国缺少文化的清单,这成为美国批评家和爱国人士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不能原谅他的缘由。詹姆斯这样描述美国文化的匮乏:
没有君主,没有宫廷,没有个人忠诚,没有贵族,没有教学,没有牧师,没有军队,没有外交部,没有乡绅,没有宫殿,没有城堡,没有庄园,没有古老的乡间宅地,没有牧师住所,没有茅草屋顶的村舍,没有长满常春藤的废墟,没有大教堂,没有修道院,没有小型的诺曼底式教堂;没有名牌大学,没有公立学校——没有牛津,没有伊顿公学,没有哈罗公学,没有文学,没有小说,没有博物馆,没有美景,没有政治团体,没有娱乐阶层——没有埃普索姆的跑马场,也没有埃斯考特赛马场! (注: Henry James,Hawthorne,ed.John Morley, 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09,p.43.)
显然,欧洲不缺少这些在詹姆斯看来孕育“审美”与“经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机制。正是对欧洲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才使得詹姆斯发现了美国文化的欠缺所在,产生了融合欧美文化的思想。
然而,詹姆斯对美国并非一味地排斥、否定,而是有所取舍的。早在1867年时,在文学界还只是无名之辈的詹姆斯就决心用自己的努力来填补这一空白。他在给好友T.S.佩里的信中曾这样描绘自己的远大抱负:
我们年轻的美国人是未来的人。我觉得我惟一成为批评家的机会就是让西方的和风尽情吹遍我的全身。我们生来是美国人——应该承担起这个职责。我视此为一大幸事;我认为当美国人是接受文化的极好前提。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有优秀的品质,事实上,我似乎觉得,我们站在欧洲民族的前列,我们可以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能自由地对待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形式,我们可以采摘、挑选并消化吸收它,简而言之,不管在哪里发现,我们都可以将它认作自己的财产。没有民族标志是一种遗憾和落后,但我觉得美国作家表明世界上不同民族在志趣和智力上的大融合和综合也不是不可以的,并且,这种融合的状况比我们所见到的成就更为重要。当然,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既是同一民族又是与众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将在我们的道德意识、我们史无前例的自由精神和活力中找到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至少应该有民族的标记。(注:Henry James,The Critical Heritage,ed.Roger Gard,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868,pp.22—23.)
在这封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詹姆斯欧美文化融合思想的雏形,而且也可以看出詹姆斯对待美国的客观态度。他的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理想是建立在对美国优势充分认识和肯定的基础之上的。美国传统中的“道德意识”、“自由精神”与“活力”便是美国站立于其他民族前列、借鉴和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分的前提。
由于对美国文化匮乏状况的不满以及对美国自由精神与道德力量的肯定,詹姆斯与阿诺德的文化整合理论产生了共鸣。按照阿诺德的文化整合理论,理想的文明形式应该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融合。只有两者的合璧和平衡,才能达到“人类的完善或拯救”。阿诺德给两者的定义分别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意识的自发性;而希伯来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良知的严谨”。也就是说,希腊文化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认识事物”,代表着“智性”、“思考”与判断力”;而希伯来文化——一种基督教文化,则意味着“行动与顺从”,代表着“道德”、“自制”、“责任”与“行动”。(注:Matthew Arnold," Hebraismand Hellenism",Culture and Anarchy,chapter Ⅳ ,Ann Arbor,The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pp.163—175.)
针对盛极而衰的欧洲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过度地张扬人性和审美,而相对忽略了对道德和理性的重视,阿诺德提出了文化整合思想。他认为,英国文化传统中具有希伯来文化的道德内涵,可以为欧洲文明的衰竭补充新鲜血液,但缺少高尚与审美是它的最大不足。正如阿诺德清醒地认识到了英国文化的优劣,詹姆斯不仅认识到了美国粗鄙的一面,而且把美国的自由精神与道德意识作为他文化融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阿诺德和詹姆斯虽然从提高各自的文化水平出发,但他们思想的结晶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但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与阿诺德的文化融合思想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就连阿诺德经常使用的一些词语,也反复出现在詹姆斯的小说中。比如,《罗德里克·哈德逊》中的主人公哈德逊就自称是古希腊文化的崇拜者;《美国人》中的特里斯坦夫人称纽曼是一位了不起的西部“野蛮人”;(注: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的第三章题名为“野蛮人,市侩,平民”(Barbarians,Philistines,Populace)。 )阿诺德把“诗和文学”统称为对于“生活的批评”,而詹姆斯经常把他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叫做“生活的批评家”,等等,詹姆斯对阿诺德文章中这些词语的沿用绝不是无意的巧合,似乎更是一种认识上的趋同与吸收。(注: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thew Arnold and Henry James,consult Alwyn Berland's
Culture andConduct 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从詹姆斯的大部分欧美主题小说中,我们更可以看出,他心中理想的美国文化正是建立在对美国传统的继承和对阿诺德文化融合思想借鉴的基础之上的。
二、文化融合思想的体现
詹姆斯的欧美主题小说尽管在内容上千差万别,却可以寻出一个大致的趋同点,那就是:单纯、善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乐观自信的美国人,带着对欧洲古老文明的向往和憧憬走进一个异己社会,当然,也带着他们典型的新世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然而,在欧洲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复杂环境中,他们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与困扰,最后大多美梦难圆,或者魂归西天(如罗德里克·哈德逊和黛西·米勒),或落魄而去(如纽曼)。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主人公在欧洲社会理想的失败,既凸显了美国个人主义思想的局限,说明了欧美文化缺一不可的事实;同时也让人们看到,真正要使两种不同的文化水乳交融是多么困难。
在詹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德里克·哈德逊》(Roderick Hudson,1875)中,他试图用一位美国艺术家的夭折揭示,在欧洲文化的压迫和美国商业文化的侵蚀下,美国艺术家面临双重身份危机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处理欧美文化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危机下确立自己的身份。主人公哈德逊——一位艺术天分很高的年轻雕塑家,因为丢失了美国传统中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丢失了清教文化的吃苦耐劳精神,人为地割裂了欧美文化之间的联系,从而迷失在欧洲辉煌的文明中,不仅荒废了自己的艺术天才,而且对身边的亲人——母亲、未婚妻和监护人,也都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
哈德逊一到罗马,便急于摆脱美国文化传统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从外表装束到精神气质都一律向欧洲看齐。不久,他爱上了19世纪末欧洲文化美与颓废并举的象征——克里斯蒂娜·莱特,把他在美国的未婚妻——新英格兰文化的道德与坚贞的象征——玛丽·加兰,抛在脑后。当他发现自己的艺术灵感衰退时,他不是恪守清教传统所倡导的踏实、苦干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而是守株待兔,被动地等待灵感的降临;在感情上,沉溺于美色的哈德逊喜新厌旧,不仅背叛了他的未婚妻,甚至用自己的绝望和颓废尽情地伤害了关心他的每一个人。美国传统中的道德意识与责任感,清教传统的坚韧不拔和隐忍自制对哈德逊来说都荡然无存。
艺术家放弃美国传统严谨的道德意识与责任感,一味追求感官情欲的满足,就不能冷静地观察、把握和反映生活,这是哈德逊留下的一大教训。詹姆斯的创作正逢美国内战后物质主义猖獗、欧洲唯美主义盛行的时代。如何避开物质主义的粗俗和唯美主义的颓废,还艺术与文化以严肃、纯洁的品格,这是詹姆斯用哈德逊的教训探讨、思考的问题,也是他融合欧美文化的主旨所在。对此,詹姆斯以他第一部小说《罗德里克·哈德逊》作一个初步的回答,即:欧美双方的文化对于一个理想的艺术家来说是缺一不可的。
在詹姆斯看来,融合欧美文化不仅是美国艺术家摆脱双重身份危机的出路,而且也是每一个缺少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人摆脱浅薄和粗俗、走向高级文明的必经之路。因此,在詹姆斯次年发表的第二部小说《美国人》(The American,1886)中, 追求欧美文化的结合仍然是他的主人公旅居欧洲的最大愿望。但稍有不同的是,这一次,詹姆斯选择了最能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特点的实业家作为他小说的主人公,进一步探讨欧美文化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纽曼那强壮的体魄,诙谐的言谈,慷慨大方、自信得近乎盲目乐观的性格,甚至连他的名字(Newman)都体现着詹姆斯心目中那个美国的概念:缺少文化,但却充满了天真的道德意识和新鲜活力。与哈德逊进入欧洲文化氛围后竭力要摆脱美国传统的表现不同,纽曼不仅热爱他的祖国,而且笃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恪守美国人的一套价值观,天真地相信,只要口袋里装满了钱,整个欧洲就会为他而存在。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大市场,有钱的人可以任意徜徉其间,自由挑选他们喜欢的商品。甚至,纽曼把选择妻子也比作要“得到市场上最好的货色”。
然而,纽曼虽然完整地继承了美国的一套价值观念,但由于他缺少对欧洲文化的体察和修养,也由于不同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他在文化寻梦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初到巴黎,纽曼就因为文化上的欠缺——审美判断能力缺乏,错把三流画家洛埃米当作落难的艺术大师顶礼膜拜,并慷慨解囊给予资助,结果反遭到洛埃米的戏弄和嘲讽。纽曼在短短一年中,遍访欧洲的几百个教堂、古迹和画廊,然而,对这样一位没有文化、毫无审美能力的人来说,到底从这种走马观花似的游览中得到了多少知识的提高和艺术的陶冶,实在值得怀疑。而这次巴黎之行的最大不幸恐怕就是他的那场求婚风波了。
自信乐观的纽曼希望通过婚姻来实现他的欧美文化融合梦。他向一位贵族小姐求婚,然而,由于不了解欧洲的诡秘、含蓄,毫无生活经验的纽曼在巴黎贵族贝勒伽德一家人面前出尽了洋相,屡屡把贝勒伽德母子的挖苦、嘲笑当作充满善意的玩笑而欣然接受,甚至最后贝勒伽德家突然反悔,撤回婚约,他仍然不识对手的奸诈。对纽曼来说,贝勒伽德家的每一个人,正如他们身后的文化一样,都是难解之谜。哈德逊与纽曼文化梦的双双破灭,从主观上讲,都是由于他们自身没有同时兼有欧美文化的优秀成分,并使之达到有机融合的结果。
同样,世纪末正在走向没落的欧洲贵族文化也不能缺少美国新生力量的补充。贝勒伽德家族代表着19世纪末期衰败的欧洲贵族文化,它虽然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富丽堂皇的外表,但它的观念到世纪末已变得陈腐荒谬,贵族家庭内部也已经道德败坏、徒有虚名了。美国来的新人虽然粗鲁无知,但贵族文化需要补充的新生力量恰好在代表美国文化的纽曼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纽曼年轻有为,无拘无束,他是自己的主人,充满自信与活力,他不必像克莱尔和瓦伦丁一样在权威和传统观念的阴影下枯萎、凋谢,而总是以现实存在的真伪作为是非判断的惟一标准。
哈德逊的不幸和纽曼的挫折充分显示了融合欧美两种文化的必要性。纽曼在欧洲遭遇不公时表现出来的道德力量与自由精神,贝勒伽德一家体现出来的含蓄深沉和堂皇的仪表,如果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必将使人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
三、文化融合思想的羁绊
尽管詹姆斯热情提倡欧美两种文化的融合,但他也意识到了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的困难。当他的兄长威廉·詹姆斯在国外呆了一个时期归来,对他谈及美国生活“贫瘠的方面”时,亨利的回答是:
我1870年5月从欧洲回来时, 就有一种强烈而永远不会忘却的感觉——在那死气沉沉的日子里,我对自己的未来生活作出了决定,当时我感到,要想在美国生活,惟一的办法就是舍弃欧洲,要想把它们混合在一起,那是绝对不舒服的。(注:Quoted in Leon Edel,Henry James,A Life,New York:Harpe r & Row,Publishers,1985,p.119.)
詹姆斯关于《美国人》的结尾所做的前后两种不同的解释也充分说明他意识到了融合欧美文化的困难。1876年,《美国人》在《大西洋月刊》上连载,主人公纽曼失去克莱尔这一沉闷的结局,令习惯于圆满结局的美国读者大失所望。于是该杂志的主编豪威尔斯(W.D.Howells )劝詹姆斯对小说进行修改,让纽曼得到他的意中人。詹姆斯在回信中解释说,纽曼和克莱尔的结合是不可能的:“譬如——说实在的——他们能住哪儿呢?”克莱尔会恨纽约,而纽曼也不可能住在法国,他们“惟一可居住的地方是西部的一个农庄”。因此,詹姆斯说,如果他写出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庸俗地向读者扔一片烂面包,这些读者确实不了解这个世界,他们也不会按一部小说对世界的反映来判断这部小说的价值”。 (注: Henry James,The
CriticalHeritage,ed.Roger Gard,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868,p.44.)相反,像他现在这样处理贝勒伽德家族与纽曼的故事,结局也许是沉闷了一点,但这是忠于故事本身的自然发展:纽曼注定不可能融入他渴望的贵族圈子里,正如克莱尔和瓦伦丁不可能走出自己的文化传统,进入纽曼生活其中的那个自由世界一样,詹姆斯在给豪威尔斯的信中说, “森严的高墙阻隔着我们”。 (注: Henry
James,TheCritical Heritage,ed.Roger Gard,London:Routledge andKegan Paul,1868,p.44.)
事隔许多年后,詹姆斯在他的纽约版序言中又提出另一种说法:其实,这个结局与现实是有出入的,实际上,贝勒伽德一家“一定会跳跃着扑向我那富有、 随和的美国佬而不会去在乎他的落后”。
(注: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p.1066.)但詹姆斯这两种前后看似矛盾的说法,实际上又并不矛盾,它恰恰说明了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当时要纽曼在欧洲遭受挫折,目的是要突出他心目中美国人的两大特点:既单纯善良又自大无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虽然意识到了这部小说与实际生活有出入,却没有在纽约版中修改小说的结尾,而是仍然维持原样。
事实上,纽曼巴黎文化梦的破灭也是1876年詹姆斯自己在巴黎文学圈子里感受到的挫折。詹姆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评论法国文学。巴尔扎克小说中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世间万象令他震撼;法国文学成熟的艺术形式令他着迷;他欣赏都德作品中真与美的结合,福楼拜的大师风范也激励着他。 (注:参见詹姆斯的文学评论集 PartialPortraits,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1985,p.208,p.314,及"French Writers",见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1985,pp.213—249,pp.314—346.)然而,当他真正深入到巴黎的文学圈子中,却发现世纪末的法国文学已经不是他想像中的样子,并且,巴黎的文学圈子极端排斥异己,对英美文学采取冷漠高傲的态度。詹姆斯意识到,他以前在巴尔扎克和屠格涅夫作品中发现的那种开阔的心灵,就像纽曼在克莱尔和瓦伦丁身上看到的贵族文化的精华一样,只能被封存在现实之外的记忆中了。
1976年,詹姆斯给豪威尔斯写信说:“我几乎看不到任何文学上的友爱,有五十种原因说明我为什么不能与他们亲近。我不喜欢他们的货色,他们也不喜欢任何其他货色”。因此,詹姆斯虽然感到自己比纽曼更深入地走进了巴黎的生活,更有能力把握这里人的思想底蕴,但他仍摆脱不了局外人的感觉。“我正变成一个老巴黎,一个心满意足的巴黎人,”他在给豪威尔斯的同一封信中写道,“我感到自己的根已经扎进巴黎的泥土,并有可能茂密地生长下去,”但他却又不得不承认,“关于纯正的巴黎性,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到。”因此,他不无悲哀地说,“我会永远是一个局外人”。他最后决定“放弃永久居留的计划,逃往伦敦,并在那儿尽可能地住下去。”(注:Henry James,"Letter of May,1876 to William Dean Howells",Henry James:Letters,Vol.Ⅱ,ed.Leon Edel,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75,pp.51—52.)他和他的主人公最终都没有在这个曾令他们心驰神往的文化之都找到一种认同感,因此,双双离去,纽曼回到了能接纳他的商业社会中去,詹姆斯到伦敦去寻找他的精神家园。
四、文化融合思想的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女士的画像》(注:本文采用的译本主要是项星耀翻译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将该小说缩写为PL,文中引文置于括号中,不另作注。同时,本文还对照参阅了原文The Portrait of a Lady,in Henry James: Novels1881—1886,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StatesInc.,1985.)中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才是詹姆斯文化融合理想的具体化身。与詹姆斯笔下大多数美国主人公一样,伊莎贝尔也是带着典型的美国个人主义思想和对贵族文化的好奇走进欧洲社会的。
英国对于伊莎贝尔来说,正如巴黎对于纽曼,罗马对于哈德逊一样,也充满无限的诱惑力:“这个小小的国家像熟透的梨子那样鲜美、香甜”。不过,伊莎贝尔与前两位同胞相比,多了几分把握环境的判断能力。在伊莎贝尔的眼中,英国文化的魅力是由她崇拜之至的梅尔夫人——一位欧化了的美国人体现出来的。梅尔夫人有一种“迷人的风度”,(PL:205)她
这么文雅,这么有教养,这么聪明,这么从容自如,可又对一切这么不以为意——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高贵的气质,何况,她的举止神态就像一位贵夫人。仿佛她就是上流社会的化身,掌握了它的一切音容笑貌和优美风度,但或许深得其中三昧,巧妙地运用了它的一切,尽管她离它很远,生活在一个名利追逐的世界中,还是能表现得这么超逸不凡?”(PL:224—225)
出污泥而不染,这正是伊莎贝尔所追求的高尚品德。于是,梅尔夫人写信,画画,弹琴,刺绣,乃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在伊莎贝尔眼中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成为她理想的贵夫人形象的体现。梅尔夫人那沉静的外表下透露出的经验和睿智深深吸引着伊莎贝尔,使她从对方的成熟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这正是詹姆斯让他的美国同胞从繁忙的商业社会走向欧洲的用意。詹姆斯使他的同胞们发现了他们经验之外的东西,使他们懂得了政治和经济的领先并不能代表一切进步,意识的扩展和深化,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勇敢探索,在拥有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对异己文化的大胆借鉴和学习才是推进文化完善的有效途径。伊莎贝尔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然而,伊莎贝尔面对文化“禁果”的诱惑,起初并没有失去及时的反思与正常的判断力,没有盲目地效仿。与纽曼在遭到欧洲贵族愚弄、哈德逊陷入堕落的危险时浑然不觉不同,伊莎贝尔在接受梅尔夫人的影响时是清醒的:
只要这是好的影响,那有什么坏处?一个人越是接受好的影响便越好。重要的是在我们要跨出步子的时候,要看清楚,知道这是在走向哪里。(PL:223)
她甚至能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去观察梅尔夫人:“她已经变得太柔顺圆滑,太纯熟,太高雅了。”(PL:226)这一个“太”字道出了伊莎贝尔对梅尔夫人的举止行为审慎的态度。伊莎贝尔对梅尔夫人的崇拜中所包含的审视,标志着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在欧洲复杂的环境中,已经具备了接受经验的成熟心智,这是一种知己知彼的洞察和明智。
包括伊莎贝尔最后爱上穷困潦倒、阴险庸俗的奥斯蒙德,而没有来得及对他的品德和动机产生任何怀疑,也可以说是她追求欧美文化融合的美好愿望的结果。在伊莎贝尔的眼中,奥斯蒙德是经验与审美的化身,他假装出来的超然物外,他的睿智老练,他的一无所有等等,这一切都符合伊莎贝尔的审美标准。她幻想着,与这个人的结合便可以与他分享思想,达到物质与精神的结合,责任与审美的统一。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身上体现出来的优雅、深刻、经验和睿智对伊莎贝尔的诱惑,也正是欧洲文化对詹姆斯呈现出的魅力,伊莎贝尔追求自己的财富、道德责任、青春活力与奥斯蒙德所代表的这一切的结合,正是詹姆斯孜孜以求的欧美文化的相互弥补和融合。
然而,伊莎贝尔要获得她追求的知识与经验,要具备这两位她钦羡的榜样身上体现出来的魅力,却不得不经历一桩不幸婚姻和友情遭背叛的洗礼。伊莎贝尔曾对沃伯顿勋爵说过,她无法“逃避大多数人的遭遇和不幸”,她果然言中了自己的不幸。也正是这不幸,使伊莎贝尔认识到了个人自由的限度和自己性格的弱点。现在,她知道了个人的判断力由于经验的缺乏,有时是不可靠的。她在痛苦中获得了沉甸甸的人生收获,因此,她才会在面对欺骗过她、亵渎了她友情和信赖的梅尔夫人时,没有斥责和申诉她,而只是冷静简短地说了一句:“我相信,我应该感谢的是你!”(PL:676)伊莎贝尔就是在沉痛的失败面前,完成了她意识的深化与心智的成熟。
露丝·伯纳德·依泽尔说:“与差不多跟他同时代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样,亨利·詹姆斯懂得,研究文明即是调查文明下的焦虑与不满。”(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第561页。 )伊莎贝尔的焦虑与不满,首先是她站在欧洲文明之外的焦虑与不满,于是,她渴望、进取;然后是她处于不幸婚姻中的焦虑与不满,于是,她反思、痛悔,并奋力崛起,这便是詹姆斯对处于文明交叉点上的美国人心理进化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像他的女主人公一样,詹姆斯自己在完成欧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詹姆斯涉足欧洲文明,最终却成了一个没有真正归属感的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流放者,饱尝了他的传记作家里昂·艾德尔(Leon Edel)所说的“双重流放”的滋味, 即“他在家有一种外人的感觉,他在欧洲又惧怕自己是个局外人。”(注:Quoted in
Leon Edel,Henry James,A Life,New York:Harpe r & Row, Publishers,1985,p.123.)然而,这种无根的漂泊感对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詹姆斯自己也说:“有这样的时候,当一系列风俗习惯,不管在哪儿被发现,对你来说,都像其他的风俗习惯一样狭隘;那么,我认为,你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了。我为自己世界主义者的视野而自豪。”(注:Quoted in Leon Edel,Henry James,A Life,New York:Harpe r & Row,Publishers,1985,p.121.)正是真诚地、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命运,詹姆斯才能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美国人,以美国人的眼光审视欧洲人,这就是詹姆斯在多年后回顾自己的命运时所说的“幸运的堕落”:(注:Quoted in Leon Edel,Henry James,A Life,New York:Harpe r & Row,Publishers,1985,p.121.)漂泊使他开阔了视野,得以抛开偏狭的民族意识,去汲取人类共同需要的文化精髓。伊莎贝尔在痛苦中的成熟以及詹姆斯的亲身经历似乎表明,对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过去、没有文化的美国人的成长来说,“遭遇大多数人的痛苦与不幸”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经历,尽管它充满着冒险与辛酸。同样,美国文化要走向成熟与完美,达到与欧洲文化的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文化模式,还需要一些有知识、有审美能力的美国人,在经历一番痛苦的心路历程之后方能实现。这也许就是伊莎贝尔的不幸与收获带给读者的启示。
五、文化融合的意义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处于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当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在美国内战后的商业社会中发展到极端、有滑向利己主义的危险时,当许多美国学者陶醉于美国既有的自由与活力中,高唱大国沙文主义的赞歌之时,亨利·詹姆斯提倡欧美文化融合的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它是对美国文化思想的反思与重构,是对爱默生理想型个人主义思想的弥补与完善。
詹姆斯提倡欧美文化的融合,首先是对当时以爱默生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排斥欧洲文化思想的一种反拨。在整个19世纪的美国思想界,爱默生无疑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为了摆脱欧洲殖民文化的阴影,爱默生用他的《美国学者》一文向美国的学术界发出了文化上的独立宣言:“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漫长学徒期即将结束。……我们要唱出自己的歌”。(注:“美国学者”,引自《爱默生集》,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2页。)然而,在詹姆斯看来,爱默生在唤起民族自尊和自立自强的同时,似乎又走得太远,多少带上了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爱默生问道:“在世界上,总有一个领袖民族……除却美利坚合众国,又有哪一个民族能担当起领袖的责任呢?”(注:“年轻的美国人”,《爱默生集》,第245页。 )这一振奋人心的民族文化独立宣言虽然在“萎靡的美国人的心灵”(爱默生在《文学的道德》一文中语)中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在号召美国学者创建独立的民族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爱默生的这些虽然自信却有些缺乏谦逊的言论可能会助长美国人的盲目乐观,久而久之使他们不屑于关注异己文化的长处,这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因此,詹姆斯借鉴欧洲文化的“审美”与“经验”以弥补美国缺少文化与传统的不足,不仅是对美国文化的一种理想性重构,而且也用自己的文学实践向美国学界表明,什么样的学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学者。
詹姆斯所提倡的欧美文化融合的理想,显然超越了爱默生个人主义思想的范畴。为了摆脱商业社会和家庭对人性的压抑,爱默生提倡个人自立自强,自律自治,而詹姆斯理想的个人,则不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对身边的人也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这就避免了个人主义在商业社会中滑向利己主义的误区。对詹姆斯小说中塑造的美国人来说,金钱从来都是和责任交织在一起:罗兰德·马利特用他的钱资助素昧平生的哈德逊到意大利学习雕塑;纽曼有了钱之后不是在美国寻欢作乐,而是到欧洲去追寻自己的文化梦,他对遇到的不幸者充满了同情,尽管他的洞察力有限,但他那份真诚助人的愿望,至少使人不忍心对他的无知和粗鲁感到厌恶;伊莎贝尔更是在自己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时,不忘自己的责任,要帮助穷困落魄的奥斯蒙德实现其艺术家之梦。
这样,詹姆斯在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使爱默生的那些脱离社会、脱离历史的个人主义者增进了历史感和社会意识,使他们意识到个人的自由会受到强大的外部环境的种种限制。为此,美国现代文学批评家昆丁·安德生(Quentin Anderson)称詹姆斯是“将欧洲文化用于美国个人主义的第一位现代派作家”。(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第574页。)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终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遐思,仍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其实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所察觉。他作品中的人物尽管不像爱默生那样对欧洲文化采取排斥态度,但是他们在实践欧美文化融合思想的道路上也是举步维艰。这说明,詹姆斯充分意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因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的不同,其冲突和差异是根本的,也是主要的,沟通和融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要成功地融合不同文化的优秀成分于一体,也许只能由他作为一位小说艺术家用虚构的世界来实现,而在这种文化的差异面前,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束手无策。
因此,我们可以说,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虽然是从对美国文化匮乏的状况不满出发,试图用借鉴欧洲文化的方式,寻找一条提高美国文化的新路,独辟一条融合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蹊径,但是,他作品中大多数人物努力的失败以及他自己后期的小说创作转向艺术技巧而不是主题思想的创新实验证明,他又不由自主地退回到美国高雅文化与纯文学的传统,成了一位最成功的、也是最后的高雅文学的表现者。(注:Vernon Louis Parrington,"Henry James and the Nostalgia ofCulture",in The Question of Henry James,A
Collection ofCritical Essays,ed.F.W.Dupee,p.129.)
标签:詹姆斯论文; 伊莎贝尔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美国人论文; 阿诺德论文; 纽曼论文; 道德论文; james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