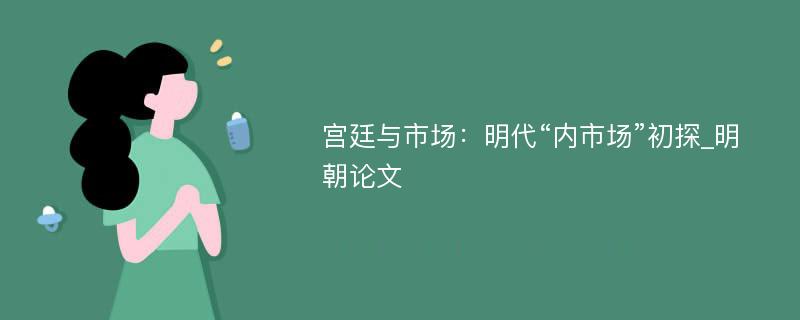
宫廷与市场:明代“内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宫廷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15)06~0077~04 一、引言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顺天府蓟州民张差经东华门入宫城,杖击慈庆宫(太子东宫)守门内官,为守卫内监韩本所擒,此事件即为震惊朝野的万历三案之一的梃击案。关于该案的后续处置,除所揭露的宫廷斗争之外,处理案件部分官员还将引发事端客观原因指向宫廷禁卫问题,即身为平民的张差何以绕过宫廷禁卫而直入内廷。对此,时任刑部主事的王之寀在奏中作出分析:“……臣因是而知,皇城之禁不可不加严也。彼后宰门之直入无忌,果张差傍若无人耶,抑有所凭之而然也。矧张差踯躅禁庭之日,乃内市纵横之日,夫内市未谂起自何年,恬不为怪。自有内市而人迹綦溷,货物綦变,铦帑利刀,纷错禁地。即奉明纶犹当议革。矧无成例,讵可漫沿。”[1]卷532,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甲子条从王氏奏言分析,张差进入内廷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抑有所凭”,即得到宫中内应的引导;二是“内市纵横之日”。由此透露出明代宫廷内的独特现象,即当时宫中存在一种称之为“内市”的交易市场。那么,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明廷为何于宫闱之地设置有悖于宫省体制的交易市场,而该市场的功能及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又是如何? 就目前而言,关于明代“内市”的探讨多局限于词典式的名词解释,而作为附带研究有所论及者,如许大龄的《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韩大成的《明代北京经济述略》,也主要将“内市”作为明代北京经济发展一种表象附带论及。此外,张丽丽也曾对于明代“内市”出现对清代皇城开放的重要影响进行探讨[2~4]。因此,就研究现状来看,并无专文对于明代“内市”的上述问题予以澄清。有鉴于此,本文仅以目前掌握资料为依据,对上述问题试作探讨,以便在弄清明代宫中的市场问题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明代的商业发展和宫廷消费问题。 二、宫廷“内市”的源起与布局 关于明代“内市”的界定,《明内廷规制考》有云:“宫阙之制,前朝后市,市在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贾贸易,谓之内市。”[5]卷3《后市》,69由此可见,明代“内市”在设置上遵循了周礼建国前朝后市之制。正如东汉郑玄所云:“建国者,必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后市,阴阳相承之义。”[6]卷7《天官》即采用以宫为基准,“左祖、右社,面朝、后市”[7]《冬官·考工记》的基本布局。但需注意的是,明代“内市”虽仿周制后市之义,但二者又存在差异。周制后市由大市、朝市、夕市三市构成,按宋人易祓解释:“大市居中,则日仄而市;朝市居东,则朝时而市;夕市居西,则夕时而市。此三市之别也。”[8]卷78由此可见,周制后市是指在一天之内不同时段开设的三个不同市场,且从布局和时间的设定来看,应为一种常设市场,而明代“内市”在结构上则作为单一市场存在。另就市期而言,每月逢四则开,即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为市期。因此,这种定期而设的交易场所从内容上看更具赶集特征,故时人谢肇淛在对明代“内市”的界定上,也将其称为按期而设的“集”[9]卷3《地理部一》,1542。 “内市”因地处皇城之内故冠以“内”字,至于“内市”起于何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根据万历朝刑部主事高之寀奏中有“夫内市未谂起自何年”之言,又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户科给事中商周祚在奏请整饬宫禁时亦有“不知何年设立内市名色”[1]卷532,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辛未条一语,可见时人对于“内市”的始置时间也并不明确。据笔者目前掌握资料来看,关于“内市”的最早记载为成化四年(1468),是年十一月行人司行人于坦奏言:“臣惟擅入内府,律有明禁,况又节蒙圣旨禁约。近见市井无知之徒,贪图小利,輙将私货布帛酒食等物进入买卖。且皇城圣天子万乘之所居,宫禁库藏于是乎在,礼法制度自此而出,岂市井小人营私买卖之地哉。宜令守卫官员并锦衣卫官严加缉访,挐送治罪,货物没官。……奏入。诏:付所司议行。”[10]卷60,成化四年十一月戊辰条据此断定,明代宫中市场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成化四年。又如,成化八年(1472)正月十三道监察御史张学等曾以星变陈言修省八事:“……一、内府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在外诸色人等,俱将物货赴玄武门等处货卖,甚非所宜,请令点闸给事中御史等官督守门官严加禁。”[10]卷100,成化八年正月戊戌条在此,张氏等人所言成化八年的宫中“内市”,无论是市期还是交易地点上均已作明晰规定,显然此时设置于宫中的“内市”已然成为一种常态。此外,张氏等人疏中以宫中货卖“甚非所宜”为由奏求禁止,并得宪宗准允,可见宫中“内市”并非依祖制而设,更有可能是一种因宫廷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的集市。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明代官方史料中不见“内市”的设置时间。至于时人提及遵循“前朝后市”的周制之说,更多的是在“内市”约定俗成之后的一种托词。 关于“内市”的具体分布区域,根据时人沈德符的描述,“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11]卷24,612。又谢肇淛《五杂俎》载,“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则于东皇城之北有集,谓之内市”[9]卷3《地理部一》,1542。《明内廷规制考》亦云,“市在玄武门外”[5]卷3《后市》,69。此外,清人宋起凤在《稗史》中言及,“内市,由东华门进,过御石桥即是”[12]卷4《内市》,119。综合以上四则材料,可见明代的宫中“内市”分布范围大致为南抵东华门、光禄寺一带,东至御马监,西达西海子的玄武门外皇城东北区域,而这一区域是明代内侍机构的主要聚集地区,当中居住着大量内侍人员①,这为“内市”的存在提供了消费市场。 万历末至崇祯年间,随着东北满洲的崛起,明朝战事不断受挫,京师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为刺探军情虚实,满洲间谍也借“内市”之机混入皇城,对宫中禁卫构成了威胁。天启元年(1621)三月,熹宗因“奴酋日肆,门禁当严”[13]卷8,天启元年三月丁卯条,被迫将“内市”移出宫外,置于东安门外的戎政府街,市期一遵旧制。此次布局变动,导致了“内市”与宫廷消费群体的脱离,故京师当时谣传有“大市去矣”之说[14]卷16《内府衙门职掌》,101,足见布局因素对于“内市”存在的实际影响。因此,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又决意将“内市”迁回原处。 (天启七年七月)圣谕:朕念成周盛时礼制所载,匠人营国朝市井,我祖宗则而法之,其意良是。朕践祚之始,正逆奴方炽,朝殿未兴,遂将内市暂移北安门外,于今七年矣。器物颇觉不敷,溷亵殊非长策。今赖厂臣覃思密画战胜,庙堂鼎建,朝殿聿新,挫虏捷音叠至,神人奋悦,朕甚嘉焉。可将内市自八月初四日为始,还遵累朝旧典,仍移于玄武门外,着该衙门严加巡缉,禁止纷嚣。皇城各门都盘诘关防,毋得疏怠。复我祖宗以来面朝后市之典,昭朕轸恤民至怀[13]卷86,天启七年七月戊子条。 该复市谕旨前后两处提及回迁“内市”的目的在于复祖宗之法,遵循前朝后市的礼制布局,但这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托词,其真正目的为“器物颇觉不敷”,即所谓“内市”交易对于晚明宫中器物的供给来说极其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宫闱深处必然存在一个实际的消费市场,这为“内市”的长期存在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力。 三、宫中消费市场与“内市”功能 明中期以后,因商品经济发展,北京地面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各类市集,如位于大明门左右的日市、东华门外的灯市、正阳桥处的穷汉市,以及城隍庙市、日昃市,等等[9]卷3《地理部一》,1542。“内市”的出现作为明代北京商业繁荣的一个缩影,反映出明代商品经济已突破政治藩篱渗透至宫闱禁地。 因交易地域及商品的特殊性,“内市”的交易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根据清人宋起凤《稗史》记载:“凡三代周秦古法物,金玉铜窑诸器,以至金玉珠宝犀象锦绣服用,无不毕具。列驰道两旁,大小中涓与外家、勋臣家,时时遣人购买之。每月三市,凡旧家器物,外间不得售者,则鬻诸内市,无不得厚值去。盖六宫诸妃位下,不时多有购觅,不敢数向御前请,亦不便屡下旨于外衙动用,故各遣穿宫内侍出货焉。凡内市物悉精良不与民间同,朝贵亦多于其地贸易,咸听之不禁。”[12]卷4《内市》,119由此可见,除宫外庶民、客商之外,宦官、勋戚乃至妃位以下的皇室群体也参与其中,成为一种等级跨度极大的独特集市。 另从上文的商品描述来看,“内市”偏向为一种古玩、奢侈品市场,亦如《明内廷规制考》所云:“外市系士夫庶民之所用,若奇珍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陶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之法瑯,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5]卷3《后市》,69由“内造”二字推之,市中所列商品多为宫中御用之物。那么,为民间禁用的御用器物珍品何以作为商品大量出现于“内市”之中,其中原由值得深究。就所见资料来看,该类商品的来源,除宫中内侍人员通过支领、赏赐等正规途径获取之外,当中不乏存在冒领、盗窃所得。正如时人沈德符所言:“内府盗窃,乃其(宦官)本等长技。”[11]卷6,173又景泰三年(1452)九月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华敏言:“臣切见内官收积家财,金银珠玉动以万计,此从何而来,非盗府库之钱粮,则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15]卷220,景泰三年九月辛卯条这也为所发案例证实:如正统十一年(1446)六月“内使阮恺盗启宝藏库锁,事觉,上命戮之于市”[15]卷142,正统十一年六月丁酉条;天顺六年(1462)十一月“内官韦亨、李才等,盗内库金银器皿及玉系腰等物,事连内外官员人等三十一名”[15]卷346,天顺六年十一月戊申条;又隆庆元年(1567)六月,礼科左给事中王治等清查内库钱粮物料,发掌供用库内官翟廷玉、掌丁字库内官马户等乾没内库财物[16]卷9,隆庆元年六月戊戌条。以上所呈现的案例,较之宫中内官的实际盗窃情况,可谓九牛一毛。 另如宫中瓷器乾没。明代宫中所用瓷器作为御用之物其价不菲,据何孟春云:“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莹无瑕疵,色泽如一者耳。噫!物苦窳不足道也,物亦奚用珍奇。为民间烧磁,旧闻有一二变者,大者毁之盏罂,小者藏去鬻诸富室,价与金玉等。”[17]卷4《外篇》因宫中瓷器价值的驱使,宫廷内侍对其乾没极为严重。如正统年间,“光禄寺日进膳于宫中,缾坛筐篓皆发出后往往留中,间有发出辄为内使取去”[15]卷291,天顺二年五月壬寅条;又正统二年(1437)英宗上谕云,“比闻进宫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还一二……”[18]卷27《光禄寺》;又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巡视光禄寺御史房壮丽言,“凡磁器漆盒绳扛等物,一入宫门,无复还望”[1]卷464,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条。可以说,大量的乾没陶瓷,很大部分是经由“内市”交易流至宫外的。 由此可见,宫中内侍人员对于宫中财物的大量乾没、盗取,无疑成为“内市”珍贵商品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与之对应,在明代宫省体制之下,如无派遣之需,宦官活动范围主要限于皇城之内,因此定期而设的“内市”存在,无疑成为其销赃的便利场所。 从市场的实际功能来看,“内市”还是一种为宫廷提供生活物资的生活市场,而该类市场的出现又与明中以来内官衣食供给形态的调整存在一定关联。明初,内官衣食主要依赖内库供给,如内承运库供给绢丝纻罗等衣料、内府供用库供给米盐等食材、丁字库提供皮张等料,且因宫中宦官的数额庞大,内库的衣食供给量极为可观。根据台湾学者邱仲麟的估算,明代在内廷走动的宦官应在两万以内,宫女也可能达九千人[19]。对于宦官群体的衣食消费情况,时人刘若愚在《酌中志》的《内臣服佩纪略》和《饮食好尚纪略》中亦进行了详细描述[14]卷19、20,165~184。譬如内官服饰布料,“旧制,(内官)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苎丝,自三月初四至四月初三穿罗,自四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三日穿纱,自九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罗。该司礼监预先题奏传行。凡婚庆吉典,则虽遇夏秋,亦必穿纻丝供事。若羊绒衣服,则每岁小雪之后,立春之前,虽纻丝穿之。凡大忌辰穿青素;祧庙者穿青绿花样,遇修省则穿青素。祖宗时,夏穿青素,则屯绢也;冬穿青素,则原色之纻丝也”[13]卷19,166。从内官的衣料材质构成,足以窥见内官衣食供给之丰富、耗费之奢靡。 明中期以后,在商品经济与白银货币化的推动之下,国家财政逐步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变,内库物料本色也开始实现部分折银,其直接影响是内库本色物料的减少,致使供给不敷。因此,自正德以来,宫中内官衣食的供给形态也逐步由本色实物向白银货币调整。正德三年(1508)六月,针工局奏请该年成造内官年例铺盖,户部巡查内库无见贮白绵,诏:“每斤折银五钱,共折银六千二百一十两给之。”[20]卷39,正德三年六月庚寅条至此开启了内官供给的折银之始,而供给承担者也由内官监管的宫廷财政转移至外臣所管的国家财政。又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因内官制靴所需皮料不足,尚衣监太监何祥奏请折银给发,得武宗批准[20]卷134,正德十一年二月庚午条。而根据天启三年(1623)六月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等人的奏报,两京内官冬衣自正德以来,也因内承运库苎丝绫紬数额不敷,由此前内库关给布料转为工部支银给发,并作为常例一直执行[13]卷35,天启三年六月庚午条。 内官供给折银的直接影响,推动了宫中消费的日趋商品化。因为此时宦官要获取部分生活物资,就不得不依赖于市场交易,这意味着内市作为一种商品交易场所,其在整个宫廷消费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与成化年间宪宗对内市的随意裁撤不同,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所引发的裁撤之议一出,随即遭到否决。其原因正如神宗圣谕所言:“其(内市)在内每月三市,相沿年久,况日用衣着等类,食用之物必不可缺……”[1]卷532,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辛未条从中可见,神宗反对裁撤“内市”的依据,就是此时宫中在“日用衣着等类,食用之物”的来源上部分依赖“内市”获取。且如前文所引,天启七年熹宗不顾宫禁安危决议回迁“内市”也是因“内市”外迁所引发的“器物颇觉不敷”的供应危机所致。 综上所述,由明代宫中“内市”的商品结构和流向来看,既是宫中珍宝财物流向民间的重要途径,也是民间生活物资流入宫廷的重要渠道。明中期以后财政白银化所引发的宫廷供给方式调整,使得宫廷消费对于“内市”依赖性越来越大,也是重要因素,即所谓“每月三市,相沿已久,以济需用,事不可缺”[21]卷75,纪75·神宗显皇帝。 四、结语 有明一代,宫中“内市”虽然在布局上遵循了周礼“前朝后市”之义,但其形成的实质原因在于京师商业发展和宫廷的实际消费需要。一方面,明季京师商业的繁荣,使得市场因素突破民间范畴,渗透至宫廷之中,而宫中潜在的庞大消费群体,及其以上供形式汇集于宫中的大量奇珍异宝,也为“内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市场条件;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的国家财政白银化,以及宫中内侍衣食供给的折银问题,使得宫中消费日益依赖于“内市”交换,宫廷、市场连为一体。与此同时,“内市”因所置地域的特殊性,其在突破宫廷、市场之间政治藩篱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明代宫禁制度,扰乱了权力中心必要的秩序规范。 注释: ①关于该区域的机构分布情况,参见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徐苹芳.明清北京城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标签:明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