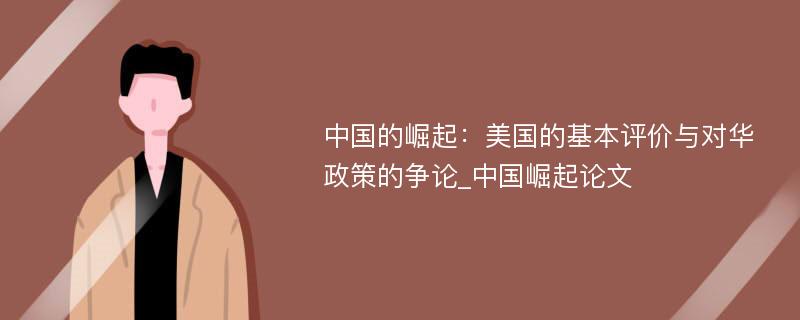
中国崛起:美国的基本评估及对华政策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民族曾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历史,拥有过世界最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强大的经济。世界“最负声望”的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认为,直到中世纪前,在科技发明、创造能力和系统观测自然方面,中国“至少不次于并且在很多方面超过西欧”。(注:[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71页。)
对中国崛起的阶段性评估
新中国成立后,视中国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力量的美国政府要人,当属尼克松总统。1971年7月6日他在堪萨斯的演说中,把中国与美、苏、欧、日并称为“五个超级力量”。尽管当时“有1亿人口的日本生产的东西比有8亿人口的中国还多”,但尼克松敏锐地指出:“这不应当使我们产生错觉……,认为中国将始终是那样”。(注:《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的讲话》,载《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7~78页。)
现代中国政治崛起的起点当然是新中国的成立,而作为具有实质意义的崛起则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行。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涉及到所谓“经济大国”的衡量标准,国际上对此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购买力平价”而言,世行90年代初开始采用这一指标,估算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这种算法并未得到广泛接受,但迄今仍然是一种依据。美国学者认为:“贸易政策原因”使人民币不断贬值,因此,以中国汇率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难以进行准确的国际对比。(注:Dwight H.Perkins,"How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hapes Its Future",Fzra F.Vogel,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W.Norton & Company Ltd.,1997,p.14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500美元,GDP为5000亿美元,(注:关于中国1978年的GDP,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624亿美元。参见《综合国力跻身世界七强》,载《人民日报》,2001年6月27日。)到1995年GDP达到2万亿美元,2000年已达到4万多亿美元。最近仍坚持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学家估计,如果中国保持发展势头,那么,25年后世界经济大国排名将出现“根本性变化”。届时,全球和美国经济总量虽会增加一倍多,但中国占世界的比重将达到26%,而美国将只能维持在21% ~22%左右。也就是说,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注:[美]H.格林韦:《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第一》,载[美]《波士顿环球报》,2001年5月21日。)美国将处于第二位。
进入新世纪后,对中国能否保持经济高增长,美国学者中不乏疑问者。但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考斯·诺兰德教授计算,即使经济增速减缓,中国也将在201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的过程到底有多长?评估指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一般认定,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中国达到1万美元,需要9%的增长率,为时20年,这“可能高得不太切合实际”;但增长6%,这“无论如何不能说不切实际”,中国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则需要30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扩张到16万亿美元,将是美国1995年GDP的2.5倍。(注:Dwight H.Perkins,"How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hapes Its Future",Ezra F.Vogel,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7,pp.144~145.)按此估计,到2025年,中国经济至少与美国不相上下。摩根·斯坦利估计,如果人世后如能履行承诺并在2005年前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速度在2005年前可望维持在7%左右,2006~2015年维持在9%左右,2015年后会“略有减缓”。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10万亿美元(以2000年美元汇率计),与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持平,人均收入亦将达到6700美元。(注:"Entering the Dragon",The Economist,March 10,2001.)
经济崛起将奠定大国地位的物质基础,其意义远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中国崛起后如何运用其力量?是否会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PeerCompetitor)?这涉及到美国内对中国未来大国地位的整体评估。及至今日,乐观者有之,怀疑或悲观倾向依然同时存在。中央情报局最新报告《2015年全球大趋势》认为:由于“面临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压力”,中国的未来“充满变数”。一些学者认定,对中国的估计应包括中国“陷入混乱”的可能性,即中国“可能面对某种混乱或崩溃的局面”。(注:Zalamay M.Khalizad,Abram N.Shulsky,DanielL.Byman,etc.,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Strategic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RAND Corporation,1999,P.14.)悲观论者还认为,即使可以避免陷入混乱,那么中国的成功也“不会持久”,因为中国人口负担过重、生态环境恶化销蚀着国内资源、地区性差距扩大、金融体系的隐患及社会潜在不稳定性等将干扰其崛起进程。
怀疑论者还认为,中国崛起即使是大势所趋,但崛起的时间比目前认识的“更长”。《华盛顿季刊》1999年夏季号载文,从“对自己有利的安全优势、军事和经济等硬件实力及政治理论方面的软实力”方面直截了当地认定“中国难以成为世界大国”。现任布什政府国务卿的鲍威尔则一度认为:从制造能力或市场潜力而言,中国无疑会发展成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否会像美国一样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则“有待观察”。(注:鲍威尔接受中国台湾《中国时报》的采访,1996年5月28日。)
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意义
围绕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意义,近20年来美国国内都有过阶段性的争论。如今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对美国是否是一个挑战。围绕此一主线的论争,大体上分为三派。
一是乐观派。中国崛起符合美国利益。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美国经济规模扩张之快远非增长率所能准确地衡量出来,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衰退同样不能提供美国整体实力由盛及衰的充分证据。过去10年,中国的发展缩小了与其他强国的差距,但与美国的差距仍处于相持状态,即并未明显缩小。以《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进行对比可知,1978年中国GDP为2000亿美元,美国为22000亿美元,到2000年中美两国壮大到约1万亿美元和10万多亿美元,几乎都翻了两番多。中美两国处于“同向发展”的状况,部分打消了美国对“新兴大国崛起可能挑战现存大国”的担心。一些学者认定“北京的崛起不会自然转变为华盛顿的衰落”。(注:[美]保罗·布拉肯:《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吗?》,载[美]《时代》周刊,2000年5月22日。)
中国崛起为何符合美国的利益?享利·托马斯·巴克尔以及诺曼·安杰尔的“相互依存论”显然提供了主要依据。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赖使相互利益扩大,一国挑战外部世界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利益远不及其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即得不偿失。因此,如果在全球化进程中“彻底拖住中国,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和平”。(注:参见[美]理查德·贝茨和托马斯·克里斯坦森:《中国:把问题搞准》,载[美]《国家利益》杂志,2000年冬季号。)
“相互依存论”意义的延伸还在于,相互依存将使中国“变得越来越愿意”遵守国际体系,即使当中国强大到“足以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的时候”,它已“完全服从国际秩序了”。(注: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RAND Corporation,1999,p.12.)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全球贸易体制对自己大有裨益。基于此,中国将“真心真意接受世贸组织”。而中国同意按规则办事,这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经济、战略和安全利益”。(注:斯坦利·罗思2000年5月9日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演讲:《未来的战略—美中关系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据新华社华盛顿2000年5月10日电。)
开放必然深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及对世界的认识,因特网的普及、私营部门的壮大、中产阶级迅速成长等,都将增大中国的民主内涵。按照“民主和平论”的观点,民主国家尽管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完全一致,观点亦不彼此认同,但它们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美国思想库提出的报告推论,“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那么它的对抗性竞争特性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会服从于一种广泛的合作战略,正所谓‘和平地带’(欧盟和日本)所遵循的一样”。(注: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RAND Corporation,1999,p.12.)
二是否定派。否定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国崛起对美国的积极意义。他们认为,中、美在观念、制度上根本不同,历史表明这些不同“经常导致误解和冲突”,而且“后起大国总会挑战现存大国”。如近现代史上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以及二战后的苏联都是这样。它们随着崛起日益不满足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且受到现存大国挤压和威胁,因而“试图”改变现状,而不是适应现存的、通常使强国受益的国际架构”。(注:美新署:参院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弗雷德·汤普森2001年2月15日在华盛顿的演讲。)今天的中国正在崛起,历史线索促使“否定派”深化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同样的认识。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内保守主义进一步回潮,甚至视中国为美“潜在对手”或“战略竞争对手”。如美《国家安全报告》、中情局及五角大楼都明确认定中国至少与俄罗斯一样是美国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注:可参见《1999年美国家安全报告》,沃沦·拉德曼和加里·哈特提交五角大楼的报告《美国的未来》及中情局局长特尼特1999年8月17日的讲话等。)布什上台前也曾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注:"Bush's Foreign Policy",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1,1999.)悲观论者”甚至认为中美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兰德公司为此还进一步予以阐述,“北京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如能顺利进行到21世纪前15~20年,将大大增加这种挑战的力度”。(注:Zalamay M.Khalizad,Abram N.Shulsky,DanielL.Byman,etc.,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Strategic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RAND Corporation,1999,pp.47~48.)
美国著名思想家亨廷顿早些年从文化角度亦论述了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包括中美在内的国家具有的对抗性。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建》指出,19世纪是民族冲突的世纪,20世纪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纪,新世纪国与国的冲突将不会再以意识形态或经济为主,而是文化和文明冲突。概言之,“人类的大分裂及冲突将主要来自文化”,不同文明的分界线“将界定未来的决战阵线”。(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r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No.3,1993,p.22.)他甚至断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的冲突也不可避免。
三是温和派。这一派介乎第一和第二派之间。偏于肯定派者既肯定中国积极变化的现实,也认为中国未来发展“并不确定”,对中国能否驾驭其发展亦抱怀疑态度;偏于悲观派者,既承认中国的变化,认为中国有可能是美国的挑战者,同时认为程度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严重。这一派中不乏前政府要员甚至包括一些对华友好人士以及一些重要的偏保守的思想库学者。在他们心中,中国对美国而言只能是一种“中间态度”的战略定位。如“非敌非友”(哈里·哈丁),或者“介于敌友之间”(彼特·罗德曼);或者“美国把中国视为朋友,中国就是朋友,视为敌人就会是敌人”(约瑟夫·奈)。
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美国“不应过早地对中国未来发展做出判断”。(注: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9月19日电。)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目前而言“只是一个愿望而非事实”。中国对美国不会构成任何军事威胁,对亚太地区也不构成重大安全威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轨道与政治轨道差距“越来越大”,将影响中国的稳定,这才是中国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原因。美《战略评估1999》亦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崛起后,其走向仍不确定。如果中国能融入西方共同体,将有助于加强地区稳定,否则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的安全问题”,中国的“军事威胁可能影响整个(亚太)地区,还会影响到美国及重要盟国的关系”。(注: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Priority for a TurbulentWorld,"Key Findings",Pxiiv.,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nd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1999.)
“中国虚弱论”亦可划归此派。按照“中国虚弱论”,中国政府被认为“如此之弱”,而经济改革所释放的离心力“如此之强”,以致中国有可能“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这可能被世界其他地区认为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繁荣的中国也许会强大得“难以驾驭”。但美国学者认为,尽管对中国和世界其余地区而言,权力分散“可能有益”,但希望中国分裂的想法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最近认为,中国的内乱同样将“演变成对美国的挑战”。因为由于内战而分裂的中国将招致人道主义灾难,并引起亚洲其他地方的动荡,因而“中国的虚弱可能比强大更危险”。(注:[美]格林韦:《胜者面临的世界》,[美]《波士顿环球报》,2000年11月16日。)
对华政策论争
与上述美国内各界对中国的发展与未来判断相适应,在对华政策选择上,形成了不同政策主张,基本上分为以下几种。
(一)接触政策
这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政策。在检讨对华政策的基础上,白宫于1993年年中审议通过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对华政策《行动备忘录》,制定了一项取代“全面对抗”方针的“全面接触”战略。“接触”后来成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在政策实践上,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虽存在“难以看清的变量”,但美要尽可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伙伴而非对手”。基于此,克林顿政府愿意采取一种全新的“接触战略”,通过“全面加强同中国的交流与对话来改变美国近年来在中美关系中的消极被动局面”。(注: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2000年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接触政策”的推行,反映出这样一种认识。首先,即不论承认与否,中国崛起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中国大国地位日益上升亦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国际政治现实。美国孤立不了中国,孤立中国只能孤立美国自己。其次,中国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将制约其“强硬”行为,因为这将威胁自身利益。再次,尽管中国的演变“难以确定”,但一旦适应现今国际“游戏规则”,并体会到现存体系如稳定的外部环境、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及利用外部资源等同样可以为中国带来利益,那么中国“可能成为一个谨慎而负责任的国际体系的成员”。总之,美国需要通过“接触”政策使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确保中国崛起符合美国利益。如果中国独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而且富有和强大,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注:Ezra F.Vogel,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7,Norton & CompanyLtd.,p.160.)中国向着开放、法治国家演变符合美国利益,对华接触“虽不能确保这一结果,但却是增加这一可能性的最佳选择。(注:W.Bowman Cutter,Foan and Spero and Laura D'Anderea Tyson,"New World,New Deal:A Democratic Approach to Globalization",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00,p.88.)
“接触政策”的设计者当然注意到,台湾问题是“主要的潜在的困难”。尽管在台湾问题上中美立场有重叠的方面(如都期望和平统一),但中国并未放弃动武,正是这一点可能导致美中陷入军事冲突。为此美国需促成海峡两岸达成一个在各种条件下都可接受的统一协定。
(二)遏制政策
“遏制战略”形成于冷战时期。尽管冷战结束,但美国内仍不乏人陶醉于导致前苏联最终崩溃的这一“战略成功”的欢欣遐想之中,不愿放弃固有的冷战思维与寻找对手的惯性心理。鉴于“悲观派”对中国发展的认知,以“遏制”一手对付中国仍有相当市场。因为认定美中“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美不仅要表明其阻止中国挑战的决心,还应防范于未然,采取行动为将来可能难以阻止的冲突作好准备。
应对中国崛起而实施“遏制政策”的建言,理论上包含两个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一是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学说认为,一般而言,崛起的大国随着其利益扩大,会自然而然地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可能与现存的国际秩序相抵触,从而常常对占支配地位的霸主国家提出挑战。从大国竞争历史看,这种挑战将导致一场体系内部的全面战争,其后果直接“决定由原来的霸主保持其地位,还是由挑战国取代其霸主地位”。二是认为中国有地区霸权主义的历史传统。崛起的中国至少在东亚寻求一种地区性的霸权,并挑战它所认为的霸权和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中国有“帝国传统”,不大可能真正实现民主化,即使完成民主化过程,它也必须对日益滋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这一派视对华遏制为确保美国霸权的真正依靠。认为美国应分清敌友,划清阵营,制定一种“战略性政策应对中国短期和长期的威胁”,包括“重建亚洲的军事和外交同盟,建立亚太民主共同体,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及创造更有效的安全态势等”,(注:Bill Gertz,The China Threat: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Regnery Publishing,Inc.,2000,pp.200~203.)甚至主张“放弃任何形式的交往,同盟友建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使中国不敢进攻台湾,并且最终改变中国政权”。(注:《关于中国政策的大辩论》,载[香港]《信报》2001年4月23日电。)这一政策的极端代表在美国自称“蓝队”。他们虽不代表美国主流观点,但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所“赏识”。
(三)遏制+接触政策
这一种政策设计动机主要在于,“接触”或“遏制”都各有难以克服的缺陷。“接触政策”虽然或多或少被认为具有清晰的目标,即促成中国向美国有利的方向演变,但当中国的政策行为与美国利益和目标发生冲突时,这种政策“就不起作用了”;另一方面,对华实施“遏制政策”也缺乏充分依据,很难得到美国内的赞同,自然难以动员国家力量;再者,“遏制政策”需要的地区性联盟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诚恳合作也“很难形成”。因此,“遏制政策”是“一项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的政策”。(注:Zalamay M.Khalizad,Abram N.Shulsky,Daniel L.Byman,etc.,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RAND Corporation,1999,p.71.)
基于对上述的综合研判,兰德公司提出了使二者有效结合的政策选择方案。布什政府上台前,兰德公司推出《美国与崛起的中国—战略与意义评估》报告,提出“遏制+接触”政策。这就是:一手“继续努力将中国引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另一手“为可能发生的中国对美进行的挑战作好准备”。前者符合美国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后者可以告诫中国:“挑战美国”将是“极端危险的”。“两手”并用可以为美国提供“完备的应对之策”。这种政策设想以中国的“现实表现”和在台湾问题上的“举动”为据,如果中国愿意沿着美国设定的“理想”方向演变,“接触+遏制”中,“接触”将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轴;如果中国对台动武或谋求地区霸权,“遏制+接触”将‘自然调整”为以“遏制”为主轴;如果美国对中国未来难以确定,或者中国走“中间路线”,美国将注意“遏制+接触”的平衡。(注:见拙文:《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倾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期,第18页。)
对论争的解读及布什政府的取向
美国对华政策不可能是片面的“接触”或“遏制”,也不可能是简单的“接触+遏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虽被认为是其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但“防范与遏制”的一手同样有所加强。正是在克林顿任内,美日军事同盟得以强化,美国军事重返东南亚步伐加快。1996年中国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时克林顿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就被美国内认为是“遏制中国”之举。由此可见,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软、硬”两手交替并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而已。其实,美国对华政策不可能在“接触”与“遏制”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结合。“接触”中有“遏制”,“遏制”中同样也有“接触”。从这个意义上.二者很难也不可能明确区分开来。“接触+遏制”看起来周全,但远难反映出美各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实质。
布什政府上台后偏离了前政府达成的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2001年4月1日发生的“撞机事件”,特别是4月23日布什宣布对台售武及在台湾问题上由“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使中美关系面临严峻的形势。
布什对华政策中一度明显表现出来的强硬色彩,决非偶然,而是与保守主义势力回潮得势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共和党这一届政府班子启用了不少冷战老兵,一些保守思想库如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等机构的谋士进入新政府并取得要职,而中国问题专家则相对失势。一些保守媒体如《旗帜》和《新共和》加紧摇旗呐喊,加重了布什政府的强硬派色彩。反映在中国问题上,极端保守势力夸大“中国威胁”,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在对待俄罗斯等国家问题上的态度同样十分强硬。在保守派看来,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既没有巩固盟国关系,也没有使俄罗斯与中国向美国期望的方向演变,在对待所谓“无赖国家”问题上同样无所作为。因此它们主张抓住重点,通过巩固民主国家间的团结来加强对世界的主导,以确保“美国世纪”的无限延伸。
在布什政府对新世纪谋篇布局、其对外政策趋于定型之际,"9·11"恐怖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自杀性袭击,造成数以千计美国平民的伤亡。这一震动世界的巨大灾难彻底改写了美国本土近两个世纪(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未再遭外敌侵袭的历史,美国本土安全防卫的脆弱性顷刻间暴露无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击恐怖主义成为布什政府压倒一切的议事日程。中国政府对"9·11"灾难迅速寄予的同情及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美国反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提供的坚定、明确的支持,确保了国际反恐联盟的广泛团结。反恐成为中美之间又一利害攸关的共同利益的领域,凸现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总统参加上海APEC会议与江主席会晤时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等于抛弃了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的提法,这种相对积极的定位将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提供新的动力。
本来,在中国问题上,"9·11"前,布什已经面临政策回归的压力。美国内理性的对华政策谋士和专家曾不断呼吁美政府给予中国“应有的重要地位”,避免出现“对华政策是华盛顿后来才想到的事”这一局面。(注:Jonathan Clarke,"U.S.Needs to Leam That China PolicyIs Not a Two-bit Affair",Herald.International Tribune,May 11,2001.)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学者也敦促政府冷静评估中国军事力量,他们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应由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来驱动,也不要以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来左右”。(注:新华社联合国2001年5月11日英文电,马斯·比克福德:《中国军事力量的神话与现实》,载[美]《外交政策聚焦》,2001年4月号。)鉴于今后若干年内,中美关系将仍然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处理”的一双边关系,布什政府必须对华实行“更为有效的接触”。
从以往美国新总统上台到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时间来看,布什对华政策的最终定型还需要一段时间。从未来发展看,反恐合作的展开不会使中美之间的固有分歧烟消云散,以反恐战略替代美全球战略的认识更不现实,夸大反恐作为中美关系中的战略基石作用同样如此。反恐也不可能彻底改变美传统的地缘政治观。"9·11"后经过修改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仍刻意强调“亚太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潜力的竞争对手”对美构成的潜在危险,说明美国内保守势力调整思维观念何其难也,何况存在抑制中美安全合作的因素,主要在于“两国都有相当重要的力量仍怀疑对方的长远意图”。(注:David M.Lampton,"Small Mercies:China and America after 9/11,"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1/2002,pp.106~107.)凡此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仍将形成制约。但对抗毕竟不符合中国、同样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不应成为美现实的对华政策选择;另一方面,“接触”亦应该是全面和广泛的,片面的接触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接触”应以消除两国间的战略疑虑为优先考虑。美一些理性的政策建议也注意到,对华政策“在意识形态驱使下转向对抗将是严重的错误”。(注:[美]萨默尔·伯杰:《不要引起中国的敌意》,载《华盛顿邮报》,2001年7月8日。)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存在广泛空间并具有共同战略利益,这将真正决定中国崛起后中美关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