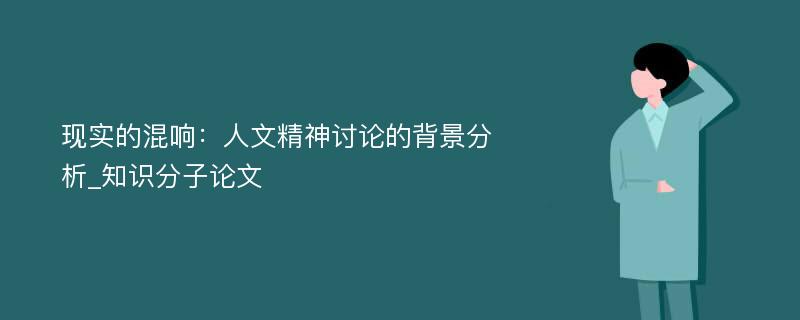
现实的回响——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现实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些年来的人文精神讨论,向人们提出了涉及意识形态敏感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与经济政治的转型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问题,知识分子的良心与终极关怀问题等等。它牵及了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吸引了部分自然科学家。其范围和意义进一步扩大。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宽松、自由的民主气氛,令人鼓舞。但是,也的确十分混乱。这不仅表现在重建的呼声既沙哑又嘈杂方面,还表现在那失落的感叹似乎与改革的步伐不十分合拍方面,就连争论的内容似乎都很难统一。因此,对之进行冷静、理智的梳理,从中引出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健康发展有益的东西,十分必要。
本文试图通过知识分子心态、农民的解放、商品经济与中产阶层崛起等几个现实问题的背景剖析,来认识这场讨论。
一
对知识分子,总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方面,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士,中国的脊梁,民族的精英。是通过科举等等途径直接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居庙堂之上的“达”士,庙堂之侧或者帘幕后边的师爷,山野中那些仙风道骨的飘逸潇洒之士。即便独善其身,把斟茅庐,也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刘备”三顾。因此,即使一贫如洗,潦倒落魄,人们也总是另眼相看。另方面,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什么“为学日深,为道日浅”之类的东西总是很难从人们心头抹掉。以至于要是填空的话,无论是在“文人”前边加个空,还是在文人后边加个空,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恐怕都是对知识分子不利的那些“无耻”、“无行”、“相轻”等词语。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民族走向世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交汇点上,经过了失落、苦闷、彷徨和欧风美雨的洗礼,直到五四才开始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自己的角色。一方面,真正的先知先觉——先百姓而知、先民众而觉——为唤醒愚昧麻木的民众而呐喊奔走,是实际上的启蒙人士和领导人士,启发和领导工农完成再造民族灵魂的历史课题;另方面,理论上又似乎是封建时代的“残渣余孽”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能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尚不十分充分,于是,就在前边又加了一个“小”字,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是“‘小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是“‘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是“‘小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一定还有“‘大的’或者‘中不溜’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大的”或者“中不溜”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是“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定还有“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中不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又是“大的”或者“中不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知识分子本身的两重性,导致理论认识上的模糊。理论认识的模糊,必然导致现实把握上的模糊。现实把握上的模糊,导致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
一会儿,实际上担负着“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一会儿,又要接受工农大众的改造,顶多是工农大众革命需要联合利用的对象,建国后一段时间一直是历次运动的对象。一会儿,“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臭老九”进牛棚;一会儿,老九不能走……8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欧风美雨飞飞扬扬,一些知识分子以为兼治天下的时机来临,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又让人感到,这个阶层,的确不如“工人可靠,农民可靠,解放军可靠”。
知识分子带着这样一些历史“问题”卷进了经济大潮。进入了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物化一切的时代。
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本质上是一场不流血的但却是最深刻的革命。它动摇着已经安排好了的秩序,迫使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家庭、个人都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价值,重新确认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知识分子,这个不具有经济独立意义的阶层,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虚空,都要尴尬。而知识分子导演的思想启蒙所举起的理性之剑,随着西方思潮的涌进与参照,最终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急剧变化,人们开始用充满怀疑批判探索精神的更加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
没有权,又没有钱,但却需要金钱吃饭买房雇保姆排队买豆腐,需要送礼办调动。从书斋里出来,脑子里还是宇宙社会民族,却迎头碰上老婆的抱怨:“窝囊废,自己的小家你都无力解决,国家民族大计,你操的哪门子心?”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如何完整地守住“兼治天下”的信念?“尽管我是个教徒,可也是个人呀?”面子、票子实在难以两全。即使自己领域里那些极少数的成绩突出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满身铜臭的大款倒爷们给自己颁发文学艺术奖。捧着靠了款爷们的赞助才能出版的自己的精神成果,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依附于政治,似乎天经地义。依附于金钱,总是感到“掉价”,总感到有点“太那个”,与文人雅士的身分不符,名不正言也不顺。可又无可奈何。越想越不是滋味,内心再也无法平衡。
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在这个物化时代和个人主义时代似乎格外苍白。一种新的观念出现了,天真淳朴的太初,亚当和夏娃也会犯罪,在这人心不古的时代,叫我可怜的穷秀才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天国的光辉暗淡了,魔鬼在牵引大家行动。一时间,文人雅士,“一地鸡毛”。有的干脆脱掉外衣,下海经商,美其名曰“儒商”。一下海,便露出了肉体凡胎的真面目。金钱面前,连神仙也不再神圣,寺庙里不食人间烟火的如来弥勒佛,也都伸出了手向香客要钱。文教卫生新闻等等诸多曾经被视为神圣的精神文化领域的“哈得莱堡”,也不再清高,不再纯洁。谁说思想混乱?大家一齐奔向经济中心。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都仗持着身(体)、心(灵)、内(知)、外(势),各显神通。哈得莱堡最后一位“诚实的公民”,却也禁不住习惯势力的诱惑,给滔滔商海败坏了,变成了“犀牛”。本来是,别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在某些地方却是,别管大老鼠小老鼠,别让猫逮着就是好老鼠。
“废都”里一批“文化人”的表演,更是惨不忍睹。知识分子头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揭了下来。此后,人们也就无所顾忌了。一批王朔们,以痞子自居,发挥刻薄之特长,嘲笑一切正统和尊严,通过嘲弄别人也嘲弄自己来玩世不恭地发泄对社会的无可奈何。
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把知识分子当做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来看待,——并且职业道德并不“怎样”的一种职业。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以下事实,知识不等于道德,学高为师并不等于精神导师。人们开始把知识与德行区分开来,把做学问搞创作首先看成是一种职业,同做买卖挣钱一样的一种职业,且职业道德决不是最好的一种职业。导电影与倒计算机和VCD的差别仅在于大倒与小倒。
但总有那么一批不合时宜的人。他们极力守住精神堡垒不放,对抗庸俗现实,呼唤道德重建,倡导英雄主义,大有堂吉诃德的悲壮与崇高。但是,声音似乎十分沙哑和微弱。
知识界关注的人文精神,实与文人精神纠缠不清。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终极关怀相联系的一种理性、批判、怀疑、探索精神,上下求索,对外在的宇宙和内在的自我的真谛的追求,对人类本性与前途的思考以及舍我其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二是对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新的金钱等级的人道的反驳,对主体的、个体的生命、力量、价值、人格、尊严等的看重,对人的爱护、关心与尊重;三是对随着经济政治的转型而必然出现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呼唤。
第一种意义是可取的,积极的。它道出了对20世纪西学取代国学以后思想文化缺乏理性批判的状态以及双轨制下既依附权力又依附金钱还依附西学的尴尬状态的不满。但是,也十分复杂。自觉或者不自觉对失去的显赫地位的感叹与各种各样的重建的呼唤,其本质,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一种复古怀旧心态,一种没落情绪。有意无意地对知识分子使命与地位的呼唤,既有着知识分子指点江山、兼济天下的宽广胸怀,又掺杂着对以往被人器重敬仰的显赫地位的怀恋与惋惜,还夹杂着对目前的金钱社会的无可奈何的怨恨与诅咒。
在其第二种意义上,则具有十分积极然而却被目前的讨论所忽视的关键的意义,这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自我意识、民主意识增强的表现:
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自我意识觉醒,农村改革的成功与亿万农民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大农民对人格尊严的意识与要求,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及其对政治法律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如平等自由,始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开放对比以及西方思潮的冲击,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在现今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领导时代新潮流的角色及其重实重信重自由重平等的观念,各种特权阶层的失落以及人民的地位的提高,等等,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素质提高了,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的意识增强了,人们意识到作为个体人存在的意义,因此,自我的人格、价值、尊严等的要求也相应地出现了。
另一方面,转轨所建立的新的秩序,本质上是以自由平等的竞争为基础、以金钱与利益为杠杆的竞争秩序。随着政治的社会中心地位被经济所代替,金钱越来越成为调节社会行为的重要的杠杆。金钱建立的新秩序新等级,在肯定了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同时,又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另一种意义上摧残否定了人的价值、人格和尊严。广大人民对金钱的威势同样发出了愤怒的抗议。这是一种人道的抗议,抗议之中包含着更高层次、更高意义上的对人性、人格、尊严、价值、力量的呼求。并且,这种呼求与那些感到失落的特权阶层对造成他们失落的新秩序的怨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十分富有时代特征的普遍而强烈的社会共鸣现象。
这种现象从80年代初中期就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的形式在思想界讨论。如果说80年代初中期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还是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局限于思想界、局限于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话,那么,目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更普遍的群众基础。因此,这决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内部的、仅仅有关知识分子的一场争论,而是人民群众自我意识觉醒、人格尊严要求的普遍心理在知识界的折射,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增强或者真正主人翁意识真正当家作主的表现。这是巨大的历史的进步。
因此,人民群众的普遍的意识心理,才是目前这场争论的基本的、主要的背景。知识界内部的争论,决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的社会心理要求在知识界的反映。
在其第三种意义上,则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考察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必需首先从这个时代的现实出发,从其经济政治形态出发。因此,考察目前我们的新的价值体系,必需从目前改革的现实出发,从改革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
事实上,就第三种意义而言,知识分子重建的努力,其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目前要建起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为时尚早。理论的先行探讨当然的是可以的,但是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决不是文人学者们在书斋里幻想和推论出来的,也不是哪一个思想伟人能够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社会现实、人民群众长期的实践等等各种内在外在因素、传统与现实因素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还没有充分地把它孕育出来。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是经济、政治的过渡时代,也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过渡时代。对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灵与肉的炼狱。知识分子像五四时期一样,又要接受另一种考验。但是,每一次的考验,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好机会。
二
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决不是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场讨论,而是整个社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我意识、民主意识觉醒的标志,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经济的变革历来是最深刻的革命。正是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时代里,中国农民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农村生产责任制带来了农民的全面的解放。
理论观念上,对人们个人利益的承认,打破了传统的“一大二公”观念,从哲学上把“公私对立”转化成“公私互补”或者“公私一致”(至少是部分一致),把斗争哲学变成合作哲学,这就从观念上迈出了由虚向实的第一步。
实践上,农业大国的中国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引发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化,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铺平了道路。
粮食问题解决,国家个人均受益。责任承包,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土地的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农民吃饱了,全国人民吃饱了,占世界人口1/4的农业大国的粮食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的解决,为农村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奠定了基础。
但是,事实上的人多地少(即使照人拉驴驮的生产力水平,土地也只能满足不到1/3的农民耕种),近2/3的农民在寻找出路。于是,“离家出走”,涌进城市;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办工厂搞贸易,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崛起了。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开始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把农民变成了农村工人;并彻底地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
农民真正有了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责任承包,农民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吃饭,不需批条吃返销粮也能活着!我一不偷二不抢,靠正当本事吃饭,谁也奈何不着我!我也不用去可怜巴巴地祈求巴结谁。农民第一次有了实实在在的人格和尊严,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于是,“乡场上”的冯幺爸挺直了腰杆,也有了胆量,站了起来,第一次“说了句公道话”,第一次感到自己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农民的解放,意义重大!把牢牢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再回头看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态,他们“失落”了,内心失去了平衡,“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打破了。他们要实现新的理想,寻找到新的心理平衡。这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思想观念改变了,思维方式也改变了。这样,他们的眼界开阔了,素质提高了。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在一个农民占90%以上的农业大国!
乡镇企业的崛起实现了农民梦寐以求的城市化理想。乡镇企业的崛起,真正缩小了“城乡差别”。很多乡镇,如山东临沂的罗庄,具备了比城市还要“城市”的条件,农民过起了比城市工人还要“工人”的生活。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这在从前把农村视为“发配”、“改造”的“广阔天地”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地位,中国农民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对自己的人格价值尊严也越来越看重。
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人道主义呼声出现的社会基础。也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潮被中国社会接受的基础之一。
农民在分化,农村中产阶层崛起。农村的专业户,及各种承包人,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这就是农村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充满活力,朝气蓬勃,领导了时代新潮流:他们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他们的愿望要求,越来越成为深沉的政治要求;他们的生活方式,为大多数人争相模仿;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个“人大代表”,或者点缀成一个“政协委员”,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要求自由与平等,自由地发财,平等地竞争,要求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他们的利益。
这样,他们的要求,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进程。民主制度不是在空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我国的历史和实现的交汇点上逐渐地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做基础,没有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做基础,没有主人翁意识的提高做基础,那是不可能的。
农民文化要求得到了重视,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农民的生存空间拓宽了,素质提高了,一直被压抑的潜在的能量也释放出来了,他们越来越为人们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愿望要求,他们的审美需求,他们的文化,等等。这样,农村文化也从土地上传播开来。
这股文化大潮冲击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冲击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冲击了中国的电影电视,冲击了中国的“雅”文化圈,冲击了中国的学术界。
这股文化大潮与农村生活方式相结合,酿成了文艺界返朴归真和反文明、反文雅的倾向,酿成了丙崽,酿成了莫言的“红高粱酒”,以反高雅、反正统、反文明、非道德的形式出现,波澜壮阔,给了几千年来在“存天理灭人欲”下喘息的人们以痛快淋漓的宣泄。
这股文化大潮与城市下层生活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市民世俗文学,产生了王朔,产生了一批“嬉皮士”。他们以玩世不恭的与正统道德对抗的面目出现,不受文明道德的约束,也没有生活信念。只知道“拉着妹的手哥的袖”,跟着感觉走,然后,“过把瘾就死”。
这股文化大潮与学术界相结合,与西方非理性哲学、文学相结合,产生了各种文化热:尼采热、萨特热、弗罗伊德热、百年孤独热、荒诞派戏剧热、荒诞派小说热、人道主义和异化热、辞书热、后现代热,不一而足。
这股文化大潮与高科技相结合,产生了卡拉OK、MTV、大屏幕、计算机算命等娱乐文化街头文化。
无论这些大潮的副作用是如何显而易见,如何之大,但有一点就是,在社会的民主和文艺的人民性方面,我们的的确确前进了一大步。
三
商品经济贯穿自由竞争和平等竞争的法则,把自由、平等竞争的机制引进社会各个领域。在这种体制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看重自己的人格、价值、尊严和力量,看重社会对个体人的关怀、爱护、尊重。因此,目前实行的商品经济具有强烈的反对残存的封建特权、反对残存的封建等级、反对残存的封建愚昧的意义。
商品经济对我国政治体制、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的影响是显著的。
商品经济促进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自由竞争需要民主制”(列宁语)。自由竞争使大多数与权力无缘的人民欣喜若狂。封建残余的羁绊不再约束人们,各种变相的进贡从法律制度上取消了。小人物敢于跟特权讲平等。广大人民要求健全各种法律,希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地竞争,自由地发财,并用法律的形式把自由竞争平等竞争的制度,把竞争的成果及其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固定下来。法律制度的完善,标志着我国民主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商品经济肯定了人的价值、尊严、人格和力量。利益的驱动,人们自主性的增大,种种人为的约束减轻,使人们不再混天聊日,许多底层的群众的聪明才智充分地表现出来,人们的创造力、主动性也充分表现出来,主体性的时代到来,人之为人的时代到来,普通百姓也有了自己的人格、价值、尊严。
是金钱建立了这种平等,弥补了小人物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金钱制度具有最彻底的反封建特权的作用。
同时,金钱又建立了新的等级制度,在另一种意义上,从另一个角度摧残了人的价值、尊严、人格和力量。金钱在摧毁残存的封建特权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等级制度。曾经是私下里交易及其人情行为公开化了,价格化了,物质化了;许多虚的、雅的、文的东西开始以明码标价的形式出现;似乎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文学艺术、电影电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金钱。唯利是图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准则。并且,双轨制使得权钱交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突出。金钱弥补了一般人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同时,金钱也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政治权力。这说明,金钱摧毁了许多应该摧毁的东西,也摧毁了许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如原则、良心等等。很多人追求金钱,把本是手段的金钱当成了人生的目的,最后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这样,金钱在肯定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的同时,又重新否定了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因而,对金钱抗议的人道的呼声四起。
商品经济导致新的价值观念。商品经济使得人们更加重实避虚;商品经济使得一切由暗转明;商品经济使得一切由雅转俗。比如,人才观念。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什么是才:能挣钱就是才;能挣大钱就是大才,能挣小钱就是小才;什么是德?有钱就能够有德;有钱纳税多,对社会贡献就大;有钱捐献就多,就能把良心道德之类的东西外化、物化,就是有德,就是光荣的人;有钱对社会贡献大,就有政治地位,就能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有社会威望。于是,门第观念受到了冲击。
商品经济,造就了中产阶层。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这个满身铜臭、粗俗欠雅的阶层,这个在改革中一点也不感到“失落”的阶层,却无论如何是中国社会最有活力和前途的阶层。它自明代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以后,几经磨难,终于在今天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上发展强大使得他们自然地要求政治上的权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然引发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经济政治的变化自然也会引起一系列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的变化。
他们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曾经支持利用学生、知识分子同“官倒”讲平等。他们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这就是,重实轻虚,讲求利益;已所不欲,勿施与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等等。
这个阶层的策略是,利用金钱这个武器,从经济上腐蚀拉拢,弥补政治权力的不足;或者把手中的金钱部分地转化成权力。权钱交易使得执政党经受着十分严峻的考验。权钱交易的实质是,一方通过钱得到权,成为新贵,这是一种财产安全保险之举;同时,又是一种投资行为,为的是使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另一方则利用手中的特权,出卖原则,转让部分权力,获取一定金钱补偿。
但是,无论这个阶层将来成为民主政治中坚后的表现如何,至少在目前,他们还多多少少与历史的进步、时代的要求有一致的地方,与人民群众有着某些一致的愿望和要求。这就是自由、平等、民主的要求,对人的价值、尊严、人格和力量的看重,对人的关怀、爱护、尊重的要求。
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分子的争论,并非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内部的事情,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的、是整个社会的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心态或者要求的反映和体现。如果只是侧重于理论上以西方思潮对人的认识的观念,而忽视中国的国情奢谈绝对的人格,忽视农业大国的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心解放的意义,忽视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分配方式以及由二者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价值观念,来讨论人文精神的重建,那是不现实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探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需弄清,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部分人一厢情愿地、主观地、人为地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人民群众长期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传统的与现代的、民族的和人类的文化精华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这次讨论要追溯到80年代初中期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讨论。如果说80年代初中期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还是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局限于思想界,讨论内容局限于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话,那么,目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具有更普遍的现实基础。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