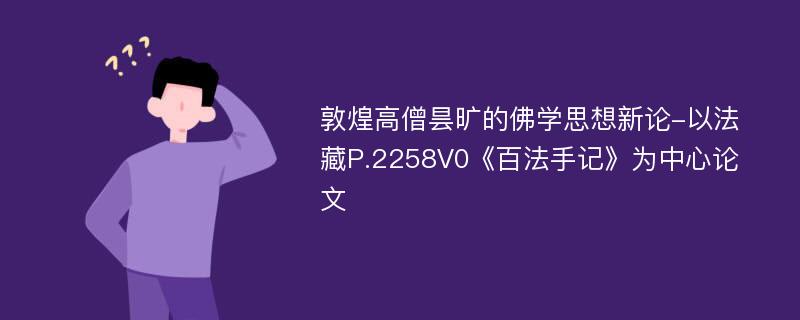
敦煌高僧昙旷的佛学思想新论 ——以法藏P.2258V0《百法手记》为中心
陈 兵 张 磊
[提要] 敦煌高僧昙旷的经历和佛学思想著作不见于历代藏经。敦煌遗书问世以来,人们发现存留有多种昙旷所撰写的佛学著作,从此中外学者开始探讨他的经历和思想。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有助于我们对昙旷自己最终成熟的佛学思想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以和昙旷有密切传承关系的《百法手记》为依据,对昙旷晚年的佛学思想主张做了进一步地探索,认为:昙旷批判性地继承了唯识宗的一些主张;关于心法的认识,依从《起信论》说;在涅槃观方面,与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所主张的一脉相承;在依时判教方面,不同于唯识宗,也不同于华严宗,而是直接将如来藏法性缘起宗安于第四时分上。
[关键词] 《百法手记》;昙旷;心法;熏习;涅槃;判教
自敦煌遗书问世以来,湮没于历史之中的敦煌高僧昙旷逐渐为人所知。由于他的诸多久已亡逸的义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他的兴趣与日俱增。中外许多学者开始探讨他的经历和思想,以及他在汉藏佛教交流史中的地位。比如上山大峻对昙旷接受《大乘起信论》(后文简称《起信论》)思想的渊源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在昙旷所生活的年代,自由的学风导致很多佛学者的思想主张和玄奘系的唯识宗学并非完全一致,这样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昙旷。昙旷在基于自身原有的唯识学的基础上,又接受了华严宗法藏所主张的“性相通融”的思想,以及为《御注金刚经》做疏的道氤的影响。上山大峻还从菩萨行、智慧、涅槃等七个方面解读了昙旷晚年所撰写的《大乘二十二问》。[1](P.17-83)巴宙也对《大乘二十二问》有过专门的研究,对每一问都有精辟的评论。[2]还有的学者如平井宥庆力图探讨昙旷的佛学思想与道氤之间的关系[3](P.333-337),加藤纯隆氏和释依昱都以昙旷所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后文简称《开宗义记》)为准,对昙旷的思想主张做了一定探讨。[4](P.390-401)另外,结城令闻对昙旷的佛学思想所依的传承也做了一定的说明,认为主要来自西明圆测。①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在没有对昙旷参学历程进行分期的情况下,将其所撰著作和其他同时代的佛学者的思想进行对比,虽然能够发现一些昙旷所受影响的来源,仍无助于我们对昙旷自己最终成熟的佛学思想主张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可能缘于他的著作所援引的学说较多,写作时往往各宗并陈;所吸收的思想没有一以贯之,以及没有固定专一的佛学宗师作为依止。
法藏敦煌遗书P.2258V0《百法手记》是以昙旷所撰《开宗义记》为教材的教学中,学生所做的笔记,产生于《大乘二十二问》之后。《百法手记》如同《开宗义记》一样,不容小觑。以“手记”或相近的名称而命名的文献在敦煌遗书中存有多号,亦成为学僧们学习领会《大乘百法明门论》(后文简称《百法论》)内涵的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其中蕴含的佛学义理非常丰富,有助于我们对昙旷本人的佛学思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昙旷的参学经历
矢吹庆辉根据昙旷所撰写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后文简称《开宗义决》)前自述的求学履历、所撰著作、弘法经历,以及其所撰写的《大乘起信论略述》序言,大致描述了昙旷的生平。[5]后来,芳村修基以S.02436号《大乘起信论略述》尾题记、S.00721号《金刚般若经旨赞》卷下尾题记、《开宗义决》前的自叙经历、S.01313《开宗义记序释》尾题记,以及S.2674号《大乘二十二问本》尾题记等信息,勾画了昙旷从公元763年到787年的教化活动的年限。[6](P.23-28)其后上山大峻对对与其经历相似的乘恩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1](P.20-31)
我们可以将昙旷的生平分作四个时期:第一时期:生长在敦煌,初学《俱舍》《唯识》,自觉“冥昧,滥承传习”[7](P.1068上),对于其中感到疑惑的问题,渴望得到圆满的解答,这或许是促使他“滥承传习”的原因之一吧;第二时期:求学于西明寺,受到自由学风的鼓舞,以及《金刚经》《起信论》思想的启发,奠定了他以后进行思想会通的基础。西明寺求法,在他的参学生涯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第三时期:回返敦煌,对多年来的学习生涯进行学术总结,相继完成了《金刚般若经旨赞》(朔方,今宁夏灵武)、《大乘起信论广释》(凉州,今甘肃武威)、《大乘起信论略述》(凉州,今甘肃武威)、《大乘入道次第开决》(敦煌)、《开宗义记》(敦煌),或许感到《开宗义记》很多初学者仍然难以读懂,于大历九年(774年)又撰写了《开宗义决》(敦煌),对《开宗义记》进行解释。但有些认识在这一时期仍然不能得到彻底转变,比如关于对心法的认识,在《开宗义记》和《开宗义决》中并没有明显的思想倾向。第四时期:教学相长,经过长期授课,一些观念逐渐成熟。
基于以上分期,可以初步看出昙旷成熟的佛学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第四个时期之后。《百法手记》中的思想应当能较多地体现昙旷本人的真实主张。即并没有全盘否定唯识宗学,而是在继承其说的基础上,也给予以《起信论》为代表的法性圆融思想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 P.2258V0《百法手记》的内容组成与讲解风格
通过多个比喻,以“俱生俱灭”说明能熏和所熏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一)内容组成
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心智模式事关企业传承,如何让海归新生代企业接班人,能够在融入中国情境的基础上,用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管理理念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发挥自己的胜任力,顺利完成企业接班的任务,就成了亟须解决的课题。
《百法手记》讲解者经常引用经论著作,有的注明出处,有的不加以注明。这些著作甚多,其中译介的佛经共有12部。引用《楞伽经》的次数最多,又以唐译《楞伽经》为重。其次是北本《大般涅槃经》。所借鉴的译介论著中,虽然《瑜伽师地论》最多,但所引无一关涉唯识宗所不同于其他宗派的思想。中土义学僧撰写的论著中,引用澄观、昙旷较多。从所引文字的出处、次数来看,《抄》的次数最多,高达16次。从讲解内容揣测,《抄》应当是一部讲解《百法论》的重要注疏。经过文字检索,确实有一些相应的出处:如《百法手记》:“一意识宗者,合前六识,如《抄》自明,合后三识,以为一识,合前合后,号为一意识宗识等”句,在《开宗义决》有相应说明,作“《摄论》所说一意识宗等者,彼论所引一意识菩萨所宗之义,而不破斥。彼合前六,但是一识,由依六根,别取六尘,开六识名,非有六识,兼第七八,总有三识”[7](P.1075中)。又如《百法手记》“《抄》云,恶作唯净,四非是染者”句,乃出自昙旷所撰《开宗义决》卷1。[7](P.1085中)但仍然有些引文在《开宗义决》中找不到依据。那么是否为正面P.2258号《百法论疏抄》呢?从笔者对该号的初步录文中,发现该号文献所摘抄的内容大部分照搬自窥基的著作,应该并非《百法手记》中所说的《抄》。
此外,对《大乘二十二问》的引用也较多,也暗示了《百法手记》讲解者与昙旷的密切关系。
(二)讲解风格。
《百法手记》共计三万余字,所疏释的名词文句共计三百余条,讲解过程并非照本宣科,而是融进了自己的感悟。《百法手记》结构特点与讲解者的讲课风格、佛学素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从《百法手记》的结构和零碎的言语之中,去了解讲解者的佛学思想。
抬高底板法分为将建筑物高度整体上移和降低地下室层高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均是通过减少地下建筑物在水中的深度来达到降低水浮力的目的。但是,抬高地下室底板法会影响建筑物的设计功能或增加建筑物的总高,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工程,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
第一、按照《开宗义记》的内容依次有选择性地摘取若干名句进行解释,可知主讲者是昙旷忠实的追随者,但这并非站在先行对《开宗义记》全文整体结构的剖解的基础上而讲述,和传统注疏先行分门的叙述风格大相径庭。
第二、讲解中时常穿插众多相关经论的内容,可见讲解者是一位饱学之士。
第三、讲课者非常细致,显示了独有的风格,比如以“夫者,发语之端绪也”作为开场白,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这是在普及汉语常识。类似的解释,在文中有多处。
第四、在诠释方面,讲解者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定的讲述。如“遍知者,谓凡夫迷暗,都名不知。二乘虽知,知有分齐。起智不遍,不得遍知。地上菩萨,超过前二。世出世间,虽则有知,犹具微细障故,不能同佛,号曰遍知。唯有如来,遍知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心心数法,名曰遍知。”
所谓“遍知”,唯识宗典籍《显扬圣教论》认为包括“所遍知事”和“所遍知义”,前者指五蕴、六根、六境等内容,后者指世俗的道理和涅槃、空性的道理,以及诸如法性、三世等内容。[8](P.502中-下)而《百法手记》的讲解者却说“遍知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心心数法,名曰遍知”,即周遍了知一切众生的心王和心所的内容,这似乎是从佛所具有的无上神通力的角度来进行诠释的。讲解者所依应来源于《大智度论》,该论认为“遍知”不仅能够周遍了知苦集灭道四圣谛的道理,[9](P.71下)还认为佛具有不共于声闻、辟支佛、菩萨的种种遍知力,如知众生三世诸业、一切道至处相、心心数法因缘果报、众生烦恼因缘、禅定解脱因缘等。[9](P.237上)
第五、有时,讲到后文,发现前述有所欠缺遗漏,则再进行补充。如所讲解的词条“分别诸法自共相”,此是《开宗义记》文前“论: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至“然八识义,差别无边,恐文繁广,略示纲要”[10](P.1049中-1055中)段中所述心法中名词,却于后文讲解,并随后援引三师关于“无表色”内容的辨答。
Conclusion: hybrid technolog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horter duration of surgical intervention,a low amount of blood loss and a lower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arly periods.These findings open new prospects for revascularization in persons with severe comorbid pathology.
第六、透露出了令学人借助《百法论》入门的用意。
第七、《百法手记》中还有36处答疑的内容,可以想见课堂上学僧们学习的热情,而讲解者也会不厌其烦地进行详细解惑。
三、 P.2258V0《百法手记》的思想义蕴
(一)唯识学的观点。
在心法的认识方面,在心识的善恶无记三性、阿赖耶识的似一似常、识四分说及识产生作用所需的条件、依根立识名的原因、异熟的认识和唯识宗还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尚有对阿赖耶识非断非常方面的认识:
赖耶不断不常者,此识念念生灭,当知刹那相续,非断非常,果生故非断,因灭故非常。
又如以麦子和芽的关系为例,说明阿赖耶识和七转识互为因果的关系:
《抄》中云,凡因与果虽定一异等者,如麦子生芽,子之与芽非一,离子无芽,离芽无子,故非异。今此前七为因,第八为果,何者?第八种子是前七熏;第八为因,前七为果,何者?从第八起种子者故为因,第七已前,现行为果。因之与果,如麦与芽,不可定一,不可定异。何者?前八即现行为因,第八为果,所以不可一异。赖耶三相之中,果相者,即是我□身,是此身是赖耶所感之果。
另外,在解释《百法论》中的心所法时,以《成唯识论》为依据进行解释;在修行阶次方面,《百法手记》云“位阶加行者,即地前四加行也。依《唯识》《杂集》,始从凡夫位,终至佛果。中间修行,阶分五位”,引用了包括唯识宗在内的大小乘各宗所共许的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究竟位等五位,并随文对每个位次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载于《成唯识论》卷十中的“六转依”[11](P.680-681)亦被《百法手记》讲解者在回答关于“转依中,报身亦断二障,法身亦断二障,此二何殊”的问难中提及,并被昙旷所重视而将《成唯识论》关于“六转依”的讲解全文引入至《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卷一中。
(二)法性圆融思想
这部分思想主要集中在对心法的认识方面:
第一、阿赖耶识与如来藏
之后,昙旷于回答的后半部分又详细地论证了声闻涅槃和佛涅槃是绝对不相同的。这个论证的部分在《百法手记》中亦有显示:
所言心者,谓八现识。由有三义,并名为心。一、缘虑义,攀缘思虑一切法故;二、贞实义,是一切法之体性故;三、集起义,集诸法种,起诸法故。[10](P.1049下)
然而窥基在《大乘百法论解》卷1中指出:
心法者,总有六义:一、集起名心,唯属第八,集诸种子,起现行故。二、积集名心,属前七转识能熏,积集诸法种故;或集起属前七转现行共集,熏起种故;或积集名心,属于第八含藏,积集诸法种故。三、缘虑名心,俱能缘虑自分境故。四、或名为识,了别义故。五、或名为意,等无间故。六、或第八名心,第七名意,前六名识,斯皆心分也。[12](P.47上)
两相对比,后者唯独没有包括“真实(贞实)义”。那么“真实义”究竟指什么呢?昙旷在《开宗义记》中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开宗义决》中虽然罗列出《楞伽经》的缘虑和真实二种心,也没有给出自己的主张。[7](P.1074上-中)但是《百法手记》中有一大段讲解内容:
明真实义者,是第八识能遍生一切法,眼变色等,若无真实之体,何能变生世出世间男女活业等事?
唯识宗认为阿赖耶识是一切万法的总根源,是一切现象生起变化的根本原因。但唯识宗认为第八识中的种子遇到合适的条件方能变现万事万物,本质上仍为杂染。上文后“若无真实之体”所要接续的内容则完全呈现出了《百法手记》讲解者的真实意图:
此心有二分:一、染;二、净。染分受生灭,净分不受生灭,是诸法体心,真如门是。
一、真心,二、妄心。真心者,梵云干栗大,此云坚实义,犹如树心,坚硬不变,说真心矣;二者妄心,梵云质多,即缘虑心,此心多能缘诸法影像之质,此质像多故,虚妄计度,攀缘前境,故名质多。攀缘者,前心攀后心缘,同刹那中便缘之。
若论其心,有其二种:一、性;二、相。性则真无生灭相,乃安有攀缘?故《起信论》云:阿利耶即生灭门,其如来藏,体无生灭,即是真心,由无明风,熏此真心,而有相生灭阿利耶,而受生灭故,云但业相灭,而躰不灭。其《起信》宗妄熏来藏,唯识妄熏第八心,唯识所熏,要须生灭,真无生灭,坚不受熏。然《起信》宗真净法界,摄一切法,(迷?)之是妄,悟乃成真,妄相熏理,悲□矣。
我们知道,《起信论》所讲的阿利耶识是一种代表清净而不生不灭的真如和代表染污而生灭变化的无明的和合体,而分两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13](P.16),显然《百法手记》所云“真实义”即主要依《起信论》之说而述。故而所谓“真实”即为“真如”,这个意思在《成唯识论》卷2所引述的“然契经说心性净者,说心空理所显真如,真如是心真实性故”[11](P.119)也有显示。
第二、熏习观
Pscr为静力触探比贯入阻力,MPa;ps0为dw=2,du=2时,比贯入阻力标准值,MPa;αw为地下水位埋深影响系数,地面常年有水且与地下水有水力联系时,取1.13;αu为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影响系数,对于深基础取1;dw为地下水位深度,m;du为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m,计算时将淤泥和淤泥土厚度扣除;αp为与静力触探摩阻比有关的土性修正系数。
为了形像地说明现行的一切活动是如何熏染第八识而形成新的种子,唯识宗特别注重“熏习”这个词语:
曹爽和他的同党们,很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何晏也没能逃过一劫,史书上以最为简单暴力的三个字,记录了他的下场:
何等名为薰习?薰习能诠,何为所诠?谓依彼法俱生俱灭,此中有能生彼因性,是谓所诠。如苣蕂中有花薰习,苣蕂与华俱生俱灭,是诸苣蕂带能生彼香因而生。又如所立贪等行者,贪等薰习,依彼贪等俱生俱灭,此心带彼生因而生。或多闻者,多闻薰习,依闻作意俱生俱灭,此心带彼记因而生,由此薰习能摄持故,名持法者。阿赖耶识薰习道理,当知亦尔。[14](P.134下)
法藏P.2258V0《百法手记》所汲取的诸宗思想很多,有的同等并列,不置可否,但在心法方面的观点,展现了不同于唯识宗的特色。
《起信论》卷1也表达了此义:“熏习义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于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气”[13](P.75-76),故而凡是身语意之业行,如同香气熏衣,必定会在第八识里留下印痕而于将来遇缘成果。《百法手记》讲解者指出:“不思议熏者,谓真自熏,真为◇真如性,前念、后念相续,自熏不令断绝,始有法体。若不真熏,真者法体,断绝无有归凭也。”
然而,有人对熏习义提出了质疑:“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本性清净,何得今日流转生死?”这确实是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按照唯识宗本有新熏义,既然先天地存储无漏种子,为何还会流浪生死,无法解脱?在这里,唯识宗采用了“依附”说,或者云“寄存”说。如《成唯识论》卷2认为“种子者,谓异熟识所持一切有漏法种,此识性摄,故是所缘。无漏法种虽依附此识,而非此性摄,故非所缘”[11](P.143),卷2又云“诸无漏种非异熟识性所摄”[11](P.108),很清楚地表明异熟识(阿赖耶识)不能摄清净的无漏种。说明“依附”和“摄”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但这仍然令人比较难以理解。而《摄大乘论释》卷3则云:“此闻熏习种子所依,云何可见?乃至证得诸佛菩提。此闻熏习,随在一种所依转处,寄在异熟识中,与彼和合俱转,犹如水乳,然非阿赖耶识,是彼对治种子性故。”[15](P.333下-334上)通过“寄在异熟识”的形容方式似乎更好理解些。“依附”仍然有从属的意味,而“寄”则有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意味。如此,即可知晓无漏的种子有一定的独立性,只是寄存在第八识中,并非构成第八识自体的形成因素。
256排螺旋CT冠脉成像检查:CT仪器为飞利浦公司提供,上缘扫描部位为气管隆突下10mm,下缘至心脏膈面,首先进行平扫,平扫结束后看,对患者实施增强扫描,注射对比剂,注射剂量为50ml,注射速度控制在5ml/s,使用仪器为高压注射器,注射完成后,实施图像扫描,将扫描数据返回工作站处理,对检测数据进行曲面、三维重建数据等方式处理图像,主要观察患者的左、右冠状动脉、左回旋支、左前降支的血管成像情况。
但是讲解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情虚妄,起不觉知,便有一分真如之性,流在生死,名随染真如、随惑真如,若不随染惑者,即名性净真如”,正好符合《起信论》的思想。
讲解者还将《起信论》之说和空宗做了比较:
式中,CL、CS分别为液相、固相比热,W/(m·K);分别为液相、固相介质的焓,J/kg;Tmelt为相变温度,K。
不思议熏者,是微细自性无明,此无明微细故,不可知其初始,名不思议也。被此无明熏本法性,真如之理,便有一分真如,流在生死,名随染真如。不思议变者,被无明熏已,变真如为有相,在生死中,为赖耶之体,名不思议也。如世间人将金销熔,其金被煎通已,任运随流,金体不改真如之性,虽随生死染时,其性不异,此诸本性,本自无生,从此一分,无生理上,生其一切诸妄法,纵生之时,性亦无变。
即无始无明熏染法性真如心,致使真如心被染污而流转生死,而真如心亦因之成为有相之赖耶之体,如金熔化而随入一切杂物之中,然金本性仍无有变异。
唯识宗依《解深密经》主张三时说,并将整个瑜伽行派列为第三时说。《百法手记》讲解者在评论《百法论》成立的所依时指出:“了教者,谓第三时教。性相俱备,说八识二无我处,即是了教大乘,何故说赖耶之处,得名了教?有何功能?赖耶之识,如世之王,行于大路,无人拥滞,能与五趣四生,而为报体。是以言究竟,当知即是了义”,认为《百法论》即依此第三时了教而立。在《百法手记》后半部分解释心所法中,认为“实理者,后为上智之人,说第三时教,不有不无之理也”。从此看来讲解者还是认可三时说的。
顿教大乘,不作如是。一切诸法,但是因缘,假和合相,妄心所生,非如上说。即此相现,摄持因果为自体相者,相即体也。即此者是第八识。此识能执持因,即是种子果,即是身形。以种子身形二法为自体因果。
从上面对疑难者的回应来看,讲解者在这方面比较依从《起信论》。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和唯识宗说的不同呢?杨维中对此做了很恰当的评价:
文章发出,读者给我们算了一把后留言:“250万瓶,28年,平均一天要尝245支酒,是我的数学不好还是肝不好?”当然,计算是没有问题的,侍酒师的职业也的确很特殊,而且还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葡萄酒销量相当大的市场。我转到侍酒师群里,也引发了一轮热议,大家纷纷要求求证。
在随机森林的基础上,尝试结合多种算法策略[2~4]。表2显示了随机森林结合各算法策略取得的结果。其中,line1表示Danger过采样方式的Borderline1策略,line2表示 Danger过采样方式的Borderline2策略;SVM表示Safe采样方式的SVM策略;M1表示只对过采样后的均衡数据进行训练,M2表示对过采样后的均衡数据和扩充数据合并训练;Tomek表示Tomek策略,ENN表示ENN策略。
这里,可能存在着这样一条发展线索:早期唯识学实际上并未完全将‘正智’与真如分开,反映在心性问题上就有了‘真如心’的提法,并以‘真如心’为第九‘无垢识’。后期唯识学则走的是真如与‘心识’两分的理路,并且以无漏种子解释佛性。尽管这是不同的两种路向,但佛性内在于众生之心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16](P.46-47)
(三)涅槃观
在涅槃观方面,《百法手记》直接吸收了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本》第十九问中的内容,其中所说的“三昧酒”出自唐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卷3,[17](P.607中)“三昧酒所醉”之语被窥基、遁伦、法藏、澄观等佛学者引用于自己的著作当中。
该十九问关于声闻是否能证取与佛同样的涅槃的疑惑,昙旷做了详尽的解答。根据巴宙的诠释,概括成四个方面:
一、以方便法门,佛陀提议说佛与声闻能证得同一涅槃。此为小乘宗的立场。二、佛之涅槃是‘万德具足,众善斯圆’,唯佛能证取,非声闻所能分享。三、声闻涅槃是有余涅槃,那与大乘的无余涅槃恰好相反。四、关于两种涅槃同一之说是小乘宗的邪见。[2](P.44)
讲解者以《开宗义记》为教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诠释,疏解内容得以大幅增加,字里行间折射出一种澎湃的激情,因此笔记的内容显得较为零乱,大致分成七个部分:(1)心法;(2)心所法;(3)色法;(4)心不相应行法;(5)无为法;(6)解脱论;(7)问难与答疑。
《开宗义记》中,昙旷认为:
变易生死者,是意生身者,言意生身者,能觉了诸法如幻相等,意无所有,得如幻三昧,及余无量诸三昧门,无相之力,自在神通,妙花庄严,迅疾无碍如意,犹如幻梦、水中月等,非四大生,似四大相,具足身分,一切修行,得如意自在,随入诸国土大众之中,名意生身。其意生身大小有别,小乘意生身者,初果罗汉化火焚身,入灭尽定多劫,不觉生力消时,或遍大悲菩萨觉观此人,神力加持,游历佛国,莲花化生,回心向大,遇佛闻法。大乘意生身者,地上菩萨以大神力,随令法生十方净土,出生入死,行乐有情,不同二乘,要人导引,方能游往也。十地菩萨有三种、六种等意生身,如《廿二问》中明。
“互联网+”为民族体育旅游提供了一个高效、便捷和互动的宣传推广平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端定制式的民族体育突出旅游环节服务的高品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其高端性、民族性特征。借助完善的网络APP工具将旅游产品展示给消费者,详细描述产品特色和详细内容,让更多消费人群了解民族体育,从而激发消费的欲望。二是,能够为客户提供高端产品的网络定制渠道,与客服人员实时沟通大大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效率。使定制服务更为顺畅。三是,可以为用户提供购买、支付、查询等功能。随着完整的旅游产品预订流程的建立,将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旅游信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提高游客体验。
此段内容亦和《大乘二十二问》第十九问相关。昙旷认为:“所灭心者灭六识心,岂能灭得阿赖耶识?所焚身者焚分段身,岂能焚得变易身相?……阿赖耶识不可断故。法尔皆有,变易报续。此变易报名意生身……意生身上六识不行,如重醉人都无所觉。后灭尽定势力尽故,佛悲愿力所资熏故,还从定起如重醉醒,见意生身在佛净土,始知不是无余涅槃……”[2](P.90)最后认为:二乘涅槃与佛同,是不定言,执见小乘,妄兴此论[2](P.90)。昙旷仅对小乘进行了阐释,而上面《百法手记》讲解者从大小乘意生身的区别方面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小乘有如昙旷所说的欠缺,而大乘菩萨获得意生身后却能随意自在前往十方净土,生死自在,利乐有情。
(四)依时判教观。
接着讲解者对空宗的观点做了评价:
我对老爸说:“你当初如果苦点累点,我现在就是富二代了,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老爸:“嗯,有道理,不如这样,你现在苦点累点,以后你孩子就是富二代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凭啥?哦,我现在受苦受累,白便宜那小子了。”老爸:“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于《百法手记》中间部分,在列举了包括唯识宗所主张的三时判教说在内的从一时到五时的判教思想后,认为“始从一时,乃至五时,皆无证据者,如上所立,菩提流支早已厈破,故亦非理,此论恐繁不叙”。对包括唯识宗三时说在内的五种判教说都不认同。菩提流支既主张一时教,也主张顿教和渐教二分法,顿、渐二分不在《百法手记》讲解者所罗列的五种判教说之中,依时判教方面是否倾向于顿、渐二分法?而此正被窥基所反对,理由是“以三乘人渐次修学,名之为渐,以行为渐,非约教时”[18](P.248上)。
讲解者另外参考了华严宗法藏所撰《大乘起信论义记》卷1中的四宗分法(小乘宗、空宗、唯识宗、如来藏缘起宗)[19](P.242),在法藏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四种理门差别”和把四宗归属“四时”,不同于法藏所认为的四宗没有前后时限差别的观点。所谓“四种理门差别”,即“因缘、唯识、无相、真如”,是就教体而说的,侧重于观门方面,最早出自于《瑜伽师地论释》卷一,[20](P.883中)后来被窥基介绍到所撰《说无垢称经疏》卷一中。[21](P.1000中)而于四宗之一的“法性缘起宗”(即如来藏缘起宗、法性圆融宗),则被安置在一个独立的第四时。这和讲解者所赞同的将大乘宗三分作空宗、唯识宗、法性圆融宗的观念是相应的。讲解者首先指出以前所立大乘唯有二宗,一者“胜义宗,远承文殊,近是龙猛、提婆、青弁、青目等,此上诸德,见诸众生,于佛灭后,示百岁中,著于有见,于无想教中观菩萨论,遂立此论宗,破诸有见。此宗云,于西方南印度境,从南海水路而来,至汉地王南京南凉府,号曰南宗”;二者“应理圆实宗,远承弥勒,近是无著、世亲、护法、护月等。诸德复见众生,佛涅槃后六百年,外九百年中著于空见,依《深密经》《瑜伽》等论,遂立此宗,破其空见,此宗出自西方北印度境,从北海北水路而来,至汉地北京太原府,厥号北宗”。前者显然是中观学,后者却有特指:“应理圆实宗者,亦云法相宗,亦云唯识宗,亦云渐宗,亦云北宗。此宗云说一切法唯识变现,而说人我及法,种种皆内识心,转似外境,诸有情类无始来,缘此执为实我实法,是故当知而无外境”,局限于玄奘系的唯识宗学。接着讲解者对这种二分法提出批评:“既有二宗,如是差别,详此文义,析义不尽,谓不摄彼性智宗,故此之二义,但约义分,非是究竟,各得一边,不融理者,则生乖诤”。因此主张再增加“法性圆融宗”,或者说“法性宗”“论中宗”。道氤对当时学者关于该宗的评论有所介绍:“依胜义门,破遣诸法,为究竟故。《花严》《涅槃》《楞伽》等经,《宝性》《起信》等论,皆法性宗。彼依法性如来藏门,融会诸法。为究竟故,乃至立一味之理。”[22](P.13中)可见如来藏法性宗的思想被认为有“融会诸法”的功能。
除了上述思想主张外,在因果关系方面,昙旷的认识也有所体现,如对“因果两相无别”的解释部分,即来自昙旷《开宗义决》[7](P.1069中)
结语
唯识宗自从创立之后,学者对之持有不同的见解。起初圆测被唯识宗人判为异端,继之圆晖对唯识宗思想进行了批判,力主《起信论》真妄相熏说,[1](P.73)华严宗法藏也大力主张《起信论》思想,在那个自由学风的年代,锋芒渐起,逐渐掩盖了唯识宗的光辉。
昙旷,作为来自四大文明交汇之处的敦煌地区的学者,深受这种自由学风的鼓舞。他晚年所撰写的《大乘二十二问》及其后产生的《百法手记》成为我们窥探他成熟思想的重要的文献。依据《百法手记》,我们对昙旷的佛学思想主张做一总结:
第一、昙旷批判性地继承了唯识宗的一些主张,不仅在《大乘二十二问》之第十五问中有所体现,在《百法手记》中也有所显明。
第二、对心法的认识,依从《起信论》说。
受传统农业生产理念的影响,当前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还一直采用传统形式,整体效率不高。在国家大力倡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之下,加大对于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是当前农民培训过程中应该给予重点关注的问题。农民科技教育中心承担着重要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职责。因此,应该不断强化农民科技教育中心的管理质量,促进培训质量不断提升,更好的为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服务。
第三、在涅槃观方面,与《大乘二十二问》所主张的思想一脉相承。实际上,《百法手记》有多处言之《大乘二十二问》,并提示座下学僧参阅,说明讲解者与昙旷的师承关系可能性很大。
第四、在依时判教方面,既不同于唯识宗,也不同于华严宗,而是直接将如来藏法性缘起宗安于第四时分上。
2.3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后对疗效予以随访与评估,观察组患儿中有1例出现感染,1例发生电解质紊乱,1例为血小板减少,不良反应率为10.0%,与对照组的36.7%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注释:
①笔者未寻得加藤纯隆氏和结城令闻的论文,释依昱在《昙旷与敦煌写本〈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的研究》中对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有所介绍,分别参见第399-400页和第392-393页。
参考文献:
[1][日]上山大峻.敦煌之佛教[M].京都:法藏馆,1990.
[2]巴宙.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M].台北:东初出版社,1982.
[3][日]平井宥庆.敦煌本道氤集《宣演》と昙旷撰《旨赞》[J].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5(3).
[4]释依昱.昙旷与敦煌写本《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的研究[A]//杨增文,杜斗城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二)[C].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
[5][日]矢吹庆辉.鸣沙余韵·解说篇[M].东京:岩波书店,1933.
[6][日]芳村修基.河西昙旷の传历[J].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58(12).
[7](唐)昙旷.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A]//大正藏(第85册)[Z].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8.
[8][印]无著.显扬圣教论[A]//玄奘译.大正藏(第31册)[Z].
[9][印]龙树.大智度论[A]//鸠摩罗什译.大正藏(第25册)[Z].
[10](唐)昙旷.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A]//大正藏(第85册)[Z].
[11][印]无著.成唯识论[M].(唐)玄奘译,韩廷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唐)窥基.大乘百法论解[A]//大正藏(第44册)[Z].
[13][印]马鸣.大乘起信论[M].(梁)真谛译,高振农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印]无著.摄大乘论本[A]//(唐)玄奘译.大正藏(第31册)[Z].
[15][印]世亲.摄大乘论释[A]//(唐)玄奘译.大正藏(第31册)[Z].
[16]杨维中.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7]大乘入楞伽经[A]//(唐)实叉难陀译.大正藏(第16册)[Z].
[18](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A]//大正藏(第45册)[Z].
[19](唐)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A]//大正藏(第44册)[Z].
[20]最胜子.瑜伽师地论释[A]//玄奘译.大正藏(第30册)[Z].
[21](唐)窥基.说无垢称经疏[A]//大正藏(第38册)[Z].
[22](唐)道氤.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宣演[A]//大正藏(第85册)[Z].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6—0077—06
作者简介: 陈兵,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张磊,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四川 成都 610065
收稿日期 2019-03-20
责任编辑尹邦志
标签:《百法手记》论文; 昙旷论文; 心法论文; 熏习论文; 涅槃论文; 判教论文;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