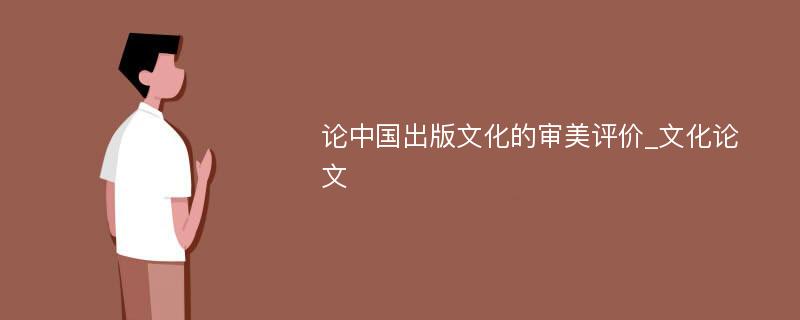
中国出版文化审美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纵的方向看,一个历史时期的出版文化状况,是衡量该时代科技与文化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横的方向看,一个国家出版文化发达与否,是该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出版文化于一国、一时代的重要性,世人已有共识。我国之所以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我源远流长的出版文化密切相关。令我华夏民族自豪于世界的、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中,有一半属于出版文化。世界著名学者英人李约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西有关出版文化的发明作过有力的对比:纸的发明,中国早十个世纪;雕版印刷,中国早六个世纪;活字印刷,中国早四个世纪;金属活字印刷,中国早一个世纪。今日中国亦世界上出版大国之一。因此,对中国出版文化进行包括审美在内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极有必要。本文仅从图书出版论说。
一
中国出版文化的审美本质,笔者以为在尽善尽美、以善为本。
在轩轾《韶》、《武》这两部音乐作品时,“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①]孔子认为,《韶》乐与《武》乐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美的最高要求,都是“尽美”的;但歌颂舜德、揖让、仁政、礼治的《韶》乐达到了“尽善”的境地,而歌颂周武王以武功得天下的《武》乐,在思想上尚未达到“尽善”的境地,所以《韶》乐高于《武》乐。孔子要求的是美与善的统一,他认为美、善统一才是一种完美。当然,这里的“善”,是按孔子的标准而定的善。历多年搜辑、整理、删选而编定《诗》(即《诗三百》、《诗经》)的孔子,堪为中国最早的图书编辑家。他编《诗》的美学思想便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思无邪”的“思”是指思想内容、道德准则,“无邪”就是“正”;正而不邪,就是审美上常说的“善”。又,《大学》曰:“惟善以为宝。”中国出版文化尽善尽美、以善为本的审美思想,肇于孔子、儒家;此后,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而一以贯之。
近代新式印书馆的问世,是中国出版文化飞跃的标志。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当是这一飞跃的里程碑。商务印书馆事业的主干是张元济。张氏的出版思想即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宗旨。张氏加盟商务印书馆之始,便提出商务印书馆承担的出版文化使命为:“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③]除积累文化、传播文化之外,教育性亦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商务印书馆负荷的使命与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教育性是一致的,其审美特色首先是“善”。当然,出版文化的教育属性的体现,并不仅仅在于狭义的教育,而是广义的教育。以出版开启民智、普及文化、自强救国、优化民族性、促进社会进步是张元济、章锡琛、邹韬奋、陶行知、胡愈之等大批出版文化人共同的出版鹄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责任心。中国出版文化的注重社会责任感,便是“尽善”。陶行知在《生活教育出版部招股缘起》中正是这样标举其出版文化观的:“以增进教育效能,而提高民族文化。”[④]开明书店自1926年开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之所以敢说自己二十八年间未出一本坏书,乃是本于其“求义”精神。它的求义精神便是:“不向钱看,只想勤勤恳恳地出几本书,老老实实地给读者送一点温暖。”[⑤]开明书店只出好书、不出坏书的“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善”。在近现代中国,出版社如林,论资历、人力、物力、财力,开明远不如“大腕”们,但实践与历史证明,它的业绩、影响、口碑,已与出版界大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足鼎立。得以如此,首先在于其求义—兢兢业业地为社会出正正经经的图书、勤勤恳恳地给读者送实实在在的温暖,这就是求善、得善。显然,出书向钱看,而不顾其社会效果,是不善的行为;出书诲淫诲盗、不择手段乃是恶。政府近年频频发起书刊扫黄运动,其审美实质是除恶求善,使出版文化尽善尽美。须知:只有尽善,才可尽美。扫黄运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出版文化以善为本位的审美特色。
中国出版文化的这一审美特色,表现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出版史上大工程—《乾隆版大藏经》的重版发行,赵朴老评之为“功德无量”[⑥]。这“功德无量”便是善。这个“善”,不惟是佛家之“善哉善哉”,而是具有审美范畴与道德范畴双重意义的。该书引起国际国内佛教界、学术界、文化界强烈反响,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正是对其以善为本的肯定。在中国抗战胜利50周年时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南京大屠杀的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其审美特征在于善、真。面对1996年日本首相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外相叫嚣对我钓鱼岛拥有主权、日议员又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妖风、日本军国主义祸心再起的现实,上述诸书的出版更显现其“善”的审美意义。乾隆朝修纂的《四库全书》可谓美、可谓大,然而“尽美矣,未尽善也”。《四库全书》虽然号称中国传统文化总汇,冠以“全”名,但并不全。不全的原因不在财力、人力不济,而在于审美眼光。大量不合清皇朝统治需要与价值标准(即“善”)的历代典籍,或禁毁,或删改,或列为存目。乾隆朝的做法,在统治者、主事者看来是善,实则为不善;今世推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将散藏世界各地200家图书馆、博物馆及藏书家手中的4000余种、六万余卷四库存目书悉数收集、原版影印,是善,是“尽善也”。
社会性是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出版文化可以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人类进步的阶梯,也可以因其反动而致社会于倒退、致人类成员于堕落。如: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学说经出版文化的途径被后来成为侵略工具的德、日读者接受;淫秽、迷信出版物之毒害社会。出版文化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合体。精神内容一旦物化为出版物,经过发行,即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物品;至此,它则直接影响社会的进步、文明。因此,出版文化的社会性召唤着出版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就决定了出版文化以善为本的审美本质。中华立国,就物质文明而论,是以农为本;就精神文明而论,是以善为本。中国道统最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审美眼光看,此八者中“格物、致知”是求真;但与西人以真为本位不同,国人则重在八者中的“诚意、正心”,也即以善为本位。
二
中国出版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充实为美。
“充实为美”出自孟子论美名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⑦]从词汇学角度看,“充实”即充足、丰富的意思。在这里,“充实为美”包括充实、大、圣三层美学境界;三者的内涵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上递进。
出版的基本属性首先是积累文化;有积累才有大规模的、长久的传播,而后才可谈其社会性、教育性、阶级性、商业性、娱情性、收藏性、礼品性等。中国文化的博大深厚,决定了中国出版文化“充实为美”的审美特征。
这种审美特征首先表现在丰富、繁多、充足。远在先秦时期,便有大批史书、诸子之书、医书、农书及天文、地理、算学、文学等书籍出版。孔子整理编纂成《诗》、《书》、《礼》、《易》、《乐》、《春秋》六书,作三千弟子的教科书;弟子又以其为教科书授徒、讲学;就当时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状况而言,这已是一种传播面很广的出版行为了。自汉至清,我国出版18余万部书,计2367000卷;它包罗了至当时为止的人类社会全部学科门类,其丰富性已臻完美。在近代机器印刷出版业之前,主要靠手工抄写、手工雕版印刷,能创造出如此书山书海,不仅展现出充实之美,这巨额数字本身便焕发出傲世的辉煌;按“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实堪称“大”。此后的三十八年(1911年—1949年),虽是内忧外患、动乱不已,尤其是还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日寇全面侵华,出版文化仍有其夺目的光辉:出书十万种。这充分显示中国出版文化的充实之美。单是日本全面侵华前夕的动荡的1936年一年,就出书近万种。三十年后,按社会发展的正常情况而言,毫无外寇与战乱的承平的1966、1967年,出书应数倍于1936年;其实不然,因“文革”浩劫,导致了出书仅千种的可怜可叹局面,而且只能出版毛选、样板戏等。出书单一、贫乏、干瘪,使中国出版文化前所未有地失去了充实之美。中国“文化大革命”革去了中国出版文化的命,实为反文化的倒行逆施。世界文明显示一条公理:一国文化的盛衰与该国出版图书的数量成正比例。世人只须一瞥某国出书数量,再参照该国人口,即可知其文明程度。作孽十年的“文革”造成了十年书荒,这对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灾难。但历史又这样昭示人们:中国出版文化充实之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出版文化的充实之美表明中华民族广博的包容心;把出版文化钦定在一己或小集团圈内,是狭隘、渺小、可怜、虚弱的表现。它同时还表明:出版文化的充实之美是一种真,它真实地积累着、传播着人们创造的文化;反充实之美即否定真、否定客观世界、抛弃人们创造的文化,乃是一种反动,终必为国人、人类所唾弃。
中国出版文化审美中的“大”,主要体现在一部部博大的书,一个个浩大的出版工程。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诗经》传唱着五百年(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华夏歌声;在空间上,它包罗十五国国风,还有《雅》、《颂》;后人(包括日本、朝鲜等)对其研究之书竟达1260部,故其不可谓不大。《史记》上记黄帝、下记汉武,一条纵贯三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不可谓不大。《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不可谓不大。纸张发明以前的诸如此类的出版工程,不啻为“大而化之”的“圣”。《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合称为“唐代四大类书”,其特点在“大”。孙思邈《千金方》刊八百余种药物、五千余个药方,不可谓不大。《资治通鉴》不可谓不大。号称“宋四大书”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每一部皆显示其大美。仅《太平御览》便有一千卷,分55门、4558子目,引书达1700种之多。辑入八千种书、总计近四亿字的《永乐大典》,真当得了书名中的“大”字。它不仅大,还是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篇幅数倍于同时的《大英百科全书》,不可谓不大。浩浩然52卷、3000万字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不可谓不大。中国历代出版的8500多种、十万多卷地方志书,不仅卷帙浩大,更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出版文化宝库的、惟我独有的珍品。《四库全书》何其大哉!今日推出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又何其大哉!这里的“大”,有的已接近或达到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⑧]中的“大美”。“大美”是已入化境的“大”,即“大而化之”,是“圣”,是充实之美的极至。
三
中国出版文化的第三个审美特征是完全意义上的悲剧。
这里所说的“悲剧”,是纯粹的审美对象,是指美好事物、正义力量、进步事业遭到远远强大于自己的恶势力的摧残,饱受蹂躏,或致毁灭。丑压倒了美,恶压倒了善,假压到了真,是悲剧;但这悲剧是通过悲壮的痛苦或毁灭,昭示了美好事物、正义力量、进步事业必胜的信念,激发了人们对丑恶势力的憎恨及与之斗争的力量,同时激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乐观愿望。这里的凤凰涅槃,不是凤凰自焚,而是他杀;但结果一致,是死灰中更生,更为新美、亮丽。由于是“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⑨],而且是更美的光明,更美的宇宙,更美的凤凰,所以说是完全意义上悲剧。
压迫、摧残中国出版文化的恶势力可分两大类:外寇与内贼。
外寇,前可举八国联军。典型之例为举世无双的《永乐大典》被劫掠。《永乐大典》共为手抄本正、副两部。藏于文渊阁的正本毁于火灾。藏于皇史宬的副本被八国联军劫掠、焚毁;因劫走而散藏于今日世界各馆的原本,合计尚不及全书的百分之三,《永乐大典》去矣!中国第一家新式出版发行机构、清末与民国前期执中国出版文化牛耳的商务印书馆,被“一·二八”日寇炮火几乎夷为平地,损失1600万元。商务之所以为中国出版文化的中流砥柱,重要原因在于其有一流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译所(编辑部),出书质量高;出书质量高的设备原因之一,是它拥有供编辑使用的骄傲于世界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该馆藏书50万册,为远东藏书最多者;宋、元、明珍本达1700余种。除抢运走七分之一外,七分之六毁于日寇炮火,纸片烟灰飘飞三日之久!内贼,前可举秦始皇。秦始皇焚书,遗臭万年。比秦皇祸烈千万倍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之焚书、禁书。一边是空前的焚毁、查禁,一边是撤销许多出版机构、遣散大批出版从业人员。除了毛选、林彪江青讲话、样板戏、赤脚医生手册等少量图书外,中国的图书出版处于基本停滞的、戚戚惨惨的悲凉境地。然而,秦皇焚书焚得了一时,他毕竟无法从阴间来扑灭汉初兴盛的出版文化,惟有向墓而泣。为害十年的“文革”收场后,中华大地出现购书热,一时间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为购好书而排长队,唐诗宋词选本等书竟几万册、几十万册地数日脱销,出版社也成倍地增加。这是对扼杀中国出版文化的丑类的有力鞭笞。日寇炸毁商务印书馆,该馆百折不挠,排除万难,于当年八月一日复业,其七月十四复业启示云:“……敝馆自维三十六年来对于吾国文化之促进,教育之发展,不无相当之贡献,若因此顿挫,则不特无以副全国人士属望之殷,亦且贻我中华民族一蹶不振之诮。敝馆既感国人策励之诚,又觉自身负责之重,爰于创巨痛深之下,决定于本年八月一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俾敝馆于巨劫之后,早复旧观,得与吾国之文化教育同其猛进,则受赐者岂特敝馆而已,我国民族前途实利赖之。”[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八·一三”日军再度为祸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无奈沦陷;商务同人乃将笨重的机器、纸张、书稿、存书等,于大逃难中千里辗转迁移内地,同年12月在长沙重新经营,何其不易!开明书店也因上海战事,靠两艘木船西运机器等一应设备物资,遭日寇掳掠,冒生命危险为中国出版文化保生机。凡此,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显示了中国出版文化卓绝的悲剧美。
这种悲剧美源自三户亡秦[(11)]、刑天猛志[(12)]那般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
当此“文革”自残出版文化三十年之际、中国现代出版业领袖——商务印书馆创建百年之际、毁我出版文化的洪水猛兽——日本军国主义旧梦重温、恶胆又生之际,我们重省中国出版文化悲剧的审美特征,当有更深的心得:中国出版文化惨遭毁灭的根本原因一为专制政治、独夫巨凶的歇斯底里,一为国弱内乱而遭外敌。这,也正是中国落后的根本所在。而维护民主政治、提高民族素质、致我于四个现代化、雄踞世界民族之林,莫不有赖于善、美、真之出版文化。
探讨中国出版文化审美特征至此,更能深悟中国出版文化使命之光荣与重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3)],吾侪勉哉!
注释:
①《论语·八佾》。
②《论语·为政》。
③张元济《涵芬楼书目·序》,参见1992年第四期《出版发行研究》孙鲁燕《为吾国人》。
④《陶行知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P.805。
⑤参见吴世灯《论“开明精神”》,《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P.416。
⑥赵朴初《〈乾隆版大藏经〉重版发行序》,参见1994年12月7日《新闻出版报》。
⑦《孟子·尽心·下》。
⑧《庄子·知北游》。
⑨郭沫若《凤凰涅槃》。
⑩一岳《“一二八”被毁后商务印书馆之解雇及复业问题》,参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P.447—448。
(11)《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12)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又,《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13)《论语·泰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