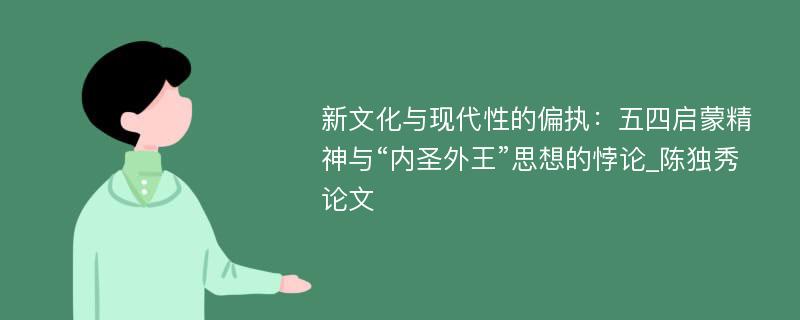
新文化元典与现代性的偏执:五四启蒙精神与“内圣外王”思维的吊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圣外王论文,现代性论文,新文化论文,偏执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4)04-0070-05
如果说《新青年》为现代中国新文化元典搭建了一个启蒙的思想平台以及思想家表演的思想舞台,那么我们说围绕着《新青年》的一批激进主义五四同仁则是搭建了一个无意识的启蒙斜塔,同时紧紧缠绕着他们的那些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新与旧命题的争论又使得他们都是在带着镣铐跳舞。解读《新青年》从创刊号到停刊的系列文章,我们要说的是:以伦理道德为指归的现代性取向,必然导致中国式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宿命。
一、士人情怀:从元典时代到时代元典
关于中华文化精神,当代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有一个共识:“内圣外王之道”。对此,著名哲学大儒冯友兰先生说得最为透彻:“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1](P138)这是对“内圣外王之道”之“内圣”与“外王”逻辑关系最通俗的解释。先人孔丘虽然不是最早概括这一关系的始作俑者,但他的论述无疑是经典的文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2]无论将其归结为政治哲学还是将其说成是社会理想,孔子那由“圣人”而为“圣王”的士人情结还是清晰可见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情结无不是这位老夫子点化的结果。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元典中,不但主张“人世”的儒家将行“内圣外王之道”,就是那遁世、出世的道家也不例外。例如庄周就是最早将这个思维模式集大成的。他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敌内圣外王之道,阉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3]“内圣外王之道”由此而来。应该看到,从中华文化元典衍发而来的“内圣外王”哲学精神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厚重心理积淀,也是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一个绵源不断的精神主题。尽管从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来看,中华元典中的这一底蕴应该走“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的分离道路[4],但是由于中国士人的经世思维模式是在一个伦理政治、而且伦理还是从与西方契约伦理大相径庭的情感伦理、关系伦理中产生的,所以尽管经世元典有着两个基本的走向——“内圣”与“外王”,但是除却在两个基本点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倾斜或倚重,传统士大夫那入世、经世的情怀还是坚如磐石的。而这一雷打不动的“外王”思想靠什么呢?无非是“内圣”。反过来,“内圣”的意义或说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呢?还是离不开“外王”。在中国历史上注重因或果无关紧要,关键是谁也不曾理性地思考过这“内外”之别。不过,鉴于这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畛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命题,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内圣外王之道”颇似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对应关系。看看《论语》中的问答就可以明白一二了:“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5]著名思想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一语道破其中的政治哲学底蕴:“修己与安人、修己与安百姓相贯通。”[6](P269)从现代学者朝上追溯,还可以看到熊十力、梁启超的认同。熊十力先生这样说:“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正、诚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国家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小人不知其身之大而无外也,则私其七尺以为身,而内外交修之功,皆所废而弗讲,圣学亡,人道熄矣。”[7](P45)熊先生是根据《大学》中以“修身”为本,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内功”,“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功”来尝试“内外”关系的。而他的前辈,也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于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将“内圣外王”与“经道合一”相提并论[8](P69),更是道出了中国政治哲学精神的实质。站在启蒙思想史的视角去审视中国近代政治理念的发生与发展,近代以来尤其是戊戌变法以后,无论是学问家、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革命家,他们都曾力图超越“内圣外王之道”窠臼的制约。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内圣”与“外王”的剥离以及必要的张力上下工夫。严复的“群”与“己”的权限界定,梁启超的“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孙中山的“个体自由”与“国家自由”,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这一命题。遗憾的是,他们也都殊途同归地走了一条由超越到回归的道路,最终皆以伦理上的“个人”为“永恒真理服务”、“为公众幸福不惜一死”而淹没和终结。这也正是五四一代先驱者不惜一切代价,决意跳出过去掌心而孤注一掷的根本原因。他们采取的“取一否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打倒”、“决裂”激进方式实在是出于对传统根深蒂固的思想情结的嫉恨心理。凡此种种,在启蒙者和士大夫这些所谓的新旧知识分子之间,不过是名词的转换,他们有着千年一线牵的传统,那就是“铁肩担道义”和“内圣外王”的打通与转化: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文化启蒙读本。
二、五四启蒙:在“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之间
《新青年》的缔造者在总结近代以来历史先驱的启蒙经验以及个人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开始策划了一轮全新的启蒙。那么,究竟该从哪里下手呢?就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划分来看,文化有硬文化与软文化之分。按照“文化堕距”理论,当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硬文化,依此类推,一个民族最难改变的当是心理积淀最厚的部分。这也是最稀软的部分,如思维方式等[9]。尽管《新青年》的创刊者陈独秀当时并不了解这么多社会学理论,但是他对历史的观察和现实的体认却是击中了要害。
就历史的经验而言,陈独秀将视野放眼到明朝中叶,并将中西文化冲突以及国人觉醒的过程分为“七期”。一是“明之中叶”的“西教西器”时期;二是清之初世的“火器历法”时期;三是“清之中世”的“洋务西学”时期;四是“清之末季”的“康梁诸人”谋求变法时期;五是“民国初元”的“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时期;六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国体”时期;而最后的第七期,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则是众望所归的“待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说:“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10]就陈独秀个人的历史观察和体认来看,他有着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睿智:一是他认为“今兹之役”是中国自有中西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二是他认定了国人“觉悟”之重要与艰难;三是他保持了一种启蒙理性的哲人态度,既反对“鲁莽的乐观”又防范“轻率的绝望”[11](P2),用陈独秀的话即是,“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而这里我们反思《新青年》文本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其根本的问题还是:“觉悟”的落脚点应该怎样着陆?用“伦理”的价值尺度能够根除伦理中心主义的底座吗?如果这样“以牙还牙”,我们会不会重蹈那个“以暴易暴”的思维套路呢?要避免学术论证的隔靴搔痒,就必须深入到这一文化元典的创刊宗旨上去。《新青年》的创刊号乃为其前身《青年杂志》。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新青年》一开始就存在着政治与伦理的吊诡。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套红印行。前3期连登“社告”,头版头条头题便是:“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在“社告”之后的首文《敬告青年》中,作者也是一种营造青年精神气质的口吻。他开门见山道:“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12]不难看出,“新青年”要的是青年的气质,切勿以“少年老成”自居;代替“老青年”(老气横秋之年龄上青年)的应该是“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与“陈腐朽败”决裂的青年是要以“新鲜活泼”的精神状态激活。这个精神状态的激活又是靠什么条件来杀青呢?主编列举了在他看来具有“是非”观念的“六义”。其中,“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是道德的,与这六项对立的“奴隶的”、“保守的”、“隐退的”、“锁国的”、“虚文的”、“相像的”则是不道德的。即是非伦理的价值观念也被列入了伦理道德的行列,因此《新青年》自一开始就打上了非常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对此,我们还可从《敬告青年》一文对“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诠释中找到答案:“德国大哲尼采(Nietz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12]
我们知道,《甲寅杂志》的创刊也是在“国势陵夷,道衰学弊”背景下发生的。这从陈独秀写给主编的信中可以看出端倪:“得手书,知暂缓欧洲之行,从事月刊,此举亦大佳。但不识能否持久耳?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13]这个“国势”也就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势,也是袁世凯窃国、违反“约法”的国势。如果说1914年“袁记新约法”尤其是修正后大总统选举法的公布,是文字形式上的终身制独裁,那么到了1915年8月,当袁世凯精心筹划成立了筹安会后,以“公民代表”名义出现的“请愿”舆论工具则是复辟帝制的身体力行。为了使得“君主立宪”合法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的“六君子”全心全意鼓吹造势。《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乃是他们这一时期的力作。与此同时,袁世凯当局又抬出两个洋顾问为自己的主张树碑立传:一个是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一时间,中国宜立宪不宜共和的舆论宣传甚嚣尘上。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创办《新青年》并紧紧围绕“人民程度”、“吾人觉悟”、“辅导青年”对症下药的。
《新青年》的出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欲定孔教为国教,《新青年》就要将这些判为腐朽;袁世凯以国民觉悟太低无法实行共和为理由称帝,《新青年》就以唤醒国民觉悟为鹄的;袁世凯以陈旧的思想麻痹、愚昧国民,《新青年》就以“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14]。从现代性出发梳理传统要比从传统出发梳理现代性更有感染力和号召力,这也是《新青年》何以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青年学生叶挺读了《新青年》后激动不已。他写信称赞《新青年》说:“足下创行青年杂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第仆中衷多怀。窃以君平不贵苟同之义,欲有所商榷焉。道德根本之基,果何如耶?觉悟耳。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流亚也。”[15]叶挺感慨良多,他与《新青年》及其主撰同声共气,专析道德觉悟以及良心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性,历数曾文正公、陈白沙、孟子、王阳明、孔子等一代又一代大儒的思想境界,从而让主撰陈独秀也为之动情,竟然礼贤下士地写了公开信以示认同:“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此说仆不非之。足下颇疑宇宙之迹,非科学所能解释。是犹囿于今日科学之境界,未达将来科学之进化,必万亿倍于今日耳。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足下其无疑于吾言乎。”[15]
在《新青年》杂志上,这类的编读往来之互动很多,但像这样共鸣的内容却很少。其实,不只在创刊号的《社告》里有“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的开宗明义,就是在一些自编自导的双簧或编读互动中也一再把自己以道德、伦理、“内圣”的主业挑明。陈独秀在回答一位名为王庸工的读者来信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16]主编在这里不但强调了《新青年》的宗旨,而且对“读者”对现实的诘问做了委婉的回答(注:读者“王庸工”在来信中说:“别后闻在沪主持青年杂志,必有崇论闳议,唤醒青年。惟近有惊人之事,则北京杨度诸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是也。以共和国之人民,讨论共和国体之是否适当,其违法多事,姑且不论,倘讨论之结果,国体竞至变更,则何以答友邦承认民国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逊位之心,何以处今总统迭次向国民之宣誓。更可惧者,此邦官民,对于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虽不以为然,心中则以此为彼国取得利益莫大之机会,几如欧战发生时同一态度。此诚令吾人不寒而粟者也。望大志着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国民幸甚、国家幸甚。”要知道,《青年杂志》刚刚创刊是不会有什么所谓读者来信的,所以主编用了“别后闻”的口气。在笔者看来,陈独秀是故意在借口表白,所谓的王庸工也不一定确凿。笔者在这里之所以大段摘引原文,实在是觉得这一“往来”的对话对解读《新青年》文本非常关键。从陈独秀对“国体变更”的回应来看,陈独秀关于谈与不谈政治的悖论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释(《通信》,《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在对“人民程度”、“历史国情”、“立宪政治”、“筹安会诸人”一一出示了红牌后,陈独秀的“雅非所愿”多少有些牵强。“非”是指非难时政,“愿”的则是“修身”、“治国”。于是他把寄托自己理想设计的骰子掷在了“伦理觉悟”上。那篇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有言曰:“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0]必须看到,在这孤注一掷的背后,还有着很不情愿的内在悖论。毕竟,《新青年》的初衷是换个视角关心政治。陈独秀叙述的第七期“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中有两个层面:一是“政治的觉悟”,二是“伦理的觉悟”。尽管这两种“觉悟”潜存着灰暗的吊诡,但《新青年》的主笔最终还将“伦理的觉悟”视为压轴戏:“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准确地说,“伦理的觉悟”与“政治的觉悟”在陈独秀那里是“吾人之最后觉悟”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一样,只不过一显一隐、一表一里而已。一枚硬币的正反也只是暂时的,在很多时候它们是互为表里的。以往学术界关于《新青年》谈与不谈政治的症结之所以难以解开,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陈独秀是怎样的一种新伦理与新政治互为表里的结合模式。
三、现代性的陷阱:伦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伦理化
关于《新青年》“谈与不谈政治”的研究,一度曾经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焦点和热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同仁包括本人在内都从不同视角对这个吊诡式的问题做过尝试性的探索。但总括起来不外乎这样几个观点。一是对“是什么”的表层分析。鉴于《新青年》有“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自我表白,还有“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的补白[17],很容易让研究者走入误区——仿佛《新青年》真是故意埋藏自己的深沉动机[18]。二是对《新青年》“为什么”不去遵守诺言而要谈政治的原委分析流于表象。鉴于有胡适的“不谈政治”之“现场”证词(注:胡适在一次题为《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中有这样的原话:“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19],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尽管胡适极力反对谈政治,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有明晰的“政治情怀”[20]。这个论证的缺陷在于:它无法解释胡适与陈独秀有着鲜明的政治共识问题。必须看到,就在陈独秀表白自己的大政治观的同时(注:陈独秀对自己的政治观是这样表白的:“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21],胡适也有对“不谈政治”的命题如下说法:“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19]三是认为《新青年》更愿意从深层次上谈政治,不是一般意义上谈论政治。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也是从文本材料出发的。譬如主编陈独秀就说过:“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应该谈谈。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做哑呢?”[22]这一前后矛盾的话语该如何解释呢?对此,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不谈政治为虚,谈政治是实”的结论[23]。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切中肯綮的论述。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要知道,即使是主编自己在当时也很难自圆其说,所以他只好说曾经表白过的“不谈政治”是不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现在谈的是这样一种非同小可的政治。下面这段话是进一步的自我圆场:“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它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笔锋一转,人家所谈的“不是普通政治”,“不是行政问题”,而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是大政方针。究竟这个“根本”的、不普通的政治是个什么政治呢?陈独秀将“根本性”的“大政”与“彻底的觉悟”联系在了一起。原来,《新青年》随着陈独秀的指挥棒再次将文化传统中“内圣外王”思维模式搬到了新文化元典的舞台上。只不过传统的是“伦理的政治化”,而现代则是“政治的伦理化”。究其实质,这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主编对传统中国的思想实质颇有见地:“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10]在“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之间,他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伦理政治”在传统中国的危害,但他对西方的“道德政治”却没有给予丝毫的提防。在反对“阶级制度”的同时,竟然把西方的“道德政治”作为武器予以坦然使用。“自由平等独立之说”本来是西方社会价值观念中的政治哲学理念,但陈独秀却将其作为“道德政治”的“大原”予以包办。撇开“道德政治”是偏正结构式的“道德政治”还是并列同位的“道德、政治”之断句,其中的新型伦理政治的模式都无法回避。就“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这个判断句来判断,不论怎样组合,伦理和政治之间暧昧、纠缠的情形昭然若揭。五四新文化元典设计的现代性方向由此滑落。从这一思想史角度理解《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也许更能抓着这一精神事件的根本。
回到本题,伦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伦理化的过程意味着无论是道德启蒙还是政治启蒙,无论是文化革命还是伦理革命,它们都在进行着无声或有声的政治现代性之和平或流血的演变。伦理中心主义,造就了“内圣外王”的哲学精神传统;道德形而上主义又是“内圣外王”政治哲学的结果。其实,早在《新青年》之前,陈独秀个人和他的启蒙导师都在无形中演绎着“解铃系铃”的“新内圣外王”思维。1904年,陈独秀就曾在安徽芜湖创办过《安徽俗话报》,他以“三爱”为笔名,用通俗话文字写作了大量启蒙、宣传文字。文章开篇便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陈独秀的解释则是:“先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古时候教人的道理,是要教人去实行那忠孝节义,才算是尽了人伦,才算是一个人。后来教人的法子,是专门教人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乱念,并不知道讲究书里所说的道理。教学生照样去做,照这个样子,就是书念的极多,又记的极熟,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人才如何能发达呢?”陈独秀沿着“心学”大师的思路发挥道:“天地闲〔间〕无论何事,都是能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制,才是有害无益。自由发达,才是他自己真发达,勉强压制,就是他能够照你的话去做,也合机器一般,不过是听人调动罢了。”怎样发达才是“有用的国民”呢?“三爱”的启蒙万变不离其宗:“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24]没有什么再比这个印证更能证明陈独秀对伦理道德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的膜拜了。
十年之后,《新青年》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它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仍然没有跳出过去的掌心。这再一次证明,在探索现代性与滑向其反面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收稿日期:2004-04-19
标签:陈独秀论文; 新青年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新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现代性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