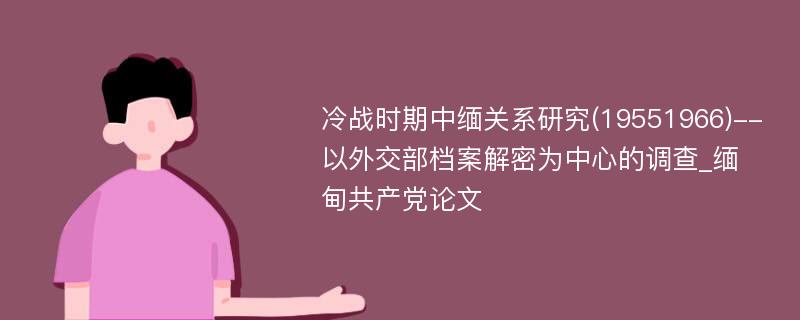
冷战时期中缅关系研究(1955-1966)——以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部论文,战时论文,期中论文,关系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8)02-0035-09
1950年中缅建交后,双边关系最初较为冷淡。1954年,两国总理互访,中缅关系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此后至1967年中缅关系破裂之前,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为冷战时期中缅关系史上最为密切的阶段。但是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不充分。余定邦教授的《中缅关系史》主要论述的是古代和近代中缅关系的发展情况,只在最后一章简要介绍了新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林锡星所撰的《中缅友好关系研究》着重阐述的是中缅经济关系和冷战后的中缅关系。王介南的《中缅友好两千年》、缅甸戚基耶基纽的《四个时期的中缅关系》仅是把中缅邦交活动做了一般性的罗列和叙述,没有进行学理性的分析,而且对“金三角”国民党军、缅甸华侨、缅甸担心的中国“革命输出”等曾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没有提及或者语焉不详。其他涉及本课题的共和国外交史研究状况也大致如此。①本文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档案为基础,对1955-1966年的中缅关系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
一、中缅政治关系(1955-1966)
继1954年中缅政治关系出现转折后,1955-1966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互访。这一时期,周恩来总理先后8次,国家主席刘少奇2次,陈毅副总理兼外长13次访问缅甸。同期,缅甸领导人吴努先后5次、奈温6次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通过首脑外交的形式,围绕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进行交流、磋商,增加了了解与互信。毛泽东曾向来访的缅甸领导人表示,“过去我们相互不了解,尤其是人们怕共产党,怕共产党侵略他们。我们说我们不侵略,人家不相信,他们还要看,要多多来往,来往多了就了解了。”[1]相互了解情况很重要。吴努第一次来访,问中国会不会侵略别的国家,那是因为彼此不了解,“因此我们建议缅甸在昆明设一个领事馆,了解了解我们是不是想侵犯缅甸,”“相互了解了,友好关系也就一年一年地发展了。”[2]
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阵营对中国构筑半月形的包围圈,中国对外交往因此受到了很大遏制。1956年中缅航线开辟,改善了这一局面。50年代,中国“主要是通过北京——伊尔库茨克和昆明——仰光两条国际航线,同世界各地相通”。[3]所以,丘吉尔曾表示,“包围中国,缅甸是一个缺口。”[4]还有学者指出,“缅甸是中国唯一可以来去自由,以及非洲、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团通过缅甸自由往返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5]
周恩来访缅以前,中共对缅甸国内革命力量的态度,一直是仰光担心北京进行革命输出的主要理由。1954年周恩来访缅时和吴努访华时,中方就向缅方承诺不进行革命输出,不干涉缅甸内政。此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多次向缅甸人表明,“我们坚持不干涉内政,各个国家怎样办事,由各国自己决定”[6],我们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主张。[7]
冷战时期,东南亚人数众多的华侨曾一度被当地看作是北京的“第五纵队”。缅甸华侨虽然人数不多,但缅甸政府在华侨问题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类似的恐惧和防范,这种担心主要体现在华侨的政治作用和“双重国籍”问题上。1954年两国领导人初次接触时,中国就向缅甸表示,不会利用华侨干涉缅甸内政,颠覆缅甸政权。[8] 195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仰光华侨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向华侨和缅方更系统地表明了这种态度:华侨要做一个守法、模范的侨民,入籍的和没有入籍的华侨在政治上要分清界限。入籍者不应参加华侨团体,华侨不应参加缅甸政治活动,“同时我们也不在华侨中发展共产党或其他民主党派的组织”。[9]周总理的讲话进一步减少了“缅府长期萦绕的不安情绪。”[10]
关于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尊重和理解华侨长期居留缅甸的历史特点,肯定和鼓励长期居住在缅甸的华侨加入缅籍,反对“双重国籍”。双方在华侨入籍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使这一问题没有成为这一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和麻烦。
1950年初,国民党军进入“金三角”后,多次进攻和袭击云南,并试图制造边境冲突,以使中缅军队交火。因此,缅甸担心自己成为台湾“反攻大陆”的牺牲品,成为另一个朝鲜。对于这种情况,中国一直保持克制和理解的态度,从而得到了缅方的称道和信任。缅甸总理吴努曾表示,“我不能不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我的态度和诚意。当国民党军提出进攻云南的口号时,中国政府如果想给我们制造困难,是可以制造的。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诚恳并忍耐地对待我们,因此我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11]
中缅未定边界问题是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缅甸一直担心中国会侵占缅甸领土。从1956年开始,双方就边界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经过努力两国先在1960年1月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保证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缔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同盟。”[12]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同年10月,缅甸总理吴努率领350多人的代表团访华,参加中国国庆庆祝活动,签订中缅边界条约,中国组织了300多万人欢迎缅甸代表团。10月2日,北京组织10万人集会,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签订。缅甸向中缅边界的100万中国居民赠送2 000吨大米和1 000吨食盐。1961年1月,周恩来率领由9个代表团组成的访问团400多人访缅,参加缅甸独立节庆典,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至此,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缅甸总统授予周恩来等19位中方代表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做出的贡献。中国向居住在中缅边界地区的120万缅甸公民赠送了240万米花布和60万个磁盘。1960年至1961年初,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以及双方借此进行的一系列的访问和庆祝活动,将两国关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
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为契机,1960年11月22日至1961年2月9日,中国军队两次出境作战,历时近3个月,同缅军联合围剿缅甸境内的国民党部队,摧毁了“金三角”国民党军在缅甸的总部。1961年4月,吴努总理到云南度假时,两国总理同意双方在必要时协同合作解决在缅国民党部队问题。此后,缅甸境内的国民党部队逐步撤退到泰国境内和台湾。
1962年3月2日,奈温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吴努政府。3月6日,北京致电仰光表示承认缅甸新政府。奈温上台后,为建立“缅甸式社会主义”,采取经济国有化等激进的政策。苏联对此表示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示了反对。1963年4月,国家主席刘少奇访缅,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了看法,对缅甸实行的社会主义表示了理解,并建议军政府和反政府力量和谈。
1962-1966年,两国在处理政治关系过程中除了继续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导性作用以外,还对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做了特别强调。1964年2月周恩来访缅、1965年7月奈温访华和1966年4月刘少奇访缅时,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都强调了经济独立对政治独立的重要意义。双方对经济独立的刻意强调,应该是针对缅甸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而言的。从仰光来看,奈温上台后实行的激烈国有化措施,导致其国内政治经济动荡,同时国有化措施又带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色彩,使缅甸的印侨、华侨和其他外来势力均受到严重的冲击,因此缅甸想得到中国的支持,增加军人政权的国际合法性,更保证在内忧丛生的情况下减少“外患”的发生。从北京来看,中国担心美、苏等大国会利用缅甸的经济困难,通过有条件的经济援助控制、影响缅甸,使其偏离中立外交轨道,因此中国此举意在促其防止外部势力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说,1955-1966年的中缅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从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3个层面来加以解读。从全球战略层面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发展与缅甸的政治关系是服务于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这一战略目标的。中国努力将缅甸作为发展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典范以及和平共处的榜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即是中国意图塑造和平共处榜样的一种努力。从地区层面来看,中国发展两国政治关系是从属于中国反制美国封锁和包围,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周边和平环境这一战略格局的。两国签订的“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正是北京这一时期努力的成果。从双边关系层面来看,中国在华侨问题、“金三角”国民党军问题、边界问题和革命输出等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上,都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与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上述两个层面的利益诉求。
即使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开始左转后,中国也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做法。1963年6月缅甸国有化运动期间,中国放弃缅甸政府将仰光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收归国有而给中国的赔偿,将两个银行赠送给缅甸政府;对缅甸政府将华文报纸、华文学校收归国有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奈温当政后实行的激烈措施,导致缅甸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中国驻缅使馆向国内报告了缅甸情况后,中国虽然并不认同缅甸实行的“缅甸式社会主义”,但仍决定支持奈温。经过双方商定,1964年7月10-12日,周恩来、陈毅访缅,免除一切礼仪活动,双方主要就缅甸国内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向奈温表示,中国支持缅甸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向其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建议其在经济上打击面不宜过宽,计划不宜过急。[13]但不容否认的是,从根本上来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左转导致中缅关系日益出现摩擦和冲突。
二、中缅经济关系(1955-1966)
中缅关系在1954年取得突破性发展后,贸易规模开始明显扩大,经贸往来逐渐密切。1955年,中国对缅贸易额比1954年增加了30倍,其中进口增加了32倍,出口增加了28倍。1955-1966年,中国对缅年平均进口额为1 450万美元,年出口平均额为1 826万美元,分别是建交初期这两项比例的4.4倍和20.9倍。[14]
1955年3月,缅甸政府采购团访华,同中国签订3个合同,购买中国钢材、棉纱、玻璃等36种商品,价值190万英镑。1958年2月21日,双方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有效期为1年。1960年10月,缅甸贸易代表团访华,就扩大两国贸易,重新开放滇缅公路达成协议。1960年10月15日,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缅,就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进行会谈,10月24日双方签订一项关于中国购买缅甸大米的协议。1961年1月27日,缅甸贸易代表团访华,和中国签订了为期5年的贸易协定。1966年,两国签署《中缅关于延长两国贸易和支付协定的换文》,同意在两国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前,继续采用1961年双方签订的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同年,中国又同缅甸签订了两份购买缅甸1966年生产的大米10万长吨②和1967年生产的大米8万长吨的议定书。
同民族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是中国争取、团结他们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认为“这不仅有严重的经济意义,而且有严重的政治意义”。[15]中国与缅甸的经济合作、对缅技术援助始于50年代中期。1956年7月17日,中国帮助缅甸扩建直迈棉纺织厂,中方提供棉纺织厂的全部设备、工程设计和所需的技术专家。此后,中国还向缅甸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德迈棉纺织厂、仰光大光橡胶厂和瑞知肥皂厂。1961年1月,双方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缅甸提供3 000万英镑贷款。到6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向缅甸派出了造纸、水电、桥梁、植物、地质、化工、轻工业等领域的300余位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缅甸利用中国贷款建设12项工程。
“对缅甸的适当又积极的经济宣传工作,介绍我国生产建设经验……通过展览、互相进行友好访问等方式进行,以达到争取缅甸和削弱帝国主义的影响,为增进两国友谊与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提供有利条件。”[16]1954-1966年,中缅两国为了促进双方经贸往来,组织了各种经贸代表团进行互访。这一时期,缅甸先后有数十个经济、贸易代表团访华,主要有政府贸易代表团、经济考察团、工业考察团等,同期中国也组织了一些经贸代表团访问缅甸。为了增进缅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了解,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中国在缅甸还举行了各种介绍中国工农业产品和经济建设成就的展览会。
这一时期中缅经济关系的发展,既有政治关系发展带动经贸发展的因素,也有经济服务政治的成份。但总的来说,中国对缅经济关系的发展是服从“我外交政策”这一根本方针,“密切注视缅甸政治经济情况及其对外政策的变化,把我们的经济贸易工作置于对缅外交斗争需要之下,有力配合外交。在可能的情况下,既保证外交斗争的胜利,也保证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17]
例如,在贸易商品上,虽然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较低,但同缅甸相比,中国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双方贸易中,“缅甸生产、生活的需要与我国出口可能,较易结合,其出口商品与我国进口需要,则存有矛盾,”[18]这尤其表现在大米贸易上。
大米是缅甸的经济基础,占其出口总值的70-80%。然而,中国“大米也是大宗出口物资之一,不可能用外汇大量购买大米,只能在缅甸迫切向我求售时,酌予购买,以示照顾,助其克服困难。”[19]实际上,综观这一时期的双边贸易,我们可以发现大米贸易在中缅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并不只是“酌予购买”。1957年周恩来总理向来访的缅甸副总理吴觉迎表示,“我们粮食产量增加了,缅甸不必害怕,我们不会影响缅甸的大米市场”。[20]中国利用大米贸易打消、减少缅甸对新中国的恐惧,推动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举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赢得了缅甸的一些信任和赞许。“吴努等人不止一次地说:‘中国在缅甸大米出口困难时,购买了缅甸大米,对缅甸帮助很大’”。[21]
1954年中缅经济关系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后,两国的年均贸易额比1954年以前增加数十倍,但这主要是由于建交初期两国贸易额过低的原因。虽然这一时期中缅经贸关系一直保持发展,但双方彼此在对方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均不占重要地位。这种状况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化程度都比较低,双方经济结构雷同,互补性不强的缘故。而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这突出表现在大米贸易、经济援助与合作的经济往来上。所以,1955-1966年的中缅经济关系实质是两国政治关系的组成部分,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经济动因小于政治因素,中国对缅的经济贸易政策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外交路线。
三、中缅文化关系(1955-1966)
中缅文化交流从1955年开始逐步密切起来。1950-1966年,中缅双方各种文化代表团互访往来有数十起,涉及体育、艺术、宗教、医药、新闻、电影等领域。其中,1949-1959年的11年内,两国文化性质代表团往来有39起,其中中国赴缅者17起,453人;缅访华者22起,244人。文化往来是两国友好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数约占两国友好往来次数的40%。[22]
这一时期中缅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的表现和结果。正如当时中国驻缅大使馆所总结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往来是以政治为前提的,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才以文化来配合;两国关系好,文化工作就容易开展,文化来往也就频繁,反之,两国关系紧张,文化工作就不能进行。”所以,两国“文化来往有时过于集中,有时又显得冷落。”[23]例如,1960年,阻碍两国关系的未定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围绕两国政治关系得到重大突破,当年两国文化交流也特别频繁,1960年被称为中缅友好年。1960年1月,中国文化代表团、民族歌舞团访问缅甸;6月,成都篮球队访缅;8月,缅甸文化友好艺术团访华。9月28日-10月4日,缅甸总理吴努、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率领由370余人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包括文化代表团、体育代表团、新闻代表团、贸易代表团、军事代表团等),参加北京国庆庆祝活动和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回访缅甸,参加缅甸独立节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此次中国访缅友好代表团,由430余人组成,包括政府、军事、文化艺术、云南省、佛教、电影、体育、新闻、边界代表团等。其中,文化艺术代表团有300多人,访缅期间在缅甸各地演出24场,观众达27万人次。
中缅文化关系的发展也是推动政治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通过文化交流来推动、服务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充分发挥文化工作的友好作用”,“充分使用文化方面的各种兵种,配合外交斗争,达到争取缅甸,削弱帝国主义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影响,鼓舞他们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24]吴努在总结中缅边界问题得以解决的经验时曾表示,“由于中缅两国先进行友好活动,然后谈边界问题,边界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中印之间则是先谈边界问题,而没有先进行友好活动,因此解决就比较困难。”[25]
缅甸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佛教,佛教在缅甸政治、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一些敌视中国的国家,利用宗教问题离间中缅关系,在缅甸佛教徒中散布“中国已经‘没有’佛教了,和尚被‘驱逐’、被‘杀光’了”的流言。[26]所以,两国的宗教交流比一般文化交流影响更大,特别是1955年10月中国将佛牙送往缅甸接受朝拜,“对增进两国友好关系有极大的作用。”[27]佛牙到达仰光时,缅甸总统、总理、上下议院议长、军政各部门首脑、三军仪仗队及外国使节均在机场迎接,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佛牙仪式。仰光市民也倾城出迎,沿途瞻拜,“对缅甸群众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28 ]中国代表团就此次活动的影响向中央报告说,“缅甸政府和缅甸佛教界在这次对我们的态度,比半年前我们佛教代表团访缅时,也更加表现热烈和亲切;”“佛教界一些领袖人物,通过这次迎接佛牙,同我们的关系表现了进一步的加深。某些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有了改变。”[29]
1955年底和1956年初期,两国军队在边界发生武装冲突,使中缅关系一度变得紧张。为此,1956年下半年两国领导人实行互访,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和沟通。中方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1956年9月至1957年初,派艺术团几次赴缅演出,帮助“缓和当时因边界问题所引起的两国紧张关系,加深了当时周总理、叶元帅、云南省长在缅访问的友好气氛和政治效果”[30],达到了“文化往来配合外交斗争”的目的。
中缅建交初期,缅甸对华的恐惧和猜忌,也是由于双方相互了解、交往不够和缅甸受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影响所致。这一时期,中缅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往来,为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来说,这些往来程度不同地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惧,澄清了一些谣言,“在文化界中结交了一批朋友,改变了一些人对我的看法”。[31]
四、中缅关系中的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中缅关系的大陆学者基本是先入为主,以中缅友好的框架和模式来定位双边关系研究(从古代到当代)[32],对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往往“省略”或“忽略”。
从宏观角度讲,1955-1966年是冷战时期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时期,双方领导人称这种关系为“胞波”友谊。中国媒体和学者经常引以为证的是陈毅所做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这种状况的形成,首先是两国的确一度形成了亲善友好的关系。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框架下,和平解决了中缅未定边界问题、缅北国民党部队问题,以及在反帝、反殖,倡导和平等国际问题上有过良好合作。其次,大陆学者研究的中缅友好模式、媒体突出友好的舆论宣传,是政治需要,政治气候决定的。再次,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结论是基于整个冷战时期的宏观性考察而得出的。
从微观层面来看,1955-1966年,中缅关系的发展是前后不平衡的,1962年后的两国外交政策均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冲突日益凸现。1955-1962年,中缅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较为亲善的状态,并在1960-1961年达到高峰,是由当时两国外交政策决定的。1954年,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和平外交政策形成,改变对中立主义国家的看法,力图在亚洲,特别是在周边地区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而缅甸奉行的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与中国新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利益共同点。具体来说,中国对缅政策的目标是,“达到争取缅甸,削弱帝国主义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影响,鼓舞他们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33]缅甸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对华友好关系,确保国家独立与安全,“不参加冷战”[34],在中国与西方阵营以及后来的苏联对抗中,力图保持中立和平衡。中国希望通过对缅甸保持足够的影响力,而不使其成为冷战中敌对力量遏制、对付中国的棋子。缅甸希望至少不要得罪邻国中国,从而避免招致中国的侵犯。所以,二者的政策目标都在于通过与对方交好而达到谋求国家安全的目的,尽管这种安全诉求的层面不尽相同。双方正是在这种利益诉求下,才各自排除国内外的干扰,努力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未定边界问题、缅北国民党军问题等,达到和平共处的。
在两国友好关系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小国对大国的忧虑,大国对小国的影响,使中缅双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和防范。从两国的政策来看,也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中共想“削弱帝国主义”在缅甸的势力,扩大自己在缅甸的影响,而缅甸则不想受制于人,力图抵制或减少这种影响,在大国纷争中保持中立。例如,中国在总结对缅工作时,就曾提出自身有“大国主义情绪”,“想过多地使缅甸接受我们的影响。”就缅方而言,“由于两国社会制度的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缅甸统治阶级害怕我们的‘共产主义’影响,害怕我们支持进步党派,时时想限制和抵消我们的影响”。[35]1962年以前,由于两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都是力图通过与对方交好,来谋求国家安全和利益,所以上述负面因素没有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主导因素。但是,随着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左转,以及缅甸实行极端排外政策以后,两国政策的矛盾日益突出,直至1967年演变成反华暴力冲突。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开始逐步左转,改变了1954年确立的谋求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务实外交路线,不断突出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指导意义,在理论和现实中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到60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大力支持和援助亚非拉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革命外交政策”。
1962年奈温军人集团执政后,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路线,对内实行消除一切外国势力影响的政策。对外,奈温政变夺权的当天就宣布缅甸坚持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但相比之下,“奈温比吴努更加积极地来平衡大国在缅甸的影响,经常是通过尽可能消除他们的影响来达到这一目的”。[36]独立自主是缅甸对外政策的一个绝对标准,奈温通过关闭外国,尤其是中国在缅甸达到其政治目的的管道,而将这一标准发挥到了极致。[37]因此,有学者称奈温时期的对外政策是一种“专注国内的、恐外的、不成熟的”消极中立外交政策。[38]
所以,中国的新缅甸政策——即争取缅甸对其革命外交政策的支持,扩大对缅甸的影响,与缅甸的新对外政策——极力消除外国势力对缅甸的影响,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1964年,中国15周年国庆,缅国内革命力量致信祝贺。北京不仅用英文和缅文广播了此信,而且贺信还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缅甸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关闭了中国驻曼德勒和腊戍的领事馆,以表示对中国的不满。
1965年7月奈温访华,刘少奇在欢迎奈温的国宴上表示,“目前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都是一片反帝革命的大好形势。”随即重点谈了越南斗争形势、中国反美支持越南革命的问题,这部分占其讲话内容的一半。1966年刘少奇访缅,在缅方举行的欢迎国宴上再次谈了越南反美和中国支持越南的问题。显然,中国希望缅甸在越南问题上支持中国,谴责美国。但缅甸不愿意跟随中国反美,在这两次国宴上,奈温对美国都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且两次互访后发表的两份联合公报中,都没有涉及美国,只是一般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对态度。在反帝、反修的对抗中,中共不仅没有成功争取到缅甸的支持,反而两国关系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据中国边防部队报告,1966年10月至1967年7月,缅甸军队和飞机连续不断地侵入云南。据不完全统计,缅甸飞机侵入中国境内共6起,43架次;缅甸军队从境外向中国境内开枪挑衅2起;缅甸武装部队越境共20起,263人次。其中有几起缅甸士兵侵入中国境内,抢劫中国边民财物,殴打甚至开枪打伤中国边民;有时出动上百名全副武装的部队,侵入中国境内,进行抢劫烧杀。对此,中国政府先后于1965年1月11日和5月11日,1966年2月12日和12月13日多次向奈温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入侵事件。奈温政府也不止一次地承认缅甸军队入侵的事实,并向中国政府保证,将下令缅甸部队尊重中缅边界,不得越入中国境内。[40]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的革命外交政策更鲜明地体现在中缅关系上,特别是从1967年开始。1967年1月4日,陈毅副总理在缅甸大使庆祝缅独立十九周年招待会上说,“一个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更有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更有力地支援亚非拉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更好地完成我们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41]
从1967年1月到6月缅甸反华事件发生之前,《人民日报》开始不断刊发文章,宣传缅甸国内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苏修,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情况。在这些宣传中,中国始终用“缅甸朋友”来指代其国内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拥护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我们虽然不能确定这些人究竟由哪些人组成,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断波及、影响缅甸,这些是奈温军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为,1962年奈温上台后,大力推行的措施之一就是极力消除外国在缅甸的影响,这意味着北京的革命外交和仰光的封闭、排外施政方针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结 语
1950年中缅建交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但从1954年开始,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双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频繁,中缅关系迅速发展,迎来了“胞波”友好时期。本文所研究的时段1955-1966年,即是中缅关系史上最为友好的时期。这一时期双方解决了影响两国关系的未定边界问题、金三角国民党军问题,就华侨问题达成共识,实现中缅通航,签订了“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这些对新中国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封锁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左转和缅甸实行封闭的排外的“缅甸式社会主义”政策,“胞波”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最终在1967年演变为中缅关系的破裂。
注释:
①例如,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9页;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191页;谢益显:《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249页。
②1长吨=1.01605公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