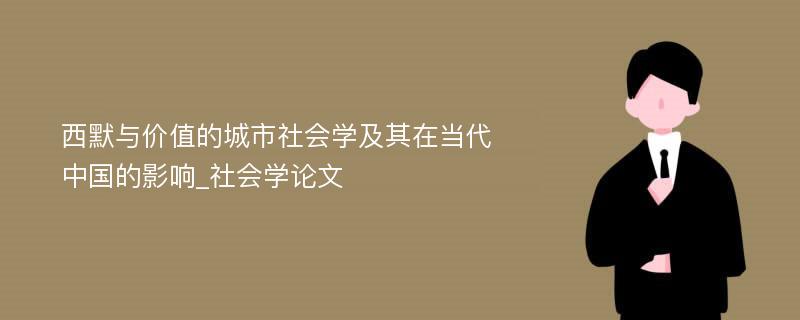
齐美尔、沃思的都市社会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美尔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理论界,都市作为一个相对于乡村的理论话语,曾随着19世纪中叶欧洲城市的发展而膨胀,但又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及市场一体化背景下各类生产要素、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跨地区的渗透,其语义内涵的特殊性相对减轻。尽管都市的意象在其后现代语境中反弹,但作为乡村和都市截然两分的传统社会对比则随着现实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而渐趋淡化。然而在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当下人文语境中,都市则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西方理论界中的有关思想资料,曾多次被国内学者汲用,其中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和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的都市社会学家沃思(Louis Wirth)等人的有关论述,因涉及大都市的精神生活及都市人的个性、理性、心理诸问题而引起国内人文学者较为广泛的关注。解读他们的都市社会学理论,不仅可以触摸到西方社会学中关于都市研究的一种思想理路,亦能引发我们对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一种人文心态的对应性思考。
一、都市社会学的崛起
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产生了两大社会变迁,即都市化发展和传统农业社会控制的解组。随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大量人口涌向都市区域,也引发了一系列都市化社会问题。诸如社会结构调适不良、价值系统离析、人际关系冷漠、心理秩序崩溃及社会犯罪增长等。这些由都市化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普遍地引起了西方社会学家的关注。
从马克思、涂尔干(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对都市问题的重视,到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的创立,都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而获得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德国学派”(the German School)的重要代表人物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及关于大都市的社会学理论,为推动这一学科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承传作用,而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建构则最终推动了都市社会学科的独立成型。“芝加哥学派”的早期成员如帕克(R.Park)、史墨尔(A.Small)、汤姆斯(W.Thomas)、伯吉斯(E.Burgess)、米德(G.Mead)等,跨越了传统社会学科范畴,把新兴的人类学、心理学和传统的人文科学结合在一起,第一次创立了有系统的用于分析都市社会的理论即“人文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都市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载体,而且是人类属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包含人类本质特征,并由空间分布性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关系显形。由于理论建构的跨学科性,其学术影响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学领域本身而播及人文学科等其他许多领域。在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的创立过程中,其灵魂人物帕克为构建以人文生态学观点研究都市的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继者沃思则在30年代将其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并在自己创立的关于都市社会的理论中,将芝加哥学派有关“都市性”(Urbanism)的探索推进至一个更符合社会学定义诠释的新阶段。
二、大都市精神生活的社会学元因素分析
如同社会学本身源自于欧洲并在美国得到繁荣兴旺一样,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理论的源流和“德国学派”等欧洲思想家们关于都市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帕克和沃思的都市理论在知识脉系上即清晰地反映了“德国学派”重要成员齐美尔的影响(帕克在柏林求学时曾是齐美尔的学生,而沃思则为帕克的学生),故三者的都市理论曾被认为是近亲繁殖的产品。从齐美尔到沃思,两者在都市社会学方法论的建构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学科化企图,其共同的特征是:一是把考察人类的集居形式、交往关系和个性特征作为研究“都市性”的重要切入口;二是希图剔选、归纳出一种和“都市性”直接相关的理论元素,以建构一种适合于都市社会分析的“纯都市意义”上的理论框架。
齐美尔(1858-1918)被看作是社会心理学和“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先驱,其都市社会学思想主要见诸发表于1903年的一篇驰名论文《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lis and Mental Life)。文中提出用以解释大都市社会关系及精神生活的三个社会学独立变因,即规模、分工和货币经济。
规模理论被其用作分析群体集居形式对社会关系及人的个性、自由和心理的影响。在齐美尔著名的“三人组合分析”案列中,"3"这个自然数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学意义。在他看来,一个两人群体和一个三人群体之间的不同,不仅是量的亦是质的。在两个群体中,任何其中的个人只能依靠仅有的另一个人,群体的社会关系纯粹是直接性的。这样就导致了对相互关系的良性确认、对另一方个性的关注和对非直接性制约因素的禁止。但在三人群体中,群体间交往的关系形式远比两人群体复杂,正是从"3"开始,群体直接性交往关系的原生态被打破,并导致了非直接的、超个人的社会制约因素和新社会关系形式的产生。可以想知:群体的规模越大,对社会制约、协调机制的要求就越复杂,群体成员间社会交往中的非直接因素就越增长。群体的统一性不再由成员间的直接交往关系来维持,而必须以正规的控制工具诸如各种法律机构来代替。如果说基于情感的传统习俗是维系小群体社会的粘合剂,那么基于理性的法律制度则是维系大群体社会的纽带。在此基础上,齐美尔论证了规模增长对社会人的自由、个性、心理等精神生活的影响。在小群体(如乡村社会)中,群体的社会关系是直接性的,这就增加了相互关系的紧密度和依赖性。但在一个正在实现某种规模的群体(如都市社会)中,每个成员越来越多地受制于那些超个人情感的机构的运作,传统社会中个人对他人所承担的情感义务相对减弱,个人的自由空间相对增大,但同时亦造成了成员间情感的疏离。群体的规模越大,社会交往关系中的情感成分和个性化程度就越低。由是,大都市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把许多陌生人赶到一起亲密相处,个人在享受自由空间的同时往往变得越来越孤独。
再是分析现代分工对都市社会关系及精神生活的影响。齐美尔认为,现代分工的作用最显著地表现在大都市中,首先是都市社会极度的分工打碎、分割了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在一个小规模、相对和谐和简单分工的社会中,成员和社会的联系往往呈现一种同中心圆状态。如:个人属于某一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则属于某一联盟,由此类推,个人最终被直线状地融合进他的社会,成员间的交往形态亦呈现出一种共同性征。但随着分工进一步发展和复杂化,产生了诸多无直接关联的和性征各异的社会圈,个人除特定的社会圈外,同任一其他社会圈的关联都可能是部分的或暂时的。个人的选择自由扩大了,但个人同社会总体结构的关系则呈现出疏离状态。其次是,分工在分割个性交往的同时,反而强化了个人的个性自觉。因为人的个性具有一定的固定性,一般而言,生活越是稳定不变,感觉经验就越少从一般走向极端,人类的个性知觉就显得越弱。而生活越是变幻、波动,人的个性知觉就迸发得越为旺盛,人类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感觉就越强烈。复杂的都市分工造成了都市社会无限变动的形势和群体经验世界的破碎感,加剧了人们的精神紧张与刺激。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惟一不变的是个人的独特性,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知觉被一种外在于自我的无限裂变的社会形势凸现了出来。由此,动荡不安的都市与稳定不变的乡村在精神生活感觉方面形成了一种深刻对照。最后是,分工使创造者和他的创造物分离,个人仅成为一架巨大机构中的一个轮齿,这架巨大的机构将个人所创造的价值从个人的手中扯开,将原本属于主观性的创造物转换为外在于个人的纯客观世界,个人创造的成果世界逐渐演化为一种客观精神与其相对。
货币经济的作用则是齐美尔用以解释大都市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的第三个理论支点。齐美尔认为,大都市始终是货币经济的中心。货币经济是一种金钱理性,是大都市理性及智力活动的来源和表达。金钱一方面成为个人自由和独立的支撑,另一方面它置真诚的个性交往于度外,因为金钱仅按“多少”来表达所有事物的质的区别,金钱的交换不会留下它先前拥有者的个性痕迹,它就像一架冷酷的“校平器”(leveller),以其苍白、冷漠的性征成为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金钱交易成了现代都市理性世界的一种最佳解释。
无疑,齐美尔的三个社会学元因素在其关于大都市生活的描述中得到了最佳演示。规模、分工与货币经济的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疏离、孤独、冷漠和充满理性算计,成为大都市区别于传统乡村社会关系和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形象说明。这种将大都市社会关系及精神生活状态归诸三个社会学元因素互动的结果,在方法论上给予其后继者以极大影响。
沃思(1897-1952),是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的一位理论健将。1938年,沃思发表了被西方社会学界认为至今影响尤存的著名都市社会学论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性》(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论文被看作是对齐美尔及帕克的都市社会学理论的整合与发展。但较之齐美尔等人,沃思的理论表现出一种更强烈地建立“纯都市社会学”的学科化企图。一方面,他承续和发展了齐美尔的规模理论,派生出了关于都市社会基本交往形式的思考,同时又以关于社会异质性的分析整合了齐美尔的分工理论,并全然剔除了齐美尔用作解释都市社会关系变动因素之一的货币经济理论。另一方面,他从帕克那里吸收了人文生态学的某些成果,将人类集居密度作为一个考量都市社会心理及其交往行为的元因素,创建了自己独特的都市社会学理论框架。在他看来,都市生活的生态结构,特别是人口集居的规模、密度及异质性是造成都市化和构成都市性的三个互动性元因素:“对社会学的目的而言,都市或许可被定义为一种相对大的、密集的和社会性异质的个人的永久性集居地”[1],而都市社会学的任务即是分析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所引起的社会关系形态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料想都市社会景象的显著特征随着规模、密度和城市功能形式中的差异性而变化”[1]。
首先是规模的作用。同齐美尔一样,他认为规模的增长与人们关系的亲密度成反比,膨胀的社会规模减少了任何两个人以个人身份相知的机会,导致了对“第二性的”(超乎纯真个性或情感基础的)而非“原初性的”(基于个性或情感的)交往关系的强调,人与人之间由此相应地增长了对他人的冷漠,这最终导致了社会情感关系的离析。沃思将这种观点同样用于对都市人际关系的解释,因为都市意味着一个大规模的群体。“都市中的交往可能确实是面对面的,然而这种交往又是非个人性的、浮浅的、短暂的和零碎的,都市居民在他们关系中显现的自我克制、冷漠和腻倦的态度,可被看作是他们抵御个人要求和他人期盼的装备物”[1]。故而,都市规模的增长,扩大了作为都市生活特征的“社会距离”(主要指精神距离),“一方面,个人从关系密切的群体对个人及个人情感的控制中获得了解放和自由,另一方面则失却了自我表达的本性、道义和与一个一体化社会共生的参与感[1],大都市的精神生活由此趋于反常,个人只是孤独地走在人群中”。
第二是集居密度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沃思依据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将密度的作用与社会分化的影响结合起来思考。首先,他接受齐美尔关于复杂的社会分工造成了社会极度分化的观点,认同分化与规模的关联作用:“分化是任何人群对一个给定地区的数量增长作出的反应方式”[1],而人口集居的密度则又“强化了数量在使人及其行为多样化和使社会结构复杂化方面的作用”[1]。在此,沃思关于密度的社会学含义是:人口集居规模的增长,导致了分工精细的职业结构以及专司社会控制的正式机构的产生,并由此造成了复杂的社会功能分化和社会结构分层。复杂的功能分化和结构分层形成了一种人们依据他们特定的身份,而非他们原有的个性的交往形式:“我们看到了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指明了各职能人员的角色地位,而忽视了隐伏其后的个人特异性”[1]。他人仅被按其所扮演的角色地位来对待,这由此而增长了一种工具式的对待他人的态度。由于人群集居的密度增加了人们交往的频率,反而突出和强化了这种非个性的交往关系,增长了人们对互不相知的感知几率。同样,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中,都市居民间的接触和交往,往往是基于职业的往来和角色互动的需要,而非建立在个性需求或情感表达的基础上。故而,都市社会的交往形式带有明显的浮面性、短暂性、局限性和匿名性。
第三是关于异质性的讨论。社会功能的极度分化造成了大量社会异质性人群的集居。同齐美尔一样,沃思认为,在同质性的小群体(如乡村)中,个人与各级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直线状地置于一个同中心的圆中,大群体中(如都市)则形成了许多异质性的社会圈,这些社会圈之间的关系是部分相关乃至毫不相干的,个人有机会参与许多不同的社会圈,但没有一个社会圈能完全支配他的忠诚,故而个人同社会疏离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个人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亦随之增长。此外,异质性人口的密集居住带来的另一种对个性的影响是,必须对异质性容忍。这就导致了一种个人必须从属于群体的社会平衡化过程:“如果个人欲完全地参与都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他必须使自己的某些个性服从大社区的要求,以此使自己沉浸于群体运动”[1]。而个人的行为亦必须是集体主义性质的方显其有效:个人的政治参与须通过代表制度方可实现;官方机构在广大范围内负责制定各类条款和提供各种服务,而个人则越来越依靠这些条款和服务。在大都市中,个人被“降低至一个实际上无能的层面”[1]。在都市中,人的个性极易瓦解,心理疾病亦相应增加。
无论是齐美尔抑或沃思,他们都试图从对人类的社会交往关系及个性特征的考察中,剥离出一种属于“纯都市”概念的社会学因子,并进行理论抽象和概念归纳,以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乡村社会经验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和价值坐标体系。特别是沃思,他甚至认为,人类的关系形态可按一对逻辑上相对的形式(“都市的”或“乡村的”)进行概念化,任何经验性的案例都可被置于“乡村的”和“都市的”坐标两极之间的刻度上,依据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的程度进行各种社会形态间的比较。
三、一种纯粹的“都市性”是可能的吗
长期以来,齐美尔和沃思各自关于大都市的论述一直引起西方学界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多方面的。但两个关键点乃在于:一是,是否存在一种完全脱离了某种经济方式、生产关系和文化语境的都市;同理,是否有可能建构起一种完全脱离了某种经济方式及其社会、文化语境的纯粹意义上的都市社会学理论。二是剥离了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联系,孤立、抽象、静止地讨论“都市性”问题是否准确?
在齐美尔的三个独立变因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对规模作用的强调。按其社会学理论,都市首先是一个大型的人类集居体,仅这样一个事实就该被料想为会建立起不同于乡村这种小型集居体的人类社会交往形式。但除了规模以外,齐美尔还吸收了其他因素(如分工和货币经济)来解释都市社会交往关系及其非个性化特征,这不免使我们在阅读其关于大都市的论述时,遭遇了一种“典型的齐美尔式的两重性”,即其论述一方面是一种关于都市的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见诸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社会现象的分析,况且,人类集居规模的增长本身即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正是这种不经意的混淆,构成了齐美尔都市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弱点。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必须以一种超越都市集居形式概念的社会构成因素来定义都市,那么这些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现象便不可被狭隘地定义为“都市”社会现象,而只能被称作一种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语语境中的“社会”现象。正如贝克(H.Becker)所评价的:“齐美尔从未把都市化作为一种解释方案来考虑……相反,他观察所及的城市仅是一种表明自15世纪至最近的西方社会所特有的分工、货币经济、工资制度、显著工业化及其他一些特征的类型”[1]。故而,齐美尔关于大都市的论述就其理论基础的成分而言,更准确的应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发展中的都市”社会学理论。
同样,沃思的都市社会学理论也遭到了西方学界类似的批评,威廉姆斯(R.Williams)甚至认为,沃思的乡村—都市两分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验的心理投射。他在其论著《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指出:“乡村与城市的对照明显地是我们意识到我们经验的重要部分和我们社会危机的主要形式之一”[3],正是通过对乡村和城市的对照,“经验找到了赋形于思想的材料”[3]。按威廉姆斯所言,这种区分意象藉以派生的经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态的感觉。“疏离”原本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景中的日常生活是:人们把“分离的、孤立的、表面的感知和行为模式”[3]当作习以为常来接受,而被压抑在人们心理记忆中的人性沟通,则被移位至关于乡村社会的表达中,“乡村的意念被引向传统的、人性的和自然的方式……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紧张,一种被当作紧张来体验的现状,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照来认定各种未被解决的分歧和各类心理冲动间的碰撞”[3]。因此,乡村—都市的对照被威廉姆斯诠释为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的生存中,用以解释他们异化经验的一种观念形态。威廉姆斯的观点在逻辑前提上瓦解了沃思对“纯都市性”及其生活方式进行概念化的企图,并把对形成都市及其生活方式的社会学元因素的探讨,拉回至一个超越传统都市概念界限的、更为宽泛而具体的解释范围,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中的都市及其生活方式”。
此外,这些批评话语中还包括:离开了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观,孤立地讨论都市或“都市性”必然是不全面的。齐美尔和沃思关于都市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和个性状态的描绘,在客观上容易给人一种悲观的感觉。这种关于都市的描述与西方文化中一种对乡村的怀旧心理和反都市文化倾向暗合。“他(按:沃思)所绘制的那种匿名的、非个人性的、浮浅的和工具主义的都市生活,与几代英国小说及诗歌中描绘的景象完全一致”[4]。
四、在当代中国影响的批判性思考
就严格的意义而言,中国学界还未对都市社会进行过系统化的研究,对西方有关研究的理论印象也是破碎的。但在中国当下人文语境中,都市化不仅被看作一种现代化的物质定向,亦曾被预想为一种催生“新意识形态、新价值观念、新心理结构、新人际关系、新人文系统”等精神文化机制的媒介。故而乡村和都市的截然两分,不仅一度被演绎为传统和现代、愚昧和文明、落后和发展的同义语,亦在文化思考中成为一种显在或隐性的价值坐标和思维框架。但随着现代化方案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和市场的迅猛推进,日新月异的器物层面对较为深层的体制、观念产生剧烈震荡的时候,作为人文话语的“都市”受到了某种质疑。人们在坚持把都市化作为现代化的物质定向的同时,亦普遍地感受到了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转型期的种种价值矛盾。其中包括生态学意义上的人与环境之间,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人文学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冲突。
在一些都市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和文化圈里,齐美尔、沃思等人所提及的都市社会交往关系和精神形态诸特征(冷漠、短暂、浮浅、非个性及金钱理性、技术理性等)亦正在被人们,特别是被一些敏感的人文学者和作家们所感知。沃思关于人“孤独地走在人群中”的著名论述,成为当代文艺批评话语中指涉都市现代性的常用语,齐美尔关于“金钱理性”和“与人相对的客观精神”的论述,则成为许多当代作家笔下关于“物化的城市”、“物化的人群”、“物化的心灵”描述的精妙理论注解。许多当代作家笔下的都市意象,往往演绎为一种以牺牲人文价值为代价换来的纯客观物质世界。有的作家则背对愈演愈烈的都市化进程,转而向传统乡村社会寻取重构精神家园的思想资料[5]。一些理论话语虽然依据历史主义理性立场,认定乡村和都市代表着两种层次的文明范式,承认现代化是一种广泛的城市化或都市化过程,认同现代人文精神的建设有赖于一种都市意识的建立,但清醒的历史主义理性往往同人们的经验世界和文化记忆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宏观理性上的认同,往往被微观经验世界中的价值疑惑所消解,人文意义上的种种奔向都市的努力,常常在不经意中悄然转化为对都市的拒斥[5]。许多人文思考者在享受现代都市文明带来的种种成果的同时,在精神上则时刻保留着逃离的姿态。西方社会在都市化进程中曾经历的物质精神两分离的社会心理状态,在客观上被处于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人文知识者所经验。“都市人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发问。
我们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产生这种价值震荡的原因。一是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少有现代都市经验。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都市,从产生迄今不过百多年的历史,根本无法与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乡村经验相比。况且,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的产生,并非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是一种饱蘸着血与火的硬性植入,是一段夹缠着民族耻辱和现代文明发育的双重历史过程,当下人文语境中的“都市”,往往和中国近现代史中人文学者的一种“乡村美,都市恶”的深度心理模式相通[5]。二是都市的现代市场生存方式及其孕育的社会交往形态、价值观念等与我们的文化积习相去甚远。正是在此基础上,齐美尔和沃思等人关于大都市生活的描述(远非其理论全部)和我们的某种人文心态达成了默契。
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本身,从生产力发展这一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源中,去认识都市化进程对中国社会发展及人文精神建设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城市”或“都市”的概念早已有之。最初的城市概念起始于军事需求和“集市”。“城”指旧时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市”则指集中做买卖的地方。《易·系下辞》中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说法。都市则指“大城市”。《汉书·食货志》上有“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的描述。但安放在乡村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城市或都市,从来都是作为封建政治、经济体系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它不可能发育出一种足以支配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完备市场体系,也不可能产生出现代公民意义上的成熟市民阶层,更不可能结构起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关系形式和人文意识。以皇宫为中轴线的古北京城,其所象征的皇权政治,本身即是农业社会家族制度的延伸或浓缩。至于我们所说的现代都市,则是一种以大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其结构底蕴,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市场运作为其基本生存法则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有机统一体。它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都市的任何一项社会文明成果都离不开其特定的经济杠杆作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形成的特定经济方式,才是都市社会及其“都市性”形成的真正社会学元因素。
世界上最早的都市化进程发生在英国。18世纪英国的工业化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劳动力、资金、企业、市场乃至知识群体都向着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地区集中,于是出现了产业和人口密集的现代大都市。随着都市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分工的日趋细密,用作商品交换和调节生产的市场亦日趋复杂和强化,并最终造就了一种与以土地为生、以简单交换作为补充的乡村生存方式完全不同质的,以交换为惟一谋生手段、以大工业提供的丰富商品为生活资料的现代都市生存方式。故现代都市社会与传统乡村社会最本质的区别,乃在于两者所据的经济基础的不同及由此造成的生存方式的差异。
现代都市经济方式所产生的意义,当然不会仅限于“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它亦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心理结构的重组。首先是市场生存方式产生了一个以交换为生的市民阶层,同时由于人们在市场活动中,理性的契约往来逐渐代替了传统经济社会中惟精神的道德承诺和单一的社会情感维系,从而导致了社会形态如德国社会学家托尼斯(F·Tonnis)所说的,以自然意志推动的古代礼俗社会向以理性意志推动的现代法理社会的进步。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现代都市化进程对中国社会人文心理结构产生最大的冲击,莫过于是其市场生存方式孕育的一套与传统宗法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交往形式和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首先是,市场生存条件下的人们作为各自商品的持有者在参与交换的过程中,其地位是平等的,这就在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以伦理纲常的“义”作为社会关系惟一纽带的道德义务原则。长幼尊卑一旦进入市场便无等级差别;士农工商一旦进入交换亦无贵贱之分,交换关系重于宗法关系,无疑为个性的发展和个人选择的自由提供了切实可能。此外,交换的动机在于满足个人自己的某种欲求,亦即肯定了人之欲望为人之本质的近现代人性观(相对于宗法社会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承认人是自利的,亦意味着必须对他人利益的认同,新的群体规范由是在强调每个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被建立了起来。这种以市场生存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形式和人性观念,影响到了都市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组织建构和制度建设。故而,在中国当下人文语境中,现代“都市人”的文化意蕴首先应该是对自然经济背景下的惟道德的“宗法人”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惟意志的“政治人”的一种历史文化超越。“都市人”不仅仅是“孤独地走在人群中”的人,更重要的是一群走出传统依附性人格和“安贫乐道”的守成型社会行为模式的现代人。这是我们在理解中国都市化进程及其对中国社会和人的个性发展的影响时,首先要作的历史文化定位。
在我们厘清推动都市化进程的真正社会学元因素、确定都市社会及其文明成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后,再次回到齐美尔和沃思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就会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和理性的眼光来剔选其真理的颗粒。尽管他们所构建的关于都市的特定理论,说到底,乃是一种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具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限定性。但无论如何,齐美尔和沃思关于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的论述及其关于都市社会学诸因素的探讨,对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都市化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其论及的规模、密度、异质性、金钱理性等问题,就其理论的出发点而言,始终将人的个性发展与人的社会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考虑,其所阐释的社会交往关系形态,往往是生活于此关系形态中的人的个性程度的显形。这对我们在一个讲究理性、效率、利益,人口集居规模和密度激增的现代都市社会中,如何保持人文情感的平衡及个性、人格的健全,创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生态环境(包括空间布局、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组织制度等),化解都市化进程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作用,推动人类社区的健康发展及其精神家园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这也是我们解读其都市社会学理论时不可疏漏的一份思想成果。
标签:社会学论文; 齐美尔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沃思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