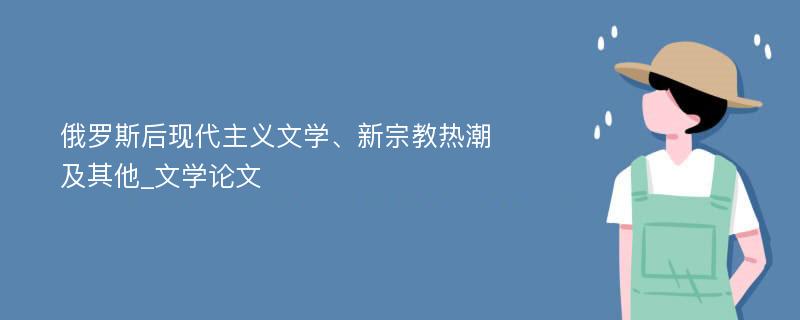
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宗教新热潮及其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及其它论文,热潮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尤其从九十年代初)起,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性变化。随着这种变化,俄国文化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两个现象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盛行和宗教新热潮的出现。本文想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宗教新热潮与俄国社会转折的关系,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宗教意识的联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
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并非始于今日,然而从九十年代起在俄国流行起来,并获得了相当的规模。如今打开俄国的报刊杂志,到处可见后现代主义一词;连续三年文学界权威的布克奖得主均为当今俄国走红的后现代主义作家〔1〕;俄国文坛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形成了从解冻文学争论以来的又一次文坛论争的高潮。这些现象表明后现代主义文学这种现象在当今俄国文学中的地位,以致于有些文学评论家(如符·库里岑)断言俄国文学进入了后现代时期。
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现的。维·叶罗菲耶夫的小说《莫斯科——别图什基》(1969年)和安·比托夫的小说《普希金之家》(1971年)可以视为俄国最初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叶罗菲耶夫的小说《莫斯科——别图什基》对俄国的现实和历史作了广阔的描述,从福音书一直到《真理报》都涉及到了。然而作者是从一大堆零乱的“碎片”,甚至是“垃圾”中创作出一部完整的作品,让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和传统汇合,碰撞,在各种文化现象的多声部汇合中,发现各种文化机制转换的无常和荒诞。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描述和研究苏联知识分子的种种心态,反映出在当时苏联社会里俄国古典文化传统存在的虚假性,展示了俄国六十年代末后现代主义现象出现的现实背景。
叶罗菲耶夫和比托夫创作的这两部作品,从内容到艺术手法上都大大有别于传统的俄国文学。从内容上看,它视现实、历史为荒诞,无序和混乱,并认为这是一种无法根除的永恒,是历史、文化、生活,存在的一种完全正常的属性。在艺术手法上运用暗示,隐喻,寓意,联想,巧合,列举,粘贴,跳跃,化入等手段,创造出一个特殊的“文化场”。他们之所以这样进行文学创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无休止地重复传统,不想去寻找那些丧失价值的传统碎片。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从前的艺术语言一去不复返,不能用以前的艺术语言去创作。所以,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艺术语言风格的转换,是语言进入一种新情景。俄国文学评论家符·库拉科夫说:“后现代主义,这不是风格,不是文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这是现代艺术语言处在其中的一种情景。”〔2〕这点也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诗学特征。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出现,有人称这是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前30年),它与俄国社会的变革有很大的关系。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是原苏联社会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出现变化和转折而随之产生的现象,表现出艺术现象出现与社会重大政治变革的“押韵”联系。五十年代中叶,在俄国(原苏联)国内开始了政治的解冻时期,“解冻文学”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学思潮出现在苏联文坛,文学作品里敢于揭露俄国社会的阴暗面,反对个人崇拜和粉饰现实,等等,这一切让人们对政治复兴抱有了希望。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末,“解冻”失败,俄国人的政治复兴希望彻底破灭,他们陷入了精神危机。因此必须寻找出路,于是从俄国文学内部引出了后现代主义。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俄国社会发展相对稳定(有人称之为“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内,俄国的理性文学得到普遍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较为缓慢。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九十年代,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活跃起来,涌现出一大批后现代主义作家,如阿·捷尔茨,尤·阿列什科夫斯基,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马·哈里托诺夫,符·马卡宁,维亚·皮耶楚赫,瓦·波波夫,维·叶罗菲耶夫,阿·伊瓦契柯,符·沙罗夫,索洛金,索柯洛夫,科罗廖夫,托尔斯泰娅等等,他们创作了相当多的作品,构成“异样文学”的庞大队伍。俄国当代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马·利帕维茨基把俄国最近十年的文学归纳为三个阶段,主要以后现代主义作家及其创作为依据的,可见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当今俄国文坛的影响和地位。
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今日俄国的盛行,与俄国社会九十年代初发生的政治剧变有直接关系,可以大胆地说,苏联如不解体,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国就不会有当今的这种局面和规模,它也不可能在俄国文学的多元格局中占据如此显赫的地盘。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盛行,是社会巨变给俄国文化带来的危机,而由这种危机带来的文学现象。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迅速发展是对俄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危机的一种回答,是对文化传统的反叛,是摆脱文化困境的出路,是俄国文学的一种新解决。我们在这里并不是给后现代主义文学作总体评价,而只是想强调它与俄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的联系。
俄国社会回归宗教也并非始于九十年代,这种回归应推到七十年代初期,就是说它的出现与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时间大致相符,而且同样是六十年代末“解冻”失败,相当多的俄国人陷入精神苦闷而引起的后果。人们在现实社会里找不到精神支柱和寄托,只好到宗教里去寻找精神的归宿和安慰。然而应当指出,当时的宗教回归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因为在原苏联,无神论思想是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八十年代末,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俄国人转向宗教信仰〔3〕, 随之恢复东正教俄罗斯的运动犹如开闸的洪水,汹涌而下,一泻千里,形成了宗教新热潮。
在这次宗教热潮里,宗教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俄国有这样的观点:当代俄国人既便不信神,也属于东正教基督徒,因为其基督徒先辈的精神以独自的方式铬记在他心灵深处,所以他尤为尖锐地感到自己作人的缺点,甚至罪孽。哲学家阿·洛谢夫对此说得更加明了:“……既然你是俄国人,那就意味着你是基督徒。”〔4〕这种观点虽然十分绝对,也未必符合实际,但它表明了俄罗斯民族是笃信基督的民族。这也是宗教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爱国派(亦称新土壤派)的文学活动在这次宗教新热潮里占着显著的地位。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国文学界分成两大营垒,一个是爱国派,另一个是民主派,两派互相对立,并就今日俄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展开论战。爱国派是一批坚持俄国文学传统的作家,其代表人物是瓦·拉斯普京,瓦·别洛夫,鲍·叶基莫夫等人。他们坚持俄罗斯走民族化的发展道路,提倡爱国主义精神,认为俄国文化应立足于俄罗斯民族的土壤,他们继承了十九世纪土壤派同人民,尤其是同农民建立有机联系,同农民接近的思想。该派批判民主派的西欧化观点,认为民主派的错误就在于迷恋西方的民主和文化,忘掉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忘掉了爱国主义和人的道德义务和职责。爱国派的意识形态是十九世纪斯拉夫派的某些思想,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史学派思想,民族起源论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的综合。爱国派作家们乐于探讨人的信仰问题,对人与上帝的关系有自己新的解释:“在任何民族及其生存的任何时期,一切人民运动的目的都仅仅在于寻找上帝,寻找自己的上帝,一定是自己的,相信自己的上帝是唯一真正的上帝。上帝是整个人类从其诞生到灭亡为止的一种综合个性,让许多人和许多民族有一个共同的上帝,这种事情在历史和现在都从来没有过,但是每个人总有自己一个独特的上帝。如果上帝变成共同的,那么他就同人们对他的信仰一起死去。人民愈强大,它的上帝就愈特殊。人们从来离不开宗教,就是说,人们从来就离不开善恶观念。每个民族有自己对善恶的独特认识……”〔5〕这段话强调上帝是人的一种直感感知, 强调人与上帝的结合,成为独特的上帝,共同承担起创建真善美的世界的伟大任务。
爱国派文学的重要阵地是俄国文化杂志《莫斯科》。《莫斯科》杂志的主编列·鲍罗金在谈到该杂志时说:“《莫斯科》……基于两个柱子上,那就是东正教和国家观念。”〔6〕可见, 东正教是《莫斯科》杂志的精神支柱之一。因此,宣传东正教成了该杂志的一个宗旨。这份杂志每期都辟出“家庭宗教”专栏,刊登上至牧首下到一般神父的正统文章,表明东正教会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宣传宗教思想。该杂志十分推崇二十世纪初“俄国宗教复兴”的一些著名宗教哲学家的思想。罗札诺夫,别尔佳耶夫,布尔加科夫,伊里因等人成为该杂志重点宣传的人物。《莫斯科》杂志的宗教立场非常保守,它反对俄罗斯东正教参加世界宗教会议的工作,反对俄罗斯东正教与其它教会进行任何接触,也反对在俄罗斯东正教里进行任何改革。该杂志根本不刊登民主派作家的作品,也几乎不刊登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象著名作家,《新世界》杂志主编札雷金的作品也很难出现在《莫斯科》上,这说明该杂志坚守自己的思想阵地,可见其思想的保守和偏激。
《我们的同时代人》是爱国派文学家的另一块阵地。该杂志自封是俄罗斯作家的杂志,实际上只是在野派爱国主义作家发表作品,宣传自己思想主张的场所。拉斯普京,别洛夫,普拉哈诺夫,利秋金,莫热耶夫,叶辛,鲍罗金等作家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此外,该杂志开辟出“特写与政论”专栏,专门刊登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文章。仅在1995年,俄罗斯前副总统阿·鲁茨科依,雅库梯莎哈共和国总统马·尼古拉耶夫,俄共总书记格·久加诺夫,苏联英雄,“8·19 ”特别行动委员会成员瓦·瓦连尼科夫大将等人都在该刊物发表过文章,大谈特谈爱国主义思想。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久加诺夫在《文明斗争中的俄罗斯》一文里提倡爱国主义同时,建议读者认真研究学习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特鲁别茨柯伊,弗罗连斯基,布尔加科夫等人的著作。这点恐怕是久加诺夫的文章能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的重要原因。《我们的同时代人》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刊登宗教界人士,特别是宗教神学家的著作。例如,圣一彼得堡都主教约翰的全部作品都在该杂志发表。在俄国近七十多年的历史中,世俗杂志为宗教界神学家提供如此方便的发言场所,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现象,是这次宗教新热潮的一个特征。
俄国的报纸也是表达东正教思想的场所。在众多的报纸中,《独立报》和《今日报》与宗教的关系尤为密切。《独立报》经常发表宗教界人士的大块头文章。这些宗教神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用宗教的集结性分析俄国历史的发展和俄国今日的现状,阐述俄国东正教在社会里的作用。《今日报》的星期六版专门辟出专栏,大谈俄国今日的宗教社会生活,强调俄国东正教是俄国文化的核心,宗教集结性是俄国思想的中心观念。
除世俗的报刊杂志外,宗教的报刊杂志在这次宗教新热潮里的活动尤为明显。1990年,原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其中一条规定宗教组织具有法人权力,可以独立从事出版活动,甚至可以施行不依赖国家的新闻政策。这项法令为宗教出版物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法令颁布后,宗教的报刊杂志犹如雨后春笋,在俄国大地上普遍出现,呈现出一幅宗教出版物多元化的繁荣景象。据1994年的统计,仅基督教(其中包括东正教基督徒,洗礼教派,天主教派,复临安息日会教派,等)的报刊杂志就有140多种。 这些报刊杂志的注册人和主办者虽然不同,其内容和形式也多种多样,但共同的宗旨是宣传宗教思想,提高广大教徒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帮助教徒的工作和生活。
电视电台这些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也不同程度变成宣传东正教思想的阵地。莫斯科电视台每天早晨8∶30分有一个固定的宗教节目。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牧首,都主教,大主教)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频频露面,并经常播放采访他们的专题报导,每逢重大节日和宗教节日,牧首或都主教往往是电视台的座上宾,他们从电视屏幕向俄国广大教民祝福,这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电台在这方面走在电视的前面。众所周知,1989年以前,俄国境内的电台从未播放过宗教节目,那时人们只能从“美国之音”,英国的“BBC”广播电台,“梵蒂冈电台”收听宗教节目。1989年,在举办了“罗斯受洗”1000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俄国(原苏联)政府解除了对宗教宣传的许多禁令,到1990年末,宗教节目开始出现在俄罗斯国家级电台上。如今,俄国国内最主要的两家电台奥斯坦基诺广播电台〔7〕和俄罗斯广播电台都辟有专门的宗教节目。奥斯坦基诺广播电台每周有12种有关基督教的节目,播音总时间达355分,象“圣经与当代”,“家庭宗教”,“光明屋”,“基督与基督徒”等节目在听众中颇有影响。 俄罗斯广播电台每周有5种关于基督教的节目,总播音时间为95分钟,在“福音书阅读”,“希望之声”,“我信仰”,“山金车”和“俄罗斯之觉醒”这5 个节目中,以播送俄国宗教生活的新闻节目“山金车”的收听率最高,充分表明俄国的当代教民、信徒对宗教生活的关心和兴趣。除上述两家电台外,青青广播电台,灯塔广播电台也播放宗教节目。可见,宗教在俄国已经充分利用象电视电台这样的传媒工具了。
以上我们从文学界和大众传媒介绍了俄国宗教新热潮的一些表现。当然这次宗教热潮的表现不仅仅这些,它涉及到俄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且其活动和影响都相当大,成为当今俄国的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
前文已述,这次宗教新热潮是俄国社会在90年代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这是这次浪潮兴起的直接原因,此外,这次宗教新热潮的出现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俄罗斯从公元988年“受洗”后,一直是信奉基督的东正教国家。 基督教无论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文化现象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将近1000年的历史。1917年的十月革命摧毁了俄国宗教文化载体的社会阶层,无神论思想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宗教并没有被消灭,基督精神深深地根植于一大批俄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里,也潜伏地存在于社会的文化领域里。一旦时机适当,它必然会强烈地表现出来。九十年代初俄国社会的巨变给宗教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因此它便表现出来,形成了这次宗教热潮。而从俄国历史来看,社会发生巨大转折时出现宗教热潮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面临着重大的社会变革,俄国应走什么路的问题摆在社会的面前。于是出现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激烈论争。斯拉夫派主张俄国走东正教的道路,坚持宗教的集结性和村社性,反对走西欧的物质化道路。在文化问题上,斯拉夫派视东正教为俄国文化的源头,以俄国东正教的精神解释各种文化艺术现象;在政治主张上,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农民应成为俄国历史的主体,认为俄国村社是纯朴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宗教集结性是俄国农民的本质特征之一。由于斯拉夫派的活动以及他们与西欧派的论战,斯拉夫派思想在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一次宗教文化热潮。一大批作家兼思想家,如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科舍列夫,萨马林,包括后来的列昂季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一方面探索俄国的宗教性,另一方面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一大批反映自己宗教哲学思想的文学作品。此外,斯拉夫派还办了《俄国漫谈》,《乡村建设》等杂志,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可以说,斯拉夫派的活动所表现的宗教文化热潮不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而且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宗教浪潮——俄国宗教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宗教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两个世纪之交时期俄国社会变革带来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普及,民粹派思想受到批判,社会上各派的政治思想斗争激烈,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和唯心主义。这个时期,社会思潮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又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别。以别雷,纳尔布特,维亚·伊万诺夫,巴尔蒙特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分子对人民的苦难深感同情和关注,对宗教表现出十分的眷恋和兴趣。以索洛维约夫,罗札诺夫,别尔佳耶夫,舍斯托夫,费多罗夫,布尔加科夫,梅烈日柯夫斯基,特鲁别茨科伊,伊里因,弗洛连斯基,卡尔萨文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宗教哲学家集团。这些宗教哲学家的思想理论各有千秋(如索洛维约夫的“大一统”思想,费多罗夫的“积极基督教”观点,弗洛连斯基的以象征主义为中心的宗教哲学观念,卡尔萨文的关于人的个性的理论等等),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在继承十九世纪斯拉夫派的宗教思想基础上,对宗教信仰进行新的探索和哲学的思考,以求在宗教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人生意义诸问题的答案。这个时期,斯拉夫派文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一起掀起了另一次宗教热潮,同时也创造出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化的五彩缤纷的画卷,对俄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对十九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两次宗教热潮作了简单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俄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宗教热潮出现的规律性。今日俄国的宗教新热潮再次说明了它与社会巨大变革的规律性联系。
二
上已述及,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盛行和宗教新热潮都与九十年代俄国社会发生的巨大的转折有关系,那么,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宗教思想的关系如何呢?
俄国后现代主义是俄国文化发生结构学飞跃而带来的一种结果,是一种文化暂时死亡的现象。在俄国,有些文艺理论家把后现代主义美学称为末日美学。这点有其道理。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往往以圣经启示录为参照,以预言,暗示,隐喻等手法创造出二十世纪末的启示录文学,具有一种宗教末日论的精神。
弗·戈连什坦的《圣诗》,符·沙罗夫的《彩排》和尤·柯兹洛夫的《夜猎》这几部后现代主义小说就是俄国二十世纪末的启示录文学,是圣经启示录的当代版本。《圣诗》是一部描写敌基督的尘世生活史。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敌基督的出现本身就是世纪末日到来的先兆。敌基督与基督的斗争是圣经启示录的重要内容。因此,敌基督作为戈连什坦的小说《圣诗》的主人公就是宗教末日论精神的一种体现。但这位敌基督与圣经启示录的那位敌基督又不同,他不是上帝的敌人,也不与基督作斗争,而恰恰相反,他把基督视为自己的兄弟,关心他,爱护他。然而这位敌基督毕竟是位恶魔式的人物,他无法过正常的尘世生活。小说的最后一幕,他与自己的养女通奸,这一罪孽暴露出敌基督的本质,表明他从本质上仍是基督的敌人。《圣诗》这部作品充满荒诞,书中描写的许多东西与人们的预料,与世界的和谐相悖,这隐喻着当今俄国社会的混乱,无序和荒诞,呈现出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景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混乱中寻找意义,在荒诞中寻找规律,在无序中寻找出路的尝试。《彩排》这部小说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也与世界末日和基督第二次降临人世有密切联系。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帮农民,他们是虔诚的教徒,按照牧首尼康的旨意去参加彩排。这不是一般的排练,而是人生的排练,是参加几个世纪来新约全书场景生活的排练。农民们在那里焦急而荒诞地等待着世界末日和基督的再次降临,然而他们的等待是枉然的。《夜猎》这部作品则更是写出世界末日前魔鬼复出的当代故事。一帮饥饿的、心理变态的乞丐在大地上到处游荡,他们是吃人的魔鬼,随时准备把自己最亲近的人吞到肚里。在他们游荡的世界上,人们对权力梦寐以求,杀人是这个世界占上风的权利。小说的主人公想在这个世界上恢复真理和正义,但他的行动又导致了杀人的新浪潮。这完全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能否出现基督,将这些吃人的、杀人的恶魔再次捆锁起来,再次出现基督治理世界的“千年王国”呢?小说里写到,耶稣基督在南极州,但这是位当代的基督,是位头一个获得党证的党员,他身边有一批共产党人,他们能融化冰雪,战胜各种疾病,把死人复活。
以上三部小说的共同特点是,故事情节都与圣经的世界末日到来前的景象相似,这暗喻出二十世纪末俄国社会的现实,小说具有一种宗教末日论的精神。此外,几部小说都写到或提到基督,但这里的基督不是个体的象征(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两部小说里的基督是个体的象征),而是一种隐喻手段,一个文本符号。在这些作家笔下,世界失去了中心,社会是一片空虚,到处是混乱和荒诞。主人公们在对生存意义的追求和探索中,发现的是痛苦,邪恶,因此,他们用基督形象去隐喻福音传遍世界、天下太平的“千年王国”。这实际上是让读者去构建一些充满末日论精神的宗教幻想。
大多数俄国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宗教是俄国人的精神支柱,宗教性是俄国精神性的主要内容,肯定宗教对个体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有巨大作用,承认宗教充满高度的伦理激情。他们十分崇向二十世纪初宗教复兴时期的一大批宗教哲学家的思想,甚至有些作家将这些宗教哲学家视为自己的偶像(如叶罗菲耶夫视罗札诺夫为偶像)。这一切在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夜间时分》,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的轨迹,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等)都反映出来。我们在此仅想以《命运的轨迹,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以下简称《小箱》)为例来说明这点。
哈里托诺夫的《小箱》一作获1992年的布克奖,是俄国后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俄国文学评论家斯捷帕尼扬称这部小说是“俄国后现代主义的圣经”。另一位俄国文学评论家阿·阿尔汉格尔斯克说:“如果我有六个布克奖,我都会奖给哈里托诺夫这部小说。”〔8〕由此可见《小箱》一作的成功。
《小箱》这部小说从思想性上看,是一部讲述宗教是人的精神支柱的小说。主人公之一未拉舍维奇是二十世纪初的宗教哲学家罗札诺夫的影子,他的那些记录在糖纸上,锁在小箱子里的充满哲理的格言是罗札诺夫的宗教哲学思想的遥远的闪光。
米拉舍维奇是位不走运的人。他本来住在首都,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但因莫须有的“剽窃”罪名被首都文学界撵出都城,来到外省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当上一位可怜的图书管理员。他生活拮据,衣衫烂褛,甚至领带上还打着补钉。家中还躺着瘫痪的妻子。总之,他独自在外省承担着不公正的命运给他压上的重负。但米拉舍维奇是位独具一格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他把自己一生中的思想、感受,断想都写在糖纸背面,这是他的痛苦和他的思维的见证。书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叫拉札文。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研究,正准备副博士论文答辩。当他的论文快要写成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命运的轨迹”)让他从档案处发现了米拉舍维奇的那个装着上面写有格言的糖纸的小箱子。于是便开始了米拉舍维奇与拉札文的对话,这是一种多层次、多声部的对话,他俩在这种对话里交换着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对信仰的看法,交换着个人的痛苦和孤独的经验。拉札文从翻阅、整理米拉舍维奇留下的那堆写满格言、劝谕,警句的糖纸中,发现了在米拉舍维奇的平凡哲学中,在他那意味深长,言简意赅的思想里,有着伟大的真理,而且从这些写在糖纸的格言中渐渐地浮现出宗教哲学家罗札诺夫的形象。这样,米拉舍维奇就变成罗札诺夫的思想双重人,表现出罗札诺夫的宗教思想。而拉札文在研究米拉舍维奇的穷困、奇特、悲剧的一生时,渐渐接受了后者的思想,又成为二十世纪末的米拉舍维奇。无论米拉舍维奇还是拉札文在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研究探索中发现了痛苦,发现了俄国现实的肮脏、荒诞和空虚。他们在外部世界找不到答案和出路,只能转向排斥外部世界的内在闭塞,只能靠自身内部的努力,用内在的精神升华去达到神圣,去宗教那里寻找精神的本原。小说中的瓦砾场很有象征意义,这便是世界离开宗教而呈现的面貌。因此,世界要想以有序的面目出现,必须回到罗札诺夫所倡导的宗教精神上去,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寓意所在。
在俄国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作品里,许多事物,甚至人物呈现出虚幻、恍惚、不定形的状态,作品缺乏形象性和逼真性,仿佛潜在地遵照着圣经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出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9〕这段圣训。 这与俄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审美观有联系。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一切事物都失去其固定的形状,事物本身无定形可言,因此也不可能有表现它们的逼真性和形象性的文学。甚至有人断言,生活的逼真是危险的东西,形象性是在上帝面前的邪恶。〔10〕后现代主义作家马卡宁的小说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上述特征。
《审问桌及其它》是马卡宁的获1993年布克文学奖的小说。这部小说描述的事件是零散、抽象、虚幻的。没有引人入胜的细节;也没有栩栩如生的描写。甚至小说的出场人物都无名无姓,年岁不祥,而只有人物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反省。因此,这部小说成了作家马卡宁进行的一次实体研究。实体在马卡宁笔下变成了“一张铺着呢布,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这正是该小说名字的直译)。实体在这里来自对自我评价和自我反省的正常需求,然而这种正常的需求在传统的形式里无法体现,因此就接受了群体对个体的审问形式。群体和个体是人的个性自我控制系统的两极。群体是普遍道德,尤其是宗教道德的聚合体,个体是以良心体现的聚合体。一般情况下,人的个性自我控制系统的两极保持平衡,即良心不违背普遍道德;普遍道德符合良心的需求。但是人的良心一旦违背普遍道德,自我控制系统遭到破坏,人就应当受到审问。马卡宁的小说中的“我”就受到了审问,其实在这部作品里,“人”总是受到审判,坐在那张桌旁的每个人都受到审问,审问让人进行自我反省,回到良心那里,让良心符合普遍的道德,以呈现出人的个性的完整和完美。
《高加索俘虏》(刊于《新世界》1995年第4 期)是马卡宁的一部描写战争的短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在哪儿作战,参加的什么战争,从小说描述是无法断定的。小说的叙述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跳跃性,仿佛作者和主人公共同扛着一台摄像机,然而却不知道人物的下一个动作和发现是什么。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无论战争、也无论胜利和失败都是一种假定的事实。谁都无法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来又会怎样。世上的一切都是朦胧的,不清楚的。
读完马卡宁的这篇小说,我们对事件和人物很难有一个固定的形象,而只能看到作者对某种情势所做的实验室内的假定,这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作家马卡宁摈弃形象性的又一次试验。
善与恶是人类道德的一个基本的内容。二十世纪末,俄国的工业文化(确切说,是后工业文化)代替了农业文化,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混乱和无序现象,恶在人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和突出,它控制着人的理性和行为,造成一种令人无法摆脱的困境。恶使人失掉人的个性,成为邪恶的制造者,给社会带来悲剧和灾难。
俄国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对善恶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对“人身上的永存罪恶”予以极大的关注,同时又在积极地寻找“人自身的善与恶的平衡关系”(马卡宁语),寻找抑恶扬善,通向善的途径。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里对恶予以强烈的否定,这种否定依据的是圣经上的那些最基本的善行原则(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是一种启示录式的对邪恶的否定。圣经的启示录,约翰对未来天国的热忱决定着他的“发现”的性质。启示录对世界的感觉,是一种尖锐到精神边缘的意识,是一种对善恶的扩张的强烈感觉,是对恶的坚决否定。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对恶的否定有一种启示录对世界的感觉。
马卡宁的小说《路漫漫》就是一部探讨人类的善恶问题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作者以一种荒诞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创造出二十世纪末邪恶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景象,这种永恒的邪恶让人感到愁怅和无奈。但是小说的字里行间透出了作家对恶的坚决否定和对善的强烈渴望和追求。而且通过奥莉娅这个形象暗示,宗教就是通往善行之路。奥莉娅是位座落在草厚深处的大型工厂招待所的女服务员,她大脑生过病,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思维停留在“上上个世纪”,但她是位教徒。在这位单纯幼稚的姑娘身上有着人性的善美。马卡宁以奥莉娅形象暗示,只有远离现代科技文明,信仰宗教的人才能显示出人性的善美,否则,现代社会的罪恶将扭曲人的个性,成为邪恶的制造者。实际上,作家在此已经指出什么是通向善的途径。马卡宁在这里与那种持“俄国道路的目标,是在历史末日之前恢复东正教俄罗斯”〔11〕观点的人遥相呼应,把俄罗斯的善美未来寄托在东正教上。
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宗教新热潮是俄国社会在二十世纪末俄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转型期出现的现象,它们具有一种暂时性的特征。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彻底结束,这两种现象也会渐渐消失的。
从近一、两年俄国文学发展情况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高潮似乎正在消退。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5年布克文学奖得主易人,落入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格·符拉基莫夫手中(他的获奖小说《将军和他的军队》)。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小说独领风骚的局面已经动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位老牌现实主义作家在沉寂多年后“重返”文坛,如瓦·拉斯普京仅1995年就写出三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女人的谈话》,《下葬》,《邻里相处》,引起俄国文学界的普遍注视;还有一些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最近一、两年推出一大批力作,如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和该杀死的》,阿纳尼耶夫的《不朽政权的面孔》等等,这都在与后现代主义作家争夺文学的地盘;几家大型杂志的主编,如《莫斯科》杂志的鲍罗金,《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的库尼亚耶夫,《十月》杂志的阿纳尼耶夫都撰文或发表谈话,强调文学既要保持与传统的联系,又要涵盖当代俄国生活的整个空间,这表明他们对当代文学脱离传统,远离现实生活的倾向所表示的忧虑。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诗学和美学里有一种自我毁坏的机制,由于它缺乏可读性而获得不了众多的读者。文学失去读者必然会走上危机和衰退。随着俄国社会转型期结束,后现代主义文学盛行的外部环境将不复存在,它将从俄国文学中渐渐离去。
这次宗教热潮也将随着俄国社会转型期结束,走向自己平稳的发展。但是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绝不会象后现代主义文学那样消失的无影无踪,它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并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影响和作用。
注释:
〔1〕哈里托诺夫,马卡宁,奥古扎瓦分别是1992 年, 1993 年,1994年的布克文学奖金获得者。
〔2〕符·库拉科夫:《诗与时代》刊于《新世界》1995年第8期,206页。
〔3〕1889—1993年,俄国信教人数急剧增加, 教徒已占全国居民一半以上。(参见B·波尔金柯的《宗教与后共产主义俄国》一文)
〔4〕转引自《青年进卫军》杂志,1995年第11期,187页。
〔5〕转引自格·波缅兰茨的《俄国文化中的毁灭倾向》一文, 刊于《新世界》杂志1995年第8期,141页。
〔6〕《文学评论》1994年第1—2期,22页。
〔7〕即俄国的中央一台。
〔8〕见俄国的《文学评论》1994年第5、6合刊, 谢苗诺娅的《‘简单和谐’的歌手》一文。
〔9〕见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
〔10〕参见米哈依尔·艾普什坦的《后先锋派:观点之比较》刊于《新世界》杂志,1989年第12期。
〔11〕见马·纳札罗夫:《西方,共产主义和俄国问题》一文。刊于《独立报》,1995年10月26日,第7版。
标签:文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宗教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基督教论文; 东正教论文; 耶稣论文; 斯拉夫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