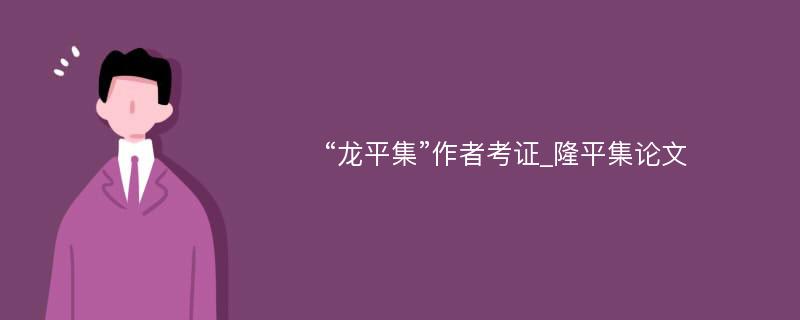
《隆平集》作者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隆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隆平集》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史籍,史料价值很高,历来为宋史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关于它的作者,至今还是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此书南宋初行于世时,题曾巩撰。这本来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自从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率先发难,提出“疑非巩书”后,聚讼遂起,到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则断定其出于伪托,而非曾巩所撰。至今学术界大多以此说为是。《四库提要辩证》作者余嘉锡曾力排众疑,认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或许是余氏所辨偏重于形式上的分析考证,未能更深入地将此书与曾巩所作其它文章进行对比,提出内证,故至今无人采纳其说。笔者在研究曾巩的学术活动和思想时,曾将曾巩文集与此书对照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再结合曾巩的学术活动和思想精神加以剖析,愈信《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无疑。今特撰此文,试图在余氏考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内在证据,解决此案。
一、否定者证据之不足
否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的始作俑者晁公武,在所著《郡斋读书志》卷六中这样说:“《隆平集》二十卷,皇朝曾巩撰。记五朝君臣事迹。其间记事多误,如以《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类,或疑非巩书。”按:晁氏所揭发的错误见《隆平集》卷一《馆阁》。《太平御览》与《太平总类》实际上是同一部书,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命李昉等编修,初名《太平总类》,后因太宗亲自按日阅览过全书,故改名《太平御览》。《隆平集》将它误为两书,确是一个不小的错误。但以书中有误即疑其作者非曾巩,显然又是轻率的。曾巩虽为一代学术巨匠,偶有差错,实亦在所难免。这在他平日所作文章中自然也是存在的。要否定此书非曾巩撰,必须另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而况,晁氏之言本身也尚有可疑之处。其一,据余嘉锡揭示,晁氏此语只在衢本《郡斋读书志》中有,而在另一版本袁本《郡斋读书志》中,却没有“其间记事多误”以下二十五字,殊属奇怪。其二,晁氏的说法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此,他大胆发出“疑非巩书”的疑问,而在同书卷十九《寇忠愍诗》条下,则又引《隆平集》卷四《寇准传》之文,并明言为曾巩之语。可见,晁氏并没有断定《隆平集》是伪书。
晁氏之疑,本已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却妄加发挥,断言《隆平集》非曾巩所著。该书卷五十《隆平集》条下云:“《隆平集》二十卷,旧本题宋曾巩撰,……晁公武《读书志》摘其记《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误,疑其非巩所作。今考巩本传,不载此集。曾肇作巩行状及韩维撰巩神道碑;罗述所著书甚备,亦无此集。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巩充史馆修撰,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进。其出于依托,殆无疑义。”这里,除沿袭晁公武的理由外,又提出两点:一是《宋史·曾巩传》、巩弟曾肇所作《曾巩行状》以及韩维所作《曾巩神道碑》未著录此书;二是据《玉海》所载,巩在史馆修国史的时间只有五个月,不可能这么快著成此书。
关于曾巩在史馆修国史的时间,《玉海》卷四十六《元丰修五朝史》条原文是这样的:“(元丰)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己酉诏: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史》通修成书(原注:是年十一月,废编修院入史馆),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五年四月,遂罢修《五朝史》。”《四库全书总目》在引用这段记载时,竟将“五年四月”四字漏掉,错误地得出“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的结论来。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曾巩修《五朝国史》的前因后果。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属江西)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次年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五年冬,奉诏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负责搜集、整理和校订史馆典籍。历时九年,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结束,取得很大成绩(注:详参叶建华:《曾巩的史学活动试探》,载《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一期;《曾巩史学思想简论》,载《中州学刊》1990年第二期。)。次年二月,神宗又成立英宗实录院,命曾巩为检讨官,负责纂修《英宗实录》。巩受命后,即上书皇帝,提出十六条详细的编写意见(注:《曾巩集》卷三十二《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但由于巩在朝廷“不知苟且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挺立无所附,远迹权贵”,受到当权者的妒嫉,“为英宗实录检讨官,不愈月,罢”(注:《曾巩集》卷三十二《齐州谢到任表》;曾肇:《曾巩行状》。)。被迫请求出京“外藩”,任越州通判。《英宗实录》后由孙觉负责编写,七月书成。
元丰四年(1081),六十三岁高龄的曾巩在做了十二年地方官后,再次回京任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典修《五朝国史》。宋代素重国史之编修,真宗时修有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仁宗时又修真宗朝国史,并与前两朝合为《三朝国史》。神宗熙宁十年(1077),命王珪监修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元丰四年七月,神宗又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之”,以成一部从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至英宗的《五朝国史》,并“专以付曾巩使合之”(注: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四《九朝国史》。)。据1970年在南丰县源头村崇觉寺出土的林希所作《曾巩墓志》记载:“(元丰)四年,(神宗)手诏中书门下曰:‘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修五朝史事。’遂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谢曰:‘此大事,非臣所敢当。’上曰:‘此用卿之渐尔。’因谕公,使自择其属。公荐邢恕以为史馆检讨。”把编修五朝大典的重任独付曾巩一人,并让其自己组织写作班子,这在古代官修国史中是罕见的。
曾巩不负众望,一担任典修国史的重任,便首先制定了详细的编写条例,以及史料搜集的范围和方法等(注:见《曾巩集》卷三十一《史馆申请三道札子》。)。这些意见得到神宗的首肯,于是编修《五朝国史》的工作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然而,次年四月,神宗却又下诏罢修《五朝国史》。为什么曾巩如此认真负责,而神宗却要废除史局呢?其中原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墓志》、《神道碑》、《行状》,以及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均说因曾巩母亲卒而史局罢。然史局罢在四月,而巩母卒在九月。《宋史曾巩传》不云被罢之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则云“当考求所以罢修之故”。王应麟《玉海》等又言曾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而罢。据余嘉锡考证,曾巩典修《五朝国史》,实际上是被当时的御史中丞徐禧以及新进之人蔡卞等所攻罢。《四库全书总目》独信《玉海》所载,是片面的。
总之,曾巩典修《五朝国史》,首尾时间在九个月以上,绝非仅五月。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仅五月,否定也不能马上成立。因为,如前所述,曾巩负责过《英宗实录》的编修,又曾参加过《宋会要》的编辑(注:《曾巩集》卷三十四《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对宋兴以来的政事国典早就比较熟悉,当时又有三朝国史材料可资参考(注:据《曾巩集》卷三十五《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称:“两朝国史,臣所未见。”),任职之后工作又非常认真负责,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曾巩修史。
那么,为什么《神道碑》、《行状》等没有著录此书呢?这是因为,《隆平集》仅仅是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未及定稿而史局已废,不久又遭母丧,曾巩离京奔丧,次年四月巩即病卒。所以,曾巩生前未加以正式定稿。其家属以其为史馆所修之官书,且是未成之稿,故藏之于家,存其手稿而已,并没有将它当作正式著作整理刊行,也没有把它视为曾巩的私人作品。徽宗时,淄王赵世雄(注:据余嘉锡考证,世雄与曾巩同时,约比巩小十二岁。)典宗正,于曾氏之家得到此书,遂录副本以授其子孙。绍兴初,《隆平集》始刊布于世。赵世雄的曾孙赵伯卫于绍兴十二年(1142)作序一篇,载于南宋董氏万卷堂本《隆平集》之首,详载内中原委。其中有云:“南丰曾巩子固为左史日,尝撰《隆平集》以进,……当时号为审订,颁付史馆,副存于家。虽非正史,亦草创注记之流也。”而且,即使弟子未提及,也不能马上否定此书为曾巩所作。曾巩著述甚丰,各种著录互有出入。如曾为朱熹《宋名臣言行录》、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多次引用的曾巩《杂识》一书,便不见于《神道碑》、《行状》等的记载。
由上可见,仅以书中偶有差错及有关著作未著录、巩在史馆时间短等理由,怀疑甚至否定《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是明显证据不足的。
二、《隆平集》为曾巩所撰无疑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反而可以提出许多可靠的证据,证明《隆平集》确系曾巩所撰。
(一)《隆平集》与《元丰类稿》比较
虽然《隆平集》是史书,而《元丰类稿》是曾巩的文集,两者性质不同,但取两者有关文字相比较,不仅可看出其中思想观点和文笔风格的许多相通之处,甚至有措辞如出一辙者。这是《隆平集》为曾巩所撰的强有力证据。
《隆平集》共二十卷,前三卷记太祖至英宗五朝事实,分圣绪、符应、都城、官名等二十六门,每门又分若干条,体例颇似会要。卷四以下为列传,分宰臣、参知政事、儒学行义、妖寇等十一类,立传三百三十人(包括附传)。在将此书与《元丰类稿》比较时,我们首先发现此书前三卷内容与《元丰类稿》中的《本朝政要策》极相似。《本朝政要策》系曾巩类聚历朝政要中之制策奏议为一编,其所立篇目与《隆平集》前三卷大同小异,甚至有文字内容也完全一致者。现将两书有关篇目列表对照如下:
《隆平集》 符 官 馆 学 取 祠 刑 户 河 宰 妖 夷 燕
应 名 阁 舍 士 祭 罚 口 渠 执 寇 狄 乐
官 郡
司 县
《本朝政要策》 感 三 文 学 贡 蜡 刑 户 水 宦 贼
生 司 馆 校 举 祭 法 口 利 者 盗
帝 考 祠 版
课 太 图
一
《本朝政要策》 契 雅
丹 乐
南
蛮
虽然在这些基本相同的篇目里,具体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本朝政要策》综论历代,而《隆平集》侧重宋代。但其中亦不乏完全相同者。如《本朝政要策》的“户口版图”目对宋太祖年间户口版图的记载,与《隆平集》“户口”门的记载,不仅方式一样(分太祖元年和末年两次),即数字也一字不差。又如《本朝政要策》“贡举”目与《隆平集》“取士”门,两者只有详略之区别,而主要叙述文字语句完全相同,现引录如下:
……开宝六年初,殿试进士,自是为定制。……
《隆平集·取士》
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
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复故。
开成间,连岁取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
旬日之间,取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
赐绿袍木简,未命官,而释褐新制也。……
……(开宝)六年,又诏宋准等覆试于讲武
殿,殿试自此始也。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
科,至唐以来尤盛,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
《本朝政要策·贡举》
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亦复故。开成间,
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至太宗即位
,……旬浃之间,拔士几五百,……又未命
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
我们再取《隆平集》中的人物传记与《元丰类稿》中有关的碑铭墓志行状等文章对比,两者的文笔风格和思想精神也是相通的,有的连语句表达和措辞都基本一致。如《隆平集》卷四十《孙甫传》与《元丰类稿》卷四十七《孙公行状》,两者只有简繁之别,而文章风格和观点基本一致,措辞亦大同小异,前者可视作后者之浓缩,明显出于一人之手。
又如《隆平集》卷十五《王回传》与《元丰类稿》卷十二《王深父文集序》、卷十五《再与欧阳舍人书》、卷十六《与王深父书》、《与王介甫三书》等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据上述文集中的文章所载,王回(字深父)病重时,王安石曾作志铭寄给曾巩看,曾巩阅后非常赞同王安石对王回的评价,认为是“发明其志,可谓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今《隆平集·王回传》虽只一百二十九字,却引录王安石的评价之语达五十余字,并以王安石语作结束:“……安石谓:‘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轲所为而不为,小廉曲谨,以求名于世,其学问所得,自汉以来列儒林者罕及也。’”这个情况,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此外,如《元丰类稿》卷四十二《戚舜墓志铭》谈到戚舜的祖先戚同文、戚纶、戚维时,与《隆平集》卷十三《戚纶传父同文附》语句措辞也基本相同。《隆平集》中的《侬智高传》、《狄青传》则可与《杂识二》的内容互通。其它许多传记的叙述,也都与曾巩平时写文章的风格相符合,如《李允则传》叙述“简严最有精彩”,“非得此妙笔,不足以传之”。《曹克明传》“错综轶宕,极有生色”。《杨邺传》“叙杨邺设谋力战处,如读《项羽记》、《刺客传》,令人可悲可涕,何等笔力”!《耶律隆绪传》“叙事中间以议论,行之何等活泼”、“措语简要,而有分寸”,“妙有姿致”。《夏国赵保吉传》“错落入妙”,“雄健错落”,“逐段引人入胜,与《五代史》可称合璧”(注:引文见清彭期所作《隆平集》批注。)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隆平集》与《元丰类稿》的作者只能是同一个人,即曾巩。唯一有所例外的是《隆平集》卷十五《徐复传》与《元丰类稿》卷四十八《徐复传》,两者不仅简详不一,记载内容差别也很大,未知何故。
(二)宋人引录《隆平集》者均称其为曾巩之书
《隆平集》于南宋绍兴年间刊行后,虽流布不广,但已为人们所重视和引用。南宋几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曾、李焘、李心传、杜大珪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引录过《隆平集》的内容,而均称其为曾巩所作,未曾稍疑其伪。这是《隆平集》为曾巩所作的有力旁证。
南宋绍兴年间吴曾所著《能改斋漫录》一书,素以征引繁富、考据精确见称。其书卷五《牛僧孺聪明台》条,曾记录有这么一段话:“《国史刘沆列传》,曾南丰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杨行密为江西牙将。有彭玕者,据州称太守,胁景洪附湖南,伪许之。复以州归行密,遂不仕。尝谓人曰:我不从彭玕,当活万余人,后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后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读书堂故基,即其上筑台曰聪明台。沆母梦牛相公来而生沆。’以上皆列传所载。”今查《隆平集》卷五《刘沆传》,果有此段记载。足证《隆平集》为曾巩所撰国史之底稿无疑。
《能改斋漫录》卷十二《晏元献节俭》条又云:“曾南丰与公同乡里,元丰间,神宗命以史事。其传公曰:‘虽少富贵,奉养若寒士。’考公手帖,则曾传可谓得实。”今《隆平集》卷五《晏殊传》里,果然有“虽少富贵,奉养若寒士”两语。
与吴曾《能改斋漫录》可以互证的是,南宋绍熙间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其中有种放、范质、刘沆、包拯等四十三篇传记之文,皆题为“曾太史巩撰”或“曾舍人巩撰”。这些传记今均见于《隆平集》中,内容完全相同。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卷四十八、九十五、九十六曾三次引用《隆平集》的内容,并在卷九十五所引文前明著“曾氏《隆平集》”五字,可见,李焘亦未曾怀疑《隆平集》为曾巩所撰。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王文正遗事》谈到张师德(字尚贤)两诣王旦门不得见,旦谓师德奔竞,李心传辨之曰:“曾子固《隆平集》云:尚贤‘守道不回,执政不悦,在两掖者九年’。则似非奔竞者。”此语今见《隆平集》卷十四《张师德传》中,可见,李心传也直指《隆平集》为曾巩之书。
此外,南宋初李元纲在《厚德录》中也曾引《隆平集》材料达三十条,而皆直称为“曾子固《隆平集》”(注:见《说郛》卷九十四。)。
(三)《隆平集》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
我们说《隆平集》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不仅有前引赵伯卫序和上引吴曾《能改斋漫录》(称其为“国史”)、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称其为“太史”)等为旁证,而且还可以从《隆平集》的内容与曾巩当日修国史时所拟订的内容进行比较,作为内证。
首先,从记事时间看,两者相吻合,皆记宋太祖至英宗五朝史事,如是伪作,很难如此巧合。
其次,从记载的范围看,根据曾巩所上《史馆申请三道札子》称,《五朝国史》的记载范围是宋兴以来五位皇帝的功德以及群臣拜罢、刑法、食货,特别是五朝名臣良士的言行功实等。今《隆平集》所记载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从编写体例和原则看,当时曾巩规定《五朝国史》略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有本纪,有记载群臣拜罢的《百官表》,有记载刑法、食货、天文、灾祥的各志,有人物传。其原则是只记“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其细故常行,不备书”。“名位虽崇而事迹无可纪者,不必传。或善恶有可见者,则附见之”。今《隆平集》虽无纪、表、志(恐未成),但前三卷内容反映的正是这些情况,其中“圣绪”冠以首篇,似本纪之内容,“宰执”、“官名”、“官司”诸篇,则与百官表无异,其余各篇则明显属志的内容。卷四以下的人物传记,则集中体现了“善恶劝戒”的记事原则。每篇传记长短不拘,长的几千字,短的百余字,都是善恶分明,并时有附传,而遇到重要的章疏奏折,亦予以记载,深得《史》、《汉》列传之堂奥。前引《李允则传》、《曹克明传》等皆是如此。而《狄青传》,也是“叙述错综简括,颇得《史》、《汉》丰骨”。《范仲淹传》则长达二千四百余字,详载仲淹的许多重要章奏,史料价值极高。另如卷十五《赵师旦》、《曹觐》、《孔宗旦》三传,采用了《史记》合传之体,将这三位同时慷慨就义于侬智高叛乱的勇士合在一起叙述,“真令人读之无不感愤涕泪,得《史记》合传之体”(注:引文见清彭期所作《隆平集》批注。)。
康熙四十年,彭期序此书云:“……公因编著五朝之事为《隆平集》二十卷以进,而《宋史》及《通鉴》皆藉为根柢。所纪撰者,典而核,博而文,其词约者其义明,其文繁者其旨永。上下百余年之事,英君贤相、典章制度、赏罚兴革、人物风俗、忠良邪匿、内外舆图、营缮赋役、攻伐营屯诸事,莫不一目了然。善恶美刺,无所隐护。即当日最忌讳者,靡不微词见意。前以继《五代史》而并行,后可以合《宋史》而互见。……晁氏讥其记事多误,又曰或疑非先生之书,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也。且斯集之体制才思,俨然左国马班之遗,有识自能辨之尔。曰作者谁肯自掩其长而让能于公哉!……今付梓以附公文集之后,以见公之前集得于经学者既粹,而此集得于史学者尤深。出经入史,兼擅其长,又何才学识之弗备哉!”康熙四十七年,曾鸿麟跋此书则云:“文定公文章名天下,既醇乎经学,而《隆平集》则其史才也。……至今读之,其短篇则如《左氏传》,其长调则如《贾太传》,其典核又如《秦风》、《小戎》,所状士马、板屋、土风,宛然在人眉宇间。真旷代逸才也哉!”余嘉锡亦说:“究之,有宋一代正史别史,笔力之高,莫过于此。即其剪裁洗伐之功,已非王称、脱脱辈所能讥及。此岂后人所能伪作哉!”
以上评价虽不免有所夸张,但至少可以反映出《隆平集》作者的文笔才识与曾巩是一致和相匹配的。
我们认为,《隆平集》既为曾巩所修《五朝国史》之底稿而非定稿,其琐碎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总得来说,称得上是一部谨严之作,能体现出曾巩的“良史之才”(注:章学诚对曾巩史学的评语,见《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志隅自叙》。)。特别是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不仅在宋代已为吴曾、李焘、李心传、杜大珪等名家所称引,而且在元修《宋史》时,亦被列为重要参考书(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修辽宋金史搜访遗书状》。)。至于今天人们在研究宋史时,使用的频率就更高了。对于这么一部重要著作,晁公武仅以书中有误而轻率地疑其伪作,《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又独信晁氏片面之辞,妄下结论,实不应该。近代有的学者也不加甄别,在未提出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跟着断言“巩之未著《隆平集》无疑”(注:王焕镳:《曾南丰先生年谱》。),尤为无稽。今天,我们在研究曾巩学术时,只字不提《隆平集》,或在著录《隆平集》时,不敢径直写“曾巩撰”,是大可不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