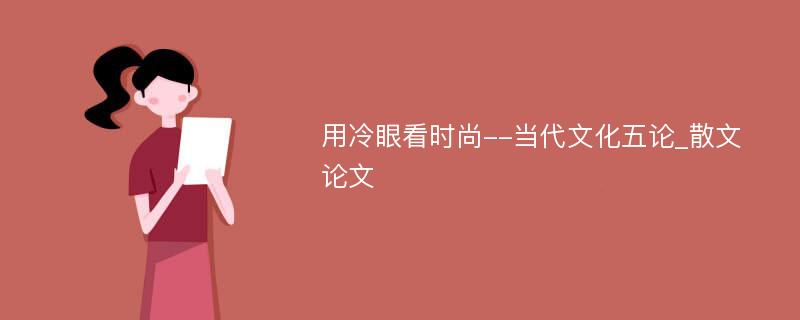
冷眼看时尚——当代文化评论五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眼看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速配的时代
这是一个速配的时代。
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应该说是在最初观看台湾的大型婚恋谈话节目《非常男女》的时候。一对对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竟然在电视上凭借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就速配成对,这实在令人吃惊!爱情何其神圣,可是在当代青年的眼中竟然也可以“作秀”,可以速配。看来,尽管人类的寿命在变长,但是在当代社会,似乎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耐烦,已经越来越不习惯于等待——哪怕是生命中的十分必要的等待。连美洲的一种鸟,求爱时还知道要先以一系列的舞步、小步快跑来取悦于对方,但是现在的人连这个也懒得做了,干脆就来他个速配。当然,我们的生活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没有了“鸿雁传书”,没有了“红袖添香”,也没有了“碧海青天”。试想,有了电灯,谁还会去“剪烛”?有了手机、长途电话、飞机、高速公路,谁还会去“折柳”?因此,在言情小说中,过去是“日久生情”,在第1页中已经认识,在第100页中却还没有拉拉手。现在却是在第1页中刚刚认识,在第2页中就已经上床。更不要说现在的懒于画眉毛的有快速眉毛贴,懒于钓鱼的有快速钓鱼竿,懒于疗养疾病的有速效胶囊,懒于下厨房的有速食食品,懒于进学校读书的有人才速成培训,懒于爬山的有快速缆车,个子太矮的有快速电子增高器,耐不住等待的也有特快专递和高速列车……平心而论,这一切都有其不可或缺之处。简单说来,就是可以省出时间干更有意义的事情,干自己想干的事。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样一来,人类的既美好而又丰富的文化感觉也就被彻底地摧毁了。速配的东西肯定缺乏积累,而文化感觉却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否则就会流于肤浅。山长水阔,才会有离愁别恨,“日日思君不见君”,才会使简单的“重逢”、“邂逅”大放异彩。遥想当年,我们的古人生活得何等优雅、何等从容:西窗剪烛、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折柳相赠、灞桥伤别……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就生活得实在是太不细致、太粗糙、太寡趣了。无论干什么都是心急火燎的,不吃就不吃,要吃就要一口吃出个胖子来。这样一来,一切都无非是倒行公事,还有什么意思可言?更不要说,还有一些人竟然会用摇头水、罂粟粉、可卡因注射剂去速成快乐呢!
因此,我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在这个速配的时代,我们的生活究竟是更快乐了,还是更不幸了呢?
二、走出男性的目光
前不久,看到一条消息,说是国际排联作出一项新规定:要求女运动员在比赛时不得再穿长袖上装,女球员的短裤必须要紧贴腰部,裤脚必须要斜向大腿两侧,并且最好是穿“一件头”的运动衣。消息一出,舆论大哗。人们公开批评说这是在以女性的性感作为“卖点”,但国际排联却毫不退让,并对巴西等五支“违规”的球队分别予以3000美元的罚款。
比赛就是比赛,然而现在却要同时把比赛变成女性自身的性感魅力的展示,这实在是闻所未闻。联想到当代文化对于女性的在“瘦身”、“挺胸”、“化妆”、“美容”方面的强烈要求,我不能不说,这个消息给女性带来的实在不仅仅是一种“规定”,而且是一种真实的处境。确实,当代社会女性之所以受到种种特殊的关注,与当代社会的审美被人为地分裂为看与被看、主动的男性与被动的女性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当代社会女性形象无处不在,并且占据了视觉的中心位置,以至有西方人半开玩笑地说:当代社会的人们,艳福超过口福,尽管为怕发胖而不敢多吃,但却可以多看。然而,也正是在这“被看”与“被动”之中,女性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剥夺了自身的根基。像“原本”的消失一样,真实的女性也消失了,这无疑是一种对于女性身份的令人痛心的“篡改”。针对这一状况,萨特的情人波伏娃说:“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这实在是精辟之见。也因此,在当代社会,女性虽然走出了封闭的世界(例如家庭、村庄、地球),却仍旧走不出男性的目光——她完全一无所有,只是某种被男性目光所凝视的“奇观”,而且,只有成为被凝视(甚至窥视)的对象,她才有价值。而且,越是被成功地观看,就越是有价值。换言之,正是男性的目光的认可,使得女性们有了所谓“成功”的感觉。女性既是审美之中男性“惊鸿一瞥”的欲望对象,又是审美之外男性“目不转睛”的欲望对象。百看不厌,秀色可餐(当然,对女性的剥夺,同时也就是男性对自身的剥夺,这暂且不论)。这,既是女性自身进入当代的确证,也是女性尊严在当代受到嘲讽的确证。这样,所谓女性的自由、独立、自主也就完全要依赖于男性的存在。女性本身并非一个主动的主体,而是一个主动的客体,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其主要的功能也只是作为男性欲望的承担者。于是,真实的女性身份就这样被篡改了。那些所谓的大众(男性目光)情人,例如以塑造“怪僻女性”著称的嘉宝、以塑造“睿智女性”著称的赫本、以塑造“政治女性”著称的褒曼,都无非是因为成功地投男性所好而倍受青睐。那么,那些“事业的成功者”、“女强人”又怎么样呢?她们尽管确实在男性社会中挤占到了一个席位,但却仍旧算不上完全的成功。因为她们的悲剧,其实并不开始于她们的勇于与男性的竞争,而是早在她们无法面对女人之为女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一个作为女人的女人,一个在生命意义上可以称为女人的女人,不应像男性那样以女性自身作为媒介,而应从自己的性别出发,去开拓女性自身的人性内涵。假如不是如此,就难免会陷入一种男性误区(以为男性的生存方式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女人的生命体验就会变成关于话语权利以及关于在男权中心“虎口夺食”争夺生存空间的生命体验。看来,在当代社会之中确实是女性无处不在,但是在当代社会之中又确实是女性意识几乎处处不在。这样,我们不得不这样地予以提示:目前,当代女性当然还不可能走出性别的困境,但是,却有可能、也必须在困境之中保持女性意识的觉醒。
结论是,当代的女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首先就要走出男性的目光。或者,换句话说,当代的女性离女性意识有多远,离自身的解放就有多远!
三、南京的伤感
最近,南京被某媒体评为“最伤感的城市”。南京究竟是不是一座“最伤感的城市”?对此,我暂时不想发表意见。但是,我必须承认,对于南京的伤感,在我,却实在是由来已久的。
我不是南京人,但是,客居南京近10年,却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我喜爱南京所富有的浓厚的文化底蕴:南朝的陵墓石刻、隋代的舍利古塔、明朝的鼓楼钟亭、明清的帝宅园林,还有碧波荡漾的秦淮河,一圈把城市包围起来的虽然残破却基本上完整的城垣(这是历史赋予南京的最大礼物),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开国君主的陵寝的明孝陵,作为结束封建帝制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寝的中山陵……可惜,也就是在这10年里,我也逐渐萌生了一种对于南京的伤感。为了建成现代化的城市,南京这几年一直在不断地追赶时尚,不断地修补、改建、包装。其中,当然不乏大手笔与成功之作。例如台城的重构,例如汉中门市民广场的建设,例如静海寺的修复,例如警世钟的捐铸。然而,令人抱憾之处也所在皆是。例如破墙开店,例如24桥的修建,例如鼓楼隧道(有人甚至开玩笑说:下雨时洗车的最好去处就是鼓楼隧道)与高架桥,例如砍树扩路,例如城市道路公路化(城市交通有什么必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呢)。例如树上缠灯(白天一看,真是活丑)……其中,新街口更是时常令人掩面而去并且最不忍再睹之处。孙中山,这本该让人仰望的伟大人物,却站在被大款富婆们从高楼大厦的茶色玻璃后俯视、也被平头百姓从天桥上俯视的街心这样一个局促一隅。而你无论从新街口的哪个方向走,想在马路上骑车或坐车体会一种接近伟人的感觉,目光也只会弹射在四座贴满广告花里胡哨的天桥上。在这当中,不难看出南京在城市建设中的一种欲行又止、遮遮掩掩、缺少通盘打算的时尚化心态。大家都在搞城市建设,我也搞,大家都起楼、架桥、挖洞、拓路,我也照此办理,你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只要旧房可以拆,就造一片新楼,既然树可以砍,就拓宽一条新马路,哪儿是城市门户,就架一座高架桥,何处是市中心,就立一座雕塑。总之,是无视城市的优势与劣势,以最短的时间,最简捷的手段,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追求一步到位,立即见效。于是,我们就只能面对着这样一座躁动的畸形的南京城。它确实不再是千年一律的城市,但却沦落为千篇一律的城市。
我有时甚至会想:南京现在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式的现代怪物、一个被时尚制造出来的城市畸象?在追赶城市时尚的道路上,面目日益模糊,特征日益丧失。显然,这一切非但不是为南京赋予意义,反而是剥夺了南京的意义。时尚化的南京,越来越缺少亲切感,越来越缺少舒缓的情趣与美感,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紧张的生存状态,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杂乱、无头绪的状态。市民们逐渐失去了对南京的温馨感觉,逐渐失去了对南京的起码的热切关注,压抑、烦躁、冷漠开始充斥着这座城市。遥想当年我读《儒林外史》,每每为南京和南京人的文化气魄而称奇。其中记载,两位挑着粪桶卖粪的南京挑夫曾互相商量说:今天的货卖完后喝口水,然后就上雨花台看落照去。一位文人闻言后叹曰: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试问,有谁能不为这样的南京、这样的南京人而自豪!
可是,雨花台上的“落照”而今安在!南京人身上的“六朝烟水气”而今安在?
四、纸上的卡拉OK
对于目前大行其道的“小女人散文”,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纸上的卡拉OK,或者用笔唱的流行歌曲。
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小女人散文”的价值类似话梅、瓜子,不能充饥,也无营养,但是却可以消磨时间。它的出现,迎合了当代美学对传统美学的意义、深度的消解。传统的散文往往是写一种“大丈夫”的心态,抒发的是国家、民族的豪情,例如杨朔、刘白羽的散文。现在却转向了写一种“小女人”的心态,是以平面的姿态对传统散文中的深度加以消解,去对普通人的生活加以关照与还原。因此,它有其存在的意义。然而,目前无论是在“小女人散文”的撰写者还是评论者那里,都出现了一种对它人为地加以抬高并且避而不谈它的根本缺憾的倾向,这则是“小女人散文”的一种误区。事实上,它的根本缺憾是极为明显的。
首先,从作品本身而言,所谓“小女人散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说过去的文学作品过于强调深度、意义,那么现在“小女人散文”就干脆放弃了深度、价值、意义。因此它披挂的语言外衣再精制、漂亮,也不过是满篇漂亮的废话(它与林语堂的生活散文也不同。在后者,日常生活只是能指,对于现代性的关注却是所指)。它的立足点从过去对意义的消费转向对语言的单纯消费,变成了为语言而语言,更是一种公开的媚俗。而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也正是使散文丧失了应有的美学品格,并且流于平庸、无聊。
其次,从作者的角度讲,所谓“小女人散文”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繁荣之后的特定现象。经济的发展、繁荣造就了一批“金屋藏娇”的“太太”们。这些“太太”们往往是经济上没有负担,也不再需要面对社会上日益严峻的竞争,并且开始退回家庭。然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她们又会产生一种特有的少女心态,我把这称之为“少妇聊发少女狂”。与琼瑶、席慕蓉、三毛一样,她们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需要思考了,就非常地怀旧、非常地多情。于是开始百无聊赖地用一种少女的情态在社会中编造诗意以期丰富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她们代表了内地的某个写作阶层。她们以笔去寻找生活中的趣味,这种寻找具有浓烈的刻意色彩。这类作品从表面上看好像要是回到真实,并与传统美学中的虚伪的东西进行决裂。但是生活在本质上却是气象万千的。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生活的真实性本身就包含着艰苦卓绝的一面,比如困惑、忧患、焦虑。这些难道就不真实了吗?将复杂的人生中痛苦失败的一面化解掉,而单纯地描写所谓平静琐碎的生活感受,其结果,就不能不充斥着琐屑的小女人心绪。据说在上海竟然有大学教授以能背诵《美人肩与美人背》这类散文为荣,我对这位大学教授的美学趣味只能表示怀疑。因为此类散文中涉及的美学知识相当肤浅简单。如果如此这般就是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写出了美,我认为实在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欺与欺人。实际上,只要随便翻阅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处处浸透着的一种小女人的非常庸俗的自鸣得意。有评论家赞颂在这些散文里“树很直,石头很光洁”,似乎惟独她们才写出了真正的树和真正的石头。但是树、石头多有不同,比如有些石头就相当媚俗,只供掌中把玩,但石头中也不乏在狂风巨浪中傲然挺立的礁石;公园里的树当然很悦目,但泰山顶上的十八棵青松,不是更为令人敬仰吗?
最后,就读者来说,“小女人散文”是一种小市民趣味的宣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对读者中不健康心理的迎合。有评论家说这些“小女人散文”是对市民趣味的迎合,这并不准确。市民趣味代表的是一个整体,所谓“小女人散文”只是对其中的小市民的趣味的迎合。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女人散文”在广州发源地并不受欢迎,但是在上海却大受欢迎。上海所存在的小市民趣味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体现在缺乏坦荡的心胸、善打小算盘、自私自利、对生活中无聊的东西津津乐道,对不劳而获充满幻想和迷恋。这无疑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趣味。与此相应,“小女人散文”主要表现的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趣味。总之,所谓“小女人散文”混淆了平常与平庸的界限。散文固然可以从崇高转向平常,但却绝不能从崇高转向平庸。在这里,平庸与平常之间不能等同起来。平庸是对日常生活的不全面的理解,而真正的生活则是平常的。这是一种有艰难有困苦有牺牲有眼泪的平常,也是一种有温情有闲适有家长有里短的平常,就像生活中有“东西”,也有“南北”,我们固然可以爱东西,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南北,而且同时也要爱南北,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创作心态,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审美心态。
五、明星出书
明星出书,是当代的一大时髦。从表面上看,它是对于明星的神秘性的“解魅”,也是明星为了展示自己的文化身份、区别于一无所有的暴发的特定方式;实际上,却是文化与经济结盟的隐秘方式(不论从明星还是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都如此),对于出书这一文化的神秘性的“解魅”。它对于文化的走向大众化,显然有其积极意义。然而究其实质,明星出书却毕竟是明星私人空间的一次社会展示、商品展示,可以称之为“明星私生活的脱衣舞”。因此,一旦任其泛滥越位,也会走向误区。
例如有些明星以“坦率”、“真实”自诩,然而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却是其卑琐不堪的灵魂阴暗面。须知,真理固然是赤裸裸的,然而赤裸裸的并不都是真理。我们曾经在卢梭的《忏悔录》中看到了真正的“坦率”、“真实”。面对作者所揭露的自身的卑琐不堪的灵魂阴暗面,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灵魂远比这一切要高大许多。然而,在个别明星的书中呢?在其对自身的卑琐不堪的灵魂阴暗面的津津乐道中,我们看到的正是比这一切要更为卑琐不堪的作者的灵魂。再如个别明星竟然一方面在书中借机自吹自擂,只要一谈到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就一味自我赞美,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更缺乏起码的谦虚谨慎。然而实际其艺术路子很窄,缺点也很明显,并且事实上已经为相当多的批评家所公认。另外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其竟然在书中大谈自己离了几次婚,挣了多少钱,出了多大名(作为一个艺术明星,本来应该更多地展示自己的艺术实践;作为读者,希望更多地了解的本来也只是她的艺术实践),竟然津津乐道自己的“时时刻刻追名逐利”的座右铭,把自己的淘金梦、淘名梦,像肥皂泡一样地吹向世界,公然把人生的价值混同于挣大钱,出大名,混同于潇洒走一回的世俗喧嚣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原始欲望,(有人甚至提出:“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令人万分震惊。因为从来就是“你是流氓谁怕你”,现在怎么竟然会成为“我是流氓我怕谁”了呢?)一会儿为能追名逐利而兴奋;一会儿为不能追名逐利而沮丧,一会儿是明星,一会儿是富婆,以致连自己都被各种角色弄得面目全非、方寸大乱。这实在令人震惊!追求名利固然是人类的天性,正视这一天性,对于消解传统的把文学艺术家看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贵族观念固然也有积极意义,但若转而一味追名逐利,视圣洁的文学艺术为“过把瘾就死”的玩物,则难免误入境界日益卑琐的歧途。艺术家不再是龙种,但难道就应该成为跳蚤?因此,这类书籍不但低估了读者的审美趣味,以读者为“窥私狂”,而且宣扬了一种颠倒的人生观、价值观。事实上,古今中外的艺术史早就告诉我们,一味追名逐利是美和艺术的天敌,也是艺术家的地狱之门。何况,明星不等于艺术家,出名不等于出师,能够永垂艺术史册的标准永远不会根据挣钱多少来决定。而成为一个艺术家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都应该是一种执著的敬业精神。在此意义上,就明星出书而言,对于相当一部分明星来说,学会沉默,应该说比学会写作事实上显得更为重要。
而从当代文化的角度来看,明星出书的泛滥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优先权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我”。于是,个人故事、个人叙事、个人写作、商业写作应运而生。换言之,生活越来越缺乏奇迹,明星自传就成为奇迹的补充(所谓“奇观”)。在其中,文化的进入生活实际上更是“退”入生活,“逃”入生活。写作丧失了叙事性,大多是片断的,成为没有深度的平面游戏,成为一种时尚。最终,文化就不再是文化,它丧失了神圣性。这样,对于历史的回忆就成为某种“奇观”的展示,甚至,这展示本身也变成了“奇观”,私人行为通过媒介公开上演,获得了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文化回到生活,就只剩下展示价值了)。而充其量,这些作品也无非是以过去的成就向今天献媚(且不说其中的文字不通、错字连篇),以表演代替抒情,以广告充当作品。
因此,对于当代文化来说,对于明星出书热中滋生并逐渐蔓延开来的不惜以“跳私生活的脱衣舞”来取悦社会以及拜金主义、拜名主义的趋向绝不能稍加姑息,更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越位肆虐,否则,必将导致文化的自杀、艺术的自杀、美的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