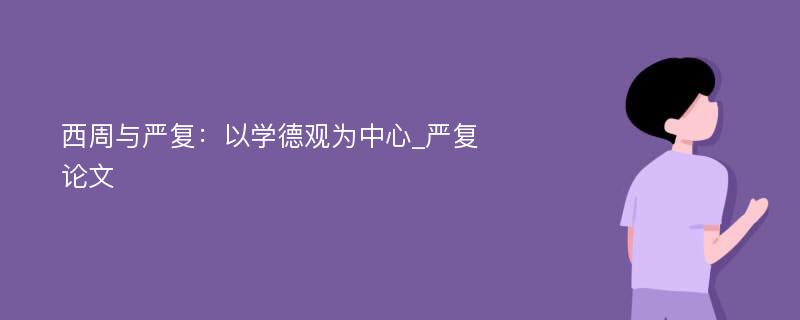
西周与严复:以学问观、道德观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观论文,西周论文,学问论文,严复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周(1829-1897),生于日本石见国津和野藩(今属岛根县)的医生家庭,自幼在藩校学习汉学,后成为藩校教官。1855年,有感于时局紧迫而脱离本藩,转而专注西学,1862年起赴荷兰留学三年。回国后,出仕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并开设私塾。明治维新后,西周先后任官于兵部省、文部省、宫内省等机构,参与起草宪法、《军人敕谕》。以近代中国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笔者,对于西周的第一印象,是其翻译确立了近代以降日本与中国思想界共同使用(并沿用至今)的多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如“哲学”等)。笔者曾笼统地认为,西周纵不能与福泽谕吉相仿佛,但作为奠定幕末至明治时期日本新学术基础的重要思想家,应当已有定评。 然而,数年前接触到的论文集《西周与日本近代》①中,却有一节称“西周(1829-1897)是被遗忘的思想家”②,这令笔者稍感意外。该书的末尾附有“西周相关参考文献一览”,从这些研究成果的数量看来,即便是当时,西周是否真称得上是“被遗忘的思想家”也应当打上一个问号(近年间发表的与西周相关的著述更是繁多③,时至今日,称西周是“被遗忘的思想家”已无可能)。 姑且不论此“事实认定”是否恰当,称西周为“被遗忘的思想家”也应当是存在理由的,如,有人推测这与其“参与起草军人敕谕带来的军国主义形象”和“对儒教缺乏批判态度带来的封建主义形象”有关④。换言之,即认为西周作为介绍西方近代知识的先驱,其言行却给人以一种“反动”的印象,因此其思想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充分冷静的评价⑤。 笔者认为,西周的这种状况,与严复(1854-1921)曾经的遭遇极其相似。严复因其《天演论》⑥而广为人知,该书于1898年正式出版,在近代中国引发了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大流行,同时,《天演论》也是中国第一本正式介绍基督教以外西方思想的书籍。严复此后还发表了多部译著,后被集为《严译名著丛刊》⑦。在清末时期,严被视为译介西方思想的第一人。 但是,与身处1910年代,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1897-1942)等人不同,严复对于儒教并未采取强烈的否定态度。非但如此,严复还声称,“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⑧,认为恰恰通过西方近代诸般学说,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圣人的正确性⑨。甚至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严复仍主张在教育中纳入儒家经典⑩。此外,在政治活动方面,由于认为共和政体无法给中国带来安定,严复于1915年参加了旨在推进复辟帝制的团体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11)。因为上述原因,过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尽管承认严复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贡献,但始终将其视为带有旧时代残余的“不彻底”的人物(但近年来已经看不到这种片面的论断了)。 总而言之,严复在着力介绍近代西方诸般学说的同时,强调儒教积极的一面,对简单的“民主化”则持否定态度,笔者感觉这一立场与西周相当类似。换言之,在接触“西方”而引发的近代东亚知识体系的转型过程中,他们二人尽管全方位接受了西方近代的各种学说,但又并行不悖地不断将其与自幼即融入骨髓的儒家文化等东亚教养相对照。 当然,毋庸讳言,从时代的角度而言,西周与严复几乎相隔了一代;同时,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思想背景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受进化论影响的大小,带来了决定性差异)。但是,笔者认为,对比、讨论他们思想中的上述“共通性”,不仅可以研究中日两国在接受“西方”时方式上的差异,也可以为研究对接受主体起着制约作用的、两国儒家教养模式之间的“异”与“同”提供一条线索。然而在现阶段,正面对应如此大的课题对笔者而言力有不足,本文的研究对象将集中在西周与严复的学问观与道德观上。 二、西“学”的划时代性 上文曾提及西周与严复“全面”接受近代西方的诸般学说,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加区别地接受近代西方的一切,显然,他们对于西方学说的价值进行了一定的判断并以此为前提进行了选择。他们发现,近代西方诸般学说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其具有一种“体系性”,而并不单纯是个别知识的集聚。例如,西周在其《知说》(1874)中称: 所谓学术者,莫非四大洲往昔既有之。然以之比诸今日欧洲之所谓学术,岂啻霄壤之分。盖其所谓学术之盛者,非谓极一学一术之精微蕴奥,众学诸术交相结构组织,集大成者之谓也。此地球之上亘古未有之事,乃纪元一千八百年之今日始见者。(12) 认为近代西方学说的优越性在于,其属于超越了个别知识集聚的“结构组织”之知。与此相应,严复在《救亡决论》(1895)中则首先批判了中国之“学”: 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13) 而关于西方诸学,他指出: 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14) 并称西学“首尾赅备,因应釐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15)。 进而,关于迥然不同于个别知识的“学”,得以在西方确立的原因,西周与严复的认识也是相通的,他们都承认,以归纳法为中心的新“方法”起到了决定性的重大作用。在《百学连环》(1870)的“总论”中,西周称: 发现真理之方略众多,诸如文章、器械、设施者皆然,至于研究运用之法,亦不可不知。有所谓新致知学一法,原称A Method of the New Logic,乃英国人John Stuart Mill之发明。其所著之书名曰System of Logic,一大作也。学域自此大为改革,遂渐兴盛。其改革之法,曰induction(归纳之法)。(16) 并进一步指出“西洋古昔亦皆演绎之学,然近来则悉归于归纳之法”(17),认为穆勒所集大成的归纳法才是近代西“学”变革的重要动因。同时,严复也认为: 洎有明中叶,柏庚(培根,译者注)起英,特嘉尔(笛卡尔,译者注)起法,倡为实测内籀(归纳)之学,而奈端(牛顿,译者注)、加理列倭(伽利略,译者注)、哈尔维(哈维,译者注)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著。(18) 可以看出,尽管在对个别历史事实的理解上存在些许问题,但严复对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之上、与客观事实相结合的学说已在西方开拓新境界这一点是认同的。此外,严复还翻译了穆勒的《逻辑体系》(19)。 尽管西周与严复都认为近代西“学”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具有“体系性”,但通过上文所引的部分,也能够看出二人似乎存在差异。西周强调体系由“诸学”构成,而严复则在一个“学”的框架下谈及知识的体系性。严复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严复称为“群学”)推崇备至,认为其所涉领域甚广,应当涵盖心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数学、逻辑学在内,以作为前提。由此可见,认为具有各种对象领域的“诸学”应当相互关联,形成体系,这一观点是二人所共有的(20)。只是,深受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影响的西周与以赫伯特·斯宾塞进化哲学为出发点的严复,对于“诸学体系”的看法存在不少差异。下文将着眼于此,讨论二者的言论。 三、“诸学体系”的问题——西周 众所周知,西周曾有过统合各领域内专门化的知识,形成“统一科学”体系的构想(21)。比如,在《生性发蕴》(1873)中,西周翻译了G.H.Lewes的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1857)中与孔德有关的一节。其中称,在各学科不断分化的时代,有必要通过统括各种学科的“哲学”,确立“统一之观”。文中解释了“统一之观”必须存在的理由,“若无统一之观,则不可施行于今日之人间”(22)。其含义可以理解为,若无“统一之观”,各学科便无法以合适的形式发挥其社会作用。如果用西周自己的话来说,则可见稍晚一些的《尚白札记》(1882)开头部分,“大凡百科之中,存有统一之观事关紧要。若于学术上立一统一之观,人间之事业亦能就绪,社会秩序自然而定”,西周进而将其与社会的“康宁”“富强”,甚至与作为“人道之极功”的“福祉”相关联(23),主张“统一之观”的必要性,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功利性”色彩。 然而,根据孔德的实证哲学,并非仅仅在诸学之间确立一个“统一之观”就可以万事大吉。正如上文所引用的,《生性发蕴》中Lewes著作的翻译部分论及了“统一之观”的必要性,但该书同时指出,以确立“统一之观”为目标的哲学家,若想不依靠其他学科的实证性方法而达到目的,便会犯下谢林或黑格尔一样的错误,因此,“实理之诸学”的必要性应当与“统一之观”等量齐观,“盖统一之观若非依据实理,则无精神,而实理之学若非基于统一之观,亦属空谈”。(24)通过这种基于“实理”的“统一之观”,孔德对学科的体系化进行了实际性的尝试,众所周知,其根据研究对象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标准,提出了以“社会学”为顶点的、具有阶层性的学科体系构想。然而,西周却断定,孔德的尝试是在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结束的。 关于孔德的贡献,西周认为,在孔德之前,“天文”“格物”“化学”领域已有前人的优秀成果存在;而“至于有机性体之二学,即生体学、人间学,其命名尚新,其学犹未立于世上,立此二学乃一大难事,不言自明”,对孔德在学科分类上明确提出“生体学(biology)”和“人间学(sociology)”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西周同时也认为,孔德并没有完全使这两个学科确立起来,他将孔德在“人间学”领域内设立“新教门”的尝试评论为“自误”。此外,关于孔德终未完全确立的“生体学”与“人间学”两个学科,西周认为,涵盖在“人间学”之内的“人间教门之学”“治道经济之学”“纲纪法律之学”等诸学,“纵非全部依据实理之方法,许多学科之中,确乎不拔之发明亦已有不少”,承认在这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真理已被发现的“事实”;而对于“生体学”,则认为其学科基础部分仍不明确,“欲据坤度(即孔德)之说,立此生体学一门,如何着手,未得其法,此乃今日之一大疑惑”。西周认为,“所谓生体学者,兼生理与性理而有之”,换言之,兼含“生理学(physiology)”与“性理学(psychology)”的内容。其中,“生理”的研究状况是,“以格物化学之法,而开生理,业已在物理家、医门等研究之中,其间名师哲匠并不鲜见”;而“性理”,则处于“唯由生理而性理,则桥梁未架,船舸未备,茫然而无津涯”的状态,因此,成为“超理家(形而上学者)培养其高妙无根说之地”。如此一来,西周完善其承袭自孔德思想的“统一科学”过程中的最大课题,就成了“本实质之理法,依生理而开性理”,也即,依据逐渐发展至实证阶段的生理学知识去解明“性理”。西周认为,“生理”与“性理”若能相关联,则“上至天文,下至人事,一联理,一脉络,左右逢源,不患统一之观不立也”(25)。西周结合“生理”与“性理”的尝试最终未能成功,关于其具体过程以及其中提出的“人间性论”,小泉仰已作了详尽的研究(26),其内容在此不再深谈。 正如西周所说,“若一旦确立性理之基础,则所谓人间学亦必随之成立”,他认为其“统一科学”所缺的只是联系“生理”与“性理”的一“环”,“性理”如能确立实证基础,则社会相关的学科就都可以作为其外延而轻易地构筑起来。这种预期可谓是西周一系列讨论的特征。当然,西周也指出,“不可推广性理以论人间之万事”,从西周关于社会的讨论可以看出,对其而言,所谓社会,首要是“个人的集合体”,他几乎没有意识到社会具有超越个人的独立性质。(27)关于这一点还有旁证,如体现在《人世三宝说》(1875)中的单纯的“公益”观(此处尚未意识到“公”与“私”的对立、或者从另一视角说“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人间社交之道,宜以公益为目的”,“合私利者公益也。若更明言之,则公益为私利之总数也”(28)。 笔者认为,这样的社会观源自西周对社会的理解,他认为,社会必然建立在所有个人的“性”的基础之上。例如,在《百一新论》(1866-1867年前后)中,西周写道,“人皆具有同一之性,此正所谓率性之谓道,不能改易”,认为但凡是人,都具备相通的“性”,“性”的具体面相有“好恶”“智”等,通过这些要素则产生出“自主自立之权”“所有之权”以及“仁”与“义”。进而,“人非虎狼,不能独居独栖,却与鸿雁牛羊相仿,有为群之性,相生养之道必起”(29),在人类相通的“性”中,存在“为群之性”,即有形成集团的性质,规范人际关系的规则也必然应当从中产生。此外,西周在《人世三宝说》(1875)中也认为,“由猿化人以来”,人类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基于“为群之性”而构成社会集团,“亚弗利加漠中之黑人”“亚墨利加山中之赤种”等与“西洲文明诸国之贤哲”之间,虽在“为群之性”的“扩充”范围上存在天壤之别(30),但毕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自原始以来,“为群之性”是所有人都具有的。 在上述西周对“性”的观点看来,依据每一个个人的“性”的内涵,必然能引申出社会的各种规范,在他所主张的“统一科学”体系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意识到“人间学”的独立性,但实质上仍认为该领域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性理”进行“扩充”的方式解决。然而,全人类都具备相通的、固定的“性”这一观点,却随着进化论的引入而大为动摇(31),在这一点上严复也不例外。下文将关注这一点,针对严复对“诸学体系”的看法进行探讨。 四、“诸学体系”的问题——严复 《原强修订稿》(1896?)(32)中,严复援引斯宾塞的观点说:“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33)进而,严复又称“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认为“群学”是以“数学”“名学(逻辑学)”“力学”“质学(化学)”“天学”“地学”“生学”“心学”等诸学科的知识为前提而出现的学科(34)。从另一角度说,在严复的意识中,“群学”是诸学科的“集大成”,“群学”以外的学科,以指导社会的“大人”之学——“群学”为归着点,形成一个体系。 可以说,这种以“群学”为顶点的“诸学体系”,与西周的“统一科学”构想极为类似。只是西周虽设想以“实理”为根据确立“统一之观”,但始终未能在“生理”之学与“性理”之学(严复称为“生学”与“心学”)间建立勾连,而严复则没有为“统一之观”问题而烦恼的必要。因为对于严复而言,根据斯宾塞的《合成哲学系统》,“统一科学”的大体框架已经确立。严复说: 斯宾塞尔者,与达(尔文)同时,亦本天演(evolution)著《天人会通论》(即《合成哲学系统》)。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第一项原则》)开宗明义,集格致(35)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生物学原则》)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心理学原则》)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社会学原理》)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伦理学原理》),乃考道德之本源,明致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呜乎!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36) 在严复看来,斯宾塞的学说是空前的“统一科学”,贯通着进化论这一“统一之观”(37)。而困扰西周的“性理”之基础的问题,稍微极端一点说,既然其已作为“进化的结果”而存在,那么,再追究其根据已经没有必要了(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否“恰当”是另当别论的)。同时,严复基于斯宾塞的学说,认为“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38),将社会比作一个以所有个人为构成要素的有机体。换言之,在严复看来社会不是所有个人的简单集合体,而具有超越个人的明确本质。因此,正如生物体的整体性质不由构成其的每一个细胞的性质直接决定一样,尽管社会依存于个人,但仍然具有不同于个人的独立逻辑。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存在沦为列强殖民地之忧。严复生活在这个危机感高涨的时代,对他而言,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使作为有机体的中国社会实现富强。他在探讨“个人”时,往往以“实现社会进化发展需要怎样的个人”“个人的素质如何制约社会进化发展的限度”等形式展开,出发点不再是“个人”本身,而是“社会”。与西周相比,这可以视作严复的一个特征。西周认为,社会得以成立、维持,有赖于人类普遍与生俱来的“性”(“仁”和“义”亦从此出),尤其是“为群之性”;而严复则对这种“为群之性”的存在予以否定。 在《天演论·导言十二·人群》的正文中,赫胥黎的观点是,正因为人形成了社会,才赢得了与其他生物的竞争而生存下来(39),《导言十三·制私》中又称,“自营(原文为self assertion)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为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40),认为抑制对自我利益的利己性追求——也即“制此自营”——的基础,是人具有的同感(sympathy,《天演论》译为“感通”),并称这一点才是“人所甚异于禽兽者”(41)。但对于赫胥黎的上述主张,严复在按语中予以了批评: 其(赫胥黎)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42) 严复认为,社会不过是人为了达成利己性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从结果上说,由于该手段在生存竞争中极为有效,而“同感”性质又有利于社会的有效生成与维持,因此具备“同感”性质的人才在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这一结果往往使人们以为“同感”能力是人的本性,是社会赖以成立的基础(西周关于人类具有“为群之性”的想法也如出一辙),而实际上,反而是社会的成立才使人们具备了“同感”能力(也可以进一步说,“现存”的所有人都在“事实上”具备“同感”能力)。 对于以“群学”为顶点而逐层构筑起来的斯宾塞“统一科学”,严复称,“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43),又称斯宾塞的学说“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44)。由此可见,据严复的理解,《大学》的所谓“八条目”与斯宾塞的学科体系性质相通,此外还可以发现,他对“八条目”的解释所依据的是朱子学的模式(至少可以说,严复对于“格致”的解释在广义上属于朱子学的说法)。与此相应的是,西周在对待世界上“理”的问题时,主张将作为“天然自然之理”的“物理”与作为“唯行于人之理”的“心理”严格区分(45),这一点广为人知。西周还认为,“所谓法、教者,皆此心理上之物,本说人之性情,与物理之事毫无关系”(46),强调“物理”与“法”“教”等人类社会的规范完全无关。站在西周的这种立场看,在“天理”这一概念中,物理法则的含义与道德规范的含义糅杂不清,朱子学对“理”的理解无疑是不正确的。而严复对所谓“格致”的理解,则显然将重点置于自然科学法则的侧面,如此一来,其“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的言论,是否等同于朱子学的思考,而“忽略”了西周口中两种“理”的区别呢? 五、“理”的相关问题 根据《天演论·论五·天刑》,赫胥黎称“为善者之不必福,为恶者之不必祸”,“用古德之说,而谓理原于天,则吾将使理坐堂上而听断,将见是天行者,已自为其戎首罪魁,而无以自解于万物”(47),以伦理观点看自然现象的过程,难以断定究竟什么是“善”。有鉴于此,赫胥黎提出主张,人类在作为“宇宙过程”而进化之外,还应当通过“伦理过程”组织社会,以对抗无情的“宇宙过程”。此时他引以为实现“伦理过程”之依据的,正是前文提及的、人类独有的“同感”性质(48)。 严复在按语中指出,赫胥黎此处的议论与《老子》中“天地不仁”等内容具有相同的道理,并称老子所谓的“不仁”并非通常道德意义上的“不仁”,而是一个超越了孰“仁”孰“不仁”的问题,因此不能以“仁”的标准进行讨论,换言之,自然现象是不能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讨论的(49)。此外,严复在《天演论·论十六·群治》的按语中说,“赫胥黎尝云:天有理而无善,此与周子所谓‘诚无为’,陆子所称‘性无善无恶’同意。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语,诚为过当,不知其善,安知其恶耶?至以善为伪,彼非真伪之伪,盖谓人为以别于性者而已,后儒攻之,失荀旨矣”(50),认为“善恶”这种道德上的价值标准并非由人类与生俱来的性质而产生,不过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而已(当然,这也不意味着“随意”创造)。 那么,在严复看来,道德上的价值判断标准又是如何确定的呢?在不久后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文译本《法意》(1904-1909)的按语中,严复以《庄子·齐物论》(51)为基础,称“言物论之本富,非是之生于彼此”,认为确定绝对的“正确”原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虽然,人生于群,是非固亦有定,盖其义必主于养生”,“居是世界,以人言人,不得不以此为程准也”(52),他承认,既然“人处于社会之中”这一事实已定,对人类而言,是否有利于社会成员的“养生”(或者,有时是作为有机体的社会本身的“养生”)就成为了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当然,如果仅就严复此处的言论而言,这个标准仍然极为模糊,但至少在他的理解中,人类是非善恶的标准(与“自然法则层面的理”相对,这已可称得上是“道德层面的理”)是在人类世界的内部独立确定,而这个世界是与物理世界有区别的。 通过上文对严复言论的考察,可以说其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西周强调“物理”与“心理”的主张相合的。稍有不同的只是在严复看来,相当于西周口中“心理”层面的东西并非由人类的“性”而产出,而应当是在社会形成后,由“处于社会中的人”确立的(可以认为,在这一点上,西周的观点更接近赫胥黎的主张)。但严复的“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一说也存在问题,他所说的“格致”指的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如何将其与“诚正”“治平”等在原有的儒家语境中明显带有道德意义的词相结合是问题之所在。正如《救亡决论》(1895)中所说,“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贵贱、善恶之殊”(53),严复口中的所谓“格致”,从认识的角度说,即冷静观察事实,而将“善恶”等问题置之度外。在斯宾塞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1873)的中文译本《群学肄言》(1903)的“自序”中,严复关于该书称,“二十年以往,不佞尝得其书而读之,见其中所以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54),强调斯宾塞此书阐明了人们是如何因为众多偏见,而不能正确把握社会现象的。此处严复所谓的“诚意”“正心”主要是为了“获得不持任何偏见而认识世界的能力”,可以认为,其中存在一种稍稍不同于儒家观念的“学术诚实”意义。 如此一来,我们也可以认为,严复所谓“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仅描述了一种“思想准备”(55),即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必须具备有关自然、人、社会冷静而客观的知识,但实际上其中也含有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四·恕败》的按语中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56)此外,在斯密《国富论》中译本《原富》(1901-1902)的按语中又称,“思盖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绝大公例也”(57)。也就是说,如果要将自己的“利”最大化,则有必要在行动中兼顾“利己”与“利他”,若损害他人,自己也将同时遭受损害,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则。据严复的理解,第一次明确提出上述法则的是近代的经济学。在过去的儒家学说中,曾有“义利之辨”一说,“义”与“利”相互对立,区分严格,但其实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如果不采取合乎“义”的行动,就无法真正获得“利”。换言之,只有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才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按照严复的上述理解,只要理解经济学的法则,原本与其他动物同样具有利己性质的人类都应该能自发地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反言之,违反道德的人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利己者,“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58),存在不道德的人这一事实,最终被归结为知识水平的问题。 若以这样一条人类社会的“法则”(在此不讨论该“法则”本身是否恰当)为前提,则严复所谓的“格致诚正”尽管基本上不出“知”的领域,但能够认识到上述“法则”的人,在自身的“利己性”推动下,必然会成为具备优秀道德的人,严复“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的主张,至少在他自己的逻辑下,是涵盖了“知”与“德”的上述联系的。 如上所述,严复至少在理论层面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由人类的“利己性”所奠定的,并且,他认为除此以外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具有超然性质的事物(59)。那么,西周的道德论又何如呢?在《人世三宝说》中,西周称“健康”“知识”“富有”是人世的“三宝”,追求其维持与发展正是道德的根本所在,在此过程中,西周认为应当以不妨害他人的“三宝”,尽可能“推进”(原文为“进达”,译者注)他人的“三宝”为“例规”。而且,西周还说,“盖此德植根于人之性中,发乎蔼然之至情”(60),认为人的“性”保证了实现“例规”的可能性。西周此处谈及的“性”,应当也包含第三节曾提及的“为群之性”等在内,仅从他的观点看来,个人对“三宝”的追求似乎都可以理所当然地实现,而不会相互冲突(61)。例如,为表示具有利己性质的个人对“富有”的追求不与公益相冲突,西周举了如下事例,“有杨朱者流之一老农,极主私利,朝夕勤劳,长己之富有,则如何。其毕生尽力培植之富有,纵不欲分与他人,其身死后,亦归于社交之一体”(62),这里完全没有提及“老农”有可能危害他人“富有”的情况,在我们看来似乎欠缺一些说服力。 实际上,当西周仅将追求私利、具有利己性质的个人定义为“杨朱者流”的时候,“利己”就只剩下“不愿将利益给予他人”(按西周的说法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63)一种形式,而忽略了“谋求自身利益时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可能。在其意识中,这位“老农”的“主私利”之程度,不过是不愿将其富有“分与他人”而已,并未设想其可能倚仗富有,在村中旁若无人,为所欲为的情况。西周这种乐观的设想,有可能源自其汉学教养中“利己主义者=杨朱者流”的信念,是一种无意识结果,但既然他以“为群之性”的存在为前提,那么,他也有可能认为,实际人数的多少暂且不论,这种“损害他人追逐私利”的人从“理论”角度看,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对于他们,应当依靠其他方法(如“刑罚”等)而非道德进行处理。但无论如何,西周毕竟没有对“为己之性”的内容及其存在与否提出明确的认定标准,追逐私利时的相互冲突、私利与公益发生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依然存在,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西周的观点中,某种意义上能够发挥弥补上述“不足”作用的是“信”(此处并非儒家道德所言的“信”,而是指对于超然性事物的信仰)的要素。西周在《教门论》(1874)中对“信”作了阐述,“人既知之,其理则为己之所有。若不能知,唯推其所知而信之耳”。这就是说,他所谓的“信”,是指对于超出自身“知”的范围的事物,应在“推其所知”的基础上抱以信仰之心。同时,从其“匹夫匹妇且有信,况谓贤哲无信乎”的言论可见,西周认为,对于超出“知”的范围的事物而产生的“唯推其所知而信之”现象,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换言之,尽管“信”的对象从“小民”的“狐狸虫蛇”到“贤者”的“上帝主宰”形式多样,但每个人都不例外地将其所“信”的对象设定在自己“知”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西周没有断言此处所说的“信”完全植根于人“性”,但也相去不远,他至少将其视为人类共同具有之物。“知之大者其信亦必高,知之深者其信亦必厚”,尽管同样称为“信”,但由于各人“知”的水平不同,“信”的对象水平也是天差地别。“苟通万象之故,究心性之微,则以其知,推有主宰,足可信之矣。既信主宰之在,则知其命之不可违”(64),西周认为,将“知”穷究至最高水平进行推测,世界存在某种“主宰”,应知其命不可违抗。换言之,西周的观点即,通过“知”来“扩充”人所共有的“信”之“端绪”,以致最终确信,世界存在“主宰”(西周也使用了“天”“上帝”等词),尽管无从得知其为何物,但“主宰”(“天”“上帝”)之命(其中也应当包括道德规范)是不可以违反的,进而,只有达到这种“确信”程度的人,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完全遵守“主宰”之“命”。 此外,同样在《教门论》中,西周还批评了朱子学的“天=理”的观点,“理自天所出”“天犹国王,理犹诏敕法令”,由此看来,他所谓的“主宰(天、上帝)”是与“理”相区别的最高级的神圣存在,至于其“命”,则带有很浓厚的“命令”色彩。因此,按照西周的观点,“主宰”是“命”的根源,也是发布“命”的主体,了解“主宰”之“命”不可违并对其悉心遵守的前提是对“主宰”存在和价值的“信”。西周主张“信为众德之元,百行之本”也可以在上述范畴内进行理解(65)。如此,在西周看来,要保证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兼顾道德规范,最终也必须依靠对“主宰(天、上帝)”的“信”来实现(66)。 日中两国的两位思想家——西周与严复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在表面上存在类似性,本文由此出发,尝试对二者进行了初步比较,但现阶段仍停留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且属于简单的“罗列”层次,有待研究的部分尚多。笔者利用此次机会,首次较为系统地阅读了西周的文章,其论稿很多在内容上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追寻其思想痕迹时感受到极大困难。再者,无论是西周还是严复,其言论的相当部分都非原创,而是对西方种种学说的复写。本文未能追溯至他们思想的“起源”而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应留作今后的一大课题。 另,在上述一般问题以外,还存在与本文相关、有兴趣今后进行考察的两点问题。 第一,关于西周对“理”的看法问题,其认为“理=相关性”,而据宋学与徂徕学的理解,“理”是事物内部的实体,西周的理解已超越了这二者,因此有人对其创新性作出了评价(67);其实在这一意义上,严复的观点与西周类似。比如,在1905年《阳明先生集要三种》的“序”中,严复认为“理”出现在复数的事物中,并举例说,当水流撞击石头发出声音时,在水与石中寻求声音毫无意义,必须从两者的关联中进行确认(68)。严复这种观点与西周有何异同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 第二,本次考察对西周文章中的一点印象深刻,即他强调“理”必须由“人”所认识才具有实际意义。 《西周全集》中有一篇题为《开题门》的文章,据推测是其在1862-1865年间的作品,其中的“附录五”部分,认为“理”是确立“学”的“四元”之一,“物有天则,示象于吾人之灵慧谓之理”(69)。此外,大约完成于1887-1889年间的《理字说》中写道,“盖理者虚体也,其气禀性质一定,故与事物相应之际而现,其关系唯人心可察”(70),西周认为“理”在很多情况下不仅自身体现出“相关性”,也对其与认识“理”的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前文引用过的《教门论》认为,“理”的产生源于具有超然性的“天”的命令,再考虑到西周强调作为自然现象之“理”的“物理”与人类独有之“理”的“心理”之间的区别,可以确定,他认为“天”不仅赋予人认识“理”的独特能力,甚至还赋予人们“特别之理(即心理)”(71)。西周在这种观点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其与儒家“天地人”的观念有何关系,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作者附记:本文部分内容曾在2010年8月2日东京大学全球化COE“共生国际哲学交流中心”国际研讨会“作为学科的日本哲学”上进行口头演讲,对各位与会者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①岛根县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编:《西周と日本の近代》,东京:ぺりかん社,2005年。 ②井上厚史:《西周と儒教思想——「理」の解釈をめぐって》,岛根县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编:《西周と日本の近代》,第146页。 ③专著有菅原光的《西周の政治思想——規律·功利·信》(东京:ぺりかん社,2009年)、清水多吉的《西周:兵馬の権はいずこにありや》(京都:ミネルヴア書房,2010年);论文有莲沼启介、大久保健晴的研究以及《北東アジア研究》一四、一五合併号“特集西周と東西思想の出会い”(島根県立大学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ナンタ一,2008)所刊载的多篇论文、狭间直树《西周のオランダ留学と西洋近代学術の移植“近代東アジア文明圈”形成史:学術篇》(《東方学報》第八六册,2011年)等。 ④井上厚史:《西周と儒教思想——「理」の解釈をめぐって》,岛根县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编:《西周と日本の近代》,第146页。 ⑤西周的这种“形象”现在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前揭菅原著作的初版侧标中就书有“是‘日本哲学之父’还是‘军国主义的创始人’”这样的疑问。当然,这是一种宣传“战略”,是为了强调菅原此书的雄心,即试图论证对西周采取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式提问本身存在问题。但既然在宣传中故意抛出上述提问,就说明至少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印象”,认为将近代西方新思想引入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身份与“军国主义者”的身份无法并存。与此相对,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即使同时提出“军国主义”主张(如20世纪初的梁启超等),也没有令人感到太多不协调(当然,必须考虑到二者时代上的差异,以及对“启蒙思想”与“军国主义”的定义及其社会功能的问题。但至少在该时期,梁启超思想中不可谓没有“军国主义”的思想要素)。这种“感觉”上的区别,可能反映了此后中日两国近现代史进程的差异,这本身就可以成为思想史上一个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⑥严复对T.H.Huxley的Evolution and Ethics(1893)及Prolegomena(1894)的翻译与评论。 ⑦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集严复清末时期的八本主要译著而出版的丛书。《原富》(亚当·斯密《国富论》)、《群己权界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穆勒名学》(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逻辑体系》)等收录在内。 ⑧严复:《救亡决论》(1895),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页。以“西学”一词指称西方的诸学科,在19世纪末以前的中国尤其频繁。其所指的具体内容,在各研究者中有若干差异,有时与“中学”相对比,仅带有狭义的自然科学色彩。但正如后文所述,严复尤其信奉以“合成哲学系统”为代表的赫伯特·斯宾塞学说,对其而言,“西学”不仅是自然科学,自然也包含社会科学。 ⑨当然,严复当时也并不是主张所有“儒教”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就在此处引用部分之前,他还说“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并认为应当以“西学”为标准,将“儒教”中有价值的部分与无意义的要素加以区分。此外,1890年代的中国正积极引进“西学”,为寻求正当理由,往往认为西学“实起源于中国”,并在中国过去的经典中寻找与“西学”相似的内容,以中国的价值标准评价“西学”的价值。与此相对,严复则主张以“西学”的标准认定中国政治、教义的价值,这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坐标转换”。在这一点上,严复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与西周相仿。如,根据莲沼启介的研究,横井小楠认为以儒家“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为标准,美国、英国的议会政治比德川幕藩体制更具统治形式上的优越性,而西周、加藤弘之则在近代西方而非中国文明中寻求政治理想,莲沼认为,“这一点上西周与加藤等人的视点更具有决定性的新意”(莲沼启介:《西周に於ける哲学の成立——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法哲学成立のためのエチユ一ド》,东京:有斐阁,1987年,第96-97页)。 ⑩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1913),另参见《严复集》第329-332页等处。 (11)实际上严复并未积极参与筹安会的活动,但作为该会的成员是无疑的。 (12)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一卷,东京:宗高书房,1962年,第458页。此外比较著名的是,西周在《百学连环》中明确意识到了“学”与“术”的区别(参见《西周全集》第四卷,东京:宗高书房,1981年,第12-14页)。然而,包括此处的引文在内,西周是否在严格区别“science & arts”的前提下,意识到其使用的“学术”一词包含上述两种含义则难以定论。但此处的引文,无疑带有承认近代西方之“学”优势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严复也强调应当严格区分“学”与“术”。例如,他在1906年的《政治讲义》中称,“学”是“问此系何物”,而“术”是“问物宜如何”,两者不能混同(《严复集》,第1248页)。但严复使用“学术”一词时,却未必都含有“学”与“术”的含义,而往往与“学”的意思相近。 (13)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2页。 (14)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2页。 (15)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2页。 (16)西周:《百学连环》,《西周全集》第四卷,第23页。 (17)西周:《百学连环》,《西周全集》第四卷,第25页。 (18)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1385页。 (19)此书以《穆勒名学》之名出版,翻译了穆勒原著的Book Ⅲ Chapter Ⅹ Ⅲ部分,剩余部分的翻译最终未出版。 (20)汪晖已指出西周与严复的这种共同性。但汪氏主要关心的是儒家的世界观如何渗透在他们二人的科学观之中,且为概括性的研究,并未详细探讨二人的观点(参见汪晖:《科学的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 (21)小泉仰在《西周と欧米思想の出会い》(东京:三嶺書房,1989年)第三章“西周の統一科学の試み”详细讨论了西周“统一科学”的构想及其遭遇挫折的过程。 (22)西周:《生性发蕴》,《西周全集》第一卷,第45页。此部分译自Lewes著作,但西周表示,“此书之根本在于显示坤度(即孔德)实理学之地位”,将其附录于《生性发蕴》中的目的,是为了“使观者知现今哲学之进步如何,信余所言之不诬”(第41页)。而西周对Lewes著作的翻译部分未加按语,则可说明这部分内容大致反映了他当时的见解。 (23)西周:《尚白札记》,《西周全集》第一卷,第165页。 (24)西周:《尚白札记》,《西周全集》第一卷,第46页。 (25)以上均引自西周:《尚白札记》,《西周全集》第一卷,第63-65页。 (26)参见小泉仰:《西周と欧米思想の出会い》。 (27)西周:《尚白札记》,《西周全集》第一卷,第65页。 (28)西周:《人世三宝说》,《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32页。 (29)西周:《百一新论》,《西周全集》第一卷,第282-284页。 (30)西周:《人世三宝说》,《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24-525页。 (31)当然,即使是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也完全没有认为有一种人类贯通古今而都具有的共同性质,如各种欲望等。这是与动物相同的要素,并不能说是人类独有的“性”。 (32)《原强修订稿》初见熊元锷编《侯官严氏丛刻》(1901年刊),故《原强修订稿》的完成时间也有可能是1896年以后。但严复1896年10月致梁启超的信中曾说,将对1895年发表于天津《直报》的《原强》加以改订,并预计在十余日内寄给梁(《严复集》,第515页)。此时是否修订稿已完成,此稿是否即现在所见的《原强修订稿》无法确认,但至少可以确定,严复早有对《原强》进行修改的想法。另,下文引用自《原强修订稿》的内容,在《原强》初稿中亦有体现,但行文方式不如修改后直接。 (33)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8页。 (34)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7页。 (35)中国当时使用“格致”一词指西方学问时,有狭义指物理学、广义指所有科学的两种用法。此处的“格致”从上下文关系看应属后者。 (36)严复:《天演论·导言一·察变》按语,《严复集》,第1325页。 (37)假设“统一科学”整个建立在以“科学”为根基的(即严复所谓由归纳法导出的意思)进化论基础之上,那么在严复先前所列举的、以“群学”为前提的诸学科中,“数学”与“逻辑学”的地位就显得有一些微妙。但按照Benjamin I.Schwartz的说法,严复信奉的穆勒逻辑学说是“极特殊的逻辑学”,是“挑战传统逻辑学主流的学说”,穆勒企图“仅在经验论的基础上构建其逻辑学”,认为“所有科学的基础,包括演绎式的、或是论证式的科学在内,都是归纳”(Benjamin I.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P.,Cambridge,1964,引自平野健一郎译:《中国の近代化と知識人——厳復と西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86-187页)。因此,严复极有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数学”与“逻辑学”具有超越进化过程的意义。 (38)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7页。 (39)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1344页。 (40)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1346页。 (41)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1347页。 (42)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1347页。 (43)严复:《原强》,《严复集》,第6页。 (44)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26页。 (45)西周:《百一新論》,《西周全集》第一卷,第277页等。 (46)西周:《百一新論》,《西周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47)见《严复集》,第1369-1370页。另,赫胥黎的原文中并没有与此处引文中的“理原于天”直接相应的部分,因此可能是严复出于宋学等传统的儒家思想而加入的。 (48)以上赫胥黎的观点,参照Paradis、James《進化と倫理——トマスハクスリ一の進化思想》(小林传司等译,东京:产业图书,1995年)的“解说”,第260-261页。 (49)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1370页。 (50)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1395-1396页。 (51)由严复此处所发之议论可见,其对“齐物论”篇名的解释是“齐‘物论’”。 (52)《法意》按语,卷十九,第2-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亦见于《严复集》,第987-988页。 (53)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6页。 (54)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严复集》,第123页。 (55)当然,对严复而言,为了指出批评朱子学“物理”与“心理”相关联的思想、认识人类社会存在独特之理的必要性,强调这种“思想准备”非常重要。例如,《政治讲义》一书反复强调,要施行恰当的政治,去除价值判断的因素、准确了解与政治相关的“事实”是必要的前提。 (56)严复:《天演论》,《严复集》,第1349页。 (57)《原富》“部丁篇七论外属(亦译殖民地)按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85-586页;《严复集》,第892-893页。 (58)《原富》“部甲篇八释庸按语”,第91页;《严复集》,第859页。 (59)当然,这只是严复的理解,其主张正确与否另当别论。 (60)西周:《人世三宝说》,《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15、520、522页。 (61)菅原光认为“仅从《人世三宝说》看,西周没有对私利间的冲突、私利与公益的龃龉作深刻考察”,并质疑“仅以《人世三宝说》解释西周的功利主义思想有失妥当”(《西周の政治思想——規律·功利·信》,第112页),因此他也关注了西周译自J.S.穆勒Utilitarianism(1863)的《利学》(1877)一书。在此基础上,菅原指出,“以往的研究将西周的功利主义思想等同于‘物质主义’、‘简单主义’,理解为预定调和式的乐观论,而西周却将功利主义理解为完全理想性的思想,重新认识被西周视为‘君子哲学’的功利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同上书,第120页)。菅原同时也称,应区分西周功利主义的两种相对的面相,即以《人世三宝说》为代表的“为‘民’的功利主义”与以《利学》为代表的“为了尽力实现公益的‘君子’之功利主义”。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本身并无不妥,但另一方面,西周在《人世三宝说》中曾说“此德植根于人之性中,发乎蔼然之至情”,似乎认为应以人类的“性”为根据实现社会秩序,这是一个留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62)西周:《人世三宝说》,《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32页。 (63)西周:《人世三宝说》,《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30页。 (64)以上引自西周:《教门论》,《西周全集》第一卷,第493、501-502页。 (65)西周:《教门论》,《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05-507页。此处所论的“信”的问题,换做现代用语,即西周所说的“宗教”问题。菅原光认为,西周的宗教论是“完全寄希望于‘知’的设想”,“其提出的方法是培育、发展‘知’本身”(《西周の政治思想——规律·功利·信》,第180页)。无疑,西周关于宗教的议论确实包含上述一面。但菅原认为,西周在《教门论》中回答“信奉上帝有何功德”这一提问时,“从问答关系上而言焦点出现了偏差”,并没有“论及信奉‘上帝’的功德”,“西周虽认为存在‘一定不易之伦理纲常’,但如若不信,则可能为‘欲’和‘情’所乱”(同上书,第172页)。对此解释笔者稍感不妥。西周的原文为“而今谓不可知而不信上帝,纵有一定不易之伦理纲常,平素行己,出半信半疑之间,为欲所挠,为情所揽,不能决然尊奉铭心之诏时,虽有几许上智相率,不为舜颜桀心、孔貌跖魂之徒乎”(《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07页)。从其中存在“不能尊奉铭心之诏时”的文字可见,西周在“不信上帝”与“不能完全实践伦理纲常”之间建立了一定逻辑关联。本文也曾提到,西周没有采信朱子学“天=理”的观点,而认为“理”是“天”的“命令”,不是“天”本身。因此,《教门论》中的这部分议论,应作如下理解,即西周的主张认为,遵守“伦理纲常”是“上帝”之命,如果不信世界“主宰”——“上帝”的存在(或者说不信“伦理纲常”是“上帝”的“命令”),那么“伦理纲常”正确性的根据则不明,就无法确立必须遵守的信念。反言之,正因为存在对“上帝”的“信”,才能一如既往地实践伦理纲常。很难认同西周在此处“没有论及信奉‘上帝’的功德”。 (66)西周在认识“天”时强烈主张这种具有“主宰”的含义,这种认识在儒家相关“天”的思想流程中处于何种位置,是一个有意思的论题。另,持斯宾塞“不可知论”立场的严复认为世界的“主宰”是“不可思议”(《天演论·论十·佛法》按语,见《严复集》第1380页等处)的,对于这一对象,甚至连西周所说的“推其所知”都无法实现。“固无从学,即学之亦于人事殆无涉也”(《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36页),严复对超过思考界限的“不可知”领域的讨论并不积极。 (67)井上厚史:《西周と儒教思想——「理」の解釈をめぐって》,第169页。 (68)严复:《阳明先生集要三种》,《严复集》,第238页。 (69)西周:《开题门》,《西周全集》第一卷,第23页。 (70)西周:《理字说》,《西周全集》第一卷,第600页。 (71)西周在“论学问在于深究渊源”(1877)中,吐露了阅读斯宾塞《心理学原理》后的感想(《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68-573页)。由此可见,他无疑知道斯宾塞的存在,另外,从时间上推测,他也应当对进化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掌握。但尽管如此,西周却没有热心接受进化论思想,这可能与他将“人”视为某种具有“特权”的物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