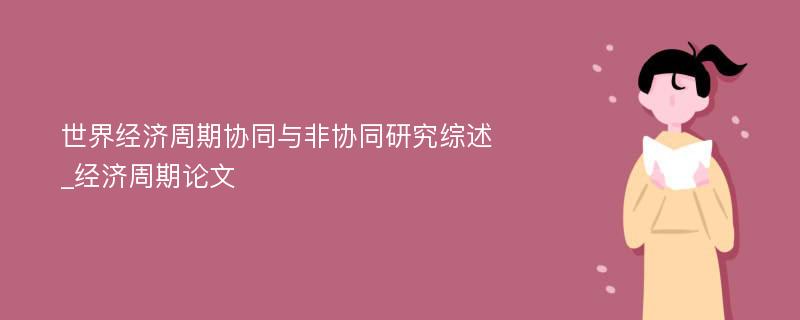
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与非协同性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非论文,经济周期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经济周期(World Business Cycle)是指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而组成的理性整体所具有的波动现象。当然从广义上说,国际经济周期(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也是世界经济周期的阶段性表现,主要是从一个国家出发,本国与他国组成的“国际”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波动现象。所谓协同性,是指不同国家的经济波动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行为的同步性;而非协同性是指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世界经济周期相似于国别经济周期,又不同于国别经济周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传导,所以,不太严格地说,世界经济周期的历史就是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synchronization)与非协同性的历史,而世界经济周期研究的历史就是对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与非协同性研究的历史。
一、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随着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贸易伙伴国之间经济周期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下滑,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和研究世界经济周期。人们发现,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例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和日本4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而Canova和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如石油冲击、相似的经济政策安排和共同的技术进步等)是生成跨国的总量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7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Karry、Ventura(2000)指出OECD国家之间表现出经济的高度同步性。他们发现,OECD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并指出OECD国家之间的经济波动通过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行传递:劳动密集型产品繁荣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进而带来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上涨,进一步带来就业和产出的增加。所以,在他们看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是形成和传递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
Ravn(1997)的实证研究表明,除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它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而Hess、Shin(1998)为了理解世界经济周期的形态,建立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周期模型并进行对照研究,指出区域间的汇率波动轻于产出波动,工资收入更有波动性等。Sarkissian(2002)指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期更是如此。Choe(2001)研究了10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经济波动随着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而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既而,人们开始研究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产生、形成和传播的机理,在宏观经济结构模型里,通过分析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等,研究世界经济的行为。事实上,人们对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成因机理的认识也是基于对世界经济周期的行为和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以及其它要素市场)的逐步扩展过程:人们不仅从贸易、投资和产出中的传导力量中理解世界经济波动的形成,也从就业和人力资本的差异中理解经济波动的传递。同时,人们将产品进行细分,发现引入耐用消费品的波动之后,能更好地解释消费与产出在国际间的传播。人们也逐步将“世界”概念放大,将原来锁定的发达国家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现小型国家的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具有特殊性。人们甚至借助物理学中的“共振”(mode-locking)现象以解释微小的经济振荡也能通过非线性过程形成世界经济的同步振动,以便理解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同性。
Cantor、Mark(1988)建立了一个两国家模型,每一个国家有相同的工业并带有不同的国家特色(主要以技术为主)的冲击。他们证明,经济周期风险来源于国家特色的技术冲击。而国际证券市场正是传递经济周期的媒介,但同时,它又为国内外的代理商提供规避这些风险的机会,而证券组合是有效规避风险的必要手段。然而,这个模型仅仅只考虑自由浮动汇率政策条件下商品贸易的传递机制。10年后,Grohe(1998)则通过研究美国的经济波动如何传递到加拿大的机制,指出了与他相反的结论:不管是完全竞争产品市场还是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仅仅用贸易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传导过程是乏力的。由于投资、产出和就业并不随价格波动而同步变动,通过金融市场和出口需求市场共同的作用,投资、产出和就业也就成为国家之间经济波动传导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宏观经济的结构模型里,为了增强对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解释能力,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决定模型进行了深入细分。例如Bruno(1997)建立了两国家、两产品模型,并假定国内外投资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以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各不相同,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品的替代弹性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重要变量,并指出特定国家的技术冲击是造成两国家经济波动的根源。而Cannova、Ubide(1998)将家庭产品(household production)引进两国家、两产品的国际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指出家庭产品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在国际国内传导的重要机制。Backus、Kehoe、Kydland(1992)将一个两国家真实经济周期的封闭模型扩展为简单的同质商品和非流动的劳动要素的竞争性的世界经济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产出是高度不相关,投资和贸易比我们从数据上了解的更具有波动性。Nadenichek(1999)将耐用消费品(durable goods)引进国际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检验了耐用消费品和产出波动在国家之间的传播,并认为正是因为耐用消费品需要跨期消费,因此必将影响消费者的行为。Bergman(1996)利用产出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VAR模型检测了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等5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结果证明需求和供给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周期的频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它们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方差的50%以上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产出的90%以上的方差来源于供给冲击。
Selover、Jensen(1999)则与众不同,提出了“共振”的世界经济周期理论,并通过数据验证了这一理论假说。所谓“共振”是指震荡系统之间即使是微弱的相互作用也通过一个非线性过程从而达到系统的同步振动。但同时他们认为,“共振”的世界经济周期理论并不否认外部供给冲击的重要作用,而“共振”只是形成世界经济周期的最根本的原因。他们还说明了即使国家之间技术、组织和管理方式存在细微的差异,经济周期行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既而“共振”也就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周期的高度同步性。同年,Selover(1999)研究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传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主要考察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以及东盟国家与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他们用主成分分析法、自回归分析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贸易量的相关性,以便找到东盟经济周期。在此,作者还提到用光谱分析法检验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共振”,并找到了东盟区域经济周期存在的证据。
长期以来,人们虽然都承认“世界经济周期”这个概念,然而在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把世界经济周期中的“世界”简单地理解为发达国家,很少提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因此,对小型国家的经济周期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例如Blankenau、Kose、Yi(2001)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波动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众多渠道之一的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经济传导的重要机制。他们还指出,世界真实利率对世界经济周期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和产出等。
显然,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仅是世界经济运动的特征,也是世界各国组成的“理性”主体的“行为”,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是世界经济主体的活动规律,也是世界经济波动的基本规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才得以存在,否则,“世界”的经济周期就“分裂”为各国自己的经济周期。但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并不完全等于“世界经济的协同性波动”的概念,事实上,在“协同性”的理解中,也包含了对世界经济的“非协同性”的理解。
二、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协同性
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协同性,并不是近年才有的事情。早在未形成“世界经济周期”的时候,人们就各自研究封闭国家内部的经济波动。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一体化,世界各国在越来越融合为一个整体的今天,再来研究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协同性就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全球化与一体化是一个过程,人们对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与非协同性的研究,就直接影响各主权国家对世界经济周期的认识,这又直接影响各主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从而反过来影响全球化与一体化。例如,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地弱得多。Heathcote、Perri(2002b)则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帮助理解冲击的国际相关性、国际资产贸易程度以及宏观总量的国际关系等之间的潜在相互作用。他们研究指出,在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是,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financial globalization)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化(real regionalization),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地降低了。
显然,世界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他们在世界中的地位得到逐步提高,他们的经济行为也必将逐步影响世界经济的“行为”和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从而世界经济周期也就具有新的特征——在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增加时期出现阶段性的非协同性。发展中国家和非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甚至所有制结构等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原来相互竞争的“同质”国家的“同质”波动“合成”之后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周期就具有协同性的特征,而现在相互补充的“异质”国家的“异质”波动“合成”之后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周期就具有非协同性的特征,就像物理学中波的作用规律一样。
特别地,在全球化越来越高的时代,由于“异质”国家的“异质”波动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协同性对世界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以前,由于人们知道世界的经济波动会叠加,因此会在世界经济联系通道上装上一层纱窗;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人们大可以放开门户,积极推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一体化。
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形成以区域经济为中心的经济行为必然影响世界经济的运动形态,从而出现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降低的现象。
当然,也有人发现,世界经济周期并非要么协同性,要么非协同性这样简单的两种状态,事实上,由于世界各国的复杂的“特质”,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和“互替”并存、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补”和“互替”并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补”和“互替”并存等等,致使世界经济周期就必然具有“复杂”的现象。
三、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与非协同的复杂性
所谓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与非协同的复杂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在长的协同阶段包含短的非协同,或者在长的非协同阶段存在短的协同;二是指由于同质国家之间和异质国家之间是并存的,也就存在某些区域的国家是协同的,另一些区域的国家是非协同的,作为研究世界整体的世界经济周期就不能简单地去掉某些国家而忽视这些现象;三是即使存在协同性的国家之间也有某些方面非协同,存在非协同性的国家之间也有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协同。但是,就笔者目前接触的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后两个方面。例如Backus、Kehoe、Kydland(1992)将一个两国家真实经济周期的封闭模型扩展为简单的同质商品和非流动的劳动要素的竞争性的世界经济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产出是高度不相关。
另一方面,“同质”与“异质”国家的经济波动所导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非协同性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例如Karry、Ventura(2001)指出了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经济周期是不同的。他认为,由于富裕国家具有专业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以及高新技术的工人,从而比只有传统产业和非技术劳动力的贫穷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专业化的差异造就了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结果。从而使得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的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相比,更少波动性和更多的同步性。Ellion、Fatas(1996)假定贸易与波动的扩张成一定比例,他们建立了一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结构模型,试图研究国家之间产出波动的传递和投资的反应等。研究发现三国之间存在非对称性传导机制:美国的冲击强烈迅速地传递到欧洲和日本,而欧洲和日本的冲击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非常小。Zimmermann(1997)也指出,不同国家的经济周期形态不同,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变量,而这些变量大多与它们经济规模的大小和它们之间贸易距离长短相关。作者构建了一个3国家模型以便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显著不同。他们通过具体研究两个例子来说明经济规模和贸易距离长短是经济周期显著不同的两个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一是瑞士与欧洲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二是加拿大与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但同时他们发现贸易并不是世界经济周期传导的主要渠道,而是通过技术的外溢和及时传导所形成的技术冲击等。Hoffmaister、Pradhan、Samiei(1998)研究发现,南部国家比北部国家的产出方面的经济周期冲击更有灵活性,并得出一个结论:即经济越开放,受到经济冲击就会越小,这既是由于资本流动的负向影响,也是源于出口的多样化增加。
Hearn、Woitek(2001)则提出了一个核心经济体和外围经济体的概念,指出外围经济体与核心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表现不同。他们认为,北大西洋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一般为7~10年的规律性,而其他外围国家则大致3~5年,而且较少规律性。同时,他们还指出,核心经济体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很强,核心经济体与外围经济体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对较弱,而外围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最弱。Lee、Huh、Harris(2003)也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增强了,但是日本与澳大利亚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在80年代增强、在90年代却反而减弱了。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来日本经济的下滑,导致日元对澳元贬值,则澳大利亚实际上降低了进口日本商品的价格从而提高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近年来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产出波动方面呈现负相关的情景。
四、简要结论与展望
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迅速,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世界经济周期的研究。随着世界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人们发现存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并不是简单的协同性或同步性,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现象,即在协同性中包含非协同性,在非协同性中包含协同性,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协同性和非协同性并存,以及存在协同性的国家之间也有某些方面非协同,存在非协同性的国家之间也有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协同等等。
但是,现有的文献都是从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决定的结构模型出发,简单地对某些变量细化、引申或扩展,因此,现有的模型总是局部地、“支离破碎”地分析世界经济周期的特征和行为,而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纵观世界经济周期或国际周期的文献发现,已有的模型都没有考虑国家之间的博弈能力,因此,引进博弈理论建立一个考虑国家力量不均等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是世界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基于动态博弈的世界经济周期模型就可以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世界经济周期,建构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在应用层次,已有的文献也都只是简单的对策研究,而以预警为对策的研究也主要局限在对经济行为的预警,但真实世界里的世界组织却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规制,也就是说,以世界组织(包括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合作论坛等)为监测主体,不仅监测经济行为还要监测政府行为,确保世界经济“运行”在安全的轨道,即建构世界经济周期指标系统和预警机制,也将是一个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