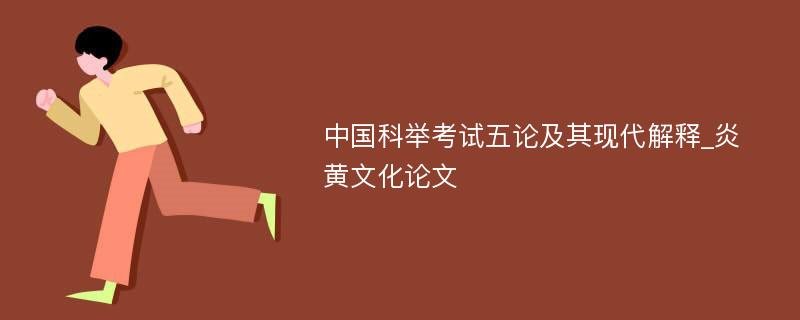
中国科举考试及其近代解释五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2-0018-10
考试的观念和制度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从前美国哈佛大学的名教授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说中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官僚体制(bureaucracy)的民族,他这样说乃是因为官僚体制必须依赖任人唯贤(meritocracy,或说才能统治的体制)的理想和制度,而中国人从孔子就已经提倡这样的思想,因此中国人的政府可以说是最早采用官僚体制的政府。
由于相信用人唯贤,主张政府要任用有才能的人,因此中国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甄选人才。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这样逐渐发展出来的。汉朝时,已经设各样的科目来举贤才,虽然录取的往往还是来自好家庭的贵胄子弟,而且数目也不多,但是至少政权必须向有才的人开放,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到了隋朝,中国政府正式把考试制度化,以后历经三百年,终于把贵族制度完全推翻,变成了一个几乎是完全仰赖科举或贡举的社会,来甄选优秀的人才。宋代以后,这个形势已经彻底建立,支配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近一千年之久,它的影响不谓不大矣。
对于考试制度的记录汗牛充栋,它毕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持续长远、影响深刻的社会兼政治制度,因此研究的人非常多,中外皆然。在过去,中国人对考试制度的了解往往受到通俗小说(像《儒林外史》)或明末清初人(特别是像黄宗羲)的影响,采取几乎是完全负面的了解。但是科举考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形成,它又对中国人的治学方法、对科学的态度以及人格的形成又有什么作用,这些在过去中国学者的研究当中,一般都未能深入地杷梳探索。
在西方,从17世纪西洋教士来华,大量向西方报导中国考试制度之后,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科举就感到很有兴趣,甚至开始发展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事实上,中国人的考试(甄试)制度早在中古已经为欧洲人所知悉,其涓滴影响,历久而不衰。就是在今天,西方研究中国科举制度本身以及它对中国及日韩越等国的影响的学者,数目也还是很多。他们往往提出各样的解释,帮忙厘清很多关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人格养成以及治学方法的种种问题。
以下我将介绍近年来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来讨论中国科举制度的意义及影响,我也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文章共分成五个部分,称为“五论”。它们是围绕同一个主体的变奏。
第一论:地域社会与教育及文化的发展(英文有关著作的回顾)
家族在考生的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在最近英文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清楚。① 接着受注意的当然就是家族的定义。如一般所知,家族的定义在传统中国乃是依据《礼记》,但是《礼记》的说法是规范性的,历代的实践变化很大。例如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大姓,其社会运作就当然和它以前及以后不同,也跟《礼记》原来的说法并不相符。对家族定义的研究,近30年来,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宋代,虽然这期间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也曾经流行了一阵子。② 学者们研究中国的家族,除了利用一般常用的正式的正史文字材料之外,有很多人利用地方志,因为在方志里可以找到比较详尽的地方家族的资料。
对地方志的应用,过去范围十分狭窄,但是近30年来,学者开始重视地方社会的差异,研究中国家族在地方上所扮演的角色,于是注意到方志材料的用处,于是大量用历史的眼光来处理方志上有关家族以及登科录材料。这是近二三十年来的重要发展。同时应该指出来的是对地方家族的研究,主要由人类学家开始,特别是研究中国南方的英国人类学家,像Maurice Freedman等人(下面会再提到)。③ 他们注意到中国的家族组织,以共有财产(corporate property)或中国人一向注意的“同居共财”为其特色。这个说法影响十分深远。他们认为要了解中国社会的运作,社会流动,一定要把家族的组织弄清楚。这些人类学者们的主张后来就开始影响历史学者。
Denis Twitchett早于1965年在东京开东方学会议时,就已经写了短文从“家族”的角度来批评何炳棣,认为何炳棣只注意到个别考生的父系前三代人的家庭背景,这样不足以让我们确定他的出身。他认为应该从“家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因为许多人或许父、祖、曾祖三代并不显赫,但是仍可能从姻亲或叔伯那里得到好处和支持。可见家族对一个人的出身还是有重要的影响;一个人所得到的经济上的支持不能只从父系的三代来判定。④ 这样见解的来源显然就是来自英国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Twitchett本人是英国剑桥的教授)。
但是对教育史的地方意义的研究,毕竟要等到教育史、尤其是科举的研究已经到了相当的成熟以后,为了更精确地了解教育对教养考生的效用,这才开始从地方志去找材料。我个人早期就曾利用福建的建阳来讨论该地的地方文化和教育(特别是书院)的关系[1],不过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考量科举的效用,运用材料纯熟而得奖的当然以Hymes的著作为里程碑。⑤ Hymes用江西的抚州来讨论所谓社会流动,虽然他的结论引发了种种的争议,但是这本书的确开启了创造性利用方志材料的大门。⑥ 我在上面提到说,他认为宋代有“地方化”的现象。
使用地方志的材料来研究地方历史的另外以Timothy Brook为最有名。[2] 他写有好几篇有关明代地方志及地方生活的文章和书。他的贡献在我看来就是引导更多的学者去注意地方上的种种社会或宗教生活,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注意到印刷业,并因此连带注意到童蒙、幼学读本的流通。[3] 他也写有有关明代书院藏书的文章[4],这些作品虽然谈的都是整个中国,但是带有浓厚的地方史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大量利用地方的观点,那么就会注意到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地方文化的分殊,以及科举如何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
最近,鲍弼德(Peter Bol)开始大量采用地方史的观点探讨宋元之际的改变。他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论文,集中研究浙江金华地区的地方文化发展史。他在替我编的《新与多元,宋代人对历史的想象》一书所写的“地方史与家庭”一文中,讨论宋元时期地方重要家族与科举之间的关系。[5] 显然科举还是保持一个地方大家族能数代繁荣的重要关键力量,只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地域观念和地方家族的影响力才是中国社会的安定力量,而地方社会得到安定,整个中国才能安定。Bol对地方史研究的贡献更扩大为对中国历史地理图的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工作。这个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将中国历史地图(主要是根据谭其骧等人所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加以改进)放在网络上,让学者可以使用。2005年初,Bol应邀参加由东京大学及日本宋史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中国的日常空间”的会议,他的论文就是围绕中国的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显出科举的成就仍然是测量文化发展的重要指针,但在结论时,他不禁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这就是既然宋元以来的中国地方文化有这样的分歧,那么它又是如何整合成为一个国家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⑦ 我个人认为儒家和一般通俗教育乃是一个最根本的因素。这一点在下面讨论。
中国地域社会的研究只能从地方志发达了以后的时代才真正做得到。因此唐代以前,实际上说不上有真正的地方史。但是宋代以后,地方史的研究可以达到相当的水准。⑧ 事实上,从地方家族与学术的立场来探究地方文化特色的,以明清之际言之,主要是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开始。他写的两本有关清初考证学派及桐城学派的书,都与地方文风的特色有关,因而也自然地涉及科举制度的实行及影响。⑨
从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中国地方历史的史料特质:它所包含的许多有关地方文教的资料及地方文化的多元特色,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地方志的修撰普及,这才谈得上真正研究地方文化和历史。明清教育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能大量使用地方文化的特色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多面性。同时,也因为资料丰富,可以讨论及描绘民间教育的真相或实情。
第二论:中国考试制度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考试制度为西方人所注意,大概开始于西洋教师到中国的16世纪末年。到了19世纪,英国为了正式将印度纳为大英帝国的一部份,开始在印度实施文官甄选的考试。[6] 这是近代英国或西方世界使用考试来录用文官的开始。文官考试制度在西方并没有变成十分重要的制度,不过至少它是模仿自中国的科举,这是不争之论。Simon Green说英国的“才能政治体制”是始于19世纪就是这个意思。[7]
不过中国的考试制度对世界的影响应当不限于此。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这里暂时不谈。中国考试制度在过去一千多年当中,也曾经对回教及基督教文明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常说的“东亚文明圈”,指的是中国文化力的儒家思想、科举教育、佛教信仰以及礼的社会秩序在东亚地区广被。中国对阿拉伯及西方的影响当然没有这么大,但是至少在采用考试的方法来认定职业资格上面,西方曾经受到中国的影响。按照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及顾理雅(H.G.Creel)的说法,中国至少从唐代已经开始举行医学考试,凡是要当医生的,都必须通过专业的考试。这个做法很可能由丝路传入回教国家,然后又传入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wo Sicilies)而普及于欧洲。[8] [9] 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因此不限于物质方面(火药、印刷术、罗盘、纸),更及于专业的资格考试制度。
事实上,顾理雅干脆主张说资格考试一早就由中国传入印度⑩,是世界上这种考试的始祖。他认为伟大的纳兰大学校(Nālandā)采用的入学考试办法,其构思就是来自中国(这所大学很值得我们注意,玄奘曾访问该学校)。这样的说法我想未免偏激,至少缺乏信服力,为一般学界所未取。
启蒙时代西方所受的中国的影响应当也很多,由于这里谈的是考试制度,因此不再讨论。(11)
资格考试的制度出自于科举重视笔试的传统。但它的产生又与科层体制(bureaucracy,或译为官僚体制)息息相关。中国人从很早就采行才能政治体制,因此资格的认定比较重要,也因此比别的文明早发明资格检定的考试。由此可见,中国重视笔试,虽然产生一些弊病,但是它毕竟有一定的长处。它和文官体制、才能政治均为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第三论:权威人格与考试文化
中国的考试制度重视笔试,不重视辩论,从宋代以后不再考“身、言、书、判”,所以就没有口试。口试和笔试的不同,是值得我人注意的。日人中山茂教授曾经写有专书比较中国和西方的考试制度,认为西方重视口试,而中国则注意文字的表意。这两样传统的确影响了中西对做学问,表达意见,以及辩论的习惯。(12) 进一步说,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也因此和重视辩论的西方有重大的不同。反映在中国的,就是“注释”传统维持得特别长久。另外,由于重视考试的“公正”,中国的考试终于发展了有名的“八股文”。理论上八股文对一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逻辑性是应该有助益的,问题是八股文只限在“四书”里出题目,可以出的题目有限,学生又要专心注意形式(八股文讲究对仗、字数有限,必须遵照其格式来写),记诵经文,甚至于背诵范文,而不是真的重视推理,也不允许发挥,所以产生许多的弊病,而这些弊病有很大部分和考试过分重视所谓的“公正”,利用“笔试”(宋代时考卷还得经过誊抄,以防作弊,不信任考官以至于此)有关。
总之,考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这一点我还是很坚持。最近有许多学者要替八股文翻案,说它是好的文体,但是我还是认为它不只窒碍人们的思想,实际上还帮忙促成中国人的威权人格。关于这一点,我只能简单地说:从明代以来,中国士人对自己成为圣人的良能、良知非常有信心,因此就渐渐发展出一种不随便妥协的性格。明太祖所垂训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以及什么“大诰”、“圣谕”之类的东西,承袭了朱熹的用语(如果不是他的用心),在民间流传,成了深入人心的价值。这些简约化了的处事原则,渐渐地导致中国人懒于思考社会结构及变化的多样性,也懒得对伦理行为的相对性等问题作深入的反省。中国人依赖的常常是诸如各种善书或《朱子治家格言》一类的教条。毫无疑问,相信权威的生命态度逐渐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权威性格。[10]
我个人认为“威权”和“权威”虽然用法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有相当的同构型,并无绝对的不同,真正的权威一定对真理有一种敬畏和信赖,而不随便以自我作为宇宙人生的中心。然而,明代以来,对自我的执持变成了一种自以为就是真理的忘形陶醉。明代以后,“自”这个字常常出现(13),我想主要是从“良知”学说发展出来,它带有一种对自己宗仰的价值、经验和知识的自信,其浮夸之处往往令人难以相信,而影响又十分广泛而且长久:现代人讲的“自我坎陷”,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其实也十分辩证地承续了这样的思想特质。这样的思维方式终于对可能的其他真理产生疏离,相当程度上不能严肃面对多元性经验的验证或历史事实。
科举制度的中心问题就是辅助了这样的权威人格的发展。考试制度文化的中心任务是透过大家都接受的标准来测量考生对真理的认识。然而,真理是什么?大部分的中国人会说:这个问题老早已经由圣人解答了。谁能熟记这套圣人之言,谁就是真理的代言人。这样的信仰不是权威人格是什么?
与人格的养成有关的其他一个问题是考生(举子)的心理状况。这是一个最近兴起的课题,值得我们注意。简单地说,由于科举影响了众多考生的生涯,因此参加考试的人往往患得患失,所谓考场百态,在通俗小说或笔记中记述非常多,有些还演变成戏曲作品。近年来,贾志扬(John W.Chaffee)和艾尔曼对这方面的材料曾作了初步的整理,让我们看见考试对学生精神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生活特质。我想一般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当然是《儒林外史》的范进。然而,历史上还有很多的其他例子让我们看出考试对中国人格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民间宗教(特如文昌君信仰或八字、星占等等)的发展,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
第四论:笔试传统的意义及重要性(14)
中国是最早使用才能统治思想的国家,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官吏选拔制度,以创造和谐的社会和国家。中国考试传统的形成及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无须赘述。但是中国考试制度非常强调所谓的“公正性”,以致发展出糊名、誊抄的办法,并因此只能使用笔试。这一个发展是中国教育史及科举史值得重视的课题。(15)
严格言之,科举考试制度到隋代才开始,这时笔试被正式采纳。在此之前选拔官吏的方法也许是依靠面试。尽管如此,口试从未被系统使用过。先于此的甄试或评审方法,其详情如何我们知之甚少。无论如何,中国一向就相信应该公开征求人才,从大范围的候选人中选拔优秀的来任官。但是这样的选举办法,一定很难达到公平,要发展出一套可被广泛接受的评价标准相当困难。因此中国终于在6世纪后期正式而普遍地采用了笔试。当然,这并不表示先此就完全没有笔试,主要是隋以后,笔试成了主流。简而言之,笔试的好处是候选人与考官互不见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见面口试或论辩还公正一些,保持一定程度的公平。这一种维护公正、公开过程的努力是一项中国的发明,况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任人唯贤传统的最重要特点。
考试的意义乃在于公正地评价考生的教育成绩或备考的程度。要公正评审,这对于所有文明来说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说考试的想法是中国人的发明,我想这是很难说得通的。(16) 但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笔试,这就和几乎是所有的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后者经常以口试为教育过程里的评审基础。(17) 这应该是反映了中国人关心考试的公平性吧!换句话说,对公平性的关注始终是中国选拔人才中特别重要的部分。中国人应该是第一个使用糊名笔试的国家,这一点大概没有问题。
总之,中国考试思想的中心措施是笔试,好维护其公正性。至于中国使用笔试的做法是否对西方有影响,这也值得深入讨论。但不管如何,我们应该注意记住中国对笔试的特别关注。(18)
笔试对于专业资格认证也相当有用。使用资格考试来授予专业学位或证书,在中国发展得相当早,而且对中国考试文化而言也非常重要。李约瑟(Joseph Needham)[8] 和顾理雅(H.G.Creel)[9] (P16-27)都认为中国关于资格考试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实践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医学方面。(19) 两人都认为:医生资格考试出现在唐早期,大约在7世纪期间,历史资料详细地阐述了为了医学官员认证而设的笔试。
因此,笔试在在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这应是不争之论。其作用至为明显。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确提升了中国人的演讲艺术,但是儒家教育传统则强调学生按规定的格式做文章的能力,而相对地不重视演讲的能力和作用。这种对比是有趣的:在佛教的鼎盛时期(大约从2世纪到12世纪),甚至在它衰弱之后,公开演讲是它布教的中心技术,表演的技巧至为细致。后来在中国的书院和大众教育中仍然赓续,但是,儒家讲究学习经典著作,就是到了宋代道学(或说宋明理学)兴起,这种演读经典的学习方法仍然持续不已。但是读经的活动,从背诵经文到阐述它们的意义,几乎都是围绕在阅读经文和演习它们的批注来进行。在私人考试和政府所举行的考试中,都没有看到任何明显的使用口试的情形,因此,唐代以后,中国人没有在任何的面试和辩论上面做出什么贡献。相对言之,中国人对文章的写作方法,倒是作了很多的分析,有各样的名称来描绘不同的写作方法或体例。(20) 事实上,公元10世纪以后,演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陆九渊显然善于演讲,后人记述甚详,但是仔细阅读有关他演讲的纪录,我们会发现它们的重点往往是放在仪式和气氛上面,而比较不强调其演讲的逻辑及思路,更少是关于其辩论的技巧或内容的质量分析。学生们所记得的大多是宋代道学家的教学方法,让我们觉得对话、小组论学,才是他们教学活动的中心。很少有人是以能滔滔雄辩,吸引众多百姓来听讲而成名的。也就是说,中国学者从宋代以后,已经不再重视举办大型的演讲,更不重视雄辩的技巧。他们一般以能亲自与数位学生做亲密的对话、小组的讨论作为他们教学的主要方法。
第五论:重视写作或记述的治学方法
日本学者中山茂比较中国、日本和西方的人文和科学传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认为重视“文献治学”的中国传统与起源于希腊自然哲学的“修辞学”的西方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21),中山茂的结论相当有趣而富有启发性。他的有关东西方不同学习风格的粗略分类不无正确之处。不过,他的侧重点不在于否认中国也有能力进行修辞学的研究,而在于认为中国人恰恰选择了一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它以重视记录性质的文献积累为特点。
谈到选择,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人的学问也欣赏修辞风格,并且事实上从佛教的讲座中得到了启发。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演说技巧被认为是教育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在4-5世纪时的中国南方会发展出“清谈”这样一门复杂的艺术。当时的人发展出一套处理谈话的详尽格式。清谈艺术和贵族的生活密切相连,因此在9世纪之后,随着贵族制度的消亡,它也跟着消失。另外,佛教对清谈风尚的影响如何,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佛教的确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发展了十分细腻的讲话技巧,但是中国的贵族教育始终缺乏对讨论或辩论的兴趣。事实上,中国人讲话,重点在于推敲文字的美或达意,重视如何调和不同的意见或思想。这就与佛教以劝人皈依的论辩或雄辩有细微的不同。寻求和谐统一才是中国风格的讲话或论辩。中国人毋宁说是一个不断要避免正面冲突的民族,他们尤其不喜欢在口头上产生冲撞,也因此口试及辩论就不是他们做学问的长处。
我上面提到陆九渊的讲演。一般言之,中国人对演讲的记忆往往不在其内容,而只在演讲的技术以及其过程(仪式)。但重要的是大家通常不注意演讲中讲者的逻辑思考,或者听众与讲者所作的辩论或甚至于讨论。换言之,重点是放在讲演所表达的方式上,把它看得比内容本身更为重要。讨论通常在讲演之后进行,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口头讨论的任何记录(语录通常记的是小群人的讨论,而不是演讲完了之后的发问)。讲演因此基本上是利用其技巧,而不计其内容,更对逻辑论辩没有助益。
最后,在中国文化活动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早期作用仅仅是承认知识在文献中是必须被找到的。文字的统一和用它来交流思想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我就不需再强调了。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提炼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把传统中国描述成一个有一致的教育实践的统一帝国是中国史学的强烈倾向。这种史学编撰上的假定当然不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最近西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喜欢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多面或多元性特色。这就产生了中西史学上的不一致性。这一点值得深思。
事实上,中国确有一个长远的传统,强调中国文化的大一统事实,并且努力要维持这样一个印象。换言之,传统的史学以一统为前提,这绝对是拜重视文字记录之赐。(22) 第二,文字和印刷的普遍使用,使中国人逐渐牺牲对讨论技巧的发展,努力强调统一不同思想的信念,专注于观点的一致性。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学习态度的形式化。我的意思是:社会鼓励以牺牲“典范”(paradigm)为代价,而努力提倡“正常科学”(normal science)。(23) 当然,我这里的说法或许过分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种显然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的做学问方法。中国人选择的是一致性,而不鼓励标榜与众不同的看法。郝若贝(Robert Hartwell)认为:传统中国人思考社会政策的问题时,重视的是资料的积累,拿过去的经验来和当前的问题相比拟。这导致了一种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方法论,强调的是模拟思想和方法。这种方法与西方那种重视概括的或抽象的法则(或定理)正好相抵触。[11] 问题是:中国人基本上对自己文化所采用的管理方式已经感到满意,自认为这个管理方法已经完善,又认为如何能达成道德上的完善生活才是惟一值得关心的课题。在这样的社会里,研究科学法则看起来真是余事。
综上所述,重视研究文献使得中国文化活动显现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风格。关于这一点也许可以进一步作更彻底的讨论,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比较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同异,这一特点是重要的。其基本原则是:中国人喜欢用积累的资料来进行模拟,制定政府或社会的政策,并以立一个和平的、甚至是一统的天下国家为目标。西方的分析方法就与中国的重点有所差别。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人所重视的文献记述,以研读经典和其他种种文字材料为治学的中心,累积文献记录来做模拟,以制定社会政策等等习惯,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考试事实上反映了中国人避免当面口头的冲突的性格特征。再由于长期实施科举考试,中国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也受到这种重视书写和累积材料,代代传承的特质的制约,满足于社会道德的一致和和谐的要求。于是“正常科学”成为治学的明显目标,“典范”的创作就收到了压抑。这就是重视文字书写的治学方法对考试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考试制度如何维系了这样的治学之道的地方。
以上对中国传统科举考试的历史发展及其特色作初步全盘性的讨论,用来尝试描绘中国考试制度的意义、贡献以及它在世界史上的角色。科举制度行之有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到今天仍然处处可见。中国传统科举废止到今年正好是一百周年,利用这个时刻来反省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谈论它所促成的单元化倾向的中国社会,它对中国人治学的偏好、思考模式、性格以及对理性科学的态度等等所造成的影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对科举的了解将与时俱进,根据各时代人的需要和关心而推陈出新。以上所陈述的不过是当前的一些比较显著的议题,挂一漏万,提供作为参考,并帮助思考而已。
注释:
①请参看我所编《中国教育史英文著作评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的“导论”,特别是第1-10页。
②最早也是因为对社会流动这个观念的兴趣,研发出像Wolfram Eberhard的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E.J.Brill,1977) 的作品,现在已经被忘记了。但是在70年代,两本比较重要的著作,现在还受到注意:一是David Johnson的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Boulder,CO:westview,1977) ,一是Patricia B.Ebrey的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 ui Famil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我写有书评讨论前书,登于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19,No.2( 1981) ,pp.249-252.
③著有Kinship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Athlone,1958)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London:Athlone,1966),及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等书。
④Denis Twitchett:" A Critique of Some 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登于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vol.10( 1965) 。按,这篇文章我曾经翻译为中文,登在1975年的《思与言》。
⑤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这本书我写有英文书评,登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09,No.3( 1989) ,pp.494-497。请参看我所编的《中国教育史英文著作评介》,第179-208页,蔡慧如所写的评介。
⑥请参看我的《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一书中译本(台北:联经,1992)的“中译本导论”,以及上面所引《中国教育史英文著作评介》的“导论”。
⑦请参看我的《什么是近世中国的“地方”?兼谈宋元之际“地方”观念的兴起》,发表于“近世中国教育与地方发展”会议,台北,2005年8月。
⑧宋代以后,“地方”这两个字才渐渐出现的比较多,有取代过去常用的“州郡”的情形,更带有与中央对应(不一定是对立)的政府统辖的地域的意思。《元史》中这样的用法清楚地出现,为《宋史》或《金史》所尚未见。请参看我的《什么是近世中国的“地方”?兼谈宋元之际“地方”观念的兴起》。
⑨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4) ; Classicism,Politics,and Kinship,the Ch' 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另外,下面两本书也与科举有关:Benjamin Elman & Alexander Woodside,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900(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我写有书评,登于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Hawai' i) ,vol.4( 1995) ,pp.93-99。 Benjamin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我也写有书评《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pp.237-267。又,我写的英文该书书评,也将登于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06) 。
⑩参看Herlee G.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第16-17页。又请参看S.Narain,Examinations in Ancient India( New Dehli:Arya Book Depot,1993) 。按,有关中国考试对西方的影响,请参考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397页。
(11)朱谦之所持的意见过分夸张,我有保留。
(12)参看下面第四论:“笔试传统的意义及重要性”。
(13)张履祥列举了一百多种以“自”为始的词(像“自任”、“自得”等),认为明代人很重视“自”,极有意思。明代人显然对“自”这个观念有相当的狂热。参看《阳园先生全集》,卷20。
(14)本(第四)论及第五论主要采自我的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a History( Leiden &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0) ,pp.658-668。
(15)顾理雅认为中国最早的笔试可追溯到汉文帝时代(公元前165年),这也应当是世界历史上有记录可循的最早的笔试(见上引其著作Origins of Statecraft,第17页)。
(16)参看Herlee G.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第16-17页。又请参看S.Narain,Examinations in Ancient India( New Dehli:Arya Book Depot,1993) 。
(17)“获得一个学位首先依靠候选人是否参加了某个指定的讲座;其次,他还得参加一些辩论(如:Sophomes、Inceptions、Determinations和Quadragesimals);第三,他需口头回答一些问题(例如在牛津逻辑学中的priorums和postiorums);第四,他或许还要能用口头发表演讲。例如:Clerums和其他的说教”,见R.J.Montgomery依据H.Rashdall的关于中世纪大学的权威研究所著的Examinations,An Account of Their Evolution as Administrative Devices in England(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5) ,第4页。这里所列的所有考试都属于口试。请并参见Gordon Leff,Paris and Oxford Universitie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Wiley & Sons,1968) ,第147-160页所列的各样的口试。先前引用的关于印度教育的书也指出:背诵课文和口试课文是基本的考试方法。
(18)请看下面第五论。
(19)既然笔试在西方相当晚才被引进,这期间有某些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可能的;此外,欧洲人对口头教育以及测验的依赖或强调,或许多少也反映出纸和书的相对缺少。
(20)在上面注释中提到了欧洲不同形式的口试和它们的不同名称。这与“八股文”文体的种种名称形成鲜明的对照。另外,谈到测试候选人口才时,在唐代和宋代,出身后的举子在任官之前,还要通过所谓的“身言书判”考试,其目的在确定通过文字的笔试的考生是不是谈吐及写字或撰写公文能像一个官吏,等等。但这样的测试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宋代以后也就取消。
(21)Shigeru Nakayama(中山茂),Academic and Scientific Traditions in China,Japan and the West(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 ,第3-16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山茂先生认为“修辞学”也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中,以名家与后期的墨家为典型。但他认为在汉武帝统治后,由于独尊儒家,这种传统就消失了。见该书第12页。
(22)木板印刷和活字印刷在复制文献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区别在欧洲并不存在,这也是纸张缺乏的结果;在中国这种区别是重要的,正因为在中国较欧洲更容易得到纸。中国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用木板印刷,显示纸的供给还算十分充裕。兹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在隋征服南朝的陈的前夕,即公元588年时,曾复印宣传材料达30万份之多。显然,这应该是用板刻的“印刷”。关于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间的关系,见Tsuen-husain Tsien(钱存训)," Why Paper and Printing Were Invented First in China and Later Used in Europe? " ,刊于李国豪等编的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上海:科学,1982)第459-470页。关于隋朝“复印”宣传单,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176:5496。值得注意的是《通鉴》的原文使用“写”,但我认为印刷是相当可能的,版刻复印的使用在这个时代已经很普遍了。若确实以人工抄制,那么,假定请了100个书记(按,晚到宋朝徽宗设立书学时,生员数也才只有210人),并假定每人每天誊写25份(征伐陈的诏令大约有152个字,大致需20分钟才写完),那么,从法令颁布之日到它的传播几乎要花四个月时间(120天),因此,如果隋朝不用版刻来复制的话,那就奇怪了。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十分重视文字材料的大量使用。
(23)中山茂认为至少在先秦时期中国并不缺少“典范”(paradigms),恰恰是政治力量(在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之后)影响了一种特殊的典范的选择,而这最终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负面的]影响。正如我所做的,中山茂给“典范”下了一个广义的定义。我绝对相信,由于外在的非科学和非理性的原因,中国人本身不太鼓励采用“典范”的形式。见中山茂的Academic and Scientific Traditions,第31-38页。有关“典范”,请看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第二版,增订版(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第1-51页。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礼记论文; 中国人论文; 公正论文; 八股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