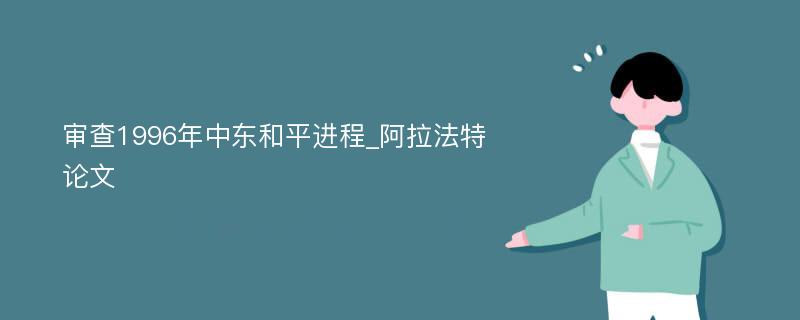
1996年中东和平进程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进程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总体局势而言,1996年的中东和平进程与前3前相比,荆棘载途、严重受挫,仍为举世瞩目的热点地区之一。
自治选举开好头炮
1996年年初的巴勒斯坦大选是当年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良好开端,标志着巴勒斯坦自治政权的正式诞生。
按照巴以既定协议,1月20日在加沙和西岸自治区的巴勒斯坦人首次举行选举,仍为以方控制的东耶路撒冷和希布伦市的巴勒斯坦居民也参加了大选。选举产生了由88人组成的具有立法权力的巴勒斯坦委员会,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以赢得88.1%选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主席。
这次大选巴勒斯坦选民登记占选民总数90%以上,巴勒斯坦20多个政党参加了竞选,巴解主流派“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委员会88个席位中获得50个席位。大选广泛反映了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对巴以和平进程的积极支持及对最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信心,确立了阿拉法特及以他为核心的巴解组织在自治区的合法领导地位。国际舆论盛赞大选的积极影响,埃及称这次选举是朝着建立巴勒斯坦国迈出的“历史性的步伐”;欧洲联盟称选举结果“恰恰是”对阿拉法特和平努力的“回报”;德国外长金克尔则把阿拉法特在选举中的胜利称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里程碑”;美国政府发言人指出这次选举是“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政权的一个重要机会和对建立地区和平的一个促进”。阿拉法特更是早在他投票之后就满怀信心地宣布:选举为新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一个巴勒斯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不过人们还是注意到,在自治选举成功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令人遗憾的阴影。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及总部设在叙利亚的巴人阵、巴民阵抵制了这次选举。虽然在大选前,阿拉法特曾与哈马斯等进行了谈判,试图争取后者参加大选,并一度有过和解迹象,但最后双方还是不欢而散。选举结束后,哈马斯拒绝承认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自治政府领导权,指责阿拉法特的胜利“虚假”、“脆弱”。
恐怖活动威胁和平
在对自治选举的不合作政策失效之后,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极端分子于2月25日至3月4日的短短9天里,接连在耶路撒冷、阿什凯隆和特拉维夫制造4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导致5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为以色列人。恐怖活动制造者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刺激对安全极为敏感的以色列公众,降低对和平进程持积极态度的工党政府的国内支持率,不时激化巴以矛盾,最终阻止中东和平进程。
客观地说,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恐怖手段是有影响的。本来,拉宾和平政策的继承人、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在国内的支持率,比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超出近20个百分点,佩雷斯在2月11日充满信心地宣布把原定10月29日的以色列大选提前到5月29日举行,而这时国内批评意见纷起,佩雷斯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骤然下降了15点,利库德集团国内声望迅速上升。而以方对自治区的经济封锁又使巴公众对自治政府产生不满,阿拉法特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在此关键时刻,为打击恐怖势力、支持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政府,挽救中东和平进程,3月13日国际反恐怖主义首脑会议在埃及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举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主持了会议,到会的除阿拉法特和佩雷斯之外,还有约旦、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及欧盟首脑、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等人。会议发表的公报呼吁国际社会联合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并计划成立一个相应的工作小组,在一个月内拿出反恐怖主义的具体方案。美国更是在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为佩雷斯政府输血打气的行动,包括向以派出反恐怖技术小组,提供先进探测仪器,以及1亿美元的援助允诺。但这次会议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成果,特别是作为和平进程另外两个当事国叙利亚、黎巴嫩领导人拒绝与会,使此次名为“和平缔造者”的国际会议黯然失色。
叙黎两国领导人认为,恐怖活动是果不是因,导致和平进程出现危机的症结在于以色列仍然占领着阿拉伯领土,不应把反抗占领的民族抵抗运动与真正的恐怖活动相提并论。况且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阿萨德自然不会与克林顿坐到一起讨论反恐怖问题。
在会议举行的同时,哈马斯发誓要继续在以色列进行自杀性爆炸,与首脑会议唱对台戏。因此人们认为这次会议雷声大、雨点小,除了为和平进程壮声势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一周之后的3月20日,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设立的“安全区”内又制造了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以军1死5伤。以军随即对黎南部真主党阵地进行报复性炮击,以黎关系趋向紧张。
黎以冲突循环报复
4月8日,黎巴嫩南部巴尔哈什特公路上发生一起地雷爆炸事件,导致1名黎巴嫩男童死亡,数名平民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认定此系以军所为,在随后两天向以北部小镇及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接连发射火箭,造成1名以军死亡,30多名以平民和军人受伤。4月11日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名为“愤怒的葡萄”反击行动。16天里,以军从空中、海上及陆地向真主党阵地及平民目标发射近4万枚火箭和炮弹,造成200名黎平民死亡,近千人受伤,13名真主党成员被打死,10多名联合国驻黎维和士兵受伤,50多万黎南部居民逃离家园。与此同时,真主党武装继续进行报复行动,对以北部发射650多枚火箭,造成以军死亡5人,伤20多人,几十名以平民受伤。
黎以军事冲突骤然升级,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法国、美国、俄等国相继出面斡旋,终于在4月26日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不向平民开火;双方各自保留自卫权;成立美、法、叙、黎、以组成的5方监督停火委员会。至此,这场自1982年以入侵黎南部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黎以冲突是老问题在新环境的重新爆发。自1982年以入侵黎南部之日起,真主党便将抗击以军占领作为其主要目标。1985年以色列以保障其北部安全为由,占领黎南部与以接壤的约850公里狭长地带作为“安全区”,至今驻有1000多名以军和以扶植的3000多名“南黎巴黎军”。
10多年来得到伊朗支持的黎真主党武装和以军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但具有鸽派形象的佩雷斯政府何以大动干戈,采取近年来少见的重击行动,其原因有三:一是针对因恐怖事件迭起而明显上升的国内不满情绪,显示工党政府确保以色列安全的决心和能力,以提高民众支持率,争取在大选中获胜;二是以军事手段迫使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或确保真主党不再对以袭击;三是通过打击真主党遏制伊朗和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影响,教训受伊朗、叙利亚支持的伊斯兰反以激进势力。
然而事后看来,佩雷斯虽然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摆出了为维护以色列而不惜一战的强硬姿态,赢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暂时缓解了国内不满情绪,但总体来说却是得不偿失。首先,以军行动受到阿拉伯各国的抨击,同时也触怒了以境内的阿拉伯人,他们表示在大选中不再支持佩雷斯;而以军炮击联合国维和部队及其守卫的难民营,导致包括维和人员在内的100多人受伤,更遭到国际社会多方谴责,和平形象受损。其次,以军的打击行动没有削弱真主党的有生力量,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仅死亡10多人,既没有迫使伊朗和叙利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也没有实现让黎民众、政府迁怒真主党的目标,反而使真主党成为黎民众和政府认同的合法抵抗组织,加强了其力量和影响,还被保留了具有袭击性质的“自卫权”。
内氏上台阿方紧张
5月29日全球瞩目的以色列第14届大选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这是以色列建国48年来首次由公民直接选举总理。选举前,佩雷斯作为“和平巨人”拉宾的接替者,拥有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支持的优势,为外界普遍看好。然后5月31日下午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内塔尼亚胡以50.4%对49.5%的选票击败佩雷斯,当选以新总理。
分析家们认为,佩雷斯之所以出乎意料地败给内塔尼亚胡,除个人的经历和形象对重视安全的以选民有影响外,主要是由于下述原因。第一,2月底3月初的炸弹恐怖事件强烈震撼了安全至上的以民众,他们认为佩雷斯推进的和平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而内塔尼亚胡高举“安全”大旗,他的“有安全保障的和平”的竞选口号显然更加动听。第二,在4月份的黎以冲突中,佩雷斯失去了至为关键的以境内阿拉伯人的选票。第三,1993年以来中东和平进程发展迅速。以国内右翼势力上升,特别是佩雷斯私下允诺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及从西岸全部撤军,并准备放弃戈兰高地,损害了犹太定居者的利益,致使西岸和戈兰高地的犹太人几乎把选票全部投向对阿以和谈持强硬政策的内塔尼亚胡。
作为鹰派色彩浓厚的利库德集团首脑,内塔尼亚胡始终在阿以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抨击奥斯陆协议和塔巴协议,坚持“三不政策”(不允许巴勒斯坦立国,不归还戈兰高地,不谈判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内氏当选后于6月提交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除具体表述上有所变化外,“三不政策”的实质依然如故,他重申要扩大对阿和平,但更强调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利益。作为中东和平的直接当事者,阿拉伯一方对内氏上台显示出强烈的担忧和紧张。巴解、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各方首脑紧急磋商,更令人注目的是6月22~23日,21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开罗举行自海湾危机以来的首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以恢复阿拉伯团结、协作,敦促以新政府继续和平进程,遵守阿以间已签协议,强调和平仍是阿拉伯国家的战略选择。
叙以和谈停滞不前
震惊世界的拉宾遇刺事件后,叙以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到1996年1月31日为止,叙以在华盛顿外围的马里兰州庄园举行了三轮谈判,虽然和谈是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谈判焦点仍是戈兰高地问题,特别是关于以方撤军范围的争执:叙坚持以应遵照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将军队全部撤至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边界线;而以只同意撤至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国际边界线,力图继续占领具有丰富水源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部分戈兰高地。2~3月的4起恐怖爆炸案促使以宣布中止僵持中的叙以和谈。沙姆沙伊赫会议后,佩雷斯表示以仍准备同叙复谈,并允诺大选获胜后从戈兰高地全面撤军。4月25日以工党特别会议决定,从其竞选纲领中删去“戈兰高地主权归以色列”的条款,作为推进叙以关系的一个积极步骤。
孰料佩雷斯在大选中败北,和谈形势逆转。内塔尼亚胡上台后,在坚持不归还戈兰高地的强硬立场的同时,又作出希望同叙复谈的姿态。随后迫于各方压力的内氏采取了避重就轻的谈判方针。6月19日叙、以驻美大使在美国国务院会晤,在美国中东和谈特别协调员罗斯的主持下,讨论如何监督4月份达成的黎以停火协议。7月29日内氏在会见日本记者时公开提出“先黎巴嫩、后叙利亚”的方针。8月2日在美访问的内氏又正式提出“黎巴嫩问题优先”的方案,其要点是:叙利亚要使黎真主党停止活动;允许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确保以北部犹太人定居点不受袭击,黎政府军收编南黎巴嫩军;以根据与黎达成的安全安排从黎南部撤军。8月5日内氏在访问约旦时又表示“准备同叙利亚就包括戈兰高地在内的任何问题举行会谈”。
内氏抛出上述方案,意在“一箭三雕”:1、以色列无意长期占领黎南部“安全区”,以军撤出黎巴嫩有利于解决以黎问题,为保障以北部安全铺平道路;2、离间叙黎特殊关系,先解决相对容易的黎巴嫩问题再回头对付叙利亚,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3、掌握政治主动权,把“球”踢给黎巴嫩,触发黎内部矛盾。
然而内氏的如意算盘未能动摇叙黎既定立场。叙黎欢迎以无条件撤军,但不接受“黎问题优先”方案,认为这是以回避戈兰高地问题,离间叙黎同盟的一个“圈套”。叙黎两国总统磋商后,再次重申在同以和谈问题上,双方继续坚持协调同步的立场,决不同以单独媾和。此后内氏又一再提出“无先决条件”恢复以叙和谈,但坚持“以和平换和平”的原则。而叙方则针锋相对地主张叙以和谈的基础是“以土地换和平”,否则绝不复谈。因此叙以和谈至今没有起色。
巴以关系出现倒退
1996年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不仅表现在叙以和谈停滞不前,更表现在和平进程的主要方面——巴以关系出现倒退倾向。
1996年前半年,巴以和谈总体情况尚属良好。巴自治区大选成功举行,即使受到2~3月间的恐怖爆炸案后,巴以双方仍能在3月28日达成以从希布伦撤军的协议。4月24日巴解全国委员会决定取消“国民宪章”中“消灭以色列”的条款作为回报,翌日以工党会议也同意取消竞选纲领中“反对巴勒斯坦人建立独立国家”的条文。5月5日巴从在埃及塔巴开始举行关于巴最终地位的首次谈判。然而内塔尼亚胡上台以来,明确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拒绝讨论耶路撒冷问题。虽在8月14日巴以在耶路撒冷恢复高层会谈,但以方在谈判中不仅拒绝执行前已同巴方达成的从希布伦撤军协议,而且提出废除前政府关于冻结定居点建设的决定,加快扩建犹太定居点的步伐,另外以方还强行关闭巴驻东耶路撒冷的办事处。
9月23日以政府下令重开东耶路撒冷的地下通道,对本已紧张的巴以关系“火上浇油”。巴方认为通道经过阿克萨清真寺地下,是对伊斯兰教的严重亵渎。从9月25日起的数日里,在耶路撒冷和拉马拉等西岸一些城市,示威游行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军警发生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双方军警直接交火,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这是自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巴以间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9月26日阿拉法特宣布推迟巴以和谈。随后,为挽救“面临夭折危险”的和平进程,在克林顿总统的直接撮合和主持下,10月1~2日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举行“紧急首脑会晤”。根据双方协商,10月6日巴以双方总算恢复和谈。到10月28日,罗斯已在双方之间穿梭调解3周多,谈判却依然未果,双方的分歧集中在确定执行希布伦撤军协议的机制问题上,主要是以方坚持以军有权进入巴辖区追捕恐怖分子;强调驻扎希市巴警只能配备手枪,并反对巴以联合巡逻以辖区,以及禁止巴车辆进入希市烈士街等。
12月巴以再次谈判,23日以色列同意在追捕巴人和开放烈士街问题上作出让步,到1996年最后一天巴以双方谈判代表甚至已经草拟了希布伦协议,却未正式达成。问题主要出在巴以双方谈判立场的本质差异:巴方愿意在大的原则问题不变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问题稍作修改,以便原同工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得到以现政府的认可并执行;以方则坚持对原有协议作一些有利于己但巴方难以接受的修改。
法俄参与调解
法俄两国以独立姿态参与调解阿以和谈,力图打破美国独揽中东事务的局面,这是1996年中东和平进程中一个令人注目的重要动向。
早在3月13日沙姆沙伊赫会议上,法、俄领导人就与阿拉伯国家一起强调推进和平进程必须与反对恐怖主义相联系,反对实行双重标准,与美国、以色列片面强调反恐怖主义的立场相左。4月中旬黎以冲突爆发后,法国外长德沙雷特率先赴中东斡旋,提出了有别于美国的停火建议,得到了黎叙方面的欢迎,从而跻身于五方监督停火委员会。虽然俄国外长普里马科夫也参与了调停,但成效不如法国。
因内塔尼亚胡上台后坚持“三不”的强硬政策,而临近大选的美国政府又难以对以施压,使中东和谈全面受阻。在此情况下,10月19~25日希拉克总统在年内第三次前往中东,访问叙、以、巴、约、黎、埃,重申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恢复阿以和谈,要求执行阿以已签协议,更明确提出欧盟应作为中东和平主持者之一直接参与和谈。希拉克刚走,10月28日起俄外长普里马斯科夫又开始为期6天的中东之行,访问的国家与希拉克相同。所不同的是,他不像希拉克那样大张声势,而是与中东各方领导人进行交流磋商,探讨切实可行的和谈方案。不过他明确表示,各方必须履行已经规定的义务,他还把中东和谈比作一支正在演奏的乐队,俄罗斯“要以自己的力量充实这支乐队”。
中东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历来是大国利益的聚焦点,法俄两国在历史上也与中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绝不满意美国一手垄断和平进程,一直在努力寻求机会,积极介入阿以和谈,恢复各自在中东的影响,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久感不满,自然对法俄介入普遍欢迎。相反以色列却对两国介入态度冷淡,充满戒心,美国更是公开表示“中东问题仍是美国一家在处理”,竭力排斥法俄。不过,一些国际舆论指出,法俄的介入有助于平衡中东天平,对中东问题全面、公正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
新年钟声刚刚敲过,希布伦又响起刺耳的枪声,一名以色列军官为阻挠巴以和谈开枪击伤6名巴勒斯坦人。现在,虽然巴以就希布伦撤军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并开始付诸实施,但人们有理由认为,1997年的中东和平进程仍将是崎岖而曲折的。
标签:阿拉法特论文; 真主党论文; 佩雷斯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叙利亚总统论文; 以色列总理论文; 美国选举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叙利亚政府军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