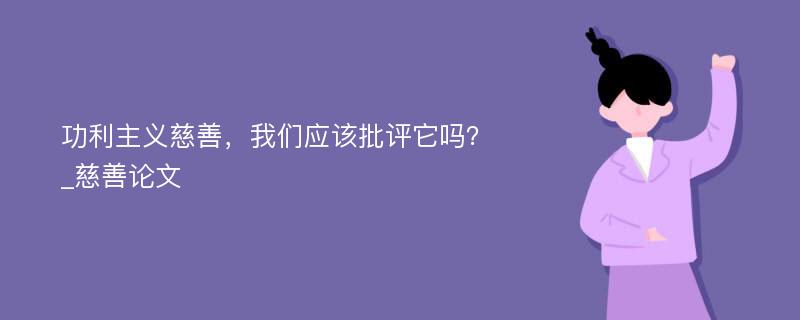
功利慈善,该不该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利论文,该不该论文,慈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功利慈善不是真正的慈善
每逢岁末年初,各种各样的慈善榜层出不穷,许多过去一年在慈善工作方面表现抢眼的企业都榜上有名。但与此同时,围绕这些企业慈善活动的争论至今仍旧不绝于耳:企业的慈善事业是否仅仅是社会责任?企业家慈善事业的核心伦理是什么?企业是否可以运作“慈善营销”?媒体应如何报道企业捐款……实际上,这一系列争论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的:如何认识商业性慈善?换而言之,企业及其企业家慈善行为是否可以功利化、商业化?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哲学史中一个经典的争论——“义利之辨”,简单来说,即主观动机和客观实际哪个在先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还是先回到慈善本身,看看到底何为“慈善”。
据《汉语大辞典》,“慈善”被表述为慈爱、善良、仁慈、富有同情心。一般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概念与儒家的仁义学说、佛家的因果报应论和慈悲观念密不可分。而在英文语境中,慈善包含三层含义:(1)对全人类的爱;(2)增加人类福利的努力或倾向,比如通过慈爱援助或捐助等;(3)为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活动或机构。
而当前国内学术界认为,慈善是一种善良意愿的社会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施予者”通过某种途径,自愿以捐赠款物、志愿服务等形式,提供社会救助和社会援助来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并不问物质回报。在当下中国,慈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基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间的关爱,更是从行政福利行为中走出来,成为社会倡导的民间行为。
在上述三种语境中,至少共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援助是基于慈爱、仁慈,这体现为慈善的无偿性,二是援助方与被援助方没有利益关系,这体现为慈善的非功利性。也就是说,无论在哪种语境中也无法回避慈善行为的无偿性和非功利性。这两层含义一同回答了“义利之辨”的问题——在慈善事业中,义在利先。
在考察了“慈善”一词后,再让我们来看看企业的商业性慈善行为。虽然,企业在商业性慈善行为中,实际上有救济他人、回报社会的行为和善良意愿,但是其目的并非是单纯地为善而善、为义而义,而是以善为媒介、以义为手段,谋求超过捐赠价值的受益。退一步而言,即使这种受益可能是非物质的,但企业往往制造噱头,借助媒体造势,获取无形的商业价值。
概而言之,企业的商业性慈善行为,在客观上有慈善之事实,但在慈善的主观动机上却是功利的。所以我们说,企业慈善的商业化行为,以“义”为名,以“利”为实。而“慈善”概念是无偿性的、非功利性的,是要求义在利先的,所以企业的“慈善营销”策略,动机上追求慈善行为背后的商业回报,必然违背了“慈善”本身的实际意涵。
马克斯·韦伯在其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释了宗教教义(伦理)及其教义所导引出的世俗行为后果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导引出的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在韦伯看来,人们追求财富的目的不在于奢侈的生活,而是怀有一颗严肃的现世关怀心。他的话无疑是值得企业家深思和借鉴的,也只有我们所有人怀有一颗真正慈善的心,才能避免陷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危险。
正是基于此,我们的媒体在报道企业慈善行为之际,也当洞察其慈善动机之实。媒体肩有引领民间舆论之责,所以用一种更为审慎的眼光审视企业慈善行为,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别让慈善也泡沫
临到岁末,各种慈善活动纷纷登场。
有慈善的地方,就有借慈善之名的欺诈。李国华、“中国母亲”胡曼莉、明星义演收取出场费、某些企业诺而不捐……诸多丑闻不胜枚举,这些慈善弊案的是非对错都很分明,该法办的法办,该谴责的谴责。但是,慈善活动中的某些灰色地带,却让人一言难尽。
《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曾透露说,“诺而少捐”是企业慈善活动的潜规则,平常年份善款的到账率也只有7%。企业在捐款现场举牌子认捐的数额往往高于实际捐款的数额,注意,不是不捐,而是“少捐”,这还是得到各方默许的一种捐款方式。
这种慈善潜规则,是迫于现实环境的无奈妥协。慈善事业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据中国慈善事业管理部门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中,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还不够高。俗话说得好,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慈善机构不得不卑躬屈膝、笑脸迎人,所以甭管捐多捐少,甭管是真大方还是商业秀,只要有些许真金白银入账到位,慈善机构就该口诵佛号了。
本来人人都有自由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是留给子孙还是惠及社会,都是个人的自主选择。不强迫、不摊派,是慈善活动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对于个人借慈善谋私利、企业“诺而少捐”之类的功利慈善秀,却不宜助长,善款难筹的现实难题,也不是原谅、容忍此类行为存在的理由。
道理很简单,这是一个涉及到诚实诚信的基本道德问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因为多多少少拿了点钱出来,就可以掩盖弄虚作假的事实。以泡沫慈善为代表的功利性慈善表演,往小处说是企业本身的诚信问题,往大处说是削弱了政府相关机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而且这种上下其手的通同造假,更是以小恩小惠模糊、扰乱了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
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在现代社会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地震中出名的范跑跑,居然还有一些人认为他“真实”、“讲了实话”,罔顾他身为老师的责任、成年人守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诚信对企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那些诺而不捐的企业已经破产消失了,诺而少捐的企业呢?媒体曝光、公众监督的后果恐怕在短时期内也是难以消化的吧。
自私之心,其实每个人多少都有,我们不妨承认企业对慈善的投入本身也是一种投资。企业慈善与企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并不相悖,重视社会效益,归根结底也是优化企业的生存环境。但若是本末倒置,借慈善活动作商业秀,口惠而实不至,长期潜规则,长期吹泡泡,不仅是对慈善事业的伤害,是对公众情感的欺骗,也是对企业自身的伤害。
应该说,单纯的道德义愤和谴责,解决不了善款难筹的现实问题。如何提高企业主动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杜绝部分企业的泡沫慈善行为,除了完善慈善法制、打造专业的慈善机构、加强舆论监督之外,也许还应该广泛树立“企业公民”的理念,强调企业的慈善责任。
什么是“企业公民”?简单说,企业必须以社会公民的身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由于企业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一方面,企业家拿出善款做善事,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了,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按照基本的公平原则,企业慈善,也是社会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慈善是善意,也是能力,有能力的企业不能回避自己的社会责任。
作家毛姆曾经说:“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宣称有其自身目标的价值,德行就是它自身的回报。”施恩不望报,原是理想的道德境界。只不过,在这个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世界里,陈义过高,难免拒人千里,倒不如实事求是,退而求其次,把道德问题换成利益问题,把慈善问题变成关乎企业良性发展的社会责任问题。
“慈善洁癖”可以休矣
喧嚷的2008年带给国人的是一份不可替代的记忆。在这份记忆中,“灾难”将“慈善”推上了时代的前台。但热闹的慈善活动之后,是舆论对中国目前慈善生态的全面反思。社会思想家呼吁更纯洁的慈善事业,那些被认为具有“功利性慈善”嫌疑的,顿时从聚光灯下的明星,陷入到一片喊打声的窘境当中。
所谓“功利性慈善”就是那些与以“无私施予”为理念的传统慈善行为不相符合的慈善行为。这些慈善行为是“有私”的:对政府机构而言,可能是想以慈善谋取业绩;对企业单位而言,可能是想以慈善拓展自身品牌或扩大经济利益;对个人而言,则可能是想以慈善谋求发展资本……总之,舆论的逻辑非常干脆:既然“功利性慈善”的利益诉求肮脏可憎,又怎能让其大摇大摆地走上媒体呢?
与舆论创造性地使用“功利性慈善”一样,笔者则愿意把上述对“功利性慈善”的非议称作“慈善洁癖”。检视一下,此种“洁癖”的核心无非两端:其一,既然慈善是天然神圣的,有所图的慈善就不配称之为慈善,只能是“伪善”;其二,如果允许慈善行为存有私利,那么“正义,多少丑恶假汝而行”的悲剧就将不可避免。首先要声明的是,笔者绝非要为伪善张目,也绝不是礼赞丑恶的愚徒。只是觉得如果任由“慈善洁癖”大行其道,恐怕其恶果也将不亚于伪善的横行。
“慈善洁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现代社会的存在与繁荣是以承认个人的利己心为哲学基础的。允许人们追求自身的幸福,从而推动全社会实现整体幸福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人类在整个二十世纪所取得的共识。人为地以“有私”和“无私”为标准,苛责慈善行为的动机其实就是要武断地否认“利己心”在慈善领域的存在,矫造出一个所谓的“无菌舱”。可这有什么意义呢?
据统计,目前中国有城市低保人口2200多万、农村低保人口2620万,每年有近8000万灾民需要救济,同时还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实施救助。慈善的本意在于救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通过整合社会的力量使他们免于饥寒。如果一个政府、一个企业或者某个个人能够拿出自己的力量实现上面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介意他们顺便从中得到社会形象改善、舆论评价提高、盈利能力上升等益处呢?如果说仅仅因为执著于一个所谓完全“纯净”的慈善领域而罔顾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急迫的痛楚,这样的真善与伪善又有什么区别呢?
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能够理解慈善洁癖的拥趸们所谓的拳拳之心,我们也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中为他们规定的“有私”与“无私”划出一条清晰可见的界线。慈善领域需要承认并面对人的“私心”的勇气。因为慈善的核心乃是爱人,而这份爱只能来自于对人之为人的真正尊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慈善行为本身可以没有底线。在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里,这条区分慈善与伪善、高尚与卑劣的红线就是法律。通过民意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慈善事业法》为首的一套完备的法制系统将成为慈善领域的“看门人”与“裁判官”。政府官员可以组织慈善,但是却不能滥用公款、以权谋私;企业可以施行善举,但是却不能借此洗钱、触犯刑律;个人可以寻求心灵宽慰,但是却不会因此而得以逃避所应承担的责任。只有理性公平的法治精神才最适合成为区分真伪慈善的“照妖镜”,也只有借用理性公平的法治精神,我们才可能在善的纯度与广度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其实就像最近热映的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与梅兰芳这两个角色:从塑造出一个倾倒众生的艺术大师这个意义上说,邱的“有私”与梅的“无私”之间并非是相形见绌、高下立判的关系,相反,两者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慈善洁癖”可以休矣。
不必深究慈善动机
记得刚毕业的时候,教授送给我这么一句话:“人是矛盾的,成为心理医生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把人当人看’。”
听着很虚?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是,自从我成为上门女婿的那一天起就顿悟了。那天,我满怀热忱地打算给一位陌生老大妈留下个好印象,原因是我已经追求她女儿10个月了。而这位老大妈对我的印象却很糟糕,不仅因为我其貌不扬,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当时毕业没多久,基本上一文不名,而北京的房价实在太贵了。
面对她老人家并不友善的态度,我立刻就陷入了矛盾之中:我的逻辑告诉我,我所心仪的女孩是她的独生女儿,所以我大可以在肚子里开骂,但务必继续保持着肢体行为和面部肌肉纤维的彬彬有礼!而我的情绪告诉我:嘿!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我的逻辑和情绪在同一时间给了我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我必须在两个答案之间谋求妥协,于是在向老大妈委曲求全的一瞬间,我就理解了:人,是矛盾的。而情绪化动机和逻辑化动机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在心理学领域被称之为“动机分裂”。
没听说过?不要紧,因为这个枯燥的学术名词在历史上拥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莎翁让哈姆雷特高喊“To be or not to be”,比如王朔自己跳出来感叹“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就连平凡如你我也躲不开它,别跟我说你对每一位上司的灿烂笑容都出自纯粹的忠诚与敬重——我是心理医生,我知道。
所以,当一个人做到了大多数人能做到的,我们就应该认可;当一个人做到了大多数人做不到的,我们就应该感激。如果你认为一个人不是圣徒就应该受谴责,那么不妨先回家照照镜子。
把人当人看,其实不难理解。
现在就有那么一种人,手里攥着钞票陷入了“动机分裂”。他们一方面想用自己的钞票为自己做点儿什么,这有问题吗?他们另一方面又想为需要钞票的人做点儿什么,这难道不值得肯定?既然没人能把他们的脑袋拆开,那么纠缠于这两个动机在他们脑袋里的主次,又有什么意义?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待到喧嚣散尽以后,只要钞票最终落在需要它的人兜里,咱就当回票友喊声好儿,吃亏吗?
可能还真是很吃亏,至少是感觉不太爽。
比如,我知道有很多人的慈善是出自纯粹的善意,这样的慈善无疑是绝对崇高的。他们出于自身动机的高尚,很难认可功利性慈善的动机中自私的那一部分。指责功利性慈善,也就成了纯粹慈善人士的一种自我肯定。
首先我承认,纯粹的慈善应该大力肯定。但话说回来,咱们不能因为自己纯粹的崇高,就否定所有并不那么崇高的。就算功利性慈善肯定不如纯粹的慈善招人喜欢,但有慈善就比没有强。作秀的确讨厌,但功利性的慈善不作秀还功利个什么劲儿?它的秀越精彩,这个社会上的“慈善”标题就越多,“慈善”也就越流行,越有曝光率。
再比如,社会上也有那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他们自己不慈善,却会忙不迭跳出来指着功利性慈善大喊:“看哪!他们多功利!”言下之意很直白:“你就算慈善了,也比我强不了多少。”
铁公鸡停止对功利性慈善的诋毁,是知耻;高尚的慈善人士容忍功利性慈善的客观存在,是有量。因为真正该指责的并不是功利性慈善,而是打着慈善旗号的铁公鸡,他们才是欺世盗名之徒。
标签:慈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