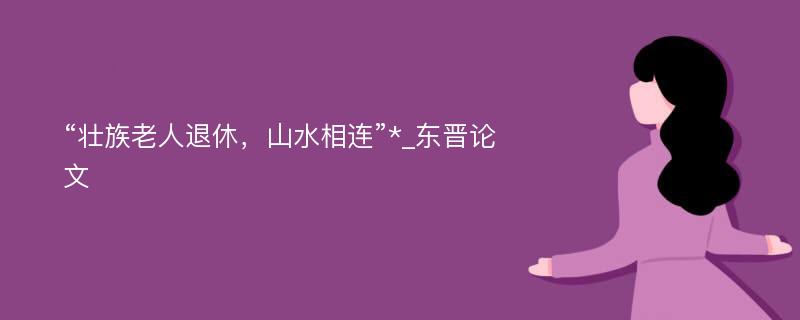
试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山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探究谢灵运对我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时,人们很自然地便会想起《文心雕龙·明诗》中刘勰所说的这样一段话: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其中尤以“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二句给人印象最深。
据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和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等的推算,刘勰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宋明帝泰始元年至梁武帝普通二年之间,即为公元465年—521年。这样一来,上面《文心雕龙·明诗》的论述,就还有同龄人钟嵘(466-518)的《诗品》和年长者沈约(441-513)的《宋书》可与之呼应。
关于刘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钟嵘的《诗品》是这样论述的: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其中,钟对晋时玄言诗风的评议,与《文心雕龙》中的刘论大抵相同,但也有差异。
刘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而钟却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
二人话中的“江左”即“江表”,指的是西晋亡后的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晋元帝),在长江东岸的建康建都,建立起的东晋;那自然是公元311年十六国的汉国军队攻占了晋都洛阳之后又先后俘获了晋怀帝及其嗣君晋愍帝之后的事。而钟所称的“永嘉”,却是晋怀帝的年号,时间相当于公元307-312年。
由此看来,二人论述的略不相同者:①时代。钟嵘认为崇尚玄言的诗文是从西晋晚期的永嘉年代兴起的;到了东晋,只是永嘉时的“微波尚传”罢了。而刘勰这里却只是说了东晋以后“溺乎玄风”的现象。然而如据《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可知在刘勰的看法中,东晋并非“玄风”的起始,《时序》里“中朝贵玄,江左称盛”的观点,正与钟嵘在话中所标明的时代相同。可见二人在此一点上实际并无分歧。②程度。钟嵘使用的是“稍尚”和“微波”,口气较和缓。刘勰却直截了当用了“溺”字。
由于刘钟二人在当时都十分尊崇沈约(据《南史》等载,刘书成后因未为时流所重,故刘欲取定于沈约;而钟亦曾欲求誉于沈约),这里不妨来看看作为长者的沈约的意见。在《宋书·谢灵运》传末史臣的史论中,沈约是这样说的: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元大变太元之气;爱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在此段引文中,“有晋中兴”自当是指西晋亡后东晋的建立;“建武”是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义熙”是东晋安帝的年号,从建武元年到义熙14年,共11帝21年号,相当于公元317年到418年,如暂不计入东晋最后的恭帝(年号元熙)被废前在位的仅仅两年(因其时尚未称宋的刘裕的实权早已超过了恭帝),则这百年的时间几乎就是东晋的全部岁月。
在沈约看来,重新建立起东晋后,文学中的“玄风”便特别昌盛起来,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撰写诗文,其核心总是离不开曾为柱下史的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和包括《逍遥游》等七篇在内的《庄子》内篇。所以他说,在几乎整个东晋的百年时间里,“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只有到了刘宋时代,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谢灵运和颜延年,二人一起才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并成为后世的典范。从上面引用的沈约原文中,我们不难看出:①沈约对此一历史时期文学变迁脉络的认识,是与刘钟二人完全一致的;②在刘钟二人略有差异的地方,即东晋时有关“玄风”泛滥的程度,沈的观点是与刘完全相同的。
尽管史籍曾载有沈对刘十分赏识的逸事(如《梁书》等就有载,沈取刘《文心雕龙》读而“大重之”,常将该书“陈诸几案”,并称刘“深得文理”),但在此论中沈刘的完全一致,似还应认为是二人对历史分析的殊途同归。因为人称博通群书的沈约,在南齐受命修纂《宋书》时,正为太子家令又兼著作郎,而其《宋书》的编纂又是有刘宋人何承天、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以及徐爰等原修的诸多《国史》作为依据的。因此应该认为,沈刘二人关于此一时期文学变迁的论断还是颇能经得起推敲的。
二
为了探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论的刘宋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深层内含,本文认为,有必要将此段文字放到刘勰《文心雕龙》全书中去加以理解。
《文心雕龙》一书相当全面地表达了作者所持的有关文学批评的主张,这主张中自然也包含了刘勰的文学史观。熟读《文心雕龙》的学者,大多可能注意到了,即在全书的50篇阐述中,刘勰有不少地方都论及到文学的历史变迁,除了《明诗》等篇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时序》及《变通》等篇。在《时序》中,刘对“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所作的具体论述里,曾有这样的话语:
晋……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在刘勰看来,文学历史变迁的原因,是因为它“染乎世情”。是因为两晋之间的那些年代出现了对玄风崇尚的世情,到了东晋此风愈烈,“因谈馀气,流为文体”,才出现了“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因此世事越是艰难到了极点,逃世的人便越爱使用平淡无奇并又大而无当的语言,因而在诗中赋中文学作品中才把《老子》、《庄子》的思想作为自己吟咏和阐释的核心。
可喜的是,《时序》中在上一段话后,紧接着便有一段关于刘宋时代文学发展的论述,它说: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风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根据当时社会的知名度,刘勰在这里列举出了其时一些有名的文士家族和个人,其中有王弘的王氏家族、袁淑的袁氏家族,颜延之的前后几代、谢灵运的前后几代,以及有名的何逊、范云、张邵、沈约诸人。他们的风采之所以能“霞蔚而飙起”,在刘勰看来,还在于65年刘宋天下里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以及宋明帝等掌权人物对文学的爱好乃至其天性和修弄。如以历史记载来映证,宋武帝刘裕等人或许也的确有些佳举和贡献;然如从下文刘勰对南齐统治者的吹捧来看,此处有关对宋武等的恭惟似也不必过于认真。如暂时忽略去时代和身份打在刘勰身上的烙印,考察刘勰对其本无所求的前代文学家的态度,谢灵运的确是刘勰推重的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
文学自身的规律,原本就是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变动,只有通于古又变于今,文学才会流传久远,才会有勃勃的生机。这是刘勰在《通变》的《赞》中用“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16个字表达的该篇中心思想。如联系到这一赞辞,那么刘勰在《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等句中,所要论述的晋宋时代文学的历史变迁,不仅为了阐明“时序”“世情”所包含的时代潮流和世事人情对文学变化的决定性影响,也是为了阐明文学本身的变化的确为其自身的发展增添了新鲜活力。刘宋以来诗文过于注重形式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今古研究者已经有了相当一致的臧否意见;原本厚古薄今的刘勰也在其《文心雕龙》的《明诗》及其他诸篇里也表达过对此现象的相当不满。然而从刘勰对晋宋文学变迁的几段论述里却也不难判定,谢灵运等在山水文学创作中的建树,还是为刘勰所充分肯定的。
三
基于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论述,后世对谢灵运的各种褒辞更是相继增生。大概因为“自天地以降”“夸饰恒存”的缘故,人们对谢公的赞辞也越来越玄,以致后来在一些论者的论著里,似乎谢灵运之前的文人都不曾注目过山水,于是“最早”、“第一”、“创始”、“开拓”之类的最高等级的帽子,便一顶顶全戴到了谢公头上。感情浓烈过度,于事实就不免产生视觉误差,以致当今某些中国山水文学作品的选本或有关山水文学发展的论文在谢公之前都留下了一片空白。
尽管这些做法几乎都自称是依据了刘勰的论述,然而却与刘勰本人的思路绝不相符。
其实刘勰在“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前,他还说过“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因”什么,“革”什么,其所指是不难弄清楚的。如果真把后人编织的诸多“开山鼻祖”的帽子都强加在谢灵运头上,谢灵运的成就反倒成了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了。而实际上,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已经论及了景物的描写,不仅论及“山林皋壤,乃文思之奥府,……屈平之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且还述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看来,既然至少早在西汉时的司马相如,就已“模山范水”了,那么可以肯定,刘勰并不认为谢灵运是我国“模山范水”的第一人。
四
不巧的是,在《管锥编》中,今人钱钟书先生又对“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提出了挑战,并明确表示了他的“山水方滋,当在汉季”的看法。
钱钟书先生的“山水方滋,当在汉季”一语,出自《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第66则。钱先生的该则评议,自《全后汉文》卷八九起论,在论及东汉仲长统《乐志论》时,联系到了谢灵运的《山居赋》,又回溯到《全后汉文》卷六七荀爽的《贻李膺书》。由此,钱先生说:“荀爽《贻李膺书》:‘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居阳城’;参之仲长欲卜居山涯水畔,颇征山水方滋,当在汉季。”而钱先生的这则评论的后面,又明白地引述了《文心雕龙·明诗》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因而可以确认,钱先生的这话确实是因刘勰而发的。
钱先生不仅在论及仲长统时联系到了谢灵运,在论及谢灵运时也联系到了仲长统。《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68则,在评议《全宋文》卷三一时,钱先生在论及谢灵运的《山居赋》,又联系到了仲长统,并特意注明“参观《全后汉文》卷论仲长统《昌言》”。因而不妨这样考虑,钱先生“山水方滋,当在汉季”的论断,也许并非与对谢灵运的评价无关。
五
如果依刘勰所说,“长卿之徒”早已“模山范水”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发展史》作者刘大杰先生在他的这一著述中便描写了一轮西汉时的可以大体概括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过程:
汉代初期的几十年中,是黄老思想的全盛时期。窦太后是黄老思想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者。“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后共四十多年,她有权有势,凡是反对黄老的都受到排斥。推崇儒术的辕固生,几乎被猪咬死;魏其失宠;田蚡免职;赵绾、王臧也逼得自杀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淮南子》的宣扬道术,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界的面貌。在这样的政治空气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描写富贵繁华、铺张扬厉的赋,是不容滋长的。难怪司马相如在景帝门下,郁郁不得志,后来只好托病辞官,到梁国去做游客。……到了武帝当权,政治、学术都起了变化。儒家定于一尊,征圣、宗经、原道的观念,成为文学理论的准则(请注意,这里的“征圣”、“宗经”、“原道”,正是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开头三篇的篇名——引者),大家都以此指导文学,批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汉赋反带着讽喻的美名,古诗的遗意,顺利地滋长起来。
历史绝不会一成不变地反复重演,但也不可否认其脉络却常常是这样那样地吻合。刘宋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自不会是西汉时这一文学变迁的搬演,但其中的某些相似却不可忽视,甚而可以为我们对其规律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启迪。
六
值得重视的是,在《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的第9则里,钱钟书先生还有一段关于《诗经》《楚辞》状物写景技法的评议。在该则中,钱先生引用了《涉江》、《湘夫人》和《悲回风》中几段景色描写的文字后,评论说“皆开后世诗文写景法门,先秦绝无仅有。”又说“窃谓《三百篇》有‘物色’而无景色,涉笔所及,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即侔色揣称,亦无以过。”还说“《楚辞》始解以数物合布局面,类画家所谓结构、位置者,更上一关,由状物进而写景。”
作为这一论述的映证,钱先生还先后引评了四段他人有关《楚辞》的议论:
《文心雕龙·辨骚》称其“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物色》又云:“然屈平所以能兼风骚之情,抑亦江山之助乎?”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游罗浮山记》云:“《三百篇》言山水,古简无馀词,至屈左徒而后瑰怪之观、远淡之境、幽奥朗润之趣,知遇于心目之间。”皆识曲听真人语也。
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四《捕鱼图序》称王维“妙于诗,故画意有馀”,因引《湘夫人》此数句曰:“常忆楚人云云,引物连类,谓便若湖湘在目前”,正谓其堪作山水画本也。(注:钱钟书先生这里的“此数句”系指前钱所引《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白薠兮骋望”。)
吴子良《林下偶谈》亦谓“文字有江湖之思,起于《楚辞》”,即举“嫋嫋兮”二句,称“摹想无穷之趣,如在目前”。
如从钱先生上面这些论述来看,在有关“山水”原始等的相关问题上,钱先生的观点、清人恽敬的观点、宋人晁补之的观点、宋人吴子良的观点,都与《文心雕龙》刘勰的观点有相当一致的地方。
七
读了前面一至六节的论述,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怎么刘勰文章会自相矛盾?怎么钱先生的两段论述前后也不尽相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问题便出现在发问人对“滋”字的理解上。
有的论者之所以把谢灵运之前中国文学中的山水(或山水文学)看作空白一片,并将种种开山鼻祖之类的话加之谢公,或者原因中也有对“滋”字的误会。
实际上,“滋”字的含意是“益也”,是“增益”、“增多”,而非“初生”。因而“方滋”就绝不是“才出现”,而是“才增多起来”、“才兴旺起来”、“才得以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如将“滋”当作“滋润”、“润泽”讲,或还会更有诗意,则“山水方滋”便可讲作“山才更青,水才更绿”,“文学中的山和水(或山水文学)也才具有了更多的文学意味”。
如果更进一步跳出许慎《说文》“从水兹声”的形声字框架,赋予“滋”字会意字的身份(用以释“滋”的“益”字也是会意字),那么“滋”的含意便是“水沾湿了蓐草”(“兹”就是“蓐”;而“蓐”义虽可引伸为“草席”,但其本义却是“陈草复生”——这一点,从“兹”的象形字也可明显地看出;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下卷所录的甲骨文“滋”,写作表示的便是作为蓐草的“兹”被“水”所浸湿)。由此,刘勰“山水方滋”一语的语意简直就太形象太生动了。
如若真按上面的字义去理解(无论你选取哪一种解释),则刘勰《辨骚》说“山川无极”,《物色》说“长卿之徒”“模山范水”,《明诗》说(刘宋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都不存在矛盾了。自然我们对今人刘大杰、钱钟书的论述也就能够更好地领会。
谢灵运对扭转东晋玄言诗风贡献卓著。对我国山水诗派的成长,他的地位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但如澄清了刘勰“山水方滋”的真实含意,除去那种原来本不该有的夸饰,并真从谢公创作实践去研究,还谢公以本来面目(因本文篇幅关系,故这里暂不论及),这不仅有助于谢灵运研究的深入,对我国山水文学史和旅游文学史的研究亦将开拓出新的境地。
作者附记:在我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曾相当广泛地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谢灵运是我国山水文学的开山鼻祖,其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便是刘勰所说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种片面的观点,似早就应该得到纠正。近世,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又提出了旅游文学的概说,不幸的是,有的学者又无视旅游文学与山水文学的差异,更将谢氏作为了旅游文学的鼻祖,乃至写进了旅游文学的教材。尽管近几年已有人将山水诗的发端勉强上移至三国曹操的《观沧海》,将游记的发端免强上移至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然而笔者认为,这仍与中国旅游文学的发展历史不尽相符。笔者此文,就是一篇辨误的文章,希望能由此消除人们旧有的对刘勰原意的误解(本文前已论及,对于山水文学,谢灵运也不是鼻祖,而且其原始也当在今人所乐道的曹马等人之前),以期与同志者共勉,促进崭新的中国旅游文学史和较为成熟的中国旅游文学教材的诞生,这才是笔者撰写此文的首要目的。
1992年4月
* 本文系一篇旧稿,原为笔者拟参加1992年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的论文。尽管笔者作为此届年会的筹委本不应请假,但因此会会期正好与需笔者主持的另一个旅游科学学术研讨会冲突,故只好向研究会道歉,论文因此也就搁置而未发表。现在看来,文中不少地方都有再作加工的必要,但为存其旧,故未改。——作者
本稿收到日期:1995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