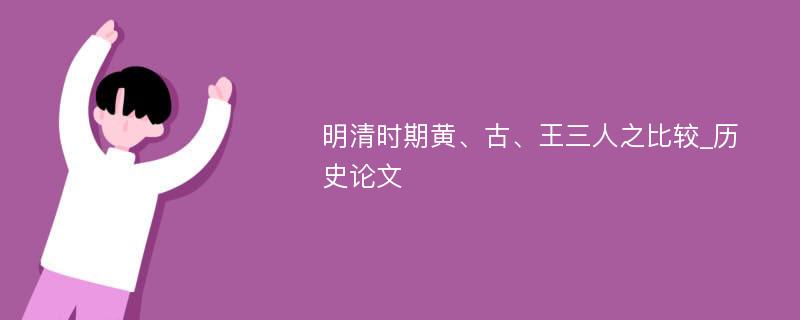
明清之际黄、顾、王三先生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王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丙子立夏后,鄙人将届八十。心里想,有很多事,该到收尾子的时候了。但收尾子这事也不容易做。因为生理软弱了,心理也软弱了,思惟也上不去,收尾子总是要形成一点高峰的,而高峰谈何容易?!即以黄、顾、王来说吧,鄙人自25岁经营此课题,迤逦五十余年,独于顾一家稍有一得之愚,而黄、王之事,虽积有笔记,终同弃置。今于病中立志,欲将三家进行一些比较,庶几可将平生一些零星识见,编织于此文之中,算作是收了一个尾子吧。
三先生生活的时代,是相同的。诸凡明末政治之腐败,大农民军之起义,满兵之入关与清朝的建立,以及康熙朝之渐臻于盛世,等等,此三先生之所共同经历者。三先生之出生,相距不出十年。黄属狗,顾属牛,王属羊,黄长于顾者3岁,而顾长于王者6岁。在9年之中,即有三文化巨人临世,非中华民族孕育之深、之厚,何得有此?!
三先生不仅生活时代相同,出身亦复类似,即所谓“出自缙绅”。所谓缙绅,前些年的用辞是官僚地主阶级,也就是指那些家里靠土地收租、成员们在京里或省里做官的人家。但在这些大体类似的家庭间,仍各有其差异。三家之中,以昆山顾家最规范,而规范也就意味着保守。亭林的学风最规范,恐与此有关。亭林的继承祖(所谓“蠡源公”)和继承母王氏(谥贞孝)给与亭林的教育都是最规范、最正统的。亭林一生笃信朱子之学,学问讲求经世济用,怕都与此有关。梨洲的家庭就不是那么规范了。父亲是京城里的御史、与阉党斗争而牺牲的东林党烈士,这个声势是很大的;在家乡的影响也大,组织民兵与清兵对抗,而部分山民竟数次纵火焚其寨,这说明浙东的形势很复杂,不是一个能文能武的权势家族是驾驭不住这个形势的。再观梨州二弟(宗炎,即所谓鹧鸪先生)被清兵捉去就要处决了,居然能劫法场把人抢救回来,在乡里中没有一点组织力是办不成这件事的。这个家庭自然比较开放些,与市民以及三教九流有着复杂的关系。梨洲宗阳明学派,但不是激进派,而是稳健派,(详后)。兄弟5人,各有所信仰,三弟宗会就笃信佛。兄弟间关系也比较宽松。船山的出身,又是另一个样子。这是在洪武、永乐间因军功从江苏高邮迁到湖南衡阳来的。弃武就文,才不过四、五代。是较顾家黄家低一个档次的缙绅。他们父子热心科举,习帖括之学,死抠经书,所以王闿运讥笑船山有“村塾师”、“浅陋”等语。船山既不信程朱,亦不信陆、王,从独立思考中,从张横渠哲学和《周易》中受到启发,在唯物观和辩证法方面,独立有所建树,这是王闿运所不可能懂得的。船山在三先生中独他是举人(亭林、梨洲均未中举),且是桂王朝廷上的行人司行人。梨洲在鲁王小朝廷上也当过什么左都御史,但一转眼就过去了。只亭林以布衣终身,仅在福王小朝廷上挂过一个兵部职方司主事(科长)的空名。
前些年,一提到某个历史人物的社会影响,总特别注重阶级出身。不错,阶级是按经济利益划分社会阵营的,但它是一个大框框,大框框里还应填入若干细部内容,如地域、家族,甚至遗传。我到老来,对遗传很感重要,后悔当年上大学没修生理学、心理学和遗传学。现在报纸上不是大谈基因吗?我想,基因在历史人物的成长中,一定起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件事,弄不好很容易落入唯心主义。
三先生还有一点相同处,即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都曾积极、勇敢地参加了抗清的武装斗争。
北明亡时,梨洲年35,亭林32,船山才26岁,均在少壮之时。亭林参加了苏州人民抗清起义和昆山人民抗清起义。苏州那次,是一场盲动主义的表演,虽然太湖人民全涌来了,但领导不利,很快失败。昆山的一次比较成功,坚持了二十几天,虽然后来也失败了,但终究显示了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进行战斗的力量。昆山失败后,亭林就只身一人进行秘密抗清活动,坚持了一辈子,从诗文中看不出任何消极、退缩的迹象,一直到死。梨洲参加的规模要大得多,在乡土上组织起一支军队叫“世忠营”,拥护鲁王,鲁王一度退到福建,他们就在四明山里打游击,等鲁王又回到舟山岛,把小朝廷成立起来。鲁王手下自然有文官武将,于是派系斗争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武将,互不服气,互相扯肘。恰在此时,清廷下令登记、拘捕抗清人员家属,梨洲借口老母会受迫害,辞朝还山。这前后,怕有四个年头的光景,梨洲接受了这一番锻炼。船山于明亡后,没有即刻投入抗清。在这四五年间,桂王及其随从们播迁于广东、广西的肇庆、苍梧、桂林之间,慢慢稳定下来。船山和朋友们在家乡衡山发动一次抗清小起义,失败了,这才投到桂王的小朝廷来。小朝廷上的文官也在闹宗派,有金堡一派和王化澄一派,船山拥金反王,几乎遭受陷害,就回湖南了。这段经历,也迤逦三、四年之久。船山在这几年里扩大了眼界,结识了一些重要人物,如瞿式耜、张同敞、方以智等,接受了他们的一些影响。其中特别是方以智,他是居于大西南的遗民领袖的巨擘,既通晓某些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精深的修养,更深通禅理。他可能给船山带来很大的影响,《姜斋诗》中有不少哭他的诗。
船山所在的湖南,当时是反复很大的一个地区。李定国大军在这里有过重要的战绩,后来吴三桂也跑来要在衡阳做皇帝。船山对此,头脑是清醒的。对李定国,他秘密地替他出谋献策;对吴三桂,他则深闭固拒,东藏西躲。从这中间,船山也得到了长足的锻炼。
大凡一个知识分子(仕子),一辈子蹲在书房里,斤斤考订或者校正几个字形和字音,久而久之,也会有一定的成绩出来,这是一种类型。另一各类型就像黄、顾、王那样,适应时代要求,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不管他们在参加过程中会有反复和曲折,有热情、积极的情况,也会有失意、动摇的情况,这些都是可以想像的;但不论如何,他们总是参加了,真刀真枪地干了一阵,北京话叫“动了真个的”,那么,当局面已经改变,他们再在书桌旁坐下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其中就包含着对历史和现实的联想,其理解就深刻了。黄、顾、王三先生之所以被后世尊重,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该来看一看三位先生,怎样料理他们一生的著述问题了。著述是要流传后世的东西,对于学者说,应该是最最紧要的事情。当然,人一辈子写的东西可能非常多,即所谓“著作浩繁”,像三位先生的《遗书》都是卷帙庞大的,但不可能全是重点著作,重点著作仅占一小部分,其余多是零星著作,还有诗词杂文等等。所以如何布署就是一桩大事。这件事不仅三先生有,我们后世人也有,所以看看他们先贤如何布署,对后学也是一个启发。
在三先生中“部勒紧严”的,要算亭林先生了。当年在昆山闹产业纠纷的邻人叶方恒曾说亭林“城府深密”。是的,他是一个平生从不轻率行事、举措全有心算的人。他在过江以前,在南京把《音学五书》基本上弄完了,这时他定居在南京蒋山之下。在苏州纳的妾韩氏替他生了个儿子叫贻谷,不幸活到4岁上害痘疮死了。他因而与韩氏离异,在南京另纳戴氏照顾生活。在这暂时的安定里,他赶着把《五书》写出来。《五书》虽然是重头著作,学术意义也很强,因为它给以后开阔了路子;但写成书并不像其他著作那么难,就那么一大批证明材料,系一系,整齐整齐,写出结论,就完了。并不拖泥带水。修订增补,那是以后慢慢来的事情。《日知录》就不同了,这是绵亘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些订正、补苴、论议、发扬,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放长线”。所以亭林在《日知录》的一些“条条”上,都有反复的复稿,有的比“定本中”的长,有的比“定本”中的短,足见是写来写去,写了多次的。关于书的问世,他的安排也比《五书》不一样。《五书》是整方整块,不再需要大动了,所以他很快就安排在淮安付刻,安排王略替他经理,张绍替他校字。《日知录》则不然,他在生前只刻过一个8卷本;32卷本是他弟子潘耒在福建刻成的。这个8卷本前些年我在青岛王献唐先生的三儿子王国华同志处见过,刻印很精致,足见王、张二友是尽了力气的。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那是亭林自24岁屡试不第、下闱讲诵以来积攒了一辈子的一批地理、历史材料。梁启超说过它是“刍狗”,意思是明天就要烧掉的东西。亭林生前为什么不自己烧掉?因为孩子怎么样,只有娘知道的清楚,亭林深知,第一,这批东西很丛杂,要整理好很不容易,自己已经没有这份力量了;但第二,丢了吧,又不行。因为其中蕴藏着若干“兵略”,亭林是自幼读兵书的人,晚年亲历山川,又印证了不少自己的若干看法,这和“反清复明”的政治也紧密挂着钩。所以这批材料他始终不舍得丢弃,经后人整理保留了下来。
梨洲在这一方面,就跟亭林大不一样。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著述方面。他要使用精力的主要部分去对待政治和社会。可是,难道亭林就不需要使用精力去应付政治和社会了吗?需要的。但亭林所从事的政治大部分是隐蔽的;他在北方25年,主要是按一条“遗民”的“单线”活动,不相干的人他不接触,也就是所谓“避人避世”。梨洲则不然,他一直在进行公开的社会活动。举两项例证。其一,明亡前夕,他正三十四、五岁,在南京反马(士英)、阮(大铖)的活动,就进行得十分蓬勃。其二,到晚年,70至80岁间,仍与钱牧斋,以及顾亭林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有着频繁的来往,而“三徐”又是康熙皇帝很宠幸的大臣,这时朝廷上正在开办“博学宏词”科,又在纂修《明史》,康熙也屡屡问起黄宗羲,“三徐”也屡屡在康熙面前赞誉黄,所以梨洲在晚年也还要应付这些事。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题辞里写道,“如箕子之见访,其庶几焉。”这就是说,康熙就是周武王,黄就是箕子,有什么咨询的一定竭诚奉献。这就引起某些看法。当时有人认为梨洲快要丧失民族立场,快要抛弃爱国主义了。可是我们今天处在“民族大家庭”的时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梨洲的祖国观念在当时就比亭林更宽容些,不管谁来统治,整个社会总是要运转的吧,那么我们提些建议,让社会的弊端减少些,有利因素增多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梨洲在自己学术著述问题上,主要抓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有明一代的文章(既意味着文学,也意味着文献)。他平生不声不响地积攒这方面的资料,到晚年66岁时,才把这些资料编成定本,扩编本和缩编本,它们的不同名字各叫《明文案》、《明文海》和《明文授》。此外,据说还有《明史案》。明朝的文章,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比较起来实在不算出色的,因为被朱元璋、朱棣父子的高度专制主义镇压的思想界,已经十分呆滞了。但梨洲还是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这其中有政治因素,当时人们爱明、思明、痛明的心情是普遍的。其二,是对有明一代的思想进行总结,特别是阳明学派,梨洲以宗仰者和乡后学的身份,更有这份责任。他写出了《明儒学案》这么一部精心结构、细致阐说、深刻分析的大著。汤斌曾说,梨洲的学问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这个特点,在《明儒学案》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梨洲把各地域的“王门”,都做了娓娓的叙述和精严的论断。但这并不是说,这部著作一点不足之处也没有。
他对泰州学派,进行了“另册”处理。把嵊县人周汝登也列入了泰州学派,就表露出对这些“异端”派有歧视的心理。这不奇怪。他是刘宗周(蕺山)的弟子,他师徒二人坚决反对拿佛学思想与“圣人”之道绞在一起谈问题;他们对阳明的心学遗教,只主张“静存”,不主张“动发”,静而不动,存而不发,王学中的一些积极东西就被阉割了。以上说的是观点;至于制作,那没有什么说的, 梨洲为学术通史的创作树立了千古少见的典范。
还有《明夷待访录》。这部书部头虽然小些,但光芒却高,因为其中对中央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进行了大胆的讨伐,主张一部分权应由地方掌握。这个思想不仅梨洲有,顾亭林在《日知录》里,王船山在《黄书》、《噩梦》里,也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足见封建专制主义蒙罩了社会一两千年,现在已经到了该“启蒙”的时候了。
现在来说船山。他对待他的著述,似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一生经常在逃避迫害。他两度参与桂王政权,自然而然清朝的官吏要迫害他;他不顺从吴三桂,吴三桂手下人也要迫害他,他东藏西躲,甚至跑到瑶区混迹为瑶民。试看,他躲藏的地方都另起一个名号,如续梦庵、西庄源、败叶庐、观生居等等。只有当他暂停了东藏西躲的生涯,相对安定下来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写作的高峰期。像这样的高峰期,在他一生中大体有两度,一度是他37—38岁时,那时他从桂王那里刚刚辞退下来,他写了《黄书》、《周易外传》和《老子衍》等。另一度是到了晚年,外界的压力相对减小了,从61岁到67岁,这是第二个高峰期,他写成了《噩梦》、《俟解》、《思问录》、《周易内传》、《庄子通》这些著作。这距离他的告别人世只剩下六、七年光景了。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情况,即同一段思想,船山往往分前后两次写书,如《周易外传》和《内侍》相距30年;《噩梦》和《黄书》相距25年;《老子衍》和《庄子解》相距24年。这说明他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给他的著述安排,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至于诗文,作者们自己也都很珍惜,一再编订。这些内容,作为作者们生活记录,也有很高的价值。不过,在三先生中间,对梨洲《南雷》诗文、船山《姜斋》诗文持批评甚至指斥态度的,每每有人(如船山爱骂市民甚至农民为“禽兽”等等,就招来诽议);而对《亭林》诗文则斥者素所未见。盖亭林于诗文有他独立见解,如他不喜欢七言,说七言多两个字,耍花样的机会就多;又不喜欢律诗,说一搞对仗,耍花样的机会又多。他的诗文,朴朴实实,服搞耕辈表但。
底下,我们该看看三位先生怎样带徒弟,也就是如何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了。
在这一方面,以船山最差,以梨洲最盛,亭林居中间状态。船山是一“穷儒”,经常奔波于乱山之中,又不象亭林那样有很厚的一个社会保护层,所以愿意来就学的人就不多了,只从文献里看到一位叫唐端笏的,曾在船山晚年一度前来随学。所以船山晚年慨叹自己的学问是“绝学”。亭林平生挚友不少,徒弟不多,只一个潘耒,字次耕,吴江人。亭林和他的关系是这样的:在苏州抗清起义时期,有一位少年英烈,也是亭林的好友,叫潘柽章。潘牺牲后,按律例其遗孀须送宁古塔服刑,而潘耒负责护送。走到淮安,按亭林的介绍,在王略家停留,王略看出潘耒是个有成就的小伙子,就收他做女婿。后来潘耒往来南北,就认亭林为老师了。除了传授学问之外,有很多私房事亭林也安排他去做,有很多梯已话亭林也跟他说。潘耒也不辜负老师的爱重,老师殁后13年,在福建把32卷本《日知录》刻印出来,还在书前写了一篇很有水平的《序》。朝廷纂修《明史》他也参加了,他主稿《食货志》,为了把《志》写好,他记了60大本资料,可惜这份宝贵文献后世人没有见到过。
带徒弟事业最有成绩的,要算梨洲了。他自五十几岁以后,就开始讲学、收徒。他的讲学,也不像当代的学校那样,按课程、按钟点讲课;倒有点像讲座,在馀姚讲讲,在宁波讲讲,在四明山的寺庙里讲讲。讲的题目也是随他而定,有时讲孟子,有时讲汉易的象数,有时讲他老师刘宗周的王学遗教,等等。在他带的徒弟中,以宁波万氏八兄弟最著名。宁波万泰(履安)有子八人,最小者斯同字季野、第六者斯大字充宗,最有识见,最有毅力,最有成就,成为梨洲学派后继者中的巨擘。季野和侄子万言(贞一)应征到北京参修《明史》,梨洲赠诗中有句云,“季野观书决海堤”,又有句云,“一代贤奸托布衣”,前一句说的是季野读书之博,后一句是明朝三百年历史就靠这么一位不署衔、不受俸的布衣前去评说了。其对心爱弟子爱惜之殷、学问上信托之重,是极为感动人的。
万斯大、斯同兄弟不仅在史学上是大家,即使在经学上也有极可宝贵的见解。他们主张《经》的《传》《注》基本不可信,必须排除它们的谬误;怎样排除呢?要以《经》解《传》;而且还不能单靠一《经》,必须把诸《经》联起来,才能更清楚地看出《传》、《注》的谬误。这个见解太深刻了,它是从大关节目上去为《中国古代史》资料的鉴定工作,打造坚实的基础;较比乾嘉考据派从一字一句一音一转上去抠搜问题,要恢恢乎大多了。
通过万季野这么一个学术使者,以梨洲为首的浙东学派,以颜习斋(元)为首的河北学派,以魏僖(叔子)为首的江西学派,在北京发生了交流,出现了融合。其中包括万斯同(季野)、刘献廷(继庄)、王源(崑绳)、李塨(恕谷)以及方苞。到这些人的时候,黄、顾、王三先生所代表的学术年代,已经过去了。而乾嘉考据派早期代表人物钱大昕(竹汀)要等到万斯同谢世后26年才出生到人世中来。
1996年5月30日,鄙人80初度前十二天,写毕于兰州大学22楼209室
标签:历史论文; 明清论文; 日知录论文; 明史论文; 黄书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宋史论文; 元史论文;
